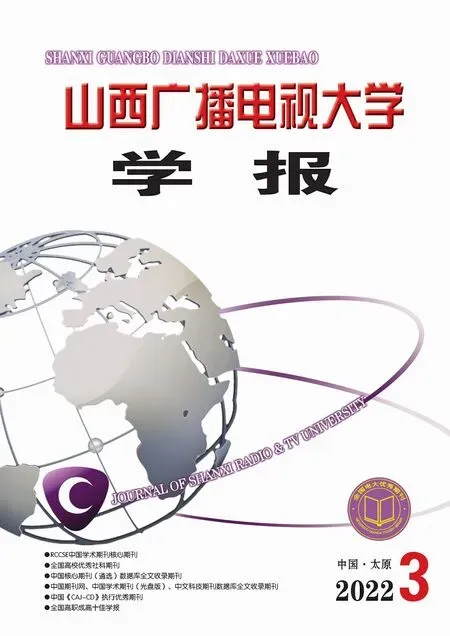淺析法顯對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作用
□李志芳
(長治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山西 長治 046000)
法顯(約337—約422)本姓龔,平陽武陽①人,3歲出家,20歲受大戒。慨律藏殘缺,誓志尋求,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和同學從長安出發,度流沙、越蔥嶺,遠赴天竺求法。前后凡15年,游歷30余國,攜回經書數十種,譯經10多卷。此外,法顯還親自撰寫了歷游天竺經過的《佛國記》(亦名《法顯傳》《佛游天竺記》等)。《佛國記》為中國古代以親身經歷介紹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情況的第一部旅行記,它保存了有關西域諸國的許多可貴的古代史地資料。
一、西行開拓和中印海陸交通的鑿空
在我國佛教史上法顯和唐代高僧玄奘并稱,正如唐朝高僧義凈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所述:“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法顯不僅是西行求法的開拓者,同時也是打通中印海陸交通的第一人。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他第一次返國后,“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各國國情,……確立了打通河西道路經營西域并進而開拓通往‘西極’的國際通道以揚漢王朝威德于四海的決心。”[1]而實際上,中印之間的絲綢通道“很可能在戰國時期已初步開通”[1],一直到漢武帝時期已經形成交通,但這是轉口貿易帶來的,而非直接貫通。基于此,發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即是公元2世紀伴隨印度、中亞一帶的商人、使者和移民,先傳到今新疆地區,后傳入中國內地的。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裴松之注引三國魏魚豢《魏略》記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一般認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而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向大月氏派遣使者求法,抄寫《四十二章經》而歸,則推進了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但是其間經籍的傳譯多由中亞及印度的僧侶來完成,受語言和文化的限制,傳來的經籍往往篇章不完備或傳譯失真。此后,漢地開始有西行求法者。三國時魏人朱士行被認為是內地往西域最早的求法者。朱士行,潁川(今河南禹縣)人,出家以后,研鉆《般若》。以《般若》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常慨嘆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乃誓志西行尋求。魏甘露五年(260)從雍州(今陜西西安西北)出發至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取得梵本《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六十萬余言。
朱士行之后,西行求法運動興起。士行之后法顯之前,西行求法的僧侶見于史載的主要有:竺法護,西晉人,祖籍月氏,隨師外國沙門竺高座游西域,帶回經卷百多部;康法朗,東晉初僧人,遠足流沙,游歷諸國;于法蘭,東晉初僧人,遠適西域,終達交趾(今越南河內境),中道而逝;竺佛念,前后秦僧人,祖居涼州,“少好游方,備貫風俗”;慧常、進行、慧辯,均為東晉人,太元四年(379)如天竺,過涼州(今甘肅武威)而史不傳其返;慧睿,東晉、南北朝僧人,《高僧傳》稱其“音譯詁訓,殊方異義,無不畢曉”;支法領、法凈,東晉僧人,其游方至于闐得經以歸。但上述西游僧侶真正達到天竺的,只有慧睿。慧睿(355—439),冀州(今河北高邑)人,少年出家,游方學經,至南天竺界,但求法未果,歸廬山不久,又北上師從生于龜茲(今新疆庫車)的天竺僧人鳩摩羅什受學,最后到南朝劉宋的京師,住烏衣寺講經[2]。所以在5世紀初之前真正到達天竺并有所成就的僅法顯一人。
法顯在其回國后所著的《佛國記》一書中聲明了他西行的真實原因,并對這一經歷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3]法顯一行經甘肅張掖,西出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穿過新疆的漫漫戈壁,翻越蔥嶺(今喀喇昆侖山)進入弗樓沙國(今巴基斯坦境內),然后南下跨越小雪山(今塞費德科山脈),約在公元402年進入北天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經過了3年的艱苦行程。由于佛教自古重記誦口傳,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因此,法顯繼續遠涉中天竺,希望能在佛教中心的恒河流域有所收獲。約在公元404年至摩竭提(摩揭陀)國之巴連弗邑(今印度之巴特那)。此邑原為阿育王之都城,為法顯西行所經之最富盛之城邑。此城有信奉大乘佛教的“婆羅門子名羅沃私婆迷”,其國王以師視之。此邑建有摩訶衍僧伽藍(大乘寺),而居于此寺的高僧文殊師利為摩竭提國內大德沙門及各大乘比丘所宗仰,時各地之高僧及學問人皆詣此寺,尋求義理。但是不久,法顯又由此向西前往佛釋得道之伽耶城(今印度比哈爾邦之伽雅城),而此城所呈現出的荒蕪景象顯然非法顯這次行程之目的地。綜合所經之途的實際情形,大概在公元405年法顯再次返回巴連弗邑。從法顯這次去而復返的情況來看,他此行之目的自然是要尋求源自釋教發源地的佛僧戒律寫本,但所經之途,終不得遂愿,不但北天竺無本可寫,中天竺“亦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于文字。”“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3]巴連弗邑遂成為他這次行程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在此間,他寫錄的戒律有:《摩訶僧祇眾律》和《薩婆多眾律》;另外寫錄的佛典有:《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般泥洹經》及《摩訶僧祇阿毗曇》。
大約在公元408年,法顯南下瞻波大國(今印度之巴格爾普爾),在此寫經畫像居留2年,后乘商船泛海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在師子國居留的兩年(約410—411)時間內,經過實地考察研究,法顯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何含》《雜藏》。公元411年搭商船泛海東歸(有關海歸路線目前學界爭議較大),于義熙八年(412年)歸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嶗山),旋南造京師,次年到達建康(今江蘇南京)。
法顯打通中印海陸交通特別是西行求法的成功,其示范、榜樣和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張騫之后法顯之前,雖然存在通過西域、中亞、西亞直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及通過中國南海經東南亞、南亞、波斯灣和紅海到達歐洲、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但史籍不載有海陸并行者。就求法僧人而言,從公元260年朱士行開創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始,到公元399年法顯西行的139年間,遠足異邦的中土僧人雖世代不息,非但史籍記錄無一海陸并行者,即使陸路求法成功者也乏善可陳。從法顯西行求法成功并打通中印海陸通道,至8世紀佛教民族化過程基本完成,西行僧侶比肩接踵,代有西行求法成功之僧人。其中有陸去海還者,如(南朝)宋永初元年(420)法勇(曇無竭)嘗聞法顯躬身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招集同志僧猛等25人往天竺,勇至中天竺,由海道歸于廣州;有陸去陸回者,如北魏神龜元年(518)惠生偕敦煌人宋云經蔥嶺入印土廣禮佛跡,攜大乘經百七十部由陸路以歸;還有海去海歸者,如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義凈從廣州乘船經南亞、東南亞赴天竺,25年后由海路歸廣州。義凈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謂“西去者盈半百”且僅限于太、高、天后三朝。所以史籍不載而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求法之盛由是可知。
法顯西行成功的示范作用及其此后西行取經成功率的提高,大大地推動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速度和佛教在中國的規范發展。應當說打通中印海陸交通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法顯這次西行尋求戒律本身的意義。
二、戒律傳譯和佛教規范發展
法顯西行之前,傳入內地并翻譯的戒律主要有:三國時,天竺僧人曇摩(柯)迦羅在嘉平二年(250)到洛陽,譯《僧祗戒祇心》一卷,為《摩訶僧祇眾律》四十卷之節要,曇摩迦羅據此在中國首創授戒度僧制度;西晉時,隨著比丘尼僧團的出現,竺法護譯《比丘尼戒》一卷;前秦時,曇摩持、竺佛念譯《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一卷。同時,中國僧人也開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結合入傳的戒律制定佛法憲章。較早對這一問題感到憂慮并付諸行動的是道安。道安(約314—385),為佛圖澄弟子,后趙時入鄴(今河北臨漳),后為避戰亂到襄陽傳法,東晉太元四年(379),前秦克襄陽,被帶入長安。在鄴時道安曾隨佛圖澄對流行戒律進行修訂,到襄陽后深切感受到戒律缺失對佛教傳播帶來的嚴重影響,在此間所著的《漸備經序》中書曰:“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乃最急。”于是,他千方百計尋找戒律原本,并制定“僧尼軌范、佛法憲章”三項。《高僧傳》本傳載:“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道安制定的戒律影響很大,《高僧傳》稱,“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同時,江南佛教領袖人物支道林也著就《眾僧集議節度》。不久,道安的弟子慧遠也在廬山寫成了《社寺節度》《外寺僧節度》《比丘尼節度》等。但與迅速發展的佛教相比,這些戒律顯然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佛教戒典殘缺不全,給教徒的管理和佛教理論的研究帶來極大的困難。當時的戒律尚處于草創階段,戒律的傳譯和創制遠遠不能適應佛教的發展。佛教傳播過程中自然造成的真空,必然在佛教的實踐中反映出來。豪強地主和寺院地主雖在理論上尊崇佛法,但在實際生活中卻不守清規戒律,且為非作歹,有的蓄財近利,有的酒色是耽,更有甚者干預國政。以上種種,一方面說明當時寺院經濟還不足以維持佛教自身的發展,廣大僧侶不得不妄作與佛教無關的甚至是與佛法相抵觸的事務來維持其生計;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無序傳播和因此造成佛徒的不規范行為,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迫切需要進行規范。因此,傳譯戒律在當時就顯得尤為迫切。
法顯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西游并取得成功的。法顯赴天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求戒律的,因此,他自天竺尋求戒律的成就巨大。
釋迦逝世百年左右,佛教內部對于教戒和教義產生不同認識而分裂為兩大部派——“上座部”和“大眾部”,此后兩大部派又不斷進行“枝末分裂”,衍生出眾多部派。而各部派則根據本部派對教義的理解,制定部派戒律。傳世的上座部主要戒律有5部,即曇無德部之《四分律》、薩婆多部之《十誦律》、彌沙塞部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迦葉遺部之《解脫戒經》和婆蹉富羅部之《婆蹉富羅部律》;傳世大眾部的主要戒律有1部,即《摩訶僧祇眾律》。在佛教傳世的6部主要戒律中,除《解脫戒經》和《婆蹉富羅部律》未傳入中國內地外,另外4部均在4世紀末5世紀初傳入中國內地。
曇無德部之《四分律》,后秦弘始(399—415)中由佛陀耶舍與竺佛念譯出;薩婆多部之《十誦律》,即法顯在巴連弗邑寫得的《薩婆多眾律》,《十誦律》始譯于公元404年,初由后秦罽賓僧弗若多羅與鳩摩羅什共譯,弗若多死后由龜茲僧曇摩流支續譯,東晉罽賓僧卑摩羅叉整理補充,在法顯回國時,此律已有完整的譯本,故《出三藏記集》卷二法顯名下著錄云:“薩婆多律抄,梵文,未譯。”;彌沙塞部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因由五部分組成亦稱《五分律》,即法顯于師子國求得之《彌沙塞律》藏本,南朝宋景平二年(424)罽賓佛陀什應竺道生之請,與于闐沙門智勝等共譯;大眾部之《摩訶僧祇眾律》,由法顯從中天竺之巴連弗邑寫得,法顯歸國后不久,在建康道場寺與佛陀跋陀羅(即覺賢)共譯。
傳入中國內地的4部主要佛教戒律中,由法顯攜歸的有3 部:即法顯取自巴連弗邑的《摩訶僧祇眾律》和《薩婆多眾律》(《十誦律》),得自師子國的《彌沙塞律》。由此可見法顯對戒律流傳的貢獻之大。南北朝以后佛教管理的逐步規范應該說法顯是居功至偉。
三、“六卷泥洹”和佛教興盛
東晉十六國時期佛教雖然得到空前的發展,但其局限性依然十分明顯,即佛教基本上為上層社會那些崇尚玄理的所謂“社會名流”所器重,普通的民眾進入佛門的社會環境沒有形成,且佛典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持。許多人想遁入空門,但又擔心自己出身卑微或作惡太多而不能成佛。而法顯從中天竺之巴連弗邑所抄之經卷《方等般泥洹經》正好填補了這一理論空白。
《方等般泥洹經》為《大般涅槃經》部分異譯,因譯出其中較為重要的六卷內容,亦稱為“六卷泥洹”。據《出三藏記集》卷八所收《六卷泥洹出經后記》載,該寫本由法顯與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羅(即覺賢)及其弟子寶云,于東晉義熙十四年(418)在建康道場譯訖。 在法顯等譯“六卷泥洹”的同時,《大般涅槃經》也由北涼曇無讖開始翻譯。曇無讖(385—433),一作曇摩讖,據《高僧傳》卷二載,為中天竺人,初學小乘,見《泥槃經》,自感慚愧而改習大乘。年20能誦大小乘經200余萬言,后到西域,因此地流行小乘,便入北涼,在北涼玄始十年(421)譯完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因其后有南本《大般涅槃經》譯出,故涼譯本亦名《北本涅槃經》。
在《北本涅槃經》還沒有傳到江南以前,《方等般泥洹經》先行流布。《方等般泥洹經》認為,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于身中。無量煩惱悉除滅已,佛便明顯,除一闡提”。所謂“一闡提”系指那些善根滅絕的人。此論一出,則引起軒然大波,稱之為魔書者有之,疑為偽作者有之,宗之者亦不乏其人。其中,竺道生對此加以發揮,大膽推論,認為闡提也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只是經本傳來未盡而已。竺道生(335—434)原是佛圖澄的(竺法汰)再傳弟子,后北上師事鳩摩羅什,東晉末年回到南方,宋初與慧嚴、慧觀為朝野所重。道生較早地接觸法顯譯的六卷本的《方等般泥洹經》。他將《方等般泥洹經》基本思想加以發揮,認為世上最壞的人“一闡提”既然屬于眾生,那么他們也同樣具有佛性,也有可能成佛。他的這一理論在初期遭到反對,為舊學僧徒所擯斥,甚至他本人一度被逐出僧團,入吳中虎丘山,住龍光寺,又入廬山。后來涼譯《涅槃》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皆有佛性之說,證明其主張不虛,他的這一學說終得到多數僧侶的認可并廣為流布。其后,龍光沙門寶林,祖述道生諸義,著《涅槃記》。弟子法寶更繼其后,著《金剛后心論》等。涼譯《涅槃》傳到南朝建康時,宋慧觀與謝靈運等以其本為主,對照法顯譯本加以修訂,成為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
涅槃之學漸盛,教徒之盛由茲。東晉以后我國佛教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促成這一情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毫不夸張地說,法顯帶回并譯出的《方等般泥洹經》起到了理論上的奠基作用和發展中的推波助瀾作用。
注釋:
①平陽武陽,一說今山西省臨汾市,一說今山西省襄垣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