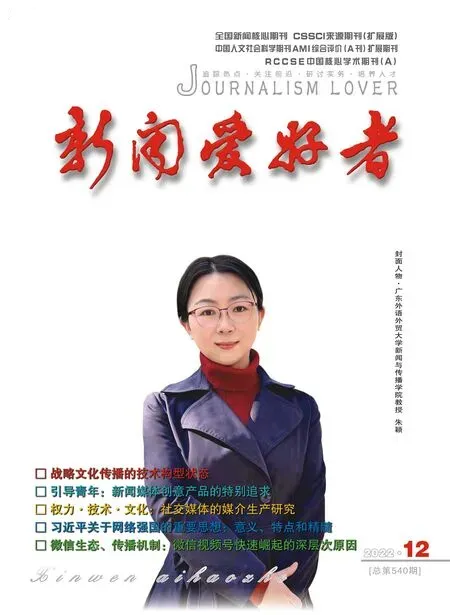從女性主義視角談影視劇中女性形象的嬗變
□但 敏 侯若男
隨著社會地位的提升、經濟實力的加強,當代女性不僅僅追求物質基礎的獨立, 在精神層面的需求也空前覺醒,她們追求性別平等,追求自身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 傳統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種種刻板印象正在被消解, 各種以女性的成長和升華為主題的電視劇應時而生。 近年來,隨著《傳聞中的陳芊芊》《二十不惑》《三十而已》《誰說我結不了婚》 等等以女性為第一主角的電視劇的播出,新時代女性的形象在銀幕上栩栩如生,盡管每部影視劇描寫的故事不盡相同,但總體來說都是在詮釋一個主題:女性實現社會的獨立、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過程。 影視作品作為大眾傳播中的重要部分,具有良好的傳播效應。 影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也一直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要內容,女性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女性該如何實現自我價值? 影視劇該如何反映女性角色的真實狀態? 影視作品該如何為觀眾塑造正面的、積極的形象?
一、影視劇中的女性角色嬗變
(一)“圍城”里的“含羞草”——男權視角下的傳統女性形象
20 世紀90 年代初期,中國的社會經濟才剛剛起步,社會觀念還比較傳統,這一時期的電視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數是男性視角下的“完美”角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渴望》中的劉慧芳,她展現了男性視角下完美妻子的形象, 能干持家、 對待丈夫一心一意,面對丈夫的背叛、兒子的離世也依舊無怨無悔,這種具有犧牲精神只為成全家庭的女性是那個年代社會的要求。 在20 世紀90 年代類似的女性形象還有《咱爸咱媽》中的老喬老婆、《轆轤·女人和井》中的棗花娘、《女人在家》中的趙家玲等,這樣的女性形象通常在影視劇中是被贊揚的, 與之相反的形象則成為批判的對象。 這一時期影視作品中女性可以是成功的、可以是美麗的、可以忍辱負重、可以大度善良,但她必須是具有父權社會下建構起來的女性特質并且完全從屬于父權體系:她們的終極歸屬是家庭,必須能在家庭私領域中操持家務得心應手, 必須具有奉獻精神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成全男性利益。 最重要的一點,這些影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她們都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 這一時期影視劇中的女性角色的呈現主要由于男性一直都是社會生產的主力軍,且女性主義在我國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 女性自我價值追求的意識并不強烈, 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依然從屬于男性價值體系內, 因此女性作為男權社會下公共領域的邊緣群體, 在影視劇作品中以一種弱勢與悲劇的形象呈現。 這是與當時女性的經濟地位息息相關的,“女性貧困化”[1]的現實讓她們不得不成為男權社會的邊緣人物。
(二)一支出墻的“紅杏”——女性形象的突破性試探
2000 年到2010 年間影視劇中的女性角色開始具有突破性的呈現, 在一定程度上對男權社會展示的價值進行反叛:2002 年的熱播劇《粉紅女郎》中呈現的女主形象不僅靚麗, 每一個女性以個體的身份出現,雖然仍然囿于男權主義的圈內,“何如男”看似明顯打破傳統女性范例, 卻實則通過男性特征掩飾來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形象;“萬人迷” 萬玲本著游戲人生的宗旨看上去完全以取悅自我的形象出現,但姣好的外貌形象使她不得不位于整部劇中男性凝視的中心地帶; 也依然有以追求賢妻良母為人生目標的“結婚狂”方小萍這樣的形象呈現,但總體來說開始試圖突破傳統男性審美,找尋自己的價值。 2003年播出的《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在影片結尾與金燕西決裂,白秀珠完成了自己的報復之后遠走異國;2010年《杜拉拉升職記》中的杜拉拉成為女性對事業追求的初步探索, 這一階段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普遍開始突破傳統女性范例中賢妻良母、 勤儉持家的優點,正面女性形象不再是單一的犧牲自我不求回報。當然,其中也依然有《賢妻良母》中朱玉芳這樣犧牲自我不求回報的傳統女性形象出現,仿佛是男權體系下為廣大女性觀眾樹立的道德標桿,宣揚并標榜著從屬于男權社會的女性形象,但這已經不是影視劇中女主角呈現的主要類型,也并不應該是屬于女性本來的模樣。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經濟的命運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會內部具有的形象。[2]也就是說,任何外在的標簽都無法定義女性,突破固有定義,突破固化形象,成為這一時期影視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三)出走的“娜拉”——追求獨立的女性形象
2010 年之后, 出現了大量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影視作品, 掀起了影視作品以女性視角敘事的狂潮,出現了《戀愛先生》《歡樂頌》《北京女子圖鑒》《上海女子圖鑒》等一大批以女性視角進行敘事的影視作品, 這些影視作品的出現都開始顛覆以往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家庭空間中的成功,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結構, 在職場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貝蒂·弗里丹認為女性放棄家庭主婦的身份走出家庭,這就是一種解放。[3]從將女性置于傳統性別結構中的公共領域敘事開始就是對女性實現多元自我價值的重要認同。
2020 年以來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影視作品依舊很多,伴隨各種聚焦女性的綜藝,女性形象的突破更是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其中的女性角色幾乎都是打破了傳統女性范例的存在。 《傳聞中的陳芊芊》以超現實的敘事手法,描述了主人公陳小千作為編劇寫的影視劇本,劇本中虛構的世界以女性為尊,其中的女權社會像極了現實社會里封建社會時期的男權社會;《怪你過分美麗》中的主角莫向晚職場上處處碾壓男性對手, 完完全全地追求著自己的職場價值和工作價值, 愛情與家庭在整個故事中屬于次要地位; 以實現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正是現代女性新的價值追求的呈現; 緊接著相繼播出的兩部電視劇《二十不惑》《三十而已》分別講述幾位都市女性的生活故事, 每部劇都一次性地將多位女性置于故事發展的中心地位, 且其中的女性角色無一例外都在探尋自己的價值, 這樣的女性角色設置帶來的沖擊可想而知。 尤其是《三十而已》中的女性角色,影片的結局顧佳放棄婚姻追求自己的事業; 鐘曉芹找到了理想的職業并且開始賺錢養家, 還給自己的婆婆買了房子; 王漫妮放棄老家的相親對象和到手的工作機會出國留學。 這些女性角色最后的歸屬都不是家庭,而是無性別差異的自我價值的實現。 這一個個全新女性角色的塑造都體現著社會和女性本身對于女性價值的重新審視。 在2020 年重點關注女性的影視劇還有《親愛的自己》《愛的厘米》《我不是購物狂》《誰說我結不了婚》《安家》《親愛的設計師》《流金歲月》《了不起的女孩》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對自我價值的追求成了影視作品中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特點。
二、女性角色嬗變的社會內核
(一)符號化:結構范例下的女性消費思想
消費隨處存在, 鮑德里亞認為我們正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境地。[4]影視作品也是如此。 觀眾對于影視作品的消費決定其生產, 消費總是通過某種被符號系統傳媒化了的關系對這種自發關系的取代來規定的, 女性的身體消費是指女性為維護自我的外在形象而進行的消費。 影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變化, 原因之一就是擁有了經濟獨立的女性在進行自我消費, 她們與自己的關系通過某種符號來表達和維持, 男權壓迫下的女性迫切地需要一些象征著解放的符號來堅定女性自己的發展之路, 那些在影視劇中出現的顛覆性的新女性形象以追求傳統男性范例中高要求、 高選擇為目的,形成了一個個突破傳統女性范例的符號,也正是在追求性別平等的女性觀眾尋找的那種符號, 而這一符號成了真正的消費物品。
(二)“她世紀”:市場決定的女性角色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影視作品從追求附屬于男性的價值到追求完全獨立的自我價值, 其中的原因少不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女性可以從事的工作越來越多, 獨立的消費能力和女性觀眾的數量龐大極大地影響了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設定的變化。 與男性擔任社會主要勞動力、 擁有主要社會財富的時代不同,2000 年后“她世紀”的到來使女性的主體性得到張揚,女性的消費開始更多地關注自身、體現女性的主體性。[5]2020 年熱播的《傳聞中的陳芊芊》微博熱搜44 次,熱度值1.5 億;《親愛的自己》共上熱搜近40 次, 單以女性角色為話題上熱搜的就有近30 次;《三十而已》播出期間微博熱搜228 次,大多數是和女性相關的話題……這樣強大流量帶動的消費市場會更加促進影視作品中女性形象跟隨消費市場而變化。 不管是突破傳統范例還是加固傳統范例中的某些女性符號,都可以看出這是由市場決定的,目的就在于通過女性取悅自我、 追求獨立的消費促進影視作品的消費市場的擴大。
三、女性角色嬗變中的問題
(一)“大女主”:真命題還是偽命題?
“大女主”電視劇由來已久,從《杜拉拉升職記》中的女性職場敘事角度到《歡樂頌》等電視劇的多女主故事線并行,“大女主” 的核心其實是在向著女性主義的方向發展, 以關注女性角色成長成為故事的主題,男性角色的出現是為了襯托女性角色的成長,輔助女性得到大眾定義的成功。 但是新事物的發展總是會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女主” 電視劇不可避免會受到傳統男性視角敘事的影響——這些“大女主”的成功,無一例外地需要依托她們身邊的男性,她們的成功價值建立在男權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之內。《我的前半生》 中女強人唐晶的成功有著亦師亦友的男性角色賀涵的指引。 看待性別離不開關系,可當描寫女性成長的影視劇中總有男性角色充當“領路人”一樣的存在,這樣的性別關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二)焦慮與刻板:性別對立中的傳統印象
女性在很多領域處于邊緣地位, 這是傳統政治文化建構的結果。 男性與女性長期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也決定了一直以來都是男性中心地位, 因此我們看到的很多歷史與故事可以說 “是男性的歷史與故事”[6],這在往常的影視作品中都有表現。
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開始大量以女性為主角展開敘事,將女性放在了中心位置,加上影視作品女性受眾的數量龐大, 對影視作品的解讀多從女性視角出發。 雙向的女性視角不可避免地將觀眾代入女性思維的巢窠。 同時劇中的角色也陷入拘泥于性別的焦慮,越來越多的影視劇開始強調女性的焦慮。 《二十不惑》《三十而已》 劇名就直接聚焦女性年齡;《誰說我結不了婚》 中童瑤飾演的程璐全劇都在面對年齡三十加未婚的焦慮中, 陳數飾演的律師田蕾作為職場中的“大齡單身女青年”,在工作上屢次遭遇性別歧視……諸如此類的女性年齡焦慮在當下影視劇作品中已成常態。 與女性角色不同的是影視作品中鮮有關于男性角色的年齡焦慮。
在當下聚焦女性的影視作品中對于除主角之外的男性角色的塑造多易形成刻板印象, 近期影視作品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三十而已》的男性角色被網友取名“許放炮”“陳養魚”“鐘綠茶”“梁海王” 這樣的綽號,顯而易見,這就是從單一女性角度進行思維的結果。劇中演員因出演一角色而遭到觀眾“罵上微博”的例子比比皆是,當影視作品中的角色設定賦予這些男性角色個體或群體以貶低性、侮辱性的標簽后會進而導致這一群體受到社會的不公正待遇,給男性強加使性別矛盾激增的刻板印象。 不管是任何一種單一性別的思維都不利于正確的女性主義觀念傳播。 從男性中心到女性中心,二元對立的視角使影視作品中的角色陷入性別對立的境地,而男性與女性本不應該是對立存在的。
四、結語
當然, 女性主義是一種視角而非評判標準且仍在不斷的發展當中, 女性主義視角本身否定一切不變, 在對影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進行審視時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變化一直是在向著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前進的, 盡管免不了受到傳統男權思想的影響, 但在近期的影視劇作品中也越來越重視女性關于獨立自我價值的實現,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影視作品作為大眾傳播的重要部分應該努力引導人們進行正確客觀的價值評判而非為了看點與流量無節制地引導話題, 以免在爭取女性自我價值的道路上矯枉過正或是矯枉不正。 就像《傳聞中的陳芊芊》中描述的那樣,女主在經歷了女權社會和男權社會之后致力于打造男女平權的理想社會, 盡管我們不知道劇中的社會能否成功, 但現實里的人們必須努力向著這樣的一種社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