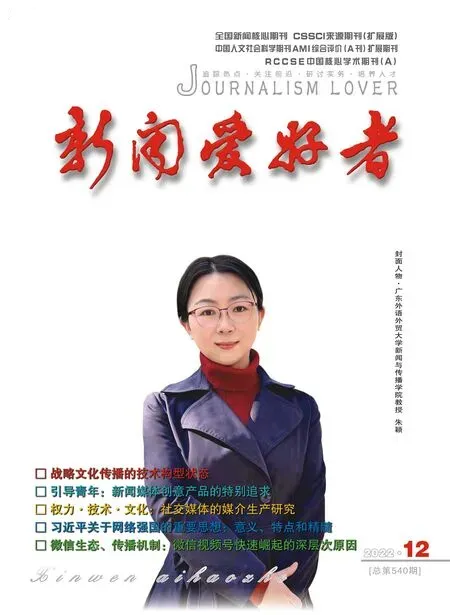新興場域的新行動者:校園媒體融合創新
□丁 莉 靖 鳴
近年來, 校園新媒體蓬勃發展是值得研究的新聞傳播現象。 這首先是適應整個傳播生態環境變化和國家媒體融合政策調整的現實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下我國輿論環境所發生的變化, 要求主流媒體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 強調做好宣傳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創新,應以“創新”為要推動媒體融合發展。 正因如此,“新聞創新研究正在成為一個備受新聞研究者們關注的新興領域”。[1]當下微妙而復雜的傳播環境正深刻重塑著新新聞生態系統,涌現出了如政務新媒體、自媒體等新興場域的新行動者,比如“由師生發起、立足于大學社區、關注校園內外公共事務”[2]的校園新媒體作品近年來頻繁見之于微信公眾平臺和社會媒體上, 作為媒體融合戰略大背景下出現的新興媒體形態,受到業界和學界的關注。
縱觀各校校園媒體的融合發展,雖然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與廣大師生的需求相比,與時代發展的要求、與社會媒體的融合發展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和努力的空間。[3]因此,校園傳統媒體融合創新的能動性何以產生? 其能動性如何影響校園新聞日常生產實踐? 作為新興場域的新行動者,校園媒體如何融合創新?
一、場域邏輯:校園媒體融合創新的動力因素
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的網絡,或者是構置”。[4]劉海龍認為,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對中國社會現實比較具有解釋力, 因為該理論的優勢在于對關系的強調, 而這“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在傳統上講究禮俗而非法理的社會來說,具有天然的契合性”。[5]高校新媒體“從行政隸屬上來說,身處高等教育界而非新聞界,接受的是高等院校黨委的領導,屬于政治場域,但從外部形態來說,它則屬于新聞場域”。[6]這就構成了校園媒體場域的內在基因: 高校作為官僚制的治理邏輯和新聞專業邏輯的潛在沖突,“互聯網技術的開放性、即時性和互動性抬升了校園新聞所處結構內蘊的張力,強化了新聞與政治兩個場域之間的復雜性”。[7]那么, 處于校園內部與權力場環境之中的校園媒體如何能夠突破封閉的場域邊界,產生新慣習、新組織形式、生產流程,使得在成熟組織場域中形成一個新聞邏輯與政治邏輯彼此平衡與融合的新興場域。
(一)開創融合機遇的技術力量
長期以來,校園傳統媒體場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組織場域,被視為權力場的一部分,場域內部不同媒介之間也是彼此分離和獨立的。 而在融合傳播時代,技術成為新媒體場域的重要構成要素,微信公眾平臺等社會化媒體不會為校園媒體提供什么技術條件來區分大學內外不同的場域,校園媒體遭遇外部環境沖擊和內部機構轉型的雙重壓力。這使得校園媒體組織場域被迫打破封閉與邊界, 政治邏輯服從新聞邏輯,形成一個嵌入在成熟組織場域中的新興組織場域。校園新媒體改變了傳統的新聞生產常規,以融合手段協同生產,走出大學社區的社會邊界,介入非校園議題,對標社會專業媒體進行新聞生產。但當校園新媒體在事實上走出校園、面向公眾,成為高校對外的代表性標志時,高校必須要考量新媒體激發的多元異質社會思潮與意見表達帶來的潛在后果。這便提升了校園新聞場域作為官僚制的治理邏輯與新聞專業邏輯的潛在沖突,又使得政治場域出現了與新聞場域進行融合的需要,高校新媒體誕生于新聞與政治兩個場域之間相互融合的嘗試與努力之中。
(二)主導融合進程的政治力量
新興組織場域得以形成最重要的力量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主導力量, 是權力場對新聞場強勢介入的結果。 在互聯網技術介入校園媒體場域之前,校園新聞主要是靠學校黨委宣傳部門管轄的校報、 廣播電視臺、 官網發布。 其總體特征是校報主導傳播主體、 輿論環境較為單純、 信息獨家發布賦予話語的“權威性”、受眾消費習慣較為穩定等。 正是在以上種種得天獨厚的“封閉”場域環境中,校園傳統媒體的傳播能力得以較好發揮, 有效完成了輿論導向的使命和任務。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播生態的變化,對傳統校園新聞生產造成了巨大的挑戰與壓力。 以00后為主的大學生用戶面臨著被各類新型網絡媒體蠶食, 繼而深刻影響到校園媒體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引導使命, 并演化成被上層管理者和從業者普遍感知到的危機。 因而,自2014 年媒體融合成為國家戰略以來, 教育系統緊跟其后開展了自上而下的教育政務融媒體戰略, 國家戰略是校園媒體融合創新的最根本動力。
(三)作為實踐主體的從業者力量
“校園媒體不是媒體”[8],這是長期以來社會對校園傳統媒體的實然判斷。 校園媒體長期落后于社會媒體,與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極不相稱。 最主要的是因為在傳統校園媒體組織場域中, 權力場的邏輯和規則在校園新聞生產中占據壟斷地位, 新聞場域的邏輯和規則被擠壓, 從業者缺少改革發展的機會結構與動力。 校園新媒體新興場域的逐漸興起與發展,得益于政治場域邏輯在新媒體方面之弱、之淡,這對校園媒體人是前所未有的激勵和機遇, 他們抓住機會依循新聞場域邏輯, 及時調整校園新媒體生產的定位、策略、話語以實現新聞專業理念,使得校園新媒體新聞化,又遵循“產品”“流量”“用戶”等市場邏輯行事,實現新興組織場域合法化建構。
二、新興組織場域建構:校園新媒體融合創新實踐
技術和市場力量的介入, 使得校園傳統媒體成熟組織場域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伴隨著嵌入其中的新興場域一步步出現、成長、擴展,舊的生產常規必然被打破,場域內新舊資本不斷融合、爭奪、轉換,在生產實踐中發展出新的生產常規、組織形式等,促使新興場域合法化地建構,同時,校園媒體場域的“自主性”在逐漸覺醒和增強。
(一)認知創新:從封閉式運營轉向市場化運營
媒體新聞生產的市場化與公共性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而校園傳統媒體長期生存于大學校園內,處于簡單生產新聞信息的封閉運作之中, 很少受到來自市場的影響。 互聯網技術讓校園媒體得以進入公共空間,影響更為廣泛的社會議題。 但借勢技術進入公共空間的校園媒體又不得不在走出校園和面向社會之間不斷調試,探索市場化運營之路。
引入市場化指標,進入流量市場。 場域是不斷斗爭和合作的過程, 政治力量的弱化給市場力量進入新興組織場域提供了機會結構。 市場力量在新興組織場域中主要體現為閱讀量、 轉發評論量和是否受到社會媒體報道等指標。 這股新勢力的介入為校園媒體市場化的發展帶來了想象力, 校園媒體對標社會專業媒體,用時下最流行的“流量”作為校園媒體內容生產新指標。 從2014 年11 月開始,為評估高校官微影響力, 中國青年報推出全國普通高校微信公眾號綜合影響力排行榜以及相應的文章閱讀量排行榜, 類似的榜單成為社會判定高校官微好壞的重要標準。 校園媒體場域從以往純粹權力場的一部分轉變為受政治和市場兩種邏輯所牽引的復雜場域。
多樣化互動形式,吸引受眾參與。 在政治邏輯主導的傳統媒體組織場域中, 受眾被視為政治傳播活動的客體對象,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和反饋,因而在強調受眾意識的新媒體時代校報等傳統媒體迅速失去受眾基礎。 “高校學生閱讀校園微信公眾號推文后互動意愿強,93%的學生曾評論、 轉發校園微信公眾號文章”。[9]新媒體新興場域尊重受眾至上理念,開發多樣化互動渠道,吸引受眾主動參與、積極反饋。 例如,武漢大學2022 年畢業典禮時,該校官微除運用短視頻、動圖進行現場直播外,還插入了2022 年畢業MV《此間珞珈》,當天生日的畢業生私信官微小編還可以領取生日禮物……多樣的互動形式引發近50萬人在線觀看,兩次沖上同城熱搜,受眾評論信息成為新的受關注的內容和對象的一部分, 受眾已成為校園新媒體的主要傳播參與者。
(二)內容創新:從宣傳本位轉向新聞本位
校園媒體不管如何融合創新,始終是“黨媒”性質,政治新聞依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媒體習慣宣傳本位,帶來政治新聞“傳不開、播不遠”的困局,沒有傳播力,后續的輿論引導更是無本之木。 新興場域積極調試政治新聞傳播并提供了突破路徑的空間, 對政治新聞擺脫宣傳本位、 回歸記錄本位。 在2021 年黨史學習教育開展過程中, 湖北省委書記應勇來到武漢大學與師生代表座談并講黨課, 該校官微發布推文《這堂課,省委書記應勇主講! 》,將座談會中的幾個亮點分列成5 個小標題, 小標題下面附上重點內容摘錄,并對重點文字標紅處理。 這一報道既保證了會議新聞的真實性,又有親和力,文字圖片排版契合新媒體簡潔、 重點突出的表達方式, 獲得4W+的閱讀量和受眾好評,體現了校園媒體的專業理念導向。
運用新技術手段,呈現融媒新聞。 當下大學生長期浸潤在短視頻、動漫之中,相比傳統的圖文稿件,新媒體集視頻、音頻等多媒體組合傳播優勢,更具表現力,契合學生興趣。 2021 年3 月,武漢大學圍繞櫻花季發布了多篇推文,《今天,武大“櫻”為他們沖上熱搜! 》《驚艷! 武大在下“櫻花雨”……》《wow! 當櫻花遇上漢服,美到尖叫》等,武大融媒體中心采用了5G+VR+AI 等前沿科技助力櫻花綻放、櫻花雨落下的瞬間的記錄和直播等,視覺效果唯美震撼。其中有13篇關于櫻花的推文閱讀量突破10W+,體現了校園媒體的技術導向,并收到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三)邊界創新:從組織傳播轉向大眾傳播
當下,抖音、視頻號等平臺媒體市場下沉之路嚴重影響到了校園網絡輿論的穩定性, 校園傳統媒體的用戶基本面臨著被社會專業媒體分流和各類新型網絡媒體的蠶食。2019 年,教育部啟動開展教育系統融媒體建設試點工作, 目前全國已有30 家試點單位。 各省份其他高校也都紛紛探索對標社會媒體的專業化生產, 將融媒體建設作為校園新聞輿論工作轉型升級的突破口,占領輿論陣地,尋找突破路徑,匯聚校內資源,謀求工作突破。 高校建立的融媒體中心,有專門的場地、配備專門的人員、設備,劃撥了專項經費,統一管理校園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作為校園媒體的“中央廚房”協調指揮各媒體的整體策劃、稿件采寫、素材編輯和聯動傳播,打造一個集文字、圖片、音視頻、H5、動漫、直播于一體的“融媒”窗口,取得了較好的融合效果。
高校工作呈現周期性的特點,比如每年的新生報到、開學典禮、招生季、畢業季等,這類新聞的特質是時間固定、內容豐富、關注度髙。新媒體打破傳統媒體報道的時空限制, 探索校園新聞系列化專題報道之徑。 2022 年,揚州大學官微圍繞建校120 周年,在倒計時一周年、100 天、30 天等重要時間節點都進行了預熱,并發布了相關的文創產品作為粉絲福利,在相關推送中回望建設歷史、重要成就、溫暖瞬間、校園美景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其系列宣傳報道作品總閱讀量超過100 萬,其中5 月19 日《親愛的揚州大學,120 歲生日快樂! 》單篇推送閱讀量超過61 萬。
校園傳統媒體一直被稱作校內媒體, 微信公眾平臺等社交媒體打破了大學社區的封閉邊界, 面對重要輿情和師生關注的社會公共事件的滲透分化,高校必須主動及時發聲,在網絡領域傳播主流聲音,占領網絡輿論制高點。 一方面,校園新媒體要善于抓住社會媒體報道中與學校相關的熱點事件, 增加學校熱度,宣傳學校形象。 如2022 年5 月,《人民日報》刊登了2020—2021 學年本專科生國家獎學金獲獎學生代表名單的報道, 武漢大學官微敏銳捕捉到了這一訊息, 發布推文 《國家獎學金優秀代表, 周章嫻! 》,對國獎優秀代表周章嫻同學在武漢大學四年的求學生活作了詳細介紹,融入學校教學、創新創業等方面的亮點和創新之處,并成功宣傳了學校形象。
三、結語
在新興組織場域中,校園新媒體在認知上探索市場化運營路徑,在內容上回歸新聞專業主義,在邊界上表現出大眾傳播的特征,實現了對傳統新聞生產的融合創新。雖然高校融媒體的整體發展尚處于探索階段,與社會專業媒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但令人欣喜的是, 新媒體讓人們看到了校園新聞生產的變化,比如,校園新聞生產從組織內部傳播邁開了走向大眾傳播生產的步伐,校園新聞生產積極探索參與社會新聞事件, 成為社會媒體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等。保持高品質的新聞生產與公共傳播的責任擔當,完成好滿足師生需求與輿論引導能力的雙重任務,真正提升影響力和公信力,校園媒體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