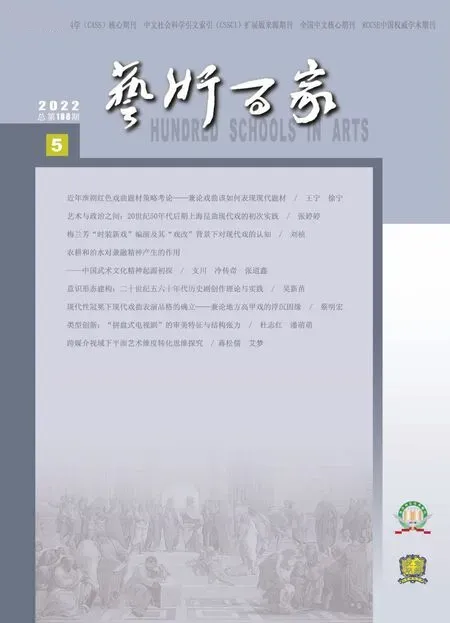農(nóng)耕和治水對(duì)兼融精神產(chǎn)生的作用?
——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精神起源初探
支川,冷傳奇,張道鑫
(南京體育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4)
兼融精神是中華文化諸多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思想模式得以產(chǎn)生的沃土。 無論是政治文化、藝術(shù)文化,還是武術(shù)文化,它們的源頭性研究都離不開對(duì)初始文化現(xiàn)象的辨析理解。 為何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能夠源遠(yuǎn)流長(zhǎng)、博大精深、異彩紛呈、兼容并蓄而不斷推陳出新? 這與中國(guó)地處廣袤的東亞大陸,既有全體必須面對(duì)的大問題,又有部分群體須面臨各不相同的具體生存環(huán)境有關(guān)。 這促成了滿天星斗般散落各地的文化。 所以,要厘清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精神,必須像中國(guó)哲學(xué)、中國(guó)藝術(shù)一樣,通過回溯其得以產(chǎn)生的母胎奇點(diǎn)來認(rèn)清自我。 人類總是在不斷回望故鄉(xiāng)的自我反省過程中砥礪前行。 農(nóng)耕、治水于兼融精神的形成有何作用呢? 這必須由農(nóng)耕、治水所可能喚醒的人們的意識(shí)說起。
一、農(nóng)耕產(chǎn)生了道的自覺和祖先崇拜
(一)道的自覺
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道,所行道也,《毛傳》每云行,道也。 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申為道理,亦為引道。 從辵首,首者,行所達(dá)也。 此中直至故亦謂之行。”[1]117以上皆是說“道”所指稱的是什么樣的事物(所行道也),與何名稱是同義的(故亦謂之行),這只是在“道已經(jīng)成為道”之后的說明。 而此處真正的工作是:“道之所以為道”的闡釋。 從辵首,首者,行所達(dá)也,《說文》“達(dá),行不相遇也”,意即“通,無礙”。 那么,“首者”就是行所通之處,或可通之處。于是“道”就是行(“從辵”)與有“所達(dá)”(“從首”)的結(jié)合。 至此,得到了一個(gè)重要的信息,道的重點(diǎn)不在于“行”本身,而在于“行”的意向(“所達(dá)”)和“行”得暢通無阻,即是否有明確的既定目的地。 “道之引申為……亦為引道”的“引道”的意思是指:(1)對(duì)目的地的指引,即對(duì)遺忘或不知目的地所在的給予指引;(2)對(duì)如何“行”才會(huì)通向目的地的指引。 這兩方面才是“道之所以為道”的重心,即為“引道”。 “引道”恰是在這個(gè)意義上使愚昧的人脫離愚昧狀態(tài),走向“智人”之路。
由此,本文認(rèn)為“行之前必先有了一個(gè)既定的、明確的目的地”,這種意識(shí)的明確化是道的自覺的誘發(fā)因素;然而,單單有了這種意識(shí)的明確化仍然是不會(huì)有道出現(xiàn)的。 道之所以為道,必先在其“行”發(fā)生的那一頃刻,已經(jīng)有了所行路線的規(guī)定,否則,又何必在茫茫的大地上最終形成一條條的道? 所以“可行與不可行”的規(guī)定是道最終躍出為道的形成因素。這里之所以沒有套用亞里士多德的“形式因”,而說是“形成因素”的原因是:(1)“可行與不可行”的規(guī)定只是劃定了行的范圍,本不是“道”的形式;(2)道是人們?cè)诖艘?guī)則所定的范圍內(nèi)日積月累而逐漸形成的,它有了一個(gè)歷史的形成過程。 我們不能說某一個(gè)人踏出那一線土地才是道,因?yàn)榈涝谧畋举|(zhì)的意義上是需要大家都有所努力,要不然,就不會(huì)有后來的“人能弘道”觀念的提出。
正因?yàn)橛辛苏T發(fā)因和形成因,才使向既定目的地的“行”負(fù)載了分外的有意識(shí)的努力。 因?yàn)橛辛恕靶小钡囊?guī)定,在向目的地前進(jìn)的過程中,必須避開不可行的路線,而這些雖然不總是有意識(shí)的,但是它總會(huì)有達(dá)到喚起意識(shí)的時(shí)候。 于是,那種“有意識(shí)的努力”便與誘發(fā)因素、形成因素一起實(shí)現(xiàn)了人們于道的自覺。 由此,也可以得出“道”的真正所指是截去兩頭(出發(fā)點(diǎn)和目的地)而后剩下的通路,它最本質(zhì)的意義便盡在于“通”。 這或許也是為什么“道”含有“方法”的意義。
現(xiàn)在來考察農(nóng)耕、游牧、漁獵三種生產(chǎn)方式,看“道的自覺”必然地會(huì)在哪一種生產(chǎn)方式中得以產(chǎn)生。 顯然,游牧、漁獵二種文化群體的行動(dòng)必然是:(1)沒有既定的、明確的目的地,總是隨遇而安,而且路線隨時(shí)可變;(2)沒有劃分可行與不可行的必要;游牧,茫茫草原盡可馳騁;漁獵則連想都無須想這個(gè)問題,因?yàn)樗麄冎灰蜓拥琅c獸跡就可以了。 所以,不可能有道的自覺。 而從事農(nóng)耕的文化群體的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它們總是不得不在一個(gè)地方停留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以俟其成,而且一旦停下,自然就有住處、耕地等不大會(huì)變的行動(dòng)目的地,農(nóng)耕也自然會(huì)于區(qū)域內(nèi)的土地有所劃分,并不是所有的田地都可以隨意踐踏。 由此,我們終于可以看見那一條條道路是如何在農(nóng)耕社會(huì)中日漸明晰地浮上地面的了。 既然有了固定的家,那么就必然是“無往不復(fù)”[2]179。 (游牧則是單向性的,他們的家是隨身帶走的。)行走的人數(shù)量的多少,最終使道有了“由小到大”的層層變化,人們一旦因?yàn)橼吚芎Φ奶煨远_始使道的意義復(fù)雜化后,便可以順著這架“由小到大”的層級(jí)之梯,逐漸走向理性化,對(duì)實(shí)在性予以消解,便出現(xiàn)了“大道”“天道”“不可道”的“道”,……漸漸地,中國(guó)哲學(xué)的豐姿便明晰起來了。 于是,上帝要觀察周人的政治,也只是看“道路”而已,“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3]106(謂上帝視察周人居住的山丘,見木撥道通,知民已歸之者益眾矣)。 漸漸地,“大道”“無往不復(fù)”等觀念便深入中國(guó)人的意識(shí)深處,成了其根本的信念(也由此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一個(gè)很大的不同,西方的道是語(yǔ)言,而中國(guó)的道是路)。
當(dāng)然剛有道的自覺的時(shí)候的情景是難以想象的,也是無法想象的。 但是,我們卻可以在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道的詳細(xì)記載里想見道在人們的心目中的地位。 《尚書·禹貢》中九州所及,無不詳細(xì)敘述其區(qū)域內(nèi)的河流的整治,道路的疏通及貢品如何運(yùn)達(dá)京師,以達(dá)“貿(mào)遷有無”[4]215的效果,這足以證明道的重要地位。如果我們能想象一下上古社會(huì)的人的認(rèn)識(shí)發(fā)展的緩慢,就可以推出道的自覺是多么遙遠(yuǎn)的事了。 (河流也是道,水行乘舟的歷史比陸地上的道的自覺要早得多,但是,水行之中人們只有因循,不可能有太多能動(dòng)的表現(xiàn),于是,我們認(rèn)為它不足以喚醒人們道的自覺,但一旦當(dāng)?shù)酪呀?jīng)成為道了,那么“水道”的形成也只是時(shí)間的問題了。)
道的自覺意識(shí)于人類社會(huì)有何促進(jìn)呢? 本研究認(rèn)為,有了道的自覺之前,人類之間的交往都是因?yàn)樽匀坏脑蛩斐傻?是偶然的;有了道的自覺之后,就變成是由非自然的原因所造成的了,雖然自然原因仍在起作用,但是人類自己卻以較自然快捷得多的方式在主動(dòng)地相互交流。 因?yàn)榈赖淖杂X,它不單單是對(duì)實(shí)物的路的認(rèn)識(shí)而已,更多是由道所產(chǎn)生的認(rèn)識(shí)世界的方式:人可以通過努力摸索出一條途徑,順利地達(dá)到目的。 所以,有了道的自覺以后,人類社會(huì)就可以以更快的方式交流、融和了,因?yàn)樗癸@了人的主動(dòng)性。 “道”的自覺本身就是人的主動(dòng)性的表現(xiàn),因?yàn)檎缟衔囊炎C明了的,道的誘發(fā)因素是“既定的,明確的目的地”,而“目的地”只能由人去主動(dòng)設(shè)定。
(二)祖先崇拜
張光直在《中國(guó)遠(yuǎn)古時(shí)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一文中于龍山期的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中有這兩點(diǎn):(1)游耕的方式逐漸被放棄,而采用定耕的方法;(2)基于上述的龍山期社會(huì)文化的革新,產(chǎn)生其儀式生活的革新[5]113-114。 一言以蔽之,龍山期的宗教儀式,除了祭社以外,出現(xiàn)制度化的祭祖與專業(yè)性的巫師,這種儀式不是以全村的福祉為念,而是以村內(nèi)一部分人的福祉為念,這一部分人的范圍界限的標(biāo)準(zhǔn)可能與親屬制度有關(guān)。
由此,我們可以說,隨著游耕到定耕的演變,社會(huì)有了大的變化,出現(xiàn)了祖先崇拜。 其目的是什么呢?祖先崇拜,固然如學(xué)者所說,以祈求本宗親屬的繁殖與福祉為目的。 但其更重要的一項(xiàng)功能,是借儀式的手段,以增強(qiáng)與維持同一親團(tuán)的團(tuán)結(jié)性,強(qiáng)化親團(tuán)成員對(duì)本親團(tuán)之來源與團(tuán)結(jié)的信念。 本文認(rèn)為此中的“但其更重要的一項(xiàng)功能,是借儀式的手段,……強(qiáng)化親團(tuán)成員對(duì)本親團(tuán)之來源……的信念”客觀上喚醒了歷史的自覺。 因?yàn)樵诖藘x式中必然要追述歷代祖先,頌揚(yáng)其光輝的歷程(當(dāng)然,這里的目的在于凸顯此精神的萌芽)。 祖先崇拜既然是在定耕階段才成為事實(shí),那么對(duì)它產(chǎn)生的緣由不妨作這樣的推測(cè):定耕群體中的每一個(gè)人都必然是生于斯,長(zhǎng)于斯,死于斯,葬于斯,因而非常自然地就產(chǎn)生了對(duì)腳下生養(yǎng)自己的土地的感恩之情。 自遠(yuǎn)古就有的社祭,把每一個(gè)人早就培養(yǎng)成了大地有靈的信奉者。[6]
由此可以得出結(jié)論:(1)現(xiàn)存最早的農(nóng)業(yè)祭是祈年祭,其時(shí)還處于游耕階段;(2)祭祀的對(duì)象是土地之神;(3)以女性或女陰為象征;(4)祈年祭只是祈豐祭的一種。 而且,祈豐祭都具有這兩個(gè)特點(diǎn)。 由此可以推證:祈年祭的發(fā)生可能在極早的時(shí)候,或許是在農(nóng)耕稍微走入人類意識(shí)的時(shí)候。 因?yàn)槠碡S祭有可能在農(nóng)業(yè)產(chǎn)生之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而農(nóng)人只是借用已有儀式來表達(dá)愿望而已。 那時(shí)的土神要么是所有的大地之神,要么是可以隨人行動(dòng)的,否則人就不會(huì)在游動(dòng)的狀態(tài)下還去祭祀。 于是,這不是局限于某一塊土地的,因?yàn)橄抻谝坏氐耐辽裰挥性诙ǜ蔀槭聦?shí)的時(shí)候才會(huì)出現(xiàn)。
而一旦再也不游不動(dòng),就會(huì)把自己腳下的土地視為有靈。 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是在一個(gè)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中慢慢轉(zhuǎn)化而成的。 當(dāng)然,在此過程中,亦會(huì)有關(guān)于宇宙的新的認(rèn)識(shí)產(chǎn)生。 在向土地感恩之余,就自然地把意識(shí)指向使自己得以生長(zhǎng)于此的人物,于是就有了祖先崇拜。
如果我們想象一下,開疆拓土的困難、危險(xiǎn),直至很久以后那些開拓者的經(jīng)歷仍作為傳說掛在他的后人的嘴邊的話,后人又怎能不對(duì)其祖先由衷欽佩呢?柯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說:一個(gè)文明的生長(zhǎng)程序可以看作人類逐漸創(chuàng)造一個(gè)較大而且較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不但通過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較廣范圍中的資源的進(jìn)一步的開發(fā)而在自然境界中如此,而且在社會(huì)與精神的境界亦然。 ……而文明人則住在一個(gè)差不多是他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環(huán)境,在這種意義上,文明乃是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環(huán)境,他用來將他自己從純?nèi)蛔匀缓驮辑h(huán)境隔離開來。[6]11
單憑這種心情就可以把他們的祖先由凡人造成半人半神,或干脆是全神的了,于是,我們?cè)谥袊?guó)的神話里就見到了那么多有神的血統(tǒng),或有神性的英雄人物。 在此過程中,祖先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就會(huì)被當(dāng)作神示一樣接受,更何況,還是在一種神圣的儀式之中呢?祖先崇拜和它的副產(chǎn)品——?dú)v史的自覺的共同作用,像在上古的各個(gè)文化群體中辦了一所學(xué)校。 在此學(xué)校中,每個(gè)人都得到了歷史的教育,從而實(shí)現(xiàn)了經(jīng)驗(yàn)在文化群體內(nèi)的積累,在文化群體內(nèi)實(shí)現(xiàn)了人的兼融;由橫的方向上的共時(shí)交流到縱的方向上的歷時(shí)性的積累與傳遞,從而使每個(gè)文化群體都有了一個(gè)小小的圖書館。 哲學(xué)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猜想與反駁》也持有類似觀點(diǎn),即知識(shí)的累積是人類的進(jìn)步的重要因素。[7]44
在此之前的星星之火般的各個(gè)文化群體,現(xiàn)在竟然都成了熊熊火焰。 也就是說,祖先崇拜促使各個(gè)文化群體內(nèi)的融合,并為不同的文化群體之間的兼融提供了實(shí)踐性的準(zhǔn)備。 在此過程中的自覺的文化融合,也使文明的發(fā)展步伐加快。
二、治水對(duì)兼融的促進(jìn)作用
在史料的梳理過程中歸納提煉,會(huì)更有說服力。上節(jié)已經(jīng)提出了農(nóng)耕才使洪水成為洪水,否則,人們就會(huì)隨便移動(dòng)一下,而不會(huì)對(duì)此太在意。 雖然如此,這終究只是理性的推導(dǎo),我們終究無法證實(shí)農(nóng)耕群體在剛遇到洪水的侵害時(shí)是否會(huì)有所作為,何時(shí)才會(huì)開始有所作為。 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日積月累的經(jīng)驗(yàn)中運(yùn)用歷史理性的想象,來補(bǔ)足那長(zhǎng)長(zhǎng)的發(fā)展歷程。雖然如此,我們卻終于可以想象性地知道治水歷史的漫長(zhǎng),從而使治水的經(jīng)驗(yàn)得以有足夠的時(shí)間來錘煉出文化精神的核心。
治水像其他任何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一樣,總是先由少數(shù)人的嘗試開始,因?yàn)橹灰獑栴}發(fā)生了,問題所關(guān)涉的人總得想辦法去解決,如此由點(diǎn)到面地?cái)U(kuò)展開去,從而使其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總是帶有地方色彩。 考古上的發(fā)現(xiàn)證明:四川的古國(guó)階段可以從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啟發(fā),這樣巨大的工程,不會(huì)是李冰父子一次治水成功的,“深淘灘,低作堰”[8]189,這不是關(guān)中黃土地帶的治水經(jīng)驗(yàn),而是四川人的經(jīng)驗(yàn),是土著文化,四川有自己的治水傳統(tǒng),治水時(shí)代,即古國(guó)時(shí)代[9]142。 (本文認(rèn)為這里的“古國(guó)時(shí)代”不僅是指古國(guó)出現(xiàn)以后,還包含古國(guó)出現(xiàn)之前的、向古國(guó)的出現(xiàn)邁進(jìn)的漫長(zhǎng)歷史中的一段時(shí)期,否則,他的論斷就不是歷史理性所能理解的了。)這是蘇秉琦在查閱考古資料的基礎(chǔ)上得出的四川治水的起始時(shí)期的論斷。 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其他地區(qū)亦是如此。
再來看徐旭生先生的研究:在共工氏時(shí),它(指共工氏治水所筑的土圍子)不過是保護(hù)自己部落不受水患影響,規(guī)模較小。 鯀時(shí)情況有所不同,共工氏時(shí)的土圍子,確已發(fā)展為城墻之類建筑物。 近年來,河南告成王城崗、淮陽(yáng)平糧臺(tái)龍山文化城址的發(fā)現(xiàn):“‘鯀作城’的傳說,經(jīng)考古發(fā)掘材料印證,確為事實(shí),所以當(dāng)日鯀為部落聯(lián)盟所推舉,興師動(dòng)眾,大規(guī)模地工作……”[3]11,依舊是在史料與考古的綜合運(yùn)用中證明了治水的歷程是由單一部落到部落聯(lián)盟,直至最后的方國(guó)。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治水起始于極早的上古時(shí)期,而且有一個(gè)漫長(zhǎng)的歷史過程。
《尚書·堯典》中,堯稱共工為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王先謙曰:蓋謂共工為人,貌似恭謹(jǐn),而其橫肆不敬之心彌漫充滿,上極于天[4]66。 大意是說共工驕傲自大,目空一切。 堯稱鯀為方命圯族,方命,鄭玄曰:方,放,謂放棄教命。 圯族,謂破壞同類[4]171,由此可以得到一個(gè)信息:共工和鯀都沒有友好地與其他文化群體聯(lián)合。 《尚書·洪范》:“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4]89,意思是:天乃賜予禹九種治國(guó)大法,常理所以被規(guī)定。 即使去掉神化色彩,由此亦可得到一條信息,即禹能夠合理地處理各個(gè)文化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使他們團(tuán)結(jié)在一起,因?yàn)椤皣?guó)”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文化群體,而且這“許多不同的文化群體”應(yīng)是處于一種和平團(tuán)結(jié)狀態(tài),否則,就不會(huì)說天乃錫禹洪范九疇。 據(jù)此,可以提出一個(gè)猜想:在治水的過程中不同的文化群體得以聯(lián)合,而且聯(lián)合體是愈來愈大,現(xiàn)在證明這個(gè)猜想是正確的。
《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記共工氏治水“雍防百川,墮高堙庳……,而鯀則稱遂共工之過。 故有鯀作城”[10]122,由此說明在治水過程中,共工氏所在的文化群體與鯀所在的文化群體得到聯(lián)合,否則鯀又怎么能學(xué)到他們治水的方法呢,又為何要贊成他們呢? 纂就前緒遂成考工[11]234,說明禹是在鯀的基礎(chǔ)之上而取得治水的成功的,但是,鯀不是禹的父親,把鯀當(dāng)作禹的父親只是古人把無限長(zhǎng)的歷史過程濃縮化而產(chǎn)生的一種對(duì)有承繼關(guān)系的人物的一種處理方法。 由引文中可見出:(1)治水的歷史源遠(yuǎn)流長(zhǎng);(2)共工、鯀分處于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依蘇秉琦先生的歷史劃分規(guī)則,則大致為:共工屬古城階段,鯀屬古國(guó)階段,而禹則為方國(guó)階段,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可能是以古國(guó)階段為始;(3)共工、鯀治水都有所成就,因而在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里為人們所運(yùn)用,所以有《天問》中對(duì)鯀的同情:“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4)因所處歷史階段不同,所面對(duì)的歷史問題也不同:共工為本部落(古城)解除洪水災(zāi)患,鯀則為本聯(lián)盟(古國(guó)),而禹則為方國(guó)(許多古國(guó)的聯(lián)合體)。 故能真正徹底消除災(zāi)禍的是屬禹的方法,“導(dǎo)”法。
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禹是鯀所在的文化群體中的一員,而且鯀是禹的前輩。 必須說明的是,當(dāng)文化尚處于口頭傳播時(shí)期,而且人群的分布是相對(duì)地疏散、獨(dú)立,那么帶來的一個(gè)結(jié)果是某一文化群體的神化了的祖先的事跡只有靠此文化群體本身的延續(xù)、發(fā)展而得以流傳,而其歷史地位亦是唯一決定此文化群體的相對(duì)的社會(huì)地位。 推而廣之,任何一文化群體的文化成果之所以得以流傳,亦是因?yàn)榇宋幕后w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不同的是,其中非宗教性的成分還可由其他群體傳續(xù)下去。 這應(yīng)是解讀上古史的關(guān)鍵。 “河海應(yīng)龍? 何盡何歷?”“焉有虬龍,負(fù)熊以游?”[11]96助禹治水的是“應(yīng)龍”,鯀死后化作黃熊,由“虬龍”負(fù)之而游。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又是融合其中的各個(gè)文化群體的圖騰按一定的規(guī)則在漫長(zhǎng)的歷史過程中滾雪球般形成的。 聞一多先生認(rèn)為:龍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態(tài)卻是蛇,……它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 李澤厚《美的歷程》:這里所謂“其神皆人面蛇身”,實(shí)則指這些眾多的遠(yuǎn)古氏族的圖騰符號(hào)和標(biāo)志[13]8。 本文認(rèn)為從這里可得出的信息:龍乃是眾多的不同的文化群體聯(lián)合而產(chǎn)生的一個(gè)象征物,一個(gè)符號(hào)。 如果從歷史的動(dòng)態(tài)的過程來看,應(yīng)該看出不同的龍緣于組成部分的變化。
那么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里的“應(yīng)龍”“虬龍”正是“漫長(zhǎng)的歷史過程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兩個(gè)不同階段的圖騰,于是,便可以由此圖騰的構(gòu)成見出這兩個(gè)不同階段的聯(lián)合體的成分的多與少。 “應(yīng)龍”,王逸《章句》“有翼曰應(yīng)龍”,“虬龍”,無角之龍[11]67。 由此,結(jié)果只能是禹時(shí)所處的文化群體處于一個(gè)比鯀時(shí)所處的文化群體大得多的聯(lián)合體的中心位置,因?yàn)椤皯?yīng)龍”是幫助禹治水的。 同時(shí),禹的親身經(jīng)歷也可證明他在治水的過程中不斷地聯(lián)合、吸納不同的文化群體:“禹之力獻(xiàn)功降省下土,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tái)桑?”[12]136-137至此,可以得出一個(gè)明確的結(jié)論:在治水的過程中,許多不同的文化群體聯(lián)合起來,只不過因?yàn)闅v史距離太遙遠(yuǎn),所以只有其中幾個(gè)最閃光的點(diǎn)把它們的光彩透過重重的歷史迷霧射到我們的眼前。
再來考察一下治水方法的流變。 在《尚書·堯典》中,共工方鳩,意即防救。 《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昔共工欲雍防百川,兩相映照,可以得出共工氏的治水方法是“堙”法。 具體的措施則是雍防百川,墮高堙庳。“墮高”就是把高地鏟平。 “堙庳”就是把低地培高,在大致平坦的地面上修筑堤防。 依徐旭生先生的說法:筑土圍子,即筑堰,鯀則是稱遂共工之過(《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即贊成推行共工氏的治水方法。 于是《尚書·洪范》 鯀堙洪水,其具體的措施是鯀作城[14]03。 由此可以得出結(jié)論:共工、鯀都是用“堙”法治水。 《尚書·堯典》:共工方鳩功,……僉曰:于,鯀哉![4]16這說明他們的治水都曾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取得過成功,否則《天問》中就不會(huì)有“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11]152這一問。《尚書·皋陶謨》:“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14]18。”《國(guó)語(yǔ)·周語(yǔ)下》:“高高下下,疏川導(dǎo)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高高下下”:順著自然條件改造,高的地方培修它使之更高,低的地方疏通它使之暢通。 “鐘”是聚的意思,聚蓄水潦就可以養(yǎng)魚蝦,種菱茨,為人民所利用,所以說是豐物。 “封崇九山”韋昭注:“封”,大也,“崇”,高也,除其雍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 “決汨九川”韋昭注:“汨,通也”。 這是說把壅塞的川流決通。 “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澤、藪”二字意義很近,……大致說起,“澤”與湖泊一類,“藪”與沼澤一類,“澤”水大,陂鄣起來,使它不致漫溢。 “藪”水少,有水可以養(yǎng)魚鱉,有沮洳可以種蒲葦,有陸地可以走麋鹿,所以說“豐殖”,這是陂鄣疏導(dǎo),使水不為患,反而為民利的工作[14]19。
兩相對(duì)照,得出禹治水的方法是疏通水道,雖然有對(duì)前人(共工、鯀)的經(jīng)驗(yàn)的吸取,但是,所有的具體措施都是在為一個(gè)中心思想服務(wù),即讓水走自己的道,人只是把它的道予以疏通。 在此精神的指導(dǎo)下,才有了因地制宜的高高下下,疏川導(dǎo)滯……的決定,所以,一言以蔽之,“導(dǎo)”。 本文認(rèn)為寫作“道”更好。因?yàn)椤暗馈笔瞧浔咀?更顯出是水自行其道,但是無論“導(dǎo)”或“道”都是在水本有道的情況下,給予幫助,而不是給水以前所未有的“道”。 之所以如此說,是因?yàn)樗辣緛砭陀?只是淤塞不通了。 鯀是以人為中心去強(qiáng)制水,而禹則是與水和平共存,讓它自然地走自己的道,人只是適當(dāng)?shù)貛椭柰ú粫惩ǖ牡蓝选?/p>
那么,為什么會(huì)有這樣的不同呢? 即何續(xù)初繼業(yè)而厥謀不同? 答案只能是聯(lián)合體在不斷地?cái)U(kuò)大。 那么,為什么有了大的聯(lián)合體就會(huì)有完全不同質(zhì)的方法呢? 因?yàn)楦鱾€(gè)文化群體作為單一的個(gè)體,與此時(shí)的眾多文化群體的聯(lián)合而形成的聯(lián)合體,從本質(zhì)上講是兩個(gè)不同的事物。 于是,由個(gè)體出發(fā)的經(jīng)驗(yàn)無法解決聯(lián)合體要面對(duì)的問題,因?yàn)闊o論有多少個(gè)有限相加都終究得不到一個(gè)無限。 因此,在聯(lián)合體形成以后,必須有認(rèn)識(shí)上的飛躍,來適應(yīng)新問題的需要。 接下來,我們來尋找激發(fā)飛躍的條件。
單一群體的本位主義,會(huì)導(dǎo)致只思考自己的利益,而不及其余,在治水上的表現(xiàn),便是“抽刀斷水”式的“壅防”。 這種方法帶來的結(jié)果是,雖然單一的文化群體的利益得到了保護(hù),但是水卻以更大的力量去侵吞其他群體的利益,以至于禍害天下。 然而,這一切卻是這一群體不會(huì)考慮的,于是,單一群體的經(jīng)驗(yàn)就只能是水可以被切割的。
聯(lián)合體一經(jīng)形成以后,思考聯(lián)合體利益的少數(shù)精英分子卻再也不能如此看問題,因?yàn)楸仨氁櫦奥?lián)合體中的每一個(gè)成員[15]112。 于是,聯(lián)合體必須在一種全局性利益的指導(dǎo)下治理洪水,從而認(rèn)識(shí)到所面對(duì)的是全聯(lián)合體區(qū)域內(nèi)的洪水,而不是單一群體所面對(duì)的一小段。 但是,或許是其時(shí)的聯(lián)合體還處于一定的階段,尚沒有大到足以改變?nèi)藗儗?duì)水的認(rèn)識(shí),或許是因?yàn)榱?xí)慣的勢(shì)力太強(qiáng)大了,人們還是用舊思想來尋求對(duì)新事物的解釋。 總之,出現(xiàn)了人們自以為正確的“有限的有限次相加等于無限”的奇怪現(xiàn)象(說到底是沒有“無限”的概念)。 于是,鯀治水仍是用“堙”法,只是因?yàn)槿硕鄤?shì)眾變成了“作城”。 然而,水畢竟不是可任意宰割的,于是,一朝“震怒”,毀其“九載”之“績(jī)”。
這一怒,震爍千古,終于迫使為聯(lián)合體利益運(yùn)籌帷幄的人們不得不重新認(rèn)識(shí)洪水。 于是,就出了以新的面貌治水的大禹。 他首先做的是什么呢?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14]22。 在總覽了大而復(fù)雜的形勢(shì)以后,他才有了如何治水的決定: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14]73。 至此,我們可以回答“何續(xù)初繼業(yè)而厥謀不同”的原因是無論共工,還是鯀的治水都沒有跑遍萬水千山去總覽水情。
那么“總覽水情”給禹帶來了什么呢? 我們認(rèn)為“總覽”給禹帶來了認(rèn)知革命。 他終于認(rèn)識(shí)到水像人一樣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不可宰割的,于是人們所能做的便是讓它走自己的“道”,幫助它疏通淤塞的道,于是“導(dǎo)”法就出場(chǎng)了。
為什么說這是認(rèn)知革命呢? 這是因?yàn)?(1)認(rèn)知視角由局部的變?yōu)槿值?(2)認(rèn)知態(tài)度由人與自然的對(duì)立變?yōu)槿伺c自然的和平;(3)認(rèn)知的對(duì)象由無生命的可宰割的物體變?yōu)橛猩牟豢稍赘畹奈矬w,有其自己的行動(dòng)規(guī)則(道)的生命體;(4)認(rèn)知方式由以認(rèn)知主體為中心的,以主觀意愿為基礎(chǔ)的主觀想象型變?yōu)橐哉J(rèn)知對(duì)象為中心的,以柔順對(duì)象的運(yùn)動(dòng)為基礎(chǔ)的主體涵泳型;(5)認(rèn)知結(jié)果由視萬物為無生命的、可隨意宰割的、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變?yōu)橐暼f物為有生命的、有各自意志的(即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不可隨意宰割的、以萬物與人和平共存的世界觀。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第二個(gè)結(jié)論:治水給當(dāng)時(shí)的精英分子帶來了認(rèn)知革命,使他們能夠認(rèn)知到世界上的萬物都是有生命的,像人一樣,都有各自運(yùn)動(dòng)的規(guī)律(道),從而建立起人與自然界的萬物和平共存的關(guān)系。 正是在此基礎(chǔ)上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才出現(xiàn)了后來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中主流哲學(xué)的核心思想的兼融精神。中國(guó)武術(shù)“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應(yīng)是由此產(chǎn)生并發(fā)展出來的。
這里要討論的是,為什么是治水而不是農(nóng)耕喚醒了人們?nèi)f物有道的意識(shí),從而為中國(guó)人得出“天道”的觀念打下了第一塊基石? 這問題的論證可以采取層層剝筍的方式,由問題的分析入手,層層逼近答案。喚醒人們“萬物有道”的意識(shí),就必須讓人們知道萬物有靈,萬物都有生命,都是活的生命體。 因?yàn)橹挥邢袢艘粯拥纳w才會(huì)有目的的行動(dòng),有了有目的的行動(dòng),才會(huì)有“道”,而且亦只有當(dāng)其如人一樣的有行動(dòng),有行動(dòng)之道,才會(huì)喚醒人對(duì)它重新認(rèn)識(shí)的意識(shí),從而打消人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觀念,才會(huì)建立起一個(gè)人與萬物和平共存的世界觀。 于是,問題就轉(zhuǎn)化為“如何才能讓人意識(shí)到萬物是有靈的,有生命的,像人一樣會(huì)有‘道’的生命體”。 很顯然,問題的重心是,如何才能讓人意識(shí)到看上去不是有生命的事物卻是有生命的生命體,并且像人一樣的有自己的“道”的生命體;因?yàn)楸緛砭捅豢闯墒怯猩氖挛?是無法使人類把“有生命的事物”這個(gè)概念的外延與內(nèi)涵作任何改變的。 而且,這些早被看作生命體的事物,都無法向人表明它是像人一樣的。 于是,我們的目光自然應(yīng)該投向那些本被看作是無生命的物體。 因?yàn)橹挥袩o生命的物體才會(huì)出現(xiàn)令人震驚的現(xiàn)象使“有生命的事物”這個(gè)概念的外延與內(nèi)涵有所改變。 于是,問題就又轉(zhuǎn)化為“農(nóng)耕文化群體的環(huán)境中會(huì)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嗎?”。 結(jié)果可能是否定的。 這是因?yàn)?(1)農(nóng)耕文化群體的認(rèn)知是在分割的時(shí)間和分裂的空間里被實(shí)現(xiàn)的,依自然規(guī)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便被碎切成了無數(shù)個(gè)片段,連續(xù)地、均勻地散布在時(shí)間的流程里;每個(gè)片段,細(xì)小到無法覺察;再加上是處于空間的一隅,于是,不會(huì)有把時(shí)間上的細(xì)微變化轉(zhuǎn)變?yōu)榭臻g上的明顯變化的機(jī)會(huì);所以,不會(huì)出現(xiàn)能震撼人的心靈,使之重新審視世界的現(xiàn)象;(2)更沒有外在的力量強(qiáng)迫他們改變這種認(rèn)知活動(dòng)的方向。 這里之所以說是“日常農(nóng)耕文化群體的環(huán)境”,是因?yàn)楹樗m是農(nóng)耕環(huán)境中才會(huì)出現(xiàn)的,但是它屬于災(zāi)患,是特殊環(huán)境而不屬日常環(huán)境。 于是,我們只能把最后一絲希望投向無邊的天空,因?yàn)樗侨藗儫o法分割的物體,而且上古的農(nóng)業(yè)是必須靠天時(shí)才會(huì)有所收獲的,于是,合理的想象是農(nóng)耕文化群體必然在很早的時(shí)候就會(huì)把“天”看作是一個(gè)有生命的主宰,而且不時(shí)地祭祀,祈求好的收成。 但是結(jié)果卻是讓人失望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這種自給自足式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里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是農(nóng)耕,主要的期盼是豐收,主要的儀式是農(nóng)業(yè)祭,農(nóng)業(yè)生活與農(nóng)業(yè)祭在中國(guó)五千年史上一直不失其主要地位。 但在那有史可考的最早的華北農(nóng)村(仰韶期的農(nóng)村)里,祈年祭是我們從考古學(xué)上可以看到的唯一重要祭祀,在歷史上祈年祭稱為“社祭”。
社祭的對(duì)象是什么呢? 因?yàn)榇蟮厣a(chǎn)魚、獸與農(nóng)作物,與婦女產(chǎn)子屬于同一范疇的事件,因此“祈豐祭“(不論是獵獸、漁魚,還是種田)就常以土地之神為祈求的對(duì)象,并以婦女或其生殖器為繁殖的象征”[4]66。 于是仰韶期的農(nóng)村里最要緊的儀式是祈豐收,拜土地。
到了龍山期,情況又是如何呢? 一言以蔽之,龍山期的宗教儀式,除了社祭而外,出現(xiàn)制度化的祭祖與專業(yè)性的巫師。 祭祖(祖先崇拜)產(chǎn)生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乃是由于龍山期逐漸放棄了仰韶期的游耕方式,而采用定耕的方法[16]77。 這就是說,是土地的原因,而不是上天的原因,才出現(xiàn)了這種現(xiàn)象,而且其祭祀對(duì)象是祖先,目的是親族團(tuán)結(jié)和親族繁殖旺盛。 由此,我們失望了,他們沒有把天看作是一個(gè)有生命的主宰。 于是,最后的結(jié)論只能是,農(nóng)耕社會(huì)人們不可能產(chǎn)生“萬物有道”的觀念。 這里必須補(bǔ)充說明的是:(1)就算有了“把天看作是一個(gè)有生命的主宰”,也不可能有“萬物有靈”乃至“萬物有道”的發(fā)現(xiàn),只可能出現(xiàn)人格神的宗教崇拜。 (2)為何大地有靈卻產(chǎn)生不出“萬物有道”的觀念,我們認(rèn)為這或許是因?yàn)榇蟮乇旧淼奶攸c(diǎn)所致:因?yàn)椤暗馈钡谋举|(zhì)在于“行”得“通”,如果連“行”都沒有,就更不可論“通”了,而大地的本質(zhì)特點(diǎn)乃是“靜”“處柔”“為而不恃”“成功而弗居”……所以極難得出大地有道的認(rèn)識(shí)。
再來看洪水,它的突發(fā)性、災(zāi)害性,必然會(huì)引起人們的震驚和行動(dòng)。 雖然人們依于慣例把他當(dāng)作是無生命的,隨意地宰割它,但是它卻用無窮的力量擊退了這種進(jìn)攻,從而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在從鯀的失敗到禹的成功的漫長(zhǎng)的過程中,它總是以巨大的力量裹挾著人們,迫使人們“涵泳”其中,經(jīng)過無窮歲月的“體察”,人們終于認(rèn)識(shí)到了它是像人一樣有生命、有自己的行動(dòng),有自己的道。 于是,人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為它疏通淤塞的道路,讓它走自己的道(這就是禹的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這里的“決”“濬”都是疏通的意思),從而達(dá)到和平共存。 但是這個(gè)發(fā)現(xiàn)的意義卻不在于此,而在于從根本上擊碎了人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信念,從而帶來了認(rèn)知革命,使這個(gè)世界變成一個(gè)人與萬物和平共存的世界。 當(dāng)人們終于認(rèn)識(shí)到“天道”的存在,以它來涵攝萬物之道時(shí),人與萬物融合的宇宙觀的出現(xiàn)就成為可能了。 當(dāng)人們終于認(rèn)識(shí)到任何人都能且僅能奉“天道”而行的時(shí)候,人類社會(huì)兼融精神的出現(xiàn)就成為可能了。 所以說,洪水強(qiáng)大的力量裹挾著那些精英分子在治水的過程中實(shí)現(xiàn)了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從而為中國(guó)文化精神的形成打下了第一塊基石。
三、結(jié)語(yǔ)
如果說是勞動(dòng)創(chuàng)造了人類,那么本文探討得出的農(nóng)耕和治水所催生的兼融精神則是中華文化的原初基因,是上下五千年歷史流變、演繹出來的千門萬類的各種亞文化的母體基因,當(dāng)然,也是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之始基。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bào)告中六次提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出“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得到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17]。 作為中國(guó)國(guó)粹的武術(shù)文化,是中華民族傲視世界民族之林的獨(dú)特的文化創(chuàng)造,是祖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蘊(yùn)含和承載著極其豐富的中國(guó)文化精神。 “闡發(fā)祖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服務(wù)新時(shí)代”,這是文化自信自強(qiáng)建設(shè)的應(yīng)有之義。 追溯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精神之源起,秉承“文化自覺”之精神,旨在“知往”以“察今”,在歷史追溯中挖掘智慧,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武術(shù)文化新時(shí)代的豐富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