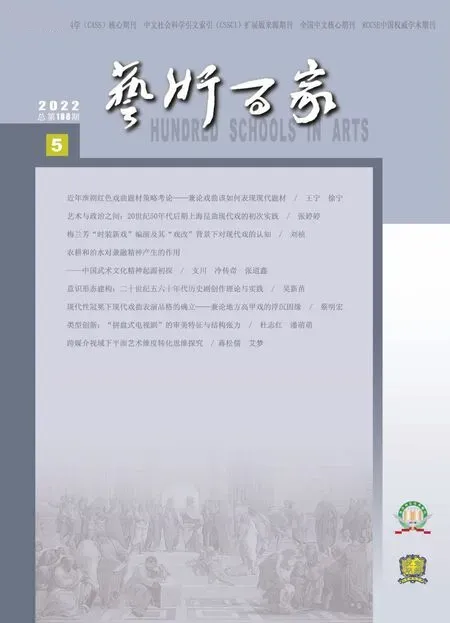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劇創(chuàng)作理論與實踐?
吳新苗
(中國戲曲學(xué)院 戲曲研究所,北京 100073)
“一定的文化(當(dāng)作觀念形態(tài)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jīng)濟”[1]663-664,毛澤東對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深入而辯證的闡述,深刻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化藝術(shù)工作的實踐。 戲曲作為當(dāng)時最受大眾歡迎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同樣被納入新政權(quán)的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工作,接受改造和重塑,新編戲曲的創(chuàng)作,更是受到這一原則的制約。 相較于和現(xiàn)實有著天然聯(lián)系的現(xiàn)代戲,新編歷史劇如何通過歷史題材內(nèi)容體現(xiàn)出“新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成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劇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批評的核心話題,時人見仁見智,有各種嘗試,也有很多爭論。 本文即以此為視角,既討論歷史劇在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又揭示歷史劇因此遭遇的問題。
一、從“反歷史主義”談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戲曲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現(xiàn)象,即“當(dāng)處理歷史題材和古代民間傳說的時候,把許多只能產(chǎn)生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現(xiàn)代來,加以牽強附會的比擬,或是把只能產(chǎn)生于今天的觀念和感情,勉強安放到古代人物的身上去”[2]。 例如:《玉堂春》中的蘇三最后鬧起了革命;許仙參加起義軍并殺死法海,帶領(lǐng)白娘子一起上山落草;鄭里(真理)老人教牛郎織女勞動,宣傳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反歷史主義”。
其實,這種情況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只是在20 世紀50 年代初表現(xiàn)得更為集中,楊紹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 他在1950 年至1951 年期間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新天河配》《新大名府》《新白兔記》《愚公移山》等多部新編歷史劇、神話劇,在這些作品中,他不僅大搞鴿子象征和平、鴟鸮象征美帝國主義等種種影射,還在《水滸傳》《白兔記》等傳統(tǒng)故事中加入不符合史實的民族戰(zhàn)爭內(nèi)容,以及婦女解放、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現(xiàn)代思想意識。 楊紹萱時任文化部戲改局副局長,是戲改的主要領(lǐng)導(dǎo)者之一,在業(yè)界具有很大影響力,因此他作為“反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艾青、何其芳、光未然、阿甲等人的猛烈批評。 以最基本的文學(xué)常識看來,“反歷史主義”這種混淆古今的創(chuàng)作顯得非常幼稚可笑,實在不值一批。 但吊詭的是,楊紹萱在受到批評后反而理直氣壯地堅持己見。 艾青的批評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楊紹萱給該報連寫三封信進行質(zhì)問,并發(fā)表《論“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危害性——評艾青的〈談“牛郎織女”〉》為自己辯護,這引來了更多的批評。 《人民日報》的一篇綜述中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收到了批評楊紹萱的“來稿、來信二百七十三件”①。 “反歷史主義”成為眾矢之的,楊紹萱被罷免職務(wù),逐出了戲改領(lǐng)導(dǎo)層。
楊紹萱那些為自己辯解的文字,并非完全意氣用事,而是相當(dāng)清晰地折射出當(dāng)時新意識形態(tài)的巨大威力。 “現(xiàn)在要依據(jù)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處理我們的歷史劇,從內(nèi)容到形式,就應(yīng)以反映中國社會發(fā)展史為主要任務(wù)”[3]41,楊紹萱將反映中國社會發(fā)展史作為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主要任務(wù),這與新政權(quán)成立伊始普遍展開的政治學(xué)習(xí)是一致的。 當(dāng)時,政府通過各種報刊、書籍、宣傳標語和學(xué)習(xí)班,在全社會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而其中最關(guān)鍵的是關(guān)于社會發(fā)展史的學(xué)習(xí)。 艾思奇在一篇談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的文章里指出,“只求經(jīng)過社會發(fā)展史——歷史唯物主義的學(xué)習(xí)中,較有系統(tǒng)地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1)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的思想;(2)階級斗爭的思想;(3)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xué)說。 掌握了這些基本的觀點,許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問題就往往能夠自己迎刃而解。由此進一步,不論是參加工作,或繼續(xù)更深入的學(xué)習(xí),都有很大的便利”[4]35。 在全國各地舉行的藝人講習(xí)班中,社會發(fā)展史是一門必開的課程,講授關(guān)于勞動、階級、國家等歷史唯物主義知識。 楊紹萱將歷史劇創(chuàng)作完全當(dāng)作了一次次社會發(fā)展史的課堂教學(xué),當(dāng)作了對現(xiàn)實中民族戰(zhàn)爭和階級斗爭進行宣講的教材。 所以,他批評反對者是“為了神話而神話”,是“打擊了抗美援朝戲曲工作者,幫助了杜魯門”,并認為反對者“引出了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什么思想在支配著戲曲文藝運動,這就關(guān)系了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問題”②。 在楊紹萱看來,自己通過戲曲宣傳勞動創(chuàng)造了世界、歌頌民族革命、支持婦女解放、提倡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領(lǐng)導(dǎo)戲曲文藝運動的表現(xiàn),掌握著無可置疑的真理,所以他理直氣壯地批評反對者。 這種極端自信也來自他在延安時期獲得的榮光,即作為《逼上梁山》的主創(chuàng)者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這讓楊紹萱產(chǎn)生了以“戲劇革命者”自居的心態(tài)。 事實上,《逼上梁山》本身就是一部帶有“反歷史主義”印記的作品,在楊紹萱的回憶中,延安觀眾“看戲變成了上課,有的同志一邊看戲一邊記筆記”[5]18,這一幕仍歷歷在目,當(dāng)年通過戲曲來宣傳馬列主義,今天為何就不行呢?
問題出在他將《逼上梁山》中已經(jīng)初見端倪的“反歷史主義”發(fā)展到了更加突出、更加不協(xié)調(diào)的地步:用老牛和破車結(jié)婚來喻示勞動工具對人民生活的決定性作用,太過荒唐;盧俊義的妻子賈氏在燕青和春梅(代表奴隸階級)的影響下,認識到丈夫參加民族革命的進步意義,從而也轉(zhuǎn)變過來,和盧俊義和好如初。 這樣通過改寫流傳久遠的經(jīng)典故事來闡釋現(xiàn)實中的政治意識,“不但是破壞了民族文化的遺產(chǎn),也是把我們當(dāng)前的政治斗爭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2]。 楊紹萱不斷在戲曲中圖解一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用力過猛,顯得滑稽可笑,從而走到其動機的反面,不但談不上藝術(shù),而且沒有起到他所追求的意識形態(tài)宣教效果。
艾青等人對楊紹萱及其“反歷史主義”劇作進行批評,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戲曲藝術(shù),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厘清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方式從而使其更為有效,因為“反歷史主義”不僅不能起到建構(gòu)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反而以其滑稽可笑的方式破壞了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gòu)。 怎樣才是有效的方式呢? 馬少波在1951年撰寫的一篇文章里,清算了“反歷史主義”“不尊重歷史條件,歪曲歷史真實,將歷史人物現(xiàn)代化,把歷史事跡與現(xiàn)代人民革命斗爭的事跡作不適當(dāng)?shù)念惐取钡淖龇?同時指出“單純的無批評的強調(diào)‘歷史真實’”也是不對的,要“把歷史的真實與對于今天現(xiàn)實的影響與作用,有機的聯(lián)系與統(tǒng)一”。[6]1這就是后來歷史劇創(chuàng)作中廣為遵循的“古為今用”原則。 概言之,在對“反歷史主義”的批判中,“古為今用”作為一個有效的方式和原則被確定下來。 但,什么是“歷史真實”? 歷史劇怎樣才算發(fā)揮了對現(xiàn)實的影響與作用? 兩者又如何有機聯(lián)系與統(tǒng)一? 人們的認識并不統(tǒng)一,這就使得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理論與實踐陷入長期爭論中,莫衷一是。 更發(fā)人深思的是,盡管“反歷史主義”在20 世紀50 年代初就遭到大規(guī)模徹底批判,但這種傾向一直是此后歷史劇創(chuàng)作中最為難纏的頑疾之一,這不能不讓人推測,“反歷史主義”或許就是強化歷史劇意識形態(tài)功能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
二、題材選擇和人物形象塑造
為了發(fā)揮歷史劇對現(xiàn)實的積極作用,做到“古為今用”,劇作家首先要考慮好歷史劇的題材。 “我們自己的民族的過去事物必須和我們現(xiàn)代的情況、生活和存在密切相關(guān),它們才算是屬于我們的。”人們經(jīng)常援引黑格爾的這番話,作為歷史劇題材選擇的理論依據(jù),并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只有那些與現(xiàn)實生活緊密聯(lián)系、與時代精神息息攸通的歷史題材或歷史生活,才能揭示出積極的思想意義。”[7]71而在當(dāng)時以各種運動形式進行國家治理和民眾思想改造的時期,政治運動和政策條文成為現(xiàn)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的主要內(nèi)容。 因此,能夠與當(dāng)下政治運動、政策條文產(chǎn)生聯(lián)系,或有一定相似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就勢必成為歷史劇創(chuàng)作者的首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xiàn)了兩次歷史劇創(chuàng)作高潮,都體現(xiàn)出這種題材選擇的規(guī)律。 第一次在“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運動時期,以京劇《唇亡齒寒》(朱慕家、王頡竹合編)為代表,出現(xiàn)了很多“假道伐虢”題材的歷史劇。 信陵君竊符救趙、六國聯(lián)合對抗暴虐強秦的故事,也成為劇作家樂意選擇的題材,華粹深《竊符救趙》是此類代表。 據(jù)馬少波統(tǒng)計,同時出現(xiàn)的信陵君題材劇作有十七種之多。 第二次在1959 年至1962 年期間,由于中蘇交惡,國家強調(diào)發(fā)奮圖強、自力更生,同時因毛澤東發(fā)表關(guān)于“海瑞精神”的講話,鄧小平提出“編一點歷史戲,使群眾多長一點智慧”的倡議,歷史劇劇作噴涌而出。 該時期有寫民族戰(zhàn)爭中英雄人物的劇作,如《滿江紅》《金山戰(zhàn)鼓》《澶淵之盟》等;寫歷史上有進步意義的君王,如《則天皇帝》《臥薪嘗膽》之類;寫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如《唐賽兒》;寫歷史上的清官,如《海瑞上疏》《海瑞罷官》《強項令》。 其中臥薪嘗膽題材有上百個劇團競相上演,其他像岳飛、武則天、海瑞也成為比較熱門的題材,每個題材出現(xiàn)過兩種以上的作品。
題材雷同是頗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除了這些題材比較適合現(xiàn)實中的政治運動、政策條文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劇作家為盡量避免題材選擇錯誤,于是產(chǎn)生了一種從眾心理。
歷史劇以歷史人物為主角,所以選材時首先要考慮如何評價歷史人物。 20 世紀50 年代初,對電影《武訓(xùn)傳》的大批判使得關(guān)于歷史人物的評價變得極為敏感,甚至導(dǎo)致對一些在民間千百年來為人們所贊美的歷史人物進行批判的不良風(fēng)氣,甚至包公、岳飛等都遭到了基于階級屬性的批判。 雖然這種不良風(fēng)氣很快得到糾正,但人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仍然小心翼翼,這導(dǎo)致較長時間里以真實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歷史劇創(chuàng)作比較稀少。 1959 年1 月,郭沫若發(fā)表《談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一文替曹操翻案,引起了關(guān)于歷史人物評價的大討論,逐漸形成歷史界關(guān)于人物評價標準的共識,除了階級標準之外,“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標準是看其在歷史上人物的作用”[8]27。 以歷史的眼光,考察人物在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將階級出身、歸屬作為評價人物的唯一標準。 往往是領(lǐng)導(dǎo)人肯定過的,或史學(xué)界充分討論過并有定論的,或翻案了的歷史人物,才能成為歷史劇的主角。 這成為劇作家規(guī)避錯誤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模式,因此導(dǎo)致歷史劇題材的高度雷同。
與此相關(guān)的是人物形象塑造。 已經(jīng)得到新意識形態(tài)認可的歷史人物及其故事,優(yōu)先被選為歷史劇的題材,但具體這個歷史人物怎么塑造,仍然會令作者大為撓頭。 這里會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傾向。
一種是徹底美化歷史人物。 歷史劇創(chuàng)作之初就是為了體現(xiàn)“時代精神”,劇作家通過塑造正面的歷史人物來宣傳民族戰(zhàn)爭中的愛國主義精神、艱苦卓絕的奮斗精神、反壓迫的戰(zhàn)斗精神以及為民請命的公仆精神,以實現(xiàn)其現(xiàn)實意義。 歌頌歷史人物就是歌頌時代精神,所以被歌頌者就不能有缺點。 比如大量《臥薪嘗膽》同名劇作,基本都刪除了西施這條線索,即使保留了西施這個人物,她也不再是越國派去的奸細,而是一個被擄的越國少女。 范鈞宏《臥薪嘗膽》原稿寫吳國索要美女,勾踐等遂將西施送去,劇中有西施離別前的抒情唱段,非常動人。 但后來范鈞宏聽說別人寫的西施都是被搶去的,他也把情節(jié)改成西施被搶去,唱段只好割愛。 人們不敢寫西施是被勾踐送給吳王的,因為那樣就使得勾踐成為一個陰謀家,而且,如果越國的復(fù)興事業(yè)中竟然有“美人計”的功勞,那在今天是否還值得歌頌就成了問題。 從這些人物形象塑造的細節(jié)處理上,我們就能感受到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中劇作家面臨的巨大壓力。 范鈞宏當(dāng)時大吐苦水:
寫作過程中,就出現(xiàn)了這么一種現(xiàn)象:在虛構(gòu)故事情節(jié)上,膽子很大;在描寫勾踐性格上,膽子很小。 我們怕犯錯誤,因而也不敢教“勾踐”犯錯誤。 自己的顧慮和別人善意的提醒,形成了清規(guī)戒律:忍辱負重要削弱,復(fù)仇思想不能提,性格上的缺點要避免,策略性的斗爭方式別亂用,不太“正義”的不能寫,不符合今天政策的應(yīng)注意……如此這般,剩下來的就是表面“高大”,其實空虛,多少還有點今人思想的人物了。[9]88
為了避免觸犯各種“清規(guī)戒律”,劇作家們選擇按照現(xiàn)實中的政治標準、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來塑造(美化)歷史人物,從而讓人物形象符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 這種情況下,人物難免就高大空,還帶有現(xiàn)代人的色彩,嚴重些的就又滑入“反歷史主義”的窠臼,出現(xiàn)茅盾在他那部談歷史劇的長篇論文里所指出的各種“啼笑皆非的描寫”③。
但還有一種相反的傾向是在塑造人物時刻意添加“缺點”,以表明主人公的歷史“局限性”。 粵劇《寸金橋》描寫近代法國侵略廣州灣時,遂溪縣令李鐘鈺帶領(lǐng)鄉(xiāng)民與外國侵略者展開斗爭的故事。 在《毀村》《過營》《誓師》《逼界》幾場戲中,李鐘鈺作為民族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塑造,但作者為了表明李鐘鈺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局限性,在最后兩場戲中讓他變得軟弱起來,描寫李鐘鈺率先撤離了陣地,同時讓之前沒有太多鋪墊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陳耀邦成為領(lǐng)導(dǎo)斗爭的核心人物。 這樣一來,人物形象塑造就前后不統(tǒng)一,給人生硬割裂的不完整感。 劇作家如此寫,說到底還是怕犯錯誤,擔(dān)心因為沒有寫出歷史人物的局限性而受到批評。 的確有讀者、批評家拿著放大鏡尋找劇本中的各種問題。 比如京劇《滿江紅》中寫了兩個細節(jié):一是岳飛接到詔書后,仍然準備北渡抗金,直到十二道金牌傳來才作罷;二是岳飛在大理寺看到岳雷、張憲被綁,有一個意欲沖出去的動作。 有評論者認為這樣塑造岳飛形象,就沒有寫出一個無限忠于君王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人物的局限性。
這里問題來了,同樣是擔(dān)心政治上出錯,但有些歷史劇對主人公無限“美化”,有些卻要刻意增加“缺點”以顯示局限性,為何會出現(xiàn)兩種截然相反的傾向呢? 我們很難找到準確答案,該美化還是該刻意增加“缺點”,并沒有規(guī)律可循。 勾踐題材的劇作中也有刻意寫其缺點的例子,這類劇作通常是為了強調(diào)人民群眾才是越國復(fù)興的主要力量。 相同的是,無論“美化”還是刻意寫“局限性”都是為了契合意識形態(tài),這主要取決于劇作家考慮要從哪一方面契合。
也有一些論者認為寫歷史人物當(dāng)然不能不反映出歷史局限性,但“美化”是在歌頌中摒棄了所有局限性,而刻意寫缺點也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所謂寫出歷史人物的局限性,實質(zhì)上無非也就是說要寫出歷史人物的具體性。 什么時代說什么話,什么階級說什么話……局限性表現(xiàn)在歷史人物身上是具體的、整體的、貫串的,而不是抽象的、割裂的、孤立的”[10]25。他們希望劇作家真實地、完整地塑造人物形象,認為在這個過程中歷史人物值得歌頌的優(yōu)點和作為局限性的缺點,就自然而然呈現(xiàn)出來了。 這旨在讓劇作家在塑造人物時不要過多受到“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局限性”這些政治話語的影響,更不要在劇作中機械地、公式化地表現(xiàn)出來。 顯然,這種聲音是理性的,也符合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但在當(dāng)時實踐起來并不容易,更多的歷史劇仍然擺脫不了人物塑造時無限美化或割裂地刻意寫缺點的傾向。
三、人民群眾的力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1]1031,唯物史觀中,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因此歷史劇如何表現(xiàn)出人民的力量,從而體現(xiàn)人民在歷史創(chuàng)造中的作用,就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寫農(nóng)民起義的歷史劇中比較好處理(起義者就是人民群眾的一分子,這種題材本身就是要表現(xiàn)人民群眾的力量),但在寫統(tǒng)治階級英雄人物題材時讓劇作家大費周章。
比較常見的一種處理方法,是將人民群眾作為支持這些英雄人物的重要力量,劇中予以比較重要的角色,或有專門表現(xiàn)群眾的場面。 1950 年華粹深創(chuàng)作的《竊符救趙》堪稱這種模式的代表。 該劇主要表現(xiàn)信陵君、平原君、如姬等封建貴族為了國家利益抗擊侵略者的故事。 劇中出身守門小吏的侯嬴就是人民的代表,是他啟發(fā)了信陵君,讓后者知道抗秦不僅是為了兄妹之情,更是為了天下,所謂“秦師東來,我大梁亦難幸免,秦肆虎狼之心,有并吞天下之志,它必要掃平天下,然后甘心。 邯鄲如若為賊所陷,則天下永無和平之日,受害者豈止趙、魏兩國而已”[12]58。 侯嬴獻出如姬竊符的計策,讓朱亥幫助信陵君奪取軍權(quán),最終救了天下百姓,而自己卻獻出了生命。 這個人物沒有太多的戲,但是在他的推動下,信陵君的抗秦事業(yè)得以成功。 另外,在表現(xiàn)平原君毀家紓難,招募民軍以抗秦時,華粹深也專門寫了一場邯鄲百姓與平原君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群眾戲。 最后一幕,信陵君、平原君、如姬和趙魏兩國百姓齊聚侯嬴的墓前,祭拜他,“齊祝告成仁勇烈老英雄,多虧你獻計救蒼生……從此后齊心攜手享太平”[12]80。 從整個敘事上看,賢明的貴族階級的愿望與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他們齊心協(xié)力保衛(wèi)了國家,贏得了和平,這一構(gòu)思線索非常鮮明,呈現(xiàn)得也比較成功。 眾多寫越王勾踐的戲曲中,人民群眾同樣起到支持他、推動他發(fā)奮圖強的作用,但有些劇作過于強調(diào)人民群眾的作用,使勾踐這一主人公顯得非常軟弱。 本來代表人民群眾的人物形象并非最主要的角色,但過于強調(diào)人民群眾后“反客為主”,上面提到的粵劇《寸金橋》就是其中一例。
將人民群眾作為點綴,貫穿始終,這也是比較普遍的做法。 這里,人民群眾不是斗爭的重要力量,主要起到線索作用、襯托作用。 海瑞題材戲曲,皆屬于此種。 《海瑞上疏》中,嘉靖皇帝聽信道士之言,要修建玉芝壇,仙人巷的幾百戶人家失去安身之所,施象清、倪樹慶作為百姓的代表向海瑞訴說苦情,這是促使海瑞上疏的重要戲劇情節(jié)。 海瑞系獄,施象清等人“跪香請命”,表現(xiàn)了人民與清官之間的濃厚情誼。最后一幕更有象征意義,嘉靖皇帝去世后,海瑞官復(fù)原職,施象清等一眾百姓趕來迎接,天空飄起雨來,這時舞臺上撐起一把大傘,海瑞邀眾人避雨,感嘆道:“可惜我這把傘太小了。”施象清說:“有這樣一把,也就難得的了。”[13]51在群眾的襯托和別有意味的情節(jié)、臺詞的渲染之下,劇作點出海瑞是人民保護傘這樣的題旨。 《澶淵之盟》是一部基本沒有群眾的戲,但劇作家也不忘安排兩名唱小曲的村姑來點綴一下,通過她們的唱來贊美寇準抗擊金兵的歷史功績。 最后一幕,寇準罷相歸鄉(xiāng),還與兩位村姑話別。 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總是受到人民的熱愛,主題意蘊就在幾筆點綴中被四兩撥千斤地揭示出來。
將人民群眾作為主角來寫,讓他們直接參與斗爭,這種敘事模式比較少,因為這會影響對本來要著重贊美的歷史人物的塑造,甚至造成主題的不統(tǒng)一。也有處理得比較好的,評劇《鐘離劍》[14]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該劇同樣是寫勾踐發(fā)奮圖強的故事,但與其他同類題材構(gòu)思完全不同。 勾踐復(fù)國的主線上,鑄造兵器成為一個核心事件,于是精于鑄劍的鐘離泉老人成為重要人物,他隱藏于深山之中,為越國鑄造兵器,后又被吳國綁走,展開了與吳國君臣面對面的斗爭。他勇敢而機智,在此之前已經(jīng)將技術(shù)傳授給孫女素女,為越國最后獲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武器。 勾踐和鐘離泉祖孫的兩條線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表現(xiàn)了越國君民上下團結(jié)一致的愛國精神,同時也體現(xiàn)了勾踐在復(fù)國事業(yè)上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因此贏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終獲得了勝利。
關(guān)于在歷史劇中是否一定要出現(xiàn)人民群眾的問題,人們有針鋒相對的爭論。 這集中表現(xiàn)在對《淝水之戰(zhàn)》的批評中。 故事取材于前秦與東晉的一場名戰(zhàn),它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 作者為了表現(xiàn)人民的力量在這場戰(zhàn)斗中的重要作用,設(shè)置了耿義這樣一位義軍領(lǐng)袖,在關(guān)鍵時刻,他帶領(lǐng)農(nóng)民部隊給予前秦致命一擊。 沈起煒在《上海戲劇》上發(fā)表文章,認為歷史劇大都注意人民群眾的作用,“但是也似乎有一個套子,就是常常請義軍出場來解決問題”[15]33。 他指出劇作家在《淝水之戰(zhàn)》中設(shè)計耿義這樣的人物和相關(guān)情節(jié),并不符合歷史真實,因為沒有任何歷史記載表明此戰(zhàn)是由于義軍幫助才取勝的,而且在東晉時期農(nóng)民對莊園地主的依附性很強,無法形成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軍隊。 此后,《上海戲劇》發(fā)表了多篇討論文章,蔣星煜對沈起煒的觀點進行了批駁,認為史料上并非說東晉時期沒有起義軍,只是比較零星或者規(guī)模很小,歷史劇本身也可以對史料進行提煉加工,從而塑造典型。[16]25沈起煒對此又進行了反批評,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學(xué)家范文瀾編撰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編撰的《簡明中國通史》等根據(jù)現(xiàn)有史料分析淝水之戰(zhàn),認為前秦失敗是其內(nèi)部原因決定的,晉軍能同仇敵愾也是原因之一。 而另外增加起義軍,于史無征,而且在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下不一定有大規(guī)模的起義軍隊伍,所以,在“基本情節(jié)、主要人物及其活動,早已經(jīng)為人熟知”的情況下,《淝水之戰(zhàn)》這樣寫,弄得半真半假,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會導(dǎo)致歷史教育出現(xiàn)問題,中學(xué)生會以為淝水之戰(zhàn)是“幸得耿義領(lǐng)導(dǎo)的義軍相助”才取得勝利。 沈起煒也強調(diào)并非處處都要按照歷史基本情節(jié)來寫,“在采取歷史上的大場面為題材時,才有這個必要”[17]24。 接著,唐真、寧富根等人也加入討論,分別支持沈、蔣二人的觀點。 寧富根堅持認為“應(yīng)該從人民群眾本身來突出人民群眾的作用,而不是借助于人民群眾以外的任何形象力量”[18]17。 另一方則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任何階段的歷史現(xiàn)實總會出現(xiàn)能反映人民意志的人物。重申值得歌頌的英雄人物,本身就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意愿,岳飛、韓世忠、楊家將這些人雖然在帝、王、將、相之列,但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起到了領(lǐng)導(dǎo)和指揮人民的作用。 是否要直接寫人民群眾,應(yīng)該由題材決定,而不能為了反映人民群眾而違背歷史真實。[19]26
顯然,只有直接表現(xiàn)人民群眾,才算貫徹了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物史觀的說法,非常荒謬。 但在當(dāng)時,這種觀點卻比較常見,按照這種觀點創(chuàng)作的劇作家也不在少數(shù)。 這不但破壞了劇作藝術(shù)的完整性,造成不必要的枝節(jié),而且正如沈起煒所說,這種虛構(gòu)偏離了歷史真實。
四、歷史真實
隨著歷史劇創(chuàng)作興盛,關(guān)于歷史劇的理論批評也繁榮起來。 歷史學(xué)家吳晗在1960 年12 月25 日的《文匯報》上發(fā)表《談歷史劇》一文,引起了關(guān)于歷史劇的大討論。 此后,吳晗又陸續(xù)寫了《再談歷史劇》《論歷史劇》等多篇討論文章,但仍沿襲了《談歷史劇》中的主要觀點。 其核心論點是:
歷史劇必須有歷史根據(jù),人物、事實都要有根據(jù)。 歷史劇的任務(wù)是反映歷史的實際情況,吸取其中某些有益經(jīng)驗,對廣大人民進行歷史主義愛國主義教育。 人物、事實都是虛構(gòu)的,絕對不能算歷史劇。 人物確有其人,但事實沒有或不可能發(fā)生的也不能算歷史劇。 ……歷史劇的劇作家在不違反時代的真實性原則下,不去寫這個時代所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寫的是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完全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在這個原則下,劇作家有充分的虛構(gòu)的自由,創(chuàng)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張、突出、集中,使之達到藝術(shù)上完整的要求。[20]
在這里,他提出了兩個話題并表明自己的看法:一是歷史劇的界定問題。 吳晗認為當(dāng)代的新歷史劇,必須在事情、人物上有歷史根據(jù),所以他將《楊門女將》《十二寡婦征西》《秦香蓮》《柳毅傳書》等完全虛構(gòu)的古裝戲排除在“新歷史劇”概念之外,稱其為“故事劇”“神話劇”。 二是歷史真實與虛構(gòu)問題。 因為他將歷史劇界定為必須以真人真事為依據(jù),所以他認為歷史劇的藝術(shù)虛構(gòu)必須遵循“真實性原則”,即“不去寫這個時代所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寫的是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完全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王子野、辛憲錫、馬少波等人都不同意吳晗關(guān)于歷史劇的界定的觀點,他們認為歷史劇指的是以古代生活為素材的戲劇,“戲劇家只問事件可能不可能,不問真有不真有”[21]。 “楊家將中有史可考的只有楊業(yè)、楊景、楊文廣三個人,但是舞臺上激動人心、多色多彩的楊家將的愛國故事和光彩照人的楊家將的英雄形象,難道不正是劇作者追求更高的真實的結(jié)果嗎?”[22]53事實上,人們很快就不再糾結(jié)于歷史劇的界定問題,而是把第二個問題“歷史真實與虛構(gòu)的關(guān)系”作為焦點,其關(guān)鍵又在于對“歷史真實”的不同理解上。 反對吳晗的論者,認為吳晗錯將被記載的歷史事實當(dāng)作了“歷史真實”,追求“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出處”,是將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劇混淆起來,實際上限制了歷史劇的虛構(gòu)性。 吳晗的確有將“歷史真實”表述為“過去人們的實踐,在特定時期確實發(fā)生過的事情,歷史家用科學(xué)態(tài)度如實地把它記錄下來”,但他也絕對承認虛構(gòu)的重要性,強調(diào)“只能虛構(gòu)在劇作家所寫的特定時期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決不可以虛構(gòu)這個特定時期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只有這樣,才能到達到歷史真實性與藝術(shù)真實性的統(tǒng)一”。[23]39實事求是地說,吳晗的觀點中有一些表述不夠準確的地方,有時過于注重歷史事實的真實性。 作為歷史學(xué)家,他似乎過于強調(diào)歷史劇承擔(dān)的歷史教育功能,擔(dān)心虛構(gòu)歷史上不存在的事件,會“歪曲了混亂了祖國的歷史,降低了歷史劇的教育意義”[20]。
反對者認為歷史真實應(yīng)該是一種超出歷史事實的“歷史本質(zhì)真實”和“更高的真實”。 毫無疑問,這種提法更為合理。 王子野、李希凡等人廣泛援引亞里士多德、萊辛、黑格爾等先賢關(guān)于藝術(shù)虛構(gòu)、歷史劇與歷史真實關(guān)系的觀點并進行闡發(fā),的確深化了關(guān)于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討論。 但問題是,這種“本質(zhì)真實”到底是什么呢? 在當(dāng)時的背景下,指導(dǎo)現(xiàn)實生活的政治意識同時也指導(dǎo)了人們對歷史的認知,所謂“歷史本質(zhì)真實”無法不被打上政治烙印,帶上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 所謂歷史事實的真理,與現(xiàn)實生活的真理,趨于同一化。 劇作家“總是憑借今天的觀點,憑借今天的生活體驗去認識過去時代的社會生活,并反映過去時代的社會生活的”,于是“劇作家為了把‘事實的真理’揭示得更鮮明、更深刻,就完全有權(quán)利通過概括、集中、提煉等藝術(shù)手法,對‘事實’做出必要的‘變動’”,也就難以避免通過改變歷史來符合現(xiàn)實需要。[24]這樣一來,歷史劇達到了“古為今用”的目的,表現(xiàn)出了時代精神,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了合法性。 對于眾多越王勾踐題材戲曲作者來說,這個故事經(jīng)過提煉、概括后反映的“歷史本質(zhì)真實”就是今天所需要的“奮發(fā)圖強”精神,越國君臣、人民在民族壓迫中奮發(fā)圖強,終于戰(zhàn)勝了強大的敵人,開始和平幸福地生活,無不是對當(dāng)下國際關(guān)系和政治現(xiàn)實的一種隱喻。在這一創(chuàng)作理念指引下,在“歷史真實與藝術(shù)虛構(gòu)”統(tǒng)一的原則下,很多現(xiàn)實中才有的思想、語言和生活元素,以“虛構(gòu)”(可能發(fā)生)的理由進入劇本,從而又陷入“反歷史主義”泥淖。 這種“片面地解釋藝術(shù)虛構(gòu),把藝術(shù)虛構(gòu)強調(diào)成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事實’的萬能法寶”[25]的情況,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皆非個別情況。 劇作家們紛紛訴苦,過多地考慮如何與今天的“時代精神”合拍的問題,“這一下子,就把步伐跨大了。 有的是并不自覺,有的是有所覺而欲罷不能,有的則是一馬當(dāng)先有意為之”[26]85。 有些人是自覺迎合,有些人是無可奈何,有些人是在政治主宰生活的環(huán)境下潛意識里以為理所當(dāng)然,于是,歷史劇成為對當(dāng)下政治運動、政策條文的圖解和說明。
事實上,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劇創(chuàng)作實際來看,并沒有那種完全依據(jù)歷史事實而不講虛構(gòu)的笨人,相反,大膽、隨意虛構(gòu)甚至過于浪漫化想象的主觀化、公式化劇本比比皆是。 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吳晗對于歷史劇概念的界定,以及對于歷史真實與虛構(gòu)問題的討論,有著重要現(xiàn)實意義。
除了吳晗,當(dāng)時還有幾位重要論者的觀點也值得重視。 王季思認為歷史劇不僅要表現(xiàn)“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征”,還要有“特定歷史時期的生活習(xí)慣和語言運用”,他質(zhì)疑郭沫若《武則天》過于現(xiàn)代化的語言和人物思想。[27]124茅盾在批評臥薪嘗膽題材歷史劇時指出問題的關(guān)鍵,即“史書所沒有的,劇作家可以想象,可以虛構(gòu),但是必須從二千四百年前越國的現(xiàn)實基礎(chǔ)上進行虛構(gòu),而不是從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基礎(chǔ)上進行虛構(gòu)”[28]120,試圖將歷史劇創(chuàng)作拉出比附、影射現(xiàn)實的泥沼。 《戲劇報》發(fā)表的評論員文章中指出:
歷史劇配合政治任務(wù)不可能像現(xiàn)代題材劇目那么密切,它對現(xiàn)代人主要的教育作用是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古人在階級斗爭、民族斗爭和日常的生活斗爭中所顯示的智慧。……描寫歷史人物必須把他放在那個時代和階級的典型環(huán)境中去表現(xiàn);無論是環(huán)境描寫或者人物描寫,必須是入情入理的。 所謂入情就是人物的心理邏輯、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緒;入理就是人物的外部邏輯、人物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戲劇沖突、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等等。[29]5
這里雖然還在不斷強調(diào)階級等意識形態(tài),但提出歷史劇創(chuàng)作應(yīng)該塑造合情合理的人物形象的觀點,將問題回歸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本身,已經(jīng)難能可貴了。
五、結(jié)語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幾部比較成功的歷史劇,如《鐘離劍》《滿江紅》《澶淵之盟》《金山戰(zhàn)鼓》《海瑞上疏》《則天皇帝》《強項令》等,正是在大關(guān)節(jié)尊重歷史事實的框架下,圍繞人物形象塑造合情合理地進行藝術(shù)虛構(gòu)。 這些劇作既具有較為鮮明的歷史感,符合歷史真實,同時人物性格鮮明,具有一定藝術(shù)感染力,也富于教育意義,在當(dāng)時成百上千的歷史劇作中,實屬鳳毛麟角。 限于篇幅,這里無法一一細致分析。 但更多的劇作,在盡力體現(xiàn)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功能時,被各種條條框框的意識所束縛,背離了藝術(shù)的真諦。 回溯歷史,無論成功之作,還是更多的失敗作品,共同提供了一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劇理論和實踐的真實鏡像,借此鏡像,我們認識歷史并反思歷史。
① “本報自十一月三日發(fā)表楊紹萱同志的《論“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危害性》一文后,各地讀者紛紛提出意見。 截至十二月三日止,本報已收到讀者來稿、來信二百七十三件。參見《批判楊紹萱在戲曲改革中的反歷史主義傾向》,載于《人民日報》1951 年12 月5 日。
② 楊紹萱寫給《人民日報》的信,附在《論“為文學(xué)而文學(xué)、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危害性——評艾青的〈談“牛郎織女”〉》一文后,載于《人民日報》1951 年11 月3 日。
③ 《談歷史與歷史劇》中舉出很多劇本中勾踐形象塑造的問題:“不但會像我們的下放干部那樣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與人民‘四同’,而且還有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chǔ)’的觀念;越國不但大興水利,大搞農(nóng)業(yè),而且還大煉鋼鐵,還請外國專家?guī)椭T造武器,改良農(nóng)具;越王勾踐不但自己臥薪嘗膽,而且還搞三反運動。”參見茅盾《關(guān)于歷史和歷史劇》,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2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