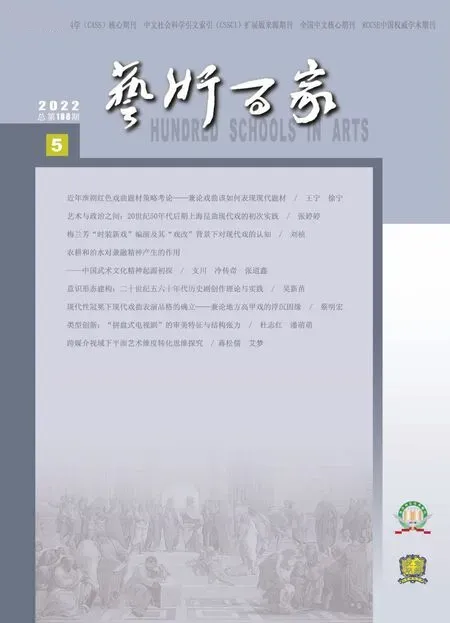中國(guó)民族歌劇“本土化”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形成路徑及啟示?
張婧婧
(南京曉莊學(xué)院 音樂(lè)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71)
一、問(wèn)題的提出
如果從20 世紀(jì)20 年代黎錦暉創(chuàng)作的兒童歌舞劇算起,那么直到今天,中國(guó)歌劇已經(jīng)走過(guò)了百年的發(fā)展道路。 通過(guò)《中國(guó)歌劇史1920—2000》[1]、居其宏《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通史》系列叢書(shū)①我們可以對(duì)中國(guó)歌劇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概況有清晰的了解。 百年來(lái),中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從無(wú)到有,我們既可以從縱向上梳理出兒童歌舞劇、小調(diào)劇、秧歌劇、話劇加唱型、戲曲音樂(lè)型和歌舞型等由簡(jiǎn)至繁再至多類型并存的中國(guó)歌劇歷時(shí)發(fā)展脈絡(luò)[1]2,也可以從橫向上把握當(dāng)前中國(guó)歌劇呈現(xiàn)的“歌舞劇、歌曲劇、正歌劇、民族歌劇和先鋒歌劇”[2]9-10五種類型歌劇競(jìng)相綻放、新作迭出的繁榮景象。
如果說(shuō)歌劇是人類“音樂(lè)藝術(shù)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在中國(guó)歌劇百年發(fā)展史中,在多種類型歌劇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基礎(chǔ)上,“民族歌劇”無(wú)疑是中國(guó)歌劇這“皇冠”上那顆耀眼的“明珠”:以“一白一黑”(《白毛女》《小二黑結(jié)婚》)、“一湖一江”(《洪湖赤衛(wèi)隊(duì)》《江姐》)為代表的民族歌劇所達(dá)到的藝術(shù)高度、所取得的輝煌成績(jī),至今仍被人津津樂(lè)道。 民族歌劇經(jīng)典作品不斷復(fù)排上演,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guó)人,觀眾追捧、專家贊譽(yù),其中的經(jīng)典唱段傳唱不衰,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神州上下“人人會(huì)唱《洪湖水》,處處齊歌《紅梅贊》”的景況時(shí)至今日仍有跡可循……可以說(shuō)民族歌劇中的經(jīng)典作品是新中國(guó)文藝創(chuàng)作發(fā)展史上當(dāng)之無(wú)愧的“高峰”。
民族歌劇創(chuàng)排的成功得益于多種因素,其中音樂(lè)創(chuàng)作是關(guān)鍵要素之一。 所謂歌劇,即“用音樂(lè)展開(kāi)的戲劇”(瓦格納語(yǔ)),即以音樂(lè)作為主要表現(xiàn)元素和手段來(lái)推進(jìn)情節(jié)發(fā)展和戲劇沖突,刻畫(huà)人物形象的舞臺(tái)藝術(shù)[1]7。 所以音樂(lè)元素與戲劇元素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兩個(gè)元素。 因此,民族歌劇成功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在于其音樂(lè)創(chuàng)作符合中國(guó)觀眾的審美心理和偏好,具體表現(xiàn)在其音樂(lè)創(chuàng)作與民歌、戲曲音樂(lè)的有機(jī)融合,特別是音樂(lè)戲劇性的展開(kāi)吸收了傳統(tǒng)戲曲聲腔,以及運(yùn)用板腔體結(jié)構(gòu)模式創(chuàng)作歌劇人物的唱段,并留下大批經(jīng)典板腔體詠嘆調(diào)作品。 那么,這種音樂(lè)創(chuàng)作路徑是如何形成、發(fā)展的? 對(duì)如今的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有何借鑒? 其間積累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對(duì)民族歌劇及其他類型中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實(shí)踐有怎樣的啟示? 相關(guān)問(wèn)題成為本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筆者不揣谫陋,對(duì)相關(guān)問(wèn)題作了一些思考,水平所限,文中不當(dāng)乃至錯(cuò)謬處,懇請(qǐng)歌劇創(chuàng)作者與專家批評(píng)指正。
二、歌劇在中國(guó)的“在地化”與“本土化”
中國(guó)民族歌劇“高峰”的出現(xiàn)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之前有“高原”作鋪墊,“高原”的形成也是從起步階段開(kāi)始一步一步積累而來(lái),這個(gè)過(guò)程及表現(xiàn),“中國(guó)歌劇史”相關(guān)論著已有詳細(xì)的梳理。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筆者進(jìn)一步提出,歌劇進(jìn)入中國(guó)先經(jīng)歷了“在地化”,在繼續(xù)發(fā)展中又進(jìn)一步“本土化”。 筆者認(rèn)為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在地化”是外來(lái)文化融入本土文化,“本土化”是傳統(tǒng)文化融入本土文化。 民族歌劇以民歌、戲曲為基礎(chǔ)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代表著歌劇“本土化”的完成。
“在地化”是與“全球化”相對(duì)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疆域內(nèi)人口、制度、習(xí)俗、文化等具有穩(wěn)定性和恒常性。 “在地化”偏重客觀,相對(duì)而言是一個(gè)被動(dòng)的過(guò)程。②具體到歌劇,作為一種“舶來(lái)品”,歌劇在中國(guó)的產(chǎn)生、發(fā)展與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歌劇在進(jìn)入中國(guó)前,在歐洲已經(jīng)有了四百余年的發(fā)展史,有意大利正歌劇、德國(guó)歌唱?jiǎng) ⒎▏?guó)大歌劇和喜歌劇、瓦格納樂(lè)劇、維也納輕歌劇等多種類型,是西方藝術(shù)的集大成者。 由于中西音樂(lè)形態(tài)、音樂(lè)文化、審美心理的巨大差異,歌劇在進(jìn)入中國(guó)后,必然經(jīng)歷適應(yīng)中國(guó)人審美心理、欣賞偏好的過(guò)程,即“在地化”的過(guò)程。 中國(guó)最早出現(xiàn)的一些歌劇音樂(lè)劇即是這種類型的作品,如《王昭君》(蕭梅編劇、張曙作曲,1930),《揚(yáng)子江暴風(fēng)雨》 (田漢編劇、聶耳作曲,1935),《西施》(陳大悲編劇、陳歌辛作曲,1935 年)等。 這些早期的作品基本是按照西方正歌劇的音樂(lè)思維、體裁形式來(lái)創(chuàng)作的中國(guó)正歌劇,但其中音樂(lè)素材選用自地方民歌。 根據(jù)戈曉毅的研究與考證,《王昭君》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就取材于粵劇音調(diào)和廣東音樂(lè),采用西洋美聲唱法,樂(lè)隊(duì)編制是以西洋管弦樂(lè)器為主、中西樂(lè)器混編的小型室內(nèi)樂(lè)隊(duì)。[3]《揚(yáng)子江暴風(fēng)雨》則呈現(xiàn)“話劇加唱式”的歌劇范式,這種范式操作起來(lái)比較簡(jiǎn)單、易行,創(chuàng)作周期短、成本低、易于制作,滿足了當(dāng)時(shí)斗爭(zhēng)環(huán)境的需要,但聶耳在這部歌劇中創(chuàng)作的《碼頭工人歌》《賣(mài)報(bào)歌》等唱段獨(dú)具匠心,且傳唱至今。 總體上,早期歌劇作品或是以西方歌劇為框架,或是用“話劇加唱”的簡(jiǎn)單方式,代表了早期的歌劇創(chuàng)作者在摸索中不斷地前進(jìn),并且這種探索方式在后世仍有發(fā)展,涌現(xiàn)出《傷逝》《原野》《蒼原》《雷雨》《詩(shī)人李白》等多部?jī)?yōu)秀的嚴(yán)肅歌劇(正歌劇)作品。
中國(guó)歌劇“本土化”偏重主觀,是在歌劇“在地化”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深度借鑒中國(guó)民歌、戲曲、曲藝中的音樂(lè)元素進(jìn)行創(chuàng)作,并以戲曲板腔體創(chuàng)作主要人物大段成套唱腔為核心特征的。 這一“本土化”過(guò)程,萌芽于黎錦暉創(chuàng)作的兒童歌舞劇,如《可憐的秋香》《小小畫(huà)家》等;發(fā)展于“延安秧歌劇運(yùn)動(dòng)”,以《兄妹開(kāi)荒》《夫妻識(shí)字》等秧歌劇為代表;成熟于“新歌劇”《白毛女》創(chuàng)演的成功。 “民族歌劇”的定名源于“新歌劇”,而“新歌劇”的“新”就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歌劇創(chuàng)作者在體裁形式、創(chuàng)作手法的底層邏輯和理念上與之前歌劇創(chuàng)作不同,形成了具有自身音樂(lè)特色的創(chuàng)作模式。
很多藝術(shù)形式開(kāi)創(chuàng)者的認(rèn)識(shí)、理念和創(chuàng)作思路往往對(duì)其后的發(fā)展有重要影響。 黎錦暉在創(chuàng)作兒童歌舞劇之初就走的不是西歐各國(guó)先搬演再模仿意大利歌劇,而后發(fā)展本國(guó)歌劇藝術(shù)的老路,而是在“在借鑒西洋歌劇的先進(jìn)經(jīng)驗(yàn)、繼承中國(guó)民間音樂(lè)和戲曲藝術(shù)深厚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堅(jiān)定走創(chuàng)作中國(guó)新型的音樂(lè)戲劇藝術(shù)之路”,而這一道路“在整體上預(yù)示出中國(guó)歌劇未來(lái)發(fā)展的整體路向”[2]18。 黎錦暉有這種認(rèn)識(shí)和創(chuàng)作思路與他自身深厚的民間音樂(lè)積累密不可分,他本人“偏愛(ài)俗樂(lè),喜唱民歌”,與民間曲藝藝人、戲曲藝人有密切的往來(lái)[4]36-38。 因此他在創(chuàng)作中常采用民間小曲、傳統(tǒng)曲牌加以創(chuàng)造性改編,如他在《麻雀與小孩》中就使用了【大開(kāi)門(mén)】【蘇武牧羊】【銀絞絲】等傳統(tǒng)曲牌填詞,且歌詞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非常適合兒童演唱。 雖然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還有其他仿照西方歌劇體裁形式的歌劇創(chuàng)作,但黎錦暉所開(kāi)辟的這條道路卻在“延安秧歌劇運(yùn)動(dòng)”中得以承繼并發(fā)揚(yáng)光大。
“延安秧歌劇運(yùn)動(dòng)”的開(kāi)展有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條件。 首先是20 世紀(jì)40 年代,一批左翼文藝家涌入延安及各抗日根據(jù)地,中國(guó)歌劇的創(chuàng)作及演出中心逐漸轉(zhuǎn)移到延安;其次,1942 年毛澤東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鼓舞了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并紛紛進(jìn)入陜北農(nóng)村,掀起了學(xué)習(xí)、挖掘、整理民間藝術(shù)的高潮。 其中對(duì)陜北秧歌這種民間歌舞形式進(jìn)行提煉和改造卓具成效,一方面用富有時(shí)代氣息和生活感的內(nèi)容簡(jiǎn)單設(shè)置故事情節(jié),另一方面運(yùn)用專業(yè)作曲技法對(duì)原始音樂(lè)素材進(jìn)行加工、改編,由此創(chuàng)造出表現(xiàn)根據(jù)地革命生活、鮮明人物形象的新型秧歌劇,其中的代表就是被稱為秧歌劇“雙璧”的《兄妹開(kāi)荒》《夫妻識(shí)字》。 兩部秧歌劇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取材于陜北民歌和當(dāng)?shù)氐拿紤魬蛞粽{(diào),在演出形式和音樂(lè)創(chuàng)作上較為簡(jiǎn)單,具有陜北民間音樂(lè)典型的形態(tài)特征,貼近當(dāng)?shù)厝嗣袢罕姷男蕾p習(xí)慣。 而大型秧歌劇《慣匪周子山》則在演出形式、戲劇結(jié)構(gòu)、音樂(lè)創(chuàng)作上均有大幅度的擴(kuò)充,為大型歌劇的創(chuàng)作、為歌劇“本土化”進(jìn)一步的推進(jìn)積累了經(jīng)驗(yàn)。
“新歌劇”《白毛女》的橫空出世標(biāo)志著歌劇“本土化”的完成。 《白毛女》雖然是在秧歌劇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lái),但初始版本仍未超越秧歌劇的程度和形式③,而是改編成五幕歌劇取得了成功,在戲劇性和音樂(lè)創(chuàng)作兩方面均達(dá)到很高的水平。 戲劇性方面,其取材于晉察冀邊區(qū)流行的“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shuō),并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性地改編,去除民間傳說(shuō)中封建迷信元素,改為革命主題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歌劇臺(tái)本,并且劇本的文學(xué)性、戲劇性也達(dá)到了很深的造詣。 音樂(lè)創(chuàng)作方面,《白毛女》采用戲曲音樂(lè)中板腔體和聯(lián)曲體相結(jié)合的方式展開(kāi)戲劇性:用簡(jiǎn)短的歌謠體抒發(fā)劇中人物簡(jiǎn)單的情緒和情感,典型唱段如《北風(fēng)吹》《扎紅頭繩》等;通過(guò)板腔體表現(xiàn)人物激動(dòng)、復(fù)雜的情緒和情感,典型唱段如喜兒的詠嘆調(diào)《恨似高山仇似海》等。另外在一些吟誦調(diào)中《白毛女》也借用秦腔、河北梆子中的板式,利用傳統(tǒng)戲曲中的垛板配合吟誦加強(qiáng)戲劇語(yǔ)言的沖擊力,如楊白勞《老天殺人不眨眼》唱段等。 從中可見(jiàn)《白毛女》并非對(duì)民歌、傳統(tǒng)戲曲音樂(lè)演奏、體裁形式、音樂(lè)結(jié)構(gòu)體制簡(jiǎn)單的借用、移植或改編,而是根據(jù)戲劇沖突、人物形象對(duì)民歌旋律、傳統(tǒng)戲曲聲腔與板式結(jié)構(gòu)作反復(fù)、展開(kāi)、變形、再現(xiàn)。 由此可見(jiàn)其中貫徹了原創(chuàng)性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理念,真正符合歌劇“用音樂(lè)展開(kāi)的戲劇”的定義,因此《白毛女》創(chuàng)作的成功標(biāo)志著歌劇“本土化”的完成。 而“新歌劇”也即被冠以“民族歌劇”,隨后這一定名得到理論界和觀眾的普遍認(rèn)可并延續(xù)至今。
歌劇在中國(guó)經(jīng)歷了“在地化”與“本土化”歷程,雖然在吸收、借鑒民族民間音樂(lè)元素進(jìn)行音樂(lè)創(chuàng)作,展開(kāi)戲劇性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具體采用的創(chuàng)作理念、體裁形式卻有著較大差異,甚至可以說(shuō)是完全不同的創(chuàng)作路徑,這也導(dǎo)致中國(guó)歌劇形成了兩條不同的發(fā)展道路。 居其宏認(rèn)為中國(guó)歌劇劃分為五種類型,提出“泛歌劇”概念,李吉提針對(duì)此提出了“西體歌劇與民族歌劇”兩種類型的歌劇劃分方式[5-6]。 筆者認(rèn)為,西體歌劇、民族歌劇在相當(dāng)程度上其實(shí)對(duì)應(yīng)了歌劇“在地化”“本土化”的兩種形成路徑,并在當(dāng)前對(duì)應(yīng)了嚴(yán)肅歌劇(正歌劇)、民族歌劇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形態(tài),共同推動(dòng)中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不斷向前發(fā)展。
三、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本土化”的新發(fā)展
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在20 世紀(jì)40 年代至60 年代形成第一次高潮,“高峰”作品頻現(xiàn),引領(lǐng)一時(shí)風(fēng)氣。 盡管民族歌劇再一次迎來(lái)“高峰”已經(jīng)是三十年后,歌劇《黨的女兒》《野火春風(fēng)斗古城》接續(xù)了民族歌劇的“一脈單傳”[2]306。 而后有影響力和傳播力的作品寥寥無(wú)幾,文化和旅游部從2017 年開(kāi)始實(shí)施“中國(guó)民族歌劇傳承發(fā)展工程”④,以大力弘揚(yáng)社會(huì)主義先進(jìn)文化、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紅色文化為己任,鼓勵(lì)和倡導(dǎo)大批文藝工作者投身于民族歌劇的創(chuàng)作,展現(xiàn)出了蓬勃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趨勢(shì),涌現(xiàn)出大量凸顯中國(guó)特色、中國(guó)文化、中國(guó)精神的民族歌劇作品。 通過(guò)全國(guó)優(yōu)秀民族歌劇展演、中國(guó)歌劇節(jié)等,集中推廣具有民族歌劇特色和較高藝術(shù)質(zhì)量的作品,對(duì)深入有效地推動(dòng)我國(guó)民族歌劇“本土化”的新發(fā)展,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如民族歌劇《沂蒙山》《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呦呦鹿鳴》等優(yōu)秀作品的呈現(xiàn),昭示著中國(guó)歌劇藝術(shù)發(fā)展步入了新的階段,展示出民族歌劇旺盛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作力。
今天的“新發(fā)展”是在創(chuàng)新上的傳承,亦是在傳承上的發(fā)展。 可用李吉提教授總結(jié)的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三大支柱”來(lái)概括:“民族音色”(民族唱法和民樂(lè)演奏)、“民族旋律”(來(lái)自民歌素材)、“戲曲板腔體”(中國(guó)式的戲劇詠嘆)。⑤這三大支柱在當(dāng)前優(yōu)秀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中均有所體現(xiàn),并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發(fā)展動(dòng)向:民族音色的選用更為多元和寬容,更多服務(wù)于戲劇性的展開(kāi);民歌旋律的運(yùn)用偏重凸顯地域性音樂(lè)文化特色和音樂(lè)形態(tài)特征;戲曲板腔體繼續(xù)在主要人物核心唱段創(chuàng)作中發(fā)揮基礎(chǔ)性作用。
以近年來(lái)廣受好評(píng)的民族歌劇《沂蒙山》⑥為例。歌劇《沂蒙山》取材于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山東沂蒙山地區(qū)的真人真事改編,展現(xiàn)“軍民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 民歌素材方面,歌劇《沂蒙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duì)如何運(yùn)用《沂蒙山小調(diào)》的問(wèn)題,作曲家欒凱介紹,他在處理《沂蒙山小調(diào)》時(shí),考慮這首廣為流傳的民歌曲調(diào)不僅傳唱度高而且影響深遠(yuǎn),因此這首歌曲不能不用,但用多了又會(huì)沖淡歌劇的原創(chuàng)性。 最終,作曲家將《沂蒙山小調(diào)》拆分使用,有機(jī)地糅入全劇音樂(lè)中,讓樂(lè)隊(duì)“在序曲、幕間曲、前奏、間奏中反復(fù)出現(xiàn),進(jìn)入唱段則使用原創(chuàng)音樂(lè),全劇在最后一首海棠的詠嘆調(diào)《沂蒙山,永遠(yuǎn)的爹娘》副歌高潮處才完整出現(xiàn)一次《沂蒙山小調(diào)》的旋律變奏”[8]。 可以說(shuō)這種處理方式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讓觀眾既熟悉又能聽(tīng)出新意,可謂匠心獨(dú)運(yùn)。 《沂蒙山》中除了使用山東民歌元素進(jìn)行創(chuàng)作,還繼承并發(fā)展了民族歌劇使用戲曲板腔體創(chuàng)作主要人物核心唱段的傳統(tǒng)。 吳可畏撰文指出,在《沂蒙山》劇中夏荷的詠嘆調(diào)《沂蒙的女兒》和海棠的詠嘆調(diào)《蒼天把眼睜一睜》中,“作曲家在表現(xiàn)劇中人物悲苦狀態(tài)的時(shí)候,均運(yùn)用戲曲板腔體來(lái)創(chuàng)作唱段,這與古典戲曲的音樂(lè)氣質(zhì)是十分貼合的”[9]53。 這種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理念和方法較為典型體現(xiàn)出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的特色。 在詠嘆調(diào)之外,劇中對(duì)宣敘調(diào)作了技術(shù)性處理,敘事段落的唱詞采用合轍押韻、結(jié)構(gòu)規(guī)整的韻文寫(xiě)成,使其更接近“詠敘調(diào)”,更具有旋律性。 這種處理手法也是在民族歌劇不斷摸索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的,并在多部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得到檢驗(yàn),已經(jīng)成為敘述性段落唱詞較為常用的處理手法。 在民族唱法方面,《沂蒙山》根據(jù)戲劇性展開(kāi)的需要,對(duì)民族歌劇唱法進(jìn)行了多元化的嘗試,將不同類型的唱法(民族、美聲)和不同的音色(抒情男高音、戲劇男高音和男中音等)有機(jī)融合,豐富了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力和厚度,也實(shí)現(xiàn)了歌劇中人物和情節(jié)的平衡,滿足了當(dāng)代觀眾對(duì)民族歌劇求新、求變的審美期待。
對(duì)于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新,我們應(yīng)該持鼓勵(lì)態(tài)度,李吉提在《中國(guó)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得與失(上)——寫(xiě)在歌劇《白毛女》首演75 周年》一文中總結(jié):“如果75 年后還僅守著對(duì)歌劇《白毛女》以來(lái)創(chuàng)作套路的慣性思路前進(jìn)、而忽視了對(duì)新時(shí)代國(guó)內(nèi)外歌劇音樂(lè)發(fā)展和人們對(duì)當(dāng)代歌劇需求變化的感知,那么,我們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的道路是不是會(huì)走得太過(guò)單一和狹窄? 是否從根本上也違背了《白毛女》的創(chuàng)新理念和探索精神?”[5]15這一反問(wèn)振聾發(fā)聵,指出了中國(guó)歌劇發(fā)展的原動(dòng)力,值得相關(guān)從業(yè)者深思。 通過(guò)中國(guó)歌劇百年的曲折發(fā)展道路不難看出,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diǎn)始終是與國(guó)家的命運(yùn)和發(fā)展建設(shè)緊密相連,在注重音樂(lè)藝術(shù)性的同時(shí)突出了作品的功能性價(jià)值。 借鑒歐洲歌劇的創(chuàng)作手法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實(shí)現(xiàn)了時(shí)代性、民族性、觀賞性、戲劇性的統(tǒng)一。我們應(yīng)以每個(gè)時(shí)期不同的審美需求為出發(fā)點(diǎn),通過(guò)運(yùn)用不同的創(chuàng)作手法,積極探索讓人民群眾接受和喜愛(ài)的音樂(lè)。
四、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本土化”成功的啟示
中國(guó)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本土化”是在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環(huán)境下,在一個(gè)不斷探索的過(guò)程中形成的。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者在融合古今中外優(yōu)秀藝術(shù)元素方面貢獻(xiàn)了高度的智慧,其成功經(jīng)驗(yàn)為今天繼續(xù)推動(dòng)中國(guó)歌劇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提供了若干重要啟示。
(一)關(guān)于音樂(lè)融合
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本土化”的成功,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要立足民族民間音樂(lè)文化傳統(tǒng),深入掌握其音樂(lè)形態(tài)特征與精髓,同時(shí)懷有廣大的胸襟、高遠(yuǎn)的格局,不斷借鑒、吸收外來(lái)優(yōu)秀的音樂(lè)形式、音樂(lè)體裁,在立足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創(chuàng)新性轉(zhuǎn)化,使這些引進(jìn)的音樂(lè)形式、音樂(lè)體裁能夠被國(guó)人所接受、喜愛(ài),不斷滿足人們?nèi)找嬖鲩L(zhǎng)的精神文化需求。 事實(shí)上,這種吸收外來(lái)優(yōu)秀文化使其不斷“本土化”的模式是自古以來(lái)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發(fā)展的傳統(tǒng)。先秦時(shí)期的“四夷之樂(lè)”不斷進(jìn)入中原,奠定了中國(guó)音樂(lè)文化的基礎(chǔ);魏晉南北朝西域歌舞涌入,直接推動(dòng)了隋唐燕樂(lè)歌舞的繁榮,營(yíng)造了這一時(shí)期中外音樂(lè)交流的盛世景象;宋元之交南北方音樂(lè)進(jìn)一步融合,助推了戲曲藝術(shù)形成;明清之際中西音樂(lè)交流加強(qiáng),學(xué)堂樂(lè)歌開(kāi)啟了“新音樂(l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后西方藝術(shù)大規(guī)模的涌入;等等。 因此,看似歌劇進(jìn)入中國(guó)后的“在地化”“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獨(dú)立的發(fā)展路徑,但我們把視野拉長(zhǎng),則發(fā)現(xiàn)這仍是中國(guó)音樂(lè)整體發(fā)展格局下中外音樂(lè)成功交流融合的又一生動(dòng)實(shí)例。
(二)關(guān)于音樂(lè)創(chuàng)作“本土化”的歷史嬗變
其一,創(chuàng)作思路。 歐洲歌劇幾百年來(lái)的發(fā)展歷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diǎn)的創(chuàng)作形式和表演形式。 我國(guó)歌劇經(jīng)歷了“在地化”,逐漸形成了民族歌劇“本土化”,這要?dú)w功于文藝工作者作為中國(guó)歌劇的探索者、實(shí)踐者,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dǎo)向,把人民群眾的喜好和認(rèn)可放在首位,抒寫(xiě)屬于人民的音樂(lè)的道路。 一味地“全盤(pán)西化”或者“硬套西化”已經(jīng)不符合社會(huì)審美需求,伴隨著國(guó)家的發(fā)展,國(guó)際社會(huì)地位的提高,強(qiáng)國(guó)觀日益凸顯,即“民族主義”音樂(lè)創(chuàng)作導(dǎo)向發(fā)展,是我們文化自信和開(kāi)放觀念的體現(xiàn)。 作曲家金湘提出的“歌劇思維”(交響思維)⑦,強(qiáng)調(diào)樹(shù)立總體思維,劇作家、作曲家必須具備綜合的素養(yǎng),將文學(xué)、戲劇、音樂(lè)、舞臺(tái)融為一體。 推陳出新,將客觀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情感、戲劇沖突轉(zhuǎn)化為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重唱、合唱等音樂(lè)形式,呈現(xiàn)“為人民”的“本土化”創(chuàng)作意識(shí),是現(xiàn)代社會(huì)需要持續(xù)探索的創(chuàng)作路徑。
其二,音樂(lè)呈現(xiàn)。 歌劇是集音樂(lè)、戲劇、舞蹈、美術(shù)等各種元素于一身的綜合舞臺(tái)藝術(shù)。 早期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生搬硬套模仿西方的創(chuàng)作形式,戲劇多以敘事為主,伴有沖突性劇情。 進(jìn)入新時(shí)代,音樂(lè)創(chuàng)作逐步突出展現(xiàn)民族特色的音樂(lè)元素,在繼承戲劇的敘事性基礎(chǔ)上,對(duì)沖突性、色彩性、抒情性有了更多的重視。 通過(guò)音樂(lè)和戲劇,進(jìn)而塑造一個(gè)個(gè)鮮明的人物形象,這也是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首要目的,更是評(píng)價(jià)一部歌劇打動(dòng)人心的重要指標(biāo),如《呦呦鹿鳴》中諾貝爾獎(jiǎng)獲得者屠呦呦,《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中農(nóng)科院助理研究員馬向陽(yáng)等,都是舞臺(tái)上讓人記憶深刻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從中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的體裁看,有完全按照西方歌劇創(chuàng)作模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秋子》,作為我國(guó)正歌劇形成的標(biāo)志,該劇采用美聲唱法的同時(shí),通過(guò)西方歌劇的形式、題材、創(chuàng)作技法,運(yùn)用西洋管弦樂(lè)隊(duì)伴奏,呈現(xiàn)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間奏曲、敘事曲、舞曲等表現(xiàn)形式;有融合了中國(guó)民族民間音樂(lè)、戲曲元素創(chuàng)作的《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該劇汲取正歌劇技法,以中國(guó)戲曲為基本元素,自然糅合宣敘調(diào)、詠嘆調(diào)、重唱、合唱;也有將中國(guó)民族元素與西方作曲技法相互融合的作品《塵埃落定》,該劇為西洋正歌劇模式的民族化,大量吸收、運(yùn)用藏族民間音樂(lè)元素,將宣敘調(diào)、詠嘆調(diào)、重唱、合唱融入作品,并在配器、和聲與場(chǎng)景音樂(lè)的交響化上做了大膽而成功的嘗試。 不論是哪種音樂(lè)呈現(xiàn)形式,歌劇的“民族性”都在不斷地被強(qiáng)化,體現(xiàn)出講好中國(guó)故事,堅(jiān)守中國(guó)文化,堅(jiān)定文化自信,傳承民族精神的導(dǎo)向。
中國(guó)歌劇近百年的發(fā)展道路讓我們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民族歌劇和中國(guó)文化密不可分,“民族性”是歌劇創(chuàng)作必須堅(jiān)持的。 “人民的歌劇必須以民族風(fēng)格和民間形式為圭臬。”[10]10“歌劇”,“歌”在前“劇”在后,顧名思義,音樂(lè)是歌劇的重中之重,以“歌”為“劇”服務(wù),“劇”與“歌”融合,把音樂(lè)寫(xiě)得讓聽(tīng)眾記憶深刻和喜愛(ài),這部歌劇就成功了一半。
其三,社會(huì)功能。 縱觀中國(guó)歌劇百年的發(fā)展脈絡(luò)[11]:20 世紀(jì)20—40 年代初,中國(guó)歌劇的萌芽期和探索期的作品更多地體現(xiàn)了民主精神和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麻雀與小孩》等);20 世紀(jì)40—50 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后,新秧歌運(yùn)動(dòng)推動(dòng)發(fā)展了一批以時(shí)代為背景,弘揚(yáng)革命精神的秧歌劇(《兄妹開(kāi)荒》《白毛女》等);20 世紀(jì)50—70 年代,中國(guó)歌劇進(jìn)入新中國(guó)成立后“百花齊放、百家爭(zhēng)鳴”的多元化時(shí)代,戲曲板式歌劇如《紅珊瑚》《王貴與李香香》等,民間歌舞劇《劉三姐》等,借鑒西方大歌劇手法和元素創(chuàng)作的《阿依古麗》等,兼容西方創(chuàng)作手法,融合中國(guó)戲曲板腔體結(jié)構(gòu)而創(chuàng)作的《洪湖赤衛(wèi)隊(duì)》《江姐》等,都以堅(jiān)定民族信仰、貼近群眾生活的角度進(jìn)行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呈現(xiàn);20世紀(jì)80—90 年代,在外來(lái)藝術(shù)和審美的滲透、相互交融下,音樂(lè)創(chuàng)作有了分化,有沿襲西方正歌劇形式的創(chuàng)作如《傷逝》《原野》等,也有積極探索融合中國(guó)特色“本土化”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如《從前有座山》《黨的女兒》等,創(chuàng)作者在“民族性”的道路上探索前行;2000年至今,隨著國(guó)家的強(qiáng)大和國(guó)際地位的提高,歌劇創(chuàng)作的社會(huì)需求也更加清晰。 在堅(jiān)守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新時(shí)代民族歌劇的音樂(lè)主題、音樂(lè)創(chuàng)作更加多元化,個(gè)性化,用不同類型的作品傳遞著正能量和時(shí)代價(jià)值觀。 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中提出:“衡量一個(gè)時(shí)代文藝成就最終看作品。 推動(dòng)文藝繁榮發(fā)展,最根本的是要?jiǎng)?chuàng)作生產(chǎn)出無(wú)愧于我們這個(gè)偉大民族、偉大時(shí)代的優(yōu)秀作品。”中國(guó)歌劇的社會(huì)需要被推向了一個(gè)新高度,在人民需求和政策的扶持下,中國(guó)歌劇發(fā)展進(jìn)入了繁榮期。 一方面講好中國(guó)故事、中國(guó)文化能促進(jìn)國(guó)際文化交流和推廣;另一方面民族歌劇的創(chuàng)作緊隨時(shí)代腳步,蘊(yùn)含著鮮明的“紅色基因”,傳遞民族精神,傳播理想信念,引導(dǎo)一代代中華兒女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而努力奮斗。
(三)關(guān)于民族歌劇的形成
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通過(guò)長(zhǎng)時(shí)間的摸索與實(shí)踐,找到了一條道路,其以吸收民族民間音樂(lè)元素、傳統(tǒng)板腔體戲曲結(jié)構(gòu)體制為基礎(chǔ),但主導(dǎo)型創(chuàng)作思路是運(yùn)用西方歌劇主題貫穿發(fā)展手法來(lái)展開(kāi)戲劇性。 正如居其宏指出的,“《白毛女》音樂(lè)整體戲劇性思維的最大特色,則是在如何對(duì)待中外音樂(lè)文化遺產(chǎn)的繼承和發(fā)展問(wèn)題上遵循科學(xué)態(tài)度和辯證思維,創(chuàng)造性地合理兼用西方歌劇主題貫穿發(fā)展和我國(guó)傳統(tǒng)戲曲中板腔體相結(jié)合的方式來(lái)展開(kāi)戲劇性”[7]。 這種結(jié)合強(qiáng)調(diào)原創(chuàng)性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與傳統(tǒng)戲曲套用固有的聯(lián)曲體、板腔體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的創(chuàng)作,在根本邏輯上形成了差異。 因此民族歌劇這種音樂(l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不僅繼承了民族民間音樂(lè)和傳統(tǒng)戲曲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而且還在此基礎(chǔ)上推動(dòng)了這些傳統(tǒng)進(jìn)一步發(fā)展。
雖然中國(guó)民族歌劇呈現(xiàn)“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蓬勃發(fā)展趨勢(shì),但在這背后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依然存在著諸多發(fā)展困境和挑戰(zhàn)。 作品選材局限,缺乏創(chuàng)新,觀眾喜愛(ài)度不高,作品功利性強(qiáng),藝術(shù)質(zhì)量不高,國(guó)際影響力不足等,均值得我們深思。
五、結(jié)語(yǔ)
歌劇在中國(guó)的落地、生根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藝術(shù)由傳統(tǒng)型向現(xiàn)代型、由民間型向?qū)I(yè)型戰(zhàn)略轉(zhuǎn)軌的產(chǎn)物”[12]5-8。 當(dāng)然這一轉(zhuǎn)型、轉(zhuǎn)軌并非一蹴而就,中間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形成了多種豐富的歌劇類型,這一過(guò)程可以通過(guò)“在地化”“本土化”兩種類型進(jìn)行觀察,表現(xiàn)為西體歌劇、民族歌劇兩大主要類型。 兩種類型的創(chuàng)作在音樂(lè)創(chuàng)作底層邏輯和理念方面有根本不同,但民族歌劇無(wú)疑代表了我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并可以屹立于世界歌劇藝術(shù)之林。
時(shí)至今日,歌劇已經(jīng)成為衡量一個(gè)國(guó)家藝術(shù)發(fā)展水平的重要參照標(biāo)準(zhǔn)。 但相較于經(jīng)典民族歌劇達(dá)到的“高峰”,目前我國(guó)民族歌劇的創(chuàng)作雖有“高原”,亦不乏亮點(diǎn),但距離“高峰”仍有不短的距離。 正如習(xí)近平主席在文藝座談會(huì)上指出的,我國(guó)文藝創(chuàng)作在改革開(kāi)放之后雖然也有膾炙人口的作品,但同時(shí)存在著有數(shù)量缺質(zhì)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xiàn)象。 習(xí)近平主席指出的這些問(wèn)題是切實(shí)存在的,需要我們引起高度重視。
近年來(lái),中國(guó)歌劇的發(fā)展拉開(kāi)了新的篇章。 國(guó)家藝術(shù)基金的設(shè)立,2017 年文化部召開(kāi)“中國(guó)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座談會(huì)”,設(shè)立“中國(guó)民族歌劇傳承發(fā)展工程”,評(píng)選民族歌劇重點(diǎn)扶持劇目等舉措,從政策導(dǎo)向、資金支持、演出支持等多個(gè)方面為中國(guó)歌劇的發(fā)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希望民族歌劇創(chuàng)作沿著此前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未來(lái)有更好的發(fā)展。
① 由居其宏擔(dān)任總編撰的《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通史》叢書(shū)包括:《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創(chuàng)作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中國(guó)歌劇文學(xué)特性歷史審視與美學(xué)視野》《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理論思潮發(fā)展與嬗變研究》《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演出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生存現(xiàn)狀與戰(zhàn)略對(duì)策(咨詢報(bào)告書(shū))》;另有3 冊(cè)唱段精粹,《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唱段精粹·美聲唱法卷》《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唱段精粹·通俗唱法卷》《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唱段精粹·民族唱法卷》;DVD《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場(chǎng)面精粹》(共3 盤(pán))。 叢書(shū)內(nèi)容囊括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近百年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創(chuàng)作思潮、美學(xué)品格、風(fēng)格樣式、文學(xué)特性及表導(dǎo)演藝術(shù)、專業(yè)團(tuán)體藝術(shù)生產(chǎn)模式和生存現(xiàn)狀等,對(duì)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的發(fā)生、發(fā)展做了全景式展示。
② “在地化”“本土化”的意涵及對(duì)應(yīng)的“客觀融入當(dāng)?shù)亍薄爸饔^融入當(dāng)?shù)亍眳⒖甲宰x秀“在地化”詞條。 筆者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闡發(fā),認(rèn)為“在地化”是一個(gè)被動(dòng)過(guò)程,“本土化”是一個(gè)主動(dòng)過(guò)程。 參考詞條地址:https:/ /book. duxiu. com/EncyDetail. jsp?dxid= 403694259675&d = EF11854F3AD08173B1CA6A8A00236 41F&stitle=%E5%9C%A8%E5%9C%B0%E5%8C%96。(2020-4-25).
③ 《白毛女》最初版本的藝術(shù)面貌較為陳舊,曾走過(guò)彎路。 根據(jù)《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創(chuàng)作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白毛女》最初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作的“劇本采用朗誦詩(shī)劇文體,音樂(lè)創(chuàng)作依據(jù)秧歌劇經(jīng)驗(yàn)以現(xiàn)成的秦腔、眉戶調(diào)配曲,表演上則參照戲曲模式”。 由此可見(jiàn)其初始版本仍未脫離秧歌劇的形式。(居其宏《中國(guó)歌劇音樂(lè)劇創(chuàng)作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第44 頁(yè))
④ 文化部從2017 年開(kāi)始對(duì)民族歌劇的創(chuàng)作、生產(chǎn)、普及推廣、人才培養(yǎng)、理論研究等進(jìn)行扶持。
⑤ 李吉提教授除了總結(jié)出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三大支柱”,并對(duì)這三方面有詳細(xì)的闡述:民族歌劇講的應(yīng)該是中國(guó)故事,采用民族唱法,突出民族樂(lè)隊(duì)音色。 作曲技術(shù)則表現(xiàn)為凸顯中華民族語(yǔ)言和音樂(lè)風(fēng)格腔調(diào)、韻味,尊重中國(guó)人偏愛(ài)旋律表述的審美習(xí)慣。 其音樂(lè)的陳述方式也與中華民族的民歌、戲曲關(guān)系更為密切。 小型或輕型的歌劇可能具有一定的民族歌舞風(fēng)格特點(diǎn),而大型或戲劇化程度高的作品,其音樂(lè)的陳述結(jié)構(gòu)中則可能汲取大量的傳統(tǒng)戲曲演唱套路(如板腔體“散一慢一中一快一散”的速度布局之類)以更方便地揭示戲劇矛盾沖突。 此外,在歌劇的舞美和演員的舞臺(tái)表演、身段等,也常采用中國(guó)人所熟悉的歌舞、戲曲表情程式而有別于西方。 詳參:李吉提《中國(guó)民族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得與失(下)——在溫故知新中尋求發(fā)展之路,第12 頁(yè)。
⑥ 《沂蒙山》由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臨沂市聯(lián)合出品,山東歌舞劇院創(chuàng)排的大型民族歌劇。 欒凱作曲,王曉嶺、李文緒編劇,黃定山導(dǎo)演。
⑦ “歌劇思維”,是作曲家金湘從事歌劇音樂(lè)創(chuàng)作多年,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實(shí)踐與思考提出的一個(gè)美學(xué)理念,強(qiáng)調(diào)在創(chuàng)作伊始就要樹(shù)立總體性思維,既要科學(xué)對(duì)待音樂(lè)與戲劇的關(guān)系,又要正確聯(lián)合作曲、編劇、導(dǎo)演三大核心人物,實(shí)現(xiàn)三位一體,共同構(gòu)思與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