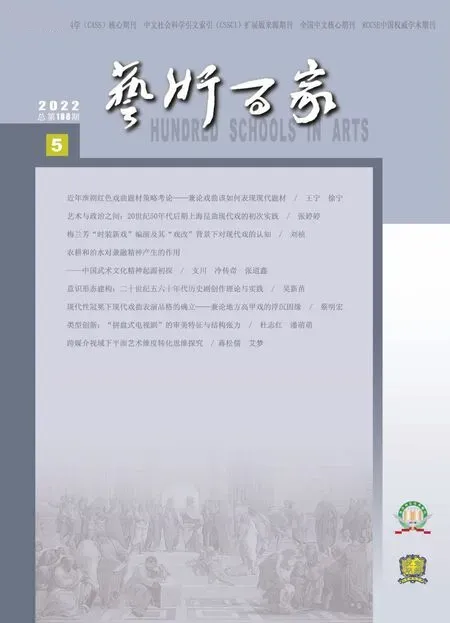類型創新:“拼盤式電視劇”的審美特征與結構張力?
杜志紅,潘萌萌
(蘇州大學 傳媒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影視類型的認知,總是基于影視創作實踐的探索,創作實踐無止境,類型認知也要與時俱進。 賴亞爾提出:“類型可定義為模式、形式、風格或結構,他們超越單個影片,指導影片制作人的制作,引導觀眾欣賞。”阿伯克龍比認為此話“也適用于電視”[1]49。近年來,在我國電視熒屏上頻繁出現一種新的電視劇類型,它的結構與傳統的單本劇、連續劇、系列劇均有所不同,往往由多個小故事拼接在一起形成一部作品,服從于某個重大主題,如抗疫報告劇《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獻禮劇《功勛》《理想照耀中國》《我們的新時代》《我們這十年》、扶貧劇《石頭開花》《脫貧先鋒》《約定》等。 對于這類電視劇,學者們有的稱之為“單元劇”,有的稱之為“時代報告劇”,還有的稱之為“集錦式電視劇”或“拼盤式電視劇”。 本文從類型分析視角對此類劇作的概念進行辨析,分析其結構特征和審美張力,并對如何提升其質量提出建議。
一、概念辨析:結構作為類型之維
劃分類型首先要確定劃分標準或維度。 一般來說,劃分電視劇類型,一是依據題材內容,二是依據結構形式。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劃分方法,依據題材內容劃分出來的類型往往產生交叉,呈現出模糊和不穩定的特性。 依據結構形式來劃分,類型的定義則比較穩定和清晰,比如塞爾夫在《電視劇導論:類型與媒介》中將電視劇劃分為單本劇、系列劇、連續劇等[2]91-108,每種類型一旦確定,就不大可能同時又是另外一種。 在我國,學界一般比較認可塞爾夫的劃分方式。 從1958 年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播出到現在,在60 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從劇場劇到單本劇,從系列劇到連續劇,我國電視劇的結構樣式不斷創新。 近年出現的這些劇目類型,從結構上看不同于以往,其概念使用還比較混亂,應該給予其一個相對穩定的概念定義。
本文認為這些呈現出新的結構類型的電視劇應該被命名為“拼盤式電視劇”,有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拼盤”一詞屬于烹飪學范疇,指在一個盤子里,幾種不同的菜肴共同組合成一道菜。 它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搭配和組合概念,這種搭配和組合并不是隨意而成,而是有著內在的邏輯或出于對風格的考量,比如為了顏色優美、營養均衡、口感豐富,或為了造型多姿多彩、相映生輝。 從這個意義上說,“拼盤”概念可以很好地概括這類電視劇的結構特點,即一部劇由多個不同的人物故事拼裝在一起,單個故事彼此之間不盡相同,共同的題材和主題使其統合為一個整體,同時因為主體多元、角度多樣,將它們組合在一起能夠達到各有特色又和諧共生的效果。
其次,“拼盤”比其他稱呼更能準確概括此類劇作的結構特征。 如“單元”一詞,帶有靜態意味,偏重于強調各個故事的獨立性;“集錦”則容易被理解為沒有內在關聯的匯聚,或者是收藏式陳列。 相較于“單元”“集錦”等概念,“拼盤”既是名詞又是動詞,帶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色彩,更強調整體性和協調性,可以概括這種劇類“形散而神不散”、特別注重內在關聯的結構特質。
最后,“拼盤”并不意味著每一個被拼合的小盤無足輕重,每一個小盤里的菜肴可能由不同的廚師專門制作,各揚所長,最后小盤被拼裝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呈現在食客面前。 “拼盤式電視劇”也是如此,多位導演各自獨立完成其中的一集或幾集,這一集或幾集既是獨立的人物故事,又與其他劇集形成互文性關聯,構成更大的時代背景或主題框架下的敘事整體。
因此,本文認為“拼盤式電視劇”可以定義為基于同一題材和主題講述多個不同故事,同時又將這些故事作為一個整體播出的電視劇。 它可以由一位或多位導演獨立或合作完成一集或幾集劇情,各自塑造不同的人物,描繪不同的場景,講述不同的故事。“拼盤式電視劇”可以作為除單本劇、系列劇和連續劇之外的新的劇類名稱,正式進入電視劇類型和結構的大家庭。 本文把“拼盤式電視劇”(簡稱“拼盤劇”)作為一種新的結構類型來定義近年出現的這類劇目,并將其概念化,這對學術研究和創作探討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價值。
當然,也有人提出用“時代報告劇”來命名此類電視劇,如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在正式會議報告和文件中,使用“時代報告劇”這一名稱組織、策劃了疫情防控、精準扶貧、建黨百年、“一帶一路”等重大主題的電視劇創作,因此涌現出一大批不同主題的“時代報告劇”。 雖然這些劇多采用“拼盤”式結構,但“時代報告劇”與“拼盤劇”這兩個名稱卻不可等同,也不可互相取代。 因為“時代報告劇”是從題材內容角度來命名,“拼盤劇”則是從結構角度來定義,“時代報告劇”可以不采用“拼盤”式結構,同樣,“拼盤劇”也不一定都是“時代報告劇”,換言之,“拼盤”式結構并不為“時代報告劇”所專有。
二、“拼盤式電視劇”的結構美學
結構既是一種劇作類型的認知路徑,又是在劇作類型規范指導下創作出的影像的構成框架。 一種結構會生發一種審美認知,即劇作的結構可以塑造觀看者的審美接受思維,讓觀看者形成新的觀劇體驗和習慣。 筆者仔細考察和概括“拼盤劇”的結構要素和創作模式,發現其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審美特征。
(一)共同主題下的獨立短故事拼裝
它既然被稱為“拼盤”式結構,那么就一定要有拼盤的內在邏輯或理由。 “拼盤劇”的內在邏輯基礎是鮮明的主題或共同的情景、社會背景。 目前采用“拼盤”式結構的“時代報告劇”大多具有宏大而鮮明的主題,比如獻禮、扶貧和抗疫。 “拼盤式電視劇”以主題為核心,多個篇章均圍繞統一主題創作,起到宣傳主題的作用。 一般來說,電視劇中如果出現多個時空場景和多條故事脈絡,就極易讓觀眾產生游離感,而“拼盤劇”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專屬的敘事主體,雖然各情節單元表面并無關聯,但因為“拼盤劇”有凝練的主題,所以無論其在故事結構上發生怎樣的改變,都不會讓觀眾感覺剪輯“撕裂”。
舉例來說,《功勛》講述了于敏、孫家棟、袁隆平、李延年、黃旭華、屠呦呦、申紀蘭、鐘南山等8 位為中國作出重大貢獻的功勛人物的不同故事。 該劇采用每6 集講述一個人物故事的結構,每個故事的敘事風格不同,但因為全劇由共同的主題統攝,所以多個故事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完美的整體。 《在一起》以2020年武漢抗疫為共同主題,選擇不同行業的人物為故事主體,采用每2 集講一個故事的結構,表現全社會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在疫情陰霾之下承受的壓力和痛苦,以及他們的選擇和抗爭。 《石頭開花》同樣是每2 集講述一個故事,聚焦扶貧工作中的十大難題。 劇作講述了在十個貧困情況不同的地區,基層干部、群眾和社會扶貧力量齊心協力擺脫貧困的故事。 從結構上看,每個被拼裝的“拼盤”都是一個獨立的短故事,每個短故事的主人公和情節脈絡各不相同,分別構成完整而獨立的敘事。
“拼盤劇”的結構模式與單本劇、系列劇、連續劇的結構模式明顯不同。 雖然“拼盤劇”的每個故事看起來都像單本劇,但是因為“拼盤”之間有內在關聯,形成整體敘事,所以“拼盤劇”的內容比單本劇豐富、厚重得多,也更具觀賞性。 同時,因為這些劇中沒有足以支撐全劇的固定人物角色,所以“拼盤劇”又與系列劇有所不同。 系列劇(如《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重案六組》等)也是每一集講不同的故事,但是其一般有幾個固定的主要人物。 最后,因為“拼盤劇”中每個故事都獨立成篇,所以它不用像連續劇那樣受縛于故事的連續性,即觀眾不一定要按照劇集順序觀看“拼盤劇”,這大大符合了今天人們的觀看習慣和觀看心理。
隨著手機、平板電腦等媒介深度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每天不得不用大量時間來處理各種信息,體驗不斷加速的社會生活節奏,不再有心情坐在電視機前從容觀劇,而多元觀看終端也解除了先前觀眾與電視劇播放時間的約定。 從某種意義上說,“拼盤劇”的出現或許正好迎合了這種生活節奏。 同時,“拼盤劇”的結構也讓觀眾獲得了類似觀影的體驗。以2022 年播出的《我們這十年》為例,該劇每4 集講述一個獨立完整的故事,4 集的時長相當于一部加長版電影,這樣既可以保證故事講述得細膩、完整,又能夠讓觀眾獲得類似觀看一部電影的情節滿足感和體驗。
(二)群像中的個體呈現與“輪轉的主體性”
“拼盤式電視劇”通過塑造大背景下的群體“雕像”來反映宏大主題、再現時代精神,從而整合出一種集體敘事,引發觀眾的家國情懷共鳴。 “拼盤式電視劇”人物眾多,主要角色分集輪流出場,進行群像式呈現。 這一特點在抗疫劇《在一起》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該劇每2 集講述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分別為抗疫過程中不同身份的人,從武漢各醫院的醫護人員到外賣小哥,從公安干警到基層社區工作者,從援鄂醫療隊隊員到各地疾控中心流調隊伍,等等。 每個故事都由兩到三個主人公共同演繹,這一安排使這一部劇有了多達幾十位主人公,眾多主人公集合在一起,構成了同一個主題框架下的“群像”。 同時,這些主人公又分別擔當了2 集劇情中的敘事主體,他們的身份、性格和精神品質都被細致地刻畫,因而每個人物形象都真實而飽滿。
這樣的一種敘事結構,讓群像中的每個個體都能從自我角度來體驗、審視和表達各自的情感、態度,并展開自己的行動,從而獲得屬于自己的主體性。 語言哲學認為,人們開口說話時,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自我概念”來建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言語者用人稱代詞‘我’建立起一個觀察和認識主體,從而建構自我意識和自我概念。 ……語言提供主體的表達形式,而語言形式的使用,即具體的言語行為,則產生人的主體性。”[3]9-15面對疫情,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在言說自己的認知,也體驗和感受疫情給生活帶來的沖擊和改變。 他們言說自我并投入集體戰斗,從而獲得鮮明的主體性。 主體性“是一種存在(existing)的感覺……主體性使得人們可以‘以自己為話題’與自己對話,并促使人們使用創造性的語言表情達意”[4]258。 獲得主體性,可以讓每個抗疫者不再是“被言說的客體”,進而讓觀看者自我代入,體驗主人公的體驗,感受主人公的感受,這樣觀看者就被“定位”在主體的位置上。
這種“輪轉的主體性”結構,不同于電視連續劇中那種固定的主體性——所有劇情都圍繞幾個主人公展開,其他人都只是配角,主角眼中的“他者”,很難獲得自己的主體性。 而主體輪轉的“拼盤”式結構中的人物,就像是在一個巨型轉盤上的雕塑群像,轉盤不停轉動,群像中的每個人都能轉到觀眾面前并停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講述完畢后,轉盤轉動,輪轉到后面的主人公。 可以說,正是這種“拼盤”式結構讓《在一起》這部劇很好地解決了多主體性展示的問題,這是根據題材內容進行的獨特創造,給觀眾帶來新鮮的審美體驗。 該劇在某種意義上真實地反映了疫情時代社會的本來面貌,即在抗疫的大舞臺上,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職務高低,每一個人都是責任主體,大家只有同舟共濟,才能攜手戰勝疫情。 同時,該劇以小人物為主體重構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讓人感受到自己和祖國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使人產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
(三)“各表一枝”:集體協作下的同臺競技
從創作實踐層面看,“拼盤”式結構中的每個故事都獨立、完整,因而劇作可以由不同的導演攝制團隊和演員陣容分頭同步進行拍攝和制作,這種類似傳統古典章回小說“各表一枝”的敘述方式,極大提高了電視劇的制作效率。 我們仍以《在一起》為例,每個拍攝團隊和演員陣容都只負責演繹總時長90 分鐘的2 集故事,這只相當于一部微電影的工作量,因而比起動輒幾十集的連續劇,這種方式的操作周期較短,一般兩周就可以完成。 多個攝制團隊同步操作,也大大縮短了整體制作周期,這讓“拼盤”式結構電視劇可以從容應對某些較為緊迫、講究時效的特殊創作任務。
更重要的是,這種“各表一枝”的高效率操作方式是提高電視劇作品質量的重要機制。 雖然各個團隊有自己的獨立故事腳本,但是因為最終要合在一起成為巨大的“拼盤”,所以就意味著整部劇的各部分要在播出時“同臺競技”,劇集創作成為一場關于導演和演員功力的比賽,觀眾或有意或無意地對不同單元的故事進行比較,這無形中給了每個團隊類似參加比賽的壓力。 當然,這種壓力同時也是動力,它激勵著每個團隊高質量完成自己負責的獨立故事,不給整部劇拖后腿。 正是這種既合作又比拼的協作機制,促使每個導演團隊和演員陣容必須拿出全部精力和創造力,讓自己負責的這個“拼盤”部分不要“掉隊”,從而保證了整部劇的質量,并使之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藝術風格。
以抗疫劇《在一起》為例,該劇的不同單元由不同導演執導,帶有他們獨特的藝術風格,不同單元之間風格與風格的轉換也非常巧妙靈活。 例如《生命的拐點》直面與病毒遭遇的主戰場——醫院,表現醫生們的大無畏精神和大愛仁心;《擺渡人》以外賣小哥的游動視角,表現疫情帶來的災難和疾苦,以及普通人克服恐懼后投入戰斗的心路歷程;《救護者》用近乎實錄的鏡頭再現軍地醫護工作人員聯合作戰的具體細節和專業精神;《同行》以兩位已各自回家過年的青年醫生重返抗疫一線的過程為情節脈絡,帶有愛情喜劇色彩,給抗疫劇增添了溫暖和浪漫;《搜索24 小時》借鑒懸疑片的風格,演繹流調人員遭遇的困難并表現他們的智慧……只有在“拼盤”式結構下,這種同臺競技才能展現出如此風格鮮明的藝術表現力。
再以《功勛》為例,全劇由鄭曉龍擔任總導演,由毛衛寧、沈嚴、康洪雷等8 位導演各執導一個人物的獨立故事。 該劇獲得了良好的收視份額和口碑,“據‘中國視聽大數據’(CVB)統計,全劇48 集攬獲20.455%電視觀眾,回看用戶規模始終位居黃金時段電視劇第一”[5]。 在“獻禮”的主旋律命題下,《功勛》做到了兼顧市場娛樂性、愛國主義教育和不同導演藝術風格的個性展現,超高的完成度體現了幾位導演的深厚功力。 該劇由于主題特殊,選角標準非常嚴格,整部劇有三十多位優秀演員加盟,其中八位主角無一是“流量”明星。 在這場同臺競技中,主演和配角都貢獻了精湛演技,把人物塑造得非常飽滿,讓觀眾在一部劇中能夠欣賞到眾多不同類型演員的表演風格和藝術魅力。
三、“拼盤式電視劇”的結構張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劇類型的演變史,也是一部類型之間通過雜交、混搭而不斷創新的歷史。 一方面,“類型的定位,可以吸收和穩定習慣于看某種類型節目的忠實觀眾”[1]51;另一方面,影視創作手法本身的開放性和靈活性,使得劇目類型結構表現出混搭和模糊的特性。 同時,隨著新技術手段的出現,電視劇的表現手法和創作觀念也不斷變化,結構類型不斷革新。 因此,類型的固定和變革是推動電視劇創新的結構張力。
當然,采用新的結構類型并不意味著就能出現好的作品,目前我國“拼盤劇”依然處于良莠不齊的狀態。 這些劇作的主要問題包括人物形象不夠豐滿、細節缺少生活體驗、故事情節簡單生硬、圖解主題意味過濃、各個“拼盤”故事水平參差不齊等,這說明一些創作者需要充分認識到“拼盤式電視劇”的結構張力,把握好類型的約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平衡,從而提升“拼盤式電視劇”的藝術水平。
(一)“拼盤”時長要服從于人物形象塑造
“拼盤劇”的每一個故事的時長都相對較短,一般只有一到兩集,因此沒有太多時間用于塑造人物形象。 但是電視劇畢竟不同于專題片,不能只滿足于表達主題,還要致力于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因此,“拼盤劇”要設定恰當的時長,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
目前看來,每一個“拼盤”故事以時長不少于2集(每集45 分鐘)為宜。 故事如果時長少于2 集,則很難展現跌宕的情節或展示生動的細節,人物性格和形象刻畫難以有較大的施展空間。 例如《理想照耀中國》每集用短短30 分鐘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而且時間跨度極大,很多情節缺少細節支撐,故事流于膚淺的概念圖解,劇集之間的排列也缺少內在邏輯,讓觀眾感覺摸不著頭腦。 這樣的創作方式導致人物形象蒼白,缺少主體性,只能淪為宏大敘事下的某種符號或標簽,不能走進觀眾心里。
但是,每個“拼盤”故事的時長太長,也不利于“拼盤劇”結構優勢的發揮。 如果一個故事講了好多集還沒有講完,會讓觀眾忘記這是“拼盤劇”,以為它是電視連續劇。 比如,在獻禮劇《功勛》中,每個人物的故事用6 集時長來講述,這雖然讓故事背景交代得更充分,情節設計和細節刻畫得更從容,人物角色塑造與具體環境聯系得更緊密,但是又使觀眾覺得故事展開過于緩慢,在一個故事里停留的時間過長。 2022年廣受贊譽的《我們這十年》,則是用每4 集一個“拼盤”的方式展開故事講述,顯得更為恰當,體現了“拼盤劇”的結構優勢。 如果說連續劇展現的是人物的成長或變化,偏重縱向的深度,那么“拼盤劇”則是展現同一主題下人物故事的共通性,偏重橫向的廣度。無論如何,人物塑造仍然是第一要務,只有人物故事真實可信,主題表達才能有所依托。
(二)巧妙構思故事,讓抽象主題落地
如前文所述,“拼盤式電視劇”的每個故事的時長僅相當于一部電影或微電影,它對主題的詮釋力量來自多個故事的拼裝與合力。 相對于電視連續劇而言,“拼盤劇”通過在平面上的鋪展表現主題,而不是垂直向的深入。 這種結構具有先天獨立性,會導致故事之間的弱關聯,這樣一來,就可能使劇作對主題的詮釋只是一種低水平的重復。 同時,對于常年沉浸于欣賞連續劇結構的電視觀眾來說,“拼盤劇”結構往往會帶來單本劇容易產生的“陌生感”:剛剛結識了一個人物,熟悉了他的生活,很快就要再換一個人物,又要重新認識和熟悉他,這種不斷重復的陌生感,很容易讓觀眾感到不能與人物“共同生活”。 因此,如果能讓觀眾在前一個單元故事中認識接下來單元的主人公,就會激起他們極大的觀看興趣。
以《在一起》為例,每個“拼盤”故事表面獨立,但是編導巧妙埋下暗線,將不同的故事勾連起來,不僅很好地解決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問題,還做到了主題表達的統一。 埋下暗線的方式是讓人物交替出現在不同的故事中,同一人物在不同單元中出現可以將不同的故事勾連起來。 例如,在第1 集和第2 集《生命的拐點》中,主角是江漢醫院的醫生們,為他們送“愛心口罩”的快遞員是第3 集和第4 集《擺渡人》中的主角外賣小哥辜勇。 在《生命的拐點》中,辜勇是一個不起眼的配角,而在《擺渡人》中,他成為主角,作為外賣小哥的他,在特殊時期發揮了“擺渡人”的作用,為不能出門的人們送去需要的東西和溫暖。他為在醫院做志愿者的賈長安送去醫生們需要的口罩,賈長安的女朋友正在江漢醫院接受新冠肺炎治療,這里的醫護人員便是《生命的拐點》中的主角。這種主、配角色在不同敘事鏈條中的互換,產生了一種視角轉換效果,讓“輪轉的主體性”得以實現,加強了每個獨立故事之間的關聯,從而深化了主題。
當然,這種設置人物關系和加強故事關聯度的方式,需要有現實基礎。 《在一起》的設置之所以完全合理,是因為它講的是同一座城市中的故事。 假如故事發生在不同地方,這些人物就不大可能關聯起來,那么電視劇創作者就要在每個“拼盤”中巧妙構思故事,挖掘和豐富細節,讓抽象的主題能夠落地,讓真實的生活折射主題,而非直白地表達。 以《我們這十年》為例,全劇故事的發生地涉及河南、新疆、廣東、浙江、北京、內蒙古、寧夏、湖北、貴州等十多個省市,還有一些非洲國家。 如果強行讓這些故事發生關聯難免顯得有些牽強,攝制組采取讓主題落地的創作思路,這樣就使每個故事都有真實的生活做支撐,鮮活的生活場景和生動的人物故事讓觀眾幾乎忘記了主題的存在。
(三)處理好宣傳性與藝術性之的平衡關系
由于故事短小精悍,加上多個攝制團隊同時操作,“拼盤式電視劇”往往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制作。因此“拼盤式電視劇”適用于有時效要求的主題宣傳,特別是獻禮題材和時代報告題材的電視劇,都對播出時間有要求,錯過了宣傳的時間節點,也就失去了播出的意義。 但是,對電視藝術作品來說,無論為了什么樣的宣傳主題,都必須把藝術性建立在宣傳性之上,沒有藝術性,主題宣傳就很難取得好的效果。可以說,藝術性是宣傳性得以附著的基礎和產生效果的前提。 因此,電視劇創作者要尊重創作規律,把握好宣傳性和藝術性之間的平衡。 電視劇創作不是“貼標簽、喊口號”,而是要用鮮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出色的影像語言來詮釋宏大和抽象的主題。 優秀的“拼盤劇”必先讓觀眾獲得審美體驗,才可能讓其接受劇作的宣傳宗旨和主題意涵。
我們仍以抗疫劇《在一起》為例。 該劇除了上文所述的結構優點之外,還在情節設計、矛盾展開、懸念營造、細節表現等方面頗具匠心,例如其根據每個“拼盤”故事的氛圍和基調做相應的影調、色調設計,讓畫面呈現出某種“電影感”。 正是因為該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非常用心,所以其才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 不少觀眾坦言,觀看此劇時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劇情場景中,忍不住掉下眼淚。 正如某位網友所說,“說它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抗疫劇,絲毫不為過”[6]。同樣,今年觀眾熱議的《我們這十年》,也是在劇本、表演、攝影、場景設計、節奏、風格等方面頗為用心,讓一個個人物故事深入人心,才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其中《唐宮夜宴》《熱愛》《沙漠之光》的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都有原型,故事充滿了生動的細節,又有曲折的情節,主人公解決困難的過程反映了時代變化的印記。 這種扎根生活、以小見大的創作思路,讓十一個故事都從生活細處落筆,通過小切口反映大主題,以小人物折射大時代,也讓每一個觀劇者能切切實實感受到這十年中的自己。
四、結語
綜上所述,“拼盤式電視劇”是中國電視劇對電視劇結構類型的一次創新。 “拼盤式電視劇”有著匯聚多元藝術個性的結構優勢,還有著廣闊的探索和創造空間,它可以容納多元風格的共存,同時,相對獨立的分段敘事能夠更好地支撐劇作主題的藝術表達,在對宏大主題的演繹方面,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隨著采用“拼盤劇”創作模式的優秀劇作不斷增多,“拼盤”式結構類型劇或將成為記錄國家進步和時代變遷的重要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