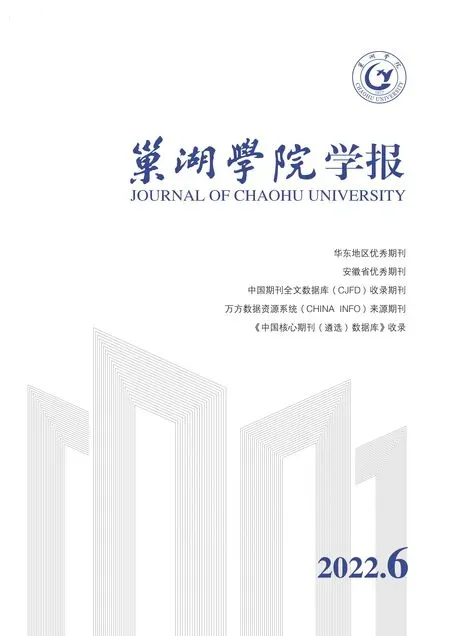近代知識分子對于“迷信”的反應
——以方志文獻為中心
宋露露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引言
何為“迷信”?其詞匯運用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當時的墓志有云:“既下車,聞有僧道巒署火於頂,加鉗於頸,以苦行惑民,人心大迷信。”[1]此處的“迷信”一詞盡管表達了盲從之義,但并未揭露非理性的本質內涵。近代意義的“迷信”含義,是由日本東傳而至,經本土三次建構而逐漸生成為一種時勢性話語[2]。“迷信”作為中國固有之詞匯,在與外來意義嫁接的同時,逐漸成為反對傳統神靈信仰的重要指涉,甚至在五四時期被賦予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批判意義。“迷信”是近代為數不多并廣泛流行于諸多領域的外來詞匯,成為新舊之爭、宗教駁難和政治攻訐最為常用的話語利器。
目前學界從概念史、思想史和社會史層面對近代“迷信”話語及行為的生成與流變有較為成熟的研究,以此透視當時的思潮激蕩和社會變遷均大有裨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沈潔[3-4]、宋紅娟[5]、徐志偉[6]、陳玉芳[7]、羅檢秋[8]以及黃克武[9]所著論文。上述研究多傾向于從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演變歷程中去考察“迷信”的嬗變,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保持著歷史的慣性,突兀性的思想轉向不是歷史發展的真實邏輯,如何從遮蔽的歷史面貌中挖掘史實真相,成為這一話語研究的重要課題。易言之,在“迷信”話語的發展歷程中,“迷信”一詞具體的指涉對象到底有哪些?傳統知識分子是如何認識“迷信”的相關行為?他們又對種種“迷信”的傳播作何反應?這對完整理解“迷信”與“反迷信”行為斗爭的誘因具有重要價值,同時對正確認識身處外來強勢話語的壓迫之下的傳統思想,重新審視其合理價值具有反思意義。
一、本土與外來:“迷信”的指涉對象與文本統計
“迷信”一詞的非理性內涵是在晚清時期由日本傳入中國,此后直至五四運動之前,“迷信”一直處于初級傳入階段,且易被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用于指涉一些社會現象和思想觀念。應該說,“迷信”在傳入之初,傳統知識分子在話語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清末民初,報刊成為新式知識分子的主要宣傳陣地,傳統知識分子對“迷信”建構的聲音,更多只能從地方文獻中反映出來。民國時期,由于方志的編纂仍有相當部分的傳統知識分子參與其中,這就使得借此來窺探他們對“迷信”的認知建構成為了可能。傳統知識分子將“信仰”和“經驗”與“迷信”做了嚴格區分,認為信仰是精神的寄托,是人們的行為依據,是一種自然而生的心理行為,不能將“信仰”與“迷信”進行等同,“信仰于觀感,則傚亦于是儒之于孔,釋之于佛,道之于老,回之于謨漢默德,敬之于天主耶穌,皆以信仰之誠,舉而行祀,禱之禮,迷信云乎哉?”[10]而“經驗”也不能一概以“迷信”等同視之,如“因果報應論”,他們認為“一輩留,下一輩接,報應循環”并非迷信,原因在于“小兒皆富于模摩仿性,自有知覺,而后見其父母所作所為,無論善惡皆以為當然,日久既可與之同化,旁觀者見其報應迅速,誤以為有鬼神。”[11]另外,“鴟鸮突呌,夜間鳴聲,最惡人,多厭之,或以其鳴處附近將死人。此雖迷信,亦由經驗而得也。”[12]“經驗”豐富者,可方便日后生活。而“迷信”多是崇拜虛無縹緲的不經之物,迷惑自身心智。概而言之,“信仰”與“經驗”不等同于“迷信”,前二者是人的心理本能和生活智慧,而“迷信”者立意虛渺,脫離實踐。
荒誕不經是“迷信”的重要表征,僅以“信仰”和“經驗”為尺度,難以對“迷信”指涉對象實現有效區分。為此,傳統知識分子也將“理性”作為衡量尺度,將社會上存在的諸多現象視為“迷信”,并分為三類。首先是神權迷信。神權作為皇權之外衣,是王朝時代君主鞏固自身統治、駕馭臣民的重要手段。傳統知識分子并非因循守舊,倡行皇權專制,很多開明人士實際以批判紳權來反對君主專制制度,認為“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各祭其先,各有專祀,無或僭也”[13],此套禮儀無可詬病,但認為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事物能夠與人溝通,并且擁有賜福降禍的職能,則屬于“迷信”的范疇。其次是偶像迷信。所謂偶像,主要指一些民間的神靈,它們充斥于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各村偶像所在,多有以土地祠、關帝廟為最多,如真武菩薩、碧霞元君、泰岳行宮、水火三官等次之”[14],人們若要行卜、求相、問卦、邀福、除禍等,則祭拜上述偶像,以求其可以保四方平安。最后是行為迷信。所謂行為迷信,主要指供奉年畫、迎神賽會、祈雨、跪香治病、組織神會、奔赴廟會、夜觀星象、堪輿、叫魂、燒胎等,認為人們參加了這些活動,就能驅災避禍,若遇災荒干旱或久病不愈時,參見上述活動,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迷信”在傳入之初,宗教成為其主要指涉對象。清末民初,儒釋道是否視為宗教,在傳統知識分子之間存在分歧,即使部分傳統知識分子也將儒家納入宗教行列,但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旨趣,即他們幾乎都反對將儒教看作迷信。民國《順義縣志》載:“中國神道設教,歷史性最長,漸成多神教,無地不神,無物非神,除少數知識階級崇拜儒道有關政治教養外,余皆迷信神權,無裨實際。”[15]根據對民國時期縣志文獻的統計,不難看出各地縣志對儒釋道是否屬于“迷信”存在較大分歧,尤其是在對待佛道二教的態度上。以《愛如生數據庫·中國方志庫》包含的20世紀上半葉縣志為例,發現“迷信”一詞出現的頻率極高,全國所有省份基本上都可檢索出相關內容。現將數據庫包含的縣志整理完畢,依據省份的不同,對含有“迷信”一詞的縣志進行數據表格化處理。
如表1統計可知,總體上民國縣志對“迷信”一詞不加避諱,文本記載頗豐。但各個省份對“迷信”記載的敏感程度卻不相同。首先,東部沿海地區(如山東、福建、江蘇、廣東、浙江等地)對“迷信”的記載較多;其次,北方中部地區(如河南、陜西、河北、山西、安徽等地)對“迷信”記載平均數在全國居于高位;最后,西南邊疆地區(四川、云南等地)對“迷信”的記載也可排全國前列。其中,山東各縣志對“迷信”一詞的記載頗多,主要由于該地文化上擁有良好的儒家知識氛圍,知識分子有記史之傳統,“迷信之談,怪異之事,游戲之文,皆附錄焉”[16]。其地理上又處于東部沿海地帶,便于近代科學主義的傳入,讓虛無縹緲的“迷信”有了參照物,“自科學興,迷信衰,而祠廟之崇祀遂歇。”[17]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得到解放,對“迷信”一詞的接受更為敏感,從而也導致當地多數“迷信”活動不攻自破。而地處中部地帶的河南、陜西、河北等省,自近代科學主義的傳入則在此區域大力宣傳:“宣傳材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黨政綱政策、七項運動、推行國歷、剿匪御侮以及風俗改良、破除迷信、天足運動等”[18],使得知識分子改變以前的思維方式,在強化對“迷信”認識的同時,也加快他們破除“迷信”活動的步伐。再看地處南方的四川、云南等省,對“迷信”記載的頻率亦是較高。自古以來川滇兩地便是中央統治的薄弱地帶,民國時期更是軍閥割據時代,政治文化上混亂不堪,“迷信之中于人心,牢不可破,縣俗尤以婦女為特甚,明哲者嗤之、謂之婆婆經。近以民智日開,斯風漸泯,然猶有可述者存焉。茲略記其一二,以存縣之舊俗。”[19]邊疆地區的知識分子,在亂世中將延續傳統文化的行為視為精神寄托,因此“迷信”活動出現較多。

表1 民國時期方志文獻中“三教”是否屬于迷信的統計
轉而聚焦到深層意義上,各省對儒釋道三教的歸類也存在分歧。由表1不難看出,對釋道二教的歸類爭議較多,多數省份易將二者歸為“迷信”。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認為道教的護符、咒語蠱惑民心,容易被狡黠之教徒所利用[20],佛教的廟會、焚香、祭祀會造成大量浪費[21],導致社會無所進步,往往將二者歸為不利的一方。但究其數量,道教較佛教的頻次偏低。據統計有9個省份將道教信仰歸為“迷信”,而將佛教歸為“迷信”的頻次則高達19個省份。其原因是:道教為中國的本土宗教,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感情羈絆;而佛教為外傳宗教,系統治者控制百姓的一種精神枷鎖,其興衰與統治者的喜好關系更為密切。“吾國黃老之學既盛行西漢,而佛教則發韌東京,至南北朝而大盛,歷千余年竝行不廢。”[22]除此之外,大致有9個省份認為儒釋道均不屬迷信,應歸屬于民國時期正常的宗教信仰;而僅有3個省份將儒教歸為“迷信”。為何將儒家歸為“迷信”的省份如此之少?主要是儒家長期居于正統地位,統治者和民眾均依賴和認可儒家文化。且儒家的“仁”“義”道德,長期禁錮人民思想,是統治者治國理民的利器。儒釋道三教為中國的傳統宗教,其之所以仍存在較多爭論,主要是科學主義的興盛、國人反思造成的結果。
由上可知,民國時期“迷信”的發展初期,并不拘泥于單一的行為指向,而是分為神權、偶像、行為和宗教的多種類別指向。傳統知識分子在調適上述類別的同時,會著重區分“迷信”到底是何種情形。又因各省的地理、文化存在差異,對“迷信”記載的頻次和儒釋道三教的歸類也存在較大分歧。總而言之,在限定傳統語境的束縛下,“迷信”在初期發展過程中,不斷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二、沖突與共識:新舊知識分子對“迷信”的認知異同
民國時期是近代中國政治劇變和思想激蕩的特殊歷史時段,新舊沖突極為尖銳和明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隨著科學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迷信”傳播進入中期發展階段,并成為主導性的社會思潮,傳統知識分子的輿論呼聲漸趨弱化,有被遮蔽之勢。實際上,這一時期新舊知識分子分子對“迷信”的認知有較大差異,主要反映在政治、秩序和民生三個方面。在此期間,也衍生出較多共識。
身處啟蒙思想和科學主義交鋒的時代,人們無法掙脫時代潮流的漩渦,安居一隅。在“迷信”傳入的中期階段,衍生出了部分共識。一是在民國方志內容的書寫上,新舊知識分子均透露著歧視女性的觀點。認為“迷信”人群,以女性居多,且思想難以開化。“迷信之中于人心,牢不可破,縣俗尤以婦女為特甚,明哲者嗤之、謂之婆婆經。”[19]“婦女迷信較男子為甚,每有休咎,求神間卜,遂許神以報答,名曰許愿。”[23]從中可以清晰感知,無論是傳統時代還是民國現代化改造時期,都深刻透露出對女性的輕視。二是一般不將儒家歸為宗教迷信,認為孔子是教育家、哲學家、大思想家,祀孔不為“迷信”,是紀念偉人的特殊方式。“邑向僅有儒道釋三教,儒教全系學說不具迷信,上級社會大都以儒學為依歸,而旁參佛學之哲理。”[24]儒家為正常的宗教信仰,是神權時代、封建專制時期以及民國開化時期所擁有的共識。三是對舊志部分內容的改動一致,對于“迷信”資料,甄別錄入。關于警示未來、民生教育、教化民眾、風俗類別以及天時人事均要詳細記載,以備后人研究。事關怪誕神話,看其是否關乎民生,酌情記錄。“舊志寺觀、禨祥概未錄入,祠祀類之協人心公義者書之如舊。”[25]對舊志的修改,新舊知識分子的認知出奇一致,都主張用科學觀點代替“迷信”的落后之處。在“迷信”共識愈多的情況下,也不能夠忽視差異的多樣性。
從秩序的維度來看,新式知識分子受西式教育和科學思想的影響,認為前清的祭典均系“迷信”,無論淫祀或正祀,應一律取消:“余前清祭典所載,凡涉於迷信者,應行廢止。”[26]反觀鄉村士紳,祀典是其精神支柱。“夫祀典所以表人心之宗仰者也。凡人有心,不可以無所系屬。理想高尚者,其所宗仰正以碻理想;低下者,其所宗仰鄙以俚要為。有所系屬,以趨於向善,則一也。人知迷信之當祛,不知迷信而外,尚有不可祛者存,則非除塑信者之所與知也。”[27]若將祀典驟然革除,意味著民間宗教團體信仰的崩塌,而統治階級也將無法控制群眾,最終導致社會秩序暴亂。傳統知識分子受封建社會殘余思想的影響,認為祀典應保留正祀,將儀式記錄下來,供后人觀摩。“使國家稍暇,當必有以重行厘訂之,然則封建時代之祀禮,雖已屬諸歷史陳跡,亦足以見一代之典章制度,是烏可以不志哉?”[28]后人通過研究當時所推行的典章制度,可以窺見當時的社會秩序,觀攬民生百態。
從政治的維度來看,中國傳統社會自古以來等級森嚴,不可僭越。而民國時期受啟蒙思想和科學主義的影響,新式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便將“迷信”與國家的命運悄然聯系在一起,認為“迷信”不破,國家不興。“近自總理破除迷信,城鎮偶像多數打倒,與其用神道愚民,孰如開新知而進取,有以治內而御外也。”[15]“迷信”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破除“迷信”被視為安定內部的一種手段。另外,一些激進的新式青年,認為理應舍棄一切“迷信”行為。據《沁源縣縣志》中載:
何夫神道設教,先王妙用存焉。近世科學昌明,民智漸啟,青年學子吐棄一切,舉前人振飭人心之具,輒斥為迷信,而不屑一顧。不知法律、道德相互為用,今日富強之國,無逾歐西,而膜拜上帝之教堂,行將遍及全球,非迷信而安得?以五十步笑百步,以國勢之強弱定禮教之優劣也哉![29]
上述材料表明的實質是,新式知識分子表面上透露出振興中華的愿景,實則摻雜著崇洋媚外之情。反觀傳統知識分子,認為“社稷壇”和“廟宇壇”設立初衷是紀念為民造福之人,此行為與國外紀念偉人毫無二致,便不愿將二者歸為“迷信”。“吾中國自古以農為本,稷功在播種發明粒食,然五谷非土,無以生故,自夏商以迄,明清均立壇,致祭以示推本報功,與歐美各邦,紀念創造事業偉人之義同一心理,若以為迷信,不免有述典忘祖之誚矣。”[30]將設壇紀念等行為歸為“迷信”,有矯枉過正之義,既傷害民眾的精神家園,又損害了傳統文化的延綿性。因而,割裂基層群眾感情的激進行為阻礙民國現代化改造的進程,更無法達到振興國家的目的。
從民生的維度來看,新式知識分子認為“迷信”積弊尤深,“惟今社會進化,趨重實際,以舊喪禮之繁雜、虛偽迷信以及不經濟、耗光陰,深與時代不合,函應加以改革。”[31]與“迷信”相伴隨行的祭拜、婚喪以及堪輿等行為,對民生造成巨大的損害。自然災害多依托于祭拜神靈;婚姻大事又往往格于生辰八字的束縛,不能自主選擇;住房選擇熱衷于風水算術等迂腐觀念,導致社會民生事系“迷信”,無法隨心所欲進行選擇。而傳統知識分子認識到“迷信”對民生的雙面性,破除“迷信”不能急于求成。若將焚香、廟會、迎神賽會等傳統活動例行禁止,必然導致產業鏈斷裂,甚至造成商業經濟的極速滑坡。“迎神賽會,雖曰跡近迷信,然亦繁榮市面,維持商業之一道也。”[32]在此期間,廟宇更是“迷信”的代名詞,但廟宇最多之處往往是商業繁榮地區,是人民活動力所表現之一端[33]。若將廟門破壞,直接導致人民失業、祭拜無門,社會活力消散。
除上述三個視角外,從方志內容改動來看,不僅存在共識,亦出現分歧部分。以奇聞軼事為例,新式知識分子認為,奇聞軼事多涉及神話迷信,應予以刪除,“歷來異聞多涉神話,方當破除迷信之際。本欄應即刪除。”[34]應當順應破除“迷信”的浪潮,奇聞一類概不錄入。但傳統知識分子觀點與之相悖,認為身經軼聞應予以保留,附錄于結尾,“妄言妄聽,摭拾數事,附錄卷尾,志佚聞。”[35]軼聞有著豐富的史料價值,可以佐證后世研究,窺探社會秩序和人民心理。
據上述可知,由于時代思想沖擊的加強,“迷信”傳播逐漸進入中期階段。其主要表現便是新舊知識分子產生激烈的觀念沖突與思想共鳴。此階段亦是“迷信”發展的強勢階段,開始滲透到社會層級的重要方面。
三、不一而足:“迷信”與“反迷信”之間產生斗爭的誘因
處在民國節點的特殊時期,以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神祠存廢條例》為界限,“迷信”的發展進入后期斗爭階段,但相伴而來的“反迷信”呼聲也日益強烈,二者順勢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其中,雙面性的難以調和是斗爭產生的主要誘因,保留傳統“迷信”觀念,是特殊時代教育的局限,是多數民眾內心的依戀,又是舊知識分子延續傳統文化的要求,從中能夠彰顯出“迷信”自然而然的正向性。而推行“反迷信”運動,是先進知識分子受到科學主義的沖擊而逐步衍生出來的具體實踐。但由于未考慮時代的現實情況,導致“反迷信”政策難以上下統一,且對社會產生了許多危害,從中不免映射出“反迷信”運動自身所攜帶的反向性。二者在正面與反面自然交織的過程中,又展現出“迷信”與“反迷信”運動之間所具有的沖突性。
在民國時期“迷信”的觀念難以破除,是二者產生斗爭的主要誘因之一。首先,“迷信”屬于普遍心理,蘊涵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時人將“迷信”作為衡量感情深淺的尺度,多數人認為“迷信深而情摯,迷信淺而情偽。”[36]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以感情為衡量標準,精神上更加依賴“迷信”活動。如“焚燒祈禱”用以支撐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香火行業則用來維持商業的發展。若此時強勢推行“反迷信”運動,則會破壞民眾長期努力營造的精神世界,損害社會秩序的穩定。另外,“迷信”的方式也是日新月異,當時出現了冥票風靡一時的情景,且銷售范圍廣泛。當時人更是戲稱“謂我國民貧鬼富,外國民富鬼貧,陰曹必有向我國大借款者。”[37]顯然,在當時“迷信”的心理、活動與方式與下層群眾關系密切,而“迷信”觀念的難以革除,正是阻礙“反迷信”運動文化宣傳的癥結所在。
其次,教育難以普及。當時主持市政之人,一味標榜現代化改造,出臺的政策難免有所偏頗,以為自己謀利。而地方當權者更是擁兵自重,各行其是,導致教育政策難以上下通達。除上述政治因素外,地理位置也是導致教育難以普及的重要因素。一些地區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經濟水平落后、與外界聯系脫節,致使當地群眾根本無法分辨何為“迷信”,內心依舊固守傳統的宗教迷信。“惟生產不豐、經濟既窘,故于教育尚未注意,而迷信亦隨之不破。”[38]且民間廣為流傳的“迷信”傳說均依據當地環境因素杜撰,不僅朗朗上口,更是貼近群眾生活,深入民心。“民間傳說雖與完縣地理有關系,而事涉迷信,幾于全屬空中樓閣,毫無真實之可言,故入風土類。”[39]可見,教育與地理位置的劣勢,直接影響了“迷信”破除的進程,亦使當地人民十分缺乏接受“反迷信”運動的能力。
最后,“反迷信”政策難以統一調度。“民國予人民以信教自由,一面力謀迷信舊污之解除。夫亦日求真理而各行其是耳。”[40]因當時政局割據,各地當權者分屬不同派別,政治觀點和文化水平不一,因此各地對“反迷信”的態度大相徑庭。“反迷信”運動的推行,離不開各個地方領導人和有識之士的引導,“按邑之習俗,多近迷信,雖遞經改革,尚多因仍。司民牧者與鄉先生蓋與有責焉。”[41]地方政府肩負著引導群眾的大任,但因多次勸導無效,難免會滋生放任自流的態度。更有少數不軌之人在推行“反迷信”過程中加上自身企圖,用以謀取私利。上述行為均與知識分子的觀點背道而馳,往往得不到下層有識之士的支持,從而導致“反迷信”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舉步維艱,依舊延續先前的“迷信”行為,在知識分子階層產生矛盾對立。
產生斗爭原因的另一重點在于,具有“迷信”觀念的知識分子建議在保留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改造,而“反迷信”的過程中會產生較多社會危害,與先前觀念背道而馳,在思想領域產生較多摩擦。其一是古跡破壞。被稱為千年國寶的獨樂寺[42]、文峰名勝[43]以及新河縣的千年古物,均被認為攜帶“迷信”色彩,應當拆除。雖然遭到當地群眾的強烈反對,但最終唯有新河廟宇壁畫繪作得以幸免,對傳統實體文化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其二是經濟損害。隨著“反迷信”活動的愈演愈烈,也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沖擊。如以售賣香火維生的人,大都面臨失業的困境,“自民國以來,禁止迷信,錫紙生意一落千丈,邇來產銷甚微,女人因此失業,全仗男人謀生,無法補救。”[44]此外,政府額外加征“迷信捐”,加重日常生活支出,削弱市場消費能力。“省頒暫行辦法,系住民舉辦誦經、禮懺、普渡、迎神等迷信事務,均須按其一次消費總額,在一百元以上者,征收迷信捐。”[45]其三是精神損害。民國時期將祭祀的一切形式進行廢除。“夫祀典所以表人心之宗仰者也。凡人有心,不可以無所系屬。”[27]導致傳統文化逐漸丟失,傷害了人民群眾留戀祖先、禱告神靈的慰藉心理,使得內心沉悶、生活壓力無處宣泄。
通過上述對“迷信”和“反迷信”之間沖突原因的敘述,可以看出在“迷信”的建構后期,近代知識分子及社會層面均衍生出與“迷信”相反的活動。而此類行為,因為觀念的先行性和推行的不合理化,導致“迷信”與“反迷信”之間產生了此消彼長的自然化斗爭。但就其實質而言,二者其實是在互相促進、相互制衡的過程中不斷游離,對社會產生福祉的同時,又會造成不可避免的傷害,但最終愿景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斗。
四、余論
“迷信”的傳統發展路徑,與特殊時期的環境密不可分。在“迷信”傳播的調適期間,梁啟超就先后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多篇關于宗教思想的文章。由此說明,先進知識分子已初步開始理清“迷信”對傳統行為所產生的影響;而傳統知識分子受封建制度和教育的束縛,對“迷信”話語的初期調適,并不靈敏。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知識分子對“迷信”的認識也呈現出初期、中期和后期的三級式發展。發展初期,“迷信”指涉對象的內容逐漸豐滿。不僅僅局限于焚香、祭祀、祈雨等具體表象,而將指涉對象進行歸類化處理,且明確指出儒家一般不為“迷信”,是正常的宗教信仰觀。在“迷信”發展的中期階段,新舊知識分子的矛盾逐漸顯露在大眾視野下。在此期間,二者沖突大于共識,傳統知識分子也在新思想的影響下,賦予“迷信”新時代內涵。“反迷信”運動推行,是“迷信”傳播發展后期的最后一環。新舊知識分子更加意識到“迷信”與“反迷信”斗爭的雙面性,必須實施強有力的手段將“迷信”所攜帶的弊端進行革除。
從“迷信”的傳入進程來看,亦可獲得頗多啟示。儒釋道為中國的傳統宗教,一般不屬“迷信”的范疇,在民國時期宗教信仰自由是新舊知識分子的共識。但隨著“迷信”概念性的增強,其對社會滲透力變得更為強勁,我們應當區分糟粕,將好的一面保留下來。所謂發展建構,便是將“迷信”放入傳統的視角下進行審視,保留中國本土特征。而此類發展路徑,其實質是反映了中國思想史演進的一個縮影。由開始的抵觸新文化,到中期的接納,乃至后期的融合,都展現出中華文化強大的張力和愿意接納新事物的決心。總之,“迷信”并不僅指代腐朽落后之物,而是經歷時代條件的洗禮后,逐漸在磨合發展中,不斷賦予新內涵的事物。我們看待“迷信”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西方啟蒙思想,應當在保留本土傳統觀點的基礎上,推陳出新,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發展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傳統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