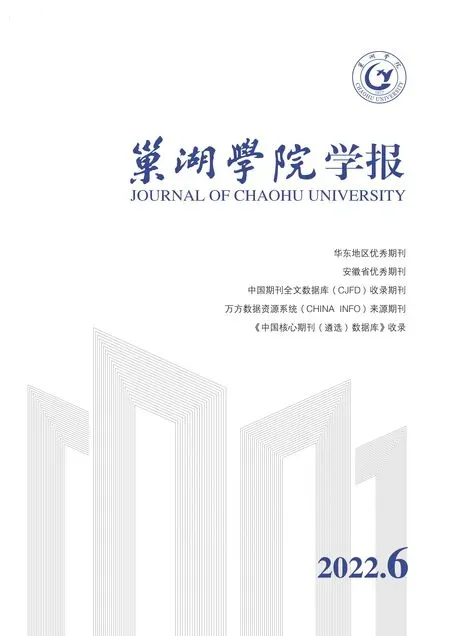從《生活的探求》看二戰時期日本知識青年的身份重構
陳婷婷
(安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引言
島木健作(1903—1945)是一位“半路出家”的日本文學家,也是與政治關聯最緊密的作家之一。島木生于北海道札幌,曾就讀于東北大學法學部,參加過香川縣農民運動,1927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在次年的三·一五事件①三·一五事件:1928年2月國會選舉中,共產黨和勞動農民黨的力量開始增大。為了鎮壓共產黨和扼殺工農運動,田中義一政府于3月15日,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1600人(全年共逮捕3400余人)。4月10日,政府下令解散勞動農民黨、勞動組合評議會和無產階級青年同盟,造成大規模白色恐怖。這次事件之后,日本共產黨主要領袖之一水野成夫發表轉向聲明,宣布承認天皇制,反對沒收天皇、寺社的封建土地,否認日本的殖民主義性質與歐美相同,宣布要建立與日共對峙的勞動者派。1933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日共最高領導人佐野學、鍋山貞親發表轉向聲明,主張實現所謂一國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以天皇制為中心的社會法西斯主義。中被逮捕,1929年發表“轉向”聲明。至1932年獲得假釋為止,島木健作在獄中度過了四年生涯。獲釋后,他走上創作之路。從他最初的短篇集《獄》(1934)到第二短篇集《黎明》(1935)到長篇《重建》(1937)、《生活的探求》(1937)再到其遺作《土地》(1946)等一系列作品,大多敘述了他參加農民運動的經歷。其中,《生活的探求》是日本“轉向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二戰時期暢銷不衰。
有學者認為《生活的探求》亦是“修養小說”①修養小說:這一文學類型起源于18至19世紀的德語文學,德語中以Bildungsroman一詞作為此類文學的通稱。此類小說一般以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為線索,主人公通常先接受家庭和學校教育,然后離鄉漫游,通過結識不同的人、觀察體驗不同的事,并在友誼、愛情、藝術和職業中經歷錯誤和迷茫,由此認識自我和世界,努力走向成熟。除德、日之外,其他國家的同類型小說多譯為“成長小說”。,但其結構相當特殊,蓋因修養小說的主人公所追求的個性解放等近代精神,在這部小說中遭到了法西斯政權的徹底打壓。并且,小說中對“應當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實現自我”的追問,始終與對“轉向”的思考交織在一起。“經典修養小說是傳達資產階級構建市民社會理想的文學載體,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是對抗近代市民社會的,但現代修養小說顯現出的卻是對運動本身的絕望與幻滅感,幾乎無一例外采取了轉向小說的形式。”[1]那么,作為修養小說的《生活的探求》所傳遞的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格教養?“轉向”這一行為本身又是在何種機制下轉化成為對二戰時期日本知識青年的“修養”的?
一、作為“轉向文學”的《生活的探求》之誕生
日文中的“轉向”一詞主要作為政治術語,即“共產主義者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要么從此對主義毫不關心,要么轉為信仰其他主義;狹義上則指共產黨員脫離其組織,并從此不參與任何組織活動。”[2]通常表現為思想路線由左翼轉向右翼。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因其反對專制主義的天皇制,反對侵略戰爭,為爭取工農群眾及其他勞動人民的生活權利和民主自由而斗爭的行動宗旨,遭到日本政府的多次沉重打擊。三·一五事件后,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佐野學、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告共同被告同志書》(1933)。其大意是批判日本共產黨已經逐漸淪為蘇聯共產黨的附庸,日共應當認清日本的歷史與現實。這篇文章被當時的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視為放棄共產主義的聲明書,在黨內掀起了很大的動搖與分裂。1935年末,約有九成共產主義者相繼宣布“轉向”。這其中也包含左翼作家,尤其是從昭和時代初期以后,在治安維持法的嚴酷鎮壓下被迫放棄原本的信仰與創作路線的無產階級文學家,他們成為了轉向文學的創作主體。轉向文學“指的是探討轉向問題的文學,即敘述共產主義者如何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或是探究其脫離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的文學;若界定得更寬泛一些的話,還包括以轉向問題作為主要創作動機的文學。”[2]身為轉向者的作家們將“強制/屈服”的二元對立關系予以文學化的表達,其作品一般是對“轉向”產生的苦惱與內心糾葛的書寫。
島木健作便是轉向群體中的一員,他曾任香川縣日本農民工會的書記。該工會支持當時的勞動農民黨委員長大山郁夫②大山郁夫(1880—1955),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社會活動家、政治學家。1914年為早稻田大學教授。1917年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論委員,宣傳民主主義思想。主張打倒寺內正毅內閣、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1918年因“筆禍事件”退社,1921年開始領導民主主義運動。1926年創立勞動農民黨,任中央執行委員長,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解散,1929年與河上肇等創立新勞農黨。,發起選舉斗爭,后遭到打壓。島木被判違反《治安維持法》,一審判決囚禁五年。島木在獄中肺結核惡化,飽受病痛折磨。二審中,島木向法庭提出“轉向”聲明,即“承認過去自己的行為存在謬誤,今后不會再次參與政治運動”[3]。與其他無產階級文學家不同,島木是在宣告轉向之后才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生涯。
出獄兩年后,島木健作發表處女作《麻風病》(1934),字里行間道出自己“轉向”的首要原因是回避責任和屈服于強權。“他還太年輕,也只不過是個知識分子,他并沒有飽嘗過實際生活的苦水,沒有在那樣的體驗中鍛煉、穩固自身的信仰。……當遭遇到復雜而冷酷的人生的苦澀之時,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思想何其無力,可悲的自己只能在現實的重壓之下幾近被摧垮。”[4]③本文引用的島木健作的作品原文均為筆者自譯,下同。在小說《重建》中,主人公試圖重建因三·一五事件而被摧毀的農民運動,他的壓力不僅來自于工農組織的思想試煉,更來自于舊同志的變節。從《麻風病》到《重建》,能夠清楚看到島木并未徹底宣告自身信仰的敗北,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與現實對抗。然而,這種自我與政治現實不屈不撓的對決到了小說《生活的探求》中,卻悄然變質。
由于“轉向文學”一脈在思想性質上的特殊性,國內難見島木健作小說的中譯本,對于“轉向文學”的研究較為匱乏。日本學界的島木文學研究則呈現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批評方法大多是將島木健作與同時期的另一位轉向文學家中野重治進行對比。高橋春雄[5]詳細梳理了島木和中野迥異的成長經歷,以及兩位原本在政治與文學理想上志同道合的作家在《生活的探求》問世后分道揚鑣的歷程,特別強調了島木長年的牢獄生活、沉疴病痛、出獄后繼續協助地下活動卻又不幸被捕的經歷讓他在文學創作上舉步維艱。荒川有史[6]整理了日本文壇自1937年至1942年圍繞《生活的探求》展開的論爭史,這篇論文同樣以中野對該作的批判為中心,串連起文壇的各派意見,也擷取了島木的自我辯白。荒川由此提出了日本現代文學中農民與農村書寫的問題,開啟了近五年來島木文學研究的新的視角。森山重雄[7]點出了島木與中野決裂的原因,在于《生活的探求》引領轉向文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轉向不只是方向的轉變,而是人的重生。”(林房雄語)這令向來以文學來思考政治的中野重治感到失望。此外,小笠原克[8]指出,島木希冀通過書寫自己作為“組織中的普通個體”的轉向體驗,來整體把握日本共產革命運動的始末,然而島木始終未能在文學作品中從日本社會歷史的視角來觀察其自我生成、精神挫折與身份重建的成長歷程。總體而言,上述代表成果均通過網羅各類相關歷史材料,進行了綿密的實證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一是沒有對作為日本轉向文學體系重要轉折點的小說《生活的探求》進行文本解讀;二是沒有交待清楚島木健作在這部作品中思想劇變的緣由。
二、《生活的探求》的“修養小說”特質
剛升入東京某大學的主人公杉野駿介因罹患肺炎而住院治療,出院后回到農村老家休養,且遲遲未透露出重回東京的意向,《生活的探求》由此開始。面對闊別兩年的農村,駿介反思了自己在東京的生活:“在觀念的世界中泥足深陷,不可自拔,沉醉于這種沒有退路的感覺。……首先自己必須得試著真正地在社會中生存才行。”[9]他認為這樣的想法在農村生活當中能夠得以實踐,于是決定輟學,轉為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這部小說誕生于日本政府嚴格審查出版物的敏感時期,故而島木小心翼翼地繞過了有關共產主義以及工農運動的表述,既沒有指明駿介的“過去”是什么樣的生活,也沒有解釋他“和過去訣別”的必要性在哪里。但對當時的青年讀者來說卻是不言自明,小說顯然是以法西斯化的日本政府當局對共產運動的鎮壓為背景展開。
小說開篇就交待駿介是因為養病才回到農村,痊愈后不過數日,他就決定要舍棄自己一直以來在學業上的努力付出,“終于決定踏出新的一步。不管旁的人怎么看待,這都是他用盡心力求索之后的結果。……他能夠確定的預想只是,踏上這條路之后,從中一定能夠產生對自己來說是全新的東西。”[9]而在島木健作此前的小說《麻風病》中,兩名因從事共產運動而被捕的主角都身染重病,在長期刑囚中從不曾改變信仰,直至走到生命的盡頭。兩部作品中的“病”都帶有隱喻意味,前者是宿命般的人生苦痛,而《生活的探求》中的“病”卻微妙地指代思想上的病,當病痛消失之時,主人公也迎來了“新生”。
駿介是貧農子弟,他奮發向上考取了東京的大學。經老家熟人介紹,得以在實業家岡島家中以打工的形式寄住,每天為了攢錢繼續學業而殫精竭慮,已沒有余力再去思考其他。但他身處大學,感受到身邊學生中不乏憧憬美麗夢想,卻在遭遇現實打擊后一蹶不振之人。駿介認為自己雖然是大學生,待在東京卻做不成什么事。他不想失去生活的熱情,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的步伐是以一種極為模糊、抽象的姿態開始邁出的,通常強烈吸引他的心的事物,乃是某種有生活氣息的、實質性的、內容充實滿溢的、具有生產性的、建設性的、不夸夸其談而是腳踏實地的東西。恰巧在那時,農村生活在他的面前徐徐展開。[9]
從中可以看出,駿介認為自己曾經產生過向往的理想有一種不切實際的鏡花水月之感,盡管共產運動的領導人是知識精英,但是“日本知識分子的歐洲素養是從頭頂灌輸的知識,也就是表層的教養,未能扎根于肉體或生活情感之中。所以這類的知識分子對于法西斯主義缺乏挺身而出地捍衛自己內在個性的智慧和勇氣。”[10]作為昭和時期日本知識階層中堅力量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出身于小工廠主、農戶、小地主、手工業者和小商店主家庭,根深蒂固的農本意識使得大學生自始至終也未能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主導作用。日本共產黨的理論和行動方針未能對標日本社會最緊迫的經濟矛盾,反而高喊打倒君主制的口號,由此招來的只是鎮壓與被群眾所孤立。回顧往昔,島木健作懷著未能做出實事的自卑感,決意不再沉浸于觀念世界,而要去追求具有生產性的且貼近實際生活的理想。回到農村,駿介從給家里挖井開始,學習壘石堆的方法,發現看似單調的勞作中實則孕含著經年累月積累的先人智慧,駿介從中獲得了一種樸實的感動,之后,種植煙草、開辦托兒所等樁樁件件的勞作軼事更是讓他切實體會到自己能夠有所作為的滿足感。
小說《生活的探求》的主人公迥異于島木健作一系列前期作品中旗幟鮮明的革命者形象,盡管駿介顯然遭遇了“轉向”的困境,但仍稱自己“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固定的思想行動立場”。也就是說,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不是一個思想已臻成熟的個體,而是一個有待成長的、“修養小說”主人公式的人物。小說將“法西斯/共產主義”這一重大時代矛盾作了模糊化處理,但是駿介強調自己要“當農民”,想要從零出發的這個“零”,實際上是在島木的《重建》中所記錄的所有反抗斗爭全面失敗之后的“歸零”。小說伊始,駿介就已經認識到,他的理想在外部世界中僅憑一己之力是無法實現的。因此與其自怨自艾,倒不如干脆舍棄知識分子的身份,拋下東京這個“新世界”中的一切,回歸自己出身的農民階層,從農村這一原點重新出發。“這一看似平常的人物設定背后,有著作者深入的思考和決心。主人公駿介肩負的實際上是以往的修養小說中未曾出現過的主題。”[1]以往的修養小說中的主要矛盾在于物質匱乏與藝術追求、審美自由與資本主義工作倫理之間的難以調和,但這部小說中的最大矛盾,卻是個體的和諧發展在根源上的不可能實現,因為一切探尋身份的活動都必須在“尊重國情”、維護軍事法西斯主義體制的前提下展開。
經典修養小說的一大特征是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中會出現“引路人”,在《生活的探求》中,引導駿介走向新生活的引路人的角色也很特殊,是他學識貧乏、經濟困窘的農民父親。因此,“啟蒙者引領蒙昧者”的這一引路人公式在小說中被倒置。這一點同樣體現在駿介與自己的前輩志村克彥的對話交鋒過程中。志村是駿介的同鄉,也是知識分子,先于駿介返回農村,小說暗示了志村也是一名“轉向者”。志村告訴駿介,所謂“歸農”已經由很多從社會上敗退下來的人嘗試過了,結局也都擺在那里。他舉出諸如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①新村:指日本白樺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受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躬耕”生活的影響,于1918年在日向創辦的以勞動互助、共同生活為宗旨的模范新村,他以此作為實踐其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場所。1923年“新村”宣布解體。理想、讓兒子從事農業的島崎藤村,以及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登場的康斯坦丁·列文等與農村有關的人物。志村認為,駿介和那些將農村作為自身地盤的政客和思想教誨師沒什么差別,實質上是一種無方向性的行動主義,是為了逃避才選擇獨善其身。駿介解釋說自己并不是要走別人沒有走過的新道路,而是要逐一嘗試,這樣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進行創造和發展的生活方式。
當今時代,把自己封鎖在小小的軀殼中,把自己一個人的生活過得像樹蔭下的花朵一樣,并不一定是什么難事。……在從前的時代,完成這樣的生活就等于實現了自我。但如今,個人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沒有可能脫離社會。所謂的自我實現,也必須得走上積極作用于社會的道路,將自身意志轉化為社會價值,否則就談不上任何的自我實現。[9]
然而細讀之下會發現,志村所指的“社會”和駿介所回答的“社會”,在內涵上是不一致的。志村認為,當代知識精英所欠缺的是直面社會惡之根源并與之斗爭的勇氣。倘若回到農村守著自家一畝三分地,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建立起民主社會的。而駿介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擺脫“轉向者”這頂帽子帶來的陰影,試圖通過參與生產實踐來完善自己的人格修養。既然轉向已是既成事實,與其執迷于悔恨,惶然于未來,莫不如換一個環境,做一些實在的事情?志村對駿介咄咄逼人的追問反而暴露出沉迷于空想的知識分子的“虛”,反襯出農村勞動者的“實”。
駿介與志村這兩大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欠缺鮮活,因為他們其實是作者本人的分身與思想糾葛的投影。他們彼此的爭論激發駿介的深入思考,賦予了小說高度的思辨性。駿介以一種相對清醒的眼光看待理想與現實,他和許多青年人一樣,謀求“作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人的生存道路”和“作為個人的自己的生存道路”兩者之間的和諧統一。然而他深知:
這樣的道路在現今時代來說何其罕見,即便能夠找到這樣的道路,也絕難踏上。……過去的人們不必如何勞心,便能如同他們偶然選擇的職業道路一般,在客觀上也等于是選擇了一條在社會中生存的人的真實道路。但是,他仍然懷抱著青年人的熱情,思索著在如今這個閉塞時代里生存的深刻意義。倘若在如今的時代,他也找到了自己所追尋的道路,并且堅定不移地走到最后,那比起他所艷羨的那些古代人來說,這會是何等的榮光啊![9]
駿介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是一個黑白顛倒、精神扭曲的時代,因此只能設法尋找在閉塞時代中盡量為理想而生活的方式。此前的修養小說的主人公探求的目標是廢除近代市民社會中的弊端,這一目標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得以短暫實現。然而,日本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卻全面失敗了。在作為個體已經無能為力之時,駿介開始反思日本共產運動中的獨善主義與謬誤。《生活的探求》中犀利指出,共產者相信自己從事的活動是在改革社會現實,但是他們所理解的“現實”只是觀念上的現實,與真實相去甚遠。這些運動內部存在的問題也確實在二戰后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實踐中暴露了出來。
因此,這一時期島木健作的創作重心不在于深入探討轉向,他在創作續篇時表示:“我想描寫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現在的我很有興趣寫幾部修養小說。我希望能描繪出艱苦奮斗的人之美。”[11]但在評判《生活的探求》時,“轉向”是回避不了的定論基調,正是這一特殊底色將它與常規的修養小說區分開來,主人公的成長實質是自我馴化,所找到的“出路”歸根結底是一條妥協的、獨善的自我精神重建之路。
三、轉向者的成長與身份重構
1927年開始,隨著日本軍政當局思想管控的強度提升,馬克思主義被日本主義①日本主義:指從明治時代到二戰戰敗前,由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嶺、高山樗牛等倡導的反對歐化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捍衛日本傳統與國粹的思想及運動。至大正、昭和時代,日本社會階級沖突加劇,日本主義主要作為反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強調以天皇為中心的皇道和國體思想。大肆碾壓。市面上涌現出大批宣揚日本精神論的書籍,日本各地的國家主義團體陸續成立。這種文化氛圍加劇了共產信仰的動搖,日本知識分子逐漸對日本社會、政治、生活以及他人失去了信賴。大宅壯一在《轉向贊美者及其痛罵者》中指出,轉向作家大多“忍受不了獄中生活,‘轉向’了,但自己還弄不清是否‘轉向’,處于一種漠然地對意識形態的怠惰似的狀態”[12]。這種轉向原因在小說《生活的探求》里得到了突出體現,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對自己信仰的理論的理解只停留在觀念層面,自然難以將其融入到現實生活的骨血之中。
“轉向”偏偏在日本知識分子身上大規模發生的事實,亦與其民族文化特征密切相關。鶴見俊輔指出:“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對轉向過程帶來影響,甚至可以說轉向過程本身大都是來自于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征。”[13]鎖國性使得除去民族自身產生的思想結晶之外,包含“外來思想”的各種進步思想都宣告無效。并且,“身處狹隘閉塞島國的日本人好似大海里的魚群,不管前進方向正確與否,只求不脫離群體……因此,‘害怕被孤立’便成為了整個日本民族特質的盲點。”[14]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也是這種宿命中的一環。經歷了農民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敗北,島木健作借駿介之口感慨:“種種夢想都已在過去全部集齊,想要將這些夢想轉化為現實的試驗也全部都做過了。”[9]正因為親身參與過共產革命運動,島木才更清楚社會主義在戰時的日本是不可行的。自1935年開始,日本共產黨就已經無法組織全國性的大規模活動了,日本學生運動也在政府的鎮壓下偃旗息鼓。而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工人階級力量的極度分散,任何形式的人民陣線組織都在萌芽狀態下便被扼殺。
上述日本法西斯政權的高壓無疑是造成大批共產主義者放棄信仰的最重要原因,但僅憑暴力摧殘肉體未必能夠讓人的精神構造發生質變。為了徹底根除共產運動,日本政府統合警方、“帝國更新會”、財閥、“國民思想研究所”等機構和人員,形成了一個國家規模的“重生”機構,對本就有些茫然的革命者實施洗腦教化,告知他們只要改變信仰,就可以獲得高尚的“天皇赤子”的身份。而思想警察為改變激進派大學生的觀念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并且出版了如何有技巧地協助“轉向”的手冊。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共產主義者脫離“叛國者”之路,走上“正軌”。不僅如此,對于出獄后處于被觀察階段的轉向者,為了確保他們從心底尊重天皇制,支持右翼活動,政府許諾只要肯放棄革命主張,就可享有安排工作、保障人身安全等生活支持政策[1];反之,則會受到嚴酷打擊。島木健作在刑滿出獄后的一段時期,就因再次參與共產活動而遭到拷問。
從《重建》和《生活的探求》所遭遇的不同命運可以看出島木健作在思想和心理上的變化。《重建》很快被禁止發行,但在僅四個月后問世的《生活的探求》卻問鼎暢銷書榜。后者不再聚焦于“轉向”本身,甚至幾乎放棄了共產主義信仰,轉為關注個體的精神問題。青年駿介的那顆努力在彷徨中找尋人生方向、彰顯社會價值的誠摯之心,驅動他從“被迫”到“自發”轉向。
其一,鑒于小說高度的自傳性質,可以從島木健作的經歷來分析主人公的精神轉變。島木個性悲觀,沉郁孤僻,自懂事起,他就對北海道早期拓荒者吃苦耐勞的開拓精神見賢思齊,胸懷大志。他的生活方式近乎清教徒式的苦修,克己、有規律和秩序、遠離享樂、執拗追尋人生之道。島木健作對北海道的農業懷有親近感,這也是駿介的“歸農”選擇并非完全出于逃避心理的原因,他在考上大學的時候就希望學習農學,但在經濟上不得不依靠實業家的資助,沒有選擇專業的自主權。因此,他決意操持農業并非突如其來的思想轉折,恰恰是一種對自我意志的回歸。
其二,駿介長期面臨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割裂。他在周圍學生的兩種生存方式之間徘徊:一則舍棄學業、投身時代革命;二則對社會漠不關心,一心鉆研技術,確保能有飯碗。和這兩種學生相比,駿介的思考是從社會全局出發,他渴望找準自己從事的工作在社會中的位置和意義。但眼看周遭青年從滿懷熱情到走上社會后變得心灰意冷,駿介意識到在當今時代“職業”與“本來的工作”二者之間不可調和,似乎只有“本來的工作”能夠帶來生活的意義,可倘若全然不顧現實壓力,舍棄“職業”,生存又無以為繼。駿介在這個問題上的掙扎也是在隱晦地言說其“轉向”的原因。
駿介難以從理想破滅的泥潭中通過深化理性認識來找到解脫之法,唯有從肉體勞動中救贖自我。在辛苦的勞作中,他拋棄一切知性上的驕傲,以謙虛而虔敬的心態向農民學習。他努力改善農村醫療,指導農村青年的科學與人文知識,為道路改修無償勞動,為農忙期托兒所的建立四處奔走,以種種務實的行動融入一個新的“集團”,從中獲得自我肯定。島木健作本人未必真正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想,但他筆下的駿介身上從未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駿介的成長過程中,出發點是農村,歸宿是日本自古以來的世界觀,即“此岸的,不含超越的價值,以把個人高度納入集團作為特征,從空間上說,重視的不是全體,而是局部;從時間上說,重視的不是過去/未來的完結性,而是重視現在”[15]。簡言之,主人公“轉向”的潛文本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注重務實生活勝于抽象理論、“(強勢客我)與弱勢主我帶來的懦弱、謹慎、憂慮、被孤立感等消極的行動傾向”[16]等,另一方面是加藤周一指出的“日本知識分子存在著現實生活與思想互相分離的情況,正因日常與思想的這種分離,他們才容易在危急時刻允許思想向現實生活低頭,服從于現實的要求”[17]。可以說,駿介的人生選擇具有日本知識分子的典型性。
《生活的探求》作為修養小說的特殊性亦在于此,主人公沒有堅持朝向更廣大的領域,而是退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封閉環境之中,用另一種方式貫徹為人民奉獻的理想,最終找到了自己在這個小社會中的位置。駿介發現,對于農民來說,勞作生產就是生活的中心,他們不僅能夠自食其力,而且能夠發揮出全部才能,這在駿介看來就是一種“自我完善”,實現了“生存”與“生活”的統一,他也最終走向了這樣的生活。雖然駿介也認為自己的選擇在本質上屬于避難求易,但至少可以解決他在轉向事實上反復的糾結沉淪。他在思想上切磋琢磨,在行動上事必躬親,才得以從苛責自貶中獲得精神解脫。就結果而言,主人公一掃小說開頭的頹靡狀態,成為了一個“想要為自己、為人民感到快樂”的人,他因為幫助了受歧視的部落民而切實感受到了一種深切而偉大的喜悅,哪怕只是做了一件“簡單的小事”。主人公駿介的自我得以完善,生活也變得充實、有序,使得文本敘事給予讀者農村生活洋溢著希望之感。然而,這一看似圓滿的結局給人一種放棄信仰乃是明智之舉的感覺,在無意中構成對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最大的反諷。此前,轉向文學敘事的既成秩序正如森山重雄所言:“初期轉向文學的主軸是對馬克思主義反復的叩問,思考是否能夠重新建起新的思想體系。”[7]轉向本身意味著不得已而為之的悲劇。但是,貫穿《生活的探求》的“是一種懺悔的沖動,即如何凈化自身罪過,甚至升華到對日本國體的信仰與獻身。”[7]
四、二戰時期日本知識青年的“引路燈”
根據日本警方統計,轉向者自述的轉向動機分為以下幾類:出于信仰的占2.21%,發現理論矛盾的占11.68%,因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出于家庭因素的占26.92%,出于國民自覺的占31.90%。這當中占比最大的“國民自覺”就是所謂的“日本國民的團結精神”在作祟。鶴見俊輔指出,人民是共產者全心奉獻的對象,但日本民眾卻在當時熱烈頌揚“九一八事變”,支持與共產人士的信仰相悖的目標,很多共產者的轉向也源于這種孤立于人民、周遭親友和家人的感覺[13]。
此外,日本共產黨在組織建設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即將黨的領導權交給了知識精英。日本共產黨創立之初,領導者山川均主張左翼知識分子必須和勞工階級結合起來,然而他的觀點遭到福本和夫的反對。后者認為,“精英知識階層首先要從群眾中抽離出來,再以激進知識分子的身份徹底武裝理論,才是左翼群眾運動與知識分子進行大團結之前的必要條件。”[13]福本理論在當時信奉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獲得了勝利,這使得日本共產黨開展的運動從一開始就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際,而所謂經過武裝之后的理論亦缺乏牢固的根基。這也導致了很多日本知識青年的困惑。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之勢的擴大,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下的知識青年苦思自己應當以何種身份投入到社會中,反復探求生活應有的方式。無論島木的創作意圖是否如此,《生活的探求》實際勾勒出了日本國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一種“理想的”生活態度,引導青年重新認識自我。小說中,主人公想要融入農民生活的動機之一,就在于他意識到作為個體(而非組織的一員)的自我。并且他在深入農村之后發現,想要在思想精神承受高壓管控的反動時期去實現身心統一,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難,甚至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其核心就是以努力主義為信條,堅持將早起、吃潔食、勞動筋骨等事情當作每天的日課,如此便能維持健康、清明的生活秩序。這對知識青年來說可謂是簡單鮮活、目標明確的生活方式指南,造就了《生活的探求》在二戰時期日本文學作品中驚人的銷量。
上述這種本分完成本職工作的生活方式正迎合了統治者所鼓勵的價值取向。《治安維持法》的嚴酷化和活字檢閱制度反映出當時對反戰異議的打擊之嚴厲,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無疑是最難以生存的時代。保持如駿介那樣的生存方式的人對于軍部來說毫無威脅,當權者所致力培養的正是這種在輿論上保持沉默、在平凡而單純的勞動上十分用心,追求那種不必真正費心的生命充實感的“良民”。中村光夫在《生活的探求》戰后重印版的后記中寫道:“本作之所以深受當時的青年歡迎,是因為駿介的生活方式為他們點燃了一盞明燈,照亮在陰郁時代的壓力中惶惑不安的良心。”[6]小說由此成為二戰時期青年讀者的“人格修養”指南,文本中的價值觀念在這一認知中獲得了正面化的裁斷。
島木健作入木三分地描繪出一幅幅農村的生活圖景,他以農民的利己主義造成的矛盾置換了社會的根本矛盾,轉移了讀者的視線。但即便主人公通過在主觀上縮小“世界”范圍的手段來試圖達成自我與外界的平衡,小說也極少深挖農村問題的根源,幾乎不曾觸及橫亙于農村青年“積極且充實”的生活狀態之下的冰山。駿介在農村遭遇的挫折雖然投射出農民的缺陷,如善于計算得失、深受迷信和習慣的束縛、達不到反抗權力的精神高度、對村外的社會幾乎一無所知,卻精于村子的內部結構運作,等等;但是,作者并不是以批判的眼光去探討小農根性。駿介樹立改良農村生活的新理想之后,發現自己仍需直面困難重重的現實。再三斟酌后,他仍對農民抱有信賴之情,最重要的是,他認為農村生活令他有腳踏實地之感,決心堅持貫徹新的理想。如此的情節安排使《生活的探求》打破了轉向文學中彌漫的自我譴責之風,塑造出一個人格具有統一性、對百姓懷有善意、誠實面對自己的人物形象,傳達出人要為真正有意義的事業貢獻出全部身心的倫理價值觀。與之前陶醉于觀念世界中的自己相比,這個被塑造出來的新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了“轉向”行為的性質。主人公致力于解決農民問題的姿態也使得“轉向=變節”的話語秩序在文本中被消解。作為個體的主人公在看似遠離政治的場域中實現了理性與情感的統一。
也就是說,在這部有悖于傳統修養小說精神的作品中,駿介所追求的目標仍然是人格調和的“統一性”,“為了生存,他的所作所為,就是能夠發揮出他全部能力和意志的生活道路——這是眾多人士的追求。也是駿介的追求。”[9]他希求能在生活中找尋到工作的意義,這意義包含社會價值與人格陶冶兩大方面。從前他所走的道路意味著分裂,因為并未使社會發生良性變化,也令自己的精神困頓痛苦。在選擇歸農的駿介看來,無論過往持有的觀念是否正確,僅僅由理論學問所構成的所謂知性是需要被否定的,因為人真正意義上的生存必須要同社會需求相關聯。作家島木健作要批判的是知識分子沉湎于不安的哲學,以至無所作為的現狀。“固然作者將批駁的矛頭主要指向那些出身‘上流’,‘幾乎不用因為考慮職業道路而煩心’的那一類知識分子,但主人公駿介以其行動和思想所反對的,其實是陷入‘無力、懷疑、絕望’狀態中的那一類知識分子,他們也想要誠實地聽從自己的良心生活,卻長期在現實的桎梏之中左顧右盼、停滯不前。”[11]駿介的出發點秉承的仍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希望與農民共同勞作,幫助解決農村問題,以期重建身份認同。在這種話語秩序下,自己不再是因為“變節”而被排斥的“他者”,而是經過自我教育后迷途知返,在生存場域充分發揮主體性的新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主人公的確獲得了“成長”。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未能被主體意識到的關鍵問題是:在國家機器全方位的規訓和監控下,這種生活方式必然牽扯出日本知識分子內在的軟弱性,看似積極改良日本社會的行為恰恰構成對日本現實矛盾的回避,以及對當時秩序的強化。《生活的探求》的文本書寫邏輯看似超越了政治立場,但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要求全民支持的大背景下,這一文本及其激蕩的漣漪其實起到了相當有力的政治作用,故它的暢銷令當政者喜聞樂見。
五、結語
小說《生活的探求》承接了島木健作前期作品中的思想軌跡,即批判知識分子,贊美實際生活的人,透露出面對生產者產生的自卑感。在該作品中,主人公駿介完成了從知識分子到農民身份的蛻變與“重生”,“積極地否定了人民戰線式的抵抗運動。”[11]
“在集體的必要性和知識分子聯盟的問題之間的互動中,沒有一個國家像近代日本那樣問題叢生又混淆不清,以致釀成悲劇。……(尊王主義)到了1915年已經成為羽翼豐厚的民族主義,能夠同時從事極端的軍國主義,崇敬天皇,以及本土主義,把個人置于國家之下。”[18]薩義德的評判點出了“轉向”有其客觀的民族淵源,故而現如今從道德層面居高臨下地苛責轉向者的做法并不謹慎。且無論是“國家惡”還是“個人惡”的問題,在二戰時期的審查體制下都不允許被大肆書寫,作家能夠表達出的內容十分有限。但作品對日本青年讀者集體的價值認知建構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導向作用,其對日本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與批判意識的影響不可低估①根據日本社會學家筒井清忠的著作《日本型“教養”的命運》(『日本型「教養」の運命』,巖波書店1995年版)第62至63頁的實證調查,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對高中生的讀書調查結果顯示,《生活的探求》位于“最近深受感銘的書籍”第2位,可見暢銷書對青少年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力不容小覷。,特別是專注于對自我內部的批判很可能導致個體對制度的盲從。對此,轉向文學家們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