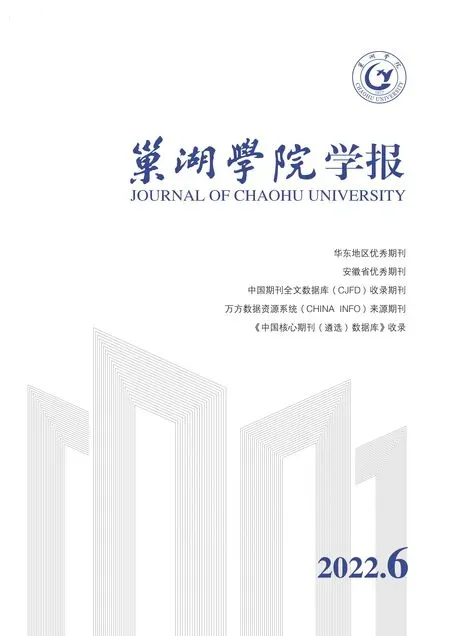“灰色地帶”中的個人見證與反思
——論普里莫·萊維的非虛構寫作
張麗瑤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引言
奧斯維辛無法被想象,見證是幸存者的責任,由此形成的見證文學在“非虛構”寫作中占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意大利猶太裔作家普里莫·萊維(1919—1987)作為一個幸存者,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接連完成《這是不是個人》(1947)、《休戰(zhàn)》(1963)、《被淹沒與被拯救的》(1986)等集中營回憶錄,履行自己作為見證者的責任。作為大屠殺書寫史中不可回避的作家,萊維在世界文壇享有盛譽,其作品均已譯成英文。中國自2013年開始譯介萊維的作品,到目前為止已翻譯出版11部。與萊維享有的盛名相比,國內有關萊維的研究相對沉寂。學者的關注點多集中于萊維的創(chuàng)傷敘事,從不同的層面進行分析,如彭倩[1]認為萊維的創(chuàng)傷敘事具有兩大主要特點:敘述語言的“閃回性”和意象的“強迫性重復”;丁鵬飛[2]認為萊維憑借故事敘述形式、創(chuàng)傷修辭以及碎片式評論的“客觀敘述”避開了情感的過度宣泄及理性對創(chuàng)傷的象征化縫合;邵路鳴[3]從見證者自身的限度,以及見證書寫所遭遇的“冷漠”回應兩個層面呈現創(chuàng)傷記憶的見證書寫所存在的倫理困境。
“非虛構”作為一種寫作方式與寫作體裁,有其特殊性與延展性。萊維的寫作一直與對“非虛構”的思考交織在一起,該體裁不僅是萊維見證奧斯維辛的起點,也是其作品風格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擬從“非虛構”這一獨特的文體形式出發(fā),來探究萊維見證書寫的獨特性。
一、以書寫對抗羞愧與遺忘
“灰色地帶”(The Grey Zone)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等廣泛使用的概念,意指“界限不明、不易歸類、難以界定或處理的領域或形式”[4]①該解釋在《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8版)中對應的詞條是“grey area”,“area”與“zone”為同義詞,兩者都可用作名詞表示“地區(qū)、區(qū)域”,而“zone”更強調具有某種區(qū)別特征而被劃分出來的區(qū)域、地帶。。與同一時期書寫奧斯維辛的作家相比,萊維見證與反思的獨特性在于他將“灰色地帶”的概念應用于集中營里的施害者/受害者分析。萊維認為,集中營不是由純粹的施害者和受害者組成的黑白兩分的世界,這個世界中存在一個“與主/客兩個陣營都有所聯(lián)系又有所區(qū)別的一個地帶”[5]。他將那些進行了道德妥協(xié)、在某種程度上和納粹合作的人都歸到“灰色地帶”之中——從從事清潔工或守夜人之類卑微勞動的囚犯,到充當“屠夫”“看守”的囚犯頭頭、勞動隊長,再到被黨衛(wèi)軍選中運營毒氣室、焚尸爐的特遣隊隊員,都屬于這個特殊的地帶。新囚犯的第一個威脅、第一次侮辱、第一記耳光,往往并非來自黨衛(wèi)軍的暴徒,而是來自他們處于“灰色地帶”中的“同伴”。萊維注意到,這些處于“灰色地帶”中的人占據幸存者中的多數,而最具有受害經驗的底層受害者卻早已進了焚尸爐。由此,萊維提出一個“悖論”:那些死亡的人才是最有資格作出見證的人,幸存者作為例外,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偽見證者。
萊維自己也曾是“灰色地帶”的一員。萊維就讀于都靈大學理學系化學專業(yè),憑借其所長,他參加了集中營化工隊的選拔考試,晉升為“專業(yè)技術人員”。進入實驗室無疑是一項“特權”,留在溫暖實驗室干雜活不僅能熬過寒冷的冬天,還能獲得額外的食物、新襯衣和短褲,也能偷到肥皂和汽油以換取所需之物。萊維曾向托斯卡納小說家吉安·路易吉·皮巧麗供認過自己的罪行,即“他以某種方式與納粹合作過,因為他們曾以他是一個工業(yè)化學家為由‘赦免’了他”[6]。萊維確信自己是無辜的,但卻為自己生存下來感到羞愧和內疚——他因某項特權幸存下來,而別人卻代他而死,“我活著,代價也許是另一個人的死去;我活著,是取代了另一個人的位置;我活著,便篡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存權,換言之,殺死了另一個人”[5]。除了這種“代替他人活下來”的羞愧感,萊維還因“缺乏人類團結精神”而感到自責。萊維自述,他曾在一個炎炎夏日找到半管蒸餾水,卻只告訴了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將自私延伸到你最親近的人,在那遙遠的時光中的一個朋友,一個可以恰當地稱呼‘我們’的人”[5],而當他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卻看到他們的伙伴身上沾滿水泥灰塵,嘴唇干裂,眼睛冒火。萊維立刻感到自責,解放后更因這件事感到羞愧,“這遲到的羞恥是否合理呢?當時我無法確定,現在仍然無法確定,但我的確感到羞恥,而且這羞恥具體、沉重而持久”[5]。此外,萊維還察覺到一種“更廣意的羞恥,世界的羞恥”——罪惡發(fā)生在所有人身邊,沒有人能擺脫,個體對不合理事件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無動于衷也是一種罪惡。
為了擺脫奧斯維辛集中營經歷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記憶的折磨及平復重新生而為人后產生的種種羞愧感,萊維在幾十年的時間中不停地創(chuàng)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奧斯維辛三部曲”:《這是不是個人》《休戰(zhàn)》《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其他著作如《緩刑時刻》《元素周期表》等也與集中營記憶密切相關。與用詩“建造空中墳墓”的保羅·策蘭不同,萊維選擇采用非虛構這一體裁梳理在集中營里11個月以及之后返回家鄉(xiāng)的經歷,并不斷對這段歷史做出反思。萊維的選擇與寫作時面臨的境況及其想用寫作達成的目的有關。萊維的第一本書《這是不是個人》完稿后在整個意大利只印行了2500冊,并沒有立刻引起關注,這時人們剛剛脫離納粹陰影,不愿意重新面對可怖的災難現場。而《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撰寫時,正值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泛起。萊維看到“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經使德國人民歸于怯懦”[5],掌握著大屠殺秘密的多數德國人選擇閉目塞聽、緘口不言;而許多見證了集中營暴行的“平民”作為潛在的見證者,因為有意地忽視和恐懼,也同樣保持緘默。如何告訴更多的人集中營里發(fā)生過什么是萊維著力思考的問題,其寫作的首要目的就是將信息傳遞給讀者。因此,選擇非虛構是適宜的,對萊維來說,“非虛構寫作體現了一種不同的需求,一種對準確的、直接的信息的需求,無論是出于使用的目的還是出于對文化的一種與己無關的渴求”[7]。
對比而言,詩歌作為一種表達形式則不能滿足萊維的寫作需求。萊維欣賞策蘭的詩歌,曾在自己的詩歌中引用策蘭的句子①如萊維《基大利的歌》:“我們的兄弟已升上天空/穿過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焚燒爐/他們在空中給自己掘一座墳墓”,化用了策蘭《死亡賦格》中的句子:“他們在空中掘一座墳墓”。,也曾在編選文學選集《尋根》時把策蘭的詩歌收入其中,但他不認可策蘭的寫作方式。縱然策蘭這位在德軍屠殺下奇跡般生還的猶太裔德國人的詩歌“映射出了他自身與他那一代人的晦暗”,但萊維還是認為這種表達“不是一種溝通,也不是一種語言,至多是一種黑暗的、被斬首的語言,正如同我們所有人在面臨死亡時,一個獨自赴死者的語言”[8]。這種極端晦澀、近乎封閉的語言是不利于交流的。對交流的渴望來源于集中營的經歷,萊維曾在營地經歷過語言的混亂,“人們被一種永恒的巴別塔所包圍,在那里大家都用從未聽到過的語言大喊著各種命令和威脅,誰一下子不明白其含義,就會倒霉”[9],那些最先被“淘汰”的正是在語言方面處于劣勢地位的人。萊維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一書中強調,他從來不喜歡“無法溝通”這個詞,寫作絕不應該用孤獨的方式進行,也不能用混亂的方式進行。他認為語言越清晰人們彼此間的溝通就越有效,對彼此的作用也就越大,被記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選擇非虛構作為敘述的起點正是以交流為直接訴求。
不可否認的是,萊維的作品中也存在一些虛構成分,但他沒有直接采用小說這一偏向虛構的形式進行寫作。這與萊維當時面臨的心理境況以及歷史境況有關。萊維于1945年1月從集中營解放,10月回到祖國,1946年便開始撰寫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并于1947年出版。創(chuàng)作時,一個無法壓制的“我”要發(fā)出聲音,萊維迫切地想告訴集中營外的人他經歷了怎樣的侮辱與損害。徐賁指出,見證敘述以第一人稱“我”敘述真實經歷,但這同一般小說第一人稱的敘述角度是不一樣的,只有真實經歷者本人才有權利這樣說,“‘我’不只是一個方便的敘述角度,而且是一個對經驗真實的承諾和宣稱。這是一個別人無法代替的‘我’,一個非虛構的‘我’。這個‘我’是‘自傳敘述’有別于‘虛構作品’的分界線”[10]。《這是不是個人》是萊維“重新為人”之后的第一聲吶喊,他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本書處于非虛構的界限之內,甚至刻意強調:“如若得補充說一句‘書中沒有任何事實是虛構臆造的’,我覺得似乎多余。”[9]萊維之后的創(chuàng)作也證明,他具有講故事的能力,但不具備完全虛構故事的能力。雖然萊維的虛構作品也廣受好評,但最受關注、得到最多認可的卻是他基于真實經歷撰寫的作品。萊維的傳記作者伊恩·湯姆森也指出,小說《若非此時,何時》是萊維最差的作品,“萊維并非喬伊斯或卡夫卡這樣的想象天才……萊維最好的作品來自他自己的經歷”[6]。
現實具有不可辯駁的力量,當現實世界中存在的事件超越想象力的邊界,“每天發(fā)生的事情不斷地混淆著現實與非現實、奇幻與事實之間的區(qū)別”[11]時,非虛構便不可避免地誕生了。奧斯維辛正處于現有歷史書寫模式、概念與想象的斷裂之處。萊維關注的一直是奧斯維辛這座“地獄”本身,他斷言:“如果我沒有在奧斯維辛生活過,我很可能永遠不會寫出任何東西。我不會具有寫作的動機和激勵。”[12]以非虛構為起點,萊維以直面現實的決心和勇氣讓不可言說的災難逐漸呈現出來。在長達幾十年的寫作過程中,萊維將非虛構這一體裁延伸,為“作見證”找到了合適的表達方式。
二、在新的敘述空間中作見證
萊維的創(chuàng)作始于非虛構,但當他意識到其作品不可避免會出現虛構成分之后,不僅坦然承認虛構這一事實的存在,還有意將虛構與非虛構交織,建造出一種新的敘述空間。在建構敘述新空間的過程中,萊維不斷對見證的“真實性”問題做出思考,以履行“作見證”的義務。徐賁指出,“作見證”與“是見證”不同,“是見證”的人曾身處災難現場,幸存后即陷入沉默,是災難的消極旁觀者;而“作見證”的人則是用文字、行動來講述災難,并把災難保存在公共記憶中,是災難的積極干預者。“從‘是見證’到‘作見證’,是一種主體意識、道德責任感和個人行動的質的轉變”[10]。
萊維在奧斯維辛的編號為174517,這是集中營的“大號”。1945年1月剛重獲自由的時候,他急切地向別人講述在集中營發(fā)生的一切,這種講述的需要“并不亞于人活著的其他基本需要”[9],他處在一種“絕對的、病態(tài)的敘事壓力”[13]之下。對處于這一階段的萊維來說,在集中營中發(fā)生的一切是不容置疑、也是不應該質疑的,他沒有對“真實性”的問題產生過思考。第一本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對他來說完全是非虛構的。1962年,萊維開始撰寫《休戰(zhàn)》,他仍認為自己所寫的都是真實的。在此書后附的《答讀者問》中,有讀者問萊維:“為什么你只討論德國集中營,而不談及蘇聯(lián)集中營呢?”他回答:
我只能見證我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事情。我的書不是歷史書籍。在撰寫這些書籍時,我嚴格地將自己限制于只報道我親身經歷的事情,而摒除我之后從書籍或報紙上讀到的故事。比如,你會注意到我并不引用在奧斯維辛遭到屠殺的人數,也不描寫毒氣室和焚尸爐的細節(jié)。這是因為,我在集中營的時候并不知道這些事情。我只是后來才了解它們,而在這時,全世界也同樣知道了這些事情。[12]
事實上,湯姆森指出,《休戰(zhàn)》也包含巨大的虛構成分。萊維在為SIVA工廠出差途中聽到過一個故事:在法蘭克福的一家老人院里住著一位老人,她在1938年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懇求他能停止戰(zhàn)爭。萊維將這個表現出非凡勇氣的故事幾乎原封不動地融入《休戰(zhàn)》之中,但故事本身卻并不是發(fā)生在“休戰(zhàn)”途中的,這種挪用并不符合非虛構的創(chuàng)作原則。
到了70年代末,萊維開始正視其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矛盾,思考何為“真實”。《這是不是個人》出版后,他至少去了130所學校為這本書進行演講,但1979年,他在一篇圍繞《扳手》的訪談中提到,“我已經決定不再接受任何這類邀請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我所寫的是否真的是事實?”[7]同一年,萊維在另一次采訪中也談及這個問題,虛假的感覺讓他焦慮,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責任將三十五年前發(fā)生的事原原本本講出來,“比如說,難道我不能為了自己的目的將它們進行輕微的改動,或者無中生有地虛構它們?”[7]這時萊維意識到了見證書寫的矛盾性:寫作究竟是為了記錄事實還是為了進行啟迪而講故事?這兩種寫作目的之間有明顯的差異。萊維坦然承認這是他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他仍在思考。
到80年代,萊維對真實性問題的思考逐漸獲得了一個較為清晰的答案。在1981年的一篇采訪中,記者問萊維:“你書中的人物永遠都是真實的嗎?或者可以說他們被你的內在視角重塑了?”他回答,不管一個作家多么努力保持客觀,他筆下的任何一個人物不可能是完全真實或者完全虛構的,即使是一個歷史作家或歷史小說家也會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印記,人物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被扭曲的,因為“修改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人類的天性”[7]。在兩本公認是自傳性的作品中(《這是不是個人》與《休戰(zhàn)》),萊維也確信自己重塑了書中的人物,即使這是一種無意識行為[7]。在《他人的行當》(1985)中,他這樣看待自己的寫作分類:“在二十五年習作生涯和半真半假的‘自傳式寫作’之后,有一天我決定跨過堤壩,罔顧當下小說究竟是生是死,其生存狀況又如何的辯論,嘗試著去創(chuàng)作一篇小說”[8]。這本小說指的是《若非此時,何時?》,在這部小說中萊維虛構了一支猶太人武裝隊伍在二戰(zhàn)最后的時日從俄羅斯到意大利的游擊戰(zhàn)。值得注意的是,在萊維的論述中,半真半假的“自傳式寫作”與小說的寫作是兩種不同的模式,前者書寫“看得到的東西”,而后者則書寫“自創(chuàng)的東西”。從“書中沒有任何事實是虛構臆造的”到“半真半假”,他對真實性的看法明顯發(fā)生了轉變。到了他的創(chuàng)造性自傳《元素周期表》(1987)中,虛構的意圖更加明顯,虛構的運用也使得此書擁有了一種奇妙的混合風格。
萊維長達幾十年的思考觸及了“非虛構”寫作的核心問題——真實性。為何萊維會對書寫的真實性產生懷疑?這是因為就要見證的對象奧斯維辛來說,見證過程本身就存在一個難題。吉奧喬·阿甘本指出,在奧斯維辛的歷史性研究中,發(fā)生了一種更深層面上的“事實和真相的不一致,確證和理解的不一致”[14]。幸存者急于解釋他們看到的一切,但他們說出、寫出的只能是并不等同于客觀事實的真相,事實與見證之間存在一道本質的裂痕。而就“非虛構”寫作本身來說,作者的主觀性與文本中存在的虛構性是其無法繞開的兩個方面。幸存者不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們因卷入事件而無法客觀見證,寫作過程也無法完全摒棄虛構手法。陶東風指出:“當我們說見證文學無法避免虛構的時候,我們的預設前提是:相比于虛構小說、抒情詩、抒情散文等整體雕構的作品,見證文學是非虛構的,也就是以作家的真實經歷、經驗等為基礎的,在整體上它是非虛構的,只是其中無法避免虛構的元素而已。”[15]
但虛構手法的存在并不妨礙見證的力度。歷史并沒有為幸存者提供一種現成的敘述方式,為了打破沉默無語的困境,幸存者需要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作見證,在歷史與小說之間開辟一個新的敘述空間。同是幸存者的凱爾泰斯·伊姆雷認為其《無命運的人生》不是自傳,甚至也不是小說,但他還是虛構了一個敘述者久爾考來統(tǒng)籌講述的材料,完成見證。伊姆雷希望通過這樣的安排以達到特殊的目的,即“找到一種語言適用形式、一種中介,以便能使奧斯維辛作為一個過程、作為一個一步步實現的(從前因實際上是推導不出來的)事件顯現出來”[16]。萊維強烈意識到在敘述和現實之間那種成問題的聯(lián)合,但他申明“從內部和自身來說,每一種見證的行為都是有效的”[9]。如若對《這是不是個人》進行敘事學分析,可以使這種見證的有效性呈現出來。在該書中,萊維頻繁地將第一人稱單數“我”轉變?yōu)榈谝蝗朔Q復數“我們”,如“我們忍受著寒冷和饑渴之苦:每當火車靠站,我們都大聲嚷嚷著要喝水,哪怕是給一把雪”[9]。在喬納森·德魯克看來,第一人稱復數形式作為一種“包容性代詞”,能夠為那些被驅逐但再也沒有回來的“被淹沒的人”發(fā)聲,如此句話中的復數主語“我們”就“作為一個可信的、權威的合唱傳達了一種共同的身體匱乏體驗,這種體驗能夠引起讀者的同情和良知”,該主語“不再位于受害者中間,而是位于集中營外某個不確定但明顯客觀的位置”[17]。此外,萊維還多次將內聚焦視角轉變?yōu)槿暯牵瑢懸环N“假定”的情節(jié)。例如,他寫自己在黑暗中聆聽集中營的聲音,聽到的是“熟睡的人的呼吸和打呼嚕聲,磨著牙床。他們夢見自己在吃東西:這也是一種集體的夢,一種殘忍的夢”[9],而那些夢在每天晚上,在整個睡眠過程中,在每個人身上無休止地重復著。這種直接跳入其他人物內部呈現他們各自主觀世界的敘述方式并不符合非虛構的寫作要求,但按照希利斯·米勒的看法,這樣的書寫與建立“共同體的設想”有關,因為該設想通過敘事學的相關技巧假設 “共間體成員有一種類似心靈感應的能力,知道其他成員的感受和想法;部分原因是因為你能假定你的鄰居在特定情形中會像你一樣感受和思考。”[18]
而主觀性的存在也并不會減損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指出,“歷史”一詞既包括過去發(fā)生的事情,也包括對這些事情的敘述。由此他認為,“歷史這一名詞聯(lián)合了客觀和主觀的兩方面。”[19]米勒在分析有關大屠殺的敘事時也認為,“任何有關大屠殺的敘事,都經過了選擇和整理。……盡管事實仍為事實,但任何敘事行為都是對事實的構建。”[18]受害者憑借記憶寫作,但經歷創(chuàng)傷后的記憶不是完整的記憶,而是扭曲的、零碎的、斷斷續(xù)續(xù)的記憶,見證者必須重新構建才能形成連貫的敘述,這種想象的建構本身就具有虛構的特征。對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一批“非虛構”見證文學作家來說,他們書寫的真實性“歸根結底總是一個人的真實”[20]。萊維要記錄的不僅是猶太人遭到屠殺這個事實,更為重要的是,他要通過書寫確認自己作為人的真實性——當一個渺小的“我”在一場群體性滅絕中經歷過疑惑、喪失和重新獲得之后,這個“我”需要發(fā)出聲音來確證自己脆弱的生命還真切地存在于陽光之下。
總之,萊維一方面認為幸存者不能真正為其他受害者作證,另一方面又使受害者在他的書寫中發(fā)出合聲。通過將非虛構與虛構交織融合,萊維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構出了一種新的敘述空間,在一定程度上繞開或擱置了他提出的“已經死亡的底層受害者才是真正的見證者”的悖論。非虛構與虛構交織融合后,萊維擅用的寫作技巧以及自身的一些寫作特質也逐漸顯現出來。
三、以“作品性”上升見證的高度
在20世紀書寫浩劫的作品中,出現了兩類低劣的類型。一種作品為補救歷史斷裂的呼求而淪為了感傷主義的宣泄,如本杰明·維爾克米爾斯基的《童年斷片——從1939到1948年》便被認為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情緒化處理”[20]。另一種作品低劣的原因是其作者因“例外命運”而產生虛榮,以致加入到無聊的競爭之中,1985年之后這類作品開始出現,“每個人都似乎向往并發(fā)現一種‘更為精彩的恐怖’”[20]。
受害者在見證大屠殺歷史時,如何保持獨立、冷靜的敘述,以避免滑入感傷主義的宣泄以及無聊的競爭之中?克洛德·穆沙在他的見證文學批評集中引用了伊姆雷及沙拉莫夫所提出的“作品性”概念,由此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穆沙寫道,沙拉莫夫經常批評見證蘇聯(lián)勞動營的人的“懶惰”,“他們以為‘見證者’的身份足以供他們自我維護,從未想到要使他們的見證達到‘作品’的高度。對沙拉莫夫來說,這個高度是必須的,因為只有它才能與他所經歷的事情相配”[20]。陶東風針對“作品性”的概念做出分析,認為從經驗到作品是“使情成體”的過程,在轉化的過程中“文學技巧的操作不可避免”[21],即使是最簡單、只作為事實證據的報告,也會受到寫作行為的限制。因此,可以認為文學性是作品性的內核,文學技巧的使用使受害者與其書寫的對象保有一定的距離,并且通過“透露這種距離,挖掘這種距離”,使作品“遠離那張由‘良好意愿’編織成的哀婉動人的網,始終保持獨立和冷靜”[20]。
萊維的作品不是干巴巴的客觀敘述,他的回憶錄、小說中有大量的人物、細節(jié)描寫,這讓他的見證得以達到作品的高度、文學的高度。萊維在訪談中也提及,雖然他是一個糟糕的意大利語文學的學生,但他還是在有意識地運用上學時習得的文學知識進行寫作,如《這是不是個人》便“完全、徹頭徹尾是文學性的”[7]。而《休戰(zhàn)》于1963年獲得意大利最高的文學獎斯特雷加獎也證明了他的文學才能,萊維稱這是他“在文學世界一次活生生的體驗”[7]。
反諷這一文學修辭的運用是使萊維的奧斯維辛書寫具備“作品性”的重要條件。《這是不是個人》開篇就奠定了反諷的基調,“我幸虧在1944年才被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9]。詹姆斯·伍德指出,在意大利語中,fortuna這個詞有雙關含義,既表示好運,也有命定意味[9]。晚進奧斯維辛意味著“好運”,但承擔這種命運的必要性卻是難以理解的。萊維因幸運才能在災難中幸存下來,而在他之前被送進奧斯維辛的“小號”猶太人生還的幾率卻微乎其微。“幸運”無疑包含著對納粹行為的批判和控訴。在集中營干活時,黨衛(wèi)軍或“灰色地帶”的“卡波”①卡波(Kapo)即集中營看守、監(jiān)督其他囚犯的囚犯,他們聽命于黨衛(wèi)隊并享有一定的特權。往往會用暴力監(jiān)督囚犯,而萊維卻用一種近乎輕柔的語調描繪這種暴力,“另外一些人在我們抬起沉重的貨物時,幾近友好地鞭笞我們,伴隨著鞭笞的卻是勸告和鼓勵,就如同趕車人鞭笞馴良的馬匹似的”[9]。暴力成了“友好的鞭笞”,暴力帶來的是“勸告和鼓勵”,黨衛(wèi)軍鞭打囚犯就如同人鞭打疲憊的牲畜。萊維的反諷冷靜而精準,反諷的使用讓他的文字蘊含著深刻的道德反抗。米勒認為,“對于奧斯維辛的書寫,反諷是最恰當的敘述語言模式”[18]。反諷的敘述方式能讓敘述者與被敘述事件保持距離,比起感傷或濫情的講述,反諷能夠讓讀者更為真實地看待這些事件。此外,反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多層次性還能使文本形成一種時空并置結構,這種結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會推遲讀者理解文本,延長思考時間,以便讓讀者產生深切的感受。如此一來,反諷便“瓦解了讀者不愿直接面對大屠殺的心理”[18],達成與讀者的交流。
除了使用文學修辭,萊維還在寫作過程中有意錘煉文字,形成自己的風格。簡潔和準確是萊維非虛構寫作的兩大特質,這種特質曾多次被萊維本人和評論家提及,構成其“作品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簡潔、準確的追求與萊維化學家的身份密切相關。對萊維來說,化學所形成的“是種追求具體與簡潔的精神習慣,也是種不把目光僅僅局限于事物表層的不滅熱情”[8]。萊維在寫《這是不是個人》前沒有經過系統(tǒng)的寫作訓練,也沒有寫作經驗,他所采取的風格是“那種工廠里常見的每周報告的形式:它必須非常準確,精煉,用一種讓工業(yè)系統(tǒng)中不同層級的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語言”[7]。在這本書開篇,萊維就用一連串的短句來描寫他被法西斯保安隊逮捕時的人生狀態(tài):“1943年12月13日我被法西斯保安人逮捕了,當時我二十四歲,閱歷淺,不諳世事,法西斯當局四年的種族隔離政策迫使我?guī)缀跎钤谝粋€與現實世界隔絕的天地里,導致我充滿著笛卡爾式的幻想,跟男性朋友肝膽相照,跟女性朋友關系淡漠。我內心滋生著一種溫和而又朦朧的叛逆感。”[9]托尼·朱特指出,萊維經由化學訓練所形成的緊湊、簡潔精煉的文風同浮華的、實驗性的、句子錯綜復雜的寫作相比,具有“中世紀素歌”的魅力[13]。
最能體現萊維對準確性追求的非虛構作品是寫于1945年到1986年的一系列證詞,這些證詞被收錄于 《這就是奧斯維辛:1945—1986年的證據》一書中。這些證詞不僅展現出萊維獨特的講故事的能力,還體現出一種近乎工廠里每周生產報告的準確性。在《關于莫諾維茨猶太人集中營的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的報告》一文中,萊維對集中營的“日常生活”進行了詳盡描述:囚犯每周淋浴兩三次,但分發(fā)的肥皂數量卻很有限,“一個月就分給一塊50克重的小肥皂,而且質量極差。那是一塊長方形的東西,質地很硬,沒有油脂,卻含有很多沙子,使用時不起泡沫,極易碎裂,因此,洗完一兩次淋浴后就完全耗盡”[22]。在這份報告中,萊維歸納了囚犯所患的幾大最頻繁的疾病及疾病的成因,他用科學的眼光平靜審視集中營的環(huán)境,“正如我們所見,營地提供的食物從數量上來說,是大大低于人體的正常需要的。從質量上說,則缺乏兩種成分:一是脂肪,……二是維生素”[22]。在《這是不是個人》中,萊維用細節(jié)密集地構建出在集中營死亡是如何發(fā)生的。“死亡往往是從鞋子開始的”[9],不能彎曲的木鞋對大多數人來說像上刑的刑具,“行走沒幾個小時后,就會磨出令人疼痛的創(chuàng)傷,一旦發(fā)炎就是致命的”“腳傷疼痛,到哪都是最后一個到,到哪兒都得挨揍”[9],囚犯的腳腫了就得上醫(yī)務室,醫(yī)生會診斷為“腳部肥大”,這是極端危險的,因為黨衛(wèi)軍知道這種病無法治愈,病人會在“篩選”的日子被送往焚尸爐。
敘事的力量來源于實實在在的具體性,對萊維來說,準確、清晰還含有一層道德指向。曾有記者問萊維:“化學的一個魅力是否在于——恕我冒昧——它與生俱來就是反法西斯的?”萊維回答:“是的,確實如此。在我看來,它內在就是反法西斯的。”[7]納粹德國套用現代工廠的運作模式以及高效的官僚體系,讓科學淪為邪惡的幫兇,“虛假的社會‘科學’和種族決定的生物學成為種族主義哲學的基礎”[23],一種現代化的屠殺方式被發(fā)明出來。這種屠殺方式讓所有的參與者免于思考——受害者在施害者面前總隔著中間人。利用這一層間隔的距離,“平庸之惡”發(fā)揮效用,施害者以“服從命令”為借口行事,而不探究行為的原因、結果。萊維在《休戰(zhàn)》中提到,在回家途中,他曾在俄羅斯見到過十幾名被遺忘的德國戰(zhàn)俘,他們的面容顯得痛苦、茫然而瘋狂。萊維對這些戰(zhàn)俘做出分析:“他們習慣在納粹當局的鐵律中生存、活動和戰(zhàn)斗。這鐵律是他們的支柱和生計。一旦納粹機器本身停止運轉,他們便發(fā)現自身是軟弱而毫無生氣的”[12]。這些順從的子民已經使自己淪為權力的得力工具,自身不具備一點力量。因此,萊維提倡在所有的大學科學教育工作者中間鼓勵一種精確的道德意識:“我接受這個任務,但是我不接受那個。我會研究種新型抗生素,但我不會研究神經瓦斯。我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核聚變的研究,但我不會去研究中子彈。”[7]萊維還要求年輕的科學家必須去獲悉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的目的和用途,如果當科研的目標令他厭惡時,他應該拒絕為毀滅的力量服務。
穆沙指出,“那些遭受極權主義暴力的人的‘現時’,我們其實是無法真正進入的;我們所能進入的只是詩本身”,但成型的作品擁有一種特殊的凝縮力,能用難以預想的形式“建造出一種半透明的縈回纏繞的結構,一座由空氣鑄成、懸于空中的墳”[20],這座“空中的墳墓”能夠將讀者無法進入的、遭受極權主義暴力的人的“現時”呈現出來。因此,為苦難作見證不僅需要見證者對其他“被淹沒的”受害者抱有責任心,還需要見證者擁有表述能力。幸存者的書寫不能僅僅止步于素材的堆積,而是必須通過使用語言的力量、敘述的力量使經驗成為作品,從更高的層次完成見證。萊維依靠敘述的藝術深入公眾道德教育中,并將個人歷史以作品的形式保存下來,其見證的“作品性”高度為見證書寫提供了一個范例。對萊維來說,記憶是一份禮物,同時也是一份責任,他進行非虛構寫作目的不僅在于提供信息,更在于要提供一種價值判斷。有價值判斷的讀者應反思當下的問題與困境,并時刻思考日常行為的道德、正義與否。唯有引發(fā)更多人的思考,才更有可能阻擋災難再次發(fā)生。
四、結語
萊維的寫作一直與對非虛構的思考交織在一起,他對非虛構的認知并非一成不變。在寫作初期,萊維身處創(chuàng)傷記憶及“灰色地帶”的折磨之中,一種“絕對的、病態(tài)的”敘事壓力推動著他宣泄自己的經歷,他急于通過寫作與讀者交流,使個人的經驗性記憶變?yōu)橹匾臍v史見證。此時在萊維的認知中,“非虛構”與“虛構”之間存在明顯的界線。隨著創(chuàng)作的不斷豐富,萊維意識到自己的見證寫作并非是對奧斯維辛事件的絕對再現,作家不可能完全真實、客觀地將現實中的人物還原到文字中,敘述和現實之間存在一種成問題的聯(lián)合。但他沒有就此刻意避免虛構手法的使用,而是將虛構手法巧妙融入“非虛構”之中,并不斷錘煉自己的敘述文字,將見證書寫提升到作品的高度、文學的高度。萊維的寫作從不同層次、角度深描處于歷史斷裂之處的事件,使個人記憶變?yōu)榫哂幸欢ㄔ偕芰Φ目绱H集體記憶,最終將災難保存在公共記憶中,實現了“作見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