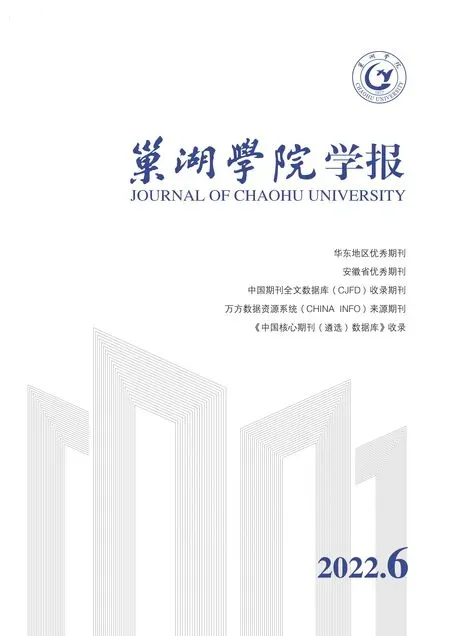譯者角色化與林譯“訛”的再研究
——以《冰雪因緣》為例
汪 琳 余榮琦
(巢湖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巢湖 238024)
引言
林紓在二十余載的翻譯生涯中,譯介了近二百部、涉及十余個國家、百余位作家的作品,涵蓋軍事、言情、政治、偵探等多種類型,成為我國近代譯介西洋小說第一人。林譯小說風靡一時,成為晚清國人開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對中國翻譯史、文學史和文化史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林譯的“訛錯”不斷,又受到諸多學者的指摘和詬病。劉半農就曾公開痛斥林譯文的謬誤,鄭振鐸也直言林譯小說有自行增刪的壞毛病。直到錢鍾書指出“這部分的‘訛’起了一些抗腐作用,林譯多少因此而免于全部被淘汰”[1],后世學者才開始重新審視林譯之“訛”。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更是為重新評價林紓及其翻譯之“訛”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尚文鵬、劉洪濤和吳小琴等多位學者[2-4]從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等不同角度闡釋林譯“訛”的合理性和創造性,為其正名。無論是語言層面對林譯“訛”的片面判斷,還是文化層面強調話語、文化等外在因素對林譯“訛”的操控,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譯者自身的個人經歷、文化身份等因素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
隨著翻譯研究的“譯者轉向”,譯者從幕后走向臺前,學界也更關注對“譯者身份”“譯者角色”“譯者慣習”“譯者倫理”等的研究。只有讓譯者在譯作生成過程中“現身”,才有助于看清譯者在翻譯活動的“中心”地位,也才有可能避免對譯者翻譯活動復雜性的視而不見。鑒于此,文章從譯者角色化出發,以林譯《冰雪因緣》為例,探究林紓譯者角色化過程中各種“訛”的表現形式和生成機理,認為林紓為實現務實性社會目標而不斷迎合社會、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社會人角色,其各種角色相互交織,互為補充,形成了林譯的“訛錯”景觀。譯者角色化研究順應了翻譯研究的“譯者轉向”范式,有助于進一步理解譯與非譯的關系,是進行翻譯批評的一個有效途徑。
一、譯者行為批評與譯者角色化
譯者行為批評是我國學者周領順經過十年的學術積累和沉淀,逐步發展和完善的以譯者和譯者行為為切入口來認識翻譯的本土化理論。該理論一經提出,就引起了翻譯學界的廣泛關注,更是受到了許鈞、劉云虹、王克非等譯界知名學者的高度評價,認為其為“翻譯研究開展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資深化的主題”[5],極大地豐富了國內本土的翻譯批評研究。
譯者行為批評注重“以人為本”,兼顧了翻譯內與翻譯外、譯者的語言性和社會性、翻譯和非譯等文本視域的研究,有助于對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作出更為合理、全面的評價。“角色化”是該理論的一個重要批評術語和核心概念。所謂譯者“角色化”,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借翻譯實現務實性社會目標而進行的不斷迎合社會、調整和改變自己社會人角色的過程”[6]。周領順指出譯者兼具語言性與社會性的雙重屬性,決定了譯者“語言人”和“社會人”的雙重角色。這與譚載喜對譯者主次身份的劃分殊途同歸,都強調譯者并非扮演單一角色,用一種聲音講話。與之相反,譯者會把抽象的、靜態的譯者角色融入到動態的、與不同社會因素和環境密切互動的社會人角色之中。具體到“怎么譯”上,譯者通常會采取嚴復所謂的非正法(偏法、變法、變譯)翻譯方法;具體到譯文上,譯文往往會呈現出語言性翻譯成色的減少和社會性選擇性翻譯成分的增多,即譯文總會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也會違背或不太貼近原文。從譯者角色化來看,這些失真和走樣往往是譯者采取的一種積極的翻譯策略,體現了他們在翻譯活動中的社會人屬性以及翻譯的社會化過程。承認譯者角色化,有利于看清譯者在復雜的翻譯活動中所真正體現出的權利和義務,也有助于理解譯文中會有“譯”和“非譯”的成分[7]。換言之,對譯者角色化的研究,有助于認清譯者超越傳統語言對等意義上的非譯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譯者多元角色和譯文多樣性。
二、林紓的多元角色與《冰雪因緣》之“訛”
林紓個人豐富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使其能文、能詩、能畫,共同構建出林紓的多元身份,如古文家、文學家、畫家等。這些多元身份融入到林紓的翻譯活動中,使其呈現出多元角色特征,扮演著操控者、協調者、創作者等各種臨時可變的非譯者角色。這些角色雖然使林紓游刃于原文和譯文之間,但也易使其擺脫原文的桎梏,造成譯文與原文語言、內容、形式或主題的不對等,形成各種“訛錯”景觀。下面將從文學敘事、倫理道德和視覺審美三個方面來探究林紓譯者角色化過程以及其對譯文“訛”的合力作用,從而客觀地理解和評價其譯者行為和翻譯效果。
(一)林紓的古文家角色與敘事之“訛”
林紓一生學習、研究、講授和捍衛古文,對史傳等經典文學更是熟記于心,運用自如,稱得上是一位古文家。憑借其深厚的古文造詣和超強的文學感悟力,他常以讀史傳方法理解和欣賞原文的謀篇布局,認為外國小說“往往于伏線、接務、變調、過脈處,以為大類吾古文家言”[8],并嘆曰“西人文體,何乃甚類我史遷也”[8]。可見,林紓不是以單一的、靜態的譯者角色走進另一個文本,而是在文本解讀中融入了古文家角色,從而對原文部分敘事進行古文化的調整和改造,以照顧士大夫階層和晚清知識分子的閱讀口味。
第一,增加文內標注。身為古文家,林紓常用古文中“伏脈”觀念去理解狄氏小說中的隱性預敘。所謂隱性預敘,即讀者需要讀到下文時才能發覺前文是在預先透露后來的情節。他指出狄氏之文“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8],又認為其文“蓋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而人不覺”[8]。這里所謂的“伏脈/伏線”“埋伏之筆”,都指向狄更斯的隱性預敘與古文的“伏脈”有相通之處,具有“猝觀之實不見有形跡”[9]的敘事效果。因此,林紓會在譯文內以加注“伏線”的方式來提醒讀者關注后文中人物、事件的發展。縱觀全文,他在《冰雪因緣》的多個章節(第 4、5、18、19、30 章)都做了這樣的標注。以第30章為例,林紓在“愛迭司,汝能于此時死者,正為其時。蓋眼前尚有一人足施其愛,若求以天年終者,則前路均嚴冰矣”[10]一句后增加了“伏線”的標注,為后文情節埋下伏筆——愛迭司最終與情人私奔,身敗名裂,孤獨終老。雖然文內標注改變了原文的懸念設計,但有助于減少讀者的閱讀障礙,增加讀者對原文情節的理解和期待。
第二,增加史家的敘事口吻。“外史氏曰”是外史或野史作者在寫作中采用的一種稱謂,同《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和《左傳》中的“君子曰”一樣,用于發表議論、表明寫作宗旨,抒發對故事中人物、事件的情感傾向以及揭示對人生、社會的感悟等。受史傳傳統的影響,林紓會在譯文中嵌入史家的干預敘事口吻,以“外史氏曰”的方式與讀者交流讀書心得。以第39章麥克斯廷厄太太好不容易找到卡特爾船長,破門而入的情景為例。原文寫道:
How the captain,even in the satisfaction of admitting such a guest,could have only shut the door and not locked it,of which negligence he was undoubtedly guilty,is one of those questions that must for ever remain mere points of speculation,or vague charges against destiny.[11]
流露出敘述者對船長即將遭受麥克斯廷厄太太的指責和辱罵的同情。而林紓譯為“外史氏曰,吾乃不審船主如此精審之人,胡以今日迎迓其良友,乃忘拴其門,得此巨禍,良天意也。”[12]“外史氏曰”的增譯淡化了原文敘述者說故事時的情感流露,增添了譯文的史傳色彩。敘事者仿佛變成故事外冷靜的敘事觀察者,口吻更加含蓄隱晦。
第三,刪減大量描寫,重塑古文簡練之風。狄更斯的小說中不乏場景描寫,也不乏對小說中荒誕人物的外貌描寫及心理描寫等。身為古文家,林紓深諳“喋言成絮,弊在不知舉其簡要”,便“棄其駢枝耳”[9],有選擇地刪去大量細節描寫,最大限度地實現古文的雅潔和精練之風。在第1章,原文花了大量筆墨描述討克司小姐的容貌、神情、服飾、動作等,而林紓在整體上把握了討克司小姐出場時滑稽、荒誕的形象之后,就粗其人文大略,摘其精要述之:“討克司長瘦人也,衣服半舊,貌至足恭。平日好聞耳語,故傾其首,因而永永其首皆微偏”和“其鼻本如懸膽,所恨半道復突一峰,遂將峰內鉤,成為鷹啄之狀”[13],譯文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在第48章,林紓又簡化了佛羅倫司離家出走時沿途的街頭場景,轉以三兩閑筆“次日乃大出,人聲亦大喧”,使“孝女遂直前行”和“孝女左右初無所見,遙遙已見木偶人矣”[14]這兩組情節相扣起來。改造后的譯文句式短小精悍,讀來頗有古文風韻。美國漢學家韋利就十分贊賞林紓的大量刪減,認為“原著中所有過多的細節描述、夸大的敘述和喋喋不休的饒舌都消失了”[15]。
綜上觀之,無論是對原文敘事結構的補充說明,還是對原文敘事口吻的改述,又或是對原文敘事描寫的大量刪減,嚴格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訛”,是林紓對原文敘事的各種“不忠實”。這與其說是林紓以譯者角色直接處置文本,不如說是其譯者身份下古文家角色對小說文本的介入,是“譯者很大程度上以非譯者的角色或者超越翻譯的角色而有條件地對‘原文’的再分配,是對譯文的處置(不完全是翻譯)”[6]。據統計,晚清小說的讀者大都“出于舊學界而輸入新學說者”[16]。這些舊式文人多浸潤于傳統文學中,林紓古文化的敘事風格符合傳統文學規范,更容易贏得他們的青睞。換言之,林紓對原文的改造是為迎合讀者閱讀習慣和審美需要而采取的一種積極的翻譯策略,凸顯了其社會人本質。從翻譯效果上看,其用中國傳統文學形式包裝西方文學的手段,給晚清讀者似曾相識之感,有利于域外文學在目的語社會的接納和吸收[17]。
(二)林紓的儒生角色與倫理闡釋之“訛”
林紓深受正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注重宣揚傳統道德,捍衛儒家正統。至老年,他仍就儒學的存廢問題與新文化文人展開筆伐。他一生雖未入仕途,但“以其大半生非科舉應試,即傳道授業的身份來說,判其為‘業儒’也并不為過”[18]。林紓儒生角色融入翻譯活動中,促使其用中國的倫理道德標準去闡釋或改造西方觀念,捍衛儒家傳統倫理。
第一,用“孝”置換基督教觀念。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狄更斯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其中,對狄更斯影響最大的就是基督教博愛精神。他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宣揚“愛”,也塑造了不少天使般的形象。在《冰雪因緣》中,佛羅倫司就是“愛”的天使,有著未受玷污的純潔心靈。她就像一盞明燈,用愛給予弟弟保羅光明和溫暖,用愛喚回冷漠自私的父親,令他回歸到家庭生活中。而在林譯文中,這種世間血濃于水的手足之情、父慈子愛被升華到“孝”的倫理高度,佛羅倫司的“天使”形象變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女形象。在第48章和第49章中,林紓不僅頻頻直呼佛羅倫司為“孝女”(多達二十余次),映射佛羅倫司之所為均“為孝感所逼”[14],更借他人之口來贊嘆其“孝”,稱“佛羅倫司之心,萬年不變,孝行令人生感”,“非但女也,且賢女而孝女”[14]。如此一來,原文內嵌的宗教博愛精神被置換成以“孝”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實現了對佛羅倫司“天使”形象的“孝女”改造。這樣的改造有利于認識到“西人不盡不孝矣,西學可以學矣”[8],從而讓晚清讀者順利接受西學。
第二,以“禮”和“義”闡釋人物言行。林紓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禮”和“義”的道德倫理觀深深烙印在其思想中,在林譯小說中出現頻率極高,幾乎每部小說中都可見。一方面,他會用極具儒家色彩的“禮”來闡釋長輩與晚輩之間、夫妻之間、朋友之間的各種行為規范,“執手為禮”“接手為禮”“引手為禮”等與“禮”相關的表達頻頻出現在譯文中。另一方面,他會賦予小說人物“義”的價值取向,在他們身上構建儒家精神的理想人格。倭而忒遠赴印度時對船長說:“I don't mean to say that I deserve to be the pride and delight of his life—you believe me,I know,but I am.”[11]原文表達的是倭而忒擔心自己走后,伯伯會因失去他而大受打擊;林紓卻將之譯為“吾未有圖報之期,而伯伯乃施其奇愛”[19]。佛羅倫司的“God bless you,dear,kind friend!”[11]也被譯為“佛羅倫司報之以禮,呼之為恩人”[14]。可見,林譯中的“圖報之期”和“恩人”均為原文所無,是林紓將“知恩圖報”的中國傳統美德注入人物的言行之中。他認為伯伯對倭而忒有養育之恩,卡特爾對佛羅倫司有救命之恩,理應回報。這反映了林紓將“義”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價值規范、人們立身處世的根本和有節操之人應堅守的“道義”。
林紓用自己熟悉的儒家倫理改寫原文的基督教思想和內容,可以看作其儒生角色融入到翻譯活動中,與社會因素和文化環境進行互動的結果,凸顯的是其社會人角色。為求譯文之用,林紓常會“稍為渲染,求合于中國之可行者”[8]。具體到譯文的倫理價值觀上,表現為其改造或者調整原文部分思想或內容,使之符合中國文化的價值規范。為此,他有意淡化原文的基督教觀念,而強化中國傳統倫理的“孝”“義”“禮”,以迎合中國的傳統道德和個人倫理需要。歷史證明,這種為外國觀念套上中國倫理外衣的做法,既有助于目的語地的中國讀者接受西洋小說,也避免了譯作有悖道德準則、違反禮防而受到社會的譴責。
(三)林紓畫家角色與符際翻譯之“訛”
狄更斯的小說都配有插圖,每幅插圖都突出了小說中的重要場景、人物及故事情節,成為其小說的精彩組成部分。這些插圖不僅成為當時目不識丁的下層英國人民領略原文大意的重要手段,也成為不識“蟹行文字”的林紓捕捉原文風格、人物風貌的重要途徑。林紓曾因看到《拿破侖傳》中氣勢恢宏的數幅圖畫而欲譯之,他會特別留意狄更斯小說中的插畫就不足為奇了。插畫成為連接林紓的畫家角色和譯者角色的一個重要符際通道,也為其因符際翻譯(非語言符號轉化為語言符號)而產生的“訛”提供了重要線索。
第一,增添小說人物的外貌特征。狄氏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豐富,且特色鮮明。雖然狄更斯對人物動作、衣飾等做了描寫,但具體到插畫上,插畫師仍需在人物外貌的具體細節上下功夫,以使人物更加立體飽滿,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船長卡特爾就是其中之一,他為人熱情,言行滑稽可笑。請看圖1:

圖1
At these words Captain Cuttle,as by an involuntary gesture,clapped his hand to his head,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and looked discomfited……
……Again the Captain clapped his hand to his head,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and looked discomfited.[11]
語至此,船主以手自摩其頂,頂毛已禿,然惶恐之狀已露。……船主又摩其禿頂,狀至慚悚。[10]
通過對比原文和譯文,可以看出林紓將原文中“on which the hard glazed hat was not”略去不譯,在譯文中增添了“頂毛已禿”“摩其禿頂”的外貌細節描寫。乍一看,原文與譯文出入頗大,但結合原文插畫,就能明白林紓的良苦用心。畫中船長正用左手鐵鉤撓頭,幾根稀疏的頭發散落于船長頭上,顯得十分滑稽可笑。林紓豐富的作畫作文的經驗使其深諳繪畫當同“歐公之文學昌黎……善于傳摹移寫”的道理,也贊同“顧長康頰上三毫,其妙理為人敘述不出者,此則專在神會矣”[9]的做法。于是,為了突出船長的滑稽之態,林紓添枝加葉,強調船長的禿頂,既讓讀者加深了對這個人物的印象記憶,也為譯文增添了幽默風趣,達到了其所謂“移貌而取神”[9]的目的。
第二,夸大或增添小說人物的動作。林紓在閱讀古文和史傳時喜歡留意原作中不經意流露出的風趣,指出“風趣者,見文字之天真;于及莊重之中,有時風趣間出”[9]。連寫古文也要追求風趣的林紓,翻譯時看到原文的滑稽插畫,難免手癢心動,為作者代勞,以增加小說的幽默感和戲劇化。再以上文提及的麥克斯廷厄太太帶著她的孩子們找到船長的情景為例。找到船長后,她大吼大叫,孩子們又哭又鬧,船長欲避而遠之。這一場面夸張得像在上演一場鬧劇,詼諧感十足。插畫師將這一鬧劇在插畫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活靈活現。請看圖2:
But,the moment Captain Cuttle understood the full extent of his misfortune,self-preservation dictated an attempt at flight.Darting at the little door which opened from the parlour on the steep little range of cellar steps,the captain made a rush,head foremost,at the latter,like a man indifferent to bruises and contusions,who only sought to hide himself in the boss of the earth.In this gallant effort he would probably have succeeded,but for the affectionate dispositions of Juliana and Chowley,who,pining him by the leg—one of those dear children holding on to each—claimed him as their friends,with lamentable cries.[11]
其始但震恐,后乃自顧性命,遂奪門而逃。復室中有小門,通地窖。船主啟之,且下,然后襟及股咸為周利亞及卻而司所執。[12]
林紓雖然沒有逐字逐句將原文譯出,如省略了修辭語句“like a man indifferent to bruises and contusions,who only sought to hide himself in the boss of the earth”,但原文的戲劇性卻不減分毫。“self-preservation”被譯為“自顧性命”,給人一種船長正處于性命攸關之際的感覺,而“奪門而逃”的“奪”字更是突出十萬火急,渲染出事情的嚴重性。在林紓的經營下,船主“啟之”和“且下”這一連串的動作讓讀者身歷其境,烘托出船長在開門逃走的那一刻被兩個孩子抱住,動彈不得的滑稽場景。這樣的改造使一個驚慌失措、急于奔命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有利于讓讀者透過譯文,領略原文“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8]之妙。
林紓多年的繪畫經驗和畫家眼光賦予其敏銳的藝術鑒賞力,也彌補了其不通西文的劣勢,使之能夠透過狄氏小說中的插畫捕捉到原文的幽默風趣。他充分發揮畫家角色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將原文插畫中蘊含的意義以語言形式表達出來,造成了種種偏離原文語言,卻與原文插畫細節相吻合的“訛錯”現象。正如林元彪所言,林紓把插圖的視覺效果直接寫進譯文,才導致譯文與原文不合[20]。從譯者角色化來看,林譯的這些“訛錯”正是其畫家角色融入翻譯活動時留下的意志體譯者的行為痕跡,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其多方面的才能。總之,林紓的看圖翻譯與原文插畫有異曲同工之妙,令人物形象更加生動,增添了譯文的幽默風格,亦有助于讀者透過文字領略原文的人物風貌和詼諧的文風。
三、結語
林紓雖然以譯介西洋小說聞名于世,但其古文家、儒生和畫家等多重身份角色在其翻譯活動中的作用不容小覷。這些角色相互交織,互為補充,在譯文中留下各種行為痕跡,對林譯的“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古文家角色促使其對原作敘事進行古文化的敘事改造,儒生角色推動其對西方觀念進行傳統倫理的改造,畫家角色又助其看圖改寫,再現原文風格。林紓的多元角色,使他不囿于原文的束縛,巧妙通過各種增刪改的策略化解翻譯中因語言不通、文化不同而造成的各種沖突,如文化缺省、藝術審美、意識形態等,從而順利地將譯本融入到晚清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達到傳播西學、維護傳統的翻譯效果。文學翻譯絕非簡單的字面對等,而是原語和譯語兩個文化系統之間的碰撞和協調[21]。在“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一個理性的譯者應該在文化碰撞和協調中做一個能夠詮釋不同角色的“千面人”,而不是一個只關注語碼轉換的“工具人”。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對外傳播,譯者應具備多元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化解中西方語言文化差異造成沖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