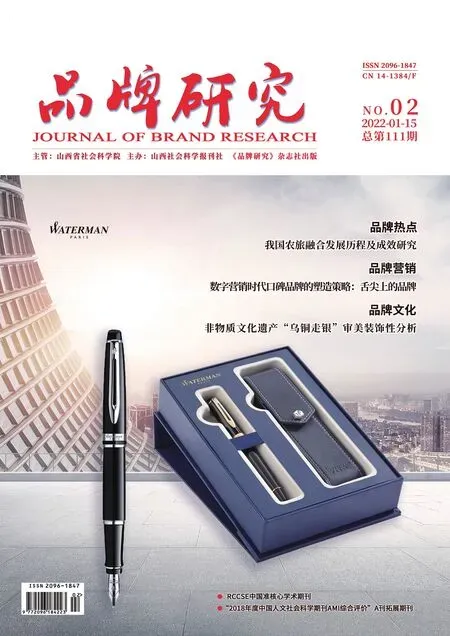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烏銅走銀”審美裝飾性分析
文/肖鈞韜 蘇箐(昆明理工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一、烏銅走銀常見的表現樣式
具有一定審美裝飾性的藝術品必定具有其獨特的表現形態,作為從清朝流傳下來的藝術工藝品——烏銅走銀,它的表現形式經歷了各個朝代更迭的影響。比如在清朝時期,整個社會處于一個相對平穩的時代,造就了當時科舉盛行,對于當時的書生來說,除了滿腹經綸以外最需要的就屬其用來寫字的案頭工具。而在社會相對動蕩的年代,這一文房用具就成為社會身份的地位象征。
墨盒,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其實并不長。它起源于清嘉慶道光年間,盛行于清光緒年間至19世紀初,器型多以四方和六方為主,只是作為文房用具中的一種輔助工具。關于墨盒的出現有一傳說:“有一個文人要去考試,他的妻子認為攜帶硯臺不方便,就把墨汁浸入到脂棉中,然后把浸了墨的脂棉放到自己的粉盒中,讓丈夫帶著去考試。”[1]墨盒的出現,不僅方便了當時考生趕考時不需要攜帶過于沉重的行李,還對當時人們在研磨時濃淡干濕掌握不當的煩惱進行了改進。
在墨盒興起之后,其存在就成為烏銅走銀的形態之一。以烏銅走銀打造的墨盒是由盒蓋與盒身兩個部分構成,盒蓋以烏銅為體,飾以銀狀走線為輔,整體以裝飾性為主;盒身整體亦為烏銅,走銀裝飾于盒體的側面,其主要功能是用于貯存墨汁的容器。作為墨盒的內胎所使用的材料一般都是銅質材料,而在烏銅走銀墨盒中通常用紫銅,這是因為紫銅的含鉛量高,可以較好地防止墨盒的內部被墨汁所腐蝕,同時紫銅的質地較軟。因此,烏銅走銀墨盒在內胎部分會和墨汁進行直接接觸的材質一般都會選用紫銅。雖然墨盒在20世紀的中期隨著新型文具的出現逐漸消失,但是烏銅走銀墨盒不僅是用作便利攜帶墨汁的工具,同時也代表了其中的文化內涵以及當時匠人們在其中凝聚的匠心與工藝技法,這也使得烏銅走銀在如今的藏品界備受矚目。
云南的烏銅走銀在表現形式上不同于傳統的繪畫形式,與傳統的工藝品形式制作也有所差異,在它制作的過程中會受到其材質與技法的限制,同時也要將當時的造物思想運用其中,從而使得烏銅走銀將傳統繪畫與金屬工藝品相結合,呈現出其獨特的美感。古人的思想最早是遵循“先器后飾”,在設計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其所將具備的功能性,其次才是利于美觀的裝飾外形。
二、烏銅走銀的材質色彩特征
烏銅走銀的色彩特征要從它的構成開始分析,烏銅走銀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分別是特殊冶煉出來的烏銅以及用作裝飾圖案的走銀。
烏銅走銀作為云南獨特的手工藝技巧,其迅速的發展離不開當地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礦產資源。云南地區號稱“有色金屬五國”。從17世紀以來,云南的銅、錫、銀就享有盛名,引起全國的矚目,在清代乾隆年間,每年運京銅達七百多萬斤,道光年間滇銅每年運京降為三百六十萬斤,稱為“京銅”,僅東川銅礦最高年產量達七百多萬斤,幾乎供應當時的大半個中國[2]。清朝時期盛行斑銅技術,而具有巧思的匠人結合了斑銅的技術并借鑒了傳統金屬技藝門類中的錯金銀技術,創造出了獨具一格的烏銅走銀技藝。
優質的材料是烏銅走銀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結合手工藝技巧才能將其制作成精美的工藝品。烏銅的主要原料為紫銅,配以金和銀等其他金屬元素來改變紫銅整體的特性,制作出成品之后的烏銅走銀會暫時呈現為紅色,需要經過匠人用手將器物不停地把玩,利用酸性汗液使之表面形成黑色氧化膜,從而將紫紅色的烏銅轉變成黑色。時間越久烏銅的表面就越黑,直至發亮。在烏銅走銀工藝品中,黑色作為主導色,在整個成品中占據了80%的面積,讓人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就會有質樸的美感。黑色以其濃度的不同,代表寂靜、沉重、嚴肅、神秘。
明成化年以前,銀礦的開采主要是官辦。據《明史·食貨志》及明代所篆修的諸種云南志記載, 先后開采銀礦二十三所。由于對銀礦的大量開采,產量日益上升,《明史·食貨志》稱天順云南銀的課額十萬兩有奇,占全國總銀課額的半數以上。不過成化以后云南官營銀礦則日趨衰落,官辦銀場由于時有“礦亂”發生,或歲課太重,或開采已盡,政府不得不停止開采,當官辦銀場衰落之際, 民營銀礦業逐漸興盛起來[3]。
在此背景下,銀礦的開采更加利民,開采量也大大提高,可用于制作藝術裝飾品的銀礦儲量也顯著提高。烏銅走銀中走銀的過程需要用質量較好、純度較高的銀塊,加熱將其熔化,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用吹管對融化的銀質溶液進行吹動,使其沿著先前鏨刻好的紋路流動,達到“走銀”的效果。作為烏銅走銀工藝品中的輔助色,白色也不是單一的純白色色調,不同純度的白色則代表了高尚、純真、明凈、簡潔。
在了解了烏銅走銀的構成之后,我們再從色彩的角度來分析其獨特的裝飾性。烏銅走銀整體的構成由“烏銅”與“銀”結合而成,其中“烏銅”所展示出來的顏色是黑色,而“銀”的屬性就是帶有金屬質感的白色,二者結合黑白雙色相伴相生。我國對于黑白兩色相互搭配方式可以說貫穿了整個國家歷史的發展,比如傳統繪畫中的水墨山水畫,抑或者是中國圍棋中的黑白二子互相博弈,斗智斗勇。烏銅走銀中的色彩也是用了黑白二色,其中作為主導的是作為器具主體的烏銅,以黑色為主;作為裝飾性色彩存在的走銀,以其具有金屬質感的白色作為輔助,襯托出烏銅走銀整體的質樸與敦厚。靈動輕巧的白色走銀“絲線”游走于莊重嚴肅的黑色銅胎之上,整體呈現給人們的視覺感官就是黑白分明的藝術工藝品。
由兩種單一材質所鑄就的烏銅走銀,其展現出來的獨特的審美特質也離不開這兩種材質的幫襯。而同樣是由單一材質所構成的就是我們常見的木質家具。
不同于需要冶煉的金屬材質,木材是天然生物材料,其紋理具有自然之美。木材本身所具備的年輪材質紋理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自然美感。作為天然的生物材料,木材對于木質家具的造型、結構和其所需的工藝設計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樹木生長的過程中,每年或者在旱季或者雨季的生長都會形成其獨特的生長輪,橫著切開樹木就能看到橫向切面所具有的一圈一圈圍起來的生長輪,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年輪。其中年輪的大小形狀都是不規則的,這和樹木在生長的時候所接觸到的陽光有關。不同的年輪形狀以及環狀排列都是木質家具不可缺少的設計靈感。同理作為樹木的一部分,其樹根、樹干以及樹枝都有其獨特的生態特征,對其進行加工之后呈現出來的木質紋理也各具特色。其不同的紋理結構造就了多重不同的美麗紋飾,加強了木質家具獨特的審美感。
樹種的不同也會造成木質家具呈現出來的色彩不同,例如梧桐木,是梧桐樹被砍伐后經過加工后成為可用的木材,有耐腐爛的特性,并且木材本身帶有一種色澤光亮的紋理,其木材適合制造樂器、家具等。中國古代傳說中對鳳凰的描述就有一條:“非梧桐不棲。”
色彩是一件工藝品的構成要素之一,其作用就是為了調動我們的審美情緒,通過色彩的表達來傳遞藝術品的情感,也是直接影響我們對其觀感的重要因素。烏銅走銀以其材質和黑白兩色的主要印象為主,給人帶去莊重和諧的色彩感官;而木質家具則以其獨特的紋理年輪給人帶去了溫馨自然的視覺感官。
三、烏銅走銀的裝飾性特征
烏銅走銀工藝品上的走銀,通過鏨刻出刻痕,然后再將融化的銀質金屬填滿刻痕,形成了其表面上的裝飾性花紋,其花紋的種類繁多,紋飾優美。本文將列舉其中幾種:

圖1 筆者拍攝于官渡古鎮烏銅走銀傳習館
梅蘭竹菊中的“菊”植物紋飾(圖1)。菊不僅清麗淡雅、芳香襲人,還開于百花凋后,不與群芳爭艷,故歷來象征恬然自處、傲然不屈的高尚品格。
就像《四君子賦》中的描述那樣:“菊,麗而不嬌。傲然臨霜,怒放于群芳凋零之際;不畏肅殺,盡展其萬方嬌媚之態。園藝之菊與野生之菊不同矣,野菊婆娑,點綴村舍疏籬,隨處而生,毋須人工;而園藝之菊,從春之下種至秋之綻放,其間治地釀土,防燥慮濕,摘頭掐葉,接枝捕蟲,防雨避霜,使藝菊之人難得閑暇。從古到今,歷代藝菊之人傾心培育,使其種類紛繁,姿態萬千。是謂:菊之美,三分出自天工,七分來自人力,藝菊之人終年辛勞,以人力助天工,菊之美,實臻天人合一之境也。”
五福捧壽紋飾(圖2)。《書·洪范》記載:“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寓意多福多壽,之后東漢桓譚在《新論·辨惑第十三》中更改五福為“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4]。原本在烏銅走銀的紋飾中多以美好寓意的植物或動物作為裝飾的主體,但是該紋飾卻由五只蝙蝠圍繞著篆書狀的“壽”字,其主要原因是借蝙蝠中的“蝠”來表達諧音“福”,中國人巧妙地用同音字將蝙蝠略帶恐怖的形象轉換成了翼騰祥云的吉祥寓意。

圖2 筆者拍攝于官渡古鎮烏銅走銀傳習館
喜上眉梢紋飾(圖3)。整體紋飾以喜鵲與梅花所構成,其表現形式常呈現為兩只喜鵲站立于梅花枝頭,借此表現“喜上眉梢”主題。從古至今,人們認為鵲這類鳥能報喜,于是喜鵲也稱報喜鳥,其存在也是代表了吉祥喜慶的寓意。而兩只喜鵲代表的就是雙喜,“梅”又與“眉”同音,通常來說,喜鵲站上枝頭就寓意著雙喜臨門之事。

圖3 筆者拍攝于官渡古鎮烏銅走銀傳習館
可以發現傳統烏銅走銀在紋飾的選擇上基本都選擇了歷史中許多代表美好寓意的圖案花紋,意在通過鏨刻美好的圖案為烏銅走銀帶去更深刻的含義。在設計中,視覺符號圖案元素的運用,深刻地影響著設計意圖的表達,其獨特的創造性和設計形式,挖掘和體現著“點、線、面”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5]。
四、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的手工藝藝術,包括了手工技藝和手工作品兩個方面;對于手工藝技藝來說,是一種非物質文化,而手工藝作品則是物質文化,兩者缺一不可[6]。烏銅走銀色彩的搭配黑白相交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中陰陽調和的哲學思想,其主題表達的就是相伴相生。烏銅走銀在審美裝飾性上都追求一種隱性的內在美,通過另一種物質來表達其想表達的含義,在器皿的紋飾設計上多選擇具有含蓄意味裝飾圖文,來表達其美好寓意。從這些要點分析,烏銅走銀所具備的審美裝飾性包含了從古流傳至今的傳統哲學思想以及含蓄的圖文裝飾,這些獨特的裝飾性元素正是它以后傳承和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