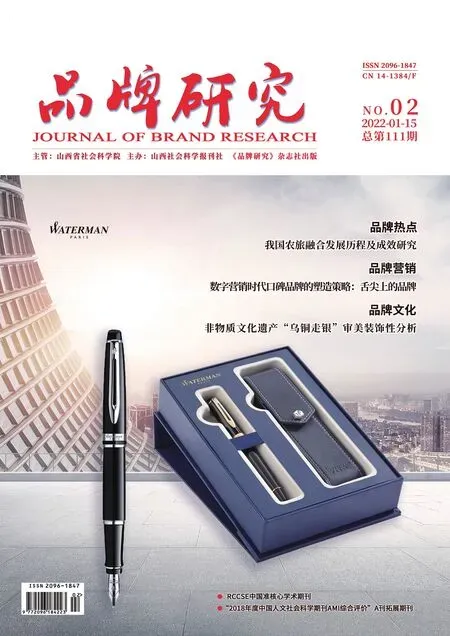企業外部網絡賦能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思考
文/肖寶嘉(廣西大學)
數字化轉型是一種商業模式,是建立在數字化轉換、數字化升級基礎上,進一步觸及企業的核心業務,以新建一種商業模式作為目標的“高層次”轉型。具體而言,企業應當開發數字化技術及相應的支持能力,重新構建出一套具備更大活力的數字化商業模式。需注意的問題為:數字化轉型并不僅僅是企業引入互聯網、IT技術或設備即可,而是應該對各項業務流程及模式、組織活動、員工能力進行全面重新定義,才能真正實現數字化轉型。
一、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力分析
(一)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行動能力
王重鳴對“行動能力”的定義是:“有一定的意愿、目標作為指導,能夠踐行某種行動策略、行動調節、行動升級的能力”,包含“策劃推進能力”和“調節升級能力”。在生活中,任何一個項目若要進行“轉型”,除了一小部分“水到渠成”之外,絕大多數轉型者都會面臨極大的轉型壓力及挑戰[1]。比如一家中小型企業需要進行全面數字化轉型,首先需要購置一定數量的PC電腦,并從第三方公司處購買智能管理軟件。涉及的費用少則數萬元,多則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對中小型企業而言,額外支出大量資金意味著企業的流動資金減少,一旦有項目的回款出現問題,則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必定大幅度增加,情況嚴重時甚至會使企業蒙受極大的損失。因此,很多中小型企業遲遲不開展數字化轉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沒有認識到此種轉型的必要性,而是承擔風險的能力較低[2]。
所謂的“策劃推進能力”包含三個要素:第一,行動目標。要求企業的決策者首先圍繞“數字化轉型”進行全面思考,將企業完成轉型后應該呈現出什么樣的狀態,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變,相關的管理規則是否需要調整等,均需要統一考量。在行動目標確定之后,才能正式啟動數字化轉型項目。第二,主動行動。對一個企業而言,“轉型”的過程如果充斥著“被動性”,那表明轉型之前的準備工作沒有做到位,甚至完全沒有準備,只是因為企業的日常運轉很可能已經受到嚴重阻滯,不得不進行調整的“無奈之舉”。而“主動行動”則帶有主觀意愿,是企業管理者對數字化轉型團隊的組建與之后的運作、資金的籌措與投入、市場的變化情況以及未來展望、有關產品的生產技術(包含研發)及產量、銷售相關事宜等進行全方位規劃且認為方案可行之后,主動啟動轉型[3]。不僅如此,企業管理者必定做好了相對完善的準備,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突發情況時能夠及時應對,達到“全程有效控制,平穩完成轉型”的目的。第三,反饋推進。“轉型”是企業為了更好地經營,適應市場新動向、政策調整新方向而主動采取的措施,不能“為了轉型而轉型”。因此,是否進行轉型,轉型過程中出現特定的情況需有效反饋給企業管理者。總體而言,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本身存在一定的風險,轉型過程中會有一定的“未知”,故“反饋推進”是數字化轉型行動能力中的重要因素。
行動升級能力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臨近完成階段的一種“高階能力”。具體而言,當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團隊已經組建完畢,已經完成數字化轉型且啟動了某些項目,得到了正向反饋時,為了進一步對數字化轉型有關行動進行監督、回顧、調整,需要做深度部署。此種“高階能力”同樣包含三項具體內容:第一,前瞻警覺。不同企業的內部運轉情況、人員綜合能力、面臨的壓力及外部環境等均存在一定的差距,故其他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功經驗不能百分百地直接應用于本企業。因此,轉型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如人員行為、項目進展情況與預期結果之間差異過大等。對此類情況,企業管理者應該有所預估,并提前做好應對機制。第二,行動調節。階段性的成果出現之后,針對其中的“正向”信息,應進行“促進式”調節;對“負向”信息應進行“防范式”調節。前者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拓展新業務,后者則是對意料之外的情況進行總結、分析,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第三,行動升級。前文提到,中小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目的在于使企業更好地發展,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因此,轉型結果如果沒有達到預期,或是在一定時間內甚至還出現超出預期的虧損,則企業管理者需要及時轉變思路。如果反饋結果較好,則企業經營者需要進一步提升效能、擴大成果。
(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團隊能力
決定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為企業的團隊能力。具體而言:第一,團隊協同能力。在我國偉大的歷史轉折階段,鄧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全面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贊同。但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便是一句空談,在實際工作中必定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阻礙。因此,在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元帥便說道:“工作重心轉移,那么大的事情,不統一思想怎么能行?”可見,在任何一個團隊中,如果團隊成員的思想不統一,便不可能形成“合力”;如果團隊協同能力較差,團隊的凝聚力和競爭力自然有限。因此,企業管理者若要進行數字化轉型,則必須統一員工思想(特別是企業中高層管理者的思想)。第二,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團隊能力可分為“目標角色”以及“協同問責”兩個大方面[4]。前者包含:(1)目標整合,即數字化轉型團隊需要在個人和群體目標之間完成協調和整合;(2)任務協調,需要注重提高團隊多任務、跨職能、綜合項目、新創業務處理能力,并關注資源分配、人員調配相關事宜,不能厚此薄彼;(3)角色塑造。轉型期間,團隊內各個成員之間都應有新的角色定位,而每個成員的定位都伴隨著資源的重新劃撥,需整體保證“公平”。“協同問責”包含:(1)項目協同,即團隊需要具備“技能互補”“合作目標”“績效關聯”的能力;(2)交叉職能,高效率的團隊必須是一個對交叉職能目標負責人的團隊,且需有人負責;(3)團隊問責,企業數字化轉型如果失敗,且被證明是轉型方向、方式方法有問題,便意味著決策階段出現問題,需要問責;此外,還包含局部利益問責和分管職能問責。
二、外部網絡賦能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的影響
(一)外部網絡賦能的特點
所謂“賦能”最早是一個網絡用語,是指“賦予能量”“給予幫助”,是指靈活運用網絡平臺,增強業務能力、提高業務效率。對現代企業而言,對“外部網絡賦能”理解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且兩者之間存在很大的關聯性。其一,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在內部管理以及業務開展模式方面均需更加重視智能化、網絡化、現代化的建設。如一些中小貿易企業,日常以代理經營為主要業務。在電商、網商的大環境下,由于實體店經營模式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而網絡銷售、直播銷售等模式異軍突起,故企業必須探索新的業務開展方式。其二,“外部網絡賦能”是表象,核心內容為“數據賦能”。當前社會已經進入“大數據分析”時代,任何事物的本質都是數據。而通過對數據進行收集、分析之后,有助于找到潛藏在數據背后的客觀規律,最終有效利用這種規律,解決實際問題。
(二)中小企業基于外部網絡賦能的數字化轉型難點分析
很多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失敗的,原因在于盲目“跟風上”,沒有學到精髓。比如一家中小型銷售公司定期對特定商品(很可能是一些十分流行,銷售量能夠得到保障且利潤較高的商品,并未無人問津的過時商品)進行打折銷售,或者配以輔助銷售用品(以手機為例,賣手機的同時,不僅能夠保證手機都是正品、新機,還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額外贈送藍牙耳機、充電寶、手機殼等物,會大幅度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這家公司對競爭對手售賣的同等價位商品進行分析后發現,對手的商品即使不打折也能出現火熱的售賣爆點,其新品流通速率比自家企業快20%,其熱門商品從未出現“二次跟進數量少一半”的情況。表面看來,兩家企業采用了不同的銷售模式,但實際上,對手基于數據賦能進行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可能遠遠超過自身企業,區別之處在于,競爭對手從“需求”和“痛點”兩個層面著手,對市場高階數據進行了全面收集,已經摸準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以及市場的動態變化情況。因此,對中小企業而言,基于外部網絡賦能(數據賦能)的數字化轉型的最大難點在于,能否真正做到“從需求出發”以及“從痛點出發”。如圖1所示為“從需求出發”的相關要素,圖2所示為“從痛點出發”的相關要素。具體而言,第一,從需求出發,推導可行解決范圍,落實到一個具體問題上。第二,從痛點出發,先找到需求背后的真實痛點,再找解決痛點的方案。而若要達到上述目的,需要借助網絡平臺廣泛收集數據,最終找到背后的客觀規律。

圖1 從需求出發的要素

圖2 從痛點出發的相關要素
(三)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后必須形成的業務開展模式
現代中小企業的通病在于,真正能夠靜下心來圍繞各方數據進行分析的人十分稀少。以外部網絡賦能(數據賦能)為例,盡管口頭上經常談到“重視數據、科學利用數據”,但實際情況是“中小企業業務能手不屑于看數據,普通業務員看不懂數據”。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最后的數據報表或者根本沒人看,或者成為一種能夠令人產生“高大上”之感的擺設,完全無法起到實際作用。為了簡化數據賦能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驟,筆者編制了一個“順口溜”:一量化現狀,(為賦能,下同)打好基礎;二梳理問題,指明方向;三篩選方法,優化效率;四監控進度,保駕護航;五總結經驗,積累成果。利用數據賦能進行數字化轉型,開展相關業務的核心要素實際上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過去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應用的業務場景為:曾經處理過類似問題,已經有一定的套路可以使用。過去的數據和本次新產生的數據之間還應進行分析,找出“引導成功”的行為特征及實際效果;第二,對新形成的方法進行測試,應用場景為:沒有過往經驗作為支撐,但現階段已經形成一個或多個解決方案;第三,找到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或團隊,應用場景為:企業目前經營的某個項目面臨困難,且當前負責的團隊無計可施,有關領導已經很不滿意。面對此種情況,只有從團隊中找出能力強的人并參考他的做法,以解決問題作為首要任務,應顧全大局。
三、結語
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能否真正明確大數據分析時代企業經營的特性,即能否建立高效率數據信息收集及分析機制。企業只有明確數據的重要性,能夠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找出其中潛藏的客觀規律,并圍繞這些規律制定發展戰略,才有可能使企業健康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