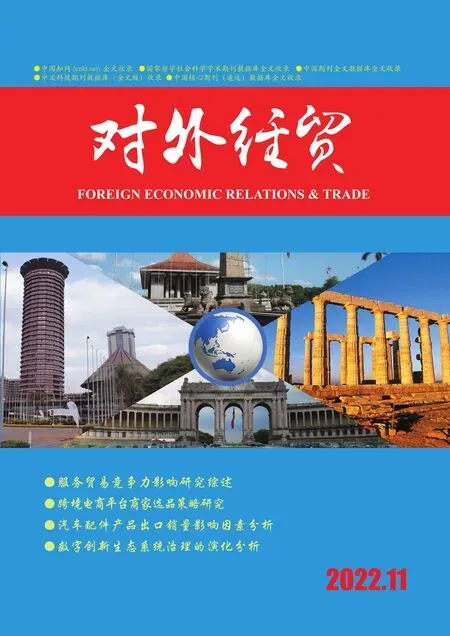服務業FDI 對我國就業質量的影響研究
——以京津冀城市群為例
趙曉梅 劉 瑋
(貴州財經大學,貴州 貴陽 550025)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擴大,我國已從“工業經濟”時代逐漸步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來愈高。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大力發展農業經濟,工業發展尚不成熟,FDI 大都流向了制造業。2001 年我國加入WTO 后,服務業FDI 準入門檻逐漸降低,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政策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外資企業大多選擇投資服務業。特別是近年來,服務業FDI 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占比高達六成之多,相應地帶來了服務就業人數的大幅增長。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流入我國服務業的FDI 在三次產業中占比僅為25.7%,到了2011 年占比首次超過50%,截止2020 年底占比高達66%,可見服務業已成為我國使用外資的新發展點。自2011 年服務業FDI 占比超過一半后,我國服務業就業人數達到了27185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比重的35.7%,到了2020 年我國服務業就業人數為35806 萬人,占比接近50%,說明服務業已成為我國吸納就業的主要途徑。因此研究服務業FDI 與就業之間的有助于我國制定外資政策以促進經濟結構轉型[1]。
一、服務業FDI 與服務業就業現狀分析
(一)服務業FDI 發展現狀
1.中國服務業FDI 規模穩步增加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逐漸放寬了對服務業的各種限制,旨在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發展,FDI 漲到104.6 億美元。2008 年受全球次貸危機影響,外商的跨國投資行為都趨于謹慎。由于積極進行了宏觀政策調控[2],我國實現了經濟的穩健增長,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增至309.82 億美元。此后,伴隨著我國引資政策的健全,中國經濟活力的上升,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隨著經濟穩步增長。服務業FDI 從2011 年的582.53 億美元增至2020 年的1072.01 億美元,增長超過45%,帶動了第三產業產值從216123.6 億元飆升至553976.8億元,增長接近61%。服務業能夠加強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合理調節社會的生產、消費、信息傳遞等過程,其發展水平可以反映一國的家庭經濟情況,可被用來衡量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此外,就業作為民生之本,是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的重要條件,相比于一二產業,服務業涵蓋的行業多且范圍廣,曾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我國勞動就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不容小覷。
2.流入新興服務業的FDI 占比上升
3.服務業FDI 顯著增加了京津冀國內生產總值
京津冀城市群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素有“首都經濟圈”的美名。它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13 個城市,約占全國面積的2.26%,2020 年實現了8.5%的全國GDP 占比。京津冀城市群現已建成“相鄰城市1 到2 小時”的交通圈,在大力發揮天津、秦皇島濱海優勢的基礎上,實現了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隨著相關政策規定的提出,近年來北京已開始向周邊轉移部分產業,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城市群開始著重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節能環保和現代物流等產業,形成了“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的空間結構。2011 年京津冀城市群服務業FDI 為145.8 億美元,2020 年達到271.6 億美元,增長近46.5%。從城市群內部看,服務業FDI 顯著增加了各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2020 年北京、天津和河北服務業增加值分別為150209 億美元、45626 億美元和94251億美元,服務業占比分別為84.51%、63.5%、52.9%,城市群產業結構逐漸呈現“三、二、一”的梯形分布,服務業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發展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服務業就業發展現狀
1.服務業已成吸納就業的主產業
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中央在“十一五”時期就制定了若干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戰略部署和具體措施,旨在加快經濟結構轉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以調整一二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到“十三五”期間,我國服務業在“質”和“量”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自2012 年起,服務業產值在三次產業中高居首位,占比達45.5%。此后一直保持穩定增長,2015 年就超過了50%。2020 年服務業產值占比穩定在54.5%。按照國際公認標準,當一國或地區的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時,便可認為該國或地區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3]。與服務業產值不斷增長相適應的是就業人數的增加,2011 年我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比35.7%,為三次產業最高,這一數值于2020 年增至47.7%。服務業就業人數占比逐漸接近50%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社會經濟已逐漸偏向服務化,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就業人數的主產業。
2.傳統服務業就業占比下降,新興服務業就業占比上升
從行業內部來看,傳統服務業就業人數在服務業的占比一直穩定在50%左右。雖然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仍然是吸納服務業就業的兩大蓄水池,就業人數的絕對數量有所增加,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零售業經營成本的持續攀升,兩行業就業人數在總人數的占比正在逐年下降。教育和公共管理與社會組織業在的占比也呈明顯下降趨勢,分別從2011 年的24.3%和22.1%下降到2020 年的19.1%和19.2%,說明傳統服務業已不是服務業就業的最熱門行業。而諸如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新興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出現顯著增加,占比也在不斷提高。由此可見,服務業分行業就業人數的增加并不均衡,傳統服務業就業人數的絕對數量有所增加但是占比卻在逐年下降,這正與我國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背景下的就業結構調整的大方向相適應。隨著我國數字技術發展與產業數字化轉型,服務業就業結構正在逐漸走向均衡,將會更加多元化和創新化,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就業者加入到新興服務行業中,推動我國朝著科技強國的方向努力。
3.京津冀城市群服務業就業增長有待進一步均衡
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京津冀區域就業聯動發展取得重大進展,帶來了就業質量的提升。據58 同城統計研究,在京津冀地區,北京的招聘求職活躍度最高。從城市群內部來看,北京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素來高校云集、人才輩出,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就業機會,一直都是大部分就業者的首選之地。北京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從2011 年的791.4 萬人增長到2020 年的1047.2 萬人,年均增長率為3.04%;天津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從2011 年的109.8 萬人增長到2020 年的160.72 萬人,年均增長率達4%;河北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從2011 年的1202.96 萬人增長到2019 年①的1460.52 萬人,年均增長率為2.38%。就業規模是衡量一個地區人力資本的基礎性指標,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該地區人才資源發展的潛力。天津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增長率比河北高出1%,由此可見京津冀城市群的區域經濟發展并不平衡,人力資源發展的潛力并不相同,為服務業從業人員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均等。
二、服務業FDI 流入為就業質量帶來新機遇
(一)推動人力資本開發,創造高質量就業機會
外資流入服務業,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人力資本開發,引導資本良性發展[2]。首先,外資企業提供的高薪報酬和優質就業環境就要求勞動者加大自身教育投入,提高專業技能水平。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通常會加大教育經費的支出。相比于其他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突出優勢,區域內教育資源集中且質量高,而教育經費支出大就更能培育出優秀技術人才,這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我國就業質量的提升。最后,大量外資涌入我國,有助于高質量人才的回流,減少人才流失。高質量人才在國內勞動力市場產生較強的“鯰魚效應”,進而促進相關就業者提高自身能力素質。綜上,服務業FDI 流入我國后,外企高質量、高標準的就業福利,促進了我國服務業增加教育經費投入,推動人力資本開發,進而提高我國就業質量。
根據具體操作的類型、特點確定評價的要素點。例如:一名學生點評操作時的醫患溝通,一名學生點評操作時的部位選擇,一名學生點評無菌操作,一名學生點評操作過程和步驟,一名學生點評操作過程中的人文關懷。
(二)勞動者技能水平的提高和行業發展水平的上升
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往往伴隨著一系列的技術溢出效應,包括競合效應、示范效應和人才流動效應[2]。首先,外資加劇了行業內部的競爭,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的合作。中關村科技園作為我國自主創新示范區,外資大多流入了園區內的支柱產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對其他服務行業產生了競爭效應,不過該行業生產的軟件可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所用,形成行業間的合作效應。其次,外資企業在新技術的開拓與使用方面更有經驗,會對服務業產生良好的示范效應。濱海新區通過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布局,積極參與京津冀地區打造世界級產業創新中心的項目,與外資進行了深度合作,在促進區域內就業人員技能水平和行業發展水平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對全國其他區域都極具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外資企業比本土企業更注重對員工的培養,高素質人才在行業內流動時,可帶來良性的人才流動效應。雄安新區作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新區,承接了來自北京的高校、醫療、金融等資源,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激勵與引進政策來吸引高端人才來雄安安家落戶,高素質人才在京津冀區域的同行業內流動,帶動了河北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就業質量。
(三)發揮區域優勢,促進勞動市場資源合理配置
京津冀城市群可以充分發揮區域優勢以吸引外資,形成優勢產業集聚,促進高水平勞動市場形成。從城市群內看,各區優勢不盡相同。首先,北京作為我國科技創新中心,集聚了眾多世界一流大學和科研機構,具有極強的知識產生能力,大量世界級科技企業和跨國公司也在此落地,可以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帶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其次,天津作為我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擁有世界等級最高、吞吐量居世界第四的天津港。近年來天津除了探索高端金融服務業之外,還利用濱海優勢在海洋交通運輸、海洋旅游娛樂、電商保稅區等新興服務業也發展得風生水起。河北曾在2020 年11月舉辦了冬奧冰雪產業交流會,為相關人才提供9000余個就業崗位。冬奧會的成功舉辦不僅促進了河北的交通、通訊、房地產等基礎設施建設和新能源、新技術項目發展,而且對提高張家口知名度,拉動河北體育事業發展也大有裨益。21 世紀以來河北高新技術產業及現代服務業展現出較強的發展潛力,前景一片光明。京津冀城市群應在研究了各區域稟賦的基礎上,針對優勢產業推出相關政策措施以吸納高素質人才就業,減少人才外流,提升服務業整體的就業質量。
三、服務業FDI 流入就業質量分析
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現代服務業已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天津也已基本實現技術集約化和產業高端化。作為我國首都,北京的產業集聚效應極強,人才和科技優勢明顯,知識型服務業非常發達,并且具有配套服務優勢,是外資進入的首選地。
就各行業來看,相比于2011 年,北京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FDI 占比增長近一倍,帶來了就業人數約5%的增長。然而流入傳統服務業的外資規模正在逐年遞減,就業人數規模也在縮小。充分體現出外資流入促進了新興服務業就業,北京的服務業發展并不均衡。天津服務業表現為外資流入傳統服務業比重下降和就業人數占比減少,大部分人才就業選擇了金融、信息和物流等現代服務行業。努力尋求轉型契機,實現了房地產業、物流行業就業水平的提升。總之,服務業的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協調性最好,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行業并存能較好地兼容和吸納各層次就業人員,三地人才合作領域亟需擴大,合作內容和形式也亟待優化和創新。
四、對我國服務業就業發展的啟示
(一)針對區域優勢引入不同類型的FDI
鑒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資源稟賦差異也非常大。東部沿海地區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對人才的吸引力極強,許多高新技術企業大多集聚于此[1]。為了使外資流入服務業后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國相關部門應根據區域稟賦的不同,有針對性地引入不同類型的FDI。例如,東部地區應將外資引入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而西部地區應充分發揮勞動力優勢,積極引入外資到住宿和餐飲、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東西部地區可根據自身經濟結構在引資時有所側重,旨在對我國服務業就業質量產生積極影響。
(二)服務業FDI 應差別對待各行業
雖然京津冀城市群的服務業FDI 正在不斷增長,但流入的行業仍存在差異。制定差異化的外資引進政策,吸引外資流入我國高科技企業,帶動相關新興服務行業的發展,使得外資均衡流入服務業各行業,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增加現代服務業的就業人數,進而提高我國服務業就業質量。
(三)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優勢
近些年我國大力增加高校教育投入,使更多人能夠受到普惠平等的教育,有利于我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1],能夠促進我國就業質量的提升。各區域應該注重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培育高素質科技人才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優勢,從而提高就業質量。
[注釋]
①因《河北省統計年鑒》只更新到2020 年,故本文選用河北省2019 年數據進行對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