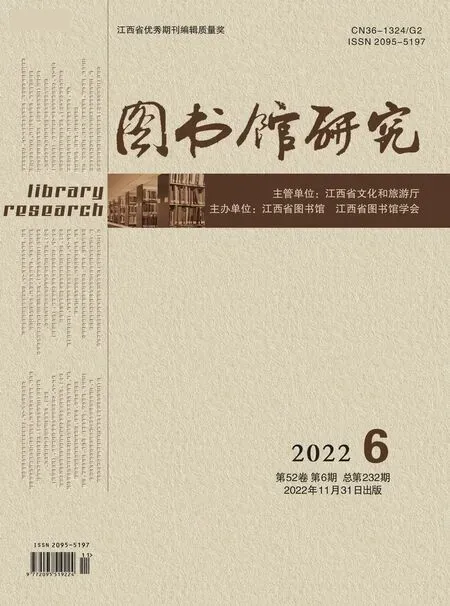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校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數字人文研究*
——以海南大學圖書館為例
李雷晗,魏胤巍,李文化,2
(1.海南大學網絡空間安全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2.海南大學圖書館,海南 海口 570228)
1 新文科的提出及特點
近年來,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文科在學術研究方式上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人文研究強調素材積累,而隨著新技術在人文領域中的應用,將從根本上改變學者研究的手段和條件[1]。有學者認為,新的需求使文科在人才培養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發生改變:一是傳統文科培養的人才需求在不斷減少,二是新型人文社科人才的供給不足[2]。2016年,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地發揮作用。”為更好地打造“雙一流”高校模式,我國更是在深化改革、服務發展需求、開放合作中加快發展,努力建成一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標桿大學。
新文科主要特點有:
(1)多學科交叉的新形式。近年來,人文社會科學與科技強國戰略相匹配,與理學、工學新興領域進行交叉融合,成為新文科的重要內容之一[3]。在新文科建設中,應當突破傳統人文科學思維的限制,引入理工科的研究理念,強調邏輯思維、科學素養和實證能力。
(2)多維度需求的新道路。建設新文科要求我國將眼光放在培養人文社會科學復合型人才上。新文科的主要發展趨勢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是在文科人才培養模式上要與時俱進,追求卓越,改變課程設置以適應新時代發展局面。二是提高史料數字化與數據庫建設能力,以此豐富人文學者的研究手段。三是融入不同學科知識的創新詮釋和文化表達,構建多元化的知識發展體系。四是優秀歷史文化的產業帶動,如“非遺活化”[4]。
(3)多方面參與的新選擇。新文科背景下的研究要改變傳統單打獨斗式的研究模式,力求協同創新,多方面參與到其中。伴隨人文資料的開放化和數字化,人文知識的獲取、分析與展示方式的變化,均改變了人文學者在人文資料組織、檢索與利用的習慣[5]。
2 數字人文及其研究概況
近年來,國內數字人文的發展已然有了浪潮之勢,該概念主要產生于跨學科研究領域,通過數據挖掘、分析、可視化等數字技術手段,將人文史料進行更深層的探究并多維度的展示出來。目的是將數字技術與人文領域相結合,運用新技術提出、探索和解決人文社科領域的各種繁雜人文問題。
截至2022年7月,全球共成立了203個數字人文中心,分布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近90%分布在歐美。相比之下,亞洲的數字人文中心相對較少。
2014年成立的普林斯頓大學數字人文中心是圖書館牽頭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和學術單位。該中心致力于開展創新數字人文項目,培養新一代精通數字人文的學者,將數字人文方法和工具擴散到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周期中[6]。耶魯大學數字人文實驗室于2015年在耶魯斯特林圖書館成立,目的是協助學者將技術與量化方法應用于人文研究,并作為一個協作空間服務于“STEAM”。該實驗室是該校圖書館所提供的一項服務,它可以幫助學者們使用數字工具和方法來解決人文問題[7]。2017年英國劍橋大學成立劍橋數字人文(CDH),其是劍橋大學戰略進程的最新階段成果,由CRASSH(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主持,劍橋大學圖書館是其主要合作伙伴之一。CDH提供了一個動態框架來支持該領域最先進的研究,為數字人文探索和新想法交流提供創意空間[8]。
我國數字人文研究起步相對較晚。2011年,武漢大學成立國內首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2015年,北京大學發起“數字人文新動向——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數據庫”協作會議;201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打造“數字人文交流平臺”,以消除人文學者與數字技術學者的認知鴻溝;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數字人文與清史研究”主題論壇;2017年,南京大學舉辦“數字人文:大數據時代學術前沿與探索”學術研討會[9];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開設與數字人文相關的榮譽課程學位。另有“數字敦煌”、安陽師范學院的甲骨文研究、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數字化等項目,以及近三年連續舉辦中國數字人文年會,都與數字人文相關[10]。2021年,“數字人文與跨學科研究”研討會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辦,相關專家學者圍繞圖書館如何助力新文科建設開展數字人文與跨學科支撐、圖書館“數字人文實驗室”建設、數字人文教育與實踐等方面進行了跨界交流[11]。
新文科建設需要新技術交叉融合到人文社科研究中,而數字人文正是一種新興交叉學科,具有極強的跨學科、跨專業、跨院系特點,其將信息技術介入人文研究,促進學術創新,研究領域極為廣泛,需要人文社科學者和工程、圖書館、計算機等多學科研究者進行密切協作。將數字人文作為新文科建設的嘗試,契合了當前數字文化、數字內容和數字創意的產業需求。
3 圖書館在數字人文實踐的優勢與地位
“十四五”時期,圖情學科要放大視角關注多方領域,利用集資源于一體的優勢,在新文科“變革”的大背景下,通過技術將人文與計算機、文旅文化等融會貫通,在這場“人文&數字”的勢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1)圖書館員在數字人文研究項目中起到關鍵作用。專業學科館員在數字人文研究中,與人文學者是合作與伙伴關系,可以為研究者提供數字人文工具,負責組織學術交流、解決版權問題、收集整理數據等。他們要同時肩負牽線搭橋者、IT專家及研究人員等多重責任。
(2)圖書館文獻資源是參與數字人文的核心競爭力。圖書館需要將數字人文研究需要的資源整合起來,把不同的數字人文信息資源連接在一起,并對這些信息資源進行科學分類、妥善保存,同時置于一個易用平臺上。
(3)館舍空間與研究平臺是數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基礎。圖書館為數字人文研究者提供相應的實體空間。如:設立工作室,讓數字人文學者、師生分享項目、共享空間;提供開展各類人文研究的系統、工具即技術平臺。
(4)圖書館對數字人文理念的推廣、項目的宣傳起到推動作用。如:杜克大學圖書館針對人文科學專業的研究生、尚未開始撰寫論文或著作的人員,引領他們探索和分析成功的數字人文項目案例;北京大學圖書館通過會議、論壇、講座等多種形式推廣數字人文理念。
4 海南大學圖書館特色地方文獻數字人文實踐
海南大學是部省合建的“雙一流”建設高校,是海南省唯一一所綜合性大學,在海南與南海歷史文化研究方面有鮮明的特色,特別是在南海海洋方面,成立了多個與之相關的研究機構,如海南省歷史文化研究基地、南海區域研究中心、南海法律研究中心、海南省“更路簿”研究中心等。海南省對于海南與南海歷史文化有關的文獻收集、整理與綜合研究方面非常重視。其中,海南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我館)是相關文獻收集、整理與保存的重要機構,其在信息技術與情報分析方面也有優勢。2021年,海南大學成立由圖書館、人文傳播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等相關工作和教學人員組成的“海南與南海歷史文化數字人文研究團隊”。
4.1 南海更路簿數字人文研究案例
南海更路簿是海南漁民長期到南海進行捕撈作業并用海南方言總結出來的航海指導手冊,是海南人民長期經略南海的重要歷史證物。一本更路簿往往包括幾十到上百條更路,每條更路一般用“自<起點>去/下/上<訖點>用<針位><航程>收”等表述形式。因其習慣用“更”數來表示航程,故后人約定俗成統一其名為更路簿。現存更路簿原件極為有限,約有四五十本,散存在海南、廣東等地文獻收藏機構和民間。其中,我館收藏有近三十種更路簿的原件及影印件共計40余冊,是比較有特色的館藏資源。
海南大學是國內首個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的高校,也是承擔與更路簿研究相關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最多的機構,研究視角有人文歷史、版本比較、地理信息等。從2016年始,筆者所在科研團隊以圖書館收集整理的更路簿為研究對象,嘗試對南海更路簿進行數字化研究,后自發組建交叉學科研究團隊,成員除了圖書館負責特色文獻資源管理的相關人員外,還有來自于人文傳播學院、信息化服務中心、公共管理學院等單位的具有人文、地理、傳播、信息等學科背景的學者參與進來,從數字人文視角對南海更路簿進行綜合研究,取得明顯成效,部分創新觀點被采納,到目前為止,主要研究成果有:
(1)更路的(理論)計算航向角與記錄航向角偏差過大,或更路計算(理論)航速與記錄航速偏差過大,說明該更路存在不合理性,應查證相關資料進行修正。目前已發現的20余條航速或針位航向偏差極大的極度存疑更路均與島礁的錯誤解讀或對更路簿手稿的錯誤識讀有關[12-13],團隊基于數字人文視角提出的全新解讀得到周偉民、閻根齊、夏代云等專家及相關漁民的認可。
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吳淑茂簿南沙一更路“銀并去**用子午二更正南”,《南海天書》將該更路錄為“自銀鍋去五風用子午二更正南”[14],并解讀為從南沙群島的“安達礁”前往“五方礁”。按此解讀,該更路的計算航速高達31.29海里/更,超過參照航速1.5倍左右,極不合理。經數字人文分析,應是作者將該更路的訖點“牛厄”錯識為“午風”,并以為是漁民對“五風”抄寫筆誤,進而解讀為“五方礁”,經與作者溝通,得到確認。
(2)團隊基于數字人文方法發現《南海天書》所述“馮澤明更路簿”存疑,后經多方調查,確認其并不存在,是原作者團隊成員二次拍攝《陳澤明更路簿》并錯為“馮澤明”的結果,極時糾正一項重大失實文獻錯誤[15]。
(3)團隊在研究王詩桃、鄭慶能等更路簿時,對以前未曾解讀過的40余處新的近海島礁與港口地名(以海南島與廣東沿海為主)進行數字化分析,結合更路歷史文化進行解讀,符合當事老船長的認知。
(4)對林詩仍之父林樹林曾使用過的百年《癸亥年更流部》暹羅灣更路與地名進行數字人文分析,得出的結論高度可信,并與林詩仍在其父指導下于林家收藏的英文海圖上所做的中文標注基本一致[16]。繼續對其他東南亞更路與地名進行分析,發現其與鄭和下西洋的主干航線高度重合,對古代中國航海歷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
(5)曾有幾位研究更路簿的人文社科學者與筆者探討部分更路簿中出現的“鳥頭”位置問題。最開始,筆者對他們將其解讀為“鐵爐港”無從辨駁,因相關更路較少,而且是遠距離更路,從數字計算結果看不出明顯異常,但后來在另外一本新發現的更路簿找到兩條短距離相關更路,再行數字化分析,發現按“鐵爐港”解讀,短距離更路極度異常,而按“陵水角”解讀,則全部更路均正常,且與蘇承芬老船長的航行認知吻合[17]。
(6)團隊成員李彩霞教授用大量數值計算佐證更路簿外洋地名的研究[18],張軍軍則從數字化視角對更路簿的國際化傳播進行了探討[19],均能看到這些人文學者的創新性思維。
更路簿地方性語言特色非常明顯,以手稿傳抄及口耳相傳為主,傳承過程中難免會發生錯漏和偏差。如果不弄清楚這些問題,極有可能出現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問題,甚至可能產生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所以,以多學科交叉融合模式為背景,圖書館館藏資源為基礎,利用數字技術手段的優勢將歷史文物古籍所隱含的問題發現、挖掘并加以解決,這是非常值得繼續深入研究與探討的。
4.2 海南民間蘇州碼子數字人文研究
海南大學館藏的海南漁民林樹教曾用過的《癸亥年更流部》中有33處用一種特殊的數碼符號記錄更數,在問詢更路簿研究同行均不知其含義后,在館藏資源的有力支持下,通過數字技術查閱了文獻數據庫后,發現其就是脫胎于中國古代算籌、起源于蘇州的商業數字、后流傳全國各地的蘇州碼子。
從我館古籍文獻庫發現,海南瓊海漁民蘇德柳曾抄寫的3個小冊子中有蘇碼近100處;在晚清至民國時期,海南海口、樂東民間所立碑刻拓片中,至少有20余份800處以上的數值采用蘇州碼子記錄;在林樹教1949年入境新加坡的一份護照上和林家一份民國時期的家譜中也發現了蘇州碼子[20]。阿拉伯數字“0,1,2,...10”對應的蘇州碼為“〇,一/丨,二/〢,三/〣,〤,〥,〦,〧,〨,〩,十”。
(1)《癸亥年更流部》中的蘇州碼子記錄數據準確可信。《癸亥年更流部》用蘇碼記錄更數的31條更路,平均值為9.78海里/更,與該簿暹羅灣30余條更路航線的平均航速10.37海里/更非常接近,與海南漁民“每約10海里”的認知相符,略小于《南海“更路簿”數字化詮釋》3 000條左右更路的統計平均航速12.0海里/更,應與這些更路靠近陸岸,風力相對較小,航程相對較短等因素有關,是合理可信的。這些統計數據,經由數字技術手段考證,并經過實際情況分析,說明該簿用蘇碼記錄更數的這些更路整體上是可信的。另外,這31條用蘇碼記錄更數的更路的針位航向與計算航向平均偏差為3.9°,與有現代導航技術指導的《蘇承芬修正本》更路簿的平均值接近,說明該簿記錄的更路航向非常精準[21]。
(2)蘇德柳小冊子涉及蘇州碼子的計算方法科學、準確。海南大學周唐工作室收藏潭門鎮老船長蘇德柳(1909年生)抄寫的3本小冊子,均出現蘇州碼子,其中用蘇碼記錄“歸訣口訣”“歸除歌法”“除法口訣”等算例結果,并基本上以“銀一元七二分買米*斗*升”為例。筆者開始以為其是“1.72元”,但看到其中買米“六斗四升”的結果是“答曰每斗該艮一一分二厘五毛”,才知道應是“7.2錢”(7.2錢/6.4升=>1.125錢/升)。后進一步研究了解,清朝曾發生銀圓以“兩”還是以“元”為單位的爭論,幣制未能統一,多數造幣廠鑄造“七錢二分”銀圓,在宣統年代,只有“七錢二分”的“宣統元寶”銀圓[22]。
(3)海南金石中的蘇州碼子存在大量誤釋與訛傳。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并逐步替代蘇州碼子后,了解蘇州碼子及記數規則的民眾和學者越來越少,所以,在解讀相關符號時出現大量棄錄、誤釋等現象。如周文彰任主編、周偉民任執行主編的《海南碑碣匾銘額圖志》在實錄金石時,大量蘇州碼子被“□”代替,一方面應與核校者沒有弄清蘇碼符號含義有關,另一方面與碑文拓片不清晰關系也很大。僅海口地區17塊石碑共有蘇碼380余處,但其僅實錄108處,缺錄高達71.8%,缺漏情況比較嚴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南碑碣匾銘額圖志》的蘇碼文化傳播功效。
另外,美蘭區潘仙廟內《瀛洲社碑·置業》當中的兩處蘇州碼子解讀均有誤:將碑文“”分別解讀為“一百七十五斗”和“一百一十四升”,而實際應是“一斗七升五”和“二升四”,應該是相關人員并不十分清楚蘇州碼子的文化內涵所導致的。
另外,筆者還對海南樂東黎族地區出現的某碑上的蘇州碼子被海南史志網稱為“黎母數字”,湖南城步苗族地區出現的神秘數字符號被稱為“苗族數字”或稱其早于蘇州碼子,以及鄂西地區的“肉碼字”被稱為“鳥文”或“甲骨文殘片”等訛傳現象進行了數字人文辨析。
關于晚清民國海南民間碑刻蘇州碼子的誤釋與訛傳情況,筆者已有相關成果發表[23]。
4.3 海南其他歷史文化的數字人文研究
(1)僑批中的人文計算與誤讀問題。僑批,是指海外華僑通過海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的家書,同時兼具有匯款功能,是一種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在我館地方文獻庫存有一套海南省檔案館編寫的《僑批傳遞赤子情》,對解放前后的海南僑批進行了介紹,其中約有70份僑批中有用蘇碼表示的兌換數額,可惜編者未對其進行解讀。經初步計算分析,筆者認為至少有17余處表述與當時的歷史(主要有當期匯率變化、僑批專用郵戳特征、蘇碼符號用法等)嚴重不符。如某僑批被標注為“為1955年黃守第先生手收(黃德福付港幣陸拾元)”[24],根據批封上的兌換人民幣“(213 500元)”計算,港幣對人民幣比值為1:3 558,與當年當期匯率(1955年3月1日前是1:4 270,之后是1:0.472)存在不符情況。經綜合研判,該僑批應為1951年。后到海南省檔案館查看實物上的僑批郵戳,證實了推測的真實性。
(2)海南古村落數字人文保護與研究。中國許多傳統村落展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遺產,向世界自豪宣講的中國故事,有豐富的中華文化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25]。我館楊瑩老師,以館藏文獻為基礎,根據相關資料提供的信息,結合田野調查,從數字人文視角,提出海南傳統村落的現狀調查與數字化保護研究思路。這也意味著,基于圖書館特色館藏文獻資源的數字人文研究,能獲得更高的價值認同。
5 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意義
5.1 以數字人文創新之意拓“新天”
(1)人文史料可為數字人文之“本”。筆者認為,數字人文研究還是以人文社科內容為對象,與傳統人文社會研究相比,研究對象沒有變化,但研究方法和思路則更多引入自然科學常用的實證科學與邏輯思維,更易發現問題、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結論更加令人信服。筆者列舉的大量以圖書館所藏海南與南海歷史文獻為研究對象的數字人文實踐案例,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2)數字技術可為人文研究之“道”。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退休老教授周偉民、唐玲玲兩位教授在我館有一間工作室,他們收藏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研究成果豐碩,是《海南通史》《南海天書--海南漁民<更路簿>文化詮釋》《海南地方文獻叢書》等著作的主創者。筆者所在團隊近年來的研究對象均與周偉民教授研究的內容相關,只是研究視角與技術手段不同。文史資料在與數字技術相融合后,這些創新性成果的可證性與可視化,及研究效率都讓周教授稱贊,也讓周教授感受到信息技術與人文“碰撞”后迸發的魅力,從而影響到他對文獻資料的查找方式。
5.2 以圖書館藏資源之物鋪“前路”
近幾年,我館的數字人文研究對象,基本上都是基于圖書館特色文獻資源,其中主要包括南海更路簿、海南民間金石拓片、海南僑批、海南古村落等。不難看出,圖書館在文獻資源方面有其天然優勢。數字人文需要多學科背景的團隊協作,而圖書館學科服務館員的知識背景往往呈現多樣性,這對數字人文研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對于數字人文研究的信息平臺,從事信息素養教育的圖書館員更為了解和熟悉,也因數字圖書館建設的需要,圖書館信息技術人才也相對充足。而相對不足的是視野廣度,故往往需要與其他機構人員相互協作,以此進行更加深入的研討。
5.3 以新時代之浪潮明“方向”
(1)數字人文研究是綜合性研究型高校應該關注的重要發展領域。新文科建設和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需要,也因人文研究引入自然科學思維方式與實證研究方法,使得其相關結論也更容易讓人信服。如今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數字人文研究發展工作,而海南大學也在2021年啟動的協同創新中心的文化旅游下的歷史文化保護與利用傳承方向中,組成了數字人文研究團隊(培育)。
(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好、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要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南海更路簿、蘇州碼子與海南僑批都在見證著海南漁民們經略南海、嶺南文化在海南民間傳播、海南與東南亞國家的往來歷史。這些文物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和研究意義。因此,收藏、整理并好好加以研究并開發利用,對更好地傳承歷史、豐富社會文化很有必要。
6 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路徑
根據國家、地區發展需要,結合館藏特色文獻資源,選擇合適的研究方向與課題,為所在地區創造有價值有深度的文化研究。筆者曾傍聽到周偉民教授《南海天書》新書發布會上幾位專家的發言。其中,當時的中國海洋法學會會長、國際海洋法庭法官高之國先生介紹了南海更路簿在南海維權方面的歷史作用,而目前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希望有更多的學者,特別是理工科研究力量的加入。筆者了解到:南海更路簿是南海維權迫切需要的歷史文物,而退休后繼續在圖書館工作20多年的周教授收集了部分南海更路簿,而從數學教學轉向計算機應用的筆者是否可以試試更路簿的研究?由此,筆者從2016年起首次從自然科學研究轉向南海更路簿的數字化研究,后又陸續接觸到蘇州碼子和僑批檔案,又恰逢習近平總書記對傳承中華傳統歷史文化的重視,故漸入數字人文研究佳境,在海南與南海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傳統人文研究學者的多方認可。
用數字技術對待研究的特色文獻資源進行優化整理、深度挖掘、知識發現以及關聯規則探索等,力求將館藏資源利用到極致。對特色文獻進行數字化處理,除了文本數字化、圖片掃描等外,有時還要研究特定文獻的內涵,構建特定的數學模型,以能更加準確深入揭示相關文獻內在本質為目標。如更路簿是由更路組成,而更路一般含有四大要素,起點、訖點是用海南地方語言命名的島礁或港口或望山,針位與羅盤有關,以及用時間概念記錄航程的“更”等等,在分析這些核心要求的基礎上,構建系列計算模型,目的是為了深度揭示更路簿內涵,從而為發現《南海天書》等著作中的大量錯誤打下基礎。
多學科交叉融合形式的創新團隊。對于數字人文項目,應有熟悉研究對象內涵的人文學者,又要有計算機方面的專家,還要有支撐項目多維度研究的其他專家。如在更路簿數字人文研究中,筆者掌握計算機技術,另一位成員是圖書館南海文獻庫管理員,對更路簿文化背景非常熟悉,而且她是海南瓊海人,懂海南話,對更路俗稱地名的歷史背景非常熟悉。除此之外,團隊成員還有數據庫技術、軟件開發和地理信息技術方面的人員,這種多學科融合的團隊為項目順利開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數字技術讓人文史料“活”起來。傳統人文研究成果多以文集方式展示,不易閱讀,而利用“數字”的優勢,可以更加直觀地進行展示。如南海更路簿方面,夏代云對3種更路簿研究成果主要是專著,其內容基本上都是用文字表述,這就使得其他研究人員在參閱其研究成果時無法直觀地獲取想要的信息。而筆者對更路簿研究成果的呈現,除了必要的文本解讀外,還有大量基于天地圖或百度地圖的航線圖、航路圖和島礁位置示意圖。其中,涵蓋20冊更路簿近3 000條更路的兩幅同航路更路圖與同航線更路圖,被周偉民教授贊為“‘更路簿’研究歷史上最全面、準確、清晰的第三張‘更路圖’”。
跨學科交流活動豐富見聞。自然科學的學者要主動參加與研究對象相關的人文學術活動,而人文學者也要敢于參加信息技術方面的學術活動。由于國內數字人文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理論還不成熟,需要學者互相交流探索。筆者所在團隊近幾年多人連續帶本人參加更路簿高端論壇、瓊粵瓊浙文化對話會、中國數字人文年會等活動,筆者甚至參加了中國文學史編撰、臺灣跨領域古籍保護交流等活動,這些學術活動對數字人文項目研究是非常有幫助的。
7 結束語
在“十四五”時期,新文科有了更好的發展勢頭,數字人文所代表的多維度研究形式已成為關鍵手段。我館雖然還未完全打造出屬于自己的數字人文體系,但也對自身設立了更高的要求。以國內外諸多圖書館下設數字人文實驗室為標榜,我館應積極參與建設海南大學獨具特色的數字人文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