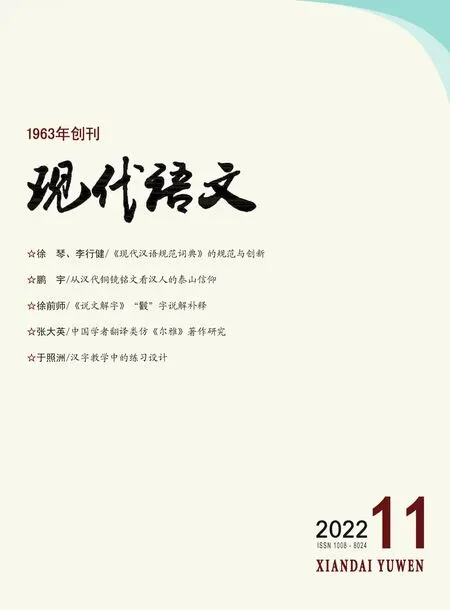語言視角下的俗字
薛 蓓
(常熟理工學院 師范學院,江蘇 蘇州 215500)
近些年來,隨著各類民間文獻的不斷發現,俗字研究逐漸興盛。前修時賢在俗字的輯錄、疑難俗字考證、俗字理論、字書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為俗字研究奠定了基礎。不過,關于俗字的定義,學界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俗字的判定尚未形成公認的標準。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歷時角度,分別考察傳統語文學時期有關俗字的記載、現代學者對俗字的觀點,以此為基礎,站在語言的立場上,探討俗字的本質,厘清俗字的內涵。
一、傳統語文學時期的俗字觀念
有學者指出:“由于漢語書面語使用的文字——漢字的特點,中國傳統語言研究主要是抓住漢字,分析它的形體,探求它的古代讀音和意義,形成了統稱‘小學’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也就是中國傳統的語文學。”[1](P2)總的來看,傳統語文學時期關于俗字的記載,大多是將某些字直接定性為“俗”,既未闡明其定性的理據,更未對俗字予以明確的界定,它主要是對用字現象的描寫。不過,仔細分析這些材料,卻可以窺探出這一時期是如何看待這類文字的。
(一)語言文字中的“俗”觀念
語言文獻中有關“俗”的最早記載,應出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從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觥,俗觵從光。”[2](P85)在《說文解字》中,常以“俗某從某/從某”“俗某從某某聲”“俗從某”的形式,指出該字的某種寫法為“俗”。如:“髆也從肉,象形,俗肩從戶。”“躳,俗從弓身。”共15 例。這說明至遲到東漢時期,人們已經產生了與文字有關的“俗”觀念。
此后,歷代字書中都有類似的記載。《正字通》卷三:“宂,俗從幾作宂,或作冗,并非。”[3](P667)《廣韻·上聲》:“柁,正舟木也。俗從?,余同。舵,上同。”[4](P175)《字匯》首卷:“凡俗作凢……姦俗作奸。”[5](P39)這些字書,均明確標注了某字或某字的某種寫法為“俗”,對單個字形進行定性。不過,它們都未解釋將這些字定性為“俗”的依據是什么。
后世有些學者也注意到“俗”或“俗字”問題,并將其運用到文獻校勘中。如明清之際的學者王夫之《詩經稗疏·詩經考異》云:“‘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月令》鄭注:‘觥’作‘觵’,‘萬壽’作‘受福’。許慎:‘觵,俗從光。’經典不應用俗字。‘我姑酌彼兕觥’,亦當作‘觵’。”[6](P243)王夫之認為,在經典文獻中,是不可能使用“俗”字形的,因此,《詩經·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中的“觥”本應作“觵”。
(二)關于“俗字”的相關記述及觀念
關于俗字的最早記載,似應出自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如《書證》云:“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為單父宰,即虙羲之后,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7](P447)作者認為,虙、宓二字因形近而傳寫訛誤;“誤以虙為宓”“俗字亦為宓”,則說明當時“宓”作為俗字已經十分流行。在《顏氏家訓》中,類似的材料還有一些,可以反映出顏之推及當時學者對俗字的認識。我們將這些材料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關于特殊字詞考證的,此類關于“俗”的記載和分析,均與方言有關。其中,有些是不同方言區域使用不同的方言詞匯來表達同一事物的,這些條目中的“俗”主要指的是方言詞語不同;有些是方言中雖然有這一詞語,卻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字形,故另造新字的;有些則是由于方言語音不同而使用不同字形的。第二類是關于典籍訛誤考證的,此類關于“俗”的記載和分析,如“俗寫”“俗本”“俗儒”“俗學”“俗傳”“俗之學士”等,主要是與書寫者的文化水平有關。其中,有的是由于書寫者學問不精而造成字形訛誤的;有的是由于書寫者不懂假借等規則而誤解典籍的;還有的是因“俗儒”“俗學”主觀臆斷而隨意解釋典籍、增加文字的。
從中可以看出,《顏氏家訓》中的“俗”或“俗字”具有兩個要素:一是受到方言影響,如方言語音、方言詞語等;二是文字的書寫者文化水平不高。對于上述現象,顏之推的態度很明確,認為是“鄙俗”的,“此臆說也”。同時,作者也承認這些現象已成為文字使用的現實:“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7](P516)這段話說明當時俗字的使用已經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以致于作者擔心使用正字則無法正常交流。面對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顏之推主張采取“通變”的策略,即根據文字的使用語境來選擇字體、字形。在文章著述這種權威性、規范性語境中,要使用正字;而在官曹文書、世間尺牘這些與世俗生活密切聯系的語境中,則可以使用俗字。
在《顏氏家訓》之后,也有一些古代文獻涉及到“俗字”的論述。比如,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云:“矛矟:矟,山卓切。《埤蒼》:‘矟,長一丈八尺也。’經文有作‘梢’,所交反,(木)名也。或作‘槊’,北人俗字也……或作‘銏’,江南俗字也。”[8](P6)這里的“俗字”,應是指同一詞語因地域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字形。唐代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云:“只如田夫民為農,百念為憂,更生為甦,兩隻為雙,神蟲為蠶,明王為聖,不見為覔,美色為豔,囗王為國,文字為學。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9](P23)這里所說的“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則反映出作者對這類字體的鄙夷態度。
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風土門·俗字》云:“廣西俗字甚多。如,音矮,言矮則不長也。,音穩,言大坐則穩也。奀,音倦,言瘦弱也……”[10](P162)這里的“俗字”,是指為記錄廣西地區方言詞而造的字。清代蒲松齡《日用俗字·自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匯》,編為此書。”[11](P1)蒲松齡認為,“日用俗字”即記錄日常生活的字,主要包括兩類:一是為了滿足“苦不能書其名”的現實需求,而造出記錄特有方言詞語的字;二是“點畫率皆杜撰”,這是將所謂“正字”字形改造后的字。
(三)關于俗字的分類
第一次對俗字進行系統分類的,應是唐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并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12](P9-11)按顏氏所說,文字應按照使用場合區分為俗、通、正三類:在籍帳、文案、券契、藥方等日常生活場合,可以使用俗字;在表奏、箋啟、尺牘、判狀等應用性的公文中,應使用通字;在著述、文章、對策、碑碣這類典雅嚴肅的場合,則宜使用正字。
按照顏元孫的分類原則,同一個字,應該具有三種不同的形體,才能滿足不同使用場合的需要。實際上,在《干祿字書》中,有些字確實是三體皆有,如:皀、皃、貌,上俗中通下正;有些字僅有通、正,無俗,如:貍、貍,上通下正;有些字僅有正、俗,無通,如:聡、聦、聰,上、中通,下正;還有些字僅有正體,如:棲棲,并正。雖然俗、通、正對應三種使用場合,但現實中并沒有三套字形。正字既可以在典雅、嚴肅的場合使用,也可以在“通”或“俗”的場合使用;不過,即使在“通”或“俗”的場合使用,這類文字的性質仍然是正字。如“棲”“棲”,無論在哪種場合使用,都屬于正字。當籍帳、文案、券契、藥方等場合在記錄某詞時,由于某種原因,采用了與正字不同的字形,這個字形就被認為是俗字;如果在籍帳、文案、券契、藥方等文獻中,未使用與正字不同的字形,那么這個字就沒有俗字。如“貍”字,并不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中沒有這個詞,而是上述文獻中在記錄“貍”時,就是采用了正字的寫法。
由此可見,在俗、通、正三體文字中,正字是文字的典范,認可度最高,可以使用在“俗”“通”的語境中;而“俗”“通”則僅能在各自的場合中使用。即使一個字俗、通、正三體俱全,正字也更具權威性。顏元孫認為,俗字是在“非涉雅言”的場合中所使用的文字,也承認此類俗字的存在,但并不鼓勵使用俗字,如果能夠改用正體,那就更好了。對通字的態度和俗字一樣,只是承認,并不鼓勵,認為到了真正寫文章或者參加正式考試時,還是要使用正體的。
總之,在傳統語文學時期,很多研究者均認為,俗字主要是受方言影響或因使用者文化水平不高而產生的,大多是在非嚴肅、非典雅的場合使用。同時,這一時期主要是對俗字使用現象的描述,并未對俗字予以明確的界定。
二、當代學者對俗字的界定
到了現當代時期,隨著各類民間文獻的不斷發現,俗字研究逐漸興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關于俗字的界定亦成為研究的熱點,它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側重于俗字內涵的說明;二是側重于俗字外延的判定;三是從使用情況來描述俗字。
(一)側重于俗字內涵的說明
這種觀點認為,俗字是民間流行的,它是與正字相對立的文字。代表性觀點主要有:
馬敘倫:此蓋由其字不見于《史籀》《倉頡》《凡將》《訓纂》及壁中書而世俗用之,故不得不削,別之曰俗字。[13](P27)
蔣禮鴻:俗字者,就是不合六書條例的(這是以前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實際上俗字中也有很多是依據六書原則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認為不合法的、不合規范的文字。應該注意的是,是“正字”的規范既立,俗字的界限才能確定。[14]
郭在貽、張涌泉:所謂俗字,是相對于正字而言的,正字是得到官方認可的字體,俗字則是指在民間流行的通俗字體。[15](P235)
張涌泉:漢字史上各個歷史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間的通俗字體稱為俗字。[16](P6)
蔣冀騁、吳福祥:俗字是相對正字而言的。……俗字指那些不見于《說文》,不能施于高文大典,民間所習用的字。[17](P25)
蔡忠霖:寫法有別于官方制定之正字,乃經約定俗成而通行于當時社會,且易隨時、地不同而遞變之簡便字體。[18](P55)
鄭賢章: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出現在民間,多數具有簡易性特點,相對正體而言的或者新造的本無正體的字體。[19](P101)
這類觀點在當今俗字研究中影響最大,接受度最高。它主要是從俗字的內涵出發,強調俗字具有兩個要素:一是流行于民間,二是與正字相對。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正字”和“民間”這兩個要素,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把握。
首先是關于“正字”的辨析。在上述觀點中,都提到了“正字”或“正體”,如“正字的規范”“相對于正字而言”“官方制定之正字”“本無正體”等。馬敘倫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正字,但“《史籀》《倉頡》《凡將》《訓纂》及壁中書”,實際上也是頗具代表性的正字文獻。蔣禮鴻認為:“‘正字’的規范既立,俗字的界限才能確定。”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與俗字相對立的正字呢?在中國歷史上,官僚士大夫階層對書寫規范有一定要求。《漢書·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20](P1720-1721)《唐會要》卷七十七云:“所習經業,務須精熟;楷書字體,皆得正樣。”[21](P1402)可見,無論是在學校教育方面,還是在官吏考核方面,書寫(包括字體)都非常重要。因此,從理論上說,漢字應該有一套正字系統。實際上,歷代并沒有官方所明文規定的正字,有些字書雖然標明了正、俗,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并不屬于官方字書;有些工具書雖然是官方頒布的,但對于文字的俗體、異體和正體的劃分標準并不一致。如《廣韻》《集韻》和《禮部韻略》,雖然同是宋代官方頒布的,但由于編纂目的和使用范圍不同,它們所記錄的俗字和異體字亦有所差異。因此,將“正字”作為“俗字”的對立面,雖然從理論上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認可,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找到可以對照的歷代正字系統。
其次是關于“民間”的辨析。在上述觀點中,還都提到了民間,如“世俗用之”“平民中日常使用”“在民間流行”“流行于民間”“民間所習用”“通行于當時社會”“出現在民間”等。在研究俗字時,學界也不約而同地選擇民間文獻作為主要材料,如契約文書、明清小說、戲曲等。在通常觀念中,“民間”總是與“官方”相對應的,就此而言,俗字在民間使用,也就意味著官方不用。不過,在部分官方文獻中,卻存在相當數量的俗字。楊小平指出:“流行于民間,與正字相對,已經成為判斷俗字的主要標準。但是從清代手寫文獻來看,俗字被官方文書廣泛使用,郡縣官員的判案批詞中出現有不少俗字,甚至官方來往的公文中也有不少俗字。由此可見,俗字并非不能應用于大雅之堂,也不局限于平民百姓使用,也流行于官方。”[22](P29)因此,使用俗字的“民間”,并不是“官方—民間”這組對應概念中的“民間”,而是應該有其他指向的。
(二)側重于俗字外延的判定
這種觀點認為,俗字是異體字的一種。代表性觀點主要有:
黃征:漢語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流行于各社會階層的不規范的異體字。[23](P18)
蔡忠霖:我們也可以說一凡一字因各種因素而衍生出不同于正字的其他寫法,都可稱之為異體字。而俗字只是異體字構成因素之一,是異體字中一部分,雖然它也屬于一種異體字,但并不等同于異體字。更明確的說,俗字是以“便利”為取向,且通行于社會的一種異體字。[18](P57)
張涌泉:凡是區別于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俗字可以是簡化字,也可以是繁化字,可以是后起字,也可以是古體字。[24](P6)
這種觀點均從漢字形體出發,認為俗字和異體字有重疊部分,只是對重疊范圍的程度看法不一。黃征認為,俗字屬于異體字中的一類,是“不規范的異體字”。蔡忠霖認為,異體字包括俗字、通假字、繁簡字、古今字、形誤字等,俗字只是異體字中以“便利”為取向的一種字。不過,“不規范”和“便利”這兩個標準,在實際操作中,也比較難以把握。根據相關研究,有些俗字的字形比正字更加復雜,俗字并不都是便利的。張涌泉則認為,俗字和異體字的范圍基本是等同的,俗字包括“簡化字”“繁化字”“后起字”“古體字”等。這種對俗字外延的界定最為清晰,可操作性最強;在整理俗字時,很多研究者也將其作為劃分俗字的主要標準。
(三)從使用情況來描述俗字
這種觀點主要是從文字使用者的角度入手來界定俗字,代表性的觀點是:
陳五云:俗文字是正字系統的補充,是正字系統由于時代的不同形成的歷時變體,是正字系統由于地域因素造成的方言變體,是正字系統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變體。[25]
曾良:一是“俗字”實際上是與“正字”相對待出現的概念。二是俗字必須被一定的人群默認使用(約定俗成)。這個群體可大可小,大可以是一個國家,小可以是某個地區;既可以是民間流行,也不排斥官員也寫俗字。[26](P1-2)
這類觀點一方面和第一類觀點一樣,指出俗字與正字相對;另一方面,則指出俗字有特定的使用場合。如陳五云指出,俗字是正字系統由于時代、方言、文化不同而產生的變體,有其特定的使用時間、地域和文化背景。曾良則認為,俗字必須被一定的人群默認使用。關于此類觀點中所提到的地域、文化等因素,張涌泉在《漢語俗字研究》中也指出:“俗文字在其流延之初,總是在較小的范圍內被使用,因而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程度的區域特征”[24](P135-136),并引《顏氏家訓·書證》“吳人呼紺為禁”為例,說明因方言語音而產生了字形變換。張涌泉還指出:“除地區性的俗字以外,各地還流行一些行業性或者團體性的俗字”[24](P138)。因此,從使用的角度來看,俗字還具有時代性、地域性和社會文化屬性。
從現當代學者對“俗字”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從“不規范的字”,到俗字與異體字的區別及聯系,再到俗字的使用,這一術語與“正字”“民間”“規范”“異體”“方言”“文化”“時代”“地域”等眾多概念都產生了聯系。那么,俗字為什么能夠將這些不同層面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呢?
三、站在語言的立場看俗字
李榮指出:“文字的基本作用是記錄語言,其他作用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27](P1)張永言也認為,文字是詞的書寫形式[28]。站在語言的立場來看,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俗字”應當是與其記錄的語言形式以及該語言的使用者有關。漢語是一種有著復雜層級結構的、動態的語言,在漢語內部存在很多變體。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漢語依次經歷了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古漢語、現代漢語等階段。從共時的角度來看,地域、社會文化的差異也造成了漢語的諸種變化。就地域差異的影響而言,不同區域的漢語往往會存在很大的差別,這種語言變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語中的眾多方言。就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言,主要是指說話人由于具備相同的社會屬性而形成一個個群體,如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社會地位等,相關成員會在群體內部使用他們所熟悉的語言文字進行交際,從而形成各種語言變體。
在漢語的眾多語言變體中,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存在——雅言。所謂“雅言”,是指在正式場合中所使用的高度規范的語言形式,它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從先秦時期開始,中國歷代都將雅言作為全社會的標準語言。它一般是以某地方言為基礎,經過不斷規范而形成的,雖然不同時代的基礎方言會有所不同,但一直都是語言規范的代表,屬于語言變體中的高變體。雅言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大量的經典文獻,主要是在典雅嚴肅的場合使用,是漢語語言規范和典雅的范例,必須接受過系統的教育才能掌握。因此,雅言的使用者一般都是社會的精英分子。記錄雅言的漢字也相應地成為具有雅正特點的漢字,成為漢字規范的代表。相對而言,漢語的其他變體則被排斥在典雅場合之外,主要應用于各種非正式場合,屬于語言變體中的低變體,其使用者也大多沒有接受過精英教育。在記錄這類低變體時,書寫者可能會受到時代、地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使用一些與記錄雅言的正字不同的字形,由于這類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形式是非雅言的,使用場合是非嚴肅、非典雅的,因此,使用雅言的士大夫就將其稱為“俗字”。
從語言的角度來看,俗字主要包括兩個層次:一是語言層面上的俗字;二是文字層面上的俗字。
就語言層面上的俗字而言,在漢語低變體中存在一些雅言所沒有的詞語,為了記錄這類詞語,書寫者往往會采取新造字形這一方法。當漢語低變體中某詞的語音與雅言不同時,書寫者通常會使用更能反映實際語音的字形,如《顏氏家訓》中所提到的“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字”[7](P491);或者是根據實際語音對正字字形進行改造,如《顏氏家訓》中所提到的“呼‘紺’為‘禁’,故以糸傍作‘禁’代‘紺’字”[7](P491)。漢語低變體的使用者,有時還會為了突出所在社會群體的某種文化特質,或表達某些特別的意義,而對字形進行改造。如清代藍浦《景德鎮陶錄》卷四“陶務方略”條:“景德鎮陶業,俗呼貨料,操土音,登寫器物花式,字多俗省。”[29](P88)這些都是因為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的俗字。
就文字層面上的俗字而言,漢語低變體的使用者,大多不知曉漢字的造字理據,書寫時只要能滿足基本的交際需要就可以,并不具有文字規范的觀念。同時,由于漢語低變體主要使用于非正式的場合,書寫者在記錄這類語言時,主觀上有時也會降低對文字規范性的要求。因此,記錄漢語低變體的文字,常常會出現一些不合規范的情況,如任意改動構字部件,隨意類化、符號化,借用同音字,新造字形等。從產生原因上看,這類字雖然屬于別字、誤字等不規范的用字現象,但有些字形已經被大眾所普遍接受,并在社會群體中代代相傳,于是就成為文字層面上的俗字。
如上所述,由于俗字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在論及俗字時,需要注意以下情況:
第一,雅言作為官方的教育工具,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記錄雅言的正字,也應是全體社會成員需要學習的對象。俗字只是作為漢語低變體中的特殊情況而使用,因此,大多數民間文獻仍以正字居多。李榮指出,有的人有錯誤的假定,以為小說一定是滿篇的俗字、簡筆字。就我們考察的小說而言,用字跟平常書籍沒有多大差別。其中大多數字符合一般的習慣[27](P15)。楊小平也指出,清代手寫文獻俗字雖然數量較多,但是俗字在全部文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正字使用仍然較多[22](P47)。
第二,從語言的角度來看,雅言和漢語其他語言變體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但在實際應用中,使用者會根據交際的需要而采用不同的語言變體。雅言的使用者在某些交際場合也會用方言,寫俗字,如《顏氏家訓·書證》所言:“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7](P516)
第三,在語言的歷時發展中,雅言和其他變體的界限也處在動態的變化中。雅言可以吸收來自不同語言變體中的成分,雅言中的成分也可以進入其他語言變體。與此相應,正字和俗字也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俗字可能會進入雅言文字系統而被正字體系所吸收,歷史上的正字也可能會轉變為俗字。
第四,漢語低變體的使用者,大多沒有明確的某字應該用哪種字形的觀念,只是在臨文時直接選取了某種字形。這一字形可能是簡化字,也可能是繁化字;可能是后起字,也可能是古體字。很難說書寫者是因為這個字形具有簡體、繁體或者時代的屬性而特意選擇了它。
第五,某類文獻中是否使用俗字,主要是與這類文獻所記錄的交際語境有關。各種州縣檔案、官府文書等,從性質上說雖然是屬于官方文獻,但這類文獻直接反映民間百態、基層情況、衙門運作等,它們所使用的語境與漢語低變體關系密切,因此,這類文獻中會使用大量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