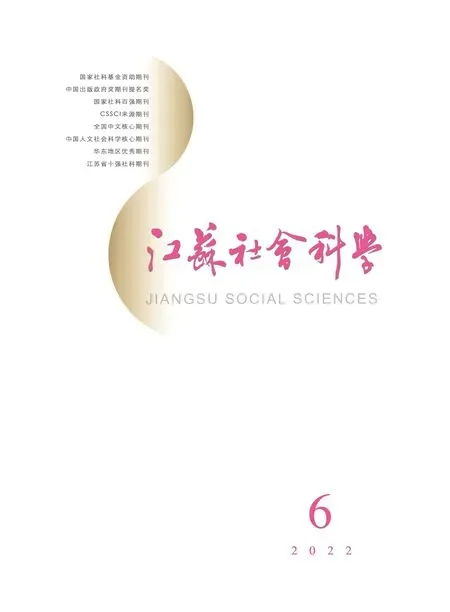“對話地圖”:當經典《浮士德》與中國網絡文學共謀“穿越”
張春梅
內容提要 作為中國網絡文學最為普遍的敘事策略,“穿越”不僅在類型和想象層面與當代文學的文本特征相聯系,也反映出文本主體、書寫者、讀者、文體的文化變遷。經典《浮士德》同樣采取“穿越”的方式重建時空并實現人生價值。歌德時代穿越文與當下網絡文學書寫在主體“穿越者”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多元化的現實情境以及文體之間的通約等方面提供了將二者平行比較的可能。以“穿越”為抓手,討論《浮士德》與中國網絡文學跨時空書寫所呈現的文本周邊問題、網絡文學的諸種特征、寫作者和讀者的關系位移及其主體精神困境,能夠為認知世界、書寫主體和文學場域提供有力借鑒,“對話地圖”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得以建立。這提供了從一種現實位置看經典的新視角和認識網絡文學的新視點,將會給關涉不同時期的文學和書寫提供別樣的理解和參考視角。
一、引言
“浮士德”從德國民間故事中的魔術師、星相家、自然科學家,到歌德筆下的著名人物,再到二百年后成為世界性的經典形象,其流變史和精神史構成了一個豐富的、不斷有新見涌出的文化表征系統。中國關于浮士德的認知概始于嚴復批駁梁啟超的一段話:“德文豪葛爾第Goethe戲曲中有鮑斯特Dr Fawst者,無學不窺,最后學符咒神秘術,一夜招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猙獰,六種震動,問欲何為,鮑大恐屈伏,然而無術退之。嗟乎!任公既已筆端攪動社會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于救亡本旨又何濟耶?”[1]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46頁。這個“開端”很有意思。我們看到,嚴復此語重在批駁梁啟超,但提到了歌德的《浮士德》,尤其是引出了“地球神”,也被譯為“地仙”[1]歌德:《浮士德》,樊修章譯,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頁。,浮士德和“地仙”的聯系與緊跟著和魔鬼達成的“契約”,在動機和行為意義上共同促成作品的重頭戲:重活一回。這樣的愿景在今天的閱讀地圖中并不陌生,并已經形成一個極具概括力和影響力的詞匯——穿越[2]現有研究在追溯穿越緣起時,常將1889年馬克·吐溫的《康州美國佬在亞瑟王朝》視為穿越小說鼻祖,但這篇小說與網絡文學興起后的“穿越文”在創作主體、寫作手段、傳播方式等方面均有質的差異。穿越文的引流之作是2004年金子的《夢回大清》,后有《鸞,我的前世今生》《步步驚心》《綰青絲》《醉玲瓏》《回到明朝當王爺》《九重紫》《知否》《極品家丁》《嫡女重生記》等諸多架空文本集束出現,打造出網絡文學的重要類型——穿越文。而形成穿越文的重點在于其“梗”:主人公離開當下生活環境獲得另一世界體驗的橋段。“魂穿”是最主要的形式,“身穿”較少,“快穿”近幾年較為流行。。
中國網絡文學(以下簡稱“網絡文學”)能有當下縱橫多媒介的態勢,離不開“穿越”這樣一個集行為與奇思異想于一身的話語表述。眾多穿越文集束之下,穿越不僅形成穿越文類,又因在不同文類常被兼用而成為具有大眾性的“梗”。本文將浮士德與網絡文學以穿越為中介進行比較,主要基于以下考慮。其一,如何借助“穿越”實現“新我”或“另一種生活”,是二者的共同出發點。在網絡文學初期,關于穿越的想象是主體離開某地進入另一時空歷險,“新鮮體驗”和“意外性”是主要的動機和敘述目的,由現代到古代,或由古代到未來,這些基本上是建立于時間線變化而帶來的主體對不同生活的體驗。當下的穿越,更重視主體以獨有的意志和自覺構架自己的生活空間和社會關系。在“圓滿人生”這個目標上,浮士德與網絡文學跨時空地達成一致。其二,同一主體以“重返自己的過去”指示出“身體”的重要性。大多數穿越者以獲得完美的身體展示出對現實身體的不滿,以回到青蔥時代作為“新生”的起點。主體、身體、青春,連綴起當代人鮮明的穿越夢想。這樣的夢想不僅為今天的大眾所有,昔日的浮士德早已將這種“重活”以抵押靈魂的方式實踐了一把,并因此開啟了“新人”的生活世界。其三,二者同處精英/大眾、傳統/當代、純文學/市場文化等多重元素雜糅的語境之中。《浮士德》被譽為“近代人的圣經”,喻示此文本所處時代的過渡性質和多重折疊。當我們給予《浮士德》極高評價的時候,不能忘記歌德的寫作已經開始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這是我們說到的“折疊”的一重性質。另一重則在于宗教開始被賦予新的世俗意義,主體意志雖沒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決絕,卻在世俗性上做出了莊重的嘗試。中國網絡文學,同樣在一個伴隨著與傳統文學復雜關聯的雜融時期生發。精英/大眾、正典/流行的爭端一直未決,傳統文化卻成為這一網絡媒體選擇的最強有力的資源支撐。網絡文學如何繼承和重構傳統文化成為不可越過的當代文化命題。
“對話地圖”[3]借用英國學者沃倫·薩克的理論。“對話地圖”主要指在網上進行超大規模對話時的一個界面。它是一種適合于新聞組的瀏覽器,可以分析內容以及信息之間的關系。它可以進行三種不同類型的圖形化分析:一是社會化網絡,二是討論主題,三是語義網絡。這種軟件可以使我們看到事先沒有注意到的互動模式或交流地點。參見戴維·岡特利特:《網絡研究:數字化時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蘭等譯,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3頁。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得以建立。網絡文學的諸種特征,它所反映出的主體精神困境、寫作者和讀者的關系位移,這些必然觸碰的研究問題,與《浮士德》隔空相向,在“穿越”這個維度上,提供了認知世界、主體和文學場域的有力借鑒,人的精神史和社會史貫穿其中。
二、社會化網絡之困:“穿越”行為與“現實”指向
福柯在論述人與空間的關系時指出,“我們所生活的空間,在我們之外吸引我們的空間,恰好在其中對我們的生命、時間和歷史進行腐蝕的空間,腐蝕我們和使我們生出皺紋的這個空間,其本身也是一個異質的空間”[4]米歇爾·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這樣一個另類的異質環境,滋生出“奇特”的存在。關系集合內的位置挪移,會將代表不同文化的空間進行勾連,這種勾連是以人物的行動和運動方向為主要紐帶和聯結點的。
穿越小說的主人公往往在現實世界有不能解決或難以面對的困境,或者純粹為穿越而穿越(一種單純對穿越的想象和向往,以之為浪漫的“奇遇”),因一場“意外”而被命運送到了一個陌生的空間,從而獲得“新生”。由于“新生”才是作者敘述的重點,也是讀者關注所在,“獵奇”成為對乏味或令人痛恨或令人感到不足之現狀的一種補充。現狀被描寫的比例則少之又少,通常只是幾句簡短的鋪墊,然后直接進入一個“奇妙”而超現實的世界。如關心則亂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以下簡稱《知否》),主人公穿越之前是這樣的:“法院的工作和港劇里完全是兩碼事,姚依依在庭上不需要說話,不要判斷,除了不斷記錄列證,她幾乎可以算是隱形人,不過最后判決書上倒會有她的名字,經手事務中最多的就是分家產和爭遺產,這讓姚依依年輕的心靈飽經滄桑。”[1]關心則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931329&chapterid=2。很明顯,姚依依遇到的現實困境在于人生之“平庸”,一場意外的泥石流成就了她的另一種人生。更多穿越者則備受現世的強烈打擊:“范慎很困難地撐著上眼皮,看著指頭算自己這輩子做過些什么有意義的事情,結果右手五根瘦成筷子一樣的指頭還沒有數完,他就嘆了一口氣,很傷心地放棄了這個工作。……他得了某種怪病,重癥肌無力,就是特別適合言情小說男主角的那種病。據說沒得醫,將來嗝屁的那天什么都動不了,只有眼淚可以流下來。”[2]貓膩:《慶余年·楔子:一塊黑布》,https://www.biqukan.com/2_2760/1110381.html。這種來自生命不可控之“困難”,是世俗人生的痛苦之一。不過,主人公穿越之后的困境和穿越之前形成鮮明反差,醒目的容顏、健康的身體、卓越的智慧匹配優越的家世,為穿越后的他們提供了“自己的舞臺”。反過來看,這恰恰是穿越者所處現實的缺乏之處。
穿越重生,與上述“純意外”或擺脫現世痛苦的穿越有所不同。重生這一類型,同樣是改變時空,尤其是改變時間線索,但其著眼點在于主體內在的“不甘心”。這與純粹的穿越文不同。純穿越的主體,往往是借助另一個身體另一個時空展開“全新”的人生,攜帶而去的是現世倚賴的生存法則和現代意識,這些金手指保證其能夠在陌生世界建立起獨特性。而重生的法寶在于“先知先覺”,因為許多事情都經歷過一番,則重生者必然會重新審視曾經發生的故事,他/她對自身、社會關系都會有反思,行為指向也就具有了雙重屬性和對話性質。可以說,重生者(包括穿越者)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這種雙重生活的在場。
浮士德也不甘心,但文本展示的卻是另一番景觀。假如網絡文學多因“意外”“困境”和強烈的不甘意志而“穿”,浮士德卻有明確動機,是為“浮士德難題”。不像網絡文學視“前史”為點綴,歌德用了大量筆墨描述“穿越”前的困境。浮士德之“難”源于對自己“無意義”人生的“發現”:“唉!我還枯守這個牢籠?該詛咒的陰郁的墻洞,/透過彩繪玻璃的天光/在這里也顯得暗淡無光!/這里塞滿大堆的書本,/被蠹魚蛀咬,被灰塵籠罩,/一直堆到高高的屋頂,/處處插著熏黃的紙條;/瓶兒罐兒到處亂擺,/各種器械塞得滿滿,祖傳的家具也堆在里面——/這是你的世界!也算個世界!”[3]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頁。知識變成一屋無用的紙堆,金錢、聲名、激情,這些“生氣”統統與其無關,苦讀一生的“博士”只能在人群之外煢煢孑立,猶如牢籠中的困獸。門外復活節的鐘聲仿佛嘲笑著他的“被棄”,黑暗的空間造成無窮無盡的威壓。此種情境,是魔鬼摩菲斯特和上帝打賭的前提。老學究浮士德希望“地仙”[4]樊修章本將“地仙”譯作“鬼神”,而錢春綺本譯為“精靈”,本文選擇樊譯本。理由是浮士德所處時代正是反抗宗教的改革時期,人們既懷疑上帝,又渴望上帝,“鬼神”一說所帶有的強烈神秘主義味道,切合浮士德的身份——神秘主義者和巫士。能助己脫困,“我這才對法術產生了迷戀,看借鬼神的口訣、威風/能否把一些奧秘揭明”。這種借“神秘”力量拯救自身的想法,民間力量和宗教的深刻浸潤是一個原因,但根本卻在浮士德意“重返俗世”以探求“人活著的意義和如何活著”,這是新時代的主題。對于浮士德書齋沉思生活的痛苦,路德維希一語破的:他(歌德)抓住了德國人所缺乏的東西:內心的充實的安全感[1]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楊成緒、潘琪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頁,第73頁。。摩菲斯特正是看到“遠近的一切,什么也不能/滿足他那無限的野心勃勃”[2]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頁,第86頁,第145頁。,才會對與上帝之間的豪賭信心滿滿。浮士德如是說:“我先要詛咒傲慢的思想,/它緊緊束縛我們的精神,/我再要詛咒迷人的假象,/它緊緊脅迫我們的官能!”[3]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頁,第86頁,第145頁。這是屬于上帝/魔鬼、理性/快樂沖動等二項式之間的悖論,孰勝孰負,或可在不打破天平情況下安然相處,昭示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對,這就是浮士德,德國人靈魂的最大象征,一個永遠得不到寧靜靈魂的活生生的證明”[4]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楊成緒、潘琪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頁,第73頁。。浮士德的“賭約”成就了他“重生”的機會,使他有可能以反思的形式重新實踐“我”的意志。有意思的是,青春和愛情是魔鬼和浮士德共同的選擇。盡管經歷了愛情的悲劇,但青春的身體卻無疑是浮士德與穿越者們共同的歷險可能。
相比之下,網絡文學中的穿越少了浮士德所肩負的民族、信仰、意義的執著,多是為引出“新世界”和“新我”,穿越成為一種工具,一種與眾不同的投入“新世界”的方式。這種穿越在敘事功能上更多是為了“求異”,不是阿Q式幻想與現實間的自得自欺,而是勇往直前的“投入”,意在開展一場讀者和寫手共同進入的奇妙探險之旅。還以《知否》為例,作者對穿越者的前意識有這么幾句簡短描述,“她只是覺得自己的人生太一板一眼了,……一輩子都在一個按部就班的環境中生活,日子固然舒服,可卻少了必要的人生閱歷,她希望能去不同的地方看看走走,了解和自己生活的不同世界的人們”[5]關心則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931329&chapterid=2。。“不同”,是幾句話中重復率最高的字眼,展現出蕓蕓眾生無數姚依依們的心中所愿。《嫡女重生記》是重生文的典型。女主韓若熙是國公府姑娘、尚書兒媳,可在她還活著的時候就已被宣布為“一個死人”,于她而言,“天下之大,已經沒有她的容身之地了”[6]六月皓雪:《嫡女重生記》,https://www.bishen8.com/page/5786/2.html。。重生,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與此同時,摩菲斯特也用異托邦的鑰匙打開了重生的大門。
三、如何“重生”:穿越者與“新世界”
從生活方式這個角度看,浮士德的“穿越”更像這幾年開始興起的“快穿流”,一個主角接受不同任務到不同空間去體驗且努力完成工作。只是,浮士德本人強大的精神念力是愛情、政治、美、事業等始終在場的剛性現實。他不斷觀察、思考,并且反省,這決定了他在這些不同空間的生存總將自己放在他者的位置,是一個體驗者卻非裹挾于生活的人。“瓦卜吉斯之夜”雖只是德國民間傳說,但其“夢幻之國魔術之邦”的象征性卻與不同時期的偉大文本契合。《浮士德》關乎瓦卜吉斯有兩個場次,發生在浮士德世俗愛情悲劇與政治悲劇之間,是對浮士德狂歡體驗的集中書寫。浮士德如何體驗這放縱的“歡樂”呢?當浮士德與摩菲斯特乘魔毯來到這傳說之地,眼前是黃金、眾生百態,“是親切的愛之呻吟,/那些美滿良辰的聲音?/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愛!/那種回聲又在呼應,/仿佛古時代的傳聞”。此情此景之下,浮士德卻質詢:“請問我們作何打算,/還是止步,還是向前?”[7]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頁,第86頁,第145頁。光怪陸離的狂歡場景仿佛浮士德看到的“另一自然”,從脫離書齋的那刻起,本能與欲望成了他穿越生活的底色,情欲、愛欲、求美、圍海造田,伴著“魔廚”的神秘,在以人生重要場景為準劃定的時空,始終如一的“浮士德主體”“清醒體驗”著理性的限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浮士德的悲劇意義得以生成。
穿越小說的主人公卻不同。浮士德通過體驗來找尋意義,網絡文學穿越者則清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故做起事來有板有眼,如何能夠征戰且征服新世界成為最主要的生存法則。其中,如何遵循異界的規矩,如何找到能倚靠的強力支撐,如何在濃密的關系網中游刃有余,構成情節的多重支線。于是乎,“假設”之下的生存成了一場在作者和讀者之間同時進行的探險游戲。而重生者,更是已經有了經驗的支撐,其全方位的投入,與浮士德的有條件的嘗試之間的區別昭然若揭。
對穿越者來說,首要的是觀察自己“被置入”的環境,猶如進入游戲界面。我們看到,“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之后,姚依依一直處于這種游魂狀態,她轉著小腦袋,四下打量屋子,這是一個類似于電視中看見過的古代房間,房間當中放著一個如意圓桌,姚依依看不出那是什么木料,不過光澤很好,亮堂堂的顯然是好貨,墻邊靠著一個雕花的木質頂柜,上面的花紋依稀是八仙過海的樣子,還有幾個矮幾和圓墩方凳什么的”[1]關心則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931329&chapterid=2。。這種“冷靜”的觀看,意在展示“新環境”的古典和穿越主體的新奇,卻無存在主義者所謂“被拋”之后的悲劇感。“姚依依”就此消失于敘事,“明蘭”則在“穿越的重生之路”上以權威“老祖母”作為披掛,整裝上陣,戰勝姨娘,在眾姐妹里脫穎而出,最終覓得鐵血柔情的“另一半”,成為異世的人生贏家。
不同生存意識決定了在新世界所關注的焦點不同。浮士德始終將視點放在對新生活的審視,場景變換只是他實現自己志向的“色相”平臺,軸心則是始終運轉的主體自省和思考。對葛雷卿,他想體驗那種強烈的愛情的甜蜜,其底色卻是性的欲望和獨占。也就是說,在這場愛情關系里,主導的是浮士德,被迷惑的虔誠少女成了體驗的對象。而海倫——這位從遠古穿越而來以美貌著稱的女子,與飲過魔廚煥顏水的俊美浮士德,在“求美”的基礎上結合,共同創造出一個不滿現狀的歐福良。這個孩子,就像浮士德,對“世界”的探索永無止境,歐福良墜地之日,也是浮士德逐美之夢幻滅之時。但浮士德并未因海倫的離去就此消沉,其“非凡”意志加上摩菲斯特極富蠱惑力的人心操控術化體驗為能指。當新生活景觀呈現在浮士德眼前,他的“興趣”和對“快樂”與“美”的追求就有了新的目標。作為穿越者的浮士德身上的探索光芒愈加明顯,一個獨立的“人格”不斷向前。如第二場“城門外”中浮士德的自白,“有兩個靈魂住在我的胸中,/它們總想互相分道揚鑣;/一個懷著一種強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須緊緊攀附著現世,/另一個卻拼命地要脫離塵垢,/高飛到崇高的先輩的居地”[2]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頁。。這基本成為浮士德與葛雷卿短暫愛情、與海倫破滅之美的創造及其政治與事業之夢等體驗之旅中的“鏡與燈”:現實之鏡只是成就靈魂之燈的界面。
穿越小說作為已成型且成為主流的網絡文學類型,要在奇異的探險情境中編織有意思能吸睛的故事就顯得很重要。比如《知否》,明蘭以青年靈魂穿越到一個5歲小姑娘身上,其“早熟神披掛”已經上身,被寄身的主人的悲慘經歷成為穿越者新生的起點。于是,迎合當權者喜好、找到人生導師、以謀略在復雜的權力關系中確定優勢位置,加上利用婚姻確定人生贏家的方向,這樣一條由生存和婚姻連綴起來的探險之線成為萬千穿越小說的公選模式。而像《天下》這樣的純愛小說,打著男男愛的旗幟,其實描畫的還是萬千腐女們的心之所系。按“簡介”所說,“明嘉靖三十五年,趙肅來到這里。最初的愿望,不過是吃上一頓飽飯而已”,但“這是一個從食不果腹的寒門庶子,到睥睨天下的大明首輔的故事”。也就是說,現實中的王寧并沒有“飛上枝頭變鳳凰”,卻成了“貧苦大眾中的一員”。故此文的焦點再清晰不過,“首先是改善生活,其次就是讀書,參加科舉”,目的是穿越后的“母子倆必然不會再這樣任人欺辱”[3]夢溪石:《天下·簡介》,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231454。。用趙肅的話說,就是“著眼于當下”,謀求“屌絲”逆襲。
因為對困境的理解、重生意圖和實踐方式的不同,跨時空穿越的結局也差異迥然。浮士德終在圍海造田大有成效那刻說出“真美啊,請停一下”,完成了不同人生階段的穿越。這似乎回到伊甸園故事中喻示的關于“人”的理解和定位。亞當和夏娃站到了上帝的對立面,使上帝變成“他者”。浮士德則站在大自然的對面,人征服大自然,令滄海變桑田,是他有意義人生的起點,是真正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動達成的極富創造力的偉業。浮士德始終向上的意志證明路德維希的反問:為什么這個宣布把自己的靈魂交給了撒旦的魔術師卻能毫無意義地以德國的天才征服了世界呢?[1]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楊成緒、潘琪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頁。于此,我們能清晰感知歌德那個時代,“個人”如何在愈趨復雜的現實中尋覓自己的位置,及其主導精神高漲的程度。隨后的恰爾德·哈洛爾德、簡·愛、于連、亞哈、希斯克利夫,就是這種時代情境下一個個不同面相的浮士德。從這個角度看,浮士德的確是歐洲社會和文明的一面鏡子。
網絡文學中的穿越者,不同于浮士德的不斷換境,不屈探索,他們在“被穿越”的前現代安穩下來,就此扎根。假如把網絡文學中的穿越者置于浮士德的體驗情境,每一情境都會構成終其一生謀劃的全部。這決定二者結局的根本不同。錢、權、愛情、安穩和幸福的一生,也就是說,現世的社會生活是一個個穿越者們謀劃一生的終極目標。在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俯視人生的上帝,而代表了欲望和否定力量的魔鬼卻亦步亦趨。有意思的是,正是這“魔鬼”,是作者和讀者雙方達成的共謀,“爽感”的獲得令雙方精神抖擻。“強烈的情欲”引誘浮士德走上出賣靈魂之路,卻最終見證理性而“走出絕望之境”;穿越者則在這世俗的快樂中找到一世安穩。如果說,作者所書寫的世界實際正是現實世界的鏡像,那么,浮士德的穿越行為讓我們看到18世紀后期的歐洲,網絡文學中連篇累牘的故事所呈現的恰是當下鮮活的日常。
四、語義網絡:精英/大眾趣味區隔下的書寫
以上立足于“穿越”行為的辨析恐怕還要回到書寫者。相對歌德的寫作,網絡文學書寫用天翻地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在歌德那個年代,印刷術才剛剛在古登堡的世界擴大地盤,被稱為“作家”的時代也才到來,“詩人”之名更加驚才絕艷。歌德從1771年開始創作的戲劇尤其是詩劇《浮士德》將他帶入偉大藝術家的小眾圈子。歌德不唯寫詩、論戲、品畫,還是個政治家,這些都使他與“大眾”遠遠拉開距離。換句話說,屬于浮士德的困境和維特的煩惱是在一個社會精英筆下得以呈現,他要自己的文字展現“狂飆突進”的德意志,強烈的民族夢想構成了歌德文學的底色,這也是他后來提出“世界文學”的原因之一。寫作者強有力的精神世界和完備的知識體系,決定其文字帶有強烈個體意識,可以說,歌德身上攜帶著浮士德的意志和身影。他力圖用自己的筆書寫彼時代的人,追敘往日尚在的親人、愛人、友人,就像“獻詩”部分作家吟唱的那般,“你們又走近了,縹緲無定的姿影,/當初曾在我朦朧的眼前浮現。/這次我可要試圖把你們抓緊?/我的心似乎還把那幻想懷念?/你們過來吧!很好,隨你們高興,/你們已經從云霧中飄到我身邊;/在你們四周蕩漾的魅惑的氣息,/使我心中震撼著青春的活力”[2]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第3頁,第4頁。。時隔多年,當想到這些同道中人,這些心底的知音,歌德“又感到久已忘情的憧憬,/懷念起森嚴沉寂的幽靈之邦,/……/消逝的一切,卻又在化為現實”[3]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 版社1989年版,第2頁,第3頁,第4頁。。至于那些“為了票子,簡直性命也不顧”的“各色群眾”,“請勿多談,/看到他們就要使詩魂逃脫。/別讓我看到那些人海人山,/他們硬要把我們牽進漩渦”[4]歌德:《浮士德》,錢春 綺譯,上海 譯文 出版 社1989年版,第2頁,第3頁,第4頁。。于此,作為“真正的藝術家”的寫作者的創作沖動、激情,與既定讀者間的心靈相通,與大眾的距離,競相呈現。但反過來看,歌德對大眾唯利是圖的評價,恰恰反映出市場與大眾文化在18世紀末期的歐洲已經開始展現其影響力的事實。作為寫作的主體,歌德本身就裹挾于國家/民族/大眾/市場所圍起來的圈子,大眾/市場在后來的發展中成為文學場域的重要環節,無論是精英寫作還是通俗寫作,都必須考量和直面大眾。這一點,往往是我們談論《浮士德》這樣的世界經典時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維度。
在這個意義上,網絡文學寫作與歌德寫《浮士德》既有不同,又有相似。
首先,對網絡文學的寫作者而言,與其說寫手有強烈的不能不寫的沖動,不如說這些故事是預先定好的大綱、模式和虛構的情境。想達成什么樣的效果,是定大綱之前就已有的考量。在《浮士德》的時代,作者處于與大眾趣味博弈的開始,精英與大眾的區隔在這場博弈中越走越遠,布爾迪厄所說的“文學場”[1]布爾迪厄在《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等著作中充分論述了法國以福樓拜和波特萊爾為代表的兩方如何成就了法國文學場,以繪畫為代表的藝術場域恰恰建立在與文學場域的差異基礎之上。大眾文化則在這一過程中蓬勃生長。的建立,即此博弈的結果,同時也是一種對現實的承認。
其次,網絡文學寫作者和讀者經由屏幕中介共同完成世界設定,形成期待,他們是共謀者。這就和歌德所批駁的為了“票子”的人群有所不同。在網絡文學片段性書寫過程中,讀者不斷參與,寫者不斷修正,在歷時幾月甚至幾年的鍵盤敲打中完成作品。這樣的作品不僅屬于寫者,也屬于讀者,面對屏幕,三方構成一個共同空間。對此,《風中玫瑰》的作者唐敏直言不諱:“《風中玫瑰》最大的特點,就是作者與讀者的現場參與互動的效果,讀者不是等待著讀一部完整的作品。而是與作者一起完成一個‘帖子’的寫作過程,真是同生共死的交情啊。”[2]唐敏:《風中玫瑰》,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寫者和讀者處在一個平面上,不分貴賤高低,聯動創作、眾籌創作、同人創作,凡此種種,都是網絡文學創作模式的標識。回看這些穿越文,好似觸摸到“文字”背后的“集體”身影,那是大眾,是普羅,是日常。
再次,網絡文學對“精英”的想象敘述建立在世俗生活的基礎上,因此具有鮮明的大眾性質,體現大眾的群體文化記憶。在歌德、康德和黑格爾的時代,人們在思考著天才和美,何為崇高,何為詩,其指向是脫離世俗的精神世界。相較之下,網絡文學的穿越者則執著于形而下,且用強有力的心智將自己牢牢拴在既得的形而下物質基礎之上。或如雅思貝爾斯所預言,日益崛起的電子文化中,技術正“以自然科學為根基,將所有的事物都吸引到自己的勢力范圍中,并不斷地加以改進和變化,而成為一切生活的統治者,其結果是使所有到目前為止的權威都走向了死亡”[3]雅思貝爾斯:《何謂陶冶》,《文化與藝術評論》第1輯,東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頁。。二者對“精英”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時代、社會結構、身份區隔和因媒介引起的文化變遷。
最后,我們看到,歌德所懷有的“德意志民族夢想”,在21世紀初網絡文學寫作者和受眾那里則轉換為力圖建立和展示的中華世界。“九州”系列寫作與后來的洪荒流、仙俠文異曲同工地指向宏闊的中國文化傳統,其間大量借鑒武俠傳統,將深入民心的“俠義”精神貫注在玄幻、仙俠、志怪以及都市各種類型的創作之中。“尋找東方式想象力”[4]江南:《九州縹緲錄》后記,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不僅是21世紀初動漫迷們的所想,更是身處互聯網和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人對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驚醒,從而接續上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化。歌德所在的年代,統一的德意志是日耳曼人的夢想,故而有“民族意識”的凸顯和夢想;于21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影響的焦慮”一點都不少,并一直延續為今天的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強烈主張和文化命題。穿越者和已經成為敘事技法的“穿越梗”,帶著強烈的意志進入新世界,并在新世界披荊斬棘,建立自己的光榮和榮耀,科學技術和國家民族觀念是建功立業的精神支撐。風丟子的《百年家書》重回抗戰年代,月關的《回到明朝當王爺》重啟崢嶸時代以展國威雄風,這些既是對歷史的重寫,也是當代民族意識的彰顯。
在上述關于寫作主體和受眾的異同當中,網絡文學與《浮士德》的差異不僅在精英/大眾的階層意識,還在于宗教/世俗之區別。《浮士德》的體驗之旅始終圍繞著摩菲斯特那句充滿嘲諷的“超俗而又入俗的情種”[1]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頁,第74—75頁。言語,而上帝和信仰的聲音也在不斷回響。在他自己深入思考的“太初有言—太初有思—太初有力—太初有為”[2]歌 德:《浮士德》,錢 春綺譯,上海 譯文出 版社1989年版,第162頁,第74—75頁。的關系線里,從“言”、“思”到“力”,再到“為”,無疑是一個世人與上帝關系的挪移過程。在《浮士德》中,就連上帝都愿意與魔鬼親切交談,這意味著高高在上、面不染血色的《神曲》之前的上帝,經由14世紀貝阿特麗采的引領,到18世紀已帶有濃重的人間色彩,或者說宗教的世俗化已然發生。但關于終極意義的探討仍在繼續。“浮士德難題”便是一場“崇高的感情”與“塵世紛擾”的戰斗,浮士德要找到世俗之樂與精神導引之間的合適位置,就必然面對“彼岸”的質詢。換句話說,“上帝”始終內在于浮士德的探索之旅。這是屬于歐洲文明的精神內核。《浮士德》能夠成為近代歐洲人的《圣經》,與世俗化宗教的主體意識正相關,所反映的恰是歐洲文學古希伯來/基督教這條隱線,不管“上帝”被擺在什么位置,始終或隱或顯地存在于文字的縫隙之間。所以,浮士德的穿越才會從與上帝/魔鬼賭約開始,繼而與葛雷卿的青春戀愛會以失敗告終,最后的回歸天堂更是近代宗教的形象化表述。與之相比,中國網絡文學的穿越者卻無論重生或者穿越,還是變鬼成神,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大凡只有一條主線:世人只說人間好!主體行為的基點落足在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表述背后是群體意志,也是中國人歷來重視現世生活的當代敘述。
五、現實情境與大眾性:可通約的“浮士德精神”
穿越的主體,從青春開始,以求“新生”;穿越者的生存空間,所折射的是不同時空主體攜帶的現代/傳統觀念的博弈,主體意志在這樣的空間中得以凸顯;編織穿越夢想的寫作者,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群體記憶。這些特征,在浮士德的穿越和網絡文學的穿越梗之間建立起聯系和差別。而在文體意義上,將二者進行比較,可為我們展示出一部文體的變遷史和社會史。
在西方,小說與長詩是兩種生長時代不同、與現實關系不同的文體。長詩歷史顯然悠久得多,從史詩時代,到悲劇的創生,詩,自然承擔起記錄和表達的形式功能。這種形式,與文字的發明、紙張的稀缺、文化資本的場域限制等,一起構成文學的小眾世界。詩歌,尤其是長詩,很長時間屬于精英文學的老大,其形式由此具有了意識形態功能和社會性質。歌德的長詩在他所在時代直到現在,一直保有這種小眾標識。小說卻不同,尤其是長篇小說。小說的繁盛和興起基本都在18世紀。這么多的字,需要很多紙張,代價上去了,也就需要更多人來讀。所以從一開始,長篇小說就牢牢與世俗世界捆在一起。市場、讀者,是長篇小說的生命線,換句話說,世俗性、日常生活,就是這個文體抓住人心的關鍵。由此筑起了日后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網絡文學也包括很多文體,有詩歌,有散文,有戲劇,但唯有小說能擔起成為網絡文學標識的重任。而網絡文學小說群落中能稱得上代表的無一不是長而又長的長篇。超長的篇幅,進一步拉近了小說與世俗人生的距離,每天的陪伴,不想結束的人生微妙心態,在一個文體上折射出來。從文體角度看,歌德對精神世界的探索,網絡文學穿越者在一個個日常生活瞬間流連忘返,似乎就有章可循了。
而將《浮士德》與網絡文學放在一起比較遇到的最大障礙也在于此。長篇敘事詩的文體很自然地將《浮士德》劃歸精英文學或者純文學,而網絡文學定位卻由于互聯網空間、寫手與粉絲界限不明和流量化的市場體系,跟“精英”文學或“純”文學基本沒什么關系。但如果我們從文體出發分析《浮士德》時代文化的混雜性和網絡文學自下而來的群體訴求,在現實情境規約和大眾性的意義上,“浮士德精神”就獲得了跨時代的共識和基于民族認知的“主體意志”的隔空對話。
首先,《浮士德》雖為長詩,卻以敘事和故事為主調,注重通過文字的延展、場面和動作的充分描寫而使讀者有代入感。《浮士德》寫書齋生活的枯燥,寫愛情的甜蜜與苦楚,寫美的希冀與落寞,寫投身政治的熱情和艱難,最后落腳在圍海造田的個人理想及其失敗,顯然在故事的容量、主體的參與度及其與世俗人生的關聯和傳奇性等多方面有了大的跨越。相應地,讀者閱讀就有了清晰的主線,循著薩特所說文本中的“路標”一路向前。這部作品在18世紀后期的德國,在長篇小說開始興起的時代,其文體已經烙上了大眾文化的印記。沒有故事的網絡文學基本和市場沒有關系,而如何把故事講得更好,如何更有吸引力和想象力,是“穿越”成為網絡文學敘事一大手段的原因。
其次,敘事主體就是行動主體,主體命運成為連綴情節結構的動力機制和線索。清晰的主體性成為聯系作者和讀者的關鍵。網絡文學的穿越者帶著“現代靈魂”在“異界”謀生存。他們并不滿足按照既有世界格局繼續行進,他們的生存必須適應現存環境又能使其為我所用,怎么做到這一點,改變環境就成了必需,這是穿越者們努力要做到的,也是寫手和讀者共同的“爽點”——他們共同使故事朝自己所想的方向發展。在適者生存的人生法則之下,是始終作為底色的追求意識,這使其意義不再沉溺于普泛的瑣碎的日常,而是使日常變成“我的日常”,進而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很多架空歷史的穿越文在這方面的表現都很突出,諸如《回到明朝當王爺》《新宋》《竊明》《謹言》都在此列。小說主人公利用穿越帶來的披掛,力圖改寫歷史,不茍活于世,關心時政的心思清晰顯豁。如果說,浮士德的世俗探索始終有強有力的個人靈魂,那么,穿越者的世界,則力求在豐富的現實中既沉入現實又改變現實,如何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其生存法則,也是其寶貴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世俗、勇氣、追求,在區隔不同時代穿越者的同時,也將他們連綴起來,表達出不同的人生境遇和現實。
再次,基于“現實”的現實書寫、社會情境和主觀感受,將作者和讀者共置于統一的文化空間。對于書寫《浮士德》的歌德來說,如何接著狂飆突進運動以民族文學的形式探求強大的德意志的統一,是最大的現實。浮士德重獲青春,所要做的既在“單一主體”范圍之內,同時也是“德意志群體”所面對的社會現實,政治腐敗是彼時的德國和歌德共同的難題。在這種“改變”和“體驗”動機之下,“有準備的出發”再一次將此時和彼時連接起來。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將“記憶”分為模仿式記憶、對物品的記憶、通過社會交往傳承的記憶以及文化記憶。文化記憶涵蓋前三種記憶并將文化層面上的意義傳承下來且不斷提醒人們去回想和面對這些記憶[1]揚·阿斯曼:《“文化記憶”理論的形成與建構》,金壽福譯,《光明日報》2016年3月26日。。浮士德精神世界里的神學、哲學、醫學、法學四大學問,既是他質疑世界的原因,也是他穿越之行的知識倚靠和資本,換句話說,被他置于一旁的上帝,對知識的質疑和闡釋,正是他能保持前行動力、不斷反思的力量所在。倘無這些“準備”,浮士德就不是浮士德,他的“痛苦”也就無從談起。最終“上天”“以清晰的基督教-教會人物和想象”給予他的“詩學意圖以恰如其分的形式和穩定度”[2]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41—642頁。,這本身就是浮士德同時代人依循的共同文化記憶。而如姚依依一般的穿越者們,栩栩如生的古代社會器具、詩書、禮儀、家族關系,中國的唐詩宋詞、文化典籍、神話傳說……則成了他們穿越生活的必備和外掛,幫助他們在異時空赤手空拳闖世界,處處鰲頭獨占。究其原因,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給了他們底氣。這些標識著當代人借由文化傳統所型構的文化記憶、文化想象,同時又因現代靈魂的存在而進行著不輟的改寫和重建。
最后,世俗與大眾化是實現主體意志和社會變革的起點。浮士德的困惑在于他皓首窮經都無法找到人生于世的意義。他想知道,什么是萬物相連的“動力和種子”,“生動的自然”何在,對快樂的探索終將于何處駐足。他相信有一種力量可讓他“覺得年輕神圣的幸福/重新熱烈地流變神經和脈管”[1]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頁,第17頁。,于是有了將靈魂讓渡給魔鬼的行為。而“統合”的關鍵恰恰就在于他的“行為”。他想以理性和意志去探索的“快樂”是魔鬼賦予的,是魔鬼給他打造了走上快樂之途的計劃。摩菲斯特從世人的“理性”生活看到“悲慘”和“折磨”,認為這“比任何野獸還要顯得粗野”[2]歌德:《浮士德》,錢春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頁,第17頁。。“尋歡和力行”是他給浮士德安排的主要行動路線,是背理性而行之,這正是困境中浮士德抓住的救命繩索。浮士德短暫的體驗生涯始于欲望,而終于欲望,其間差別只在不同經歷中的“相”之差異:性欲、愛欲、權力欲和征服自然的欲望。顯然,摩菲斯特的存在不僅是“否定的力量”,他就是世俗,是一種不同于古典時代的快感政治。這好像在昭示,只有真正踏入人群,走進世俗,才能洞徹人生快樂的真諦。對于彼時代站在世紀之交的浮士德們,精神的追求須得在世俗的底子上才能飛升。這是一種發現,也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這意味著,當重返精英/大眾、詩/小說這樣的區隔和劃分時,在浮士德的穿越和網絡文學穿越者之間奇妙地出現了統合的趨勢。其奧秘在于穿越者與空間確立的行為關聯。基于合理性的“善”,是彼時此刻的書寫者和主體共同面對的最大現實訴求。列斐伏爾指出,人民與空間的關系是批判性的。人們分別地(一點一點地)把一個被設想為是中立的、與利益無關的、客觀的(純潔的)空間中的那些欲望、功能、地點、社會目的聯系在一起,人們在它們的背后建立起了很多聯系。這些過程與社會空間的分割有著明顯的聯系,……這些術語(活動、欲望、對象、地點)之間存在著一些局部性的聯系,而關于這些聯系的理論,則促成了一系列規劃[3]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中國的傳統、浮士德的知識庫,各自所攜帶的身份暗示,看似都是“舊物”,卻在穿越者的行為中煥發生機,這種對文化的記憶、改寫和發展,建構出一種新現實中的文化傳統。
六、結語
跨越時空品讀兩種文本和文類,也不啻于一場穿越,這場比較可幫助我們理解不同時代的寫作,不同時代的文化,還有文學與社會的緊密關系。彼時的浮士德,需要找到個人立足于世的力量,其背后是德意志民族的強國訴求;此時的中國穿越者們,遍歷世界,脫離失敗和平庸者的境地,帶著中國傳統,走上由弱變強、改造自身和現實的逆襲舞臺。此時與彼時,同為穿越,所需所求已是大相徑庭,其間卻有一條“人的歷史”的紅線在蜿蜒穿行。誠如愛德華·薩義德所言:“我們在闡述表現過去的方式,形成了我們對當前的理解與觀點。”[4]愛德華·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頁。從這個角度,或許我們能夠理解21世紀的讀者緣何因為這些曾不為人所看好的網絡文本而重新煥發了閱讀的興趣,進而使文學在網絡時代依托新的媒介進行著“新文學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