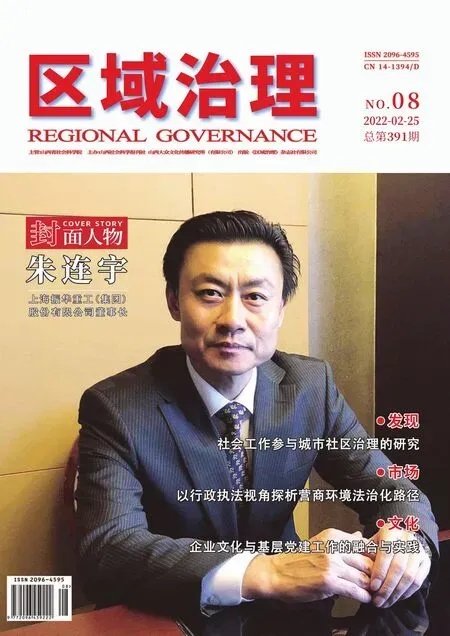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的現(xiàn)狀、問(wèn)題與完善建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xué) 石琴莉
一、國(guó)內(nèi)外對(duì)于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踐
(一)國(guó)外實(shí)踐
國(guó)外對(duì)于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踐早于我國(guó)。1968年,伊萬(wàn)在對(duì)從相關(guān)世界組織獲取的資料、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后,設(shè)計(jì)出了一套包含70項(xiàng)指標(biāo)的法律指標(biāo)體系,對(duì)于法治政府的指標(biāo)評(píng)價(jià)也囊括在其中。1979年,梅里曼、克拉克、弗里德曼,首次提出對(duì)法律制度進(jìn)行“定量比較法”的研究。1996年,世界銀行推出“世界治理指數(shù)”(簡(jiǎn)稱WGI),該指數(shù)設(shè)置了六個(gè)指標(biāo),旨在對(duì)世界各國(guó)或者地區(qū)的治理狀況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但是對(duì)于法治或法治政府的評(píng)價(jià)只是其中涉及的一個(gè)部分。2008年,美國(guó)律師協(xié)會(huì)聯(lián)合部分律師組織發(fā)起了“世界正義工程”(簡(jiǎn)稱WJP)項(xiàng)目,旨在對(duì)各國(guó)的法治狀況進(jìn)行量化評(píng)價(jià)。WJP以4個(gè)原則為根本依據(jù),包括16個(gè)一級(jí)指標(biāo)和68個(gè)二級(jí)指標(biāo),其中政府受法律約束為其原則之一。
綜上可知,國(guó)外的評(píng)價(jià)體系主要針對(duì)一個(gè)國(guó)家整體的法治水平,在其考慮的諸多方面中,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量化評(píng)價(jià)只是其大框架下的一小部分內(nèi)容,缺少針對(duì)性。由此,國(guó)外對(duì)于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的相關(guān)實(shí)踐相對(duì)較寬泛,對(duì)于一國(guó)各地方的評(píng)價(jià)的具體適用性較低。
(二)國(guó)內(nèi)實(shí)踐
國(guó)內(nèi)對(duì)于地方法治政府的量化評(píng)價(jià),主要以各地的“法治指數(shù)”“指標(biāo)體系”“考核評(píng)價(jià)體系”等來(lái)體現(xiàn)。我國(guó)的首個(gè)法治指數(shù)是2005年誕生的“香港法治指數(shù)”,用之評(píng)價(jià)我國(guó)香港的整體法治水平,該指數(shù)在當(dāng)時(shí)也只是將法治政府的量化評(píng)價(jià)作為其中的一個(gè)條件,并沒(méi)有專門、有針對(duì)性地對(duì)政府的法治建設(shè)狀況作出更詳細(xì)的評(píng)價(jià)。在我國(guó)內(nèi)地,“建設(shè)法治政府”的目標(biāo)于2004年被明確提出,并不斷出臺(tái)相應(yīng)的文件。從目前收集到的資料可以看出,我國(guó)在建設(shè)法治政府的進(jìn)程中越來(lái)越重視對(duì)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量化考核、量化評(píng)價(jià),旨在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最后以一種直觀的、可視化的方式反映各地法治政府建設(shè)情況。此后,各地包括省、市、區(qū)(縣)也隨之出臺(tái)關(guān)于對(duì)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的相關(guān)文件(見(jiàn)表1)。

表1 部分省、市、區(qū)(縣)法治政府建設(shè)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
二、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wèn)題
(一)現(xiàn)狀
縱覽全國(guó)各地方出臺(tái)的關(guān)于建設(shè)法治政府的相關(guān)文件,再結(jié)合國(guó)內(nèi)近些年的實(shí)踐來(lái)看,不可否認(rèn)的是,在地方法治政府的量化評(píng)價(jià)上我們的確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也在此過(guò)程中得到了不斷完善與升級(jí),使我國(guó)的法治政府建設(shè)邁上一個(gè)新臺(tái)階。
以我國(guó)內(nèi)地誕生的第一個(gè)法治指數(shù)—余杭法治指數(shù)為例,該指數(shù)主要應(yīng)用于杭州市余杭區(qū)的法治建設(shè)和社會(huì)管理。自誕生至今,余杭區(qū)通過(guò)數(shù)據(jù)收集、群眾滿意度調(diào)查、內(nèi)審組、外審組評(píng)估、專家組評(píng)審五個(gè)步驟,自行進(jìn)行著一年一度的法治“體檢”。經(jīng)過(guò)十多年的研究、實(shí)踐、評(píng)審,余杭區(qū)的法治指數(shù)從2007年度的71.6分,到2017年度的78.7分,總體呈現(xiàn)逐年小幅上升趨勢(shì),為杭州市余杭區(qū)推動(dòng)改革開放、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營(yíng)造了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同時(shí),根據(jù)余杭法治指數(shù)評(píng)價(jià)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以及措施,給群眾帶來(lái)了看得見(jiàn)、摸得著的實(shí)惠,提高了群眾對(duì)于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認(rèn)可度、權(quán)威性,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
除了余杭法治指數(shù)之外,其他地方的法治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對(duì)于當(dāng)?shù)氐姆ㄖ握ㄔO(shè)也發(fā)揮著重要的、積極的作用,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國(guó)法治政府建設(shè)取得了重大進(jìn)展。但是,目前我國(guó)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突出的問(wèn)題。
(二)存在的問(wèn)題
1.各地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缺乏橫向可比性
各地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動(dòng)全面依法治國(guó),是對(duì)中央建設(shè)法治政府目標(biāo)的貫徹,是依法治國(guó)中重要的一環(huán)。因此這不僅需要各地方政府根據(jù)其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進(jìn)行縱向的自我對(duì)比,推動(dòng)其在原來(lái)基礎(chǔ)上有針對(duì)性地自行改進(jìn)薄弱領(lǐng)域,同時(shí)也需要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進(jìn)行橫向?qū)Ρ龋郧笳g優(yōu)勢(shì)互補(bǔ),倒逼政府法治水平的提升。
而從國(guó)內(nèi)實(shí)踐現(xiàn)狀和收集到的資料來(lái)看,國(guó)內(nèi)各地方的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在指標(biāo)設(shè)計(jì)上,各指標(biāo)的數(shù)量、內(nèi)容及權(quán)重賦予均不一致。例如在“余杭法治指數(shù)”中主要是“1(一個(gè)指數(shù))4(四個(gè)層次)9(九項(xiàng)滿意度調(diào)查)”[1]包含27項(xiàng)二級(jí)指標(biāo)以及77項(xiàng)三級(jí)指標(biāo);而在《法治昆明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中由“法治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指標(biāo)”“法治的制度環(huán)境指標(biāo)”和“法治的人文環(huán)境指標(biāo)”3個(gè)一級(jí)指標(biāo)、13個(gè)二級(jí)指標(biāo)和33個(gè)三級(jí)指標(biāo)構(gòu)成。[2]雖然地方量化評(píng)價(jià)要結(jié)合各地特色、因地制宜,但形式上的諸多差異,各地橫向比較無(wú)法得以實(shí)現(xiàn)。
2.評(píng)價(jià)主體缺乏中立性,第三方評(píng)價(jià)主體力量薄弱
對(duì)政府的法治化程度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是為了厘清政府權(quán)力邊界、提高政府的行政、決策等能力,最后建設(shè)為人民服務(wù)、人民滿意的法治化政府,因此,地方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不僅要真實(shí)地評(píng)價(jià)政府的法治建設(shè)程度,還需要公之于民、信服于民,并保持中立性。但縱覽各地的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量化考核標(biāo)準(zhǔn),評(píng)價(jià)主體主要是政府,主要分為由政府直接主導(dǎo)或政府主導(dǎo)狀態(tài)下部分評(píng)價(jià)、調(diào)查委托第三方進(jìn)行。比較典型的“余杭指數(shù)”“昆明指數(shù)”都是由地方的法治建設(shè)小組牽頭與高校課題組或者第三方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合作。除此之外,一些地方則直接由政府內(nèi)部根據(jù)量化體系自上而下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事實(shí)上,筆者認(rèn)為,政府牽頭領(lǐng)導(dǎo)對(duì)自己的法治建設(shè)情況進(jìn)行評(píng)估,避不了“自導(dǎo)自演”之嫌,缺乏應(yīng)有的中立性。此時(shí)法治評(píng)價(jià)容易成為各級(jí)政府“秀政績(jī)”的新的戰(zhàn)場(chǎng),尤其是法治指標(biāo)的設(shè)計(jì)掌握在政府自己手中的時(shí)候,其能否真的實(shí)現(xiàn)表象與實(shí)質(zhì)的統(tǒng)一就變得更為讓人懷疑。[3]即便是政府將部分評(píng)價(jià)委托第三方進(jìn)行,在政府對(duì)第三方的資金支持、數(shù)據(jù)支持等情況下,委托方在評(píng)價(jià)時(shí)是否會(huì)受制于各地方政府,我們也無(wú)從得知。
近年來(lái),當(dāng)然也出現(xiàn)了第三方獨(dú)立發(fā)起的并推出的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雖然這類評(píng)價(jià)獨(dú)立于政府之外、不受政府的控制,其評(píng)價(jià)的公信力、民眾認(rèn)可度可大大提高;但在目前,其數(shù)量較少、規(guī)模尚小,自身力量相對(duì)薄弱,受重視程度較低,不具有權(quán)威性。最重要的是,它們?cè)跀?shù)據(jù)獲取上面臨巨大困境,無(wú)法獲得政府所掌握的第一手?jǐn)?shù)據(jù)資料,評(píng)估的數(shù)據(jù)來(lái)源只能是政府公開的信息,但囿于現(xiàn)實(shí)中一些政府信息公開的不主動(dòng)性和滯后性,以至于數(shù)據(jù)獲取不全面、不準(zhǔn)確,最終導(dǎo)致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偏差,如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的法治政府的量化體系在起初也受制于公開數(shù)據(jù)不足和政府信息獲取上的困難,而只能放棄某些本可以更好地反映法治政府建設(shè)程度的指標(biāo)。這不僅無(wú)法正確反映當(dāng)?shù)氐姆ㄖ握ㄔO(shè)水平,還會(huì)給部分地方法治政府建設(shè)帶來(lái)不良影響。
3.評(píng)價(jià)的對(duì)象不統(tǒng)一,各評(píng)價(jià)體系缺乏實(shí)效性
從現(xiàn)有的地方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來(lái)看,大部分地方針對(duì)政府職能、行政制度體系、行政決策、行政執(zhí)法、權(quán)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化解糾紛等方面對(duì)政府的法治水平進(jìn)行評(píng)綜合評(píng)價(jià),其關(guān)注點(diǎn)在于政府“做了什么”,側(cè)重于已經(jīng)實(shí)施、完成的行為,是對(duì)形式上的評(píng)價(jià),不問(wèn)其實(shí)施的成效。而少部分地方則是對(duì)政府的績(jī)效進(jìn)行量化評(píng)價(jià),其聚焦于對(duì)政府實(shí)施行為的滿意度,關(guān)注的是,政府在“做了什么”的基礎(chǔ)之上“做得怎么樣”,是對(duì)于實(shí)效、績(jī)效的評(píng)價(jià)。但困于各地對(duì)于“法治政府評(píng)價(jià)”這一概念理解不同,導(dǎo)致各地量化評(píng)價(jià)的對(duì)象不統(tǒng)一,進(jìn)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最終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
由于目前存在這兩種評(píng)價(jià),且對(duì)于地方政府“做了什么”的評(píng)價(jià)居多,而這種以形式為依據(jù)而生成的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又僅僅是浮于表面,導(dǎo)致該地政府存在的真實(shí)問(wèn)題無(wú)法得以反映并公之于眾;此時(shí)只有政府內(nèi)部知曉,這明顯與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的根本宗旨、目標(biāo)相背離。可想而知,這樣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將無(wú)法發(fā)揮其實(shí)際效用,使量化評(píng)價(jià)淪為“完成任務(wù)式”的評(píng)價(jià),甚至還會(huì)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刻意隱瞞存在問(wèn)題的后果,導(dǎo)致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形式化、盲目化。
三、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的完善建議
值《法治政府建設(shè)實(shí)施綱要(2021-2025年)》發(fā)布及各地對(duì)此政策的貫徹落實(shí)之際,筆者有以下完善建議。
(一)統(tǒng)一共識(shí)性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增加橫向可比性
對(duì)地方法治政府建設(shè)進(jìn)行量化評(píng)價(jià),是完善地方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全面、直觀感知全國(guó)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市、區(qū)縣的法治政府建設(shè)水平,應(yīng)在保留各地方法治建設(shè)特色的同時(shí),增強(qiáng)區(qū)域間橫向可比性。
筆者認(rèn)為,國(guó)家應(yīng)主導(dǎo)建立兼具各地特色且符合全國(guó)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通用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具體言之,由國(guó)家劃撥專項(xiàng)資金,設(shè)立專門小組。該小組首先對(duì)各地的具體建設(shè)情況進(jìn)行考查,后召集各地方的評(píng)價(jià)主體代表全國(guó)通用體系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商議,結(jié)合實(shí)際情況,對(duì)各方共識(shí)性標(biāo)準(zhǔn)予以確認(rèn),構(gòu)建初期評(píng)價(jià)體系,其中包括各項(xiàng)指標(biāo)的具體核心內(nèi)容、等級(jí)數(shù)量、權(quán)重賦予以及主要計(jì)算方法等。其次,在設(shè)定指標(biāo)內(nèi)容及權(quán)重占比時(shí),為各地的特色法治建設(shè)進(jìn)行內(nèi)容與權(quán)重的預(yù)留,完成評(píng)價(jià)體系的最終構(gòu)建。確保指標(biāo)體系在全國(guó)通用的基礎(chǔ)上,靈活融入地方鮮明特色,平衡好指標(biāo)體系的全國(guó)普遍性和地方特殊性的關(guān)系;使政府在評(píng)價(jià)后及時(shí)發(fā)現(xiàn)其在法治建設(shè)中存在的問(wèn)題,及時(shí)查漏補(bǔ)缺,借鑒、學(xué)習(xí)同級(jí)別其他政府的法治建設(shè)措施,激勵(lì)其提升法治水平。
(二)采用第三方獨(dú)立評(píng)價(jià),增強(qiáng)中立性、認(rèn)可度、公信力
對(duì)于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評(píng)價(jià)是對(duì)政府自身的評(píng)價(jià),要保證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與結(jié)果的真實(shí)性、客觀性、準(zhǔn)確性,有效防止地方政府權(quán)力過(guò)度干預(yù)評(píng)價(jià),應(yīng)再采用第三方評(píng)價(jià)獨(dú)立評(píng)價(jià)。第三方參與評(píng)價(jià)不同程度上改變了政府內(nèi)部考評(píng)屬性, 引入獨(dú)立的關(guān)聯(lián)主體,[4]其在不受制于政府的情況下,能夠?qū)φ块T作出客觀公正的評(píng)價(jià),進(jìn)而提升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和認(rèn)可度。筆者認(rèn)為,主要從以下兩個(gè)維度實(shí)現(xiàn):
首先,國(guó)家層面。通過(guò)立法或發(fā)布相關(guān)文件承認(rèn)正規(guī)的第三方評(píng)價(jià)主體,確定第三方評(píng)價(jià)的權(quán)威性,對(duì)第三方評(píng)價(jià)主體的資格認(rèn)定、評(píng)價(jià)規(guī)范等問(wèn)題作出相應(yīng)規(guī)定和解釋。對(duì)于符合相關(guān)規(guī)定的第三方評(píng)價(jià)主體給予國(guó)家層面認(rèn)可,彰顯國(guó)家對(duì)采用第三方獨(dú)立評(píng)價(jià)的重視程度,對(duì)于不符合相關(guān)規(guī)定的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處罰與公示,并將其列入黑名單,進(jìn)而保證這類主體的自身的專業(yè)性以及在民眾中的權(quán)威性。
其次,評(píng)價(jià)主體自身層面。在理論上,要加強(qiáng)對(duì)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的深入研究。在我國(guó),獨(dú)立的第三方評(píng)價(jià)主體主要包括各高校相關(guān)專業(yè)人員組成的研究中心、社會(huì)專門調(diào)查機(jī)構(gòu)等,這就要求相關(guān)高校的研究中心或其他相關(guān)研究機(jī)構(gòu)不斷提升科研能力,從國(guó)外實(shí)踐到國(guó)內(nèi)經(jīng)驗(yàn),不斷探尋對(duì)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的可行性新路徑。在人員構(gòu)成上,應(yīng)當(dāng)豐富內(nèi)部人員構(gòu)成。對(duì)于法治政府的量化評(píng)價(jià)不僅需要具有深厚法學(xué)功底的法學(xué)專家,同時(shí)還需要來(lái)自社會(huì)學(xué)、統(tǒng)計(jì)學(xué)、大數(shù)據(jù)等相關(guān)學(xué)科的專業(yè)人員,打造綜合、全面的評(píng)級(jí)團(tuán)隊(duì),以保證民眾對(duì)評(píng)價(jià)體系的信任度。
(三)明確評(píng)價(jià)對(duì)象,兼顧實(shí)質(zhì)與形式,增強(qiáng)效用性
評(píng)價(jià)不僅關(guān)注政府法治建設(shè)“做了什么”(即“實(shí)然性”結(jié)果),更要關(guān)注“應(yīng)該做什么”(即“應(yīng)然性”結(jié)果);不僅要檢驗(yàn)建設(shè)目標(biāo)完成情況,更要求建設(shè)過(guò)程體現(xiàn)法治精神。[5]因此,對(duì)于地方法治政府的量化評(píng)價(jià),除了關(guān)注政府“做了什么”,更要關(guān)注的是“做得怎么樣”,即要明確評(píng)價(jià)對(duì)象,兩者兼顧,使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發(fā)揮應(yīng)有效用,避免評(píng)價(jià)只是流于形式、無(wú)法深入實(shí)質(zhì)的狀況。筆者認(rèn)為,主要從以下兩點(diǎn)進(jìn)行:
第一,在指標(biāo)設(shè)計(jì)上,加入對(duì)“行政效率”“廉潔程度”“服務(wù)工作”等關(guān)于群眾滿意度調(diào)查的指標(biāo),且這些指標(biāo)在設(shè)計(jì)上應(yīng)當(dāng)是人民群眾切身能夠感知、易于理解且與其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便于群眾在自己的認(rèn)知范圍內(nèi)作出正確評(píng)價(jià),努力克服群眾評(píng)價(jià)中的主觀性,倒逼政府進(jìn)行不斷糾錯(cuò)。第二,在人民群眾上,相關(guān)部門對(duì)政府的政策、措施、最新動(dòng)向等以喜聞樂(lè)見(jiàn)的方式加強(qiáng)對(duì)人民群眾的宣傳。宣傳應(yīng)遍及各工作領(lǐng)域的民眾,使民眾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對(duì)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認(rèn)知。同時(shí),民眾也應(yīng)當(dāng)自行加強(qiáng)對(duì)法治政府建設(shè)的關(guān)注,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政策,減小評(píng)價(jià)中的主觀性,彌補(bǔ)數(shù)據(jù)的機(jī)械性,對(duì)于政府的各個(gè)方面作出真實(shí)評(píng)價(jià)。
四、結(jié)語(yǔ)
對(duì)地方法治政府進(jìn)行量化評(píng)價(jià)即對(duì)地方政府進(jìn)行法治“體檢”,是實(shí)現(xiàn)依法治國(guó)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同時(shí)在政府行政效率、行政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增強(qiáng)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雖然現(xiàn)在評(píng)價(jià)體系還存在著一定的問(wèn)題,導(dǎo)致一些地方法治政府的評(píng)價(jià)趨于形式化,但隨著《法治政府建設(shè)實(shí)施綱要(2021-2025年)》的發(fā)布、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科技的不斷融入,地方法治政府量化評(píng)價(jià)體系將會(huì)不斷得到完善,我國(guó)法治政府建設(shè)將會(huì)取得更大進(jìn)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