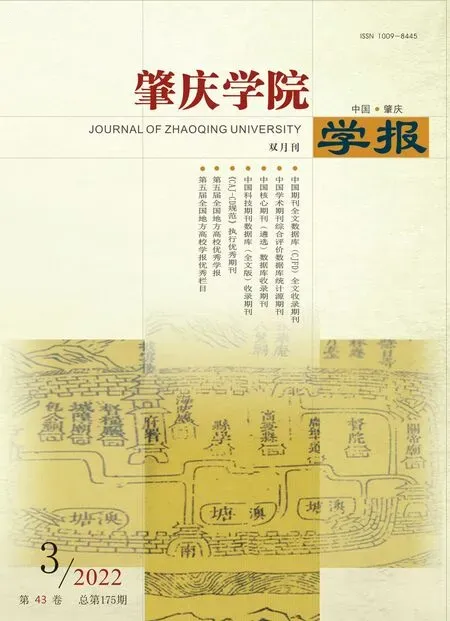釋“言不必信”:傳統(tǒng)儒學(xué)視野下的守信問題
王 格
(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哲學(xué)系,上海 200433)
誠實(shí)守信是人類社會生活共同訴求的一種基本美德,也是一個(gè)正常運(yùn)作的社會所必須廣泛采用和遵守的規(guī)則。在康德哲學(xué)中,不說謊是一條“可普遍化”的原則,所以是“定言令式”,即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人們都不應(yīng)該說謊——康德以此排斥了任何哪怕迫不得已的假承諾。但是,這只是一種哲學(xué)抽象理論上的推演,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世界的考慮中,似乎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很明顯,一旦落實(shí)到具體生活世界中,善意的謊言和不得已的假承諾隨時(shí)都可能會以一種非常正面的情形出現(xiàn),日常生活中的人們大都會樂意去接受。
一、“信近于義”——儒學(xué)視野下的守信難題
儒學(xué)傳統(tǒng)十分重視“信”,在儒家最重要的經(jīng)典《論語》一書中大量論及“信”,孔子甚至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政治上則是“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漢代大儒董仲舒將信與仁、義、禮、智一起列為“五常”(《賢良對策》),從此成為中國儒家道德文化的重要綱維。
在今天一般看來,守信就是講信用,就是一諾千金。可是,先秦主要儒家學(xué)者卻似乎并不這么看。在《論語》一書的記載中,孔子雖然多次強(qiáng)調(diào)“主忠信”,強(qiáng)調(diào)朋友有信,而且孔子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慎于言”大概也包含著守信的層面,但是,孔子對一味守信似乎并不太贊賞,甚至有明顯貶低的意味,這一點(diǎn)從“子貢問士”章可以看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xiāng)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脛脛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
在此,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這樣一種在常人看來理應(yīng)受到褒獎(jiǎng)的人給予了比較低的品級,被看作“小人”,雖然不一定特別低,可能也還可以勉強(qiáng)算作“士”。《論語》中還有一處在解讀上有些模糊可疑:尾生可能是一個(gè)忠實(shí)守信、一諾千金的典型人物,但孔子卻對他評價(jià)不高。而在另一處,孔子的弟子有子明確地說“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論語·學(xué)而》),言外之意是,如果“信”(承諾)背離了“義”,那么是不可以去兌現(xiàn)承諾的。孟子大概是有見于此,所以才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即“義”更為根本。荀子亦然,他指出,“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荀子·強(qiáng)國》),這是為政層面上的。總之,在有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學(xué)者看來,“義”跟“信”是有交疊的兩件事情,有義而不信的,也有信而不義的,但二者取舍時(shí)我們應(yīng)當(dāng)選擇義而不信。也就是說,“義”對“信”是有優(yōu)先性的,要成為“信”的準(zhǔn)則和依據(jù)所在;如果守信的行為將要違背義,就可以通過不守信以成全“義”。這是儒學(xué)對其守信的理論原則進(jìn)行抽象論說的起點(diǎn)。
“義”也是儒家最核心的價(jià)值觀念之一。早期的“義(義)”字可能與威儀有關(guān),但周代以后,“義”便開始確立其道德哲學(xué)的獨(dú)特意涵,并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成為諸子百家爭相論述的核心概念之一[2]。就儒家傳統(tǒng)而言,《中庸》明確有所謂“義者,宜也”,宜是合宜,處理得恰如其分、恰到好處,亦即是應(yīng)當(dāng)如此的意思。“應(yīng)當(dāng)”和“不應(yīng)當(dāng)”構(gòu)成了倫理學(xué)的基本判斷,即所謂“應(yīng)然”,與我們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不合宜”的“實(shí)然”狀況相對。因此,我們今天經(jīng)常使用的正義、道義、見義勇為、義不容辭、大義凜然等語詞,所關(guān)涉的都是直接與“應(yīng)當(dāng)”相關(guān)的問題。在與情感相關(guān)時(shí),有“仁義”;在與理智相關(guān)時(shí),有“理義”;在與儀式、節(jié)目、制度等形式相關(guān)時(shí),有“禮義”;等等。
可是,“義”雖然如其字源學(xué)涵義一樣,表明是一種權(quán)威性的尺度,是對人們行為的絕對評判,但落實(shí)到日常經(jīng)驗(yàn)中時(shí),它卻往往缺乏客觀化的準(zhǔn)繩。在康德哲學(xué)那里,行為的“可普遍化”構(gòu)成了“義”之于“信”的尺度性作用,從而獲得了很大程度的客觀化。而“義”在儒學(xué)中難以做到外在的客觀化,特別是在孟子的“義內(nèi)”說作為主流的儒學(xué)傳統(tǒng)中,判準(zhǔn)的主體內(nèi)在性決定了實(shí)際運(yùn)用上會有諸多的麻煩。這個(gè)難題大致上可以說是:“權(quán)”作為與“經(jīng)”相對的一個(gè)大原則,一方面給予處世應(yīng)事中隨時(shí)而變的活動(dòng)性,讓人們在生活中不會因?yàn)檎軐W(xué)而走極端;另一方面,“權(quán)”與“經(jīng)”之間的張力,特別是“權(quán)”的尺度問題卻是在抽象論說中擺脫不了的說不清道不明的困境,甚至留下重重“潛規(guī)則”生長的空隙。作為內(nèi)在準(zhǔn)繩的“義”,似乎無法成為一種可以外在言說的客觀化尺度。如果更加形象地表述,一端類似于刻舟求劍,另一端類似于見風(fēng)使舵,二者之間怎么把握,是儒家倫理處境中人們?nèi)绾瘟⑸硖幨赖碾y題。這一論說困境不斷地困擾后代儒者,具體就“信”而言:如果守信這件事是可以權(quán)變的,那么作為其尺度“義”究竟如何約束這些可能出現(xiàn)的權(quán)變?
二、“謹(jǐn)之于始”——抽象的解決
在一次“策問”中,朱熹給學(xué)生出過這樣一道考試題:
問:忠信所以進(jìn)德,而夫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其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果”者為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焉。然則學(xué)者將何所蹈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則硁硁之號,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其揚(yáng)榷之。[3]
正如我們在上一節(jié)所展示,到底該不該守信,在《論語》《孟子》文本中似乎出現(xiàn)了一些前后矛盾之處,朱熹考問學(xué)生該如何理解。本節(jié)我們將考察朱熹本人是如何回答這個(gè)問題的。
朱熹對“信”的闡釋集中在對《論語》“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一句的解釋:
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dāng)謹(jǐn)之于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茍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4]73
“言必信”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杜絕虛假言語,另一方面是踐行諾言。朱熹強(qiáng)調(diào)的是“謹(jǐn)之于始而慮其所終”,即從一開頭的言語就要謹(jǐn)慎,他認(rèn)為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diǎn)的話,最后不論是否去踐行都不好。在《四書或問》中,朱熹有更直接的表述:
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于義,二者無一可也。[4]629
由此可見,朱熹堅(jiān)持“信”本身的意義就是踐行其言,并認(rèn)為這種要求是無條件的;不管怎樣,“失信”都是不好的。在朱熹看來,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可不可以不守信”的問題,只是在于最初的言之不慎,避免“言之不慎”的方法是要“慮所終”。朱熹在與人論學(xué)的書信中指出:
“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后言可復(fù),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5]
由以上可知,在這個(gè)問題的解答上,朱熹與康德的確有共通之處,強(qiáng)調(diào)守信具有絕對性,朱熹堅(jiān)持“言而無信”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出現(xiàn)都是不可以的,或者至少是不好的。而朱熹所謂“慮所終”雖然不一定是康德所言的“普遍化”,但也有相通之處,朱熹的“慮所終”強(qiáng)調(diào)的是承諾之前必須考慮最終執(zhí)行諾言時(shí)是否“合義”。因此,對于“信近于義”的“近”字,朱熹給出創(chuàng)造性詮釋,認(rèn)為說“近”就相當(dāng)于說“合”: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6]768
如果會出現(xiàn)不“合義”,一開始就不可給出任何承諾,這樣才能避免“所終”可能會面臨的“二者無一可也”的兩難狀態(tài)。可以看出,朱熹強(qiáng)調(diào)絕對的守信,而這一點(diǎn)先秦儒家學(xué)者們可能并不認(rèn)同,除了上一節(jié)提到的孟、荀的論說,《左傳》中還記載有一段葉公對勝的評論,其中將“信”作出了不同流俗的重新界定: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wèi)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fù)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fù)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左傳·哀公十六年》)[7]1947-1948
葉公認(rèn)為,真正的“信”不是說出去的話就一定兌現(xiàn),就像真正的勇敢不是以卵擊石去送死。正如前文已經(jīng)提到,“復(fù)言”不一定是信,因?yàn)楦鶕?jù)孔門弟子有子的觀點(diǎn),只有“信近于義”的情況下,言才“可復(fù)”。哀公十六年,孔子卒,當(dāng)時(shí)儒學(xué)已經(jīng)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影響力,所以,我們可以推測,葉公對作為德性范疇的“信”以及“勇”給出重新界定,也可能是展示了基于儒家守信觀的一種哲學(xué)解答:將仁、義提到高一層次,對普通人所謂的信、勇進(jìn)行約束,認(rèn)為這樣的“信”和“勇”才是真正的(即具有道德價(jià)值的)信和勇。可是,朱熹并不愿意重新界定,他對此作出如下的評論和解釋:
或曰:然則葉公所云“復(fù)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復(fù)者發(fā),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fù)其言而得之也。今不警其言不盡義之差于前,而責(zé)其必復(fù)其言之失于后,顧與信之所以得者而亂之,則亦矯枉過其直矣。諸家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fù)者,是乃使人不度于義而輕發(fā)其言,以開誕謾欺偽之習(xí),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圣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意也。[4]629
朱熹將葉公的論述看作是有針對性的策略性教誨,但這其實(shí)與《左傳》原文的語境并不合。朱熹認(rèn)為正確的做法是“警其言不盡義之差于前”,非常嚴(yán)厲地批評諸家由此而“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必復(fù)者”的解釋開啟了極大的弊端:欺偽。朱熹對《孟子》中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一段,則是緊緊抓住“大人”二字進(jìn)行調(diào)和和圓場:
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jié),變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遍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個(gè)有不必信處,須著如此。學(xué)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6]775
眾所周知,與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的講法不同,理學(xué)家的思想是具有高度理論體系性的,他們所探討的是可以作為行動(dòng)準(zhǔn)則的條理化的“理”。朱熹所采取的規(guī)則是,嚴(yán)格遵守“言必信”,但將“義”的作用提前,作為承諾與否的判準(zhǔn),而不是履行與否的判準(zhǔn)——這當(dāng)然與孔子所講的“慎于言”是一致的。所以,按照這種標(biāo)準(zhǔn),生活中是不能輕易給人很多承諾的。如果進(jìn)一步嚴(yán)格推衍并且去執(zhí)行,那么朱熹哲學(xué)將會與康德倫理學(xué)一樣,極端的情況是成為一門高度形式主義的倫理學(xué),不具有生活世界的高度實(shí)踐性。當(dāng)然,這只是朱熹守信論說的直接推演,而作為儒家的朱熹絕對不會真的這樣,他會去避免極端情況。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朱熹甚至?xí)谝欢ǔ潭壬戏艞墝φ撜f邏輯上自洽性的追求。
當(dāng)然,并不是每一位理學(xué)家都會選擇朱熹的解決方法,心學(xué)的思想家大概大多不會同意朱熹對“言必信”的遵守。比如,與朱熹截然不同,晚明王學(xué)的周汝登(1547—1629)在其《四書宗旨》中這樣解釋《孟子》這句話:
有意便是必,無必便是義,義亦強(qiáng)名,在亦無所,若有義有在,則非義之義矣,大人勿為。[8]
周汝登顯然是將王學(xué)“四無”下的工夫論思想注入其中,以一種超越對待的論說,進(jìn)行了另外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哲學(xué)闡發(fā),但那最終將可能取消世俗的道德價(jià)值。
三、“要盟不信”——具體的處境
據(jù)說在孔子身上發(fā)生的與守信相關(guān)的一個(gè)最著名的案例便是“蒲人要盟”事件,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茍毋適衛(wèi),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xùn)|門。孔子遂適衛(wèi)。子貢曰:“盟可負(fù)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9]
孔子在這里單方面毀約,不遵守已給出的承諾,給出的理由是“盟”的性質(zhì)為“要盟”。所謂“要盟”,是指一方在另一方要挾之下強(qiáng)迫簽訂盟約,孔子以此為由對此采取不遵守的態(tài)度。北宋理學(xué)家二程兄弟對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所記載的“蒲人要盟”的這段歷史曾表示過質(zhì)疑: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況圣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wèi)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10]16
但在另一處,二程卻也正面提及了這件事: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wèi)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wèi)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10]72
這段話是將“蒲人要盟”作為論述要盟不可用的依據(jù),而末尾的“賣國背君”一語似乎透露出很可能有非常特定的話語背景,即大概會與當(dāng)時(shí)北宋國家政治外交上的“要盟”有關(guān)。而這兩處的截然不同評論,大概是緣于不同的話語場景,這其中正可透露給我們更可能的信息是:也許在二程看來,究竟選擇守信與否,要看當(dāng)時(shí)的具體場合進(jìn)行忖度——大義凜然之下,可以要盟不用。
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對于“要盟”為什么可負(fù),孔子給出的理由是“神不聽”。在春秋時(shí)代的國際外交中,也有人認(rèn)為這樣的盟約是可以不具有約束效應(yīng)的,比如《左傳》記載: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qiáng)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qiáng)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zhì),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左傳·襄公九年》)[7]1006
這里子駟、子展為“背盟”行為辯護(hù)的一大段說辭,可以分為兩個(gè)層面:首先從盟約上去摳字眼來看,并沒有真正的違約;其次才是“要盟可背”的問題。也就是說,“要盟不信”這一條原則也并不能構(gòu)成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理由,因?yàn)檗q護(hù)者第一步的辯護(hù)是試圖論證沒有真正違背盟約內(nèi)容,只有退一步的辯護(hù)理由才是“要盟不信”。與孔子的說法一樣,這里“要盟不信”依據(jù)同樣是“神弗臨”,大概是因?yàn)楣湃恕懊恕钡臅r(shí)候是對天神起誓的,違約會受到來自天神的懲罰。天神作為正義的象征成為了一個(gè)更高的約束力,允許了在聽命于天神的情況下可以違背人間的盟約。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指出了“神臨”與否的依據(jù)和理由“所臨唯信”,并接著對“信”作出了一個(gè)道德價(jià)值判斷上的界定——“言之瑞,善之主”,這當(dāng)然反映出先秦儒學(xué)背景下,將作為原始信仰的人格神向作為“價(jià)值之源”的神的轉(zhuǎn)換。“仁”和“義”作為價(jià)值居于神的地位,具有了神圣性和絕對性,因此才有了“義”之于“信”的優(yōu)先性地位,這樣的“信”(包括在某些情況下的“不信”)方才具有道德價(jià)值。易言之,儒學(xué)中“義”作為一種內(nèi)在尺度,其根源是具有神性的。
有趣的是,北宋蘇轍在《論刺客》一文中,認(rèn)為《史記》對刺客曹沫事跡的記載可疑,他提出的理由有:(一)曹沫是“知義”之人,不該“要盟”;(二)如果真有其事,就應(yīng)該是“要盟”,但《春秋》的記載為“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盟”的“要盟”性質(zhì),不符合《春秋》體例[11]。這當(dāng)然是蘇轍多少有點(diǎn)牽強(qiáng)的反駁,但從中可以看出的是,“要盟”的性質(zhì)判別,以及對“要盟”的態(tài)度是很難一概而論的。可是,究竟何者為“要盟”?如果一切可被視為不平等的盟約都可以廢除而不承擔(dān)的話,那么“普遍化”的結(jié)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要盟”因此甚至可成為“背信棄義”的托辭。在唐代元稹《鶯鶯傳》中,張生始亂而終棄,崔鶯鶯在給張生的信中就說:“如或達(dá)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丑行,以要盟為可欺。”[12]當(dāng)然,這只是崔氏的書信婉辭,拋開其他問題的爭議,以“要盟”為由為不守信的行為辯護(hù),這種用法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同時(shí),我們馬上可以聯(lián)想到,如果反過來是張生給崔鶯鶯的信,“要盟”可能就成為一種被濫用的借口,會產(chǎn)生很大的負(fù)面影響。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面對一個(gè)具體場景、具體事例的處理方式,作為個(gè)案會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如果將其抽象歸納成一條簡單的“準(zhǔn)則”而普遍推行,則可能會出問題,因?yàn)楹芏嗍录木唧w情況會復(fù)雜得多,往往因時(shí)因地而變。
四、結(jié)語
在儒家視野下,“權(quán)”作為一種高度智慧,其依據(jù)是“義”,所謂“義不容辭”,發(fā)源則是“仁”。儒學(xué)中仁、義在一種很寬泛的意義上成為道德價(jià)值的根源,但它們本身并沒有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在宋明理學(xué)的語境下,這種本源是“天理”,所謂“天理難容”。在這個(gè)意義上,理學(xué)家的仁學(xué)即理學(xué)。但是與此同時(shí),儒家倫理要密切落實(shí)到日常生活中,這種落實(shí)表現(xiàn)在與“權(quán)”相關(guān)的問題并不作為抽象而被闡釋和探討,而是具體的場景具體地應(yīng)對,天理、良心等因此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易言之,“權(quán)”是在天理(義)大背景下的隨時(shí)權(quán)變。雖然今天的學(xué)者也可以在一種較弱的意義上通過類型學(xué)的方法從中歸納出若干“類型”[13],可是,“類型”的指導(dǎo)作用是有限的,因?yàn)榫唧w的場景可以有千萬種的不同。因此不難理解,在儒家論說中,“權(quán)”往往被看作是一種很高的智慧。孟子舉了若干事例對“權(quán)”進(jìn)行闡釋,如“嫂溺援之以手”“紾兄之臂而奪食”“逾墻摟處子”等(參見《孟子·離婁上》《告子下》相關(guān)文段)。在每一件具體事例中,基于特定時(shí)空下的文化背景,大多數(shù)是比較容易選擇的,但如果從中歸納出規(guī)則,卻并不那么容易。因?yàn)榍拔囊呀?jīng)提到,在儒家思想中,“義”是具有某種神性的道德約束力,但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儒家傳統(tǒng)的“義”失去了原有的超越性制約,而成為此岸的、現(xiàn)實(shí)的利益考量,“義利之辨”的基礎(chǔ)變得十分岌岌可危。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守信的抽象論說很容易淪為一種游戲規(guī)則,而失去其原來的崇高道德價(jià)值。
另一方面,追求普遍化的哲學(xué)與我們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似乎始終處于一種“不離不雜”的關(guān)系中。比如,在很多情況下,人們說謊了,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謊言,也可能是上文說到的“要盟不信”,但這種事件卻并不會作為一種簡單抽象的規(guī)則通過普遍化而產(chǎn)生惡果,相反,它們還會造成局部的美好和正義,這一種復(fù)雜的微妙,不能用簡單的規(guī)則來概括,因?yàn)槊恳粋€(gè)具體的事例往往有其復(fù)雜的時(shí)空背景。馬克思在對黑格爾哲學(xué)的批判中曾經(jīng)這樣說:“有一種神秘的感覺驅(qū)使哲學(xué)家從抽象思維轉(zhuǎn)向直觀,那就是厭煩,就是對內(nèi)容的渴望。”[14]歷史上儒家學(xué)者們的思考也總是在這抽象思維與內(nèi)容直觀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