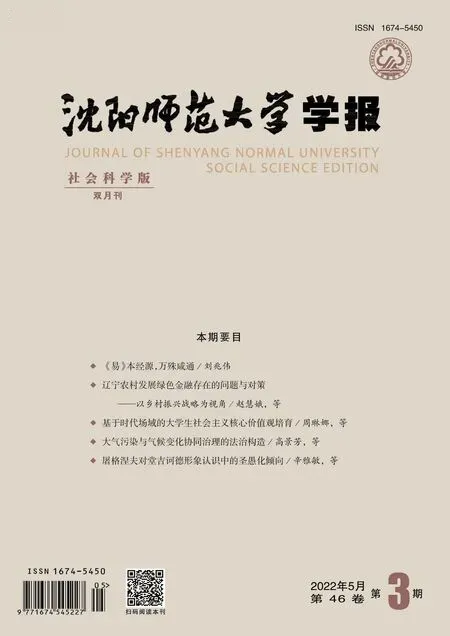屠格涅夫對堂吉訶德形象認識中的圣愚化傾向
辛雅敏,孫愛迪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世界對于堂吉訶德的形象解讀一直處于不斷的變化狀態,自《堂吉訶德》傳入俄國后,俄國評論界對其解讀體現出了不同于世界同時代評論家的特點。之所以產生這種不同,與俄國自身的傳統文化影響密不可分。
一、19 世紀俄國對堂吉訶德形象的闡釋
加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意義從未被其作者的意圖所窮盡,當一部作品從一個文化歷史語境傳到另一個文化歷史語境時,人們可能會從作品中抽出新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許從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時代的作者預見到[1]75。自塞萬提斯創作《堂吉訶德》起,堂吉訶德的形象在其流傳過程中一直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
起初它作為一本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劇讀物被西班牙人民接受。為此,納博科夫在《〈堂吉訶德〉講稿》中說,這部書從本質上仍屬于原始小說的形式,屬于結構松散、雜亂無章、光怪陸離的流浪漢和無賴冒險故事一類,而且最初的讀者就是把它當作這樣的故事來接受、來欣賞的[2]16。在整個16 世紀末17 世紀初西班牙的大環境下,《堂吉訶德》絕非一部嚴肅作品,它包含大量西班牙的俚語、傳說、低俗笑話,更多地被評論家視為喜劇作品。因此,當時的文學界對待《堂吉訶德》這部作品,主要以反面評價為主,并沒有認可其價值。羅德里格斯·馬林曾經考證在《堂吉訶德》誕生之初的西班牙,那時在西班牙的很多城市出現了堂吉訶德的形象,人們視其為喜慶的標志——“堂吉訶德和桑丘、杜爾西內婭一起,出現在眾多的民間喜慶節目中,被人當作逗樂的小丑到處演示”[3]6。同時,因為堂吉訶德的高知名度和其喜劇表現性,17 世紀就已經有不少戲劇作者不同程度地將堂吉訶德搬上舞臺。洛佩·德·維加雖然鄙視塞萬提斯,對《堂吉訶德》更是貶低,但反過來無意中擴大了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的影響。作為西班牙“黃金世紀”的文壇泰斗和戲劇至尊,洛佩在其喜劇《傻夫人》中把女主人公傻夫人比作堂吉訶德,并借人物奧克塔維奧之口評價其只會逗世人發笑[3]8。
相較于16、17、18 世紀的諸多反對聲音,自19 世紀浪漫主義以來,對堂吉訶德形象的描述開始發生了轉變。如大詩人海涅就認為,《堂吉訶德》是崇高與滑稽的完美統一。雖然出現了這樣一些對于堂吉訶德的肯定,但在歐洲堂吉訶德的整體形象依然以滑稽和愚蠢為主。隨著堂吉訶德形象不斷向東傳播,到了19 世紀的俄國,諸多俄國評論家對堂吉訶德形象進行了令之升華的高度評價。從別林斯基開始,俄國對于堂吉訶德這一形象的解讀就富有著不同于時代大潮的氣質。
別林斯基在其有關堂吉訶德的文章中提到,塞萬提斯的小說是一部沒有國界和時間的小說:“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堂吉訶德,但成為堂吉訶德的大多數人都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想象力、充滿愛心的人和一個高尚的人。的確,堂吉訶德只有在杰出的人中才能找到。但重要的是,他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這是一種類型,這是一種始終,根據一個世紀或一個國家的精神和特點,體現在數千種不同的類型和形式中。”[4]137這一想法表明,別林斯基閱讀、評論和詮釋堂吉訶德的方式與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認為堂吉訶德不僅僅是一個喜劇人物,更像是一個小丑的文學評論家是不同的[5]。
繼別林斯基之后,屠格涅夫的演講《哈姆萊特與堂吉訶德》成為堂吉訶德形象轉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正如海涅的評論具有劃時代意義一樣,通過屠格涅夫的評價,堂吉訶德的形象獲得了進一步的升華。屠格涅夫在演講中說:“我們應當承認堂吉訶德精神里有崇高的自我犧牲的因素,只不過表現了它的滑稽的一面罷了。”[6]181堂吉訶德可笑的舉動不再是瘋子的異常行為,反而成為帶有崇高犧牲精神的故作滑稽。“他整個人,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生活在自己之外,活著是為了別人……他身上連一點利己主義的痕跡也沒有,他不關心自己,他整個人都充滿自我犧牲精神——請珍視這個詞!——他有信仰而且堅信不疑,義無返顧。因此,他無所畏懼、不屈不撓,滿足于吃最粗劣的飯食和穿最寒酸的衣服,因為他顧不上這些。他心地溫順,但精神上偉大而勇敢;他息事寧人的虔誠沒有對他的自由形成限制;他雖無虛榮心,但他不懷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懷疑自己的體力;他的意志是百折不回的意志。一心追求同一個目標,使得他的思想有些單調,思維方式有些片面;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他知道他的事業是什么,他為了什么活在世上,這就是主要的知識。”[6]183屠格涅夫的這一觀點得到當時世界上很多評論家的高度認可。福樓拜在1869 年致友人信中說:“每到周末,我總是鐘情于《堂吉訶德》;在它面前我們幾乎全都是矮子。哦上帝,我們覺得自己好渺小!”[3]76席勒在1781年《〈強盜〉序言》中評價,堂吉訶德是“我們所厭棄而喜愛、所驚訝而憐憫的”[7]3。這些評論進一步確立了《堂吉訶德》幾乎無與倫比的經典地位。
總而言之,在屠格涅夫解讀《堂吉訶德》之前,評論界對堂吉訶德的態度有褒有貶,但在屠格涅夫解讀后,19 世紀的評論界對其觀點和聲不斷,整體對堂吉訶德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圣伯夫稱《堂吉訶德》為“人性的圣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評價《堂吉訶德》時說:“全世界沒有比這更崇高和強大的小說了。迄今為止,他是人類思想的最高表征,是人類所能企及的最苦澀的自嘲。”[3]76堂吉訶德儼然成為人類最崇高精神的一種代表,整個世界在重新閱讀和領悟堂吉訶德,堂吉訶德對騎士道的瘋狂迷戀和求而不得被隱喻為整個人類的命運悲劇。通過這一系列的轉變,我們不難發現,屠格涅夫在堂吉訶德的形象批評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是什么原因促使屠格涅夫對堂吉訶德的形象得出與之前研究主流相左的全新闡釋呢?這顯然與俄國的歷史文化語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屠格涅夫等俄國評論家之所以對堂吉訶德另眼相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在閱讀《堂吉訶德》時所帶入的視角不同。這一視角的代入,受到俄國傳統圣愚文化的深刻影響,使得堂吉訶德的形象在屠格涅夫等俄國評論家眼里發生了巨大變化,被抬高美化,甚至賦予圣性。屠格涅夫在評價堂吉訶德這一形象過程中所產生的全新感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俄國傳統圣愚形象的影響,更因為堂吉訶德的形象本身就與圣愚有著諸多相似之處,才使得其在俄國評論界獲得高度贊揚。
二、屠格涅夫對于堂吉訶德形象的再認識
屠格涅夫于1860 年1 月在為清貧文學家和學者賑濟會集資而舉辦的公開講座上,發表了上述名為《哈姆萊特與堂吉訶德》的演講。在這一次的演講中屠格涅夫對堂吉訶德形象所作出的新的解釋是在他與赫爾岑的論戰中產生的。赫爾岑在《來自彼岸》一書中回憶1848年垮臺的革命的活動家時,將他們諷刺為可笑的堂吉訶德。屠格涅夫認為,赫爾岑貶低了堂吉訶德的形象,因此撰寫這篇演講稿并在其中強調堂吉訶德的英雄主義因素,把堂吉訶德看成是一個戰士和革命者。
屠格涅夫在整篇演講中,對堂吉訶德的形象進行了新的界定,他提出:“堂吉訶德整個人充滿著對理想的忠誠,為了理想,他準備經受各種艱難困苦,犧牲生命。”[6]182屠格涅夫認為,堂吉訶德對待其信仰的態度是義無反顧且堅信不疑的,“他無所畏懼,不屈不撓,滿足于吃最粗劣的飯食和穿最寒酸的衣服,因為他顧不上這些……他的道德觀念的堅固性(請注意,這個發瘋的游俠騎士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使得他的所有見解和言論,使得他整個人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顯得特別有氣魄,雖然他不斷地陷入滑稽可笑和受屈辱的境況之中”[6]183。這些解讀都跳出了傳統評論家對于堂吉訶德形象的固化認識,堂吉訶德不再僅僅是一個瘋瘋癲癲的丑角騎士,所收到的也不再是人們的可憐和同情。屠格涅夫使堂吉訶德成為了一面精神上的旗幟,他對騎士道的癡迷也逐漸被提升為對信仰的篤信和執著。
同為俄國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認同屠格涅夫那篇演講稿(即《哈姆萊特與堂吉訶德》),文中的理念在他本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痕跡,也體現在他將自我犧牲的堂吉訶德式形象投射到梅什金公爵身上。屠格涅夫的名作被證明是對堂吉訶德這個有信仰之人的頌歌,并且堂吉訶德被一個超過他自身能力的理想所鼓舞(即便可笑地受到欺騙)。為了不讓自己的分類所暗示的東西留下任何疑問,屠格涅夫提到了空想社會主義者夏爾·傅立葉,把他作為堂吉訶德類型的例證[8]323-325。這充分表明,正如俄國傳統圣愚們做出種種怪異的舉動以求精神上的自我提升一樣,堂吉訶德似乎也在荒誕怪異的舉動中向世人宣揚著他的騎士道。由此可見,屠格涅夫對堂吉訶德的別樣解讀并不是空穴來風。
歐洲傳統文化對待瘋癲者并不持一種肯定態度,他們認為瘋癲是一種理性的缺失,是一種脫離上帝的行為。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說:“自中世紀初以來,歐洲人與他們不加區分的稱之為瘋癲、癡呆或精神錯亂的東西有某種關系。”[9]3歐洲一些國家自中世紀起就開始興建精神病院,失去理性者被剝奪社會權利、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受到討伐。而俄國對于愚者和瘋子的態度卻截然相反,他們對這些難以琢磨的對象懷有高度的敬重心理,認為這些愚者的舉動是對世俗肉身的貶斥,是追求高度精神境界的途徑,認為這些人是靠近于上帝的圣者。堂吉訶德在歐洲傳播的過程中,一直在相當程度上被視為一個瘋子或小丑,這一先決視角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很多歐洲的評論家無法將堂吉訶德與自我犧牲從而獻身信仰的高大形象聯系起來。然而,當堂吉訶德傳入俄國后,他所謂的瘋狂舉動恰恰符合俄國對于圣愚的傳統肯定,觸動了俄國作家評論家對于瘋癲這一概念的敏感性,這也就導致了俄國評論家對于堂吉訶德的同情與贊美。
屠格涅夫作為俄國作家,雖然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卻創作出了許多“神秘小說”,如《奇怪的故事》中本身就塑造了帶有圣愚和圣徒意味的人物,代表作《羅亭》中對于羅亭的塑造也富有傳統圣愚的漂泊無根性,而羅亭本身就被稱為“俄國的堂吉訶德”。這足見圣愚傳統對于屠格涅夫的深刻影響,同時其也樂于用圣愚這一文化形象對文學人物進行創作和理解。
因此,屠格涅夫在反對他人對堂吉訶德形象進行傳統界定時引入圣愚性的解讀并不意外。當認真解讀屠格涅夫對于堂吉訶德的整體理解時,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的豐富圣愚因素。屠格涅夫在解讀堂吉訶德時認為,堂吉訶德本身首先表現的就是信仰,“對某種永恒的、不可動搖的東西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一句話,對那種處于個人之外的真理的信仰”[6]182。屠格涅夫之前的評論家對堂吉訶德的贊美多集中于對騎士道的堅定追求,并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哪怕是別林斯基也仍舊是從騎士道的角度對堂吉訶德進行解讀的。“別林斯基開創了俄國文學批評的傳統,認為堂吉訶德主要是一個騎士的思想,俄國文學評論家已經習慣于這樣稱呼堂吉訶德。”[5]但是,屠格涅夫對堂吉訶德的解讀顯然進行了進一步的提升,他認為堂吉訶德的犧牲精神是一種“為它(真理)服務時持之以恒并且做出大的犧牲”[6]182,將自我的犧牲歸結到“為了信仰和真理的付出”上去,是符合俄國對于圣愚定義的。
屠格涅夫認為,堂吉訶德并非真的瘋子,只是看起來讓人覺得他是瘋子而已。其與世人之間的鴻溝主要在于,世人對其行為的難以理解,以至于他的行為被世人怪化為瘋子行徑。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堂吉訶德卻保持著難得的堅定和不可動搖——“他不大容易產生共鳴,也不大會進行欣賞;但是他像一棵千年的古樹,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既不能改變自己的信念,又不能把思想從一件事情轉移到另一件事情上”[6]183。這種飽藏于瘋狂外在下的虔誠,也與圣愚不謀而合。
屠格涅夫對于堂吉訶德形象的分析,獲得了很多與他處于相同文化環境下的俄國作家、評論家的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受堂吉訶德影響創作出了白癡——梅什金這一富有極其典型圣愚氣質的文學形象。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長篇小說(指《白癡》)的主要思想是描繪一個絕對美好的人物……在基督教文學的美好人物中,堂吉訶德是最完整的一個。但他之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時滑稽又可笑。”[10]188這些對于堂吉訶德的進一步理解和塑造,表明了堂吉訶德在屠格涅夫等俄國文學家視角里的群體想象。他的瘋狂行徑和他因此承受的苦痛,以及他堅定不改的追尋之心,深深地打動了俄國學者,并使他們將其與本國的圣愚形象逐漸聯系起來。
堂吉訶德之所以在俄國得到迥異于歐洲的解讀與發展,并不僅僅因為俄國評論家對于瘋癲者這一形象的敏感性,更因為堂吉訶德與俄國傳統圣愚形象本身就具有很多相似性。
三、俄國傳統圣愚形象與堂吉訶德的相似性
圣愚是俄國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直譯為“為了基督的癡愚”。本質上是東正教背景下一種特殊的苦修者,大多是一些行為怪異、瘋瘋癲癲、滿口胡話的乞丐或是流浪漢。與傳統基督教對待瘋子的態度不同,俄國從上層貴族到下層農民都對這些怪異者異常尊敬,認為他們超脫肉體的痛苦而錘煉自我的精神,奉他們說的話為預言,甚至在俄國有過多次大型的圣愚封圣活動。
圣愚之所以在俄國備受尊崇,與其傳統影響密不可分,湯普遜在《理解俄國:俄國文化中的圣愚》中提出:“在俄國圣愚現象中,有兩種傳統匯合為一:異教傳統和基督教傳統,從而大大促成了俄國的雙重信仰。圣愚的某些傳統特征來源于基督教,另外一些特征來源于薩滿教。隨著時間的推移,俄國教會對于區分兩種來源的意識逐漸消失,但是這樣一種現象卻保存了下來。”[11]22
俄國傳統文化中的圣愚形象隨著年代的不同曾多次發生細小的轉變,但是其主體形象依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其外在形象主要表現為對肉體的摒棄和自我折磨,一些圣愚會在身上佩戴沉重的鐵器,并且故意做出引人發笑的舉動,甚至主動惹怒他人對自己進行侮辱和迫害。而其內在則表現為對于信仰的絕對尊崇。從這些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堂吉訶德與圣愚形象之間有著極多的相似性,因此才會被俄國評論家以一種近似圣愚的角度進行解讀。
首先,堂吉訶德的精神狀態與圣愚們多有相似。堂吉訶德一直被稱為“癲狂的騎士”,在塞萬提斯筆下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被騎士道迷昏了頭的怪人。他懷揣著不合時宜的夢想,喊著陳舊的口號,衣著打扮也十分稀奇古怪,迥異于常人。他身材消瘦、高個子,身著一件破爛盔甲,手執一柄長矛,騎一匹駑馬,說著一些難以理解的胡言亂語。旁觀者可能一開始會因其怪異而略感恐懼,不過很快就會對他的癡愚大肆嘲笑和捉弄,把他當成一個傻子。
然而,實際上的堂吉訶德不止一次在書中的片段描述里展現出他過人的智慧和見解。“他穿著綠色羊毛背心,戴著托萊多式的紅色睡帽,又干又瘦,坐在床上活像一個木乃伊。他向兩人表示了歡迎,兩人問他身體如何,他講了自己的情況和身體,思路清晰言辭文雅。閑聊之際,三人談起國內時政和治國之道,什么弊端應該譴責和革除,什么風氣應該改革和取消,儼然成了新上任的立法官,當代的來古格士,再世的梭倫……在談到的所有問題上堂吉訶德都談得合情合理,切中要害。”[12]1這樣的堂吉訶德讓人不由得懷疑,他在外旅行時的一言一行是否是一種偽裝,而非其本來面目。堂吉訶德似乎在病弱的學者和瘋狂的騎士病患者間反復跳躍,這種表現令人迷惑。
堂吉訶德這種時而清醒、時而昏聵的形象與圣愚如出一轍,我們不難發現,其所作所為看似癡傻可笑,但卻無一不是在維護他所篤信和渴望恢復的騎士道。他呵斥鞭打男孩的農夫,釋放被押送的犯人,為多洛苔婭小姐報仇等行為,雖然多以可笑的結局收場,但其出發點確實符合堂吉訶德口中的真正的騎士行徑,這也恰恰證實了堂吉訶德的正道性。這種對騎士道的內在信仰和其自身荒誕不羈的外在表現與圣愚高度相似。
其次,堂吉訶德的外在打扮和行為舉止,符合俄國傳統文化對圣愚的界定。俄國圣愚會在身上披掛一些破銅爛鐵,早期圣愚一絲不掛、赤身裸體。到了中晚期,圣愚雖然會穿一些破衣爛衫,但大多衣不蔽體,盡力使自己的穿著打扮異于眾人。堂吉訶德的騎士裝扮明顯與他所處的世界格格不入——戴著借來的頭盔,穿著生銹的盔甲,騎著駑馬。無論怎樣也不能將其與光輝的騎士聯系在一起,但是他確實是全書中最富有騎士精神的人。外在形象的落魄卻無法掩飾他內心對騎士道的純澈追求,也契合俄國那些看起來瘋癲癡狂卻永遠心懷上帝的圣愚形象。
同時,堂吉訶德的瘋狂舉動和胡言亂語符合圣愚所謂的“第二視力”。“第二視力”是指圣愚們可以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事物,他們會因此說出一些令人費解的語言,但這也恰恰是他們高于常人的證明。堂吉訶德沖進山羊群、與風車搏斗、劈砍酒袋,最終的結局是頭破血流,毫無收獲。這些看起來出自一個瘋狂者的舉動也被賦予了另一種解讀方式,“沒有人認可一個瘋子的思想,大家看到的只是這個世界赤裸裸的現實。這個世界沒有魔鬼,只有風車;這個世界沒有強盜,只有羊群;這個世界沒有城堡,只有旅店;第一視力成為人衡量世界的唯一標準。可憐堂吉訶德至死才明白這個道理,原來他只不過是個瘋子”[13]。堂吉訶德以悲劇收場的壯舉恰如圣愚們降格生而為人的尊嚴來接近上帝卻不被他人所理解的行為。
正是由于堂吉訶德身上這些讓人很容易就與圣愚聯系起來的特質,他在屠格涅夫等俄國評論家的觀念里才不再止步于單純的瘋子形象。如果將堂吉訶德瘋瘋癲癲的舉止理解為其故意為之,且目的是為了正道,那么他的確可以被勾畫為一個胸懷大道、警醒世人之人,也正是這種理解的產生讓堂吉訶德的形象發生了變化。
四、結語
19 世紀堂吉訶德形象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有了巨大的轉變,與俄國評論家們對其形象的全新解讀密不可分。以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俄國評論家更是將堂吉訶德的形象提升到信仰追求者的高度。這一形象的解讀實際上充分受到俄國東正教傳統的影響,俄國評論家對瘋癲的敏感和不同于歐洲的別樣理解,促使他們將堂吉訶德與本國傳統形象——圣愚逐漸聯系在一起。自屠格涅夫解讀堂吉訶德伊始,其對堂吉訶德的認識中便富有俄國圣愚特性,而堂吉訶德自身的行為舉動,也與圣愚有諸多相似之處。兩相結合之下,誕生了對于堂吉訶德的全新解讀,推動了《堂吉訶德》的經典化進程,進而影響了世界對堂吉訶德形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