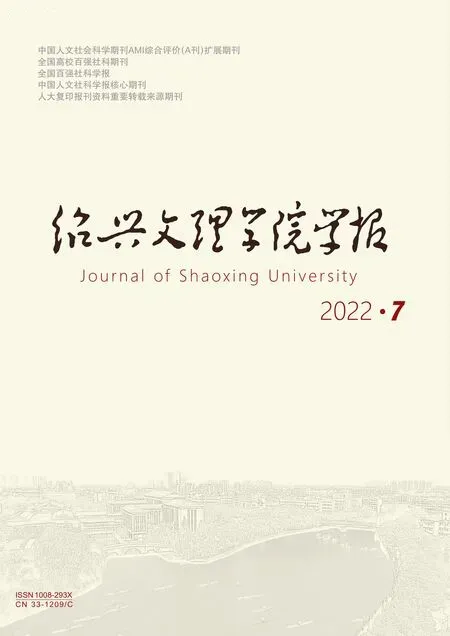海子詩歌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接受與偏離
應道天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一、引言
“丑”是一種具有與“美”相對之內涵的事物屬性。隨著人類理性的發展,美丑關系的流變歷程逐步衍化為“美學史”或“丑學史”。最初,古希臘人不自覺地運用前邏輯思維方式所塑造的與感性直接相關的神,實現了對感性生活的神圣化,并將“美”推至感性世界的超越地位[1]30。而“丑”的地位被壓抑,不被接受進入藝術,例如萊辛認為“丑”的存在是為了引起“可笑性和可怖性所伴隨的情感”,且“在缺乏純然愉快的情感時,詩人就須利用這種混合的情感,來供我們娛樂”[2]143,這種顯著的目的性證明了“丑”僅處于依附“美”甚至可被“美”舍棄的地位。因此“美就是古代藝術家的法律,他們在表現痛苦中避免丑”[2]12成為難以逾越的古典審美鐵律,直到弗洛伊德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出現并產生大規模影響,“審丑”才作為一種對18世紀理性主義的反撥被賦予了理論化的自覺意識。
西方丑學于19世紀末勃興,法國象征主義先驅波德萊爾滋養了一朵殘酷而美艷的“惡之花”,“病態”則作為其創作的首要特征和“丑”的重要類型之一,通過人的生理、事物的表象等外在的異化、殘損或衰亡,展現人的心理、事物的本質等內在的破壞、缺失或傾覆。波德萊爾把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病態稱為“美”,又對其進行無情的揭露與批判的做法看似矛盾,實際上是為了顛覆和超越傳統大眾審美,塑造別具一格的“病態審美”:第一,在藝術追求上,以病態的“丑”替代“美”的純粹形式,張揚“唯美”精神,排斥虛偽;第二,在風格呈現上,秉承現實主義精神,以現實本質的病態加強藝術表現的病態;第三,在創作手法上,通過象征手法將丑的意義與形式相連,呈現“惡的特殊美”[3]。
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興起是美學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標志性事件,它對后世藝術風格的影響頗為巨大。值得關注的是,學界關于我國當代詩人海子創作的國外淵源研究已成體系,成果集中于蘭波、荷爾德林以及愛倫·坡等人對海子的影響,鮮有注意到波德萊爾美學風格與海子詩歌的聯系。實際上,海子創作中體現的“病態美”(或稱“惡美”)深受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影響,而且又在接受過程中出現了偏離,向中國傳統審美理念回歸。這一現象蘊含著豐富的跨文化研究意義,對中國當代詩歌發展譜系的再認識具有重要價值。
二、海子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接受
(一)以“真”為指歸的“審丑”取向
在波德萊爾對“現代美”的理解中,至少包含著三種可以表現現代英雄之美的要素:激情、現代精神與道德訴求[4],即波德萊爾認為詩歌可以通過激情的生命體驗,直面丑陋的精神力量以及藝術所展現出的“詩性正義”,抵達“真”的境界。在詩人“發掘惡中之美”的要求下,“審丑”不僅打破了“審美客體是否符合人類視覺審美習慣”的美學標準,而且超越了“審美主體是否尊重審美對象的真實性”的道德約束,其所展現的是契合波德萊爾“現代性”追求的藝術之“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兩位詩人的美學追求產生了共鳴。通過對西方文學作品的大量閱讀和深入理解,海子感知到了潛藏在中西不同審美態度之下的共識——“真”,由此成為少數能夠接受西方丑學對中國詩歌創作的影響并將其納入寫作范疇之中的中國詩人。
海子曾為波德萊爾獻詩《公爵的私生女——給波德萊爾》[5]368,用詩歌表達了他對波德萊爾的認同和接受。這一方面證明了波德萊爾影響海子詩歌創作的事實聯系,另一方面體現出“獻詩”作為研究資源在文本內容與藝術形式兩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從藝術風格來看,此詩氣氛陰暗,意象晦澀,可謂是對《惡之花》幽冥深邃的病態風格的直接模仿。從詩歌內容來看,詩尾處海子稱波德萊爾是“石頭門外,守夜人”,將波德萊爾置于某種詩學變化的臨界處,呼應了波德萊爾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從文學發展進程上來看,波德萊爾代表了象征主義的勃發;從美學觀轉變的角度來看,波德萊爾延續了雨果與愛倫·坡“以丑為美”的“丑學”思想,進一步將“以丑化美”的“審丑”觀納入表現“現代美”的藝術化過程之中。
在獻詩中,海子敏銳地捕捉到了波德萊爾以“真”為指歸的“審丑”取向。“我們的生存/唯一的遭遇是一首詩/一首詩是一個被謀殺的生日”一句,混雜了海子所理解的人類面對詩性之“真”時產生的復雜心態。出生之日被謀殺,或者在死亡之日誕生,看似離奇詭異,卻是對人類陷入困頓時絕望心理的真實寫照,傳遞出作者本人對詩歌“審丑”價值的認識:“審丑”不僅能夠幫助詩歌創作掙脫形式上的束縛,同時也潛藏著突破常規,求變求新,進而求真的精神追求,這正是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詩人所需要的。正如羅丹所言:“在美與丑的結合中,結果總是美得到勝利,由于一種神圣的規律,‘自然’常常趨向完美,不斷求完美!”[6]61在現代社會中,“真”多以無常、瞬變、偶發的“丑”的表象出現,“審丑”卻能夠從中發掘出潛藏的生命之“美”。波德萊爾“以丑化美”的藝術辯證法賦予了詩歌更深刻的內涵,為海子創造了一個嶄新奇異卻不失真實的審美世界。
(二)死亡書寫中的反抗意識
在西方基督教原罪思想與資本主義人性異化的雙層重壓下,波德萊爾的叛逆精神直抵19世紀的巔峰。詩人的死亡書寫一方面通過營造死亡場面的陰郁氣氛,影射現實的墮落風氣;另一方面又通過描寫“自殺”,直接與基督教信條相對立,流露出個體對生命存在的迷茫與不安。例如《快樂的死者》[7]168刻畫了一個寧死也不愿“苦苦地哀求世人的淚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被現世煩惱侵擾的“我”的眼中,死者是懂得“享樂的哲學家”,擺脫了塵世的一切煎熬悔恨,“可還能受什么折磨?”為何人只剩下軀殼反而比有靈魂快樂?為何死去反而比活著幸福?對這種病態處境的審視和思考構成了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內在悖論和價值所在。可見波德萊爾的生命哲學是陰郁的,卻并不是完全消極的,生死困境帶來的詩歌張力進一步凸顯出詩人以死反抗丑惡現實的叛逆精神:不憑借延續“生”來反抗活著才能觸碰到的現實,反而要利用“死”進行批判與揭露,從而實現徹底的顛覆。
由于有著與波德萊爾相似的生命經歷,中國詩人海子接受了復雜深刻的死亡命題。不圓滿的家庭生活、慘痛失敗的愛情,以及文學追求的不被欣賞與理解,兩人各自咽下了孤獨與憂郁,并開始把視線置于解脫一切痛苦的“死亡”之上,海子甚至最終以自殺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對此,古大勇先生說:海子自殺在本質上應屬于西方的自殺譜系,即屬于非政治性自殺[8]。實際上,相較于同時代的中國詩人,海子精神世界的西化傾向更加明顯,對“死亡”的理解更加深刻地受到了西方死亡敘事藝術的影響。例如《死亡之詩(之一)》[5]158和《死亡之詩(之二:采摘葵花)》[5]160體現了海子對西方藝術家筆下的死亡主題與死亡意象的接受,以及詩人借助死亡的敞開追尋詩歌力量與美感的嘗試。詩人筆下的死亡狀態隱藏著一種非理性的力量,蠻橫地昭示著自身的強力意志,且不受自我和外界的任何約束,以混雜為一體的生死激情對抗著一切,這都與海子所傾慕的“原始力量”相契合,反映出詩人對自由的向往和對精神困境的反抗。
(三)城市“審丑”意象
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其靈魂是病態審美觀,而各種“審丑”意象的組合與對峙構筑了詩歌的實體,最能映射出作者的創作理念與生活態度。波德萊爾早期生活放浪,混跡于各色階層,后來他把他的真實生活經歷用各式各樣丑陋恐怖、骯臟血腥的意象記錄下來,從此打開了文學“審丑”的新紀元。巴黎是詩人的主戰場,在藥物與性的刺激下,波德萊爾極度憂郁的心境投射到城市風貌上,不僅扭曲了城市真實存在的美麗,也放大了城市不容忽視的丑陋,進而產生了寄居于詩人幻想中的城市病態意象。可見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與膨脹是波德萊爾創作的重要產生條件,城市文明在昭告新時代來臨的同時也摧殘著人類自然淳樸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情感,因此成為“丑”的代名詞,而海子對這種理念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海子生長于農村,十五歲到北京讀書時才真正接觸到城市文明,城市文明卻給這位“鄉村知識分子”(西川語)留下了孤獨憂郁的印象與愛情、事業皆不順遂的痛苦回憶。因此,城鄉對立這一社會難題便隱秘地潛入了海子的病態審美意識之中。在20世紀的中國,城市文明、工業經濟的興起以及鄉村文明、農業生產的退場,成為無法遏制的歷史潮流。然而海子的創作是特殊的,他的詩歌使中國現當代詩歌的鄉土抒寫再次回到文明意義上的城鄉對立這一現代化社會背景中,同時突顯出城鄉文化沖突下無法避免的個人苦難。如出現在《麥地》[5]119一詩中“窮人和富人”“紐約和耶路撒冷”等各種相互對立的意象,正是生長于鄉土文化的中國詩歌進入20世紀后與西方城市文明結合的產物。此外,海子的這種創作傾向同時反映出詩人受到西方丑學與城市文明影響后在面對鄉土自然時的內心矛盾,一種由沖突、對話與和解所組成的悲劇循環。例如《麥地與詩人》[5]413中的“你不能說我一無所有/你不能說我兩手空空”,表現的正是詩人面對窘迫的真實生活情形所產生的恐懼與無力,城市文明不僅帶給海子具體實在的困頓,也引發了詩人抽象的精神迷惘。由此可見,傳統農業文明被城市文明擠占碾壓的悲劇,加劇了詩人內心的痛苦折磨,滋養了海子創作中的病態審美觀念。
三、海子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偏離
(一)對“審丑”功利性的揚棄
海子與波德萊爾的“審丑”態度皆以“真”為指歸,然而兩人對如何在詩歌中表達“真”抱有不同的態度。波德萊爾的立場是強硬而激進的,他運用極端病態血腥的“丑”反襯已消逝之“美”的偉大,以詩人的個體生命激情、時代先鋒性精神與道德批判目的,深刻貫徹了對真實的藝術追求。然而,波德萊爾雖由此受到舉世矚目,但也蒙受了不少質疑與非難,他的創作一度因“有傷風化和妨礙道德”而被查禁,晚年的落魄生活也與其文藝思想遭受學界冷遇有關。海子在獻詩中表達了對異鄉詩人所處的生命困境的認識:既稱波德萊爾的偉大如“抱著三枝火焰”驅散黑暗,拓寬前路,又料見詩人的寂寞與隔絕將使其“埋下雙眼,一夜長眠”。這種既向往又畏懼的矛盾態度使海子在接受波德萊爾“以丑化美”的病態美學觀時留下余白,形成了與前者同中存異的“病態美”。
波德萊爾詩歌中的“審丑”,其目的是追求唯美以及揭露與批判,從而達到“真”的最高境界,并強調道德訴求對于“現代美”的重要性。對此,海子選擇了淡化詩歌的社會道德功能,側重于詩歌的精神升華作用,給予“實體”表達與傾訴的機會,使其直面自我的真實:“詩提醒你,這是實體——你在實體中生活——你應回到自身。”[5]1018因此,海子在創作中有意識地排除了外界強加于詩歌的目的性,比如對“審丑”功利性的揚棄。海子并不為了實現“真”而創造“丑”,而是通過詩歌抒發主體對美丑的直接感受,重新發現生活中本就存在卻難以正視的丑陋,還原“詩是實體在傾訴”[5]1018的狀態,從而靈活協調“病態美”和與之對應的“常態美”的關系,創造理想主義的精神家園。
海子的組詩《給母親》[5]107,不僅表現出受西方“丑學”影響的“病態美”風格,也傳達出詩人對回歸傳統和諧的“常態美”的追求。“母親”在海子的詩歌中多以受難者的形象出現,生活的折磨以及疾病與衰老催促著她走向丑陋。然而,母親并沒有化作波德萊爾詩中的女尸,表現出憂郁悲傷、充滿戾氣的一面。面對既定的死亡,親情的守候和堅忍的品性使她成為美的化身。此時的母親形象脫離了藝術虛構帶來的震撼力,僅以“水”“果實”和“小小的風”的姿態展現出“常態美”,將西方古典美學的突出特點與本詩相貫通:即使悲劇性沖突中皆是苦難、災禍、蹂躪、瀕死,也絕不流露出恐懼與哀絕。海子通過協調母性之美的病態與常態,實現了個人詩歌創作中的“化丑為美”。
(二)犧牲、復活與再生的輪回
與波德萊爾暗示性的死亡主題不同,海子筆下的死亡更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其所體現的病態美營造出超越時空界限的悲劇氛圍,并投射到人性與神性對立統一的思辨之中。一方面,海子接受了波德萊爾在死亡書寫中源自生命個體的病態自毀意識和反抗意識,把“生”當作“死”的過渡;另一方面,根源于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的民族自新意識將海子的死亡意識升華為富有中國文化色彩的“犧牲”崇拜,把“死”看作是“生”的啟程,從而形成了接受上的偏離。另外,海子筆下的“犧牲”主動要求死亡更有價值、回報和意義,因此海子在書寫死亡的過程中同時也強調“復活”與“再生”。與在西方文化中被認作神跡的復活不同,在中國文化中,依靠個人意志的錘煉、覺醒與更新即可達到圣人的精神境界,超越對死亡的恐懼,實現非肉體層面的新生。
人是大自然的產物,走向死亡是顛撲不破的自然法則,海子秉承著對自然的原始信仰,將人性的復活與自然中的生命輪回融合為一體,海子詩歌中出現的“斷頭”意象即是死后復活的象征。邵寧寧先生認為,斷截的頭顱不僅是農作物梢端最早成熟、最先掉落的果實,也是在春季播撒的種子,這體現了以農耕作物之死作為新生之開端的神話生命觀[9]。舊的“我”埋入土里死亡,等待再次煥發出新生,從而以死的形式表達了生命的延續與更新,并迎接自然生命的下一次循環。海子在《復活之二:黑色的復活》[5]259開篇就發出質問:“熄滅有什么不好”,熄滅(即死亡)換來的是盛大的復活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生。詩中“我繼承黃土/我咽下黑土/我吐出玉米”,塑造的是民族的“大我”形象,而個人在“大我”之中既經歷著死亡也踐行著再生,這同樣屬于典型的“死亡——再生”的生殖神話原型,體現了海子的自然生死輪回觀。
不難發現,面對更宏大的集體,海子筆下的死亡雖然仍舊殘忍、恐怖,卻不再裹挾著暴虐與絕望的反抗情緒,反而體現出一種個體屈服于群體的受難病態。個體沉痛卻馴順地匯入生死的集體大循環之中,死亡便成為“生”的機械環節和刻板義務,這種無法超脫生死的壓抑感難免加重了詩人的自殺情結。詩人的絕筆詩《春天,十個海子》[5]540中,死去的、光明的“一群”嘲笑茍活的、野蠻的“一個”,這是詩人心靈極度受苦的寫照,在這種痛苦中,唯有死亡才能把個人的苦難推向高潮,從而實現所有靈魂的復活。這種獨特的生死觀,已經超越了海子對個人死亡的囿見,上升到了思索整個漢民族、整個人類群體之生存境遇的高度。
(三)鄉村——自然“審丑”意象
師承西方象征主義,同時又接受了中國現代新詩影響的海子,他的筆下不乏與波德萊爾創作類似的病態意象,它們承擔著相似的病態美學觀念,卻具有不同的意象類型和特征:海子詩歌中幾乎沒有城市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遠離現代社會的偏僻農村與人跡罕至的自然野性。海子的偏好是有跡可循的:一方面,海子對鄉村與自然有著與生俱來的情感,正如西川所言:“他在詩歌里多次運用農村的意象,描寫農村的生活。他的靈感來自他對這片土地的記憶和熱愛。”[10]另一方面,海子在城市文明中所遭受的痛苦經歷,印證了他稱作“不幸的兄弟”的荷爾德林的觀點,加劇了詩人的“鄉村情結”:現代文明是欲望深淵,神性棲居在自然當中,對于都市來說農民只是“擅闖者”和“丑陋的釀造者”[5]336。
在文學作品多描寫現代化建設的大時代背景下,海子力求用大自然最純真的美表現人性美,同時也用大自然最真實的丑表現個體極度矛盾的心態,以自然的一體兩面關照人性的多樣復雜。海子所追求的是更遠大的創作目標與理想抱負:創造一個能夠接納矛盾雙面性的完整詩性世界,那里既有麥浪滾滾的富饒景象,也有麥子割完后的一片荒涼。《重建家園》[5]415一詩展現了詩人對如何建設理想世界的深刻構想。詩中,作者一方面提出要“放棄沉思與智慧”等機械理性的束縛,脫離歷史施與個體的重負,“讓大地自己呈現”生存的本真,從而實現“美”的救贖;另一方面認為應“保持緘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不必隱藏心靈中病態的一面,接納它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從而發揮“丑”的力量。如此雙管齊下,方能實現詩人“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的設想。因此,在過濾了西方象征主義中過于消極與反動的部分后,海子詩歌中的病態鄉村自然的“審丑”意象在中國新時代文化中找到了生長點。
海子詩歌中的三大自然意象——象征家園的大地,象征自我的鄉村與象征無限的草原,皆在詩人筆下展露出病態之美。“大地”常以病變的姿態出現,詩人借此控訴了人類的傲慢與無知,在《土地·憂郁·死亡》[5]352中,人類的血污染了大地家園,殘害了地上的生靈,當“最后的晚餐端到我們面前”時,人類才發現走向終結的是人類自己。“鄉村”承載了詩人大部分的生命體驗,詩中既有“蘆花叢中/村莊是一只白色的船”[5]39的寧靜悠哉,也有“巨日消隱,泥沙相合,狂風奔起”[5]76的愛情悲劇,還有“兩座村莊隔河而睡/海子的村莊睡得更沉”[5]324的孤獨無助,各種個人情感在此失去了明顯界限,再經過詩人無限放大和投射,極易形成喪失自我控制的心靈病態,展露出海子真實的困頓心境。“草原”是詩人心中的幻想鄉,包含著無限的自由和悲傷,然而面對宏大的無限,孤獨的個體只能望而卻步,顯得愈發渺小。《九月》[5]205一詩基調極度哀沉,體現了有限之個人與無限之世界的永恒矛盾,而詩尾“只身打馬過草原”一句又展現出面對死亡的勇氣和微弱卻帶來希望的人性之光。可見,海子詩歌中的審丑意象掙脫了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中追求“現代性”的要求,詩人重返鄉村與自然尋找人性之根,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描述中國、想象中國乃至想象世界的方法”[10],以詩性叩問著中華民族的靈魂。
四、海子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偏離之成因
首先,其他西方詩人的審美觀與哲學思想對海子產生了較大影響,以至于削弱了海子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接受效果。例如,葉賽寧的自然詩審美思想將海子的創作進一步引向了對青春、真實、質樸、平凡之美的追尋,激化了詩人的“大地”情懷,然而卻與波德萊爾以丑陋恐怖的都市社會為主體的病態審美直接對立。再者,波德萊爾的病態審美觀立足于以揭露與批判為手段的“摧毀”,海子卻在受到蘭波(韓波)的流浪經歷、荷爾德林的溯源意識,以及尼采等人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啟發后走得更遠,立志“重建”家園,用詩歌和生命追尋生存的本質,追尋人類以及自我的精神故鄉。由此可見,不斷變化的現實所賦予詩人的社會責任隨著人類精神的進一步發展而更加深遠,因此海子不可能僅遵循著“審丑”之路踐行他的詩歌目標,他必須兼容各家所長,經歷無數次嘗試和磨礪,才能成就“王在寫詩”[11]的理想狀態。
其次,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海子對波德萊爾病態審美觀的偏離,主要體現在海子的死亡觀上。海子意識中的“死”是一種包含著新生的“犧牲”,源于以舍身取義的“殉道”精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而在中國歷代詩人中,將生命意識和士大夫精神結合得最顯著的便是屈原,海子詩歌便體現出了作者對屈原的死亡崇拜。《水抱屈原》[5]357的詩題表現出詩人對屈原投汨羅江自盡的態度:水不會淹沒屈原,而會溫柔地環抱著他。海子對屈原的自戕方式與行為產生了極端浪漫的幻想,因此通過詩歌思考了知識分子之死與道德責任的關系,展露出海子對死亡意義的詩性探尋:“水抱屈原是我/如此尸骨難收。”可見,無論是海子美化屈原之死,還是海子本人之死,他對傳統士大夫犧牲精神的浪漫化理解和其個人的精神孤獨皆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上,這種將陰郁憂愁的死亡與在絕望中綻放的再生相結合的詩歌理念是作為中國詩人的海子的獨特創造。
另外,分析海子沒有接受波德萊爾用來承載病態美學觀念的意象類型——城市意象的原因,需要考慮到西方原始主義思潮的影響。大量運用原始神話、習俗以及生活景象作為創作素材,體現了原始主義思想對海子詩歌的滲透,詩人通過生死輪回表現出對“史詩”的構想和對原始家園精神的復歸。海子在《詩學:一份提綱》中所指出的西方文化與原始力量的密切關系,也展現了他對原始自然、原始藝術以及原始精神的癡迷與追求:“人/活在原始力量的周圍。”[5]1024因此,海子將波德萊爾所關注的“人與病態城市文明”的關系在創作中替換為“人與病態自然”的關系,雖然在形式上看似走向了復古,卻能夠透過機械理性、人性異化、社會偏見等現實生活的病態束縛,更加貼近詩人呼吁重新反思人類自然本質中的陰暗面的詩歌理想,發掘“丑”的力量,從而實現原始精神家園的回歸。
五、結語
波德萊爾與海子有著相似的審美追求:摒棄病態之“丑”受到偏見的一面,展現出與現實世界同構之“真”,從而實現對“美”的昭告與呼喚。接觸“病態”的丑才能真正理解“常態”的美,這即是人類理性發展至今對感性的深刻指引。正如《祖國(或以夢為馬)》[5]436中所寫:“我必將失敗/但詩歌本身以太陽必將勝利。”在西方丑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下,海子的詩性追求終將升華為關照全人類的世界情懷,其對西方審美觀的接受與偏離現象不僅體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強大的感召力,同時也點明了一條解讀世界文學的線索,由此便能更全面系統地考察世界意識在中國當代詩歌譜系中的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