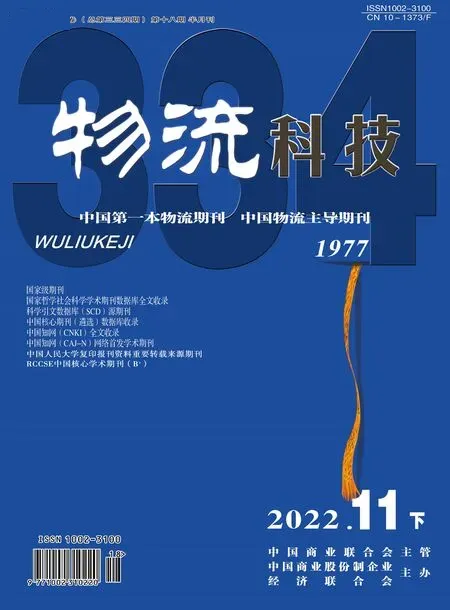數字化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的影響
賈建鴻,葉春明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0 引 言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推動物流企業生產方式、組織架構的變革,在重新定義物流行業經濟功能的同時也重構了其技術基礎、要素結構。而供應鏈作為一種動態生態系統,它能最大程度地滿足供應商直至終端客戶的多元化需求[1]。
推動物流企業數字化轉型,既是順應信息技術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選擇。新冠感染使得部分數字化轉型嚴重滯后的物流企業受到重創,尤其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甚至出現供應鏈斷裂現象,而反觀一些數字化轉型較早的企業不僅能在新冠感染期間通過“線上復工”穩產保供,在新冠感染結束后也能快速恢復到原先狀態。另外,“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也明確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發展規劃[2]。當前,各行業尤其是物流行業都在加速實施數字化轉型以迎接數字化浪潮,數字化轉型最終是否能促進供應鏈管理的改革升級也是物流企業關注的重點,因此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于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的影響極具理論和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從宏觀層面看,學術界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大多從現狀描述、影響因素、內在機理、路徑探究等方面進行,很難形成統一標準,例如學者楊繼東等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因素為切入點,通過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狀,提出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影響因素在于“宏觀經濟波動以及低利潤造成數字化高成本”“基礎設施不足等企業內部因素對數字化的制約”,認為當前階段數字化轉型在催生新的商業模式的同時,仍然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3]。
從微觀層面看,學術界對于數字化轉型的評估與測算一般較為困難,原因在于數字化轉型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中,很難通過具體的指標進行準確測度,既有文獻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大多以某一方面作為切入點進行探討[4]。例如學者趙宸宇等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切入點,基于中國物流上市公司的數據,從理論層面對數字化轉型如何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梳理,并利用實證分析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認為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驅動企業創新、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促進物流行業與服務業融合、提升企業運營水平以降低成本等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該結論有助于評估數字化轉型的生產率效應[5];本文認為在研究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如果將其作為整體來研究可能會有失偏頗,因此參考學者周慧慧等的文獻,從技術轉型、效益轉型、創新能力轉型三個方面對我國物流上市公司的數字化轉型展開量化研究[6]。在供應鏈管理方面,現有文獻大多以現金循環周期來衡量,現金循環周期的改變,將會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經營資本需求產生直接影響,同時也是衡量供應鏈管理能否跨越公司界限的重要指標[7]。
2 研究假設
2.1 數字化技術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
推動物流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首要路徑是加強數字技術的研發、引進,加強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物流供應鏈的融合,加快數字技術在物流企業內部的發展。應該加大高素質專業人才引進力度,吸引優秀的高端數字化人才,為數字化轉型帶來先進思想與新鮮血液,賦能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改革升級[8]。
基于以上分析,做出以下假設。H1:數字化技術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2.2 數字化效益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
物流企業的數字化效益轉型是指將數字技術應用到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以實現降本增效。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企業運營數據對生產制造進行智能化改造升級,推動了物流效率的提高。另外,通過大數據智能化分析,可以幫助企業實現精準化服務、創新性營銷,在降低時間、空間成本的同時減少用戶的信息噪聲。
基于以上分析,做出以下假設。H2:數字化效益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2.3 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
數字化轉型在促進物流企業創新升級的同時,也使得企業內部各個部門間的聯系愈加緊密。學者孔存玉認為,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使數字技術平臺開放化、創新生態系統網絡化、公共服務平臺共享化以及價值創新鏈重構化,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延展了企業邊界[4]。學者鄭瓊潔等經過實證分析指出,研發投入越低的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概率越低,認為企業的研發支出是數字化轉型的基礎,企業應加大研發投入、加強與科研機構的合作,以互聯網作為平臺加速企業數字化的進程,支撐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2]。
基于以上分析,做出以下假設。H3: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來源與變量設計
本文根據證監會2012版行業分類,選取2015—2020年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了ST、*ST等企業以及重要數據缺失的企業,共計選取112家物流公司672條數據。數據主要源自國泰安數據庫、CNRDS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等。本文參考現有研究,具體變量如表1所示。

表1 具體變量相關情況
3.2 模型構建
基于上文所提出的三個假設,設計出如下3個模型,其中,模型(1)研究數字化技術轉型對物流公司供應鏈管理的影響,模型(2)研究數字化效益轉型對物流公司供應鏈管理的影響,模型(3)研究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對物流公司供應鏈管理的影響,其中Control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公式如下:
4 實證分析
4.1 相關性分析
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具體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從數字化技術轉型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TT1)的相關性系數為0.091,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數量(DTT2)的相關性系數為0.273,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初步說明數字化技術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影響效應,與本文的假設H1基本相符。

表2 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的具體結果
從數字化效益轉型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成本費用利潤率(DBT1)的相關性系數為0.761,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主營業務利潤率(DBT2)的相關性系數為0.716,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初步說明數字化效益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影響,與本文的假設H2基本相符。
從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研發強度(DIT1)的相關性系數為0.131,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專利申請(DIT2)的相關性系數為0.046,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初步說明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影響效應,與本文的假設H3基本相符。
4.2 回歸分析
本文的回歸模型通過Hausman檢驗,發現P值均小于0.05,拒絕原假設,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歸分析具體結果
模型(1)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TT1)的回歸系數為0.012,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TT2)的回歸系數為0.097,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當企業加大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或者增加技術研發人員的數量時,現金流循環周期會隨之縮短。據此可得,本文的研究假設H1通過了實證檢驗,即數字化技術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模型(2)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BT1)的回歸系數為0.223,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BT2)的回歸系數為0.359,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現金流循環周期會隨著成本費用利潤率或者主營業務利潤率的提高而縮短。據此可得,本文的研究假設H2通過了實證檢驗,即數字化效益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模型(3)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IT1)的回歸系數為0.048,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IT2)的回歸系數為0.012,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當企業加大研發強度或者增加專利申請的數量時,現金流循環周期會隨之縮短。據此可得,本文的研究假設H3通過了實證檢驗,即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正向作用。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更好地驗證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還通過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通過隨機效應模型得到的數字化轉型與現金流循環周期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通過隨機效應模型得到的數字化轉型與現金流循環周期關系的檢驗結果
模型(1)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TT1)的回歸系數為0.009,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TT2)的回歸系數為0.100,在1% 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后,數字化技術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之間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研究假設H1仍然成立。
模型(2)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BT1)的回歸系數為0.099,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BT2)的回歸系數為0.483,在1% 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后,數字化效益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之間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研究假設H2仍然成立。
模型(3)分析結果顯示,現金流循環周期(CCC)與數字化設施投資(DIT1)的回歸系數為0.030,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與技術研發人員(DIT2)的回歸系數為0.009,在10% 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結果表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后,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與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之間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研究假設H3仍然成立。
5 研究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根據證監會2012版行業分類,選取2015—2020年間112家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上市公司,共計672條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利用國泰安(CSMAR)數據庫、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以及手工收集和整理所獲得的研究數據,對本文提出的一系列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通過上述實證檢驗結果的整理,得出以下研究結論:從數字化技術轉型層面來看,數字化設施投資、技術研發人員的增加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數字化效益轉型層面來看,成本費用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率的提高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數字化創新能力轉型層面來看,研發強度的提升、專利申請的增加對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2 研究建議
針對所提出的結論,為加快我國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的改革升級,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通過加強物流企業在供應鏈各個環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強化供應鏈一體化的精細管理,加大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投入,加快數字技術在物流企業的融合發展,同時也要加強基礎領域、技術領域的理論研究和技術發展,從而為先進技術更好地融入供應鏈管理奠定基礎[9]。
二是應加大創新研發、引進數字化人才的力度,物流企業應充分認識到創新能力對于供應鏈管理改革升級的重要性,創新能力的提升會給物流企業帶來價值并最終體現在企業績效上。另外,應明確和突出核心人才的重要性,推出吸引專業化技術人才的措施,引進國內外在數字化建設方面有所建樹的高端人才,為推進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的改革升級提供權威性的指導。
三是通過打造數字化產業生態實現供應鏈的動態優化管理。從戰略角度來看,物流企業整個供應鏈的效率、價值創造能力都與內部智能化架構、外部合作伙伴密不可分。在物流企業內部,應打造兼備網絡化、情景化的數字工作環境、數字資源平臺,以便適應新時代員工的數字化工作方式,提高員工工作場景的體驗感,提高團隊的溝通協調能力、創新科研能力,為搭建物流企業供應鏈管理系統做好生態基礎;在物流企業外部,供應鏈管理改革升級光靠物流企業內部是無法實現的,需要整個產業鏈的合作,包括物流企業上游供應商、下游經銷商以及終端消費者的整個價值供應鏈的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