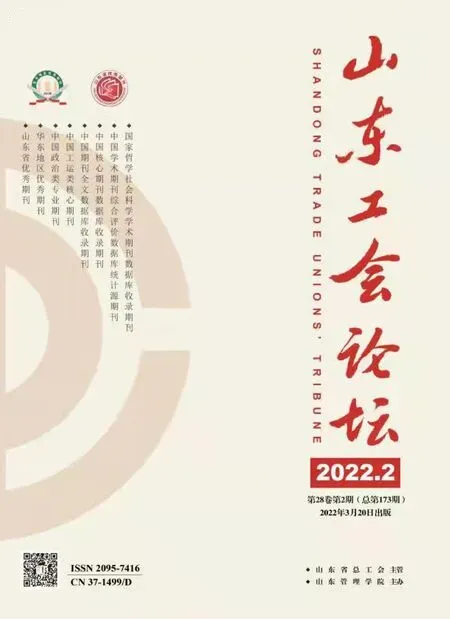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的類型化
常 春
(武漢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引言
一直以來,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被視為民法聯結價值世界的管道[1]。乍看之下,其似乎僅適用于民法等私法領域。但來自實務的數據顯示,在勞動司法過程中,裁判人員引用公序良俗原則斷案已是常規化操作。以“公序良俗”為關鍵詞在“威科先行法律數據庫”平臺進行全文檢索,可得勞動爭議案件6201件,其中有高達4908個案例發生于近5年①。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雖然幫助了數以千計的勞動爭議案件得以定紛止爭,但其在理論和實務上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一,勞動法并未確立公序良俗原則,裁判者援引或許有其理由,但亦可能存在超越“依法裁判”的風險;其二,公序良俗原則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其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傳統的概念思維難以在其適用過程中發揮作用;其三,在援引該原則判案時,法院判決存在說理不清、適用情形混亂甚至是誤用和濫用的問題;其四,勞動關系與民事關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盡管民法學界對公序良俗原則如何具體適用有一定的有益探索,但基于勞動法本身的特性,勞動爭議的解決不可能完全照搬其經驗。故此,本文以公序良俗原則的諸多理論成果為基礎,對我國法院判決作全面、系統的整理和分析,并提出該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的類型化方法,以此破解理論和實務上的難題,使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案件中得以規范適用,形成符合司法價值的審判脈絡。
二、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中的適用現狀分析
(一)適用的總體情況
截至本文檢索日期,有關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的案件數量共有6201個,經過分析,該類案件主要呈現如下特點:1.案件復雜性較高,數量總體呈逐年上升趨勢(近五年)。2017—2021年,各年發生的案件數量分別為833、896、1124、1282、746件。可見,自2017年以來,案件數量連續四年上升。此外,在所有檢索結果中,進入二審程序的案件數量占比高達55.34%,這說明此類案件復雜性較高,當事人一審“服判”概率較低。2.公序良俗原則的援引遍及各種情形。例如,勞動關系的解除是否合法②;用人單位批假決策是否妥當③;勞動合同的變更是否有效④;勞動合同的簽訂是否有效⑤;用人單位的勞動規章制度是否具備效力⑥;用人單位的內部決議是否有效⑦等。
(二)司法適用亂象的表現
1.與其他法律原則混用
法官“依法裁判”是一個不言自明的誡命[2]。基于不同的視角,“依法裁判”或許有多種不同的內涵,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裁判者需要選擇恰當的法律規范來對案件進行裁決。這就要求法官能夠正確區分各個法律條款。但就司法現狀來看,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司法中的適用并不盡如人意,裁判者容易將其與其他法律原則混淆適用。例如,在何俊與南京匯眾合一健身服務有限公司勞動爭議中,勞動者為了提高自己的業績而虛構交易單量。法院判決則稱勞動者的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⑧。勞動者的一個行為同時違反誠信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的情況或許存在,然而,本案中勞動者通過虛構交易的方式來實現勞動給付,其違反的更多是誠實信用而非公序良俗。又如,在星光精細化工(張家港)有限公司與施曉鳳勞動爭議中,法官在判決書中直言寫道:誠信,為公序良俗的基礎之一⑨。這更是將誠信和公序良俗兩項法律基本原則混淆的典型。再如,在林輝與福州冠洲電子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勞動者在工作期間患病住院治療,但并未被認定為工傷,不能享受工傷待遇。法院依據“公平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判決用人單位對勞動者予以經濟補償⑩。公平原則系指“各人得其應得”,勞動者在工作期間患病,且有“過勞”情形,但卻不能享受到工傷保險待遇,此種情形之下,適用公平原則無可非議,而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卻難以令人信服。
2.僭越規則而濫用
“不得向一般條款逃逸”乃是法律原則最重要的適用規則之一[3]。在具體個案中,法律規則具有適用的優先性,而非法律原則[4]。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相比于規則,原則處于基礎地位,為了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在用詞上不得不追求抽象,因此,其并不指向具體的時間、地點、主體等情形;而規則卻不然,其目的本就在于與個案相適應。另一方面,法律原則具有價值性[5],而價值的判斷往往充滿爭議。然而,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司法實踐中適用時僭越規則的現象并不鮮見。在張小林與平頂山天安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勞動爭議一案中,勞動者冒名頂替進入該用人單位工作,應當屬于“以欺詐手段訂立勞動合同”,違反了《勞動法》第18條之規定,但法院卻在判決書中寫道:該行為擾亂了用工秩序,并違反了公序良俗原則。此舉顯然有“向一般條款逃避之嫌”。裁判者棄法律規則而不顧,任由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介入勞動爭議,這不僅是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更是司法僭越立法的不當之舉。
3.淪為“道德審判”的工具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不可否認,“德治”如同“法治”一樣重要,早已深刻地嵌入人類的社會生活之中,規范著人們的行為。但二者卻不能等同,法律僅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富勒將道德分為兩種——義務的道德與法律的道德,前者是道德的最低限度,后者是最高限度[6]。梅迪庫斯也曾說到,民法典公序良俗中的道德并非全部道德,僅有被打上法律烙印的那部分[7]。可見,并非所有的社會道德均可以通過公序良俗原則的援引而被用來調整當事人的行為。在勞動關系領域,由于行業的不同,法律對勞動者在道德上的要求可能千差萬別。因此,裁判者在適用公序良俗原則斷案時應當保持更高的謙抑性,切忌令該原則淪為道德審判的工具。然而,事總與愿違。就以違反性道德這一類型的案件來看,在盛瑛與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勞動合同糾紛案中,涉案勞動者因與他人發生不正當男女關系而被用人單位開除。法院支持了這一行為,其理由是“個人私生活應建立在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不違背社會公德的基礎上”。再如,在黃黎明與特靈空調系統(中國)有限公司上海研發分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中,涉案勞動者因在公司電腦中儲存大量淫穢資料而被開除,法院以“該行為確有違職業道德和公序良俗”為由而支持了用人單位的決定。又如,在鄧柱堂與紐寶力精化(廣州)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勞動者因受行政處罰而被開除,法院判決對此予以支持。眾所周知,用人單位合法解除勞動關系的情形被規定在《勞動合同法》第39條之中,從法條內容來看,無論是私德不檢點還是被科以行政處罰都不屬于勞動合同合法的解除情形。顯見之,裁判者的上述決斷對勞動者的道德水準要求嚴苛,有“道德審判”之嫌,這有悖于公序良俗原則設立的初衷。
(三)司法適用亂象的原因
1.公序良俗原則內涵不明確
公序良俗原則源起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對“意思自治”限制的需要。從稱謂上來講,大陸法系國家一般稱之為“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公共秩序與道德”“社會秩序與善良風俗”等幾種;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則將之稱作“公共政策”[8]。上述各種各樣的稱呼足以說明各法域對公序良俗的內涵均沒有達成共識。具體而言,通常把公序良俗原則分為兩個部分來理解——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然而,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內涵。就公共秩序而言,主要有以下理解:一般秩序說,即為社會存在與發展所必要的一般秩序[9];一般利益說,即國家社會的一般利益[10];社會公共利益說,例如我國《民法通則》強調對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的保護[11]。善良風俗則是指國家與社會所認可的一般道德[12]。這一點國內外的學者并無異議,其爭議的焦點在于道德的范圍。例如,有人認為其僅限于家庭以及宗教道德[13];也有學者認為其并非一般的道德,而是具有法律意義的那部分[14];相反,也有認為其是指法律之外的倫理秩序[15]。
以上論述僅僅是基于民法的視角來進行的,但是在勞動法領域,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內涵還會有其特殊性。例如,不同職業所要求的職業道德可能會有所差別,餐飲企業對于勞動者的衛生要求與一般企業相比往往更高。再如,以性道德為例,如果勞動者在職場之外存在不正當男女關系的行為,這確實有違善良風俗,但是對勞動關系的存續和發展來看,其是否有著必然的影響是值得商榷的。總而言之,公序良俗原則的內涵本身就處于一種不明確的狀態,將之適用于勞動爭議領域之后,其復雜性程度還會增強。
2.裁判者本身固有的缺陷
正是由于內涵的不確定性,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司法過程中的適用只能依賴裁判者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由于裁判者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法官在行使這一權力時容易出現異化的現象。其一,根據公共選擇理論,裁判者是理性經濟人,具有自我性,其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可能存在回避不利于個人利益決策的傾向[16]。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權力的擁有者都容易濫用權力[17]。因此,如果不加以約束,法官極易濫用自由裁量權。其二,如同普通人一樣,裁判者不僅在認知能力方面是有限的,而且在裁判能力方面也并非絕對無懈可擊。其三,由于每個人人生閱歷的差異,裁判者的價值判斷傾向未必能夠契合于公序良俗原則所要追求的法律目標。正是由于上述三個方面的缺陷,裁判者在援引公序良俗原則時才會作出各式各樣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決。
3.缺乏合理裁判規則的指引
就實踐中的情況來看,裁判者援引公序良俗原則斷案時主要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將勞動合同視為私人(私法)合同,因此私法原則和規則仍有適用于勞動關系的余地[18];二是直接援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中有關職業道德、勞動紀律的規定對案件作出決斷;三是將《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第43條之規定——變更后的勞動合同內容不得違背公序良俗作為突破口,進而適用公序良俗裁決案件。遺憾的是,雖然法院援引公序良俗原則裁斷的勞動爭件案件比比皆是,但實際上我國勞動法并未明確確立起該原則,遑論可資指引法官裁判的合理規則。即便是上述第三種思路中的司法解釋文件,其也并未對公序良俗原則的內涵、適用情形等作出明確說明。因此,法官在適用該原則時完全處于一種“盲目”的狀態,統一的裁判標準無從談起。
三、公序良俗原則適用于勞動爭議的方法:類型化
(一)類型化的原理
公序良俗原則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開放性的特點[19],這一特點導致其對法的安定性造成了削弱[20]209-210。也正因此,傳統的概念思維在理解和運用公序良俗原則的過程中總是難以取得最佳效果。類型化思維是指根據研究對象的特點形成類型,進而運用類型進行推理的一種思維方式[20]119,它是為了彌補傳統概念思維的缺陷而產生的一種思維方式,比后者有更強的解釋力及更大的適用價值[21]118。類型化適用就是運用類型化思維來適用法律原則,使法官能夠據以對案件作出合理的裁判。具體而言,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法中的類型化適用,就是根據勞動關系的不同情形各自所具有的“同理性”建構起類型,然后在司法過程中根據“同理性”對同一類型的案件進行合理的判決。這不僅有利于實現個案正義,也有助于維護法的安定性[22]。勞動法本身所獨有的價值體系,決定了其在借助公序良俗原則進行斷案時不可能對民法領域的相應內容照搬照抄,而應當根據自身情況靈活調整。在此過程中,類型化的適用方法則可以做到在不破壞勞動法安定性的前提下,使該原則得到恰當運用。
(二)類型化的優勢
1.可以彌補概念思維的缺陷
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立法是以概念為基礎而展開的[23]。概念思維具有以下特點:彼此之間截然對立;致力于形而上;重視形式。如果法律主要由抽象的概念來組成和描繪,那么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案件事實亦可以為抽象規則所涵蓋,遵從演繹推理的規則即可以推導出法律結論[21]119。但除了規則,法律中尚有大量的原則以資適用。法律原則通常并不具有明確的內涵,更不具有清晰的概念。此時,對于概念自身的解讀如何“自圓其說”,概念本身已無能為力[24]。當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邏輯體系不足以掌握某種生活現象或意義脈絡的多種表現形態時,我們首先想到的補助思考形式是“類型”[25]。類型化思維所獨有的描述性、相似性、模糊性和開放性特征,正好能夠彌補概念思維下涵攝模式的不足,對于糾正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領域適用時的亂象大有裨益。
2.防止裁判者濫用自由裁量權
公序良俗原則的目的核心在于以公共利益限制私人的意思自由,其在本質上具有謙抑性[26]。同時,由于內涵的抽象性,此原則的具體規范功能只能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實現。因此,法官在適用時更應秉持謹慎態度。為了達致這一目的,最高院可以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用以約束法官的裁判行為。但囿于原則的不確定性,司法解釋亦難以窮盡公序良俗的所有范圍。換言之,以大量的司法案例為基礎,對其進行歸類處理,從而總結出裁判規則,仍是約束法官在適用公序良俗原則時的自由裁量權的必要路徑。而這一過程,即是類型化思維功能機理的具體體現。
3.滿足法的安定性與正確性需求
在任何法律制度中,“確定性(安定性——筆者注)”都是法律所追求的目標[27]。要為社會提供公共行動與判斷的標準,法律就必須具有安定性[28]。但法不只有安定性,它還強調正確性,此二重性質共同形成了法律的內部張力[29],缺一不可。然而,在某些情形下,固守法的安定性可能會犧牲其正確性;反之,亦然。為了緩和二者之間的這一矛盾,立法者在法律中設立了諸多的法律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便是其中之一。其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同樣背負著維護法的安定性和正確性的使命——在沒有具體法律規則時可以將其用以闡明法律、補充法律,實現個別正義,在有具體規則時可以避免機械地適用規則或者克服規則的局限性。即便如此,這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若公序良俗原則不能得到正確適用,法的安定性或者正確性仍然會遭到損害。故此,尋求一種恰當的方法以使公序良俗原則抽象的內涵具體化,進而達到規范適用的目的,便不失為上策。同時,由于我國的勞動法尚未全面確立起該原則,面對日益增多且不斷變化的勞動爭議,唯有類型化的適用方法才能“對癥下藥”,使之做到“不辱使命”。
4.有利于促進司法與立法的良性發展與互動
通過類型化思維的運作,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的大量案例得以被歸類,形成不同類別的案例群。在此基礎之上,司法機關可以總結出每一案例群的共性、構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進而為裁判規則的形成提供源源不斷的實踐指引。如此,實務法官既可以從中獲得裁判指引,提高案件辦理的效率,同時也在規則的約束下裁審訴爭案件,不至于造成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另外,頗高的援引頻率顯示出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法領域具有巨大的適用價值,因而該原則在勞動立法上的空缺不可能持續存在,在時機成熟之時,立法者極有可能會考慮將其納入到勞動法的規范體系。在此之前,公序良俗原則首先要建構起在勞動法語境下獨特且穩固的學理乃至法理,而類型化的適用方法本就具有“定型”的功能,能夠析出公序良俗原則最本質的特征,進而向立法者以及學術研究人員提供豐富的實踐素材。
四、公序良知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類型化的具體呈現
類型化是一種以司法實踐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或判例研究方法[30]。因此,有人認為類型只能被發現,而不能被設計;一旦談及設計,其便脫離了現實而帶有了預測性。這一立論是建立在案例類型會不斷更新的基礎之上的,且不無道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公序良俗原則的功能類型卻是明確的。同時,基于功能視角對原則進行類型化適用的研究成果早已有之[31]。因此,本文試從公序良俗原則的功能出發,并以已獲取到的大量司法判決為基礎,對該原則在勞動爭議中的適用進行類型化分析。
(一)公序良俗原則的功能類型分析
依照學者的分析,公序良俗原則有三項功能[32]:一是查明功能,即運用公序良俗原則查明和確認案件事實。二是限制功能,其包括限制行為和規范兩個方面。三是適用功能,即用公序良俗原則來定紛止爭。據此,參照法律原則的功能,并結合勞動法的特殊性[33],本文認為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法中的功能類型應當如下:第一,查明功能。即當勞資主體的某些行為對勞動關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但并不屬于法定或者約定應當約束的情形時,裁判者可根據公序良俗原則認定該行為應當被約束。此功能的本質在于將法律的規范意義賦予其他非法律的規范,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將此稱為“繼受功能”[34]。第二,限制功能。即援引公序良俗原則對勞資雙方的行為或者規范進行限制,其目的在于設定勞資自治行為(或規范)的邊界,若當事人之行為、協議決議乃至其他規范在限度上超出了社會公序良俗所允許的范圍,法官可據此宣布其具有“不妥當性”,以達致限制之目標。第三,修正功能。在特定情況下,對勞資之間的行為進行修正或者取消,與上述的適用功能相對應。這一功能的目的在于取消或者糾正某些由勞資主體根據法律作出但卻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其與限制功能的主要區別之一在于,限制功能所限制的是“意思自治行為”,而修正功能所修正的是當事人根據法律的規定所欲達成的法律效果。
(二)公序良俗原則查明功能在勞動法適用的類型化
勞動合同具有不完全性[35],并不足以單獨承擔起調整勞動關系的重任。同時,由于其還具有繼續性,因此,極有可能存在雖然在勞動合同中未能預先約定,但卻為勞動關系之維系所必須的情形[36]。當勞資雙方就這些情形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而發生爭議時,法官不得拒絕裁判,必須遵循公序良俗之查明功能判斷勞資雙方各自應當遵循的義務和準則。例如,在劉志超與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勞動者劉志超將糞便涂抹在同事的辦公桌上,用人單位據此解除了與劉志超的勞動關系,此舉獲得了法院的支持。在李燕明與深圳市保輝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景輝物業管理分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中,勞動者擅闖女廁所,引起女職工恐慌,因而遭到用人單位的開除處理,法院認為勞動者的行為違背了公序良俗,故支持用人單位的開除決定。
“用糞便涂抹在同事辦公桌”“擅闖女廁所”等行為并不能歸屬到勞動關系解除的法定情形,但在上述案例中,一審法院以違反公序良俗為由確認了用人單位關于解除勞動關系的決定,二審和再審法院均對此予以支持。其最本質的原因在于,這一行為對其他勞動者工作所需要的身心安全因素產生了不利影響,損害了用人單位的生產秩序。由此可見,公序良俗原則查明功能的核心要義在于幫助法院識別那些對勞動關系及其維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但并不屬于法定或者約定應當約束的情形。故此,查明功能類型的構成要件如下:一是屬于違反公序良俗的情形;二是對勞動關系及其維系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三是不屬于法定或者約定應當受到約束的情形。
(三)公序良俗原則限制功能在勞動法適用的類型化
作為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勞動法規范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其還賦予了勞資雙方一定的意思自治的空間。換言之,勞動過程中存在著某些屬于勞資自決的事項。例如,《勞動法》第47條賦予了用人單位自主決定工資分配方式的權利。依據此條款,用人單位可以依法自主制定績效考核標準以及工資分配方案等。此外,即便勞動者應當根據用人單位的指示來完成勞動任務,但在具體的工作方式上,其同樣擁有較多的自主權。然而,意思自治并非漫無邊界,而是應當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公序良俗原則的限制功能可以幫助司法找到其邊界的所在[37]。
具體到勞動司法實踐,公序良俗原則發揮其限制功能的案例并不鮮見。在袁美華與雅馬拓科技貿易(上海)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中,袁美華通過私下許諾回扣的方式為公司銷售設備,法院判決書言明,袁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用人單位將其開除的決定并無不妥。在北京熙辰建筑咨詢有限公司與陳麗麗勞動爭議案中,法官在判決書內寫道:用人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不得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及政策規定,不得明顯違反公序良俗,否則相應條款無效。
由上可知,公序良俗原則限制功能類型的構成要件應當包括:首先,勞資主體或共同或各自在意思自治范圍內作出了一定行為;其次,該行為之作出系為建立、維系勞動關系或者完成工作任務;最后,該行為有悖于社會公序良俗。
(四)公序良俗原則修正功能在勞動法適用的類型化
在勞動關系的持續過程中,即便勞資主體擁有意思自治的空間,但在許多情況下,雙方仍應依照勞動合同或者法律之規定而行事。然而,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勞資雙方的行為之結果仍有可能會偏離法律規范或者合同約定所預設的目標。此時,若法定或者約定的規則或條款難以作為法院裁判的依據,法官可以援用包括公序良俗原則在內的諸多法律原則對案件作出裁判,以糾正勞資主體所作的不當行為。這是公序良俗原則的修正功能。
對此種類型的構建,我們仍以司法判決作為基礎。在周小琴與瑞安市蘭桂坊娛樂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雙方當事人試圖通過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但由于勞動合同的內容是“要求勞動者在經營場所提供異性陪侍服務”,法院認為這違背了公序良俗原則,遂認定勞動關系無效。在張紅鑫與湖北新華欣保險銷售有限公司黃梅營業部、余秋香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中,新華公司為“挖走”張紅鑫團隊,與之約定補償其在原用人單位尚未發放的工資,但此后新華公司并未履約,張紅鑫遂訴至法院。法院認為,若支持該項請求,則違背了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公序良俗原則,因此判決雙方的約定無效。
可見,公序良俗原則的修正功能類型應滿足以下構成要件:其一,勞資主體依據法律之規定作出一定行為;其二,該行為本身并不違規,但其后果違背了社會公序良俗;其三,法院應當對該種行為或其引起的法律效果作出或取消或糾正的判決。
五、結語
作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發揮著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功能。勞動法作為私法社會化的產物,依法理亦應貫徹公序良俗的原則與理念。即便當前我國的勞動法規范并未明確該原則,但其已經被裁判者在勞動司法過程中廣泛援用。本文以司法判決為基礎,分析了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中適用的現狀及亂象,進而提出了該原則在勞動爭議案件中適用的類型化方法,并對三種類型進行了具體構建,以此達到公序良俗原則在勞動爭議案件中得以類型化適用的目的。但還應注意的是,類型化方法并非無懈可擊,其依然有自身所固有的弊端。因此,理論界與實務界仍應繼續探索其他方法,用以彌補類型化方法的缺陷。
注釋
①檢索時間為2021年12月1日。
②參見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浙甬民一終字第216號判決書。
③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滬02民終10692號判決書。
④參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1民終3481號判決書。
⑤參見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浙甬民一終字第852號判決書。
⑥參見安徽省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皖05民終857號判決書。
⑦參見廣東省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14民終524號判決書。
⑧參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蘇01民終6530號判決書。
⑨參見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蘇05民終7008號判決書。
⑩參見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閩01民終1120號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