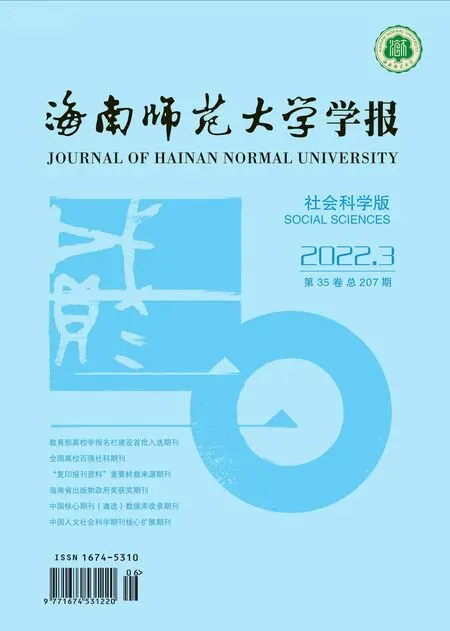風景書寫與民族國家想象
——現代詩歌中國家形象的生成與演變
萬 沖
(南通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通226001)
近年來,風景與民族國家的關系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風景(Landscape),最初是指肉眼所能看得見的土地或領土的一個部分,20 世紀初期以后,風景被定義為“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顯著聯系形式而構成的一個地區”(1)[美]約翰斯頓:《人文地理學詞典》,柴彥威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67-368頁。。風景不僅是有別于人造世界的自然景觀,更凝聚著家園情感、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等豐富內涵。正如學者段義孚所言:“風景是一種意象、一種心靈和情感的建構。”(2)[美]段義孚:《風景斷想》,《長江學術》2012第3期。而關于民族國家,根據安德森的定義,“民族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睿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8頁。。正因為民族國家的想象性和共同性,它極易誘發人們的集體認同感。而作為一種凝聚著集體記憶的載體,風景對于民族國家的塑造與認同,自然而然具有重要的作用。(4)李政亮:《風景民族主義》,《讀書》2009年第2期。目前,中國學界對此問題主要有兩種研究路徑:一是引用外國的風景理論,對風景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做引介性的綜述;二是針對某一特定時期(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研究在危急時刻風景書寫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而針對現代中國豐富復雜的歷史情況,上述研究顯然略顯單薄。在中國由“天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的過程中(5)[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一個重要的文學問題便自然凸顯出來:當象征古典中國的“山河”形象不足以描述現代中國時,現代文學該如何想象現代中國形象,風景書寫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本文從現代詩歌的角度出發,系統梳理風景書寫與民族國家想象之間的歷史演變過程,深入揭示風景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深層聯系,一方面可以理清現代文學發展與現代國家建構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或許可以為詩歌研究打開新的路徑。
一、風景與文化中國認同
被朱自清稱為“愛國詩人”(6)朱自清:《新詩雜話·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7頁。的聞一多,在西化風氣盛行之時,不無激憤地說道:“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那里?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那里?那里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7)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9頁。在表達了對西化風氣的不滿之后,聞一多表達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我們熱愛祖國的思想就是由熱愛鄉土的思想發展出來的”(8)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1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頁。。黃河、昆侖、泰山等獨特的自然風景,被視為最具特色的民族象征。聞一多渴望建立本土民族文化尊嚴的呼吁,隱約透露出民族認同危機與民族自豪感并存的復雜心態,這其實也折射出現代詩人所處的境遇發生了變化——不再以天朝上國為中心自居,而是在世界之中尋求民族國家的認同,經受著“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9)[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7頁。。處于建構期的現代民族國家,并不是一個已然存在的形象,而是一個化無形為有形的過程(10)朱自清:《新詩雜話·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9頁。。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獨具民族地理特色的自然風景承載著歷史積淀、文化記憶以及民族美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風景如何參與到民族國家的建構之中呢?
在“五四”時期,將風景與國家認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主要有郭沫若、聞一多、康白情等詩人。在旅居日本游覽今津時,郭沫若寫道:“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著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卻不曾去憑吊過一回,又在渴望著踏破萬里長城呢!”(11)郭沫若:《今津游記》,周作人編:《新中國文學大系·散文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第178頁。在自然風景中指認出蒙古時期的戰爭遺址成為旅行的動機和目的,表現出對中華民族的強烈認同。在強烈的愛國熱忱的驅使下,郭沫若采用較為粗暴簡單的比附方式,將自然風景與國家民族聯系在一起。同樣葆有深沉愛國情感的聞一多,在風景之中寄托家國之思,采取更為圓熟的抒情方式,表現出更為深厚的文化內蘊。聞一多旅居海外身處異域文化中,飽受思鄉思國之苦,他在《太陽吟》中寄寓了思國思鄉之情。本沒有地理屬性和民族屬性的太陽,被聞一多強行賦予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太陽被認領為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到來的“神速的金烏”:“太陽啊——神速的金烏——太陽!/讓我騎著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12)聞一多:《太陽吟》,《聞一多全集》第1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頁。在中國遠古神話中,太陽代表華夏民族的先祖之一炎帝,它載著名為三足烏的神鳥在天空中飛行。聞一多將太陽比喻神烏,與中國的神話傳說聯系在一起,喚起的民族感情不言而喻。聞一多和郭沫若將普適性的自然認領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一方面暗示了“天朝上國”的潛意識作用;另一方面,也暗示這種方式難以為繼,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遭遇了危機。
聞一多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轉變,因此很自覺地選取帶有鮮明民族文化特色的“菊花”形象,作為尚未成型的民族國家的象征:“鑲著金邊的絳色的雞爪菊;/粉紅色的碎瓣的繡球菊!/懶慵慵的江西臘喲;/倒掛著一餅蜂窠似的黃心,/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長瓣抱心,密瓣平頂的菊花;/柔艷的尖瓣攢蕊的白菊/如同美人底蜷著的手爪,/拳心里攫著一撮兒金栗”(13)聞一多:《憶菊》,《聞一多全集》第1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頁。。作為一種固定的文化符號,菊花極易與中華文化聯系起來,既有梅蘭竹菊的文化積淀,又與陶淵明等高潔之士的精神形象相連。但聞一多并不滿足于這種抽象的精神類比,而是對菊花的形體和色彩進行精雕細琢。在對菊花“形體”不厭其煩的雕刻和書寫中,聞一多潛在的精神動機可能是為了刻畫唯一的“菊花”形象,以對心中唯一的祖國進行賦形。如此這般,在形質兩個層面,菊花便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征:“啊/自然美底總收成啊/我們祖國之秋底杰作啊/東方的花,騷人逸士底花啊”,表達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這種民族熱忱同樣表現在康白情身上。動身前往美國留學的康白情,回望浩浩蕩蕩的黃浦江時,發出了如許感嘆:“黃浦江呀!/我只看見黑的,青的,翠的,/我連聲唄出幾句/‘山川相繆,郁乎蒼蒼’!”(14)康白情:《少年中國》,李怡編:《中國新詩大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49-251頁,在黃浦江畔的風景之中,康白情感受到披發行吟的屈原、為民高呼的杜甫、以苦為樂的蘇軾等等古代詩人形象。因此,在描寫黃浦江時,他并沒有對其進行細節刻畫,而是優先將眼前之景與獨特的文化記憶關聯,個體的表達意志讓位于共同的文化記憶。積淀在自然風景之中的文化記憶和美學趣味,已如文化基因一樣嵌入在風景之中。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上述將自然風景與民族國家緊密聯系的詩人,多為留學異國的青年學生。他們詩歌中的風景,除了作為本民族文化想象的載體,還在與其他民族的比照之中,顯示出豐富的獨特性與優越性。如聞一多將高潔的菊花與異族的薔薇等進行對照:“你不像這里的熱欲的薔薇,/那微賤的紫蘿蘭更比不上你。/你是有歷史,有風俗的花。/啊!四千年的華胄底名花呀!你有高超的歷史,你有逸雅的風俗!”(15)聞一多:《憶菊》,《聞一多全集》第1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頁。聞一多以此來顯示菊花在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深厚積淀,表達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深厚忠誠的情緒。
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天下時期的中國,華夏族的我者和他者的界限都是相對的,他者可以轉化為我者,原本只是中原一支的華夏族,憑借自身所擁有的較高的文明力量,將周邊的族群逐漸融合進來。而在近代中國,一個絕對的他者的出現,真正刺激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覺悟,許多留學生,置身于異邦的環境之中,于是有了近代國家的覺悟,也產生了國族的自我意識。”(16)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頁。在天下時期的中國,“我”可以通過懷柔政策將“你”轉化為內部的一員,所以內外差異和對立并不明顯;而在現代民族國家關系之中,“我”和“你”的差異則是絕對的。只有通過確立一個他者,才能建構起民族內部的一致性。對確定民族身份至關重要的,是民族認同的差異性和排他性原則。自然風景作為一種具有差異性的視覺化形象,具有直接的視覺刺激性和獨特的文化屬性,從而能夠很輕松地被用來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征。
除了表現出排他性和差異性,作為民族象征的自然風景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延續性,河流則常常成為標志性意象。河流具有地理的延續性,也具有伸向未來的潛在性。大江大河在民族之初,便沉淀在文化記憶之中,并且延伸到邈遠的未來。另外,河流擁有生動的外觀,其時而遲緩、時而沉潛、時而激越的流動狀態,不斷轉彎迂回、而又一往無前向前奔流的氣勢,與一個飽經滄桑、歷經劫難而不斷再生的民族形象具有高度的同構性。河流形象與延續性、神圣性的民族國家形象相符,表明了一種擁有豐富歷史淵源的正當性,也表明了一種無限延續的連續性和不朽的夢想。作為身處茫茫宇宙之內的人,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物種,人(比如中國古人)擁有戰勝生命的偶然性以獲得不朽的遠大理想。在神圣的時代,宗教等等思想形式,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將宿命轉化為生命的連續性,暗示生命不朽的可能性。在現代世俗社會之中,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一種不朽的精神想象,這種想象將從傳統家國天下秩序之中脫離而出的自我整合在有意義的連續體中,獲得無限延續的不朽意味,大江大河正好為之提供了便捷而醒目的隱喻。
由于共同的地理環境和負載其上的文化記憶,自然風景被賦予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色彩。作為一種獨異性的美學趣味,一種人格精神境界的象征,一種傳承有自而具有延續至未來的文化想象,自然風景在現代民族的認同與建構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然之道之印證,其所贊美的日月、河山或草木也意不在風景之美學效果,而在于自然神性,或者在于帶有自然神性負荷的生命、家國、故土。”(17)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1-163頁。自然不僅參與現代民族國家的重構,而且還提供了一套價值標準和感覺體系。新詩詩人們將眼前的自然景觀與負載其中的精神價值和文化記憶聯系在一起,將破碎、無序的經驗整合在一套價值感覺體系之中,將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期許聯系在一起,使自己處于一個連續的體系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自己的價值失序狀態,增強了文化認同感與民族自信心。
二、鄉土風景與烏托邦想象
在20 世紀20 年代,留居海外的青年學生主要是在具有文化意味的自然風景之中,尋求文化中國的認同,表達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而20 世紀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當資本主義侵入鄉土中國時,在本土遭遇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的雙重沖擊的中國現代詩人,如何在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格局之中想象一個鄉土烏托邦,寄托美好的想象,構建現代國家的想象呢?
在古典農業社會,雖然遠在戰國時期,中國的城市已經成型(18)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53頁。,但城市并沒有對農業文明形成壓力和挑戰,鄉村也沒有在與城市的對照中,形成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文化空間。雖然有山林與堂廟之別,但城市與鄉村的區別并不明顯,它們同屬于一套宗法體系。古代詩人所作的山水田園詩,并非真實的農民生活圖景,主要表現士大夫階層的審美趣味與恬淡的生活情趣,并未將批判殘酷的社會作為其主要目的。即便有表現農民艱難生活的詩歌,也主要是作為一個旁觀者表達對被剝削的農民的同情,寄予著諷諫君主施行王道的政治訴求。
鄉土自然作為一種奇特景觀被新詩表達,則大致上始于資本主義侵入鄉土中國,是在20 世紀30 年代。很顯然,資本強化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的生活面貌,以及農人的生存現實,催生了一個新的詩歌群體——無產階級詩人。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言:“不是社會主義實踐對人類的具體生活的改變是最大的,而恰恰是資本主義精神在很深的程度上真正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19)[美]蘇珊·桑塔格:《重新思考新的世界機制》,貝嶺譯,《天涯》1998年第5期。在這種視野之下,被資本主義侵入的自然進入到現代詩歌之中;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烏托邦想象,象征和睦、平等、自由的鄉土中國也進入到漢語新詩之中。
在資本主義入侵鄉土中國時,有大量的新詩作品表達了對農民的同情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畢奐午《春城》中有如下詩行:“過高高的城垣,到雜速的街頭,見那花崗石,水泥各樣的建筑物之間/……沒有一棵苜蓿花!沒有一棵金鳳花!//一個鞋匠,/以麻縷維系其生命,摸索于人類之足底,向炎夏走去。”(20)畢奐午:《春城》,《掘金記》,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28頁。這首詩描寫棉麻農趕車進城售賣棉麻的情景。鄉土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遭到破壞之后,人的命運寄托在一絲微小的棉麻之上;在微末的個體與宏大的城市生活之間,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更加凸顯了人物的卑微與無可奈何的艱辛命運。與畢奐午從農民命運的角度描寫自然鄉村之變不同,駱方則從景觀的角度展現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林立在天空里的煙囪里的黑煙/沖散茅屋頂上晚炊底白煙,/來到兩世界底中間!/我不能忍受/狂笑與哀號在耳中隆隆一默默地/咽下眼淚/站在兩世界底中間”(21)駱方:《兩個世界當中》,《水星》1934年10月10日第1期。。工業生產的黑煙與農舍的炊煙相對照,機器的轟鳴聲與鳥鳴的和諧之聲相對照,諷刺了城市對和諧優美的鄉村景觀的破壞。當然,這種諷刺和批判還停留在風景的表層,而較為深入地涉及城市對農村生活改變的,很可能是王亞平《農村的春天》一詩:“阡陌里,螻蟻自由地挖掘穴洞/縱有婦孺驅著瘦牛春耕/但租稅地繁苛/使他們不敢望秋日的收成”(22)王亞平:《農村的春天》,《王亞平詩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第21頁。。秋日的收成本是農民命之所系,繁重的稅收則令他們命懸一線,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不得不涌入城市謀求生計。城市和資本主義對鄉土最為致命的改變,并不在于自然景觀的破壞,而是破壞了小農經濟的自足性,并且異化了農民的勞動。在小農經濟時期,勞動維系著人的基本的物質生存需要,勞動與生活的意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為生活提供了自己的價值和意義。而在資本主義侵入之后,勞動與生活之間的同一性被打破,勞動的主體不再具有主體性,被迫成為大機器工廠中的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受到資本主義的控制,農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根基。
如果說這還只是對個人境遇和局部景觀的呈現,那么蒲風描寫黃浦江的詩作則描繪了一幅當時中國整體的畫面:“黃浦江——/你是中國最真切的寫照!你是中國最壓縮的形相!/在八十年前,在那古銅色的時光一你的神情/是多么安恬,舒暢:/整日夜挾著江南的輕風,/靜靜地溜過和平的上海灘上。/萬里長城到底擋不住帝國主義的鐵掌,/上海馬上變成了紅塵十丈的洋場……”(23)蒲風:《黃浦江》,《蒲風詩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7頁。這首詩歌選取黃浦江畔之景,透視中國的狀況。江南風情和漁舟唱晚的鄉土中國形象,被資本主義奴役,成為爾虞我詐、階級對立的殖民地。感到恥辱和憤怒的詩人呼喚祖國在反抗中崛起:“啊啊,黃浦江喲!/你被揉蹦壓迫已經將近一世紀了!/難道你還愿意繼續當奴隸,/還不打算起來跟人家算總賬……”(24)蒲風:《黃浦江》,《蒲風詩選》,第7頁。很顯然,這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奴役,同時也表達出重建平等自由的鄉土中國的愿望。
上述詩歌還僅僅局限在資本與鄉土之間的對立,還有一種更為激進的態度和表達則來自于詩人柳倩,他將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上升到文明批判的高度:“祖國喲,往昔你的光榮與偉大,/你荷鋤歸去,農人自由的和歌,/樵夫牧童之野語,日中集市的交易,/你富有人性的和平……/而今竟隨白霧隱退/再尋不出世界的蹤跡,/尋不出一切:一朵花,一株樹”(25)柳倩:《霧》,《無花的春天》,中國詩歌社1937年,第18頁。。柳倩把鄉土與城市的對比,放置在中華民族文化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對抗中來表達,鄉村的語義和內涵因此擴大到民族文化的層次。以和諧安詳的鄉土中國,控訴資本主義帝國。在二元對立之中,熱愛和眷戀之情不可謂不強烈,而控訴不可謂不沉痛。在這種對農耕文明的想象里,鄉土中國本身的愚昧、停滯等等均被忽略了;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中,原先處于精英階層的啟蒙讓位給救亡圖存的革命。
在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之中,當大自然被人類的活動所破壞,詩人卻依然向往著統一和諧的鄉村世界。另一方面,在屈辱感的刺激之下,詩人蓄積了大量的革命能量,渴望建立一個改變了剝削關系,擺脫真實社會焦慮的地方,一個和睦平等的世界。這兩種力量結合,則似乎很自然地產生了鄉土烏托邦的想象。這類烏托邦想象大量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新詩之中。比如:“我歌贊秋天:/不是芙蓉滿開,/不是菊花盛放,/也不是桂花爭芳;/是久經風雨雷電的戰斗樹已結下了果實金黃/通過嚴冬,我們要戰取新的宇宙,/哦,我們要戰取新的宇宙!”(26)蒲風:《秋天的歌》,《搖籃歌》,詩歌出版社,1937年,第11頁。蒲風描述了一個通過斗爭而建立的新世界,再如:“春天不在那棵棵茂樹;/春在我們的農村合作社,集體農場/春在我們的城市,首都;/春像愉快的太陽,天天渲染我們的國土全部/我們自己又是花,是小鳥,是大鷲/我們享受了戲院,輪船,飛艇,氫氣球”(27)蒲風:《春天的歌》,《搖籃歌》,詩歌出版社,1937年,第4頁。。蒲風在渴望建立新世界后,邏輯性地想象了春天的光明景象。這些詩作中充滿了“新宇宙”“戰爭”“集體”“光明”等極具情感沖擊力的詞語。這些詞語的含義本來極為模糊,即使一大推詞語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當它們與一種征服自然的力量緊密聯系在一起,它們就有了神奇的力量,成為一種美好的未來想象,充滿了改天換地的激情與號召力。
令建立在自然之上的鄉土烏托邦具有強烈精神感召力的,除了上述心理作用之外,更為核心的是,他們想象的鄉土烏托邦其實與勞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上文已經提及,資本主義對勞動的破壞,最為核心的是對勞動的異化,而這在根本上改變了農民與自然的審美關系。農人對自然的審美,首要的不是在高山流水、松柏荷菊中欣賞高潔的品性和偉岸的人格,而是在最基本的層次上與勞動緊密聯系。自然的曉月星辰、春花秋實提供了生產勞動的節律,以及勞有所獲的欣喜、希望與滿足。一旦勞動遭受異化之后,自然豐美的意象,便失去了審美意義。既然資本主義以異化勞動的方式異化了自然,那詩歌最為核心的應對方式,便是想象一種新型的勞動關系。這些詩人在想象鄉土烏托邦時,在破除剝削關系的基礎上重構自然的意義,試圖在自然風景中尋找與落實自身的自然形象,通過勞動塑造和想象新的主體。“春在我們的農村合作社,集體農場/春在我們的城市,首都;/春象愉快的太陽,天天渲染我們的國土全部”(28)蒲風:《春天的歌》,第4頁。——在一種集體勞動之中,創造豐厚的果實,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令生活和勞動重新獲得同一性的意義。再如王亞平的如下詩句:“黃昏,西天染出赭色的云霞,/我們從暮靄里升上天涯,/追隨著那姣好的月亮,/愉快地開始了辛勤的工作,/就這樣在黑夜中舉起燈籠,/永遠沒有疲倦,畏怯……”(29)王亞平:《晨星》,《王亞平詩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第72頁。抒情主體以勞動者自居,在黑暗中啟示光明,肩負起永恒,充滿了強烈的進取精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爾“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他自己的勞動的結果……把勞動看成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30)[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頁。。在這個以勞動為核心要素的烏托邦世界里,詩人不僅通過勞動創造著世界,也創造著確證自我的生活方式。這個以勞動為核心的鄉土烏托邦世界,與古典文人所想象的回到黃金三世的世外桃花源迥然有別(31)孟二冬:《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理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也與同時期現代派詩人——比如何其芳等——的烏托邦想象大不一樣:它充滿了強烈的解放和斗爭意識。它以歷史的進步為目標,以未來的光明前景為指向,是一個包容了底層苦難者的精神世界,是一個充滿了運動之力和勞動之美的自由世界。
在這種鄉土烏托邦想象里,原先被資本主義破壞的自然景觀,具有了重新審美的可能性:“我們又回到鄉村/原來都從這兒長大,/我們愛那每棵樹,每莖草,/犬聲吠走了黃昏,/晨雞啼醒了太陽;/更愛那一張張忠實典型的臉,/泥腿,赤足,鐵臂膀,/鋤頭鐮把揮走流年,/風霜里終年奔忙。/你們才真是中華的主人呢,/馱起萬種災害,苦困,/把歷史的生命繼續,增長。/歸來了,我們歸來了”(32)王亞平:《回農村去》,《王亞平詩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第51頁。。這首詩塑造了一種在革命的洪流之中重新將自然鄉村審美化的方法。農民不再是舊時代的農民,而是經過啟蒙之后具有反抗意識的大眾,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和階級權利而奮起抗爭。自然和鄉村重新歸于農民所有,寧靜的鄉村重新具有了審美的可能性。人欣賞自然風景,是從中感受到社會目的性,感受到社會勞動成果以及社會的前進,也就是前進的社會目的性成了合規律性的形式。在這個想象的世界里,原先僅維持自身生計的勞動具有了推動歷史進步的意義。鄉村在想象的空間里確立了自己的位置,重新變成和諧的世界。
三、土地形象與民族國家建構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相較于此前的文化中國、鄉土中國所遭遇的危機,民族國家遭遇的危機更為劇烈,甚至達到了滅族絕種的地步。在這一時期,個人與民族的關系更為緊密。很多詩人在其作品中,表達了家國認同之感。如何在風景書寫之中建構起民族國家認同,亦表達個人情感,正是本節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抗戰時期,有大量書寫季候循環的詩歌。這點可以從標題中便可以得到直觀的呈現,如艾青《春》《冬天的池沼》、彭燕郊《冬日》等等。蔣錫金寫道:“像是山峰在一點一點披上新的光輝的/像是干涸的河床一點一點在漲滿著的/象是枝頭的嫩芽一點一點在萌發著的/是光明勝利真理,……/呵,中國的春天。”(33)蔣錫金:《中國的春天》,《文藝陣地》,1938年5月1日第1卷第2號。以春天欣欣向榮的情景象征個體生命的希望,以及民族的光明未來。這種“春天——光明”的象征圖式,還停留在簡單粗淺的層次,其他更為重要的詩人逐漸進入到更深層次的生命體驗。彭燕郊《冬日》有如下詩行:“蕭瑟的冬日啊/風雪的冬日呵/使大地沉默/使雷雨初歇/使草木復歸到泥土里去了/然而,末月的花朵/帶著蠟色的容顏/終于/在行將嗚咽的池邊/綻放了/一年間最后的花瓣。”(34)彭燕郊:《冬日》,綠原、牛漢編:《白色花二十人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3頁。在冬日的嚴寒里,草木承受、抵抗寒冷,以更堅韌的姿態體現了承受與綻放的生命邏輯。這種以生命歷程與季節循環相聯系的抒情模式,在艾青那里發展到更為圓熟的階段。艾青甚至具體到每一個月份,似乎更加具有恢弘的氣勢:“我是季候的忠實的使者/報告時序的運轉與變化/奔忙在世界上/經過悠久的黑暗與寒冷的統治/為金色的陽光所護送/向初醒的大地飛奔……”(35)艾青:《春》,《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48頁。春天孕育希望的喜悅,冬天降臨不幸的死亡,生命處于持續運轉之中。抒情者既游歷于土地和人間之上,俯瞰著生命的生死榮枯和大道周行;又表現出對生命的深厚同情,介入到生命的困苦之中,促進生命的發展。在生命完成一輪周期之后,又開始新的傳播希望之旅。在生命周期的持續循環之中,艾青呈現的是直線向前的時間觀念,表現自然生命不可更改的發展進程。艾青等現代詩人詩歌中的季節循環,一方面繼承了“死亡—新生”的象征意味;另一方面,又以自由、解放等豐富了季節循環的意義。他們作為一種推動力量,主動介入季節的變遷之中,表現出強烈的改造意識,令季節的更迭象征歷史和社會的進步,預示著民族國家的新生。
除了體現生命運行的季節循環,空間的遷徙也被納入民族國家新生的歷程之中。穆旦寫道:“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呵平原,/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著干燥的風,/在低壓的暗云下唱著單調的東流的水,/在憂郁的森林里有著無數埋藏的年代/它們靜靜地和我擁抱。”(36)穆旦:《贊美》,《文聚》1942年2月16日第1卷第1期。在祖國大地漫長的遷徙途中,像考古勘探家認領民族的苦難與記憶那樣,與深埋在地層中的文化記憶緊密聯系。鄒荻帆則這樣寫道:“我們以沉重的腳步走向北方。/我們將以粗柄的腳趾/快樂而自由地行走在中國底每一條路上,/吻合著祖先們底足跡。/我們以紅色的筆/勾寫著明天的計劃與行程,/在明天啊,/我們更將堅決勇敢地走向北方的北方。”(37)鄒荻帆:《走向北方》,《塵土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 年,第52頁。在由南方走向北方的征途中,由淪陷區朝向政治中心的運動中,鄒荻帆獲得了對祖國國土和文化記憶的深切感受。“北方的北方”作為一個并非實在處所的想象之地,提供了一種對未來的憧憬,激發出不竭的激情與行動力。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擁有遼遠邊界線的龐大空間,很難讓人直觀地去體驗它。這些詩人在一步步的遷徙之中,認領土地上的文化記憶,獲得崇高感和儀式感,去貼近想象中的祖國形象。
上述的時間運行和空間遷徙,還停留在個人與民族國家關系的表層。真正令個人與現代民族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受難意識。彭燕郊吟道:“我愛祖國/這被清潔的雪所掩蓋的土地呵/從那僅有的溪澗踏過冰塊的阻礙/我們橫渡而過/祖國呵/我愛你/我們的艱苦的戰斗……”(38)彭燕郊:《雪天》,綠原、牛漢編:《白色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9頁。被雪花覆蓋的潔凈土地是國土的象征,卻在異族的踐踏之中變得骯臟不堪,使土地重新恢復潔白的艱苦行動,具有了解放民族的意義。在這方面,艾青的詩有更為突出的表現:“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中國的苦難與災難/像這雪夜一樣廣闊而漫長呀/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中國/我的在沒有燈光的晚上/所寫的無力的詩句/能給你些許的溫暖么?”(39)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大地上》,《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69頁。以承受雪花的降落為受難的隱喻,依托于土地的死亡與復活的想象,艾青在土地的“死亡——復活”的永恒循環之中,把日本侵略者帶來的暴力和苦難,轉化為一種必然的光明與復活。而令“死亡——復活”的情感邏輯得以成立的,正是詩人的受難意識。“苦難的本質提供的是一種朝向真實情境和事件,從而超出私人主觀性的世界構造,并以此作為個體的整個生存狀況,隱秘地包容在靈魂的深層空間中,對苦難的感受是一種依賴并尋求意義的感受,涉及神或終極關懷的問題。”(40)王凌云:《詞的倫理》,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第90-91頁。基于共同的生存感受和生命境遇,苦難將個人、時代與民族國家聯系起來。基于強烈的意義感受或終極關懷,受難被放置在新生與救贖的意義鏈條之中獲得意義。正如學者萌萌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的天道自然觀中,苦難只是天命向善,人命為之的一個從屬的偶然的方面,它是應該而且可以在懲惡揚善除惡之中消除的。近代以來轉向歷史進化論,原來苦難可在周期輪回的太平盛世中得緩解,也就推向永無休止的未來期待中,為了將來的幸福,現在的苦難就變成了應該付出即奉獻的自我享受了。而個人的受難則是這種中介。”(41)萌萌:《情緒與語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75頁。在古典時代,天道具有最高的正當性,王朝的更迭是天道運行的結果。在天道輪回之中,苦難并不具備正面的意義,而是在秩序的好轉中得以解脫,以證明天命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而在現代進化論式的歷史觀中,歷史變化的合法性在于是否符合歷史前進的方向。在一個向前進化的歷史架構中,個人的挫折被轉換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個人的出路與國家民族的出路合而為一。受難被當作莊嚴而有意義的過程,具有了道德倫理意義,能夠推動社會和歷史的進步、民族國家的新生。
除了保留這種延續與進步的時間規律,土地還提供了一個闊大的空間,將大地上的人民聯系起來。正如艾青在詩歌中表現的:“一棵樹,一棵樹/彼此孤離地兀立著/風與空氣/告訴著它們的距離//但是在泥土的覆蓋下/它們的根生長著/在看不見的深處/它們把根須糾纏在一起。”(42)艾青:《樹》,《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36頁。土地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想象:在受難的大地上,各個階級的人被統合在人民這一集體概念之下,形成了一個承受苦難與迎接新生的共同體。比如穆旦就很準確地說:“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的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43)穆旦:《贊美》,《文聚》1942年2月16日第1卷第1期。在大地上有著承受苦難而依然挺立的人民,他們正是歷經劫難而依然燦然如花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被想象為一個共同體,因為盡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愛。”(4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第13頁。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重要基礎,便是對互不相識而被整合到一個共同體之內的國民的熱愛。
綜上所述,土地在現代詩歌中具有了豐富的意義。在時間上,它脫離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環時間,而與解放、進步、自由、人民等概念聯系在一起,在受難-新生的模式之中,擁有一種線性的進步的時間觀。在空間上,它確定了一個國土范圍,將深藏在地層中的文化記憶、天降的苦難聯系起來,把祖先與我們組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承受苦難而迎接新生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土地成為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征。
四、祖國的象征:從“山河”到“土地”
在古代中國,天下是華夏文化世界的空間想象山河則是標顯其重要的地理形象。山河顯示了華夏民族世代居住繁衍的空間含義,承載著豐富深厚的文化記憶和歷史積淀,它比傳統文化中與社稷相關聯的“江山”更為寬廣。杜甫在大歷四年(769)清明,從眼下的洞庭春光中想到長安和整個神州大地,就以“漢主山河錦繡中”稱贊祖國的大好山河。杜甫在山河之中認領的并非自己身處的唐朝,而是象征華夏的大漢。
在古代中國,高聳入云、直插云霄的高山,是空間中的多層次事物,充滿了超越性的意義,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詩經·崧高》有言:“崧高維岳,駿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45)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3頁。高山大河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來自于天和受命于天的君主。就詩人與祖國的關系而言,山河所表征的人與祖國的關系,是擁有個體意識的臣民與君主的關系。詩人在對山河的熱愛與崇拜之中寄托著對君主的忠貞與熱忱。就時空觀念而言,古典時代的中國人,以“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46)周振甫譯注:《周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57頁。的方式觀看宇宙與自然,所感知的世界是一個循環往復的時空結構,所追求的理想是在循環之中回歸到原初的起點。這種觀看方式也影響了古人的歷史觀。古人并不肯定一種直線式的歷史進步論(47)錢新祖:《中國思想史講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0-33頁。,而倡導回到原初起點的歷史循環論,指向過去德位一致的黃金時代——堯舜盛世。在天命的授予下,在垂直形象的支撐下,山河便具有了超越一姓之社稷的意味,而體現出一種循環往復的歷史觀(48)敬文東:《皈依天下》,北京:天地出版社,2017年,第143頁。,成為天下中國的象征。在古典時代,當國破家亡時、江山易代之時,詩人可以在山河之中,追憶家國之思,感發歷史興亡之嘆。正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言,山河表現的是大于朝代更迭之外的“天下”含義。
與山河相比較,土地也具有神性。在以農耕安身立國的中國,土地在歷史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古代神話中就多有盤古開天辟地、女媧造人的傳說。這些神話、傳說大多將土地視為生命之起源、繁殖延續的象征。誠如耶律亞德所言:“凡是自然界的事物如土、石、樹、水、陰影等所展現出來的神圣質性,無不被它聚攏在一起。土地這個宗教形式最根源的洞見是:豐富的神圣力量之大寶庫——它是任何存在的‘根基’(foundation)。凡存在皆土上,它與萬物相連帶,它們連接成為更大的整體。”(49)Mircea Eliade,Pattern in Comparative Religion,Translated by Rosemary Sheed,New York,Sheed&Ward,Inc,1958,p.242.整體而言,土地作為造物與母親形象,得到人們的依戀與崇拜。土地的如許含義都為其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征提供了必要條件,但其替代“山河”成為祖國的象征則需要更豐富的內涵。朱自清指出,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超越了社稷和民族,也統括了社稷和民族,是一個完整的意念,完整的理想,而且不但揭示了,簡直代表著,一個理想的完整的國家”(50)朱自清:《新詩雜話·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8頁。。可見,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完整理想的概念,一個超越性的抽象意念,一個要求絕對忠誠的形象。在這種要求之下,形成一種與祖國相適應的象征形象,土地則需要承載理想、抽象理念等諸多義涵。
在現代詩歌之中,祖國與土地開始了新的意義之旅。郭沫若以他發自肺腑的高音量詠嘆道:“地球,我的母親!/那天上的太陽——/你鏡中的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從今后我也要把我內在的光明/來照照四表縱橫。”(51)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84頁。郭沫若將地球推崇為祖國母親,宣揚一種普泛的世界主義情懷,并不特指中華民族。這種空泛高蹈、缺乏實質的音調,難免令人心生疑竇。與郭沫若高亢的贊揚不同,戴望舒的愛國語調更為深沉厚重。他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中這樣寫道:“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國!”(52)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戴望舒全集》詩歌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52頁。在手掌撫摸土地的過程中,戴望舒將土地袖珍化和抽象化(53)[美]漢娜·艾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頁。了,將土地塑造為一個為受難者提供精神庇護的祖國形象。在戴望舒這里,人與祖國的聯系建基于對隱秘精神家園的渴求之中。對比郭沫若和戴望舒的詩歌,前者為祖國塑造的地球形象,因尺度過大而不能具體細化到民族國家;后者為祖國塑造的土地形象,因尺度過小尚不能負載起深沉厚重的民族感情。真正令土地的象征意義得以強化,以及讓土地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征形象,則是抗戰時期艾青的詩歌。
艾青在《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中這樣寫道:“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54)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艾青詩選》,第68頁。。他一經落筆,便以厚重的筆觸刻畫出土地與中國相連的畫面。在一片廣闊的視野內,在象征著苦難的雪花籠罩下,土地和中國獲得了同一性,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共同體。隨著雪花緩慢降落帶來的視覺和心理效應,艾青也參與到土地和中國受難的過程之中。在對雪花的感受中,艾青以旁觀者感受祖國遭受的暴力,更為深入的是在行走之中以承受姿態感受大地的寬廣與深厚。這在其《曠野》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走過那些不平的田塍,/荒蕪的池沼的邊岸,/和褐色陰暗的山坡,/而霧啊——/灰白而混濁,/茫然而莫測,/它在我的前面/以一根比一根更暗淡的/電桿與電線,/向我展開了/無限的廣闊與深邃……”(55)艾青:《曠野》,《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29頁。作為一個渺小的行者,艾青在土地上艱難而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對每一寸土地、河流與道路的跋涉之中,領悟土地深刻的記憶、民族徘徊而多舛的命運。艾青塑造出回環往復、深沉厚重的音節形式,使多災多難的土地國家形象得以顯形;在這種嗓音和音質之中,艾青也將個體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承受沉重感之后,艾青也表達了渴望民族新生的信念。在《吹號者》中,艾青這樣寫道:“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地愛著的土地上,/然而,他的手/卻依然緊緊地握著那號角;/而太陽/使那號角射出閃閃的光芒/聽啊,那號角好像依然在響”(56)艾青:《吹號者》,《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24頁。。在沉重而鏗鏘的音響之中,艾青塑造了一個這樣的形象:站在土地盡頭呼喚并引領民族新生的吹號者形象。誠如許紀霖所言:“近代的國家非古代的王朝,它是一個有著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政治正當性的來源不再是超越的天命、天道、天理,而是回歸為人的自身意志和歷史主體。”(57)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頁。艾青筆下的國民承擔著民族的苦難命運,又以堅強的意志為民族的新生而奮斗。
整體而言,在艾青的詩歌中,土地形成了一個時空結構形式,使個人與祖國形成一個共同體;在空間形式上,營造了一種空間縱深感,為個體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可供拓展的空間;在時間維度上,土地形塑了一種線性直線時間(58)[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22頁。。土地為承擔當下苦難的個人提供了一個持續地必然來臨的精神遠景。
除了建基于命運共同感之外,現代民族認同更為重要的是對民族精神品性的深刻認同。許紀霖說得很清楚:“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可以整合國家內部不同民族和族群、有著共享的文化和命運共同感的國族。”(59)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頁。艾青便在土地之中領悟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根性,例如《北方》:“我愛著悲哀的國土,/它的廣大而貧瘠的土地/帶給我們以淳樸的言語/與寬闊的姿態,/我相信這言語與姿態/堅強地生活在大地上/永遠不會滅亡;/我愛這悲哀的國土,/古老的國土——這國土/養育了為我所愛的/世界上最艱苦/與最古老的種族”(60)艾青:《北方》,《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75頁。。艾青感受到土地如許精神品格:寬廣能普及萬物,深厚才能承載萬物。植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四季循環,民族共同體的血緣鄉土情感,種種因素匯聚而成的生命、自然架構,構成連綿一片的永恒連續體。土地不僅僅只是一個容納生命的場所,更是一個象征道統秩序的天地境界;土地上的生命則是以土地為連接點、以天為朝向的共同體,而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空間遼闊感以及時間的永恒感。這種土地精神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領悟了這種民族的精神根性之后,艾青對土地獻出了最真摯的感情——一種誕生在最沉重的苦難之中最深沉的熱愛,一種深深認同之后毫無保留的忠誠。
地理學家段義孚指出,現代國家是一個處于地方與帝國之間的形態,需要與之合適的情感認同尺度。(61)[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等譯,第148-151頁。艾青的詩歌完整地呈現了一個化土地為國土的過程,塑造了與現代民族中國相匹配的精神征象。在“家國天下”體系解體之后,以現代民族為中心的認同,成為個人獲得國家認同的唯一合法性追求。這意味著必須找到一個唯一性和整全性的形象,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承載著民族生存資源、文化記憶和歷史積淀的土地,相較于山河,既能提供當下的認同經驗,又能整合過去的歷史記憶,并投射出遠方和未來的美好理想,更具有象征國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抗戰、民族受難的危亡時刻,個人難以自外于民族國家之外,而是將民族國家與個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方面,命運跌宕的個體在土地之中尋求終極庇護,在土地所提供的精神形式之中容納個體的生命與希望;另一方面,個體對土地表現出完全獻身的忠誠,個體與土地結成了命運共同體。正如朱自清所言:“我們在抗戰,同時我們在建國,這便是理想。抗戰以來,第一次我們獲得了真正的統一,第一次我們每個國民都感覺到有一個國家,第一次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中國是自己的。”(62)朱自清:《新詩雜話·愛國詩》,《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8頁。在這種命運共同體之中,個體難以用興亡循環的歷史觀,來旁觀祖國的興衰榮辱,而是對祖國保持著高度的忠誠與熱愛,以受難促進土地的復活與新生,對光明的未來表達強烈的憧憬,以歷史的承擔者促進民族的新生。相較于受命于天的山河作為天下中國的象征,傾注了人類意志和力量的土地,成為了現代中國的象征。
五、結語
從富有文人情趣、具有文化意味的風景,到無產階級詩人筆下的鄉土風景,再到具有廣闊情感凝聚力的土地形象,現代中國形象的生成與演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最后,承載著民族生存資料、文化記憶和歷史積淀的土地;既能提供當下的認同經驗,又能整合過去的歷史記憶,并投射出未來美好理想的土地;能夠將民族國家與個人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個體生命提供支撐與庇護,又能承受苦難而獲得新生的土地,最終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征,這似乎成為了一個必然而唯一的選擇。在這種偶然性與必然性的變奏中,或許可以從文學角度看到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動態過程,認識到風景參與到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的深層機制,逐漸厘清現代民族國家生成和現代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