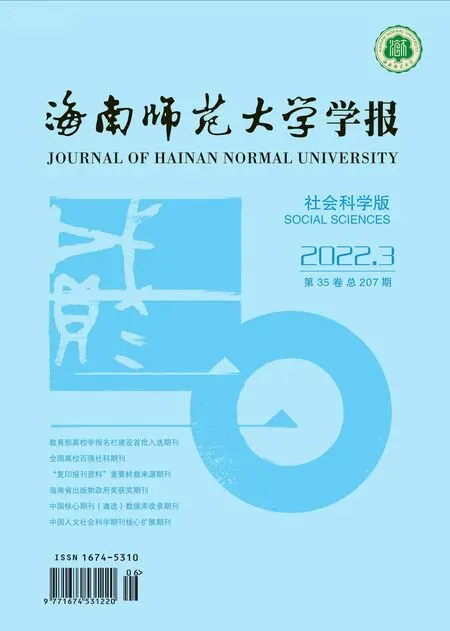失意人的詩意語
——論王蒙20世紀60年代舊體詩中的自我書寫與精神邏輯
黃 珊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300071)
20 世紀60 年代,以小說創(chuàng)作見長的王蒙陷入了創(chuàng)作的低潮期,除了1962 年創(chuàng)作的兩部短篇小說《眼睛》《夜雨》外,整個20 世紀60 年代王蒙的小說創(chuàng)作完全中斷。但也就在這一時期,作為一名曾歡呼著“青春萬歲”的“少年布爾什維克”,王蒙卻突然轉向了舊體詩創(chuàng)作,在1961—1965 年之間創(chuàng)作了十四首舊體詩,具體來說,主要包括王蒙1961 年在北京郊外農場勞動改造時創(chuàng)作的《感遇》(七律二首),1963 年底王蒙在西行火車上寫下的《赴新疆》(七絕四首),以及1965 年夏王蒙在新疆伊犁巴彥岱參加勞動期間創(chuàng)作的八首舊體詩:《即景》(七絕二首)、《伊犁》(五絕三首)、《運麥》(五絕一首)、《聽歌》(七絕一首)、《八月》(七絕一首)。就詩作內容來看,其中有痛陳自我改造的決心,抒發(fā)革命建設豪情的詩篇(如《感遇》《赴新疆》),也有贊美田園躬耕之樂的閑適曠達之作(如《即景》《運麥》)。在目前學界對于王蒙創(chuàng)作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將王蒙20 世紀60 年代的創(chuàng)作視為空白而直接略過(1)就目前了解,關于20世紀60年代王蒙的創(chuàng)作鮮見于針對性的論文述評,而多為王蒙相關論傳中的史料性的介紹。同時,這些論傳在敘述20世紀60年代的王蒙時也或多或少存在某些問題,如何西來在為賀興安《王蒙評傳》寫作的序言中認為,王蒙“中間雖有因被錯劃為‘右派’而綿延20余年的空白,但復出以后卻進入了創(chuàng)作的噴涌期,全盛期。”事實上,王蒙“劃右”后雖創(chuàng)作銳減,但仍有少量創(chuàng)作,并不能籠統(tǒng)概述為“20余年的空白”。(參見何西來:《〈王蒙評傳〉序二》,賀興安:《王蒙評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2頁)又如溫奉橋認為,王蒙作于20世紀60年代的舊體詩有12首,這一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也不夠準確。(參見溫奉橋:《淺論王蒙舊體詩——兼對當代舊體詩創(chuàng)作的思考》,《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6年第3期),但事實上,王蒙的這些舊體詩因為在創(chuàng)作時無意于發(fā)表流通,其相對封閉的私人語境為我們部分地還原與審視王蒙20世紀60 年代的文化行為和心態(tài)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對于王蒙創(chuàng)作的這十四首舊體詩,首先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作為在20 世紀50 年代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家,懷揣社會主義理想的王蒙在進入20 世紀60 年代后將如何適應他政治生涯的巨大轉折,舊體詩中的自我書寫,反映了他對于現(xiàn)實處境的何種心境?同時,為什么在這段堪稱是王蒙人生最失意落魄的歲月中,王蒙創(chuàng)作的大部分舊體詩中卻常常帶有樂觀豪放或者田園牧歌般明朗燦爛的色彩?舊體詩中所吟哦的詩人情感,與王蒙的現(xiàn)實處境之間存在哪些反差和聯(lián)系?而就作品形式來看,作為一名曾經(jīng)熱情學習弘揚新文化,關心新社會的青年作家,王蒙為何在這一時期突然開始創(chuàng)作舊體詩?舊體詩這一特殊的文學形式,表現(xiàn)出王蒙怎樣的文化心態(tài)與身份認同?從這些被以往研究者們忽略的舊體詩中,可以補充描繪出一幅與公眾視野中的王蒙不盡相同的文人肖像側影。
一、“風風雨雨意彌堅”與“奇異的保護色”
1958 年后,王蒙的境遇陡轉,作為曾經(jīng)頗有前途的青年團委干部、備受矚目的年輕作家,王蒙開始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壓力,在北京遠郊的生產大隊間參加勞動改造。不過從王蒙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舊體詩中的情感表達來看,面對社會身份和生活境遇的突轉,王蒙的政治信仰和個人理想?yún)s似乎沒有因此動搖,反而在他對“戴罪之身”的自我反思中加以明確和豐富。如這兩首《感遇》(2)《感遇》二首參見王蒙詩,謝春彥、謝奕青畫:《繪圖本王蒙舊體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頁。此詩集或為目前所見最早收錄《感遇》二首的文獻。:
(一)
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月曾相欺。
朝拾暖夢多綺麗,夜論高天亦費辭。
枉使清談迷耳目,全無良策助妻兒。
昏昏舊事拋云外,且舞鍬鋤逐大旗。
(二)
可哀最是未覺前,置死方生意轉歡。
一點天良愧父老,三生皮肉獻河山。
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鬧自然。
換骨脫胎知匪戲,決心改造八千年!(3)王蒙在《感遇》二首后注釋:“以上兩首七律寫于一九六一年,由于找不到舊稿,有些句子是后補的”。此處“決心改造八千年”一句語義夸張,略露嘲諷之意,與全詩感情色彩不符,疑為后補。
“感遇”二字顧名思義,正是王蒙有感于當時的生活境遇而作。《感遇》(一)首聯(lián)與頷聯(lián)表現(xiàn)了王蒙此時痛苦、后悔與羞愧的情感。從詩句的意義指向來看,王蒙似乎完全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創(chuàng)作,在他看來,“舊時”的創(chuàng)作充滿了風花雪月和綺麗,這不過是一場欺騙,令人頭痛腸煎,而他曾經(jīng)的言辭則是自不量力的高談闊論。如果說此詩的前兩句是“悔過”,那么后兩句則是“立新”。痛定思痛后,《感遇》(一)的頸聯(lián)與尾聯(lián)以堅定的態(tài)度表明詩人揮手告別舊我,積極改正,追隨革命腳步“逐大旗”的決心。《感遇》(二)的情感表達與《感遇》(一)大致趨同。“可哀最是未覺前”,未察覺自己的錯誤時才是最悲哀的,而既然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便可置之死地而后生。造成痛苦的是“過去”的錯誤,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現(xiàn)在”痛改前非徹底改造。要實現(xiàn)革命理想,就必須將“昏昏舊事拋云外”,肩挑日月,且舞鍬鋤,一心一意投身建設的洪流。
同樣表達獻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和決心斗志的,還有王蒙在1963 年初攜婦將雛奔赴新疆時創(chuàng)作的《赴新疆》四首(4)丁玉柱在《王蒙舊體詩傳》中認為,《赴新疆》四首最早見于王安《王蒙與崔瑞芳》一書(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此觀點或不準確。據(jù)筆者所考,本文所載《赴新疆》的前三首最早應見于方蕤《放逐新疆十六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11頁),第四首“死死生生心未冷”則最早見于烏魯木齊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辦公室編《詩花滿天山》(烏魯木齊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辦公室,1979年,第102頁)。:
(一)
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
似曾相識天山雪,幾度尋它夢巍峨。
(三)
烏鞘巋峰走鐵龍,黃河浪闊跨長虹。
多情應笑天公老,自有男兒勝天公。(5)除《放逐新疆十六年》外,《王蒙與崔瑞芳》亦收錄《赴新疆》四首詩,而《繪圖本王蒙舊體詩集》與《王蒙文集》第2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中僅收錄《赴新疆》三首,未收錄“烏鞘巋峰走鐵龍”一詩。王蒙在這后兩本作品集收錄的《赴新疆》(三首)后注釋:“以上三首寫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自北京舉家遷新疆的路上——火車上,共寫了八首,只憶起此三首。”故“烏鞘巋峰走鐵龍”一詩或為《繪圖本王蒙舊體詩集》與《王蒙文集》收錄時遺漏之作。
(二)
嘉峪關前風噭狼,云山瀚海兩茫茫。
京華漸遠西陲近,笑問何時入我疆。
(四)
死死生生心未冷,風風雨雨意彌堅。
春光唱徹方無恨,猶有微軀獻塞邊。
這四首詩在結構上基本趨同,即前兩句都為描述詩人赴疆途中所見的自然景色,后兩句抒發(fā)詩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感情基調沉郁之后見豪放,感慨之后見樂觀。一方面,云山瀚海,巍峨雪山,陡峻的烏鞘峰,翻騰的黃河……這些在邊塞詩中常見的壯闊蒼茫的景色難掩詩人的離愁別緒。“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寫的不僅僅是自然的變化,更是人生的跌宕起伏,命運難料,頗有幾分滄海桑田之感。“云山瀚海兩茫茫”既是寫景,也呼應著王蒙對于未來忐忑迷茫的心境。“京華漸遠西陲近”一句,雖未直接描寫“我”的感情,但詩人在風雪中與北京漸行漸遠,背井離鄉(xiāng)的蕭索悲涼之感已躍然紙上。但另一方面,對個人經(jīng)歷的感慨并沒有使詩人陷入自怨自艾的低落情緒中難以自拔。“多情應笑天公老,自有男兒勝天公”,“春光唱徹方無恨,猶有微軀獻塞邊”幾句筆鋒一轉,勾勒出一個雖然遭受打擊,但是在風風雨雨中仍不畏艱險,懷抱報國理想,曠達樂觀的詩人自我形象。
如果說《感遇》二首塑造的詩人形象是一個痛定思痛、一心期望通過勞動改造來脫胎換骨“逐大旗”的“悔過者”,那么《赴新疆》書寫的則是一個在風風雨雨中毫無怨言,渴望奔赴邊疆建功立業(yè)的“奉獻者”。僅就詩作本身傳達的意義來看,無論是“悔過者”還是“奉獻者”,王蒙對自我形象的書寫都突出了他堅定追求革命理想,無私奉獻祖國建設的一面。在自我情感的書寫上,也傳達出一種詩人從不抱怨現(xiàn)實困厄,始終“向前看”的樂觀積極情緒。因此,有學者評價,王蒙的《感遇》二首“以‘肩挑日月’、‘足踏山川’的豪邁氣概,重新確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發(fā)出了達不到‘脫胎換骨’的目的就要改造‘八千年’的決心和信心,詩風粗獷豪放,意境壯美,不失為王蒙舊體詩中抒情言志的一首力作”(6)丁玉柱:《王蒙舊體詩傳》,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頁。,并評價《赴新疆》,“抒發(fā)了他對新疆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和“自己面對新的天地而涌動的新的豪情壯志”(7)丁玉柱:《王蒙舊體詩傳》,第38頁。。如果著眼于將詩做字面的解釋,以上評價是準確的,但是如果聯(lián)系王蒙創(chuàng)作《感遇》《赴新疆》時現(xiàn)實處境與其思想性格的復雜性,或許還可以對這些舊體詩進行更多層面的闡釋。正如錢鐘書所說,以文觀人,自古所難。(8)錢鐘書:《談藝錄》(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62頁。王蒙立志脫胎換骨,痛改前非,獻身邊疆的感情是否真如詩作中表現(xiàn)的那樣樂觀、熱烈和真誠,或許還有一定的討論空間。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對王蒙參加勞動改造時的精神狀態(tài)的記述或許可以為了解20 世紀60 年代的王蒙提供另一種參照。同在一擔石溝勞動改造,從維熙在與王蒙的閑談中表達了自己仍有寫作的想法,然而面對這位“難友”,王蒙卻不茍言笑,頗為嚴肅地說:“劃右以后,我打報告要求自謀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賣糖葫蘆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9)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9頁。對于從維熙的創(chuàng)作沖動,王蒙表示:“算了吧!別自作多情了。我是沒這份心思了!只想當好地球修理工!”(10)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第49頁。從維熙并不認為王蒙的回答是真誠的,因為在他看來,“反右斗爭之后,許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種奇異的保護色……但盡管如此,我還是感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嚴一些,好像他不茍言笑,真是到這大山里來大徹大悟,立地成佛似的”(11)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第49頁。。在從維熙眼中,王蒙痛改前非一心改造的說辭并不是發(fā)自內心,而是不得已的偽裝和自我保護。有意味的是王蒙也在自傳里提到了他與從維熙在一擔石溝的這次交談:“作家從維熙也在這里,他居然還找我談創(chuàng)作問題,我覺得他不識時務了,我覺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覺得他實在迂誠。”(12)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182頁。王蒙一方面認為從維熙在接受勞動改造時還談創(chuàng)作是“不識時務”“找倒霉”,另一方面他自己卻也偷偷借舊體詩創(chuàng)作抒懷。他雖然口頭表示“只想當好地球修理工”,并在《感遇》二首中痛陳悔過之情“覺今是而昨非”,一心“且舞鍬鋤逐大旗”,但當處境轉圜,王蒙又重新搞起創(chuàng)作。“我的人格似乎真的分裂了,要忠于革命,必須背叛文學,而愛文學搞文學,竟意味著變成革命陣營的可恥的叛徒。”(13)王蒙:《我在尋找什么》,《文藝報》1980年第10期。言談與行為的矛盾分歧之處,暴露出王蒙在風風雨雨中掙扎矛盾的內心世界。如果結合歷史語境來看,或許正是這種矛盾性才更貼近20 世紀60 年代真實的王蒙。
同樣,《赴新疆》四首也不能簡單認為是表現(xiàn)了王蒙“自己面對新的天地而涌動的新的豪情壯志”,看似振作樂觀的詩句背后其實潛藏著作者不得已的苦衷。雖然在王蒙復出之后的解釋中,他1963 年底奔赴新疆的選擇是為了尋求新的創(chuàng)作資源(14)如王蒙在采訪中曾表示“去新疆是一件好事,是我自愿的,大大充實了我的生活經(jīng)驗、見聞,對中國、對漢民族、對內地和邊疆的了解,使我有可能從內地—邊疆,城市—鄉(xiāng)村,漢民族—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較中,學到、悟到一些東西。”參見王蒙:《文學與我——答〈花城〉編輯部XX同志問》,《花城》1983年第4期。又如在自傳中他這樣解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對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學與渴望生活,對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參見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20頁。,目前也有諸多研究者沿用了王蒙的這一說法(15)如賀興安認為,遠赴新疆“是王蒙自己主動提出來的,而且是他‘摘帽’以后、可以發(fā)表作品、在大學講壇有份優(yōu)越工作后提出來的。……這位不到30歲的青年作家,處逆境,不喪志,在未來的安排上,仿佛是要先潛入谷底,以便獲得更高的翱翔。”參見賀興安:《王蒙評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47頁。。但是,一個始終被忽略的問題是,從常理上來看,王蒙這種拖家?guī)Э凇⒎艞壈卜€(wěn)的大學教師職位從北京奔赴新疆的做法,倘若只是如他所說,僅僅是為了尋找新的創(chuàng)作資源,未免太費周章,代價太大。即使北京教職的生活讓王蒙感到“不接地氣”,因而失去了與當時的主流文學導向相契合的機會,但要接近人民,接近農民,也不是非要去新疆不可。更何況王蒙當時還打算在新疆一待十年?(16)崔瑞芳曾問王蒙打算在新疆呆多久再重返北京,王蒙“毫不猶豫地自信地”回答妻子:“三、五年,頂多十年。”誰料到,他們一去就是十六年。參見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10頁。雖然從王蒙日后的創(chuàng)作和人生經(jīng)歷來看,在新疆的十六年生活的確如王蒙所言,成為他人生道路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僅就王蒙奔赴新疆的動機來看,除了尋找新的創(chuàng)作資源,王蒙赴疆也是因為其在1963 年底參加西山讀書會后敏銳地預感到了風雨欲來的政治環(huán)境,因此不得不疏離躲避風暴中心。如果將王蒙的這種“主動”理解為不得已的“自我放逐”,或許可以更好解釋《赴新疆》中“寒溫易貌越千河”“云山瀚海兩茫茫”“風風雨雨意彌堅”等詩句表現(xiàn)出的蒼茫沉郁,近似于貶謫詩的情感基調。而詩作中“春光唱徹方無恨”等表達詩人投身邊疆建設,奉獻“小我”融入“大我”的決心之語,既是詩人不愿自怨自艾,努力振作的樂觀性格使然,也難免有時代規(guī)范潛移默化的影響。偏離主旋律、沉湎個人“小我”情感的詩歌常常會受到批評和質疑,連帶著詩人自己也會被懷疑思想的正確性(17)郭小川《望星空》在1959年所受到的批評最能說明這一點。對于詩作中個人的“小我”的惆悵情緒,有評論家不客氣地指出:“怎么突然寫出這樣虛無縹緲、頹廢絕望的詩呢?是不是因為詩人的靈魂深入個人主義的東西沒有被清洗掉,一有所感或抵觸就自然地冒出頭來,因而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發(fā)生了動搖吧?”參見蕭三:《談〈望星空〉》,《人民文學》1960年第1期。。
由此可見,無論是《感遇》還是《赴新疆》,王蒙對自我情感的書寫中既包含著他自身深切的現(xiàn)實生活體驗,也摻雜著一定的修辭策略。兩種不同的影響因素相互聯(lián)系,交織在詩作中,體現(xiàn)了秉承著“少布”的理想主義精神的王蒙在進入20 世紀60 年代的歷史環(huán)境后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之間復雜糾結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相對于沈從文、曹禺等深受“五四”文化思潮影響的一代作家,王蒙這一代人更具有理想主義的樂觀、單純和朝氣。正如王蒙在自傳中所說,“我們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論,相信民族團結和人間友誼,相信工作,相信文件、會議、社論和總結,相信歌曲,相信領導,更相信人民”(18)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第246頁。。王蒙這一代人在革命勝利的號角聲中接受了革命理想主義教育并堅信不疑,接受了關于理想社會終將實現(xiàn)的允諾并虔誠地身體力行。作為來自革命內部的年青知識分子,王蒙懷有一種深厚而虔誠的社會烏托邦情節(jié),這既作為一種精神信念支持著他們投身于社會實踐,同時也使他們對革命的認知過于理想化和崇高化,缺乏理性的距離審視。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原罪”意識,這批年輕的“少布”們在遇到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時總是習慣性地將癥結歸結于自身,以批判和自我批判解決問題。《感遇》中“疾首煎腸”對自我創(chuàng)作的否定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做出的。而越覺得自己有罪,就越要堅定政治信仰和崇高的社會理想,以此表忠心,獲得“贖罪”。《赴新疆》中“春光唱徹方無恨”,“風風雨雨”也不改理想初衷,要把“微軀”獻給塞邊的奉獻精神正是這種“贖罪”“表忠心”的具體體現(xiàn)。
而另一方面,20 世紀60 年代,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的磨練后的王蒙已不再是楊薔云或林震那樣單純而天真的青年了,為了適應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真感情與“場面話”混雜在一起成了他不得不為之的處世策略。這也就是為何《感遇》《赴新疆》雖無發(fā)表的機會,但詩作的字里行間卻仍能辨認出作者被主流話語規(guī)范影響操控的痕跡。王蒙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遭際時這樣說道:“解放后的每次政治運動幾乎都是以文學開刀,終于,開刀輪到了自己頭上來了。于是,我‘自覺地’努力去否定文學,拋棄文學,首先否定自己……于是我由衷地歡呼‘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我認真地努力去領會‘沖霄漢沖云天能勝天’之類的樣板壯語。不怕人笑話也不怕人抓辮子,我其實覺悟得很晚,更談不上有什么抵制,我甚至曾經(jīng)努力去領會‘三突出’,‘高大完美’。盡管在我的潛意識里對此充滿了厭惡,盡管我常常在睡夢中哭濕了枕頭。”(19)王蒙:《我在尋找什么》,《文藝報》1980年第10期。當兒子王山問起王蒙這段往事時,王蒙亦是潸然淚下,不愿多談。(20)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第51頁。由此可見,對于勞動改造與奔赴新疆的這段經(jīng)歷,王蒙真實的情感體驗或許并不能僅僅以他在這一時期詩作中所表現(xiàn)的痛改前非、積極改造、向往奉獻邊疆的豪放樂觀之情概之,倒不妨用從維熙對他的一段評價進行補充:彼時的王蒙“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覺,其實在睜眼看著四周。與其說他表現(xiàn)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說他對這個冷酷的世界有著相當?shù)木X”(21)從維熙:《走向混沌三部曲》,第49-51頁。。20 世紀60 年代的王蒙已然告別了青春時代的天真和單純,變得更加深沉、謹慎,“蛻去了與生俱來的那層嫩皮,換上了一層堅實的外殼與鱗甲”(22)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二、現(xiàn)實的苦樂與紙上的“逍遙”
1965 年夏天,王蒙在新疆伊犁巴彥岱紅旗公社二大隊作為“蹲點”干部參加勞動期間,創(chuàng)作了《即景》《運麥》等八首舊體詩。如果說《感遇》和《赴新疆》書寫的是詩人在痛定思痛,在低沉悲愴中進行自我勉勵,努力振作的情感活動,那么王蒙這八首舊體詩則從側重內心世界的情感表達轉向對外在生活世界的關注,以輕快活潑的語言譜寫出一曲曲溫馨愜意的田園牧歌。例如:
即景(一)
濯腳渠邊聽水聲,飲茶瓜下愛涼棚。
犢牛無賴哞哞里,乳燕多情款款中。(23)以下四首詩最早均見于詩集《詩花滿天山》(烏魯木齊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辦公室編:《詩花滿天山》,烏魯木齊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辦公室,1979年,第102頁)。詩作署名王蒙并注明“以上諸詩作于一九六五年于伊犁農村參加勞動時”。其中《運麥》《八月》二首王蒙相關文集及傳記中皆未收錄,或為軼詩,特此補錄。
這首詩寫的是勞動一天后的詩人坐在纏繞著瓜果藤蔓的涼棚下休息飲茶的生活場景。聽著潺潺的流水聲,詩人洗去腳上的泥土,身邊的小牛犢“哞哞”地叫著仿佛在歡迎詩人,屋檐下新出生的燕子則在他頭頂款款飛翔、呢喃絮語。又如《運麥》描繪了生產勞動火熱場面:
運麥
運麥裝車緊,歸來星滿空。
依門阿娜望,涼面快耶棱!
有的舊體詩還贊美了伊犁當?shù)氐娘L土人情:
八月
清風清水繞青楊,果海瓜山土亦香。
酒似流泉歌似夢,叫人渾不憶家鄉(xiāng)。
即景(二)
蠶豆花開苦豆鋤,薔薇初謝馬蘭疏。
聲聲啼鳥春歸也,戶戶磨鐮夏麥熟。
在1965 年的大環(huán)境下,王蒙能寫下如此具有詩情畫意的田園牧歌,這首先與其當時的生活處境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相比從維熙、張賢亮等同時期作家的境遇,王蒙可以說是十分幸運的。雖然王蒙不得已遠走邊陲,但恰是因為伊犁的偏遠、消息閉塞使他遠離了政治活動的中心,獲得了天然的“避風港”。同時,伊犁當?shù)氐纳贁?shù)民族農民善良、質樸,他們并不因“右派”的政治身份而對王蒙另眼相待,反而與之相處融洽。此外,雖然王蒙也日日參加挖渠、揚場等繁重的體力勞動,但他還是以下放干部的身份參加勞動的,不僅無人對其強行管制、勞教,王蒙甚至還一度成為生產隊大隊長,受到當?shù)剞r民的尊重。所以,王蒙后來感嘆:“古語說,大亂避城,小亂避鄉(xiāng)。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亂,政治性的亂子,越是大城市越厲害。我當時若在北京,不被揭掉一層皮才怪。恰恰是邊疆伊犁,什么事都‘慢三拍’的伊犁,又是少數(shù)民族,所以和緩得多……我們到伊犁,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24)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64頁。1979 年復出之后,王蒙還以這段在伊犁生活勞動的經(jīng)歷作為寫作素材,創(chuàng)作了《在伊犁》系列小說。在小說中,伊犁的生活也被描繪得如同世外桃源般美麗寧靜,“我”不禁感嘆:“伊犁河谷,這是多么富饒的地方,盡管‘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國都亂糟糟,伊犁河谷的少數(shù)民族農民相對來說還算比較逍遙。”(25)王蒙:《好漢子依斯麻爾》(《在伊犁》之三),《北京文學》1983年第8期。
沒有理由懷疑王蒙對于伊犁的深厚感情。但是如果僅僅根據(jù)王蒙功成名就后對往事的追憶,和幾首當年留下的“田園牧歌”就認為王蒙真的能夠在“文革”前夕的邊陲“詩意地棲居”,那么我們將忽視王蒙精神邏輯中復雜糾結的一面。雖然王蒙遠離政治中心,但他的生活卻未必真如其詩作中表現(xiàn)得那樣愜意自得。
例如王蒙在伊犁參加運麥、揚場等生產勞動,舊體詩中著眼于“依門阿娜望”的溫馨人情和“運麥裝車緊,歸來星滿空”勞動歸來的愜意浪漫,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王蒙的勞動也有狼狽的另一面:“一到揚場時,王蒙的頭發(fā)上、眼鏡上、臉上、身上、衣服上和鞋子里外,不但掛滿塵土,而且全是細毛毛的芒刺纖維。那種土中求食的樣子,著實難看”(26)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53頁。。被王蒙描繪為“酒似流泉歌似夢,叫人渾不憶家鄉(xiāng)”的伊犁,實際上也并沒有那么美好。據(jù)崔瑞芳回憶,伊犁“大街上幾乎看不到小汽車,偶爾走過一輛蘇聯(lián)吉普‘嘎斯69’便算是豪華車輛了……車馬過處,塵土飛揚,空氣中充滿著牲畜糞的氣味”,而且走了不到一個小時,王蒙就不好意思地對崔瑞芳說:“其實,你已經(jīng)走完了伊犁的主要街道。這里就這么一條大街。伊犁的市容我們已經(jīng)欣賞完了。”(27)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39頁。
除了物質生活上的艱辛落魄,王蒙的精神世界也承受著很大的壓力。王蒙從北京不遠千里奔赴新疆,本是打算換個環(huán)境,重整旗鼓,卻不料他僅僅在新疆文聯(lián)工作不到半年,1964 年他就因為“文藝整風”的影響再次成為有“政治問題”的“多余人”,不但已經(jīng)寫好準備付印的報告文學《紅旗如火》被撤,下鄉(xiāng)搞“社教”的資格也被取消。無奈之下,新疆文聯(lián)只得將王蒙下放到伊犁巴彥岱作為“蹲點”干部參加公社勞動。短短幾年間,一個曾經(jīng)才華橫溢的年輕作家竟然只能在邊疆一間簡陋的農家小屋勉強找到立足之地,不僅創(chuàng)作無望,壯志難酬,政治身份又再次成了問題,王蒙精神上的苦悶可想而知。“這時期,王蒙經(jīng)常喝酒,飲酒量比過去增加了好幾倍。這現(xiàn)象我能理解,他心中太郁悶”,“王蒙的情緒很低沉。從城市到農村,幾乎所有的機構都癱瘓了,無政府主義達到極點,連巴彥岱農村的莊稼地都無人管理……在家里實在無聊,他反來復去地用維語熟背‘老三篇’;他養(yǎng)貓逗貓,他剁碎了白菜梆子喂雞……”(28)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67-72頁。在2000 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狂歡的季節(jié)》中,王蒙也借主人公錢文的經(jīng)歷揭示了這段新疆經(jīng)歷中落魄的一面。和王蒙的遭遇一樣,赴疆后錢文渴望重整旗鼓的夢想很快也遭到現(xiàn)實的打擊:“他沒有東西可讀,沒有東西可寫,沒有任何會議通知他參加,沒有任何事等著他去做。他瘦骨如柴,比在權家店時還不成樣子。在權家店勞動時盼著的是表現(xiàn)得好獲得摘帽,如今還能盼什么呢?摘了帽的叫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也就永無摘帽之日了。”(29)王蒙:《狂歡的季節(ji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頁。
由此可見,王蒙在20 世紀60 年代舊體詩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與崔瑞芳及王蒙在《狂歡的季節(jié)》中所敘述的新疆生活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反差。(30)需要補充的是,除了王蒙20世紀60年代創(chuàng)作的舊體詩,在王蒙20世紀80年代初創(chuàng)作的《在伊犁》及其重歸文壇后的諸多言談中,王蒙都對自己這段新疆經(jīng)歷充滿感激和贊美,而回避了艱苦和不光彩之處。但是在《狂歡的季節(jié)》中,王蒙卻一改常態(tài),揭露出這段新疆經(jīng)歷中的落魄艱難的一面。對于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具體論述,可參見黃珊:《從“逍遙游”到“受難記”——論王蒙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小說中的新疆經(jīng)驗書寫》,《文藝爭鳴》2020年第2期。在此去甄別哪一幅圖畫更接近王蒙當年真實的生活,或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論是“逍遙”還是苦難,其實都是王蒙對生活的主觀體驗的一部分。或許正如王蒙在自傳中所說:“到了伊犁,我基本上過的是‘三不管’的生活,是一個自由王國里的王子。然而無形之中自己又是一個無罪的罪人,是一個臉上刺著金印的流放者,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31)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第256頁。因此不妨將王蒙在伊犁的生活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和同時期其他作家的遭遇相比,王蒙的確因為遠離政治風波,免受肉體的拘束勞役而獲得了相對“逍遙”的生活,是“自由的王子”;但另一方面,王蒙作為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壯志難酬,“翻身”希望渺茫,巨大的生活落差,不得不虛耗生命的生活……這一切也確實成為王蒙沉重的精神壓力。一面是陽光,一面是陰霾,這或許都是王蒙當年“自我放逐”新疆生活的組成部分。
此處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王蒙在新疆的生活體驗既有陽光也有陰霾,但是在1965—1974 年這段時間僅有的幾首創(chuàng)作中,他對生活中的苦難陰霾避而不談,而總是大加歌頌生活中陽光的那一面?原因之一,應該是作家應對現(xiàn)實處境的生存策略。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以及1963 年、1964年關于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等,促使文藝界處在一種“風雨欲來”的緊張氣氛中。在這一大環(huán)境下,作家們往往憑著心理感應慎之又慎地審視忖度創(chuàng)作,任何偏離或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表達或許在創(chuàng)作者的“自我審查”中就被取消了表達的可能性。因此,像王蒙這樣報喜不報憂,回避苦難,歌頌生活的“樂觀”生活態(tài)度不是個例,俞平伯、沈從文、蕭軍等作家也在相似的歷史境遇下寫下了同樣閑適清新的田園牧歌。如俞平伯1969 年在“五·七干校”時創(chuàng)作的《楝花二首》《東岳集偕柰小坐玩月》,沈從文1970 年描寫干校生活的組詩《大湖景詩草》,以及蕭軍1969 年在京郊沙河接受勞動改造時創(chuàng)作的《自甘棄隨》等。即使在這些未公開發(fā)表,屬于“潛在寫作”范疇的作品中,這些作家也是依舊按照主流意識形態(tài)允許的范疇進行謹慎的創(chuàng)作。同時,王蒙等作家的這種謹慎的創(chuàng)作心理,也可從他們以舊體詩這一形式來抒懷的選擇見出。“整個中國雖然文網(wǎng)遍地,動輒得咎,但整個社會文化素質很低,舊體詩又有非同一般小說、散文通俗、普及易被抓辮子的優(yōu)點,對于無知淺薄的告密者又有不敢輕慢的特點,從而促成了古詩的先脫穎而出。”(32)林書:《說“紺弩體”》,羅孚編,朱正等箋注:《聶紺弩詩全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44頁。舊體詩相對曲折、古奧的表達方式,恰好滿足了詩人在緊張的文學環(huán)境下隱晦地傾訴自我情感的需要,為王蒙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情感表達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
此外,王蒙舊體詩中有意回避苦難、歌頌日常生活的創(chuàng)作,更是他在理想失落之后尋求自我的精神救贖,設法緩解現(xiàn)實施加于心靈重壓的一種方式。如果說20 世紀50 年代初的王蒙秉承著一種“社會主義新人”的角色自持,對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認知與敘述帶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和理想主義傾向,而20世紀60 年代初參加勞動改造與決定奔赴新疆時,王蒙雖然遭遇了“風風雨雨”,但是仍“心未冷”“意彌堅”,依然堅定著理想抱負,那么在1965 年寓居伊犁,理想落空,淪為“多余人”的王蒙已不得不收起“少布”時代對自我與社會的浪漫想象。《運麥》《即景》等詩中已再無之前作品中“且舞鍬鋤逐大旗”“三生皮肉獻河山”“自有男兒勝天公”“猶有微軀獻塞邊”之類的理想抱負之語,取而代之的是對農家日常生活的欣賞與滿足。當理想與激情隱去,如何適應生活的落差與承受精神的重壓并生存下去成為最重要也最實際的問題。“窮極無聊,是的,那歲月的最大痛苦是窮極無聊,是死一樣地活著與活著死去。死去的你的心,創(chuàng)造之心,思考之心,報國之心;死去你的心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憶——過去的一切如黑洞,慘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象似乎都只能帶來危險和痛苦。”(33)王蒙:《我是王蒙——王蒙自白》,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年,第100-101頁。在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下,王蒙只有從日常生活中尋找出路,獲得精神的慰藉與解脫。在伊犁創(chuàng)作的幾首舊體詩中,王蒙不寫勞動的辛苦疲憊,而是寫勞動后“依門阿娜望,涼面快耶棱”的溫馨,寫洗去一身灰塵后“濯腳渠邊聽水聲,飲茶瓜下愛涼棚”的輕松愜意,從辛苦的勞作中品咂出了陶淵明般的田園樂趣。甚至在與妻子的家信中,王蒙也以詩意甚至不乏夸張的筆觸贊美生活,“每封信都是熱情歌頌,一片樂觀、信心和贊美”(34)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26頁。。王蒙這種有意將生活詩意化,而回避現(xiàn)實艱辛與不光彩之處的做法,讓崔瑞芳不禁感嘆:“真是奇怪,已經(jīng)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了,這個王蒙仍然那樣透過玫瑰色的色彩描繪著、感受著邊疆大地,用無比光明與歡樂的胸懷去擁抱生活”(35)方蕤:《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第26頁。。其實,這不是王蒙看不到生活中卑瑣破敗的一面,也不是感受不到生活境遇的落差,而是王蒙需要借這些從日常生活中發(fā)掘的詩意來調整心態(tài),填補理想主義精神失落后空虛的內心世界,為生存注入勇氣與信心。
三、傳統(tǒng)文人心態(tài)的復活
無論是生活環(huán)境的不得已遷移,還是郁郁不得志的心態(tài),王蒙20 世紀60 年代的遭遇都與歷代傳統(tǒng)文人的貶謫經(jīng)驗存在某些部分的相似性。“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國古代文人們氣盛才高,卻因忠被貶者不在少數(shù)。而這些被貶文人在憂憤感傷自己命運不幸的同時,往往愈加堅定了自己的理想和忠心:“兩地江山萬余里,何時重謁圣明君”(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何由返滄海,昨日謁明君”(崔峒《初入集賢院贈李獻仁》),“孤寒明主信,清直上天知”(王禹偁《謫居感事》)……中國古代文人們身處貶所而忠心彌堅,王蒙亦如是。在一擔石溝,他“昏昏舊事拋云外”,用“且舞鍬鋤逐大旗”證明自己虔誠的理想。在“自我放逐”,遠走邊疆的火車上,他寫下“死死生生心未冷,風風雨雨志彌堅”。在王蒙的自我修辭中,“我”仿佛一個歷經(jīng)磨難的“圣徒”,雖然受到很多挫折磨難,但是“心未冷”“志彌堅”,仍然要將最后的熱血奉獻給祖國邊疆。同樣,當烏托邦的社會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激情在現(xiàn)實一次次打擊中逐漸消逝,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們在歲月空度中轉而向日常生活中尋找詩意,以填補精神空虛,尋求自我救贖的選擇,也很容易在王蒙等20 世紀60 年代的作家身上找到相似的側影。例如王蒙《即景》:“濯腳渠邊聽水聲,飲茶瓜下愛涼棚”,描寫詩人于農閑小憩時的田園之樂,就與陶潛“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歸田園居五首》其五)所表現(xiàn)的詩人躬耕田間,安貧樂道的心境有頗多相似之處。又如“酒似流泉歌似夢,叫人渾不憶家鄉(xiāng)”“蠶豆花開苦豆鋤,薔薇初謝馬蘭疏”等句,王蒙將“落難地”視為世外桃源的詩情也與蘇軾“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黃梅次第新”(《惠州一絕·食荔枝》),韓偓“旗亭臘酎逾年熟,水國春寒向晚多”(《雪中過重湖信筆偶題》),劉禹錫“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秋詞二首(其一)》)等詩人仕途失意后寄情于村野湖山的詩懷遙有呼應。
當然,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處世經(jīng)驗不僅為王蒙等作家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精神資源,也影響了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體。作為以小說見長的作家,王蒙20 世紀60 年代突然改以舊體詩作為思想與情感表達的主要體裁,個中緣由,除了上文所提及的舊體詩表達上隱晦曲折的特點之外,也與舊體詩這種“有意義的形式”承載著現(xiàn)代詩所不具有的傳統(tǒng)文化情感有關。“在舊體詩定型化的表達方式和它所對應的情感現(xiàn)象之間,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感時書憤、陳古刺今、述懷明志、懷舊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說禪慕逸……構成了吸引著歷代詩人的情感圈。”(36)劉納:《舊形式的誘惑——郭沫若抗戰(zhàn)時期的舊體詩》,《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王蒙作為一個現(xiàn)代文人,其迫于政治等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從首都遷往大漠邊疆的心路歷程,恰好與舊體詩“感情圈”中所包含的某些情感產生了呼應。抒懷遣志,或寫身居田園恬淡曠達之樂,或述遠遷塞外孤獨迷惘之殤,這既是王蒙詩中的主要情感表達,也是舊體詩這一文學形式本身早已定型化的情感指向。可以說,并不是王蒙有意以舊體詩的形式來書寫他的這些感情,而是這些感情本身就早已和舊體詩的形式融合在一起。
作為一名曾經(jīng)滿懷現(xiàn)代革命理想的“社會主義新人”,王蒙由“新”轉“舊”——由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轉向舊體詩,文體轉變背后映射的正是王蒙等知識分子文化心態(tài)的轉變。舊體詩所蘊藏的歷代文人們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固然為這些身處特殊年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處理精神信仰危機與表達個體生存經(jīng)驗的最佳形式,可如果僅僅將這些歷史經(jīng)驗作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生存策略和心理慰藉,那么這些知識分子就失去了將歷史經(jīng)驗加以轉化超越,反思與解決當代產生的新問題的機會。例如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文人們秉承儒家精神,“篤信善學,死守善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追求德化人世和人的完美性恰好是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之一,亦即儒家革命精神的理念基礎”(37)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個人信仰與文化理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0頁。。儒家所弘揚的這種“此心應擔當?shù)禄途葷煜轮笕巍本哂泻軓姷某墒ネ醺信c救濟天下的使命感,該思想一旦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這種集道德權威與政治權威于一體的政體很容易帶來嚴重的后果。而在另一方面,對人的日常生活訴求的正視,對世俗欲望的肯定,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則可以制衡或者消解政道結合的準宗教化的意識形態(tài)。“在一個‘圣化’社會中,社會制度的合法化機制與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都帶上了準宗教的特點,缺乏這種神圣資源……的生活被認為是邪惡的,大逆不道的或至少是無意義的;而世俗化則使得人的存在,人的日常生活與這種‘圣化’的精神資源之間的關系被解構或者被極大地削弱,人們不再需要尋求一種超越的神圣精神資源為其日常生活訴求(包括與物質生活相關的各種欲望、享受、消退、娛樂等等)進行‘辯護’。”(38)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第170頁。然而無論古今,在很多情況下知識分子們轉而關注日常油鹽、田園雞黍,都是在不得志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他們贊美日常生活常常是為了回避苦難,或尋求仕途失意后的心靈安慰,而不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以追求真善美為目的來對教條化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予以否定和消解,故而無助于現(xiàn)實的改變。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王蒙等知識分子對革命理想信念的追求與中國傳統(tǒng)士人對“道”的理想主義精神的奉持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直到20 世紀90 年代,王蒙才在新的文化思潮沖擊下以“躲避崇高”為名展開這場遲到多年的反思。
同樣,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借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歷史經(jīng)驗來回應現(xiàn)實問題,棲居于心靈的“避風港”時,也將無法對這些傳統(tǒng)文人心理的局限性進行反思與超越。中國古代文人們在遭遇貶謫后往往沿襲著“窮則獨善其身”的思維模式,他們注重個人的道德品格修養(yǎng),借松、竹、金、戈等物以自勉自喻,“時來終薦明君用,莫嘆沉埋二百年”(李昌符《詠鐵馬鞭》),“不與夭艷爭春色,獨守孤貞待歲寒”(王禹偁《官舍竹》),以身遭貶謫而不降心辱志為傲。而當他們意識到理想落空,報國無望時,他們便將目光投向外在自然世界,以此化解現(xiàn)實的苦難:“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蘇軾《初到黃州》),“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歐陽修《黃溪夜泊》)……這些處世經(jīng)驗固然體現(xiàn)出文人樂觀的精神和達者胸懷,但歸根結底,這終究只是一份指導人們在困頓中如何自我開解的生存策略,是中國古代文人流傳下來的對人生榮辱起落的解釋方法,其遵循的其實是這樣一個邏輯:如果遭遇仕途不順,被君主所棄,那一定只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因此人越在困厄的環(huán)境中越不能抱怨現(xiàn)實,降心辱志。文人們要做的,無論隱逸也好修身也罷,“千淘萬流雖辛苦”,其終究還是渴望等到“吹盡狂沙始到金”的一天。而一旦等到“明君”撥云見日將其召回,這些士人們便無一不心懷感恩,然后又回到舊有的體制中去了。即使是批判,他們也常以維護權威意識形態(tài)為終極目的,而少有純粹出于對真理和美的追求。正如鄧曉芒所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善其身是濟天下的資本,濟天下是窮獨時的向往,向往而不達則是一切牢騷的根源。所以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眼光總是盯著政治和官場,不是爭寵攬權,就是憤世嫉俗,少有對自然知識和客觀真理的探索和研究”(39)鄧曉芒:《批判與啟蒙》,武漢:崇文書局,2019年,第218頁。。
傳統(tǒng)文人的這種思維模式已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積淀的一部分,并潛移默化地融入了當代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如果我們的追求是執(zhí)著的,我們的文學發(fā)展為什么總發(fā)生非邏輯性的起伏?是否在我們價值觀的深處古人的‘出世與入世’‘拯救與逍遙’‘光宗耀祖’‘衣錦還鄉(xiāng)’與‘隱逸山林’的兼容性選擇依然陰魂不散?”(40)李揚:《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252頁。一個明顯的例證,即王蒙在1961 年勞動改造時寫下的《感遇》二首。“疾首煎腸憶舊時,風花雪月曾相欺”,在遭遇波折時,王蒙首先將問題歸結于自身,一邊否定前作,一邊努力通過勞動“修身養(yǎng)性”、努力奉獻,證明自己未改的忠誠。而到了20 世紀80 年代,當王蒙的《春之聲》《蝴蝶》《雜色》等作品被看作是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學習成果受到非議,并在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被胡喬木勸導“少來點‘現(xiàn)代派’”后,王蒙的文風又為之一變,其創(chuàng)作的《在伊犁》系列小說無論在藝術風格,還是思想內容上,都與《雜色》等作品大相徑庭。《春之聲》(1979)、《蝴蝶》(1980)、《雜色》(1981)與《在伊犁》(1983)的創(chuàng)作時間不過相差幾年,作品中的人物又幾乎處于同樣的歷史背景下,可是《在伊犁》中的“老王”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而鐘亦誠、張思遠們卻飽受靈與肉的磨難。如此短暫的創(chuàng)作間隔,作家對同一個時代的理解與評價卻發(fā)生了相當明顯的變化,這種“變”,恐怕只能理解為“應時因勢而變”。雖然王蒙對《在伊犁》頗為滿意,稱其為“真正的小說”,但是作為一名當代知識分子,王蒙又提供了哪些超越了傳統(tǒng)士人心態(tài)的處世經(jīng)驗呢?而當代知識分子們試圖借用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歷史經(jīng)驗來回應現(xiàn)實問題時,可能也需要警惕傳統(tǒng)文化所留下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