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內(nèi)外與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一個側(cè)面
——論付秀瑩《陌上》中的“超市”書寫
李保森
(河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河南 開封475004)
付秀瑩的長篇小說《陌上》是近年來鄉(xiāng)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它繞開了波瀾壯闊的經(jīng)濟改革、社會更迭等重大主題,而以具象豐饒的細節(jié)、微妙復(fù)雜的關(guān)系、綿密纏繞的心思,對時代作一側(cè)面的回應(yīng)與再現(xiàn)”(1)曹霞:《美學(xué)的自覺與“陌上中國”的建構(gòu)——付秀瑩小說論》,《當(dāng)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4期。。在這部小說中,居于北京的付秀瑩把經(jīng)由和父親通話、自己返鄉(xiāng)等途徑獲得的感性經(jīng)驗進行了文學(xué)的熔鑄,從而完成了對“芳村”,也即當(dāng)下中國鄉(xiāng)村的素描和塑形,并凸顯了本人獨特的美學(xué)經(jīng)驗和審美創(chuàng)造,如古典美學(xué)和抒情風(fēng)格等等。在寫作內(nèi)容上,付秀瑩延續(xù)了賈平凹《秦腔》中“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2)賈平凹:《秦腔·后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18頁。。不過兩者又有差異,付秀瑩有意打破了章節(jié)前后的時間聯(lián)系,不是“流年式”的連續(xù),而是跳躍的、自由的,不以事件為紐帶,而以人物為中心,章與章之間僅僅有人事上的微弱關(guān)聯(lián),而無時間上的彼此呼應(yīng),從而形成了“桔子”式的結(jié)構(gòu)特征,而“芳村”正是包裹這些桔子瓣的果皮。這一特性使敘述者獲得了極大的自由,也使文本獲得了開放性,鄉(xiāng)村包括外在空間變遷和內(nèi)部肌理嬗變等在內(nèi)的生活狀況,盡可能地在文本中得到顯露和呈現(xiàn)。因此,可以說,在寫作主題上,《陌上》和新世紀以來的鄉(xiāng)土寫作保持了一致,“寫的不再是一個或幾個人物,而是寫了一個村莊、一個文化群落、一種生存狀態(tài)”(3)雷達:《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概觀》,《小說評論》2007年第1期。。而在這部小說中,具有現(xiàn)代性特征的“超市”被重點展現(xiàn)和書寫,從而使“超市”書寫得以成為考察處于社會變遷中的村莊、文化群落及其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有效視角。
一、《陌上》與鄉(xiāng)村的現(xiàn)代性進程
《陌上》中茂盛、駁雜的日常生活構(gòu)成了其敘述的主要部分,作為日常性事物的超市自然也被納入了其中,并在文中多次出現(xiàn)。超市是一個攜帶著現(xiàn)代文化信息的物質(zhì)空間,因而也可以被視作現(xiàn)代性的表征。如此,當(dāng)超市進入鄉(xiāng)村并作為一股隱而不顯的力量參與鄉(xiāng)民的生活運轉(zhuǎn)、鄉(xiāng)村的文化重構(gòu)時,正構(gòu)成了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一個側(cè)面、一種具體體現(xiàn)。付秀瑩在《陌上》中的超市書寫,不僅是對當(dāng)前鄉(xiāng)村的時代狀況進行呈現(xiàn)時所借助的途徑或意象,還以具象的方式接續(xù)和展示了鄉(xiāng)村的現(xiàn)代性進程。在這個意義上,《陌上》嵌入到百年鄉(xiāng)土文學(xué)敘事譜系中,并以自身的當(dāng)下性而涌動著鮮活的氣息。
有學(xué)者認為,“從20 世紀40 年代解放區(qū)開始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實際上就是表現(xiàn)新的現(xiàn)代性秩序?qū)ψ栽卩l(xiāng)土社會的滲透、介入、整合、改造的過程,這類小說我們也可以稱之為‘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敘事’”(4)王宇:《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敘事與鄉(xiāng)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紀40—50年代趙樹理、李準文本為例》,《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3年第1期。。其實,這一進程從中國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的工業(yè)化、城市化起步之時,就已經(jīng)在進行了。更準確地說,是在晚清遭遇西方列強時就已開始,“現(xiàn)代性在中國的發(fā)生,既有以大炮為表征的強暴的一面,也有以新奇的洋貨為表征的誘惑的一面”(5)王一川:《現(xiàn)代性體驗與文學(xué)現(xiàn)代性分期》,《河北學(xué)刊》2003年第4期。。不過,這一時期的現(xiàn)代性在規(guī)模和程度上都不夠顯著,存在著明顯的地區(qū)差異、群體差異。與之相比,肇始于20 世紀40 年代的新的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出更為整體、明確的特征,且有更為一體化的政黨政權(quán)、更具說服力的理論學(xué)說(共產(chǎn)主義理論)、更廣泛的社會動員、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參與其中,從而使整個的中國鄉(xiāng)村和民眾都卷入其中,相繼出現(xiàn)了互助組、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生產(chǎn)和生活組織形式。這些社會主義實踐使農(nóng)村發(fā)生了可謂是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兩個時期的差別,鮮明地體現(xiàn)在“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敘事”(6)在“五四”時期,以魯迅等為代表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以啟蒙者的身份,在文學(xué)作品中借助現(xiàn)代文明之光對鄉(xiāng)村進行了照亮,著重展示了農(nóng)村的愚昧狀況,揭示了農(nóng)民的精神污垢。但這種啟蒙敘事,忽視了鄉(xiāng)村民眾的物質(zhì)處境,脫離了民眾的生存體驗,因而顯得格格不入,造成了啟蒙的悖論。進入延安時期,農(nóng)民的社會主體性獲得了充分的認可和推崇,寫農(nóng)民、為農(nóng)民寫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命題,因而在題材、人物塑造、主題安排等方面,都表現(xiàn)出較強的民族性、地方性特點,如趙樹理等的創(chuàng)作;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廣大農(nóng)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實踐,在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乃至生活方式都出現(xiàn)了新的調(diào)整和變化,這一時期的文學(xué)作品將這些實踐作為創(chuàng)作主題,論證實踐的合理性和先進性,動員民眾積極參與,如趙樹理、柳青、周立波、李準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
隨著中國社會發(fā)展方向的調(diào)整,尤其是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的新路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路徑和目標也有所變動——以追求個人或家庭致富為主要動力。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首先從農(nóng)村開始,積極推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極大地恢復(fù)了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生活自主權(quán),實現(xiàn)了對勞動力的解放,從而解決了吃不飽的歷史難題,農(nóng)村貧窮面貌逐漸得到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市場和商品貿(mào)易日漸放開,對農(nóng)民而言,追求和積累個人或家庭的財富成為一種可以實現(xiàn)的愿景。在這里,財富不僅是指貨幣積累,還包括對現(xiàn)代物質(zhì)的有償消費和使用,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心靈體驗。例如劉慶邦《到城里去》中,宋佳銀的購買自行車,并用心保管,引來了村人的羨慕之情,滿足了宋本人的虛榮心,生動表明了消費具有在使用價值之外的意義生產(chǎn)功能。
隨后,規(guī)模日漸宏大的城市化、工業(yè)化、商業(yè)化進程也把鄉(xiāng)村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huán),或者成為勞動力輸出地,或者作為消費市場的開拓地,或者成為特定資源的提供地,又或者是某種后果或代價的承受者。這些力量持續(xù)地改寫著鄉(xiāng)村的面貌。可以說,從新時期農(nóng)村改革到20 世紀90 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在延續(xù)至今的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進程中,主流意識形態(tài)仍然作為主導(dǎo)性因素,又加入了城市、商品、商業(yè)、技術(shù)等新興因素。主導(dǎo)性因素與新興因素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當(dāng)日新月異的現(xiàn)代物質(zhì)、技術(shù)開始重塑整個社會生活的面貌時,也在瓦解著鄉(xiāng)村的舊秩序,同時建立著新秩序,如電視、手機、洗衣機、電腦、汽車(7)關(guān)于這些物質(zhì)的文化功能分析,可參見南帆《雙重視閾——當(dāng)代電子文化分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汪民安《論家用電器》(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徐敏《消費、電子媒介與文化變遷——1980年前后中國內(nèi)地走私錄音機與日常生活》(《文藝研究》2013年第12期)等等。,以及本文所論述的超市等等。這些新事物便利了民眾的生活,擴展了他們的活動空間,打開了他們的視野與想象力。因此,這些具體的物質(zhì)、技術(shù)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在參與、影響著鄉(xiāng)村秩序的建構(gòu),顯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問題。
通過上述簡單的梳理,可以說20 世紀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先后經(jīng)歷了啟蒙現(xiàn)代性、革命現(xiàn)代性和物質(zhì)現(xiàn)代性等三個歷史階段。雖然鄉(xiāng)村在這三個歷史階段中所發(fā)生的變化廣度與深度不一,但都攪動了“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8)參見金觀濤、劉青峰:《盛興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整體上使鄉(xiāng)村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穩(wěn)定走向變動,踏上了艱難而沉重、幸福而苦澀的變革之路,也使鄉(xiāng)村文學(xué)敘事在歷史階段形成了不同的時代主題。鄉(xiāng)村作為中國社會現(xiàn)代性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鄉(xiāng)土文學(xué)不斷滋長的重要動力。鄉(xiāng)村在種種外部力量的介入下不斷被塑形,而“鄉(xiāng)土”的語義隨之發(fā)生著嬗變,鄉(xiāng)土文學(xué)也就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風(fēng)格和主題。付秀瑩《陌上》即是以鮮明的時代色彩為百年鄉(xiāng)土文學(xué)提供了新的敘事,書寫了當(dāng)下的中國鄉(xiāng)村。
需要說明的是,鄉(xiāng)村文學(xué)敘事并非簡單地對鄉(xiāng)村的社會主題進行呼應(yīng),而是在某一時代背景下,在具體的敘事情境中,寫出個體成員的命運軌跡和悲歡體驗。對此,付秀瑩有著自覺的意識:“寫芳村的各色人物,寫他們在時代巨變中的命運和悲歡”(9)付秀瑩:《為什么如此執(zhí)著地書寫中國鄉(xiāng)村》,《學(xué)習(xí)時報》2017年08月04日第08版。。相比于社會學(xué)、政治學(xué)的宏觀分析而言,文學(xué)始終在對個體生命的遭際給予及時的回應(yīng)和關(guān)懷,從而始終擁有自身的魅力和獨特價值。
二、超市與鄉(xiāng)村的耦合
在《陌上》中,許多現(xiàn)代性的事物出現(xiàn)在鄉(xiāng)村中,并已然在鄉(xiāng)村落地生根,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汽車、手機、微信、服裝等等。例如小說中的服裝,作者細致地描寫了許多顏色豐富、樣式各異、四時不同的衣服、飾物,如素臺的“蔥綠小衫兒”“鵝黃軟坎兒”“茶色薄呢裙”“奶白的高跟鞋”“淺粉色絲綢裙子”,春米的“淺黃裙子”“藕荷色小夾襖”“靛藍色燈芯絨肥腿褲子”,建信媳婦的“鸚哥綠薄呢裙”“桃紅高領(lǐng)小毛衣”“嫩黃水紋絲巾”“草綠暗花的大絲巾”等等。作者不厭其煩地描寫這些色彩斑斕、樣式各異、分類細致的衣物,不僅是對人物的生活水平、裝飾風(fēng)格和審美觀念等的顯現(xiàn),以及對鄉(xiāng)村的點綴,還有著豐富的社會學(xué)意味:現(xiàn)代商品已然開始組織著甚至支配著鄉(xiāng)村民眾的生活,鄉(xiāng)村民眾同樣在共享商品社會和物流通達的福利與便利。
但無論是服裝,還是手機、汽車等,這些現(xiàn)代性事物都主要附著于私人之上,鮮明地體現(xiàn)著個人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和經(jīng)濟狀況,是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程度在單個個體或家庭上的體現(xiàn)。而超市則與上述事物有著不同的特征:它是一個公共的、開放的、流動的場所,是群體交往的中介,因而也是展示各色人物言行舉止的窗口;它以展開商品買賣為主要內(nèi)容,具有現(xiàn)代交易的相似特征,是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進程的直接反映。在這個意義上,本文中所論述的“超市”實際上起著“認識裝置”的作用。
超市,是超級市場(super market)的簡稱,是一種規(guī)模大型的現(xiàn)代零售業(yè)商店。超市內(nèi)一般會按照一定的秩序,擺放不同品牌、種類和價格的商品以方便消費者自由選購,并在出口處統(tǒng)一結(jié)賬。這種自助式的商業(yè)經(jīng)營模式保證了消費者的購買自主權(quán),滿足了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超市最早出現(xiàn)在20世紀30 年代的美國紐約。“二戰(zhàn)”后,特別是20 世紀五六十年代,超市在世界范圍內(nèi)獲得了較快的發(fā)展。在20 世紀90 年代,超市開始進入中國大陸,“它們短短幾年時間就在中國內(nèi)地確立了零售業(yè)新的經(jīng)驗理念與方式,并且徹底地改變了中國消費者習(xí)慣的購物方式”(10)孫驍驥:《購物兇猛——20世紀中國消費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年,第412頁。。隨后,大陸本土的超市經(jīng)營公司開始出現(xiàn)。隨著中國城市化、現(xiàn)代性進程的深入,超市也日漸進入鄉(xiāng)村。
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鄉(xiāng)村的商品買賣主要是通過供銷社(11)949年11月,中央成立了中央合作事業(yè)管理局,主管全國合作事業(yè);1950年7月,中央合作事業(yè)管理局召開了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lián)合總社章程(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華全國合作社聯(lián)合總社,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和管理全國的供銷、消費、信用、生產(chǎn)、漁業(yè)和手工業(yè)合作社;1982年,在機構(gòu)改革中,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第三次與商業(yè)部合并,但保留了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牌子,設(shè)立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保留了省以下供銷合作社的獨立組織系統(tǒng);1995年2月,黨中央、國務(wù)院根據(jù)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和深化農(nóng)村改革的要求,從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出發(fā),在總結(jié)供銷合作社過去改革和發(fā)展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作出了《關(guān)于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明確了供銷合作社的性質(zhì)、宗旨、地位和作用,并決定恢復(fù)成立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提出了支持供銷合作社改革發(fā)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進入新世紀后,該機構(gòu)再次做出調(diào)整。實現(xiàn)的,而且還要憑票購買。物資短缺、供應(yīng)不足、購買能力不足、服務(wù)人員態(tài)度不好,是其時商業(yè)制度的主要弊端。隨著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的過渡和轉(zhuǎn)型,私人經(jīng)營的商店開始成為鄉(xiāng)村商業(yè)活動的主流,供銷社日漸失去國家庇護的優(yōu)勢,在市場競爭上盡顯落魄之色。超市進入鄉(xiāng)村后,憑借在經(jīng)營模式、商品規(guī)模等方面占有的優(yōu)勢,開始成為新的主要商業(yè)經(jīng)營方式。
在日常性的商店交易之外,鄉(xiāng)村還有另外一種交易方式作為補充,即集市,鄉(xiāng)民稱之為趕集,“鄉(xiāng)村集市不僅融入村民生活之中,且在其發(fā)生、發(fā)展中帶有鮮明的鄉(xiāng)村烙印”(12)韓茂莉:《十里八村——近代山西鄉(xiāng)村社會地理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第150頁。。這種集市通常是露天的,以約定俗成的方式定期舉辦,早期主要以美味小食、生活用品、農(nóng)產(chǎn)品、農(nóng)具、農(nóng)畜為主,后來交易內(nèi)容日漸擴展,也有許多現(xiàn)代商品。《陌上》中就描寫了喜針在農(nóng)歷八月十二這一天去青草鎮(zhèn)趕集的場景。
對于鄉(xiāng)村而言,超市是外來的新事物。超市在鄉(xiāng)村的運營,既是超市適應(yīng)鄉(xiāng)村特征的一個過程,又是鄉(xiāng)村接受超市的一個過程。鄉(xiāng)村的超市,在商品的規(guī)模、種類、質(zhì)量、價格等方面,以及消費的層次、頻率、數(shù)量等方面,都難以與城市中的超市相比。同時,由于鄉(xiāng)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人際交往模式和特征,兩者的差異影響了超市的具體經(jīng)營方式。鄉(xiāng)村的地理空間有限,且處于相對靜止的文化狀態(tài),民眾的生活方式相似,人際網(wǎng)絡(luò)又是主要建立在血緣、婚姻、地緣等基礎(chǔ)上,人們在長時期的接觸和交往中,彼此相當(dāng)熟悉了解,形成了費孝通所說的“熟人社會”(13)參見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費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113頁。。城市則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這與它的空間繁多、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且處于流動狀態(tài)有關(guān)。在城市中的人彼此互不認識,除了工作、生活等相對固定的交往空間外,有的即使是鄰居也因為安于自己的屋內(nèi)而互不相識,在其它場合上基本是臨時性、一次性的交往。
超市的出現(xiàn)適應(yīng)了城市人的生活和交往的需要,提高了購物的效率,保護了顧客的隱私,免除了遇到熟人時可能會有的尷尬、不便等顧慮。顧客根據(jù)自己的需要自由挑選,商場的服務(wù)員僅僅提供向?qū)У淖饔茫p方互相不知根底,自然無從交流。但在鄉(xiāng)村則是另一幅不同的情形,且不說顧客在超市遇到熟人的概率極高,開超市的人就是熟人。這樣,彼此之間打招呼、聊天、問詢等就經(jīng)常發(fā)生,這時候的超市提供了社交的場所。這種熟人相遇與交談的場景,具有兩面性:既使買賣增添了人情味,得到店主的主動讓利,又可能給顧客帶來不便,造成某種負擔(dān)(如耽誤時間、影響選擇等),不能隨心所欲地購買所需。
鄭也夫曾針對我國的傳統(tǒng)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的不同人群特征,提出了“人格信任”和“系統(tǒng)信任”兩個概念。“人格信任”建立在熟人之間的彼此熟悉這一前提下,“系統(tǒng)信任”則是在陌生人之間展開合作時生長而成的。(14)可參見鄭也夫:《走向殺熟之路——對一種反傳統(tǒng)歷史過程的社會學(xué)分析》,《學(xué)術(shù)界》2001年第1期。在社會向流動性、開放性的轉(zhuǎn)型、建設(shè)和發(fā)展過程中,“系統(tǒng)信任”顯然具有相當(dāng)重要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基礎(chǔ)性的。對于以等價交換、自愿買賣為原則的商業(yè)活動而言,“系統(tǒng)信任”顯示了買賣雙方的平等地位。但在由“人格信任”占據(jù)主流地位的鄉(xiāng)村社會,既有可能增強、滋養(yǎng)“系統(tǒng)信任”的生成,又有可能破壞、干擾“系統(tǒng)信任”的生長。這一點在《陌上》的幾處場景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顯示。
三、“超市”內(nèi)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觀念的博弈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超市既是一個物質(zhì)空間,又是一個觀念載體,是鄉(xiāng)村新秩序(現(xiàn)代秩序)建構(gòu)的一塊基石。超市的功能不僅在于提供民眾的日常生活所需,還由于它本身就是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攜帶著現(xiàn)代社會的相關(guān)準則,進入鄉(xiāng)村后,起著傳遞新的價值觀念的功能。那么,當(dāng)它在有著深厚文化慣性和特定倫理規(guī)則的鄉(xiāng)村中出現(xiàn)時,會發(fā)生什么樣的場景呢?
芳村中的超市有好幾家,但小說中的幾處場景都是圍繞秋保家的超市展開描寫的。這首先與這個超市的地理位置有關(guān):秋保家的超市位于芳村大街的正中央,是村委會小白樓的臨街門臉,附近還有難看家的小飯館、耀宗的醫(yī)院,人來人往,一片熱鬧景象;其次,可能是作者在敘事上操作簡便的考慮;再次,還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借助這個現(xiàn)代性空間展現(xiàn)鄉(xiāng)村的人情物理,“鄉(xiāng)土小說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諸因素變成為舉足輕重的事件,并且獲得了情節(jié)的意義”(15)[蘇]M.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9頁。。在秋保的超市里,既有其樂融融的鄉(xiāng)間溫情和民間意趣,又有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觀念之間的碰撞與沖突。這也就是說,秋保家的超市雖然是構(gòu)成鄉(xiāng)村空間秩序的日常部分,卻具有癥候式效應(yīng),在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起著“磨刀石”的作用。因此,對這些場景的關(guān)注和考察,可以具體地透過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一個側(cè)面,探討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實境況,具體內(nèi)容如下文所述。
(一)溫情:熟人社會的交往特征
在城里“開發(fā)廊”的香羅回到了芳村,去秋保家的超市購物。秋保一看見她,就喊著“嬸子”,趕緊招呼起來,并互相開起了玩笑,還夾雜著頗有暗示性的性話語,這就惹惱了香羅,形象地展示了鄉(xiāng)村的民間性。香羅在超市里挑了一箱酸奶、一箱六個核桃、兩盤雞蛋、一只白條雞、半斤咸驢肉和一些零嘴。秋保開心地算賬收錢,幫著香羅裝袋,又讓自己的媳婦國欣把香羅送回家,還拿了一個保溫杯作為贈品。(16)付秀瑩:《陌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46頁。同樣,當(dāng)蘭月來到秋保家超市時,秋保便問道:“啊呀,人民教師下班啦?”接著,還是用性話語“挑逗”對方,引來了蘭月既惱又羞的責(zé)罵。一番口舌后,蘭月挑了一袋豆奶、一袋芝麻糊和一箱方便面。秋保跟在后面,說蘭月連二斤肉也舍不得割,一方面是在逗趣,另一方面也有想要擴大自己生意的意圖。(17)付秀瑩:《陌上》,第241頁。
在這兩個場景里,敘述者首先展示的是鄉(xiāng)村中的熟人交往特征,商家和顧客彼此之間總有著或多或少的關(guān)系關(guān)聯(lián)。秋保對顧客的職業(yè)、收入、個人品性等情況都有所了解,因而能相應(yīng)地和她們展開對話,并獲得對方的回應(yīng)。這一點顯然不同于城市中單純的超市購物行為。其次,從香羅和蘭月所購物品來看,這些商品已經(jīng)不只是生活的必需品了,而具有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質(zhì)量的作用,側(cè)面展示了她們各自的生活水準和經(jīng)濟狀況。在這里,現(xiàn)代商品的符號作用在鄉(xiāng)村已有所顯現(xiàn),“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看到當(dāng)代物品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當(dāng)做工具,而被當(dāng)做符號來操縱”(18)[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108頁。。再次,從秋保讓媳婦國香幫著香羅提東西,送她回家這一行為來看,這固然是秋保對香羅在自己這里高消費后的服務(wù)延伸,有秋保對利益的衡量,但也可以看出鄉(xiāng)村超市的空間輻射范圍是有限的,主要服務(wù)對象是同村的居民,鮮明地體現(xiàn)了鄉(xiāng)村超市的在地性。
當(dāng)然,更主要的是,這些看似無聊又無趣的笑談,雖然仍是鄉(xiāng)村民間性的一種體現(xiàn),但在銷售與購買的商業(yè)行為之間,顯示出了鄉(xiāng)村特有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在人與人之間都可能出現(xiàn),但在熟人之間更具有天然性。同樣,盡管如今的商業(yè)活動,也越來越強調(diào)銷售人員對顧客的尊重,追求服務(wù)的貼心,體現(xiàn)溫暖與關(guān)懷,但對于鄉(xiāng)村而言,這種人情味首先是內(nèi)生的,是人們在長時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而不僅是基于服務(wù)水平的提升。
在這兩個場景中,與其說購物和那些商品是主要的表現(xiàn)對象,還不如說秋保和他們之間的笑談是主要內(nèi)容。超市在這里僅僅提供了一個交往的空間,卻鮮明地體現(xiàn)了鄉(xiāng)村人際間的交往特征。鄉(xiāng)村特有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為現(xiàn)代商業(yè)活動抹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使買和賣這種冷冰冰的事情有了一定的溫度,反過來又進一步維系了這一人際網(wǎng)絡(luò)。
(二)沖突:對商品觀念的不同理解
在秋保家超市門口,還有幾個小動物形狀的電動搖椅,可愛又好玩。這種小玩意兒,主要是用來吸引小孩子的,既能夠增加商店的收入,又可以聚積人氣。使用者需要投幣,一次一元,使用時間固定。玩一次后,使用者若想再次使用,需要再次投幣。這天,鳳奶奶帶著自己的小孫子在這里玩。孩子玩了一次后,哭著表示還想玩。鳳奶奶不愿意在這上面花錢,認為這種機器是在坑人。另外一個老太太也附和說,這種玩法太費錢。這時,秋保媳婦走了過來,回應(yīng)道這是自愿的事情,又非硬拉著你們玩。那個孩子還在哭,鳳奶奶一時火起,罵道:“愿意挨刀子的東西,有錢還不如買塊糖,還能甜一甜嘴呢。非得犯賤給人家送錢來”(19)付秀瑩:《陌上》,第207頁。。接著,雙方就吵起來了,鳳奶奶指責(zé)對方壞了良心,秋保媳婦詰問對方,什么叫壞了良心;鳳奶奶指責(zé)對方,兩口子紅白臉配,賺了村里人不少錢;秋保則拿鳳奶奶的兒子說事,越扯越遠。圍觀的人群中,有說秋保不是的,有說鳳奶奶不是的。
在鳳奶奶看來,在這種機器上面花錢是不值的,進而把責(zé)任推到放置這些機器的秋保夫妻,認為是他們在誘惑孩子玩。的確,“玩”是一種服務(wù)性商品,主要滿足個人的游戲快感,并沒有什么實際效用,還不如一塊糖帶來的口腹之歡。這種成本考量,顯然不是一個孩子所能具備的,他也就不能理解鳳奶奶的苦衷。鳳奶奶在這里的指責(zé),除了有老輩人的勤儉、節(jié)約、樸素等慣習(xí)在發(fā)揮作用外,也與鳳奶奶對現(xiàn)代商品社會的契約精神不夠理解有關(guān)。周圍人群之所以站在鳳奶奶的一邊,也是由于這個原因。但從這一現(xiàn)象中,我們可以看出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兩種觀念在商品交易中引發(fā)的沖突。
契約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基石。商品交易建立在交易雙方共同認可并遵從的契約之上。這份契約未必是以書面方式呈現(xiàn)的,大多時候是觀念性的,卻同樣含有規(guī)范和約束社會成員的作用,是開放社會建構(gòu)“系統(tǒng)信任”過程中的有效支撐。秋保夫妻的做法是一種商業(yè)行為,消費者則本著自愿原則,對這些游戲娛樂產(chǎn)品進行消費,并無什么不妥。就此而言,鳳奶奶的指責(zé)實在是冤枉了秋保夫妻。不過,在以“人格信任”為主要基礎(chǔ)的鄉(xiāng)村社會,建立在等值交換基礎(chǔ)上的商品買賣行為,讓金錢參與了人與人之間的往來,使人與人的關(guān)系蒙上了一層利益的面紗,并在實際上代替了傳統(tǒng)觀念中強調(diào)的利讓于義等道德觀念。習(xí)慣了傳統(tǒng)觀念的民眾對由金錢為主導(dǎo)的現(xiàn)代買賣,尤其是非明顯的商品買賣(貨物交易),自然難以理解和接受。當(dāng)鳳奶奶用“一心賺錢,壞了良心”指責(zé)秋保夫妻時(20)付秀瑩:《陌上》,第207-208頁。,實際上表達了對現(xiàn)代物質(zhì)主義擠占鄉(xiāng)間淳樸民風(fēng)的不滿。
隨著經(jīng)濟建設(shè)成為整個時代的宏大主題,鄉(xiāng)村也奔上了致富之路。人們一心撲在賺錢上,漠視、拒絕甚至是否定了鄉(xiāng)村熟人之間應(yīng)有的情感聯(lián)系。鳳奶奶對于這種情感聯(lián)系的道德化維護,既是對情感聯(lián)系的肯定和珍視,但同時又是對它的混淆和誤用,這正是這場沖突發(fā)生的主要緣由。
(三)饋贈:私人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維護
當(dāng)秋保夫妻和鳳奶奶吵架的時候,軍旗媳婦臭菊也在圍觀的人群里。小閨和她打招呼,問她來干嘛,臭菊說買點東西去看看腳崴了的傻貨他娘。小閨認為這是小事,不值得一看,還說她太講究禮法了。臭菊解釋說,傻貨他姥爺跟軍旗他爺是親堂兄弟,應(yīng)該去看看。進入超市后,臭菊拎了一包點心、一袋芝麻糊和一袋豆奶粉。付了錢后,臭菊感到心肝兒疼,這種疼顯然不是生理上的疼痛,而是心理上的,表明了花錢后的一種情緒,即既必須買東西又不愿高支出的復(fù)雜心理。(21)付秀瑩:《陌上》,第209頁。臭菊的解釋說明了自己為何要去看傻貨他娘,顯示出傳統(tǒng)禮法在現(xiàn)代鄉(xiāng)村的延續(xù)以及它們的效力。費孝通認為我國鄉(xiāng)土社會的基層結(jié)構(gòu)是一種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道德觀念,而這種觀念又對個體和社會具有支配作用,“從社會觀點來說,道德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制裁力,使他們合于規(guī)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和綿續(xù)”(22)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費孝通全集》第6卷,第132頁。。臭菊去看傻貨他娘,正表明了她對鄉(xiāng)村道德倫理的服膺。只不過,隨著鄉(xiāng)村的發(fā)展,維護私人網(wǎng)絡(luò)的成本已經(jīng)有所增長。從臭菊對花錢的心疼,可以看到鄉(xiāng)村的商品現(xiàn)代性在豐富了鄉(xiāng)民的物質(zhì)享受、便利了鄉(xiāng)民的購物行為的同時,也無端增加了鄉(xiāng)民的支出和負擔(dān)。這也就意味著并不是誰都可以自由參與和享受這種便利的。
無獨有偶。春米在芳村見到了同村的纓子,兩人東家長西家短地聊了起來。纓子的丈夫在儲蓄所工作,她就自己在家做貸款業(yè)務(wù),憑親疏遠近,利息有高有低。春米家開飯館的時候,就是從纓子那里貸的款。纓子在利錢上對春米有所照顧。對此,春米抱有感激,于是執(zhí)意要留纓子在飯館吃飯,卻未如愿,又趕忙抱著孩子去秋保家的超市,買了一堆吃的玩的送給纓子。纓子嘴上客氣著,心里卻十分受用。(23)付秀瑩:《陌上》,第263—264頁。此外,大全媳婦去超市“買了一只燒雞,半斤咸驢肉,一大塊牛腱子,總有十來斤。一些個營養(yǎng)品,牛奶雞蛋八寶粥等營養(yǎng)品……”并將自己的衣物,送給嫂子(24)付秀瑩:《陌上》,第158頁。;從外地回來的小梨在超市買東西,也是去串門(25)付秀瑩:《陌上》,第438頁。;小鸞帶禮物去看生病的二嬸子(26)付秀瑩:《陌上》,第86頁。,喜針在集市上碰到了自己的親家即兒媳婦梅的娘,內(nèi)里心疼卻又不得不故作熱情地買羊肉和香蕉,送給對方(27)付秀瑩:《陌上》,第222頁。等等,都與上述行為有著相似的功能,即維系自己的私人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鄉(xiāng)村社會中私人網(wǎng)絡(luò)的培養(yǎng)既是一種權(quán)力游戲,又是一種生活方式,關(guān)系不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計算,也涉及社會性、道德、意向和個人感情。”(28)[美]閻云翔:《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wǎng)絡(luò)》,李放春、劉瑜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頁。這些人購買的商品并不是為了自己的生活所需,而是將自己的道德、情感和目的等都注入其購買的商品之中,贈給對方,而對方也通過商品,感知和接受對方的心意。這種溝通方式,有利于鄉(xiāng)村私人網(wǎng)絡(luò)的再持續(xù)。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秋保家的超市只是作為購物的場所而出現(xiàn),但在溝通人際關(guān)系上起著物質(zhì)支撐的作用。一方面表明了鄉(xiāng)村仍然遵從舊有的社會交往邏輯;另一方面又因為超市的出現(xiàn)而增添了新的饋贈內(nèi)容,提高了維系人際關(guān)系的成本,可謂“水漲船高”。就此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超市正在重新組織鄉(xiāng)村的生活秩序。
盡管都是禮物饋贈,同樣都是為了維持鄉(xiāng)村社會中的人際網(wǎng)絡(luò),臭菊和春米還是存在明顯差異:前者出于對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遵從,主動而為之,體現(xiàn)的是鄉(xiāng)村人情;后者則有理性計算在其中,被動而為之,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功利。這種差異也可以視作是代際之間的。這一跡象表明:舊的道德觀念仍然在鄉(xiāng)村起作用,新的價值觀念也開始逐漸地覆蓋鄉(xiāng)村。新的價值觀也預(yù)示著,在鄉(xiāng)村日益開放的環(huán)境下和越來越多的合作機會中,新的鄉(xiāng)村人際關(guān)系正在慢慢涌現(xiàn)和成型。
(四)“殺熟”或者“欺生”:鄉(xiāng)村商業(yè)的“惡之花”
如果說秋保在鳳奶奶不公允的評價中,是受到了傳統(tǒng)觀念的“侵害”,那么他在對待小梨時卻利用了傳統(tǒng)人際關(guān)系提供的便利,顯示出鄉(xiāng)村商業(yè)丑陋的一面。春節(jié)期間,小梨從北京回到了芳村。在鄉(xiāng)民對城市的想象中,小梨也被想象為事業(yè)有成、賺錢甚多、生活優(yōu)越的一員。當(dāng)青嫂子見到小梨時,讓小梨感到的并不是熟人相見的脈脈溫情,而是一種不適。她一直在問小梨的月收入,大有問不出來不罷休之勢。直到然嬸的到來,才解除了小梨的尷尬。看到芳村的日益豐盛,小梨不禁感嘆道芳村的年味不比從前的了。(29)付秀瑩:《陌上》,第430頁。
當(dāng)小梨來到秋保家的超市時,秋保表現(xiàn)出了極大地?zé)崆椋±嬉步辛怂宦暩纭煽谧雍托±媪牧艘粫汉螅±嬲f自己來挑些東西去串門兒。顯然,小梨也是通過禮物饋贈的方式來維系她在鄉(xiāng)村的人際網(wǎng)絡(luò)。秋保讓媳婦囯欣幫小梨挑東西,還有意地擠了擠眼,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幅場景:
她一口氣挑了一大堆,一箱六個核桃,一箱蒙牛鮮牛奶,一箱露露,一只燒雞,一只鴨子,一大塊驢肉,半個醬肘子,兩盤雞蛋。小梨忙說夠了夠了,國欣哪里肯聽,又把一些個酸奶火腿雜七雜八的零食塞過來。小梨只好拿出錢包結(jié)賬。(30)付秀瑩:《陌上》,第438頁。
這幅場景極具畫面感,國欣的賣力和小梨的無奈都在其中淋漓顯現(xiàn)。作者不厭其煩地展示這些商品,與其說是在表現(xiàn)鄉(xiāng)村和城市的物流共享,不如說是為了近距離地顯示秋保夫妻的心機和貪婪。盡管如此,秋保還是責(zé)怪國欣給小梨挑的東西太便宜了,故作夸張地說:“小梨北京來的,還差那幾個小錢兒?”(31)付秀瑩:《陌上》,第439頁。這話表面上是在埋怨國欣不會挑東西,實際上是說給小梨聽的,意在賣出更多更貴的物品給小梨,頗顯強賣之姿。當(dāng)小梨把這件事告訴其大姐時,大姐忍不住罵道:“秋保這兩口子,窮瘋了,見誰都想咬一口。六親不認,狗日的”(32)付秀瑩:《陌上》,第439頁。,同時責(zé)備小梨在花錢上大手大腳,數(shù)落她講究禮數(shù)有些過了。大姐的“罵”并非完全沒有道理,這是以粗魯?shù)姆绞浇掖┝饲锉5男袨閯訖C——拐彎抹角地揶揄小梨是為了賣出更多的商品,指出了鄉(xiāng)村商業(yè)活動中丑陋的一面。當(dāng)然,這種現(xiàn)象在城市也會發(fā)生,但出現(xiàn)在本以人情為紐帶的熟人社會的鄉(xiāng)村,就顯得格格不入,暴露了鄉(xiāng)村在現(xiàn)代性進程中對自身傳統(tǒng)的摒棄。這雖然只是秋保的個人行為,但仍然可以表明物質(zhì)主義對鄉(xiāng)村的侵蝕。
芳村是小梨的故鄉(xiāng),是她生命的起點,在這里度過了童年、開始了成長,并在長時期的接觸中認識了許多鄉(xiāng)親,感受到了鄉(xiāng)村的質(zhì)樸。在離開芳村后,小梨就中斷對芳村的參與,原先對鄉(xiāng)村的熟悉也就停留在記憶中,她本人成為了“在而不屬于”的過客,僅僅是在特定時期回到故鄉(xiāng),且不會久留。這兩種形態(tài),使得小梨和芳村形成了若即若離的關(guān)系。因此,對于秋保而言,小梨既是歸來的熟人,又是短暫停留的陌生人。那么,秋保兩口子的所作所為,既像是“殺熟”,又像是“欺生”。在這里,重要的不是對“殺熟”“欺生”這兩種概念和現(xiàn)象的辨別,而是這些現(xiàn)象在鄉(xiāng)村的發(fā)生說明了什么?這里當(dāng)然有人性的自私、勢力、貪婪等因素在作怪,但同樣也與此時鄉(xiāng)村所處的環(huán)境有關(guān):既保留著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特征,又漸被現(xiàn)代社會風(fēng)氣所浸染。針對如今的鄉(xiāng)村社會狀況,有學(xué)者提出了“半熟人社會”,認為“社會變遷中,農(nóng)民的熟悉和親密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識也在劇烈變動中減弱甚至喪失了約束力,農(nóng)民的行動邏輯因而表現(xiàn)得非常理性”(33)陳柏峰:《半熟人社會——轉(zhuǎn)型期鄉(xiāng)村社會性質(zhì)深描·前言》,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3頁。。這個概念脫胎于費孝通的“熟人社會”,點明了現(xiàn)如今鄉(xiāng)村的過渡和轉(zhuǎn)型狀態(tài)。
盡管如今的鄉(xiāng)村已經(jīng)逐步走向了開放、流動的狀態(tài),但由于自身各種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在城鄉(xiāng)秩序中處于低位,它仍然處于相對封閉、靜止的狀態(tài),保留了鄉(xiāng)土社會的基本特質(zhì)。在這種社會中,熟人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人際關(guān)系狀況。對“熟人”的親切和熟悉的另一面,就是對“陌生人”的辨識更為敏感。在秋保看來,小梨的工作、生活都在北京,大多數(shù)時間不在芳村,那么小梨在大城市的收入具有被“宰”的價值,只是偶爾回到芳村則免除了“宰”熟人后會經(jīng)常面對被宰者而帶來的愧疚和擔(dān)憂。因此,秋保乘機利用了熟人關(guān)系提供的便利,為自己謀利。市場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的商品交易是自由、平等的,并應(yīng)充分尊重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quán),但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由于特有的人際關(guān)系脈絡(luò),屬于消費者的這種權(quán)利并未得到全面的尊重和踐行,因而出現(xiàn)了上述讓人感到驚訝和氣憤的一幕。
《陌上》中的這些場景,從不同角度展現(xiàn)了“超市”內(nèi)外的人情物理,揭示了如今鄉(xiāng)村的社會變化和文化狀態(tài),從中除了可以看到鄉(xiāng)村物質(zhì)的豐富,還有鄉(xiāng)村傳統(tǒng)倫理的失序。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場景中的小說人物,既有臭菊的心酸、鳳奶奶的無助、小梨的無奈,也有秋保的八面玲瓏等多種姿態(tài)。這些姿態(tài)其實是處于不同位置的人們對鄉(xiāng)村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不同回應(yīng),因而生動展現(xiàn)了鄉(xiāng)村現(xiàn)代性的復(fù)雜面向。
四、結(jié)語
通過對《陌上》中與超市相關(guān)的場景的論述,可以發(fā)現(xiàn),盡管以“超市”為代表的現(xiàn)代性事物和為表征的現(xiàn)代性已經(jīng)進入鄉(xiāng)村,并具體地參與到了普通鄉(xiāng)民的日常生活中,但諸如平等、自愿、自由等這些指導(dǎo)并支配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理念并未在鄉(xiāng)村獲得普遍的認同和接受,也并未完全轉(zhuǎn)為民眾的自覺實踐。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并未隨著鄉(xiāng)村內(nèi)外空間的變化而全然失效。現(xiàn)代性的市場理念與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相遇并引發(fā)一系列沖突,反映了鄉(xiāng)村處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斑駁復(fù)雜的過渡和轉(zhuǎn)型階段,鄉(xiāng)民們在此期間演繹著新舊相摻的喜劇、鬧劇或悲劇。付秀瑩通過書寫鄉(xiāng)村超市這個具有現(xiàn)代外觀和傳統(tǒng)內(nèi)在的場所,不僅呈現(xiàn)了這一時期的鄉(xiāng)村社會的現(xiàn)實狀況,也描摹了生活在其間的鄉(xiāng)民生命個體的隱秘心事。
對于有著久遠歷史和深厚文化根基的鄉(xiāng)村社會而言,現(xiàn)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晚清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整體轉(zhuǎn)型中的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城市與鄉(xiāng)村等飽含文化意義的差異序列,不僅影響和塑造著民眾的觀念、心理、情感與價值觀,更直接地表現(xiàn)在他們的行為邏輯上。《陌上》中的“超市”內(nèi)外,即是對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生動描寫,無論鄉(xiāng)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演繹出怎樣的悲歡離合,時間流淌中的現(xiàn)代性進程仍然不會停止前進的腳步。超市嵌入鄉(xiāng)村,融入鄉(xiāng)民的日常生活,超市因此成為一個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并存的雙重物質(zhì)文化空間,展現(xiàn)著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之間的對立、滲透、磨合等復(fù)雜關(guān)系。芳村中的“超市”與超市中的“芳村”就成為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現(xiàn)代性進程中的樣本,正如曹文軒在《序》中所說,“芳村不小,芳村很大。它幾乎就是整個的中國農(nóng)村,中國農(nóng)村的縮影,甚至更大,大到整個人類社會”(34)曹文軒:《序》,付秀瑩:《陌上》,第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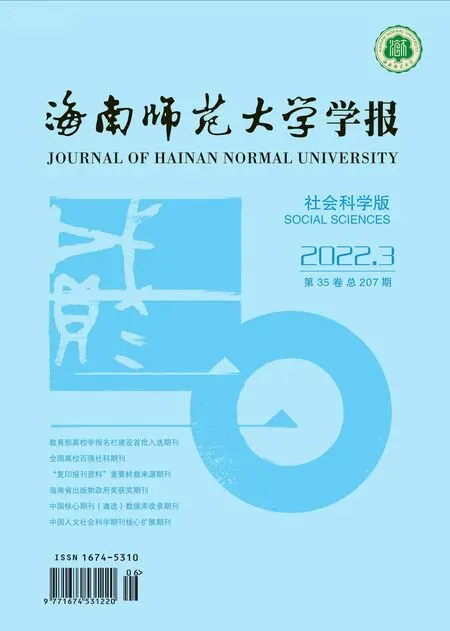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2年3期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2年3期
- 海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越南南方的儒家傳承
——同奈省鎮(zhèn)邊文廟案例研究 - 以客家話閱讀馬來文:詞書編繤與民謠互譯探討
- 主持人語
- 兩種宋版《三蘇文粹》比較研究
- 現(xiàn)代女性的“從軍”與“從軍日記”
- 編輯部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