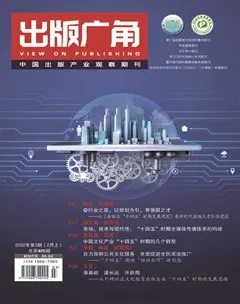中國故事的跨媒介敘述
【摘 要】文化類綜藝節目《典籍里的中國》將典籍文本進行了影像化呈現, 使中國故事獲得了廣泛傳播。節目里的典籍文本經歷了文字、戲劇和影像的跨媒介敘述,這個轉碼過程離不開視覺修辭的參與。文章嘗試從視覺修辭邏輯、視覺修辭策略與視覺修辭效果三個方面對《典籍里的中國》的視覺傳播及文化意涵展開討論,以期為電視文藝節目提供視覺修辭范本,進一步推動受眾的文化認同。
【關? 鍵? 詞】《典籍里的中國》;跨媒介敘述;視覺修辭
【作者單位】惠政,南京大學藝術學院。
【中圖分類號】G220 ? 【文獻標識碼】A ?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3.014
中華典籍雖然是傳統文化的精華,但常因語言艱澀難以被大眾理解。2021年,以中華典籍為主題的綜藝節目《典籍里的中國》(以下簡稱《典籍》),采用文本解讀與戲劇演繹結合的方式,讓晦澀難懂的典籍變得平易近人,傳播值得歌頌的中國故事。《典籍》實現了文本、戲劇與影視的跨媒介互動,從多個層面呈現經典的內涵,這個過程離不開視覺修辭的參與,可以說,節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視覺修辭。
視覺修辭是以視覺化文本為主體的修辭對象,通過使用和構建視覺話語和視覺文化,從而達到勸服、溝通效果的實踐與技巧[1]。傳統修辭主要關注語言的修辭。讀圖時代,圖像對人的影響與語言一樣不可估量,于是,針對圖像的視覺修辭研究興起。視覺修辭延續了語言修辭的傳統,又發展出新的理論內容,為視覺文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本文分析《典籍》的視覺修辭邏輯、視覺修辭策略和視覺修辭效果,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跨媒介操演性:《典籍》的視覺修辭邏輯
學者何成洲認為,文學藝術中的跨媒介現象可以看作一場“表演”(performativity,又譯為操演)。《典籍》從文字到影像的轉碼過程,正是中國故事的跨媒介敘述過程。跨媒介操演性是《典籍》視覺修辭的內在動力,也是修辭行為跨文本發生的主要邏輯。《典籍》中最直觀的一次跨媒介轉換是由文字到戲劇的轉換,包括兩次轉碼過程。戲劇化創作之前,主創先深入理解典籍文本,在心理上還原語言所描述的視覺形象,學者陳汝東稱這一過程為語言視覺修辭。《禹貢》一章,演員閉目齊誦“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短短三句,大禹行走山林,劃定九州的畫面便如鏡頭般在觀眾腦海里呈現。之后的戲劇化創作中,創作者依據心中還原的形象進行藝術創作,這是第二次轉碼過程。在這次轉碼中,視覺修辭的應用更為復雜和廣泛。編劇對敘事進行編排,設置精彩的戲劇沖突;導演設置場面調度,通過蒙太奇手法實現時空穿梭與古今對話;演員通過揣度人物性格,生動再現先賢形象。
不同媒介在《典籍》內部共存與互動。內部媒介之間不是簡單的包容和并置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共同構建節目的文化意蘊與精神價值。從節目最具看點的部分——戲劇表演來看,典籍原作、演員訪談、專家對談等是隨著戲劇文本一起傳達給觀眾的附加因素,學者趙毅衡稱其為“伴隨文本”。這些成分隱藏在文本前后或文本邊緣,影響了文本的解釋[2]。“伴隨文本”包括“先文本”“同時文本”“前文本”。相對戲劇表演來說,典籍原作是“先文本”,也是節目呈現的主要內容。演員訪談被稱作“同時文本”,其發生在戲劇創作過程中并影響最終的呈現效果。關于排練和漢服展示的紀錄文本也屬于“同時文本”,向觀眾展示了演員理解角色和進入角色的過程。專家對談則是對節目的文化背景知識進行補充式解讀,其解讀內容就是“前文本”。這些“伴隨文本”在戲劇文本之外,但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深刻影響戲劇文本的意義解釋,又與戲劇文本共同存在于電視綜藝節目這一媒介空間。這些文本之間的互動效果,同樣依靠視覺修辭來實現。
二、符號表意機制:《典籍》的視覺修辭策略
傳統修辭推崇在語言維度把握意義的生產方式,認為修辭意義主要來源于視覺語言構成層面的修辭結構,即隱喻和暗指等修辭形式所激活的“認知—聯想”機制[1];新修辭學則將修辭理解為一種傳播行為。美國修辭學家肯尼斯·伯克提出了以認同為核心的新修辭理念和方法,他認為視覺文本不再局限于傳情達意的語言功能,還試圖通過視覺修辭實踐影響人的文化認同。無論是傳統修辭學所關注的修辭結構,還是新修辭學所關注的象征實踐,實質都是在探討修辭過程中視覺符號的意義生成,其具體表征就是視覺修辭策略。因此,我們可以從視覺隱喻、視覺轉喻與無意識認同三個方面對《典籍》的視覺修辭策略進行分析。
1.視覺隱喻
隱喻是一種聚合關系,建立在相似的基礎上,幫助人們的認知從具體經驗層面抵達抽象概念層面[3]。在視覺文本中,隱喻修辭的具體實現方式就是使用隱喻性的視覺符號。借助隱喻修辭,讓觀眾通過圖像的顯在意義把握圖像的隱性意義,從而深刻了解文本的深層內涵。由此,視覺文本的主旨也得到了升華。
節目第一種主要的隱喻修辭方法是以古代先賢的事跡來表現“中華文明”的概念。《典籍》每期以特定的主題將著名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聯系在一起,從農事與醫術到歷史與思想,都是對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隱喻。從文明肇始、部落一統到播種五谷、重修本草,一個個故事串聯起來的就是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孔子周游列國”“李時珍遍嘗百草”“司馬遷發憤著書”等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通過戲劇化演繹成為具象的視覺符號,觀眾從中感受中華文明的魅力。
節目第二種主要的隱喻修辭是通過當代故事來表現我國的現代化成就。在時空對話中,撒貝寧向先賢展示了典籍所承載的傳統文化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呈現的新面貌、新發展,電子書、飛機、火箭等視覺符號作為現代化的代表出現在舞臺上。一方面,這些視覺呈現展現了現代科技給人們的衣食住行帶來的諸多便利;另一方面,表明了在現代技術支持下,傳統文化以多樣化的形式得到了廣泛傳承和發揚。這些科技創新的展示就是節目對現代化成就的隱喻。
2.視覺轉喻
轉喻建立在相關或鄰接基礎上,語言學家雅格布森稱其是組合關系[3]。在視覺文本的意義表達中,基于轉喻修辭的“圖像指代”是隱喻修辭的基礎,幫助人們通過事物的部分認知事物的整體。視覺文本中的敘事往往體現為圖像的轉喻修辭,這種視覺轉喻在節目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古代先賢事跡的展現。
通過“一部典籍、一個人物、一個主題”的呈現方式,《典籍》塑造了一批被稱為古代先賢的視覺形象(人物),又以這些人物的典型事跡來梳理中華文明發展與傳承的脈絡,精練呈現中華民族精神。以《史記》一期為例,節目從書中精雕細琢的300多個人物中挑選出10余位大眾熟悉的歷史人物,舉辦了一場群英薈萃的“歷史盛會”。在司馬遷的游學歷程中,節目帶著觀眾前往九嶷山追念舜帝,到孔子故里拜祭先師,去汨羅江畔追慕屈原……通過個體敘事,節目將人物身上展現的崇高道德價值與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接,讓觀眾在視覺體驗中感受精神的洗禮。同時,這些精心選擇的片段組合充分調動了觀眾的聯想,讓他們對典籍文本和人物故事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和再創作,使得文本的潛在意義在觀眾參與過程中不斷增值。
3.無意識認同
新修辭領域的開創性人物肯尼斯·博克將認同分為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誤同(無意識認同)三種類型。他認為前兩種仍屬于亞里士多德的傳統修辭范疇,而無意識認同則最接近修辭情景的根源[4]。視覺文本通過構建視覺圖景來影響觀眾對意義的解讀,按照博克的修辭情景與認同理論,視覺文本的意義就產生于觀眾與視覺形象的符號互動中。對于《典籍》如何幫助觀眾按照傳播者的既定意圖進行文本解讀,無意識認同說能為我們提供一些解釋。
首先,《典籍》通過“當代讀書人”的身份代入引發觀眾的情感認同。“當代讀書人”聯結古代與新時代、戲劇空間與現實空間,是帶領觀眾穿越時空、融入戲劇的重要媒介。此外,“千年以后的讀書人”也指觀看節目的每個讀書人。在節目中,撒貝寧不僅作為戲劇敘事的重要元素參與故事構建,還引導觀眾從自身體驗出發參與歷史故事,感悟經典的魅力。在撒貝寧與古代先賢的對話與互動中,觀眾被帶入歷史情景;隨著撒貝寧固定的儀式展演,觀眾的參與感被一次次深化,并產生廣泛的情感認同。
其次,《典籍》通過炎黃子孫的身份確認引發觀眾的文化認同。炎黃子孫是中國人身上獨特的印記,節目中,從主持詞設計到嘉賓發言再到戲劇臺詞,都在有意識地引導觀眾認同炎黃子孫的身份。比如節目的《禹貢》章節,通過“大禹劃定九州”的故事引出節目的核心價值和主題——華夏一體,然后選擇炎黃部落合并的情節進行重點呈現,追溯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頭。這些視覺呈現體現了創作者在講好中國故事過程中對民族記憶和文化認同的觀照。
最后,《典籍》通過“時代主題”的選取引發觀眾的社會認同。《典籍》的主題涵蓋政治、科技、醫藥和思想等各方面,從古至今,祖先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都是一致的:民生問題、科技發展、醫學攻關……這些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時代主題,還是當下中國的時代主題,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典籍》通過展示古人對這些問題的不斷探索,以及科技迅速發展的當下人們所交出的答卷,引發觀眾對時代主題的社會認同感。
三、文化價值書寫:《典籍》的視覺修辭效果
修辭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傳播者的預期,所以,視覺修辭的效果是分析視覺文本的重中之重。《典籍》亦講亦演,對話古今,用“戲劇+影視+訪談”的方式影視化再現傳統文化,從多個層面給觀眾帶來了豐富的視聽享受。一方面,節目著眼于高雅文化的精英化視角,大大提升了節目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節目采用大眾化的表達方式,推動了中國故事的廣泛傳播。
1.以跨媒介敘事拓展文本內涵
《典籍》節目由文字、戲劇表演和電視綜藝跨媒介組合而成,文本之間相互影響又形成合力,實現了中國故事的多層次敘述。在節目中,作為視覺呈現重點的戲劇表演,采用打破時空的戲劇構思,結合特殊的舞臺造型和環幕投屏等舞臺技術,通過身臨其境的視聽體驗引導觀眾參與敘事,體現了節目以影像傳播中國故事的特有優勢。同時,節目展示了主要演員與專家學者的人物訪談、劇本研討會等多個“伴隨文本”,這些文本作為戲劇創作的記錄,是表演文本的補充,這兩類文本共同構建了一個多元共生、富有層次感的文化表意系統,準確而全面地表達了《典籍》所承載的文化內蘊。
2.以精英化視角呈現價值引領
《典籍》由專家反復比選代代流傳的經典,并精心設置了專家對談環節,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文本解讀,保證了文本解釋的專業性和節目的思想深度。此外,節目還在戲劇表演中設置語境關聯來引導觀眾對文本的理解。比如在古今對話環節中,節目將宋應星與袁隆平這兩位時代的造福者通過“禾下乘涼夢”聯系了起來,讓兩人跨越300多年握手,這充分詮釋了科學精神的傳承。
3.以大眾化表達助力文化傳承
數字媒介的興起使得經典之爭逐漸演變為體裁之爭,很多作品靠大眾體裁勝出。為了應對這場文化劇變,晦澀難懂的典籍必須尋求更為大眾化的表達方式[2]。當下,包括網絡視聽在內的視聽文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眾文化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并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徑。比如《典籍》創新舞臺設計,綜合運用多種視聽語言打造多重表意空間,以豐富的視覺修辭帶給觀眾多層次的視覺體驗,由此激發觀眾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為高雅文化的大眾化傳播提供了優秀的范本。
綜上,《典籍》通過一系列視覺修辭實踐喚起視覺圖像的認知與情感可視化功能,促使觀眾積極參與文化意象與文化認同的建構。創作者當以《典籍》的視覺修辭范式為參考,探索文藝視聽節目提升的新路徑,講好中國故事,為新時代的文化傳承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劉濤. 視覺修辭學[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2]趙毅衡. 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羅蘭·巴特. 符號學原理[M]. 黃天源,譯. 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
[4]肯尼斯·博克,等. 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M]. 常昌富,顧寶桐,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58550058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