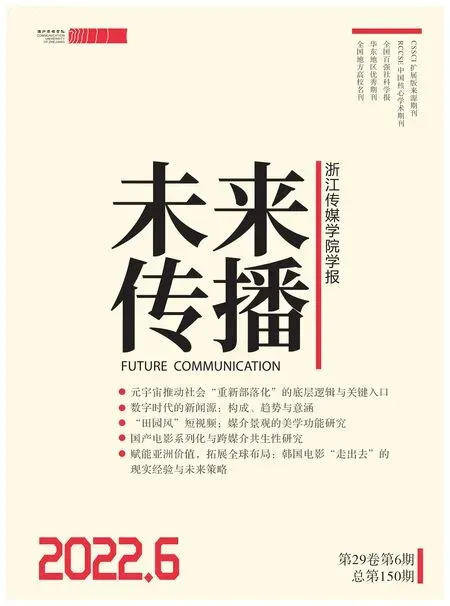開放性闡釋:交互紀錄片的真實建構與意義生成
王更新,賀琳雅
(南京傳媒學院廣播電視學院,江蘇南京211172)
自紀錄片誕生百余年來,每一次形態的變化都離不開技術的進步。從紀錄電影、電視紀錄片到網絡紀錄片,從無聲、配音到同期聲,從線性敘事到互動參與,從單向傳播到點狀傳播,無不表現出技術對創作實踐的影響,并不斷刷新人們對傳統紀錄片的認知。“紀錄片”概念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形式越來越多樣。尤其當數字技術被更多地應用到藝術創作領域,紀錄片實踐也異常活躍起來,呈現出特征不一的新范式,如“網絡紀錄片”“新媒體紀錄片”“跨媒介紀錄片”“交替現實紀錄片”“交互紀錄片”等。這些名稱由創作實踐與學術研究而定義,強調紀錄片在網絡、新媒體平臺以及跨媒介的傳播特性,展現紀錄片非傳統的互動敘事特點,其共同之處是在新的媒介和技術環境下多元地敘述“真實”的故事。其中,交互紀錄片隨著技術成熟和作品數量的增多,它所具有的交互性和開放性為受眾提供參與互動的機會,并在參與過程中重新生成作品文本,形成一種創作者與受眾共同建構、闡釋意義的敘事語境。
一、被動—主動:交互紀錄片概念的界定
從目前國內外有關“交互紀錄片”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定義有不同的認知和側重點。國外較為代表性的觀點有:卡洛琳·米勒認為“交互紀錄片是一種非虛構的交互電影。在其中,觀眾可以選擇觀看的素材以及觀看的順序”[1]。這個定義中的“交互”指出觀眾的主動性,即觀眾可以選擇觀看的內容和順序,但沒有強調實際的互動。戴娜·加洛維認為,“任何以交互性作為其核心分配機制的紀錄片都可以稱之為交互紀錄片”[2]。“交互性”和“分配機制”是定義的核心內容,而如何“交互”和“分配”則需要從創作層面開始實踐這種可能性。對“交互紀錄片”界定的拐點出現在2012年朱迪思·阿斯頓和桑德拉·高登茲在《紀錄片研究》上發表的文章《交互紀錄片:設定領域》中,他們提出“任何以紀錄‘真實’為目的,并且利用數字互動技術去實現這一目的的作品即可被稱之為交互紀錄片……交互性就是觀眾置身于作品之中的一種手段,通過這種交互觀眾與作品所要傳達之真實進行協商”[3]。這個定義一方面強調了紀錄片的“真實”屬性,同時又指出數字互動技術對完成作品的支撐作用。至于受眾參與互動“協商”的效果和意義,由此生成的新文本具有不可預知性,這也是探討這種紀錄片新范式的價值所在。因此,桑德拉·高登茲的這種界定被普遍認同。
雖然國內交互紀錄片的創作實踐還在起步階段,但是,近幾年學術界對交互紀錄片的研究逐漸升溫,且產生一定影響。李智、鄭幽嫻在《交互式紀錄片的敘事研究》(2014)中認為,交互紀錄片也可以稱為“網頁紀錄片”或“多媒體紀錄片”,主要是“結合網頁的交互性設計,使制作人能夠創造一種將照片、文本、音視頻、動畫以及信息圖表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紀錄片作品”[4]。網絡多媒體及其交互性是交互紀錄片的載體和傳播渠道。李坤在《交互紀錄片:一種紀錄片的新范式》(2016)中,追溯20世紀中后期的交互影像藝術為交互紀錄片的緣起,從作品、平臺和學術研究的不同側面分析交互紀錄片產生的技術、媒介及敘事因素。在朱迪思·阿斯頓與桑德拉·高登茲定義的基礎上提出“交互紀錄片是一種以交互性為核心,在當前的媒介環境下主要是依賴數字媒體平臺的一種探索真實的新藝術形式”[5]。王家東的《交互紀錄片的界定與紀錄片地位的獲得》(2020)則對國內外“交互紀錄片”的定義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盡管這一概念的界定還處在一個“混亂的語境”,有的側重于傳播載體,有的強調媒介屬性,有的依賴網絡技術等,但是,“實踐應用領域則遠遠超過理論研究,交互紀錄片項目對所有新形態紀實持開放姿態,……紀實的數字故事成為主流表述”。他尤其提到交互紀錄片發展的新動向是“新興媒介開始取代網絡媒介的重要地位,交互紀錄片平臺越來越偏向于新興的VR、AR以及AI”[6]。
然而,不管人們從哪個角度去理解和界定“交互紀錄片”,它作為一種因信息與網絡技術而生的紀錄片新范式已被認可和接受。其核心在于“交互”,主要是受眾在觀看時與屏幕的互動,即人機交互。通過互動參與紀錄片真實的建構和意義的闡釋,從而打破傳統紀錄片線性的敘事框架,在開放的敘事語境中形成新文本。因此,沒有互動就不能稱其為交互紀錄片。交互紀錄片正是借助網絡與交互技術平臺,在原創作品的基礎上由受眾“在線”參與生成紀實內容的一種紀錄片新樣態。
二、紀錄—闡釋:交互紀錄片建構真實的可能性
不管技術和觀念怎樣演變,“真實”始終是紀錄片的底線和生命。20世紀30年代約翰·格里爾遜提出,紀錄片是“對現實生活的創造性處理”,這是至今最權威的關于紀錄片的定義。紀錄片以記錄歷史、反映現實,承載不同社會的意識形態、民族歷史和文化價值觀,并通過傳播對受眾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體現出它的功能和價值。那么,如何理解和再現真實卻是人們始終思考的一個哲學命題。從闡釋學角度看,任何藝術創作都是作者對創作對象思想和情感的一種闡釋行為,紀錄片亦如此。同時,作為藝術研究的方法論之一,闡釋學還關注受眾對紀錄片接受行為的闡釋。在闡釋的過程中,紀錄片創作者、紀錄對象及受眾都不是單向度的闡釋,而是有可能形成“對話”或“視界融合”的多向度闡釋行為。
(一)對“真實”命題的闡釋
闡釋學(hermeneutics)這一術語起源于17世紀,當時被作為一種解釋圣經和古典文學的方法引入,以闡明文本的含義。18世紀末闡釋學開始探究創作者的個人意圖和作品的特征,主要應用于對文化藝術作品的詮釋,這一階段闡釋學的奠基人是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后來的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則認為,從施萊爾馬赫開始讓闡釋學成為關于解釋和理解的一般學說,從而擺脫了教義因素。[7]20世紀,闡釋學家們對其理論進行了革新,把闡釋學與存在論進行結合,闡釋學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轉向存在論層面。闡釋學存在論轉向的提出者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闡釋學現象以及他對此在歷史性的分析,目的是為了普遍的重新提出存在問題,而不是為了建立某種精神科學理論或克服歷史主義先驗論”,[7](334)他強調了在闡釋的過程中應該關注于存在本身。伽達默爾在海德格爾的基礎上提出了理解的普遍性,把闡釋學從存在論的層次又轉回到原文理論層次。他認為理解是對一事件的復述,理解本身受歷史性的限制。他提出“世界被看做一種擴大了的文本,理解現象遍及人與世界的所有關系,理解行為發生在人類活動的所有方面,理解不單是主體對客體把握的技術性問題,而且是主體存在于世的基本方法,離開理解就談不上存在”[7](321)。伽達默爾闡釋學中提出了“前理解”“效果歷史”“對話”“視界融合”等核心概念,其中“對話”是指理解不僅是闡釋者對文本的單向理解,同時也應該是文本向闡釋者敞開自身的意義,通過文本與闡釋者之間進行相互問答式的對話,意義才能不斷提升。另一個核心概念“視界融合”是指通過深入理解之后,闡釋者的視界與文本的視界融為一體,達成一種更高程度的理解。他認為,我們對文本所持有的意義應保持“開放”的態度,并欣然接受。因此,基于闡釋學的觀點,“對于事實的紀錄與闡釋,從本質上看,都是事實真實和事實理解真實的融合,是一種在理解本身中去顯示事實的真實,是闡釋者‘先判斷’介入的‘效果歷史’”[8]。
作為非虛構藝術作品的紀錄片,對現實的理解與闡釋遵循了客觀真實的基本原則,但往往局限于創作者單向度的闡釋,而忽略了紀錄對象和受眾可能參與闡釋的行為。實踐證明,紀錄片創作者對紀錄對象的闡釋與認知,不是封閉的單向度表達,而是一個互動開放的過程。[9]同時,這種認知在主客體之間的對話不斷提升,真正的理解和闡釋就是在創作者和紀錄對象循環往復的對話中提升各自的視界,最終實現雙方視界的融合,紀錄對象的意義得以呈現和開放。而且,數字化技術發展使受眾參與紀錄片“真實”闡釋與建構的行為成為可能,并催生了交互紀錄片等新媒體紀錄片的誕生。參與性與互動性是交互紀錄片區別于傳統紀錄片的本質特征。
(二)交互紀錄片敘事主體性
傳統紀錄片的真實是創作者選擇和再現的真實,是從創作者到受眾的線性敘事過程,維度比較單一,受眾根據所看到的有限真實對其進行闡釋,某種程度上是被動的接受真實。加洛韋認為“互動紀錄片不應被視為紀錄片的替代品,而應被視為一種有效的、額外的創造性形式,讓人們探索并促進我們對世界的理解”[10]。交互紀錄片中受眾則可以利用新媒體平臺的交互性,主動參與真實的建構,即在觀看的過程中持續的、開放式的建構和闡釋作品的真實,進而使紀錄片文本生成或被讀解出不同的意義。正如卡羅琳·漢德勒·米勒在《數字故事》一書中提出“交互記錄是觀眾可以有機會選擇要看什么素材,以什么順序看”[10](27)。盡管紀錄片的真實生成是一個開放式闡釋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也是在技術賦能之下,紀錄片文本敘事時空越來越寬,闡釋方式愈加多元的過程。從紀錄片自身發展來看,20世紀60年代之前,創作者和受眾都是各自闡釋文本的意義,并從中尋找共情點。“真實電影”出現之后,讓·魯什和埃德加·莫蘭在《夏日紀事》中讓被拍攝對象觀看他們自己在影片中的行為并進行交流,這種“觸發—感應”的互動創作理念重新定義了紀錄片創作者與紀錄對象的關系,將創作者的主觀意識納入整體紀錄文本中,在再現真實的過程中主、客體同為主體。20世紀90年代的新紀錄電影采取“新虛構”策略呈現真實,去中心、個人化、非宏大敘事的理念進入紀錄片領域。如埃羅爾·莫里斯《細細的藍線》在想象的基礎上建構事件的敘事邏輯,通過證偽復盤或重新建構真實。為了更好地呈現真實,他們吸取了真實電影的經驗,實踐更強的互動方式,如《科羅拜恩的保齡》《華氏911》的導演邁克爾·摩爾,《浩劫》的導演克勞德·朗茲曼都有在影片中面對鏡頭直接“闡釋”、表達自己主觀“真實”的行為。紀錄片建構真實的敘事主體不再局限于紀錄對象和藏在攝像機鏡頭后面的創作者,還有直接出鏡參與的導演和觀眾(也可以是被拍攝對象)。這種互動參與的方式也是改變主客體關系的嘗試。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創作觀念的迭代更新,紀錄片融入了真人扮演、CG動畫、場景復原、VR技術、受眾交互等多種復原和再現真實的手段,盡管表現風格和敘事方法不同,但是表達真實是共同的追求。
從現代闡釋學來看,紀錄片的文本包含創作者對事實的理解和闡釋,同時也包含了受眾對紀錄片的理解與闡釋,“理解不是一種復制作者原意的過程,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11]沒有受眾的紀錄文本也就無法實現其意義。在此基礎上,無論是傳統紀錄片還是交互紀錄片,作為非虛構影像文本,客觀真實是紀錄片紀錄和呈現的準則,創作者首先要對事實理解,進而對事實進行闡釋。紀錄片借助視聽語言對真實表達的過程就是闡釋學生成意義的應用。紀錄片的邊界逐漸擴張,而交互紀錄片受眾的主體意識也越來越突出,受眾通過參與、互動所建構的真實,無疑是對傳統紀錄片真實觀念的一種突破,“即傳統敘事中的確定性元素正在逐漸喪失,整個敘事傾向于一種無中心、反規則與開放性的存在樣態”。[5]
三、參與—創造:交互紀錄片的“出位之思”
“出位之思”是德國的美學術語“anddersstreben”,指藝術媒介想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和表現性能,以尋求另一種藝術媒介的表達優勢和美學特征,即跨媒介敘事。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提出:“雖然每門藝術門類都有著各自特殊的印象風格和無法轉換的魅力,而對這些藝術最終區別的正確理解是美學批評的起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可能會發現在其對給定材料的特殊處理方式中,每種藝術都會進入到某種其他藝術的狀態里。通過它,兩種藝術其實不是取代彼此,而是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12]龍迪勇的《空間敘事本質上是一種跨媒介敘事》則認為,“所謂‘出位之思’之‘出位’,即表示某些文藝作品及其構成媒介超越其自身特有的天性或局限,去追求他種文藝作品在形式方面的特性。而跨媒介敘事之‘跨’,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即跨越、超出自身作品及其構成媒介的本性或強項,去創造出本非自身所長而是他種文藝作品或他種媒介特質的敘事形式”[13]。
無論是傳統紀錄片,還是交互紀錄片,其文本形態都是視聽藝術,屬于同一媒介。但是,由于數字化新媒介的出現,交互紀錄片作為一種紀錄片的新形態,其“出位”就在于它“跨”出了傳統紀錄片的敘事模式和美學特征,而具有了交互式的新特點。具體表現為從傳統電影電視向新媒體的跨媒介敘事,意即從原有形態中跳脫出來,克服傳統紀錄片在媒介、形式與內容上的束縛和限制,突破原先的自足狀態,在新的跨媒介中發揮效用。就交互紀錄片而言,在除了作品本身的媒介特征外,研究作品跨越其自身媒介所體現的網絡媒介特性,發現其對于真實的建構邏輯。無論是時間藝術、空間藝術還是影視這種綜合藝術,都需要使用某種媒介成為表達自身的符號。而當表達媒介跨出自身界限呈現更多的表達可能,也就是“出位之思”構成了藝術創作中比較具有創造性的一面。交互紀錄片開放性闡釋從技術上是跨媒介的敘事,從內容生成上是多義性,因而是一種創造性的闡釋。值得注意的是,交互紀錄片的“出位”不但具有跨出“他”媒介特征——新媒體的參與互動性,還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紀錄片敘事的方式和手段。
(一)人機交互建構紀錄片敘事語境
比爾·尼克爾斯在《紀錄片導論》中將傳統紀錄電影按照其“嗓音”(表達方式)分為詩意模式、闡釋模式、觀察模式、參與模式、反身模式、陳述行為模式等六種類型。然而,紀錄片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具有流動性和邊界模糊性,對真實的界定與闡釋也不斷豐富著紀錄片的藝術形態,紀錄片新的類型與形式同樣繼承了傳統紀錄片對于真實的追求。交互紀錄片在傳統紀錄片的基因底色上,打破了封閉的線性敘事,借助人機交互技術,加入了互動理念。基于桑德拉·高登茲依據交互視角的不同對交互紀錄片模式探索的基礎上,本文對交互紀錄片文本類型特點、創作理念及交互方式的分析,發現交互紀錄片的受眾在參與建構真實的同時重塑了紀錄片的敘事語境。
其一,沉浸對話式語境。這種語境重點強調創作者與受眾的對話應該是雙向交流的,受眾不再是傳統觀看型的個體,而是變成了作品中的視角。同時,使用3D技術重新創建場景進而玩轉現實的選擇,強化了受眾與交互系統互動過程的沉浸式感受。1978年,MIT開放紀錄片實驗室的創意超媒體實驗項目《阿斯彭電影地圖》(AspenMovieMap)是最早的非虛構互動影像作品,在VR及新媒體技術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雖然當時還沒有“交互紀錄片”這一概念,但這是第一部嘗試提供數字化紀實的交互作品。該影片讓用戶在“媒體室”中駕車穿過整個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彭市,用戶通過與屏幕界面交互來控制進入城市的速度和方向,自由地即興移動。觀眾(用戶)視角等同于司機角色,在虛擬的城市地圖中駕駛,這個探索就如同置身于真實世界中有了強烈的沉浸感體驗。觀眾在“城市漫游”的過程中可以通過點擊的方式與空間建筑場景進行互動,了解細節信息,觀眾的操作、探索以及交互程序的設定是一種“對話”式的敘事語境。至此,文本的概念從對現實的解釋過渡到對現實的模擬(使用圖像)。伽達默爾認為,效果歷史得以實現視界融合主要是由于闡釋者和文本之間進行的不斷的提問和回答,是雙向“對話”式的表述。《第71號灰熊》(Bear71)作為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早期交互紀錄片的嘗試,在傳統線性紀錄片的基礎上,有個旁白模擬71號灰熊進行敘述。一開始是71號灰熊實時定位的紀實影像,之后是實時地形圖,觀眾可以在森林公園漫游,能看到所拍攝的影像、監視器影像、三維街景效果,仿佛沉浸其中,模擬片中71號灰熊的主體視角,以第一人稱與文本內容進行交互對話,進而完成對作品的理解。2020年,作為國內第一部交互紀錄片,《古墓派·互動季》在優酷平臺上線后提供了兩個版本:一是在電腦網頁端觀看的不加任何互動內容的傳統紀錄片版本;二是通過手機客戶端觀看時觀眾可以體驗到互動內容的交互版本。該片嘗試將交互技術融入考古歷史事件與紀實影像的闡釋之中,對于紀錄片內容與形態進行了首次突破性的探索。
其二,動態反應式語境。該語境的建立主要基于虛擬現實技術,移動媒體和GPS技術定位,將觀眾在虛擬世界的操作與實際的物理空間聯系起來,增加對現實的感知層次,為參與者創造一種動態的游戲式體驗。用戶(觀眾)在探索空間中扮演一個角色(自己),參與的同時添加內容,構成了一個動態的反應過程。《騎手說》(RiderSpoke)中,把手持式設備(諾基亞N800)安裝在自行車的車把上,內置耳機和麥克風,30名參與者根據發出的音頻指令,同時騎自行車進入倫敦街頭,根據創作者計劃的四組問題,建立參與者、城市和Rider Spoke之間的關系。創作者在體驗中引入隨機元素,讓每個騎手都會被問到不同的問題,比如第一組問題為了提高騎手對周圍環境的認識,騎手必須隨機回答,直到找到與問題符合的位置停下來,并通過麥克風記錄自己的回答,同時可以聽到其他人的答案,既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利用受眾生成的內容來填充數據庫,構成了一個動態系統,體現了充滿游戲感的混合社交空間內涵。開放的數據庫和封閉的屏幕界面的雙重特性使《騎手說》成為一個有趣的交互紀錄片案例,通過強烈的動態參與感與游戲性,“將藝術帶入現實世界,在互動性的儀式中,建立新的藝術與現實交融的混合空間”[14]。這種沉浸式游戲化的呈現方式,消解了傳統紀錄片的理性和深度,卻拓展了紀錄片中“真實”的生產模式和美學意義。同時,也實現了紀錄片敘事空間與時間的媒介轉換。
(二)主動參與重構紀錄片的真實體驗
傳統紀錄片是以創作者為主體建構真實,基本上是閉合式的敘事,觀眾所看到的是“完成時”的時空故事。交互紀錄片在開放式的網絡交互技術支持下,再現和呈現真實的方式發生改變,受眾可以結合自身體驗,主動參與“生成”個性化的內容,為受眾(用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動體驗感。而交互紀錄片“既涵蓋了媒介層面上的互動操作(互動實踐往往出現在互聯網和跨媒介平臺的藝術作品中),又涵蓋了美學層面的交互原則(交互正是所謂‘交替現實’成為可能的動力)……在不同的數字媒介之間的自由過渡與拓展便預示著這種跨媒介、跨平臺的存在是可能的”[5]。受眾參與對現實進行延伸和重新建構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進行時的創作體驗,帶有一定主觀性和超文本開放式的敘事特點。
其一,主觀參與式體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更新了受眾與內容之間的關系,使得創作者和受眾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成為可能。主動參與是時代賦予受眾的角色定位,受眾不再滿足于被動接受或旁觀,而是更積極地與內容創作者進行直接溝通。觀眾在自由選擇觀看內容和順序的同時,還可以參與到素材內容生成和制作的過程中來。《繪制緬因街》(MappingMainStreet)中主街的界面是一幅地圖,觀眾可以根據創作者在地圖上標識出美國境內緬因街的位置,定位標志自己的位置,并上傳帶有地理標記的照片、文本或視頻等素材,從而生成新的文本內容。《70億其他人》(7BillionOthers)采訪了世界各地的人們,了解他們的生活和信仰,并將他們的面孔和答案上傳到網站上。用戶(受眾)可以通過點擊其中一張面孔,看到采訪他的視頻片段,還可以錄制自己的視頻上傳至網站,主動參與內容再生和意義闡釋。交互紀錄片的“項目創作者更像是一個龐大的敘事系統的設計者,用戶是故事素材的提供者”[15]。這種創作方式與基于UGC影像重構的紀錄片《浮生一日》有許多相似之處。《浮生一日》的導演凱文·麥克唐納(Kevin Macdonald)聯合全球最大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邀請全球網民記錄下2010年7月24日這一天的生活,以及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190個國家及地區的網民們提供了總計4500個小時的視頻素材,通過剪輯后在約1個半小時的影片中展示了世界各地人們同一天的日常生活。類似的作品《手機里的武漢新年》《煙火人間》同樣是通過內容眾籌的方式,重新編排不同個體的敘事,創作出新的影像并賦予其不同的價值和意義。不同的是,這類作品的受眾只是參與素材創作,卻不能像交互紀錄片的受眾那樣,還可以選擇性地觀看,并且在觀看的過程中進行二次創作。正是通過對多元信息的整合和再創作,交互紀錄片為觀眾提供了更強的主動性和參與感。
其二,超文本開放式體驗。納爾遜在他的理論著作《文學機器》(LiteraryMachines)中定義了“超文本”是“非相續著述,即分叉的、允許讀者做出選擇、最好在屏幕上閱讀的文本。正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樣,它是一個通過鏈接而關聯起來的系列文本體塊,那些鏈接為讀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徑”[16]。交互紀錄片的創作者為用戶提供了一個探索性的體驗角色,利用超文本紀錄,通過選擇預先存在的選項(視頻)來實現超文本鏈接。這種超鏈接技術能夠將交互式紀錄片中文字、影像、聲音、圖表等不同媒介形式的信息建立聯系,通過互動操作從一個信息界面跳轉到下一條信息界面。這種模式似乎描繪了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我們的選擇永遠不完全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別人給我們的選項中做出選擇。[10](246)盡管這種模式在敘事上表現為分枝樹狀結構,但實際上它仍然是創作者設定好的整體封閉、內在開放的空間。又如,1989年蘋果多媒體實驗室制作的《莫斯蘭丁》(MossLanding),在美國小鎮莫斯蘭丁組織了一次為期一天的拍攝,幾臺攝像機同時拍攝了莫斯蘭丁人們的生活。這部作品設定了人們可以點擊選擇人或者地點,啟動視頻點擊觀看,也是第一部被正式稱為交互紀錄片的作品。觀看過程中,觀眾點擊畫面中的人物或地理位置的超鏈接,就會彈出相關人物或者地理位置的影像信息。同樣,《我的窗外》(OutofMyWindow)的創作者提前在全球13個城市拍攝了49個故事,觀眾可以自行點擊選擇觀看。2020年優酷平臺上線的國內首部交互紀錄片《古墓派·互動季》中也有大量超鏈接的嘗試。受眾通過手機客戶端觀看并體驗考古知識相關的互動內容,以“探秘者”的身份猜測和設計劇情發展,通過點擊屏幕上諸如“滑動開棺”“長按排除棺液”“放大X光片”等“按鈕”,實現沉浸式的觀看體驗。如此基于邏輯線和故事性,將單線敘述變成多支線敘述的時空拓展,不僅增加了互動體驗的懸念感,同時還設置了很多隱藏的拓展資料和知識點,讓超鏈接的選擇更加豐富和有趣,最終構成一個超文本開放式敘事語境。
四、對話—互動:交互紀錄片意義生成的開放性
“紀錄片創作者對創作對象進行闡釋的過程是在主客體之間互動、創新的效果歷史,對真實性的表達處于開放性的狀態中,最終實現闡釋者與被闡釋者的視界融合,使紀錄片作品達到高度真實性和審美可能性的境界。”[17]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媒體內容的消費者正逐漸成為內容的創造者,并將他們各自獨特的理解和闡釋融入到作品當中,從不同角度去建構和呈現紀錄片真實的時空故事。紀錄片以開放的姿態,不斷吸納新的內容生產和意義生成。
(一)受眾介入的開放性
從高登茲對交互式紀錄片互動模式的劃分可以看出,所謂“對話式”“超文本式”“參與式”和“體驗式”,其實都是受眾介入作品再創作的方式或途徑,顯然是一個開放式的敘事語境。安德烈·巴贊提出電影的完整性就在于它是真實的藝術,而這種真實應該包括拍攝對象真實和敘事結構真實以及可見空間真實。闡釋者只有挖掘和認知闡釋對象全面完整的信息,才能真正理解和闡釋其中的意義。這里所說的“完整”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傳統紀錄片的“完整”主要依賴于創作者所呈現的事實,交互紀錄片的受眾則在原創作者的基礎上,成為新的創作者,而且不局限于一個人。他們“第一人稱的主觀參與性敘事視角不僅能夠打破文本與受眾之間的界限,也能更有效地為受眾營造出一種切身體驗影片議題的參與感和互動感”[15],以不同視角所呈現的不同視野和圖景,進而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并拓展了作品的敘事空間和時間,使之更加完整,同時也從多元的角度去理解和建構真實。《古墓派·互動季》整個敘事的過程用解說串聯,穿插醫學家、考古學家等參與者的講述,內外視角交叉轉換,增強了敘事的真實感和客觀性。同時,還設置了大量的問題來推進情節發展,允許觀眾在體驗考古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分析問題,尋求結論,呈現客觀行為和主觀探索,賦予觀眾更多參與建構的開放性。《全球生活》(GlobaLives)是一個至今仍在不斷變化的項目,正如其官方網站所寫“全球生活計劃是一個生活體驗的視頻圖書館,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創建”,在形式與內容上都具有開放性。《拉各斯寬和近》(LagosWideandClose)的觀眾“跟隨”巴士司機在城市中穿梭,可以選擇一個遙遠的(寬)視角,或者一個親密的(近)視角接近蓬勃發展的大都市拉各斯。另外,《高層建筑簡史》(AShortHistoryoftheHighrise)、《第71號灰熊》(Bear71)、《70億其他人》(7BillionOthers)等一些備受關注的交互式紀錄片,打破了傳統紀錄片的創作生態,開創了以“交互”為核心的“闡釋—接受”模式。
交互紀錄片采用行動和選擇、沉浸感和感知作為建構真實的方式,通過事先創造好一組“現實”,然后交由觀眾(用戶)以多種途徑重新構建,就一個共同主題或問題,分支一系列觀點,紀錄片傳統的被動接受模式被打破。在交互紀錄片中,空間是被賦予敘事功能的場域,而不再只是事件發生的地點。受眾對敘事的選擇和組合以及選擇的結果對事件進程的影響和制約,顯然作品意義不只來源于作者觀點的表達,還融合了互動者對再創造空間的闡釋和使用,因而賦予文本開放性的意義呈現。受眾通過參與協作不僅可以擴大數據庫,還能夠改變紀錄片在未來的樣態和內容。
(二)敘事結構的多線性
在傳統紀錄片線性敘事結構中,創作者往往對影片信息的呈現與結構的把控占有主導權,是單向的交流模式,只能遵循創作者設定好的信息被動接受。比較而言,交互紀錄片采用的不再是線性敘事結構,而是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具有多線性、分支性敘事的結構特征。克勞福特所謂的“分樹枝”框架更能闡釋大多數的交互紀錄片的互動架構。“分樹枝框架每到交互的情節點上,情節線索就一分為二或者一分為三。如此一來,每增加一個交互層級,可能性就成幾何倍數增長。”[18]交互紀錄片的受眾互動參與恰好生出N個“分樹枝”,形成多層級的交互模式和樹狀分枝性敘事結構,突顯了受眾的參與感。同時弱化了傳統紀錄片中創作者呈現真實的權威性,受眾接受信息的方式打破了單向性,創作者則是在有效的整合和組織中為受眾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影像素材和探索渠道。受眾在觀看《古墓派·互動季》時,每一次“選擇”都會觸發不同的解釋與拓展資料的分支敘述。例如,第三集《致命死因》中,根據畫面內容提示,受眾可以參與推斷福州茶園山兩具尸身的死因,二人究竟是死于吞金、投毒,還是另有原因。如果受眾選擇“投毒”選項,將會觸發關于水銀中毒與水銀防腐的醫學解讀,醫學專家從專業角度講解水銀中毒后人體不同器官的病變反應。接著,紀錄片會回溯契丹王朝第一位皇帝耶律阿保機用水銀進行尸身防腐的傳說,并引出甘肅、寧夏地區的水銀防腐風俗。受眾對一個問題的好奇(選擇點擊)可以引出數個相關聯的故事,這種分支性結構形式使真實的建構和意義的生成更具開放性和多元性。反之,也更有利于調動受眾的參與意識,受眾的每一次“點擊”都可能是一個發現之旅。《我的窗外》(OutofmyWindow)設定地點、空間、臉龐三種模式:選擇地點,展開一幅世界地圖;選擇空間,是一個多層建筑物的景觀,點擊不同的窗口可以看到不同的故事;選擇臉龐,則是不同人的面孔以及他們的故事。《繪制緬因街》中地理標記、城市街景、文字介紹和指引等,都具有同樣的多線性敘事功能。
另外,交互紀錄片敘事的多線性也帶來了游戲感體驗,成為吸引受眾參與、激發受眾創造性的重要因素,能夠進一步豐富紀錄片的敘事視角和呈現樣態,具有互聯網思維特點。如《古墓派·互動季》中,從如何處理棺槨,到為何棺槨超重、尸體不腐的判斷,受眾選擇正確時屏幕會出現“才識過人”“心明眼亮”等文字表示認可,并配合正確選擇的音效;如果判斷失誤,還會收到“請睜開眼睛看清楚”等文字提示,配合錯誤選擇的音效,極具游戲感。除了選擇題,交互過程為受眾設定了開棺、放水等操作類的游戲互動形式,觀眾需要進行“滑動屏幕打開棺蓋”“長按屏幕,排出棺槨中的棺液”“長按屏幕進行X光掃描”等動作,這些動作操作成功與否,同樣會觸發相應的劇情。大量的交互素材,所采用的游戲設定是網絡時代對娛樂性和故事性的追求,符合網絡時代作品跨媒介表達的審美表征。
五、結 語
依托新媒體平臺產生的交互紀錄片,是紀錄片跨媒介生成的新樣態。交互紀錄片中觀眾的參與和互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生成了作品文本,形成一種作者與受眾共同建構真實、闡釋意義的開放式敘事語境。移動互聯媒體創造了作者、用戶(受眾)、技術和環境之間的動態關系,交互紀錄片在用戶(受眾)和現實之間創造了新的維度,賦予用戶(受眾)更多選擇和參與構建真實的敘事空間,從而以主觀介入的方式與創作對象之間建立對話機制,并通過對創作對象的進一步闡釋而生成更加多元的意義。其敘事邏輯具有闡釋學分析的理論意義,闡釋者與闡釋對象各自在開放性的空間中對話,在對話中實現雙方的視界融合,創造出文本的新時空、新內容和新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