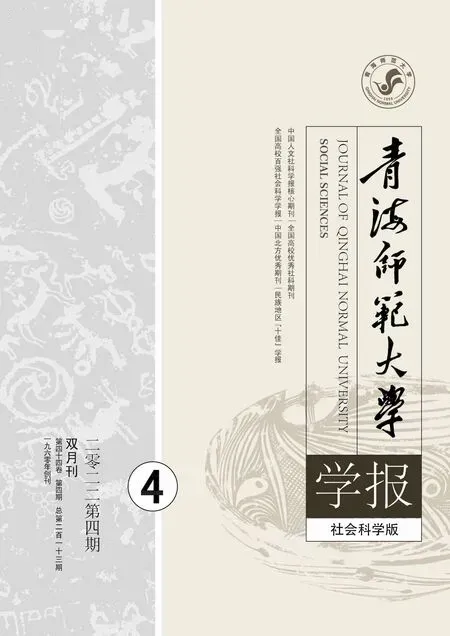“民主儒學”引論
——定公八年魯國“寶玉”被盜事件詳考
劉 斌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中華先民與玉的接觸至晚在一萬六千年前就已開始。其后經歷過以軒轅黃帝為首的傳說時代,以夏啟為首的三代時期,以漢唐為代表的晚近歲月,至于今天,玉依舊是華夏兒女日常生活中不可或替的財富與瑰寶,圍繞玉發生過的貴族交誼、家族故事、情感傳奇數不勝數,這其中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魯國“寶玉”被盜事件因為被記錄在《春秋》當中尤為引人矚目。故事的大體經過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出于拱衛周室,同時也是為了表彰周公德行的目的,分給魯國的夏代寶玉“夏后氏之璜”,在魯定公八年失竊后又在魯定公九年失而復得。
孔子在《春秋》當中這樣記載:
(八年)盜竊寶玉、大弓。[1](P2141)
(九年)得寶玉、大弓。[1](P2143)
據《魯周公世家》,武王克商以后封周公于魯,但周公為輔佐武王并未就封,而是命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之后不久武王故去,成王即位。因成王年幼,周公繼續輔佐周天子直至故去,成王則為褒揚周公之德,命魯國得以郊祭文王而有天子禮。我們要討論的“寶玉”應該就是周成王統治期間賜予魯國的一件玉器。
魯定公四年也就是魯“寶玉”被盜之前四年,衛國的祝鮀還曾有過這樣的追述: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1](P2134)
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即《春秋》所記“寶玉、大弓”,前者據說為夏代寶玉,后者為古封父國所制。《周禮·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玄璜禮北方”[1](P762)之言,概周天子賜予魯的寶玉本是夏朝時人用以禮敬北方之神顓頊所用,三代相沿周室得之,其后出于表彰周公的目的賞賜給了魯國。至于魯定公時期應該已在魯國保存了五百年之久。遺憾的是魯人晚節不保,作為國之重器,“魯寶玉”居然被人盜走,還作為一次歷史性事件被寫到了史書之中遭人譏笑。
一、內外背景
任何偶發事件都展現著歷史發展的大邏輯。本來周公是周代禮制的制定者,作為周公封地的魯國理應成為這一方面的楷模,而且自伯禽以降至于魯真公時期歷代魯公立嫡以長、兄終弟及,魯國在遵行禮制方面一直都中規中矩無可挑剔。然而自周宣王時期開始,因為周宣王欲立魯公少子而強行干預魯國繼承制度,導致魯國統治階層欲循禮制行之而反不可得,魯公室依禮傳國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其后“諸侯多叛”,[2](P1528)公室日趨式微和衰落。魯僖公、魯文公之世季氏、孟氏、叔氏三桓勢力崛起,魯國政治開始進入私強而公弱的新階段。“魯寶玉”被盜事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當時的大背景是,隨著晉楚爭霸局面的形成,特別是晉國在北方中國的崛起,魯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特別是魯昭公時期,任期內的第二年、第五年、第十二年、第十三年、第十五年、第二十一年、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年先后八次主動訪問晉國,六次被拒,導致魯國的實際地位某種程度上比宋國和鄭國還低。而且魯執政三桓,先是魯昭公十三年第六代季氏(1)從季友開始算起季孫意如為魯國季氏第六代人物。參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季孫意如在魯昭公蒞盟的情況下被晉國拘禁,后是魯昭公二十三年叔孫氏又因為小諸侯國的控訴親自赴晉說明情況時再次被晉國羈押(兩年后于昭公二十五年卒),十年之內兩位上卿接連被諸侯盟主所拘禁,對于周公的封邦而言無異乎奇恥大辱。叔向說:“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1](P1972)魯公室既不得于諸侯之會,魯三桓復不能自保其身,這是一個公室丟臉而三桓蒙羞的時代,地位極低。
其二,國內形勢矛盾復雜。首先是公室與三桓之間相互支持又相互打擊。魯公室欲去三桓勢力由來已久,早在“公室卑,三桓強”[2](P1536)局面剛剛出現的魯宣公時期魯公室就曾嘗試借助勢力打擊三桓,至于魯昭公時期昭公伐季氏不成而逃亡國外,已是公室打擊三桓的第二次嘗試。而以季氏為代表的三桓對于魯公室更是“離心離德”。昭公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國因小國之訟而拒絕魯公與會,同時拘禁季氏自秋天至于第二年春天,其后隔了兩年為了當年之事(魯公被拒并季氏被禁)昭公再次訪晉,又為晉國人阻撓羈絆于晉國多達半年之久始得回國,舊籍記載云: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1](P2080)
說昭公幾經阻撓和羈絆終于回到自己的國家,滿懷正義感的子服景伯在對話時批評晉,季氏不僅不為魯君說話,反而譏諷子服景伯不懂關系和國家政治,以魯公之被阻為應然,這自然是有負其臣子之職。事實上,當時的魯國政治一邊是三桓執掌政權而公室形同虛設,一邊是三桓勢力內部“世卿”偏廢而陪臣當政。先是魯昭公十二年季氏有南蒯之叛,后是定公年間季氏再逢陽貨之亂,陪臣當權而執政失勢,世卿違公室,陪臣令世卿,魯國極其微妙而復雜的政治形勢是“魯寶玉”被盜事件的第二重背景。
其三,寶玉文物行情看漲。春秋中后期以來諸侯之間索賄受賄屢見不鮮,甚至當時的周天子都不能幸免,舊籍記載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居然在妻子剛剛安葬后就公開向參與葬禮的晉國人索賄,其時政界風氣之不堪于此可見一斑。隨著政界人士的貪婪成性,寶物彞器的價值和價格亦隨之大漲。魯昭公十六年就在周景王索賄事件后一年,晉國執政韓宣子親赴鄭國索要“玉環”。(2)舊籍敘述更為詳細但不免鋪張,為行文計引文有縮略。韓宣子索要“玉環”或者更有其他的政治目的,但“國際市場”上“寶玉”價值漸增也是不爭的事實。舊籍稱: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韓子買。商人曰:“告君大夫!”韓子曰:“敢以為請。”曰:“失諸侯。”韓子辭。(引文較文獻所載有刪減)[1](P2079-2080)
晉國是當時諸侯國中的盟主,以盟主國家執政的身份親赴小國索要玉環,足見當時的諸侯貴族中愛玉之風的興盛。
其四,以孔子為代表的民間力量崛起。如上所言,魯國從周宣王時代以來上自公室下至私家違背和僭越禮制的事情屢見不鮮,無論是禮制、禮儀還是禮義至于魯國宣公和昭公時代在公室和貴族生活層面早已如深秋枯葉一般零落殆盡。舊籍記載魯昭公七年三桓之一的孟孫氏隨同國君出訪,鄭楚期間兩次都因為缺乏基本的禮儀知識而出丑,舊書謂其“鄭伯勞于師之梁,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1]P2048。這說明到了魯昭公時期,至少是魯國的孟孫氏家族,在禮學知識方面已經匱乏到不足以應付基本國際政治需求的地步。這對于天選的“禮儀之邦”而言實在已是太過不堪。同不學無術的貴族集團不同,就在禮學衰微的襄公和昭公時代孔子應世而來,一片早春時期才能見到的葉開始在魯國的大地上悄悄生長。而且大約當時當世的智者早就已經知曉此事并開始悄悄向外傳播圣人降世的消息。所以恨不懂禮儀的孟釐子對自己的家臣講:“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1]P2051孟釐子隨訪楚國的時候孔子才十六周歲,還只是一個剛剛篤定自己志向學習禮文化的青年。十七年之后孔子過而立之年,孟釐子去逝,魯貴族孟孫氏正式從學孔子,積年好學的孔子開始在魯國上層貴族集團中嶄露頭角。而所謂禮儀之邦的魯國也終于在迷失很久以后迎來了一次借助民間力量重回禮教正統的最佳契機。
以孔子為代表的民間政治文化集團的崛起是魯“寶玉”被竊事件即“陽貨之亂”的第四個重要背景。
二、陽貨之亂
從相關資料的記載來看,陽貨為人博學多識、驍勇善戰又專橫跋扈。魯哀公九年宋國人攻打鄭國,晉趙鞅在救鄭的問題上猶豫不決訴諸占卜,陽貨占以《周易》謂:“宋方吉,不可與也。”[1](P2165)眾所周知孔子壯年后素以博學著稱,但獨于《周易》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1](P2482),說明早年的孔子對《周易》并不精通,反倒是陽貨能以之斷大事,作為季氏家臣和實際在當時的國際政治中馳騁多年的精英,至少從《易》學的角度來看陽貨算得上博學而多識。又據記載陽貨為季氏臣期間曾于昭公二十七年、定公六年兩次參與征伐與作戰,一次是與孟孫氏攜手攻打魯國的鄆城(實際攻打魯昭公),一次是隨同魯定公、季氏和孟氏一起侵略鄭國,兩次作戰均獲成功,第二次還從鄭國獲匡地,大約陽貨確也算得上驍勇善戰之輩。當然或者與個人能力有關,作為家臣的陽貨最大特點是專橫跋扈,且不說魯國無君的背景下與孟懿子一起攻打魯昭公明顯屬于大逆不道、蔑棄公室,就算是魯國的實際執政若季氏、孟氏也不被陽貨放在眼里,據記載魯昭公六年魯定公攻打鄭國后返魯陽貨曾強迫季氏和孟氏從衛國國都穿城而過,惹起衛國人的極大憤慨,而以臣令主的行為更是將專橫跋扈的特點暴露無遺。
陽貨作亂之前曾經和孔子有過一次會面,也就是今傳本《論語·陽貨》的首章,章文謂: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涂。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1](P2524)
我們推測本章內容所及應該是在魯定公八年的春天或夏天,理由是:一,本章提到孔子對陽貨自己“將仕”的承諾。孔子初仕在魯定公九年(3)《孔子世家》提到陽貨在定公八年作亂,其后不久魯國以孔子為中都宰,再后來魯定公十年孔子相魯公于齊魯夾谷會盟,由是我們推斷孔子初仕當在魯定公九年(公元前501)。,依孔子“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做人做事風格,[1](P2463)既然親口承諾“將仕”,對話當時距離實際出仕在時間上應該不會相去太遠;二,孔子弟子當中直接就有魯國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孟懿子,所以我們分析從孔子做出出仕的承諾到真正實現出仕時間上不會間隔太久;三,從章文敘述來看當時的陽貨既然能從容地饋禮孔子而后與之相見于中途,無疑依然是在扮演著季氏家臣的角色,所以我們推斷其時約是在魯定公八年陽貨為亂之前,也就是說本章文字最有可能或者說最合理的時間應該是在魯定公八年的春天或夏天。
這個時間就陽貨為亂和魯“寶玉”被竊事件而言無疑十分微妙。
此前魯昭公十三年不能輔佐國君參與平丘之會而自己更被公開拘禁半年多的魯國第六代季氏季孫意如剛剛在定公五年去世,而有意思的是這位曾經被外國人公開拘禁的魯國第六代季氏的繼任者甫一履職就因為人事矛盾被本國人也就是自己的家臣陽貨拘禁,后者更在其后半個月時間內對親近季氏的基本力量進行了徹底清洗,還脅迫季桓子與之盟誓,定公六年更是挾定公并三桓再次盟誓。可以說陽貨在當時的魯國近乎權勢熏天。《公羊傳》有謂“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確乎不假。[3](P600)
我們分析陽貨見孔子或者恰是要為自己作某種輿論和人才方面的準備,部分地也是更主要的應該是要借包括孟孫氏在內的力量牽制新任第七代季氏季桓子。季桓子繼任的第二年赴晉國出訪陽貨強迫孟懿子隨行一定程度上大概正是出于此一目的。至于定公八年這種專政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取季氏而代之的思想和實踐。《公羊傳》記載季桓子當時曾以“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之言向孟孫氏、叔孫氏求救,[3](P600)舊文言之鑿鑿,自然是確有其事。只是事情并沒有陽貨計劃的那么順利。首先是陽氏親近臨南(或謂林楚)不忘季氏舊恩關鍵時刻背叛陽貨;其次是孟氏集團在相關地點伏兵數百以救季氏,于是陽貨的計劃尚未執行就中途夭折在了前代季氏的榮寵與孔子門徒(孟懿子及孟氏所準備的武裝力量)的搭救上。然而陽貨或是為昔年舊事所激或是一時的氣憤所致也或者為了其他目的,居然在打仗打輸之后公然進入定公的宮殿取走了魯國的鎮國之寶,也就是我們開篇提到了“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據記載魯國當時還有一件寶玉名曰“玙璠”,孔子曾有“美哉玙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的感嘆。[4](P3)魯定公五年季孫意如卒后陽貨曾想用“玙璠”為之隨葬卻被季氏的另一名親近仲良懷拒絕,此或正是計劃落敗后的他盜取魯國鎮國寶玉的直接誘因。
陽貨盜走魯寶玉后輾轉去了晉國,其后第二年夏天又把寶玉還給了魯國。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么一時不好考證。就當時的魯國而言,昔年周天子所賜的鎮國寶物失而復得倒也算幸運。
但是真正值得魯國人為之慶幸的大約還不在“寶玉”的失而復得,而在關鍵的時候他們啟用了孔子。魯昭公二十四年或稍后孔子訪周歸來后一直在魯授徒講學。其后昭公出走,孔子一度入齊,不久又因為齊不能以季氏待之,且包括齊國官僚的排擠憤而返魯。
三、魯用孔丘
我們講,盡管對陽貨不大感興趣,但在追平季氏這一點上,兩人倒是頗為一致,而且較諸陽貨欲去季氏而自立,孔子在齊國時在個人待遇上追平季氏的努力似乎還要早好幾年時間。說起來在爭取“更大權利和待遇的問題上”,孔子還算的上季氏家大夫的前輩。
關于孔子與陽貨的關系,在我們看來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陽貨和孔子一定程度上都代表著魯國社會中下層力量的崛起。同魯公室和魯三桓相比,陽貨作為季氏的家臣屬于魯統治集團中的下層力量,而孔子作為曾經的貴族后代至于魯襄公時代已經與平民無異,所以無論是陽貨在季氏集團中權勢的增大還是孔子在魯國貴族中學術影響的增強,一定程度上都代表著春秋中后期魯國社會下層力量的壯大,不過是一個居于上層表現為某種反叛和暴動形式,一個處在民間呈現出積極救世的態度,或者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所謂“先賢的民主”。第二,陽貨代表著顛倒的政統而孔子代表著復興的學統。魯國的繼承制度周公時代以來一直都是兄終弟及、立嫡以長,所謂“一繼一及,魯之常也”[2](P1532),季氏的先祖季友本來是魯莊公的三弟,既屬于合法的魯公繼承人,又不是第一位的繼承人,而在當時魯莊公既未立季友更沒有立季友的兩位兄長,而是立了自己的兒子,就魯國的繼承制度而言事實上屬于違制,所以季氏集團后來在魯國成為執政的世卿,某種程度上反倒代表著魯國長期以來錯位政統的一個回歸,盡管客觀來說屬于顛倒的政統(4)在周代封建統治秩序的意義上魯國季氏集團長期執政還帶有某種部分的“下層”官僚統治國家的“民主”氣息。,因為季友之后的歷代季氏既便作為世卿也斷然已經沒有繼承政權的資格,但是作為實際執政的季氏似乎確又接續了魯莊公時期應然的繼承法則,所以我們稱之為“顛倒的政統”。與陽貨長期以來一直待在季氏集團不同,孔子最初不過是一個喜歡禮學的沒落貴族、事實上的平民,但他年少好禮,在魯國正統的禮制以及禮學衰落之后積極向學,希圖重建“郁郁乎文”的宗周文明,[1](P2467)更曾為禮學專程赴周都城訪學請教,代表著長期以來禮學衰微的魯國漸漸復興的“官學”正統或者說正宗的學統。第三,從相去甚遠到漸走漸近。因為小的時候曾經被陽貨公開拒絕,孔子本來對陽貨并沒有什么好的印象。但幾十年服務季氏的家大夫終究不是等閑之輩,同在魯國之內的孔子大約也不可能不對在執政集團內部影響巨大的陽貨的存在每有風聞。當然,魯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從學孔子之后,陽貨對于孔子的學問大概也會略有知曉。所以,從魯昭公二十四年開始孔子和陽貨之間的關系應該就已經出現了從漸行漸遠到漸走漸近的轉變。至于魯昭公二十七年陽貨和孟懿子一起攻打魯昭公,作為世卿師的孔子和作為家大夫的陽貨某種程度上已經站到了同一條戰線里,因為無論是季氏也好,還是孟氏也好,無非代表著實際控制魯國政權的三桓勢力。
至于魯襄公八年,陽貨作為家臣為季氏服務已有三十四年時間。對于孔子而言,從年齡上來說陽貨算得上他的兄長。當然孔子一直以來對陽貨都沒有什么好印象,即便作為季氏家臣陽貨越來越位高權重。更何況二人一者為季氏的家大夫,一者為孟氏(孟懿子)的世卿師,作為不同政治集團的人物不可能不因為各自的利益而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與沖突。雖然至于魯定公五年第七代季氏季桓子的時代,因為共同的目標,在對待季氏的問題上孔子和陽貨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種不結盟的統一戰線。
從《論語》全部記載來看,無論是稱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好,[1](P2465)還是說“季氏富于周公”也好,[1](P2499)孔子對魯國的季氏集團實在沒有多少好感。(5)但事實上,魯國的季氏大約并不向孔子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至少魯昭公被三桓趕出魯國以后,當時的諸侯盟主晉國沒有過度責備季氏,而是繼續讓其執掌魯國政權,這本身無疑也是對三桓執政能力的一種肯定。對于魯定公五年之后第七代季氏季桓子時代的陽貨而言同樣如此。而且,因為長期服務季氏,對于第六代季氏的晉國受辱、魯昭公入晉時的連番被拒以及魯國國內包括季氏在內三桓勢力的種種作為,陽貨更是有其切身的體會,就像季桓子繼任伊始入費邑時的仲良懷輩之類。所以與大多數魯人至于成襄昭時代已經“不知公室”,即所謂“民忘君矣”[1](P2128)一樣,陽貨對魯國政治之不堪大約也是早已心生厭倦,所以在“政變”(陽貨攻季氏算不得政變,我們姑且以“政變”相稱)失敗以后扔下“孺子得國”[1](P2340)的不屑之詞率性而去。不過對身處民間的孔子似乎頗有不同。陽貨包括季氏集團陽貨一派的家臣大約都對孔子——一位憑借個人能力三四十歲左右折服齊國國主的年輕才俊——的學問頗為欣賞。究其原因來看,我們認為且不說為孔子所折服的齊景公對當時逃亡在外的魯昭公都不怎么待見(6)《史記·孔子世家》所謂:“昭公師敗,奔于齊,齊處昭公干侯。其后頃之,魯亂”云云。[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10頁。,即令與當時的諸侯盟主晉國國君相比齊侯的份量也不遑多讓,所以孔子雖不用于齊,但其出訪齊國的經歷包括陽貨及陽貨一派家臣在內的魯人應該頗有了解,而作為周公封地的魯國所需要的正是孔子這樣的人才。
所以,陽貨才說“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說孔子口口聲聲宣傳“仁”與“知”,實際上“懷其寶而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以“仁”與“知”責之,孔子于是爽快地答應說自己“準備出來當官”。這之后大概沒過多久,陽貨“政變”未遂去魯赴晉,魯國則正式啟用孔子,官居中都宰。史書謂:“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2](P1915)
于是,更有意思的一幕出現了。作為陽貨集團骨干成員的公山不狃,在孔子被魯國啟用之后不久居然不顧魯公室和三桓統治集團的猜忌,又一次向孔子拋出新的橄欖枝,《論語》中記載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P2524)
中都在魯曲阜西偏北,公山不狃所在的費這個地方在魯曲阜東偏南,[5](P26-27)從孔子對子路的回答來看,大約做中都宰后仍覺得才不能盡,如果說中都比于宗周,那么費邑至少是成周洛邑之類的存在,說不定還能再造一個東周文明,所以孔子頗有些動心。《孔子世家》說:“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欲往。”[2](P1914)自然大約孔子并沒有真的如自己所講的那樣去公山不狃那里主政,但魯國統治者包括三桓大約又一次感覺到了某種政治力量和政治優勢有可能失衡的危險,于是進一步提拔孔子為司空,而后又做了魯國的大司寇。
四、結 語
如果我們的分析不錯,那么,過程上來看正是魯國的鎮國寶玉給了孔子真正出仕的機會。我們不知道“魯寶玉”失竊以后孔子當時是什么態度,但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頗惹人遐想: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1]P2490
“待價而沽”這個成語應該就是出自孔子師徒之間的這一段對話。
我們推測孔子所以在子貢的追問下公開承認自己是一位待價而沽者,有這樣兩條原因:一者,魯國自魯真公以后禮制衰壞民心思變,一生好禮的孔子早已對魯國政治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對他而言國寶丟失亦無需大驚小怪反倒是在言談之間與子貢開起了玩笑;二者,孔子飽學宿儒門徒廣眾,又不斷有弟子追問自己為什么不出來從政之類問題,所以本人確也希望有機會將自己的學識運用于政治生活以安邦定國一展頭角,而子貢所提到的美玉當售的觀點恰合了孔子寶玉若己可以待價而沽的的心理;其三,如果說子貢和孔子討論的正是“魯寶玉”(7)在孔子和子貢,在魯定公時代早期孔子正在授徒講學這一大的言說背景下來分析,我們認為這一章所提到的“美玉”確有相當的可能就是作為夏后氏舊物被陽貨竊走后給魯國帶來空前政治危機和政治機遇、《春秋公羊傳》所提到的魯之“寶玉”。而且就算其談論的不是“夏后氏之玉”,在關于“玉”的討論的意義上,我們用為分析孔子關于“魯寶玉”丟失以后可能的態度也有其相當的參考價值。,那么,最重要也最值得人們遐想的正是陽貨給魯國留下的對孔子大有利的一個“國事大象”:
魯有寶玉大弓,持國重器,請君上尋之。
《易·系辭》謂:“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6](P343)“象也者,像也。”[6](P373)
幸運的是,就在陽貨作亂后的第二年,孔子的才華第一次真正在魯國政壇得以綻放,恰如“陽貨所‘期’”一定程度上亦如孔子所“愿”。至于不久孔子又在另一位陽貨集團重要成員公山不狃的反向推動下進一步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我們只能承認陽貨“公山不狃”對于孔子從政確實從側面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同陽貨和公山不狃不同,在孔子從政的問題上,作為魯國“寶玉”的“夏后氏之璜”一定程度上則從正面起到了特殊而關鍵的“呈象”和推動作用,孔子走上政途,魯國之“寶玉”事實上功不可沒,而這大約是很多學人,儒學研究者包括歷史學人所考慮不到的。(8)孔子主政包括以后周游列國再返回魯國研究文化,對于魯國國祚的延續都有突出的正面價值和意義,其后魯國作為周初封國繼續享國二百四十多年,孔子之功與有力焉。
盡管一生談不上十分成功,但是以“一介布衣”通過勤苦學習而官至大司寇,開派講學弟子三千,整齊經書傳承文明,至于身后“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2](P1945),當時后世文化影響之大無出其右,作為早期中國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成功是民心所向、是志士之選、是早期中國民主精神的巨大成功與光輝實踐。而在這個過程中,陽貨、公山不狃等人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亦可謂早期中國民主精神的先賢人物。某種程度上或者還可以說,后世以孔子為導向的儒學本就是“民主精神”之子。近現代以來關乎儒學可不可以開出民主價值的討論至此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