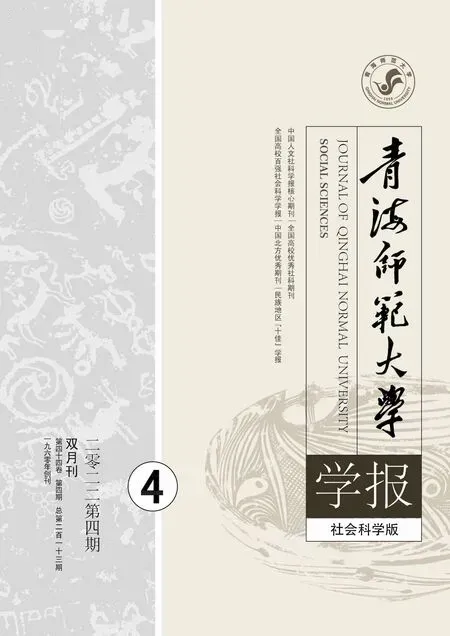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的民族化:研究現狀、不足與建議
梁永紅
(太原師范學院 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一般認為,1892年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的問世開啟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有幾段比較重要的語文改革實踐運動,分別為國語與白話文運動、大眾語文建設運動及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現代漢語書面語的最終定型正是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結果,同時也是這幾次實踐活動的成果。其中,大眾語文建設運動,尤其是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接決定了現代漢語的精神和面貌。這一運動是指,在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觀念的指導下,把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結合起來,并將現代化、大眾化、民族化三者相統一的實踐活動[1]。其中,書面語言的民族化,也就是將大眾化、口語化與民族化統一起來便是其建設的主要內容。革命根據地正是這一實踐的重要場域,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但是,目前關于這方面的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還有較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找出其中仍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研究現狀
革命根據地是指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權所控制的革命區域,后來也叫作“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區”等[2]。為了全文統一,本文除了一些已經習慣的術語外,比如解放區文學,其余均使用“革命根據地”這一稱謂。現有的關于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實踐的成果大都從宏觀角度進行,主要討論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實踐的表現或特征,從研究角度來說,主要分布在語言學、文學以及文化研究等方面。
(一)語言學視角
從語言學視角進行的相關研究,目前主要零散地分布在三大方面,即中國語文現代化與現代漢語的發展、國語的分化與海峽兩岸漢語差異的源頭、革命根據地教科書與語言文字教學狀況等,以下具體闡述。
1.中國語文現代化與現代漢語的發展
中國語文現代化是指中國在現代化時期以現代語文觀念為指導進行的語文建設或實踐活動[1][3]。其中,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便是語文現代化進程中的主要實踐活動之一,而根據地又是其實踐的主要場域,所以人們在討論語文現代化運動時往往會涉及根據地的情況。
韓立群將這一建設運動的目標總結為文學語言的口語化,途徑為對民眾口語的提煉和汲取,同時指出應該在技術性上集中處理三個問題,即如何精煉大眾語言、如何使用方言以及如何對現代語法和大眾口語進行統一,并認為《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新水滸》等作品在語言運用上既以普通話為基礎,而且也較好地運用了通俗且有地方色彩的通俗語言,是兼具語言通俗性與地域性的典范[1]。但是,對于根據地的具體建設情況并沒有詳細論述。刁晏斌也從語文現代化的角度討論了根據地的語言運用情況。文章認為,“民族形式”論爭是一場重要的語言規劃與實踐活動,受此影響,大眾喜聞樂見的表達形式,即“革命白話”出現在許多作家尤其是根據地(解放區)作家的作品中,語言文字的通俗性成為新的追求,常用詞、常見詞以及較為簡單的合乎語法規范的句式成為常見的語言形式,陌生化和歐化句式被盡量避免[4]。
當然,語文現代化與現代漢語的形成及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這一運動正是現代漢語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因。因此,人們在討論現代漢語的形成或發展時也往往會涉及根據地的情況。比如,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組在討論“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的的變遷和發展”時就稍有涉及[5]。書中認為在“兩個陣營,兩條路線”的對峙過程中,“蘇區——左聯——根據地(解放區)”的語言風格為通俗化,但并沒有單就根據地(解放區)進行歷時考察。刁晏斌根據發展演變的特征,將現代漢語分為四個階段,并分別總結了各個階段的語言特征[6]。其中第一階段,即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正是上述幾次語文建設運動進行的時段。書中將這一階段的語言特點總結為紛紜復雜、同義形式多、超常用例多。同時,以30年代初為界又將這一階段分為前后兩段,認為后段比前段條理、簡單一些。當然,這里所述后段的特征主要就是在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觀的影響下出現的。
總之,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是語文現代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直接決定了現代漢語的面貌。正因如此,當人們討論語文現代化或現代漢語的形成發展時往往會涉及到根據地的語言運用情況,但大都只是幾筆帶過,并沒有進行系統分析。
2.漢語的分化與海峽兩岸漢語差異的源頭
革命根據地與國統區的語言風格差異較大,這種差異實際上也是傳統漢語分化的表現。因此,人們在討論國語的分化以及海峽兩岸漢語差異時也往往會涉及根據地的語言運用情況。
吳亮認為,在不同政治取向的推動下,傳統國語向著不同目標、沿著不同路徑進行演變或分化,這種分化直接表現為國統區與根據地語言個性特征的顯化及差異的日益擴大,具體表現為兩個語言社區在文言和白話、本土與外來成分等的不同比例分布或使用頻率上的差異[7]。另外,吳亮還以丁玲解放前后小說語言的變化為例來討論漢語在國統區與解放區呈現出的典型性差異,后者表現為文言比例降低,歐化現象減少,口頭通俗語言增多等[8]。雖然只是個案研究,但也從中反映出了當時革命根據地語言運用的追求或普遍特征。
1949年以前國統區的書面語風格在后來的臺灣的漢語中被較多地保留和延續,并成為臺灣漢語最重要的語言特色之一,而今天的普通話卻與革命根據地的語言風格基本一致。因此,人們在討論海峽兩岸漢語差異時往往也會涉及根據地的情況。比如,郭熙在談到海峽兩岸漢語各自的“源頭”時就總結了國統區與根據地的語言差別,并將后者的特征總結為:政治、軍事等術語社會化,表達通俗化,個別詞語運用范圍擴大化,借詞蘇俄化等。同時,分析了其中的原因[9]。總之,雖然人們在討論漢語的分化與海峽兩岸漢語差異的源頭時會涉及根據地的語言運用特征或風格,但也只是一個“副產品”,并不是其中討論的主旨。
3.革命根據地教科書與語言文字教學狀況
有關革命根據地教科書與當時語言文字教學狀況的研究也主要是語言方面的,只不過,這些研究著重從教學角度,即教材、教學內容及效果等方面進行。比如,楊楊、李新、肖娜以晉冀魯豫邊區《初級新課本》為例,分析了革命根據地教科書的話語特色,即在分析字面意思的基礎上挖掘出了背后的深層意蘊[10]。文章認為,教科書反映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的話語特色,具體表現為順應時代的政治話語、聯系農村生活的鄉村話語以及符合心理特征的兒童話語。除教材外,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2014年度有調研項目“西柏坡時期語言文字工作調查與研究”,涉及的正是當時的語言文字工作,其中李霞的《西柏坡時期小學語言文字教學考察》便是其階段性成果[11]。文章考察分析了西柏坡時期初小教學過程漢字書寫的教與學、作業與練習、錯別字的改正、造句與作文等,并分析了西柏坡時期語言文字教學的方法與特征:前者表現為注重漢字的讀音與書寫、加強課后作業與練習、認真糾正錯別字、精練小學作文等;后者表現為語言文字教學具有較強的實用性、教學方法靈活性以及語法教學的欠缺等。曾建平、黃儉根、邱斌總結了紅軍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展語言文字應用工作的主要形式,即婦女識字班、軍官教導隊、政治宣傳教育、文藝作品創作等,并討論了當地個人語言使用的復雜狀況以及紅軍與當地群眾互相影響的情況[12]。
總之,這里考察的主要是當時語言文字普及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從教學角度進行的。雖然涉及的也是語言文字,但更多是漢字的教學,對于詞匯、尤其是語法討論得很少,而且著眼點并不是當時當地的語言面貌,因此對于語言尤其是書面語使用的具體情況也便不得而知。
(二)文學與文化建設視角
從文學角度談“民族形式”論爭或語言通俗化問題的成果比較豐富,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區文學和個別作家作品兩個方面。
1.解放區文學語言特征
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從宏觀角度來討論解放區或延安文學語言的通俗化、大眾化等特征。比如,王力從語言共同體的角度分析了解放區小說的語言特征[13]。所謂的語言共同體可以理解為知識分子向人民大眾學習、靠攏,同時人民大眾也學習新的詞匯,由此形成以方言為主、彼此交融的共同語言。其主要特征為,農民語言、新文學敘述語、時代政治語匯在小說文本中交錯并存,具體表現為敘述語逐漸呈現出“民族”特色,句式結構、長度以及詞匯運用等消除了歐化痕跡,更多的“方言”被整合進來,以及農民對政治語匯的使用、轉述等。袁盛勇認為,延安文藝整風后,農民語言和民間語言開始大量進入延安作家的話語實踐,并改變了延安作家的語言觀[14]。沈文慧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與延安語言革命是20世紀兩場針對漢語的語言革命,后者與前者不同,它的主要特點是運用農民大眾的鮮活口語來彌補“五四白話”過分歐化和過于文人化等的弊端[15]。侯業智指出,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大眾化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既是之前工作的總結,也為之后的大眾化指明了方向[16],同時總結了《講話》前后延安小說語言面貌的變化,即由過度歐化與文人化變為大眾化、通俗化。但是,文章的用力點更多是從中國現代文學的角度梳理當時的歷史。李萍也討論了延安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問題[17]。文章認為延安文學的語言形式在1942年以后呈現出全新的面貌,主要表現為運用口語化、通俗化、民謠化的陜北方言、口語、土話等,之前那種注重辭藻、煉詞煉句、意象意境以及蘊藉文采的現象大大減少,延安文學的樣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2.趙樹理、馬烽文學語言特征
除了就整個解放區或延安文學語言進行討論外,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有時也會涉及語言民族化的內容,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趙樹理和馬烽。比如,王彬彬將趙樹理文學語言的特征總結為簡潔、明快、干凈利落,能用很省儉的語言把很復雜的事情說清楚,同時也指出其語言蘊藉不足的特征[18]。張衛中認為,趙樹理文學語言的表層特點是某些修飾性語言成分或修辭手段的簡省,語言具有簡略、質樸、渾厚、粗線條和極富張力的特征[19]。后來,張衛中又分析了趙樹理大眾化語言形成的原因,即早年的生活環境、早期教育的影響、對自己農民或農村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以及戰爭時期特殊的時代導向,并認為后兩點才是關鍵因素[20]。李松睿以趙樹理的文學語言為中心分析了地域色彩對于解放區文學的影響[21]。趙凡對趙樹理小說《邪不壓正》進行話語分析,并由此探討了革命道理的“新話語”和傳統鄉村的“日常話語”在接洽時產生的復雜層次,同時指出革命背后的語言問題[22]。除了趙樹理外,馬烽也有這方面的表現。白振有將馬烽解放區小說語言的表現風格概括為通俗與簡練,認為前者主要表現為語言的淺顯、俚俗與曉暢之美,后者主要表現為簡明、精練[23]。文章認為,馬烽在詞匯方面注重運用常用詞和方言土語,在句式方面大都使用簡單的常式句,很少使用奇特的變式句,辭格也很少使用,即使用到,其構成材料也通常是老百姓熟悉的事物。
除文學視角外,根據地文化建設方面的成果也較為豐富,其內容涉及紅色報刊、新聞傳播、戲劇、紅色歌謠及歌劇等很多方面,這些都是以語言為載體的,所以人們在討論時有的也會提到語言的大眾化和通俗化,但因為都不是專門從語言學角度來討論,所以最終成果展示的也都不是系統的語言學方面的內容。總之,只要是涉及“民族論爭”這一段歷史的研究都會或多或少談到語言的大眾化、民族化等內容,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這也是下面我們要討論的內容。
二、存在的不足
總的來看,目前關于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比較薄弱,雖然凡是涉及那段歷史的研究都免不了要談到語言的大眾化和民族化,涉及的學科也比較多,比如語言學、文學、新聞傳播、文化等,但是專門就這一內容進行系統研究的卻還很少。目前的研究狀況我們可以用“三多三少”來概括,即文學視角的研究多、語言學視角的少,宏觀研究多、微觀研究少,共時研究多、歷時研究少,以下具體闡述。
1.文學視角的研究多,語言學視角的研究少
前面我們主要從語言學和文學兩個視角對相關研究做了總結,雖然從分類來看,語言學方面的頭緒更多,比如前面談到的中國語文現代化與現代漢語的發展、漢語的分化與海峽兩岸漢語差異的源頭、革命根據地教科書與語言文字教學狀況等,這些都涉及到了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這一問題,但是從具體論述來看,這一問題都不是其討論的主旨內容,大都只隱含其中或者只是其中的“副產品”,比如前文談到的韓立群[1],其論述的主旨是現代中國的三段語文改革,其中的第三段即為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革命,討論的核心為這場革命的背景、性質、理論體系、意義等,只是在談到“民族形式討論”這一問題以及關于大眾語的建設目標時才涉及到根據地的一些情況,也可以說,建設大眾語也是根據地的目標,所以根據地也有這方面的表現,但文中并沒有單就根據地進行專門論述。前文談到的其他成果也大都如此:刁晏斌討論的主要是早期現代漢語的特征[6],郭熙為海峽兩岸漢語的差異[9],吳亮為國語的分化[7]。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的民族化只是其中很小的“副產品”,當然有關這一方面的論述其系統性和翔實性也就欠缺一些。
相對來說,文學視角的成果就要多一些,比如我們分別以“根據地語言”“解放區語言”“書面語言民族化”為主題在中國知網上進行檢索,排除掉美術、書法、音樂等學科外共得到18篇相關論文,其中只有3篇為語言學方面的,其余15篇均為文學方面的。也可以說,關于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的問題在文學領域比在語言學領域受關注的程度要高,語言學領域對于這一主題的關注還很不夠。雖然從理論上來說,文學領域的關注與語言學是一樣的,文學研究與語言學研究也有很多聯系或交叉,但是畢竟它們的側重點、分析材料的方法目的等還不太一樣:前者重在思想,重在“‘語言’在文學家和文學過程中的意義與功能”[24];而后者重在語言形式,更多是對語言現象的解釋以及語言規律的挖掘。正如劉世生總結的,“語言學側重形式研究,其本質特征是描寫;文學批評側重內容研究,其最大魅力是闡釋”[25]。其實,早有學者注意到從語言學視角進行的研究還很不夠這個現象,只不過其著力點放在了“大眾語”方面,比如薄守生指出,“‘大眾語’曾一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熱門話題,語言學對它的研究卻很不充分”[26]。文章還呼吁讓“大眾語”回歸語言學,做一番“純而又純的語言學”研究。大眾語如此,書面語言的民族化亦是如此。從語言學角度來說,民族化形式的書面語是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前身,了解清楚其內在的語音、詞匯、語法結構等也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現在的漢民族共同語。
2.宏觀研究多,微觀研究少
無論是上述語言學視角的研究還是文學視角的,大都從宏觀角度進行,往往只是概括其中的特征或風格。即使是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很多也只用一句話,如“使用常用詞和結構簡單的句式”來概括,往往給人一種比較模糊或籠統的感覺,具體而詳細的考察和論述還非常少,微觀研究還非常薄弱,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目前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學語言,有關新聞、通訊、評論性作品等方面的語言討論得還很少。
書面語言并不等于文學語言,文學語言只是書面語言的一部分。但是,目前關于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的研究基本上只集中在文學語言這一個方面,尤其是從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更是如此,主要討論的是解放區文學或趙樹理、馬烽等作家作品的語言風格。但是,書面語不只表現為文學語言一種,形式也不只文學作品一種,革命根據地還有很多報刊、雜志,其中的新聞、通訊、評論等都是書面語言的表現形式,而且與一般文學作品的表述還有一定的差異,它們都應該是研究的對象。只有對這些書面語形式進行全面研究,我們才能比較深入、系統地了解當時的語言狀況,但現有的成果對這些內容涉及的還很少。
其次,書面語言的風格、特征談得多,而對其中具體語言形式的表現討論得少。
目前的成果大都集中于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的風格、特征方面,其中使用最多的關鍵詞便是“口語化”“大眾化”“通俗化”“革命白話”“去歐化”“民間語言”等,但是對于其中具體的表現形式進行系統考察和研究的卻很少,比如“口語化”到底有哪些語言形式、具體的詞匯和語法項目到底是什么樣的等,并沒有詳細論述,其他也大致如此。總之,有關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的具體表現,目前研究得還不系統、不具體,還沒有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清晰的面貌展現給大家。
3.共時研究多,歷時研究少
在現代漢語的形成過程中,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接決定了現代漢語的精神和面貌,而根據地正是這一語文建設運動的重要實踐場域,它是現代漢語形成與發展這條線中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環。正如吳亮所說的,后來的普通話正是沿著此時開啟的道路繼續前進并發揚光大,如果沒有這個階段一系列的語言實踐,就不會有后來的普通話,而且百年漢語的發展路徑與方向很可能要改寫[7]。以往的研究雖然也有討論,但更多是共時平面的,將它處于現代漢語或普通話的形成和發展這條線上的討論還很少。比如,上述風格和特征的研究以及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等,反映的主要都是共時平面的情況,其中的具體脈絡或某些語言形式的具體歷時發展表現并沒有討論。從語言學視角、切切實實地分析各類語言項目變化以及此時與之前和之后語言異同的具體表現很少呈現,所以我們對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實踐具體脈絡的認識并不是很深入,歷時研究還很不夠。正如薄守生在談到大眾語運動時指出的,“有關中國語言學史的各種專著、論文,無論是通史、斷代史還是專題史都很少提及;即使在某些著述中偶有提及,一般也都語焉不詳,無圖無驥”[27]。只有在共時研究的基礎上,加強歷時方面的研究,我們才能更加深入地認識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這一問題,也才能更加了解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及發展過程。
三、相應的建議
前面我們總結了相關研究的一些不足,針對這些不足,我們建議今后的研究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加強語言學方面的研究
“民族形式論爭”“大眾語”“民間語言”等有關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的內容曾是現代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專門從語言學視角進行的系統研究還比較少,其實里面也涉及很多語言學方面的問題,我們應該從語言學視角進行系統研究。這些語言問題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如何實現語言建設目標的問題。
通俗化、大眾化、民族化是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建設的目標,實際上就是使用人民大眾看得懂、記得住、用得上的語言,所以也就盡量靠近大眾的日常口語,但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對大眾口語的提煉和汲取,那么這就涉及到革命根據地如何進行提煉和汲取的問題,提煉和汲取的最終表現形式或結果是什么的問題,而這些都是語言學需要研究的內容。
第二,去歐化、通俗化、簡約化在語言形式上的具體表現。
郝銳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現代漢語總結為去歐化、通俗化、簡約化三大趨勢[28]。文章在論述的過程中也提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情況,并認為“解放區的民族形式建設運動和整風運動的開展已經為新中國成立后的語言變革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也就是說,這三大趨勢實際上在根據地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后的語言基調也是根據地時期就奠定了的。因此,革命根據地在去歐化、通俗化、簡約化這三大方面的具體表現也需要從語言學視角進行全面考察與分析。
第三,語言規劃與推廣的問題。
上述問題涉及的大都是語言形式的問題,除語言形式本身外,還有針對語言服務對象的特點進行的語言規劃與推廣的問題,這同樣是語言學研究應該探討的內容。革命根據地原本的書面語言形式并不完全具有口語化、通俗化的風格。比如,我們在查閱1937—1938年的《抗敵報》(《晉察冀日報》)時發現,還存在大量的歐化句式和文言句式,后來經過一系列語言規劃與推廣活動,這些句式才慢慢減少,大眾化、通俗化的目標也才慢慢實現。這些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成功的語言規劃和推廣活動,所以這些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總之,涉及的語言問題很多,并不僅僅是風格或特征一種,我們還需要對上述語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著力于微觀研究
上面我們總結了可以而且需要從語言學方面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問題,這里主要討論做相關研究的著力點。從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著眼于宏觀分析的要多,微觀的少,所以往往給人一種比較模糊或籠統的感覺,并沒有一個從微觀開始再到宏觀這樣一個系統的面貌呈現給大家,所以目前還是應該從微觀研究開始。我們認為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的微觀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第一,以某一具體革命根據地為突破口。
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革命根據地比較多,比如人們熟知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井岡山、延安、沂蒙,此外還有晉察冀根據地,冀魯豫根據地,晉綏根據地,蘇南、皖東根據地,陜甘寧蘇區等。這些根據地在書面語言民族化實踐過程中有很多共性,而且每個根據地都留有寶貴的文獻材料,所以我們可以從其中的一個入手,應該能收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效果。
第二,從某些具體的語言形式入手。
以某一具體的革命根據地為突破口可以縮小我們考察的范圍,降低考察的難度,而研究還是應該從具體的語言形式入手。前面談到,去歐化、通俗化、簡約化是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的主要特征,我們需要找出各個特征的具體表現形式,比如虛詞使用的特征,方言詞或俗語的改造和運用,句中修飾語的使用情況、句式的類型以及辭格的運用等。
3.進行系統的歷時研究
前文談到,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是現代漢語形成與發展這條線中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環,革命根據據地書面語言的民族化便是這一語文建設運動的主要內容,因此從歷時角度、將革命根據據地書面語言的民族化放在現代漢語形成與發展這條線上進行考察與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
第一,以革命根據地某一作家作品或某一連續出版物為考察范圍。
某些作家在不同歷史階段其語言使用情況是不同的,不同時期的作品往往帶有當時歷史的痕跡,所以我們能夠以某一或某些作家為核心,考察其在此期與之前及之后作品語言的變化,由此便可形成革命根據地在以民族形式為本位的語文建設運動中與之前及之后在書面語方面的發展脈絡。吳亮曾從語言學角度對丁玲的作品進行考察。文章從歷時角度比較了1927—1936年和1937—1949年丁玲小說的語言風格,并總結了她在國統區和解放區語言運用風格的不同[8]。當然,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比較漢語在國統區與解放區呈現出的典型性差異及各自的發展軌跡,與我們這里的研究目的不盡相同,但是其中的方法是可以借鑒的。除丁玲外,趙樹理、馬烽、李束為、孫謙、胡正、西戎等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從歷時角度進行分析。此外,革命根據地還創辦了很多刊物,其中有一些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也可以作為歷時研究的材料,比如《晉察冀日報》《新華日報》《大眾日報》等。
第二,對某一或某類語言形式的運用進行歷時考察。
以上我們談的主要是歷時考察的材料問題,考察的目的還是要發現語言形式的變化,所以各類語言形式才是研究的主要對象。我們在翻閱《抗敵報》(晉察冀日報)時發現,很多語言形式在不同階段其表現不盡相同,比如代詞“我們”“俺們”“咱們”,虛詞“也”“亦”“的”“之”,修飾語復雜的長句,同素異序詞等在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表現。這些都可以作為具體的項目進行歷時考察。
總之,從語言學視角、切切實實地分析各類語言項目的變化,才有助于我們了解革命根據地書面語言民族化實踐的具體脈絡,也才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及發展過程。正如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指出的,五四運動以后的四十年,書面語言的變化更為明顯、突出,值得我們好好研究,這種變化和建國后漢語語法的規范化有很密切的關系,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背景,那么后來的語法規范工作就會很困難[5]。而在這四十年中,以民族形式為本文的語文建設觀念及其在根據地的具體實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階段之一,所以具體而系統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