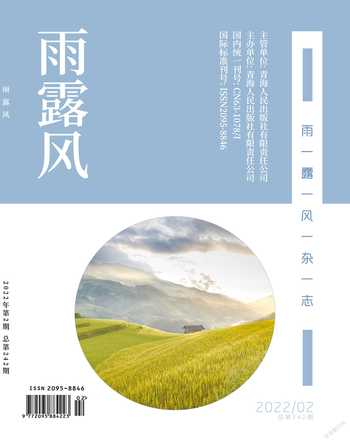美麗與毀滅
摘要:在對菲茨杰拉德的小說及與其有關的傳記研究中,對其妻子澤爾達形象的書寫層出不窮但傳統單一。在以往的傳統書寫里,批評家們從男性視角出發,以“對菲茨杰拉德的影響”來判斷澤爾達的功過是非。但作為一戰后美國新女性(現代女性)的代表,澤爾達是爵士時代女性特有風尚的代言人,也是女性主義的先行者,時代造就了她,也毀滅了她。她終其一生都在與父權社會抗爭,試圖在“失語”環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為飽受非議的自己辯護,為正處于解放中的女性辯護。
關鍵詞:澤爾達;菲茨杰拉德;爵士時代;女性主義
一、“菲女郎”的原型
澤爾達·菲茨杰拉德(Zelda Sayre Fitzgerald),本名澤爾達·塞爾(Zelda Sayre),出生于蒙哥馬利,是美國20世紀20年代的一位小說家、詩人、舞蹈家和畫家,也是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的妻子,他們被譽為美國爵士時代的一對“金童玉女”。澤爾達給菲茨杰拉德的人生帶來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她即是他創作靈感的來源,又是文學創作的阻礙。
菲茨杰拉德以她為原型創作了《人間天堂》中的羅莎琳這一貴族小姐的形象,他在小說中如實地描繪了澤爾達的美麗容貌和性格。而在《漂亮冤家》中格洛莉亞更是與澤爾達如出一轍,菲茨杰拉德與澤爾達在婚后的揮金如土、嗜酒成癮、爭吵不斷等生活細節,在小說中的安東尼和格洛莉亞的身上都生動地重現出來。[1]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黛西向尼克介紹自己女兒的時候說:“我很高興是個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將來是個小傻瓜——這就是女孩子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出路,當一個美麗的小傻瓜。”[2]這正是澤爾達在第一眼見到初生女兒時滿心歡喜地說的話。而澤爾達與法國海軍航空兵尤多亞德·約桑的那段風流韻事,以及因精神崩潰而住院的經歷都為菲茨杰拉德的第四部長篇小說提供了素材。
從讀者期待視野來看,“菲女郎”的原型就是澤爾達,而菲茨杰拉德也樂于塑造出原型是他妻子的女主角,借此滿足讀者的閱讀需要,以及讀者對他們這對“金童玉女”名人生活的窺私欲。澤爾達被塑造成小說里的各色人物,成為所有人公開的凝視對象。
二、澤爾達的美麗人生
菲茨杰拉德與澤爾達生活的年代是被稱作是“柯立芝繁榮”的時代。經濟上的空前繁榮讓無數年輕人沉迷于“美國夢”的追尋,清教主義的控制力量逐漸減弱,傳統觀念開始受到質疑和否定,新一代的年輕人要求文化反叛,他們急于標新立異,表現自己。[3]這個時代也是女權運動和女性解放的時代,一戰的爆發和結束讓全世界女性追求獨立解放的意識自然覺醒,她們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改變。
在富裕家庭出生的澤爾達,從小就表現出不同于上一代的反叛、大膽,極其具有個性,熱情奔放,是美國新潮女性的代表人物。“她天性中自有一種驕傲的態度……也許循規蹈矩的人生并不吸引她,她更愿意在靈感中尋找奇跡。”[4]爵士時代不僅賦予了澤爾達大膽不羈的性格,也讓澤爾達覺醒了主體意識。她嘗試過繪畫、舞蹈還有寫作。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們自己的影后》發表在《芝加哥周日論壇》上,1929年她連續在《校園幽默》雜志上發表了6篇從不同角度描寫現代社會中的年輕女子們生活方式的短篇小說。[5]她的長篇《給我留下華爾茲》是一部華麗的自傳體小說,與丈夫的《夜色溫柔》構成了一對“最不尋常的夫妻篇”。學者朱法榮曾評價道:“該小說是女性主義文體的典范。小說語言高度視覺化、片段化,運用了大量明喻和隱喻,有許多張愛玲式的機智和悖論。”[6]
三、澤爾達的毀滅
(一)浪漫的自私主義者
菲茨杰拉德曾在信中說:“因為她非常美麗、非常睿智、非常勇敢,你可以想象到這些——但她完全是個小孩兒,是比我們更沒有責任感的伴侶。”[7]他強調了兩個人的不成熟,他就像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孩子,需要別人的肯定,而她像個任性的孩子,需要別人的關注。兩個人都試圖占據舞臺的中心,相互愛慕又相互嫉妒,既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各有所好、互為頡頏,她們都是浪漫的自私主義者。
菲茨杰拉德為了寫作,借用妻子日記里的對話當作小說素材,任其污名化。為了在爵士時代出人頭地,將自己的利益擺在首位,希望妻子以他為中心。阻止澤爾達開創自己的事業,貶低澤爾達所取得的成績,甚至將澤爾達的作品占為己有,不允許澤爾達在他的專業領域與他平起平坐。澤爾達活在這所謂愛的牢籠里,一日日地衰敗下去。
而澤爾達也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她膽大妄為,倔強執拗,婚后依舊保持著以前的性格,只關心自己喜歡的事物,忽略周圍人及家庭,甚至在菲茨杰拉德沉迷寫作時迷戀上了法國海軍飛行員愛德華·居贊。兩人在婚姻的后期形同陌路,在同一個屋檐下各自過著自己的人生,澤爾達不滿于菲茨杰拉德對她的掌控,菲茨杰拉德不滿于澤爾達的叛逆,他們無法忍受對方,澤爾達最終精神崩潰進了療養院,而菲茨杰拉德最終潦倒而亡。
他們嘗遍了婚姻中的一切酸甜苦辣,是爵士時代最般配的“金童玉女”,但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信中向澤爾達所說:“我們是在親手斷送自己的前程——我過去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我們是在自相踐踏,我毀了你,你也毀了我。”
(二)爵士時代的迷惘者
菲茨杰拉德在寫給帕金斯的信中說:“我命名了這個時代,并為此感到自豪……它指的是從1919年5月1日的平息騷亂到1929年10月發生的股市行情暴跌這十年間。”在這個絢麗多彩、令人頭暈目眩的時代里,“美國夢想”是可以企及的,財富就在你的手邊,個人的理想完全能夠實現。菲茨杰拉德與澤爾達也不由自主地縱情參與了這個時代的酒食征逐。他們出雙入對往返于巴黎與紐約之間,揮金如土,狂歡作樂,過著酣暢闊綽的生活。富足的物質帶來的卻是貧乏的精神。他們一邊沉湎于其中,一邊又感到惶惶不安。他們處于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臨界點,世界充滿著焦躁,混亂無序,身處其中,只能感覺越來越迷惘與失落。[8]“我們是不是太無聊了?”“絕對無聊,不過多好玩啊——我們出名了至少。”澤爾達跟隨著菲茨杰拉德迷失在大城市的紙醉金迷里,迫不及待地想趕上時代潮流,“人們已經厭倦了平淡樸素,大家爭先恐后地開始出名”。在這種時代氛圍下,澤爾達變成了一個時代的迷惘者,認不清自己,也把握不了時代,任憑時代的浪潮把她淹沒,消失得無聲無息。
(三)女性主義的殉道者
據斯科蒂說,如果認為父親阻止母親的事業追求,從而加速了她精神狀況的惡化,那就想錯了。人們對母親境況的關注日趨高漲,她將其歸結為女性解放運動。“她們的意識覺醒了,需要一個殉道者。”澤爾達就是這個殉道者。澤爾達不斷地找尋自己的社會價值,一次次遭到打擊與破壞,在被迫患上“失語癥”的社會中掙扎抗爭。除了舞蹈與繪畫外,澤爾達試圖通過寫作確立自身的存在與社會價值,但在爵士時代沒有雜志會發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性寫的東西。如果要發表,那么必須附上“菲茨杰拉德”的名字,如同澤爾達的第一部小說《我們自己的影后》,菲茨杰拉德只為小說添加了高潮部分,這本小說最后以他的名字出版,并賺了幾倍的美金。澤爾達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成果與作品被冠上別人的名字,她的社會價值被菲茨杰拉德剝奪,她迷茫于自身的存在,最后以精神崩潰來反抗社會與保持自我。
“女人們需要心照不宣地承受很多規矩,默默承受,不能有怨言,即使最聰明的女人嫁給了最愚蠢的農夫也不能有牢騷。”[9]澤爾達力圖打破這種時代氛圍與局面,女權運動與女性解放也在如火如荼進行,但父權統治面對女性主義的進攻不僅不讓步反思,還進一步打壓與撲滅。這種沖突是女性解放在爵士時代所要面臨的困境,而澤爾達也在這場斗爭中獻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與生命。
四、被隱匿的聲音與權威
一直以來澤爾達生活在菲茨杰拉德的陰影下,很少人會真正了解到澤爾達的魅力與才華。澤爾達在戀愛期間就為菲茨杰拉德提供一些小說故事的想法,如《冰宮》。除此之外,菲茨杰拉德還借用澤爾達的日記當小說素材,在《美麗與毀滅》里澤爾達曾提到,“認出一部分舊時的日記……”這些日記“在結婚之后不久便神秘地消失了”,還有“一些信件的片段……聽起來……模模糊糊似乎很熟悉”。菲茨杰拉德在后來更是用自己的名字或者兩人聯合署名出版她撰寫的小說或文章。澤爾達想繞過菲茨杰拉德的修改和點評直接以她的名義寄給出版社,以尋求個人在寫作方面的發展,而菲茨杰拉德卻極力要求掌控澤爾達的作品。澤爾達幾乎所有小說都有菲茨杰拉德的參與,并得以菲茨杰拉德的意見為主,表面好像文本傳達的是澤爾達的思想和言語,但真正占主導地位的卻是男性的話語權威,澤爾達的聲音被菲茨杰拉德代表的父權思想所掩蓋。
正是父權統治下的男性控制了話語權,才讓澤爾達真正患上“失語癥”直至精神崩潰,對社會徹底絕望。在父權制體制下,在強大的男性話語權威面前,女性的聲音在男性的話語權力中被消解得無影無蹤。澤爾達的在場與失語,更加突出了女性在父權社會的低下地位,她們是供男性消遣的對象,男性話語權威剝奪了澤爾達作為一個父權受害者說話的權利,隱匿了她的聲音與權威。
五、結語
澤爾達所在的爵士時代及她個人的多重身份讓后世對她充滿興趣,也招來了不少爭議,丈夫取得的事業成就及家庭生活的變故更讓她身處輿論漩渦,但不可否認的是,澤爾達自身的光芒無法掩蓋,她代表的是爵士時代與傳統價值決裂的具有現代意識的新女性形象。近來關于澤爾達的研究日益增加且趨近多元化,足以證明,澤爾達不是菲茨杰拉德的附庸,她首先是她自己,她那短暫又絢爛的一生使我們窺見到了爵士時代的吉光片羽。
作者簡介:劉芬(1998—),女,漢族,江西吉安人,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女性主義。
參考文獻:
〔1〕王一然.美國爵士時代女性生活在菲茨杰拉德長篇小說中的呈現[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4:11-24.
〔2〕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巫寧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20.
〔3〕郭肖君.消費主義視角下的菲茨杰拉德小說研究[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2020:12-18.
〔4〕澤爾達·塞爾·菲茨杰拉德.最后的華爾茲[M].秦瞳譯.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23.
〔5〕吳建國.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125.
〔6〕澤爾達·塞爾·菲茨杰拉德.最后的華爾茲[M].朱法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6.
〔7〕斯科特·唐納森.愛中癡兒:菲茨杰拉德傳[M].許若青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7:82.
〔8〕馬爾科姆·考利.流放者歸來[M].張承漠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57.
〔9〕特雷澤·安妮·福勒.Z:澤爾達·菲茨杰拉德的故事[M].劉昭遠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