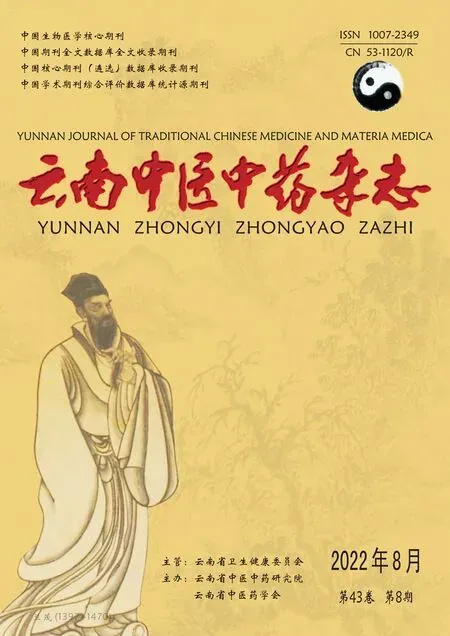王佩娟教授中西醫結合論治宮腔粘連經驗*
陳 玥,陳 思,盧 燕,鐘偉萍,王佩娟,王 靜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中西醫結合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8)
宮腔粘連(intrauterine adhesions,IUA)是指子宮內膜基底層損傷,從而導致宮腔部分或全部粘連閉塞。醫源性子宮內膜損傷是IUA的主要病因,該病治療的最終目標是恢復生育功能。本病常見的臨床表現包括月經過少,閉經,反復流產和繼發性不孕等[1],嚴重影響女性身心健康,并可伴隨一系列家庭和社會問題。中醫古籍中雖沒有“宮腔粘連”一詞,根據其臨床表現及致病特點,可將本病歸入“經水量少”、“閉經”、“不孕”等條目的范疇。中醫認為,該病的發生多因金刃損傷胞宮,又逢術后正氣虛損,外邪趁機侵入,最終導致瘀血阻滯的病理因素形成。中醫藥在術后調月經、提高妊娠率等方面有其獨特優勢。王佩娟是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第六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江蘇省名中醫,從事中西醫結合婦產科臨床30余年,對婦科生殖內分泌疾病有獨到的見解診治方法。筆者有幸跟師臨證,受益頗多,現將王教授診療宮腔粘連的經驗淺述如下。
1 病因病機分析
“夫月經者,津液血脈所成。茍榮衛和,經候自然應期[2]”。月經是由腎氣、沖任、天癸對胞宮產生作用,且在經絡、氣血、臟腑協調作用下子宮定期藏泄所致。腎為先天之本,主藏精,精生血是月經產生的基礎。《女科經綸》曰:“況月水全賴腎水施化,腎水既乏,則經水日以干涸,或先或后,淋漓無時。若不早治,漸至閉塞不通,而必為勞極之證,不易治也[2]。”故腎虛為本病主要病機,調經之本在腎,早期治療尤為重要。《圣濟總錄》認為:“論曰瘀血者……皆本沖任氣虛,風冷所乘,氣不能宣,故血瘀也,瘀血不去,結痼成積[3]”。宮腔操作時金刃器械直損胞宮血海,血液運行受阻化瘀,舊血瘀結,新血不生,日久不通粘連形成癥瘕。因此王教授認為宮腔粘連的病因不外“虛”“瘀”兩端。一方面,金刃損胞宮胞脈,擾亂腎—天癸—沖任—胞宮的正常生理,致腎中精氣受損,沖任氣血不足,血海空虛,不能濡養內膜。另一方面,宮腔操作后余血未凈,術后防護不當,風濕熱毒乘虛入侵,離經之血不能速去而留瘀。故王師認為本病的基本病機是腎虛血瘀,其中腎虛為本,血瘀為標。
2 臨證思路
2.1 重視“治未病”,積極早期干預 子宮內膜具有周期性再生的特點,這依賴于供應子宮內膜的血管的周期性生長和退化[4]。嚴重的子宮內膜損傷就是上皮下毛細血管叢的損傷,導致子宮內膜再生受限[5];上皮細胞、間質細胞、血管內皮細胞等被成纖維細胞和肌成纖維細胞取代,產生包括膠原纖維在內的大量細胞外基質,最終導致內膜瘢痕的形成。因此,損傷缺血組織的快速血運重建是恢復組織功能的關鍵[6]。王師將整個病理形成過程機制類比于濕熱瘀結證之病機,濕熱之邪客于胞宮,與血搏結,日久成瘀。這與西醫的術后早期修復不良,組織缺血壞死甚至感染形成炎性滲出、肉芽形成、瘢痕組織形成相對應,由此提出獨到的早期干預理念。近些年隨著性意識的開放,育齡女性宮腔操作次數顯著增加,而多次宮腔操作史作為宮腔粘連的獨立危險因素應該在就診初期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且現代人喜食肥甘辛辣之品,易使濕熱內生,脾土受困。王師臨證凡遇反復人流等患者,術后多予自擬方為基礎,藥物組成:生黃芪12 g,黨參12 g,薏苡仁12 g,白術10 g,當歸10 g,赤芍10 g,生山楂10 g,續斷10 g,川芎6 g。方中黃芪、黨參為君,大補心脾肺之氣,資宗氣、暢血行,補氣而無留滯之虞,且五臟六腑得到濡養而能行使正常的氣化之功能;赤芍、當歸共用祛除頑固之血瘀;瘀熱搏結,氣血運行不暢,故予薏苡仁清熱滲濕;川芎行血祛瘀;生山楂善入血分,為活血化瘀之要藥,可“除痃癖癥瘕,女子月閉,產后瘀血作疼”。一方面生山楂酸斂,疏肝理氣,可調節氣機而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另一方面還可化已成瘀血;配合白術、續斷益氣扶正之藥共同促使濕熱之邪外出,推動氣血運行。臨床上根據病邪性質偏重和正虛程度酌情調整用藥,收效顯著。有部分學者以為產后應多以溫補為主,實則不然。誠如《續名醫類案》:“蓋產后瘀血,熱結為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干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即死,輕者或堅痞褥勞等疾[7]”。現代藥理研究發現:清熱利濕化瘀藥具有抑制組織中細胞因子表達,調控信號通路發揮抗纖維化作用[8],從而有效防治子宮內膜纖維化粘連。
2.2 “既病防變”,滋腎育膜,活血消癥 王師認為TCRA本身即為重復性宮腔操作,因此預防術后再粘連至關重要。醫者術后第一時間就應該考慮到再粘連的預防以及內膜功能的恢復問題。《傷寒纘論》:“經水適來,而即止必有瘀結[9]”。《證治準繩》:“經水澀少,為虛為澀。虛則補之,澀則濡之[10]”。故以“滋腎育膜,活血消癥”為大法,自擬方包括熟地黃、山茱萸、南北沙參、黃精、菟絲子、枸杞子、桃仁、莪術、澤蘭、澤瀉、牡丹皮、丹參、五靈脂、蒲黃、山藥、薏苡仁、茯苓等藥物。此方中熟地、山萸肉為君,熟地黃滋腎養肝,善補真水;山茱萸滋陰益血,為補肝助力陽良品,腎乃肝之母,即子令母實之義也。菟絲子、黃精、枸杞子、南北沙參補腎益精,補益先天之不足,共為臣藥,加強君藥之效力。澤蘭有散血之功,《本經》載其功效勝于益母;澤瀉其功尤長于行水;五靈脂、蒲黃取自失笑散,五靈脂入肝經,有通利血脈,行瘀的作用;蒲黃生用性滑,破血行瘀;山藥、薏苡仁、茯苓利濕祛邪,又健益脾氣,調補后天之虧損,二者同用兼顧先天后天之本;丹參效具活血調經,祛瘀止痛,“色赤味苦……心與包絡血分藥也”;丹皮以清心肝為主,和血消瘀;莪術專走肝家,破氣中之血;桃仁味苦、甘,苦以泄滯血,甘以生新血;四藥同用,加強化瘀調經之功效,同時得補氣藥固護,扶正祛邪。全方諸藥合用,先后天兼養,攻補兼施,使精氣充盈,沖任調和,氣血順暢,瘀血得去,新血自生,月事如期而下。
2.3 “瘥后防復”,調經助孕 為了避免IUA復發,目前臨床干預措施包括術后放置宮內節育器(IUD)、Foley導管球囊、新鮮羊膜移植和透明質酸凝膠等。盡管采取了各種輔助治療,但復發和生育結局并不令人滿意[11]。一般認為當子宮內膜<6.5~7 mm[12]時,生育力明顯下降。在臨床中,王師運用補佳樂(2~4mg,每日2 次)聯合地屈孕酮(10 mg,每日2次,后半期)人工周期治療以促進內膜復舊,并配合中藥調經助孕治療。行經期“以調經為要”,治法活血調經、除應泄之經血。加用化瘀清利活血之品如益母草、丹參、牛膝等,促進內膜除舊生新。經后期滋陰養血為主,兼以降火,不降火無以復陰。促進卵泡和內膜生長發育,根據病情輕重酌情適當加用歸芍、鱉甲、牡蠣等,同時需注意少佐助陽之品,陰陽并調。經間期用藥促陰陽轉化,誘使卵泡、內膜發育成熟。著重使用的藥物如桃仁、丹參、赤芍、土鱉蟲等。經前期暖宮疏膜,扶助陽長,從氣、血中補陽,常用藥物有淫羊藿、菟絲子、紫石英、鹿角等。
2.4 心理疏導,調暢情志 中醫學素來重視情志致病,心理精神因素在多種婦科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傳統文化中,生育往往被視為女性的家庭義務[13]。而當女性罹患生殖功能障礙時,會經歷各種負面情緒,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往的研究表明,子宮內膜粘連術后再粘連率約為3.1%~23.5%,嚴重粘連率高達62.5%[14]。由于本病治療周期長、易復發,患者更易出現自責和負性情緒。楊歡等[15]研究發現:101例IUA患者抑郁、焦慮的發生率分別為59.4%和24.8%,明顯高于其他患者。研究還表明,長期的不良情緒刺激可能最終影響其生育能力[16]。因此應調暢情志,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醫者在臨床過程中,對此類患者應有充分的綜合管理計劃,包括心理咨詢等,增加幫助患者克服消極情緒的應對策略,并制定合理的干預措施,使患者能有效應對和減少疾病的心理負擔。
3 典型病案
李某,女,32歲,因“清宮術后月經未潮2月余”于2019年 11月25日首診。既往月經尚規則,5/28 d,月經量尚正常,無痛經。患者2019年9月因“稽留流產”行清宮術,術后月余月經未潮,外院就診曾予“達英”口服,月經仍未來潮。生育史1-0-1-1。就診時:帶下不多,色白,無陰癢及異味,納眠可,二便調暢。舌淡苔略紫,脈細。婦科檢查:外陰,已產式;陰道,通暢;宮頸,光滑;子宮,后位,常大,活動尚可,無壓痛;附件:雙側未及異常。實驗室檢查:性激素六項均處于正常范圍內。婦科B超:子宮內膜兩層厚約3 mm,余未見明顯異常。四診合參,中醫診斷:閉經,證屬腎虛血瘀;西醫診斷:宮腔粘連。
首診:患者暫拒服中藥,予芬嗎通2/10 mg口服。
2020年1月6日二診:患者服藥后月經仍未來潮,有乳脹感。患者月經未至,以滋腎養陰、助瘀調經為主,方選滋腎育膜湯加減,處方如下:熟地黃12 g,山藥10 g,山茱萸10 g,南北沙參各10 g,澤瀉10 g,澤蘭10 g,牡丹皮10 g,丹參10 g,菟絲子10 g,枸杞子10 g,蒲黃炭10 g,桃仁10 g,薏苡仁10 g,黃精10 g,莪術10 g,蒲黃炭10 g,五靈脂10 g,共10劑;日1劑,水煎服,分溫二服。
2020年1月20日三診:患者訴服藥后月經來潮,量少,1天半即凈。囑行宮腔鏡檢查,術中探查:宮腔粘連成桶狀,子宮內膜蒼白,雙側輸卵管開口不可見,宮腔中段至宮底部見粘連帶,予行宮腔鏡下粘連分離術,上宮型環一枚預防再次粘連。術后診斷:宮腔粘連。術后同時予補佳樂3片q 12 h 口服促進子宮內膜增生,后半周期予“達芙通”10 mg q 12 h口服。患者處于經后期,以補腎滋陰益氣為主,在前方基礎上去蒲黃炭、五靈脂、莪術、南北沙參、薏苡仁、澤瀉;加入黃芪15 g,淫羊藿10 g,鹿角霜10 g,首烏藤10 g,杜仲10 g,白術10 g,茯苓10 g,紅花10 g,雞血藤10 g,川芎6 g。
2020年3月2日四診:服藥 1 周期后復診,訴此次月經來潮經量較前明顯增加,3 d凈,予原法治療3個月經周期。經期處方:當歸10 g,川芎10 g,巴戟天10 g,仙茅10 g,紅藤10 g,敗醬草10 g,益母草15 g,香附9 g,陳皮6 g,共5劑。
2020年6月13日五診:訴近3月月經量已恢復至正常經量3/4,經凈3 d后予行宮腔鏡下取環術。術中探查:宮腔形態基本正常,體積偏小,宮內膜偏薄,未見明顯粘連帶,雙側輸卵管開口可見,取出宮型環一枚。取環術后門診繼續予補腎化瘀中藥口服、中藥調周及B超監測排卵,2020年12月自測尿HCG(+),后行B超提示宮內早孕,妊娠4+月時因家庭原因行引產術。
按:本案患者因清宮術致宮腔粘連,中醫認為腎為先天之本,主生殖,腎氣旺,沖脈充盈則經血自調。而宮腔操作使用金刃器械直接損傷胞宮致瘀血阻于經脈,血脈無以充盈,表現為閉經或月經過少。故王師認為清宮術后出現月經過少的病因病機為腎虛血瘀,其中本為“腎虛”,標為“血瘀”,故治療本病以滋補腎精、活血化瘀為主。針對本類患者以自擬滋腎育膜方為主,輔以補腎調周,通補兼施,共奏補腎化瘀之效,使氣血順暢,血脈充盈,經水自多,后成功妊娠。
4 小結
宮腔粘連是由于各種因素導致子宮內膜受損,從而引起內膜纖維化粘連帶形成,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炎細胞浸潤[17]。IUA的程度和位置決定了疾病的嚴重程度,重度粘連時宮腔內可見結締組織形成,內膜萎縮,腺體失活,間質血管形成障礙,粘連局部處于缺血低氧的微環境[18]。其影響因素包括分娩、手術流產、剖宮產、宮腔鏡下子宮內膜息肉切除術(HREP)、宮內節育器(IUD)放置、子宮內膜結核、盆腔放療等[19]。據報道,90%以上的IUA是由宮腔手術引起的[20]。隨著宮腔鏡的普及,本病的發病率和診斷率已升至2.2~36.8%[21-22]。雖然宮腔鏡下粘連松解術(HA)已廣泛應用于臨床,但術后復發率高,妊娠結局差,依然給臨床診療帶來很大挑戰[23]。而民眾的生育熱情與本病復雜性、長期性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得本病成為婦科領域重難點。研究顯示:中醫藥辨證論治與雌孕激素人工周期相結合,能夠有效幫助子宮內膜增生,改善宮內膜環境[24]。大量現代藥理研究也證明補腎活血類中藥可改善內膜容受性,具有類雌激素樣作用,可恢復生殖軸功能。王師在診療過程中圍繞中醫“治未病”思想,以“滋腎育膜,活血消癥”為法,分期論治,中西結合,輔以心理疏導,療效頗佳,為宮腔粘連的治療提供了新的臨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