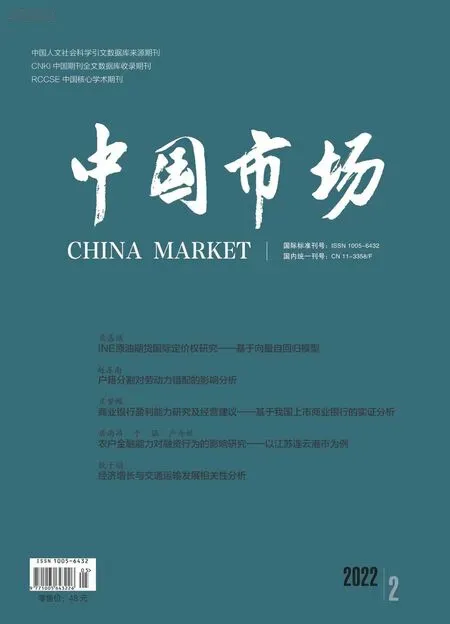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分析
趙蘇南



摘 要:文章從“劉易斯拐點”到來的2003年和“人口紅利”趨于消失的2013年兩個時間節點出發,使用相對扭曲系數來構建勞動力錯配指數,并通過選取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來探討分析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通過2003年與2013年的比較,靜態分析發現戶籍分割會顯著地加劇勞動力錯配程度,政府行為雖不能將戶籍分割造成的錯配影響消除,但卻能顯著地改善勞動力錯配。
關鍵詞:戶籍分割;勞動力錯配;人口紅利
中圖分類號:D631.4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2)05-0009-03
DOI:10.13939/j.cnki.zgsc.2022.05.009
1 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商品市場日趨完全競爭化,而要素市場仍存在諸多錯配、失配的現象。因此,促進一國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改善要素配置扭曲已迫在眉睫。本文以“劉易斯拐點”到來的2003年和人口紅利趨于消失的2013年為時間節點來探討戶籍分割對勞動力資源錯配的影響,發現無論2003年還是2013年戶籍分割都顯著地加劇了勞動力的錯配,而代表政府行為的戶籍改革變量雖不能消除這種影響,但卻能顯著地改善勞動力錯配。
當前對中國資源錯配尤其勞動力資源錯配的大量研究大多從市場因素進行探討,從政府或者說從制度因素進行的研究還較少,本文的研究豐富了制度層面相關理論,為政府進一步進行戶籍改革以激發勞動力市場活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2 文獻綜述
本文與研究勞動力錯配的文獻相關。當前我國勞動力錯配問題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日益凸顯,大多學者認為中西部地區的錯配程度要高于東部地區(梁泳梅等,2011);而朱喜等(2011)研究表明東西部地區資源錯配嚴重。劉偉和張輝(2008)發現第三產業錯配最為嚴重。Hsieh和Klenow(2009)以美國為參考系重新測算中印兩國TFP,得出由于勞動力錯配中印TFP效率損失為30%~50%和40%~60%。
本文還與戶籍制度文獻相關。戶籍制度由于其“屬地性”特征,會造成勞動力流動障礙。現有文獻表明戶籍制度改革能夠破除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Whalley J. and Zhang S.,2007;朱江麗和李子聯,2016)。當前,國內學者都認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能帶來巨大效益,不但能促進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還能促進城鄉一體化,實現國內大循環(蔡繼明和李新愷,2019;陸銘,2020;蔡昉,2020)。
因此,戶籍分割會通過其“屬地性”特征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構成障礙,從而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造成各地勞動力分配不均,即區域間勞動力錯配。
3 數據及變量
3.1 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力統計年鑒》,以及2003年和2013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考慮到CGSS2003與CGSS2013有不重疊的地方,遂剔除CGSS2003中海南與新疆的樣本,CGSS2013中青海與寧夏的樣本,即本文考察2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勞動力錯配情況。此外本文還剔除了年齡不在15~64周歲以及主要變量中有缺失的樣本,共獲得2003年4846個樣本,2013年8997個樣本。
3.2 勞動力錯配指數的構建
本文借鑒Hsieh & Klenow(2009)、季書涵等(2016)的方法使用相對扭曲系數來衡量勞動力資源錯配指數。當勞動力錯配指數大于0時表明資源配置不足,同時為了回歸方向的一致性,本文將在回歸時取其絕對值,絕對值越大說明錯配程度越高,當回歸系數小于0表明該變量能改善勞動力錯配。關于勞動力錯配指數的估算表達式如下所示:
其中,τi表示i省的勞動力錯配指數,γi表示i省的勞動力絕對扭曲系數,γi的表示方式如下:
其中,Li表示i省份的勞動人口數量,si表示i省支出占整個經濟體支出的份額,βi是i省勞動力產出彈性。因此要得到各省的勞動力錯配指數,需要先對各省份的勞動力產出彈性進行測算。將生產函數設為C-D形式,并取對數,即lnY=lnA+αlnK+(1-α)lnL,再將lnK和lnL回歸到lnY上時,本文還額外控制了各省的受教育水平。其中產出變量以各省份經零售價格調整的GDP表示,勞動投入量以各省份就業量衡量,資本投入量以各省份固定資本存量表示,并運用永續盤存法來計算:Kt=ItPt+(1-δt)Kt-1,Kt為當期固定資本存量,It是各省總的固定資產投資,Pt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δt為折舊率,并賦值9.6%[1]。經本文測算,相比于中部地區,東、西部地區的勞動力錯配程度較為嚴重,2003年東部地區表現出勞動力資源配置不足,西部地區則表現出配置過度;而2013年則發生了逆轉:西部配置不足而東部配置過度,此外中部地區的錯配程度也有所加深。
4 實證分析
4.1 基準模型
本文分別對2003年和2013年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進行分析,并控制社會融入度:幸福感、信任程度和與親友的密切程度與個體特征:性別、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狀況、年齡,見式(3)。為了觀察政府行為(在2003年表現為 “農轉非”,在2013年表現為“戶口改革”)的調節效應,在式(3)中引入表示政府行為的調節變量,見式(4)。
其中,τ表示勞動力錯配程度,hk表示戶口狀態,ξ表示社會融入度,λ表示個體特征,gov表示政府行為,ε表示隨機擾動項。
表1為回歸結果,結果顯示不論是2003年還是2013年戶籍分割都顯著加劇了勞動力錯配程度;且當加入表示地方政府行為變量時,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程度的加劇程度更大,分別提升了0.33%和0.121%。戶籍制度人為設置了戶籍遷移阻礙,不僅束縛了勞動力遷移,還加劇了戶籍分割對省級勞動力錯配的影響。從“戶口改革”使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程度的加劇程度不足“農轉非”相應的加劇程度的一半表明政府已不再滿足于“農轉非”這類發展型戶籍改革,開始訴諸更深層次的戶籍改革路徑,以促進本地經濟的發展。通過(1)(3)列的對比分析,社會融入度對勞動力錯配的作用由2003年的顯著加劇到2013年的改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的系數分析表明,在2003年年輕的未婚男性能夠顯著改善勞動力錯配,這一結果表明2003年雖然是“劉易斯拐點”,但由于“人口紅利”中的勞動力儲備大軍仍有剩余,因此地方政府仍能享受到“人口紅利”帶來的效益。但將時間鏡頭切換到2013年,婚姻狀況和年齡已經不再顯著,而且更多關注男性會惡化勞動力錯配,進而可以推測出“人口紅利”走向枯竭,尋求經濟新的增長點迫在眉睫。通過(2)(4)列的對比分析,“戶口改革”的改善效果較“農轉非”而言提升了2.88個百分點,這表明通過更深層次的戶籍改革能夠更好改善勞動力錯配。
4.2 內生性檢驗
勞動力素質關乎勞動力的生產效率,若勞動者無法將自身素質準確傳達到勞動力市場,雇用者無法從勞動力市場中讀取到相應勞動力素質,則會造成勞動市場信號傳導機制失效,進而造成錯配。本文通過代理變量法來解決遺漏變量問題,具體而言,使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來代理勞動力素質(當前勞動力市場主要通過求職者文憑來匹配所需人才)。與基準回歸相比,相關結論在方向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雖然2013年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并不顯著,看似是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消極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除,但本文認為這可能是由于當地為了留住人才戶籍屬性已不再那么重要。政府行為從2003年的不顯著到2013年的顯著,也更加凸顯了基準回歸中關于政府行為通過更徹底的戶籍改革能夠更好改善勞動力錯配的表述。
4.3 穩健性分析
張吉鵬和盧沖(2019)得出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落戶門檻較高且有上升趨勢,因而本文在考慮穩健性時剔除了北京和上海。通過與基準回歸的對比,主要結論的顯著性和方向并未改變,只是2003年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表明戶籍門檻中低水平地區在2003年提前走向“人口紅利”的枯竭。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兩個時間節點出發,構建省級勞動力錯配指數,并選取CGSS2003和CGSS2013數據來探討戶籍分割對勞動力錯配的影響。通過2003年與2013年的比較靜態分析得出:戶籍分割顯著地惡化了勞動力的錯配,政府行為雖不能將其消除,但能顯著地改善勞動力錯配。
為實現國內大循環,面臨著如何改善中國勞動力資源錯配這一核心問題,鑒于戶籍分割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負面沖擊,政府更應充分發揮好其“有形的手”的作用,讓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充分發揮其效能。政府應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改進:一是深化戶籍改革;二是努力提升勞動者的社會融入度;三是努力提高基層教育水平;四是推動建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參考文獻:
[1] 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35-44.
[2]WHALLEY J,S ZHANG.A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Hukou) labour mobility restrictions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3(2):392-410.
[3]HSIEH CHANG-TAI,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4):1403-1448.
[4]RESTUCCIA D,R ROGERSON.Mis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J].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3,16(1):1-10.
[5]朱江麗,李子聯.戶籍改革、人口流動與地區差距:基于異質性人口跨期流動模型的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6,15(2):797-816.
[6]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1):28-41.
[7]張吉鵬,盧沖.戶籍制度改革與城市落戶門檻的量化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9,18(4):65-77.
[8]蔡繼明,李新愷.深化土地和戶籍改革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J].人民論壇,2019(24):114-115.
[9]陸銘.牽一發而動全身[J].上海國資,2020(5):8.
[10]蔡昉.合理評估“就地變更戶籍身份”的改革潛力[N].北京日報,2020-11-09(10).
[11]梁泳梅,李鋼,董敏杰.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錯配[J].中國人口學,2011(5):36-48.
[12]朱喜,史清華,蓋慶恩.要素配置扭曲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J].經濟研究,2011(5):86-98.
[13]劉偉,張輝.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08(11):4-15.
[14]袁志剛,解棟棟.中國勞動力錯配對TFP的影響分析[J].經濟研究,2011(7):4-17.
[15]季書涵,朱英明,張鑫.產業集聚對資源錯配的改善效果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6(6):7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