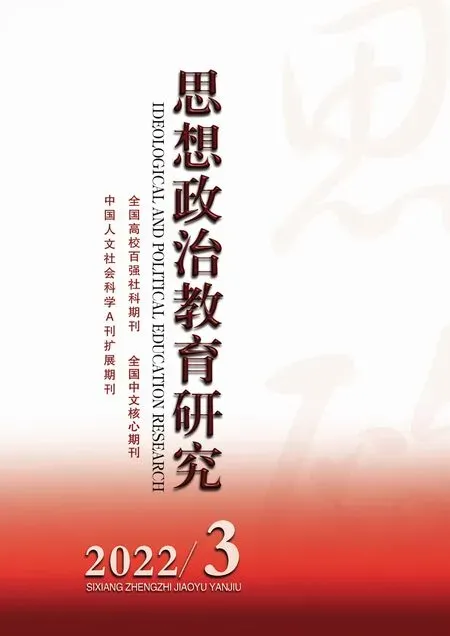孔子“樂教”的審美闡釋及其當代美育價值
郎松雪
東北石油大學 人文科學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中國美育理論的建構時間較晚,但是中國美育思想古已有之,一直與中國傳統樂教發展關系密切。上古時期,樂教表現為巫樂展演形式背后審美價值觀的趨同;西周時期,表現為服務國家政治需要的禮樂制度;孔子時期,樂教成為真正具有美育意義的面向普通大眾的教化工具。正如《樂記》所說“廣博、易良,《樂》教也”[1],樂教成為衡量一國百姓美育素養的重要方面。通過樂教,可以使百姓和通廣博、簡易善良。當前,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美育的重要意義以及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育文化。我們可從孔子“樂教”為代表的傳統美育中獲取精神源泉與時代啟示。
一、孔子“樂教”的審美特質
孔子面對“禮壞樂崩”的社會現實,倡導恢復西周時期的禮樂文明。同時,孔子“樂教”強調符合“禮”的音樂審美形式,積極抬高“雅樂”的社會地位,以“仁”的思想貫通樂教育人全過程,形成了基于情感升華的音樂美感與高尚靈魂相統一的審美特質,開啟了具有美育意義的樂教傳統。
1.立于禮,成于樂:孔子“樂教”的審美表現形式
孔子會唱歌、會樂舞、會編曲、會擊磬、鼓瑟、彈琴,可以說是一個全能型的音樂家。孔子始終堅持音樂的“禮”性,所謂“以禮節樂”。“禮”是“樂”的規范,只有符合“禮”的“樂”才是符合審美要求的音樂形式。同時,孔子還將“樂”的“禮”性,融入到育人過程中。《八佾》篇載,當孔子跟學生談到季氏,說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八佾之舞乃是太子御用,而季氏作為大夫只能用四佾。孔子說季氏連僭越禮制的壞事都能狠心做出來,還有什么壞事做不出來呢。孔子對季氏評價中盡顯“以禮節樂”的審美特點,而且“樂”也成為衡量人性的重要依據。《先進》篇載,孔子曾評價仲由彈瑟音調不入孔門,這句略帶情緒的音樂點評,導致其他弟子對仲由不敬。孔子意識到音樂評價失去“禮”的規范,就會影響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可見,不僅音樂本體要符合禮制的要求,對他人音樂能力評價也要在“禮”的范圍之內,兼顧公眾形象及其個人威望。
孔子提倡“禮”“樂”互為表里,“樂”要符合“禮”的規范,“禮”要成全“樂”的追求。“禮”是外在的、務實的,更體現規約性;“樂”是內在的、精神的,更體現感染性。王齊洲說上古“樂”有二音二義,讀樂(yuè)指音樂,讀樂(luò)指內心的喜樂。而音樂本就產自人心喜樂,又是人心的表象,還以陶鑄人心為目標[3]。因此,音樂本身是快樂心情的體現,又是塑造人心的介質,能夠架起情感與人性的橋梁,起到情感溝通、思想交流、規范行為、提高審美等多種作用。孔子早就認識到樂教的重要性與獨特性,無論是詩教、禮教都貫穿樂教,還把樂教作為最終成人的標志。
2.雅正中和:孔子“樂教”刪詩正樂的審美標準
“雅樂”又稱“先王之樂”,是當時宮廷演奏、祭祀的重要樂曲。但隨著地方音樂流行,鄭、衛俗樂逐漸替代雅樂,走進大夫雅集、宮廷宴飲之中,威脅到了“雅樂”的正統地位。孔子再次強調中和之美的音樂形式,弦歌雅樂《關睢》,發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感嘆[4]。
雅樂是當時的正統音樂。從音樂形式看,雅樂主要使用編鐘和編磬演奏,曲風莊重、典雅,曲調中正、平和,變化少,歌詞典雅、純正;從表現內容看,雅樂歌詞多來自《詩經》大雅、小雅、頌等篇章,主要用在祭祀、宮廷以及外交等重大場合,多為對人行為的規范以及對人思想感情的熏陶。但可惜的是,孔子時期,雅樂早就名存實亡。
西周以后,樂教逐漸失去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逐步喪失其作為宮廷音樂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以“鄭衛之音”為代表的民間音樂開始大量進入王室宮廷,商代末年縱欲賞樂的情況再度上演。另一方面,愿意接受傳統樂教的人群逐漸縮小,能演奏、聆聽雅樂之人更少,各國樂師也因得到不公正待遇而逐漸解散[5]。《微子》就記載了魯國樂師四散流亡的具體情況:“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6]可想而知,一直奉行周禮的魯國都衰敗如此,雅樂在其他諸侯國更是全面衰敗。
孔子及其弟子卻一直非常推崇雅樂,因為樂教不僅是音樂教育,更是情感教育、生命教育。孔子強調音樂作用人心,通過人心陶冶情感,通過情感升華志向,通過踐行志向實現社會和諧,從而獲得美善兼備的人生境界。雅樂發乎情、合于心、止于禮、致于和,正是孔子樂教的核心內容。且雅樂的中正和諧,亦成為孔子刪詩正樂的審美標準。當時孔子已是暮年,針對雅樂衰敗情況以及《韶》《武》之樂繁復的特點,重新整理《詩經》為三百零五篇,并將每篇都打造成獨具雅樂特色的唱詞。孔子用最真摯、純潔、中正、平和的音樂教化人心,增強人們對雅樂“中和之美”的價值認同感。
3.盡善盡美:孔子“樂教”審美追求的終極目標
孔子言論中,多次表達“禮、樂”應該歸于“仁”“善”的觀點。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7]如果沒有“仁”的思想內容,“禮、樂”就成為一種裝飾,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8]如果沒有“仁”的真情實感,玉帛、鐘鼓的禮、樂形式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仁”的提出使孔子樂教思想與西周相比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孔子將“仁”的思想融入樂教之中,是對前人思想的繼承與創新[9]。孔子在“禮壞樂崩”社會背景下,發現人人心中的“仁”愛之心,這是人的道德情感歸宿,也是樂教的最終歸宿。例如,《衛靈公》篇記載,孔子在見到盲人樂師時: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10]這段話是樂師冕拜見孔子的過程,雖然沒有與音樂相關的談話內容,但是通過極其細致的時間與空間詞語序列,突顯孔子與樂師交往時非常重視禮節,表現出孔子對音樂的虔誠追求,更細膩地呈現了孔子的“仁愛之心”。
“仁”的情感驅動源于人類本性中的“善”,孔子“樂教”中處處彰顯“仁”與“善”的光芒。《八佾》篇中記載了孔子對音樂的著名評論:“《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11]孔子在評價《韶》樂時,認為它贊美了舜帝的德治,是盡善盡美的;而《武》樂是武王伐商的戰功之樂,雖然做到了盡美,但未能盡善。在這里,“美的”不一定是“善的”,但“善的”一定是“美的”。可見,孔子的“樂教”不僅只注重音樂的形式美,更關注音樂的內容之善,而“盡善盡美”就是孔子“樂教”審美追求的終極目標。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孔子“樂教”的審美特質:符合“禮”的審美形式,符合“雅正中和”的審美標準,符合“仁善”的審美內容,最終達到“至善至美”的藝術境界。
二、孔子“樂教”的審美實踐
歷史上,真正具有美學意義的樂教是從孔子開始的。孔子“樂教”的美育傳統也在后世得以繼承和發揚。正如徐復觀所說:“到了孔子,才有對音樂的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而在最高藝術價值的自覺中,建立了‘為人生而藝術’的典型。”[12]孔子依托“六藝”審美元素,輔之以先秦專門典籍,將樂教的美善境界融入到審美實踐之中。
1.樂以養心,孔子“樂教”陶冶心靈,培養高尚的審美與道德追求
音樂源自人心,能夠與人心相通,因此也能夠感化人心。《禮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13]致樂治心,音樂能夠帶動我們對于聲音的審美體驗,通過中正美好的音樂導向,激發人類心靈深處對真、善、美的追求,從而提升審美能力。孔子對音樂審美的不懈追求,《論語》多有記載。如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竟然很長時間都吃不出肉的香味,并慨嘆“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14]孔子贊嘆《韶》樂境界超凡脫俗,描述的文字讓人對音樂美的極致充滿想象。孔子還關注唱歌技巧的提升,“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喝之。”[15]通過復唱與和唱形式,追求唱歌零瑕疵。孔子甚至把唱歌當做一種信仰執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16]孔子唱歌一直遵循著古樂禮儀。由此可知,孔子非常重視音樂對人類心靈的滋養作用,并通過不斷提升審美水平,塑造人心,實現藝術與禮儀道德的統一。
孔子及其弟子非常重視音樂直抵心靈的作用,并逐漸形成理論來闡發音樂與心性之間的關系,這在出土文獻中多有體現。郭店楚簡的《五行》《性自命出》《六德》《語叢》《緇衣》等篇章都涉及了《詩》樂思想[17]。《性自命出》更是被公認為心性教育的專論,文中指出,心術、修身與樂教有重大關系。
2.樂以養志,孔子“樂教”濡養志向,培養具有高遠的理想境界
孔子樂教講授的是中正平和的雅樂,其特點是變化少,節奏平緩,長時間受此種音樂熏陶,會使人心胸開闊,志向遠大。《荀子·樂論》記載:“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18]志向也是需要滋養的,雅頌之聲猶如羹湯,沁潤著每個遠大的理想。《先進》篇中論及孔子及諸弟子志向時,也有精彩印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19]
這段話是曾皙在暢談自己的志向,值得仔細品讀的是子路、冉有、公西華在談論理想時,都不曾有音樂,而曾皙出場卻對音樂進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寫。曾皙的理想正是孔子所贊同的,這樣遠大的理想同時伴隨著鏗鏘有力的鼓瑟,伴隨著典雅音樂的從容。這個實例證明,孔子教育學生樹立理想時,經常伴隨音樂的引導與教育,充分彰顯了樂以養志的重要作用。
3.樂以養行,孔子“樂教”滋養善行,促進知行合一
樂教的特殊性在于不需要通過文字或者其他符號來掌握,而是直接作用人心,表現為聆聽、創作、表演等理論與實踐相同的輸出模式,因此也成為美育的有效形式。孔子重視樂教知行合一的作用,并展開一系列實踐活動。在個人層面,孔子弦歌《詩經》,詮釋“樂”對學生心靈、思想、情操的陶冶作用;通過樂與詩的結合,施行對學生的教化,修繕人與人的情感、道德,培養文質彬彬的君子。在社會層面,孔子“樂教”強調禮、樂共生,“樂”是有感于心的人類情感內在表達,“禮”是外化于行的人類行為的道德規范。在國家層面,孔子整理《詩經》文獻,通過刪詩正樂,駁斥鄭聲,糾正了當時魯國混亂的宮廷樂舞,重歸“樂”于“禮”的范疇。
在孔子“樂教”審美實踐中,孔門弟子逐步完善自身人格塑造,踐行自己所學到禮樂知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子游。《陽貨》篇載: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20]這是子游在武城作縣長,利用彈琴鼓瑟形式教育當地民眾。孔子到達武城時,正好聽到歌聲,于是覺得子游有點兒小題大作。子游卻義正言辭地說,是老師“樂教”促使我使用這樣的方式讓百姓產生仁愛之心,這樣百姓才容易管理。孔子于是后悔自己說的話。子游能夠突破老師局限,于小城之中踐行樂教理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三、孔子“樂教”的當代美育價值
孔子“樂教”突破西周時期的政治束縛,是歷史上真正具有美學意義的樂教,更是中華傳統美育精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正如《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指出:“弘揚中華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納入各級各類學校人才培養全過程。”[21]孔子“樂教”通過詩、禮、樂無縫配合,培養三千弟子;通過重新抬高雅樂地位,打造情感與道德高尚的翩翩君子;通過貫通“仁者愛人”的思想,涵養根植于內心的善良與熱情。孔子“樂教”有許多當代美育建設值得借鑒的地方,對實施全方位、全過程美育育人具有重要啟示。
1.詩禮樂一體,系統“育”人
當前美育更多被狹隘地理解為“藝術教育”,呈現一定程度的“孤島”現象[22]。實際上美育由“美+育”兩字構成,《說文解字》講“羊大為美”、“養子使作善為育”[23],這就說明美育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包括審美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育等綜合元素。孔子應該早就意識到審美的獨特作用,由此提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三位一體的美育育人路徑[24]。且孔子提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25],其樂教思想始終與道德、仁心融合一體。為此,孔子樂教先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教育學生逐步掌握技能,再以《詩》《書》《禮》《樂》先秦典籍教育學生掌握思想,打造獨具藝術性與思想性的彬彬君子。孔子樂教給當代美育的啟示從橫向看,音樂等藝術類學科應加強與學科內、外的交叉與融合,這樣才能突破學科本身設置上的限制,適應當代教育形式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如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古典詩詞吟唱的新媒體傳播”,就是融合文學欣賞與藝術品鑒,并以國家一流課程、QQ音樂唱片、全國范圍內講座、俄羅斯遠東訪學等多種成果形式發揚中華傳統美育精神。從縱向看,音樂教育應該貫穿人生教育的每個階段。小學、中學美育側重美育技能與審美能力,大學美育側重美育思想與審美情感,使美育真正成為一種情感教育,一種生命教育。
2.和諧雅樂,以美“化”人
《說文解字注》曰:“化,教行也。教行於上,則化成於下。”[26]化,有教化、改變之意。一般來說,音樂根源于人心,因而能與人心相通,感化人心,這使得音樂本體所具備的屬性格外重要。孔子就是看到了雅樂所具備的規范人心、協和萬物的獨特屬性,因此,無比推崇雅樂,駁斥鄭衛之音。以鄭聲為例,鄭聲就是鄭國的音樂,鄭國因受故商影響及其發達的商業水平,音樂帶有商品化風格,極度注重美感,強調娛樂性與藝術性,缺乏中和之美與道德規范。孔子認為鄭國的樂曲破壞了典雅的樂曲,特別是破壞了雅樂所具有的規范性。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強調,藝術創作要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國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要兼具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27]。根據孔子“樂教”經驗與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音樂創作通俗但不可低俗,要始終堅守音樂的道德規范性;為藝術而不可為媚俗,要始終堅守藝術創作的思想性。例如,疫情期間,一首《希望》刷爆了朋友圈,歌曲表現的上下團結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正是時代所需,導向人們積極抗擊疫情,堅守信念、堅定信心的勇氣與行為。
美育既要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不良風氣,又要強調學習過程的“娛樂”精神。當前美育過分重視藝術教育的知識化,逐漸把美育變成專業技能的訓練,導致美育在專業高度分工背景下變成一個個知識的代名詞,無法滿足絕大多數學生全面發展的需求。孔子樂教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很好的示范,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孔子樂教重視情感感化,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28],雖然沒提音樂,但是孔子學習秉持的快樂精神,感染著身邊的每一個弟子;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知者”[29],“知之、好之、樂之”體現的學習態度,由知識領悟上升到情感感化,喚醒學生好奇心與學習熱情。二是孔子樂教重視潛移默化,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30],通過山水自然之美,潛移默化地熏陶學生追求“仁”與“知”;“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31],通過孔子與魯大師對話,潛移默化地提高學生的音樂素養與審美能力。三是孔子樂教重視藝術生活化。曾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32],孔子贊同曾點的想法,能快樂地在沂水旁洗澡,在舞雩臺吹風,唱著歌回家,生活充滿著藝術的美感與愜意。孔子重視音樂對人的情感、人的性格、人的追求的塑造作用,在樂教中融入音樂的快樂精神與生活化表達,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與興趣,從而實現美育對人真正意義的改變。
3.仁心樂善,鑄魂培“元”
席勒《美育書簡》首次提出“美育”一詞,主要針對近代大工業革命導致的矛盾與人性分裂。這種分裂稱之為“心靈異化現象”,表現在教育方面主要是學生對學習缺乏興趣,對專業缺少喜愛,對加之于身的外在事物表現麻木。因此,美育只有突破知識教育、技術教育的局限,成為一種情感教育、生命教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心靈異化的問題。孔子樂教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一是樂美樂善,關注生命教育。孔子在齊國聽到了美善兼備的《韶樂》,竟然三月不知肉的滋味,這是一種饒有趣味的審美體驗,當孔子以味覺去描寫聽覺感受時,激發了學生對《韶樂》本身的極大興趣。同時在學習《韶樂》的過程中,得到了審美經驗的提升與道德建設的完成。所以說,美是藝術的標準,善就是仁心的體現。美善融合的音樂才能啟發學生心智,浸潤學生心靈,激發生命體驗。二是樂者仁心,提升心靈境界。美育的真正目的并非完全知識傳授而更重視啟迪心靈。孔子非常重視音樂對人心靈的滋養作用。孔子及其弟子被困陳蔡之際,弟子們愁眉不展,孔子仍然弦歌不輟,并說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33]這種高尚的人生追求伴隨著音樂感染著身邊每一個弟子。古人非常重視喪禮,孔子曰:“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34]孔子在喪禮上從未吃飽過,是想為逝人家屬分擔痛苦。可見,孔子的仁心不僅惠及生者,更兼顧已逝之人。而且如果傷心哭泣,這一天就一定不會唱歌。孔子的仁心在音樂中滋養,孔子高尚的追求在音樂中升華。三是天人之樂,追求知行合一。孔子樂教理論與實踐是融為一體的。孔子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知行合一,“三月不知肉滋味”是知行合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知行合一[35]。孔子樂教的知行合一側重興趣與追求完美結合、藝術與道德互為表里、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美育激發了人類心靈深處的感情認同、價值認同,從而形成良好的育人效果。
結語
綜上所述,孔子樂教將“樂”的詩、樂、舞形式提升至人類對美好情感、美好人格塑造的高度,并以“人心之仁”的思想得以貫通,開創了歷史上真正具備審美意義的美育。這種美育以“雅樂”為核心,以詩、禮為表彰、以美育實踐為常態,涵養了中華傳統美育精神。這種精神離不開中華幾千年來的禮樂文明,特別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重視禮樂,把禮樂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手段[36]。孔子還將“成于樂”看作完備育人的最高境界,形成了歷史上最早具有美學意義的樂教育人傳統,為當代美育建設提供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