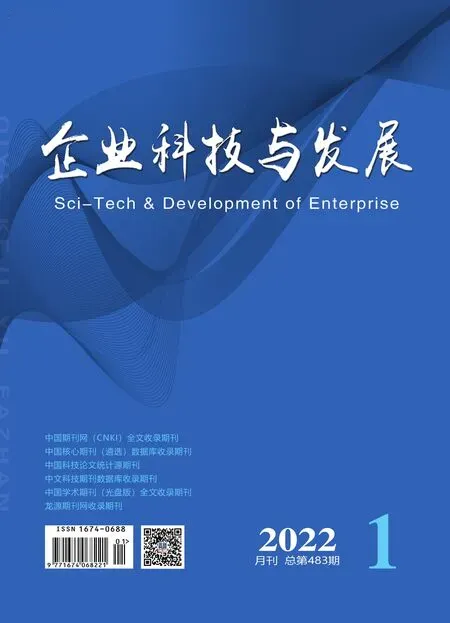環(huán)境信息披露、高管特征和企業(yè)財(cái)務(wù)績效
——來自573家污染企業(yè)的經(jīng)驗(yàn)證據(jù)
趙硯
(浙江工業(yè)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浙江 紹興 312000)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jīng)濟(jì)得到了快速發(fā)展,就當(dāng)前所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可知,我國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在2018年已經(jīng)達(dá)90萬億元,相對于2017年的經(jīng)濟(jì)情況而言,有著明顯的提高。但是,我國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尚不完善,大部分企業(yè)為重工業(yè)生產(chǎn),并且我國的科技水平有限,工業(yè)廢水排放問題直接影響著我國的環(huán)境。根據(jù)EPI報(bào)告中的數(shù)據(jù)可知,我國環(huán)境問題較為嚴(yán)重,在180個(gè)國家和地區(qū)的環(huán)境績效指數(shù)打分中,我國排在第120位,僅得5 074分,在所有的國家里面排在倒數(shù)的位置。2015年習(xí)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fā)展理念,我國生態(tài)問題首次得到了重視。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針對我國生態(tài)文明和綠色發(fā)展目標(biāo)進(jìn)行重點(diǎn)剖析,確定生態(tài)紅線,提高對環(huán)境保護(hù)的重視,加大懲罰力度,確定重污染企業(yè)類型,加強(qiáng)企業(yè)排污管理制度。但是,企業(yè)自身的環(huán)保意識并不強(qiáng)烈,所承擔(dān)的環(huán)保責(zé)任有限,并且大部分情況下處于被動的局面。重污染企業(yè)在推動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帶來了嚴(yán)重的環(huán)境問題。本研究通過對重污染型企業(yè)進(jìn)行重點(diǎn)分析,以期挖掘企業(yè)當(dāng)前的高管特征,加強(qiáng)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以相關(guān)的理論研究為背景,針對當(dāng)前我國的法律法規(guī)提出具體的建議。
1 文獻(xiàn)綜述
1.1 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研究
關(guān)于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最早源于國外,Narver(1971)提出,環(huán)境問題和社會責(zé)任息息相關(guān),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意識到這一問題,提高對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關(guān)注程度,當(dāng)前部分學(xué)者通過對CEP的排名對企業(yè)所承擔(dān)的環(huán)境義務(wù)展開論述[1]。Spicer(1978)將環(huán)境績效評分作為自變量研究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義務(wù)承擔(dān)比例越大,企業(yè)盈利能力越高,同時(shí)環(huán)境績效評分越高,企業(yè)的系統(tǒng)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能力越強(qiáng)[2]。Li Long等(2009)研究了臺灣地區(qū)的800家民營企業(yè),將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情況進(jìn)行總結(jié),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在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的成就越大,對于環(huán)境義務(wù)履行越到位,企業(yè)的經(jīng)營績效越好[3]。國內(nèi)很多學(xué)者也針對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展開研究。例如,葛家澎、李若山(1992)從綠色會計(jì)的角度展開了研究[4]。耿建新、焦若靜(2002)選取了在滬市上市的50家重污染企業(yè),對這些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情況進(jìn)行分析[5]。張秀敏、薛宇等(2016)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政府的監(jiān)管是緊密相關(guān)的[6]。
1.2 高管特征的研究
Wowak和Hambrick(2010)在對高管特征進(jìn)行分析后認(rèn)為,高管本身所具有的優(yōu)勢和行政特征將會影響到企業(yè)的發(fā)展,高管的優(yōu)勢越多,對企業(yè)的促進(jìn)作用也就越大[7]。李華晶、張玉利(2006)以電子信息行業(yè)為研究對象,對企業(yè)績效同高管背景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分析,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高管團(tuán)隊(duì)的背景越好,在制定戰(zhàn)略決策時(shí)考慮的內(nèi)容也就越全面,對企業(yè)治理結(jié)構(gòu)的分析也就越到位,有利于企業(yè)的長遠(yuǎn)發(fā)展,也是提高企業(yè)綜合競爭實(shí)力的方式之一[8]。
1.3 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企業(yè)財(cái)務(wù)績效相關(guān)性的研究
目前,關(guān)于環(huán)境信息披露和財(cái)務(wù)績效相關(guān)性的研究結(jié)論不統(tǒng)一。Sulaiman、Theodore(2004)研究了198家美國上市公司,探索環(huán)境信息披露狀況和經(jīng)濟(jì)效益指標(biāo)的相關(guān)性,研究結(jié)果表明:環(huán)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經(jīng)濟(jì)狀況類指標(biāo)也越高[9]。Patten(2014)研究美國上市公司,也得到類似的結(jié)論[10]。Gatimbu(2016)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財(cái)務(wù)績效顯著正相關(guān)[11]。還有部分學(xué)者得到的研究結(jié)論是兩者不相關(guān)。Hassel(2005)發(fā)現(xiàn)企業(yè)履行環(huán)保責(zé)任的行為與企業(yè)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相背離,企業(yè)從事環(huán)保行為支出會增加企業(yè)的運(yùn)營成本,不利于提高企業(yè)利潤[12]。Clemens(2010)通過對215家上市企業(yè)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研究結(jié)果表明:環(huán)境信息披露水平與財(cái)務(wù)績效之間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13]。Bahari(2016)認(rèn)為企業(yè)履行環(huán)境義務(wù)時(shí)會帶來環(huán)境成本的增加,得出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財(cái)務(wù)績效負(fù)相關(guān)的結(jié)論[14]。蔡飛君、柴小鶯(2017)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財(cái)務(wù)績效是正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部分學(xué)者所得到的研究結(jié)果為負(fù)相關(guān)[15]。常凱(2015)以我國湖南省重污染企業(yè)為研究對象,研究發(fā)現(xiàn)重污染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越低,企業(yè)財(cái)務(wù)狀況越差[16]。隋芳芳(2012)選擇了100家深市A股重污染企業(yè)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不太相關(guān)。張亞杰(2015)選擇了2010—2014年上市的200家重污染企業(yè)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自愿披露的環(huán)境信息與財(cái)務(wù)績效不相關(guān)[17]。
當(dāng)前,大部分的學(xué)者認(rèn)為環(huán)境信息披露同財(cái)務(wù)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主要有3種,分別是正相關(guān)、負(fù)相關(guān)和不相關(guān),但是具體的關(guān)系尚未有統(tǒng)一的結(jié)論。學(xué)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財(cái)務(wù)績效影響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財(cái)務(wù)績效影響的研究文獻(xiàn)比較少。之前的研究大多數(shù)是直接研究企業(yè)管理者的特征與企業(yè)經(jīng)營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而將管理者特征作為中介變量進(jìn)行研究的比較少。本研究重點(diǎn)分析了企業(yè)環(huán)境信息披露同財(cái)務(wù)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一步確認(rèn)高管團(tuán)隊(duì)同環(huán)境信息披露和企業(yè)財(cái)務(wù)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及相互影響,以期通過本研究獲得有價(jià)值的內(nèi)容,進(jìn)而推動我國經(jīng)濟(jì)的綠色發(fā)展。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從利益相關(guān)者的理論出發(fā),政府與企業(yè)股東、企業(yè)債權(quán)人等都是企業(yè)的利益相關(guān)者,企業(yè)的利益與政府息息相關(guān),政府出臺的優(yōu)惠政策或補(bǔ)貼政策會直接影響企業(yè)的收益,企業(yè)在經(jīng)營過程中也應(yīng)該遵循政府的規(guī)定,主動披露企業(yè)相關(guān)信息。企業(yè)為了保證正常的經(jīng)營活動,則需要充足的資金。企業(yè)用于經(jīng)營活動的大部分資金,都是由這些人提供的。對于企業(yè)來說,獲得越多的投資,則有利于提高企業(yè)在市場中的競爭實(shí)力,進(jìn)一步提高企業(yè)的經(jīng)營效益。同時(shí),要進(jìn)一步提高企業(yè)資金流入到環(huán)保中,才能更容易獲得企業(yè)的股東和債權(quán)人的投資,推動企業(yè)的可持續(xù)化發(fā)展。本研究將從利益相關(guān)者的角度出發(fā),為了進(jìn)一步實(shí)現(xiàn)企業(yè)的經(jīng)營效益和目標(biāo),獲得更加長遠(yuǎn)的發(fā)展,企業(yè)需要將保護(hù)環(huán)境放在發(fā)展戰(zhàn)略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并努力提高環(huán)境治理水平。同時(shí),企業(yè)要主動披露。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在重污染行業(yè)的上市公司中,環(huán)境信息披露和企業(yè)財(cái)務(wù)績效正相關(guān)。
高管的一個(gè)特征就是年齡。受到年齡因素的影響,不同的高管具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其管理水平和管理經(jīng)驗(yàn)也有所不同,也會具有不同的思考方式。隨著年齡的變化,企業(yè)的高管更希望能夠提高企業(yè)的效益和聲譽(yù),并通過該種方式進(jìn)一步提高高管自身的聲譽(yù),實(shí)現(xiàn)他們對自我價(jià)值的追求。一方面,高管面臨著企業(yè)內(nèi)部同事的壓力;另一方面,高管承擔(dān)著外部環(huán)境治理的壓力。因此,高管會將環(huán)境治理作為企業(yè)經(jīng)營發(fā)展的責(zé)任。一旦企業(yè)具有破壞環(huán)境的行為,會使企業(yè)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形象崩塌,給企業(yè)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高管的年齡在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財(cái)務(wù)績效的關(guān)系中存在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
近年來,我國對環(huán)境保護(hù)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提出了企業(yè)發(fā)展不能以破壞環(huán)境作為代價(jià)。國家近年來發(fā)布的一系列環(huán)境保護(hù)政策都是希望能夠提高我國企業(yè)的環(huán)保意識,在經(jīng)營活動中主動承擔(dān)起環(huán)境保護(hù)的重要責(zé)任。對于企業(yè)高管來說,他們是企業(yè)和政府之間的重要聯(lián)系人,也是企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認(rèn)為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對企業(yè)績效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更可能提前知曉國家政策發(fā)展動態(tài),對企業(yè)發(fā)展產(chǎn)生有利的影響。綜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3:高管政治背景在環(huán)境信息披露和財(cái)務(wù)績效的關(guān)系起到正向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3 研究設(shè)計(jì)
3.1 數(shù)據(jù)來源
本研究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泰安數(shù)據(jù)庫。研究的樣本選取2010—2019年的A股市場污染比較嚴(yán)重的上市企業(yè),樣本中去掉沒有環(huán)境披露的企業(yè)和沒有社會責(zé)任報(bào)告的企業(yè),去掉ST企業(yè),去掉缺失和數(shù)據(jù)比較極端的企業(yè)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數(shù)據(jù)為573份。
3.2 變量設(shè)定
3.2.1 企業(yè)績效(ROA)
根據(jù)前人的研究得出,目前對企業(yè)績效的測量指標(biāo)主要有總資產(chǎn)收益率(ROA)、凈資產(chǎn)收益率(ROE)、托賓Q值、每股收益等。資產(chǎn)收益率(ROA)代表的是凈利潤與總資產(chǎn)的比值,反映的是企業(yè)整體盈利能力。凈資產(chǎn)收益率(ROE)表示的是凈利潤與凈資產(chǎn)的比值,可以反映企業(yè)投資資本的獲利能力,但是這個(gè)指標(biāo)易被企業(yè)管理者操縱。因此,本研究選擇總資產(chǎn)收益率為企業(yè)績效指標(biāo)。
3.2.2 環(huán)境信息披露(EID)
本研究根據(jù)上海證券交易所發(fā)布的《上市公司環(huán)境信息披露指南》中,總結(jié)10個(gè)有關(guān)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評價(jià)指標(biāo)。其中,如果沒有相關(guān)指標(biāo)披露的評為0,簡單披露的評為1,大致披露的評為2,詳細(xì)披露的評為3,分別對每個(gè)企業(yè)進(jìn)行打分評價(jià),最終加總得到企業(yè)關(guān)于環(huán)境披露的綜合評價(jià)EID值。相關(guān)評價(jià)指標(biāo)見表1。

表1 相關(guān)評價(jià)指標(biāo)
3.2.3 高管政治背景(PC)
根據(jù)公司的高管董事中的是否有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或者在各級政府部門任職經(jīng)歷判斷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其中有政治背景編碼為1,沒有政治背景編碼0。
3.2.4 高管年齡(AGE)
本研究以管理層的平均年齡衡量企業(yè)家精神,其中管理者平均年齡小于45歲的編碼為1,45~50歲的編碼為2,50~55歲的編碼為3,55歲以上編碼為4。
3.2.5 控制變量
企業(yè)績效除了可能受上述因素影響,還受到自身發(fā)展情況和宏觀環(huán)境的影響,因此選擇股權(quán)集中度(TOP1)、公司成長機(jī)會(GROW)、企業(yè)年齡(CAGE)和企業(yè)所在地區(qū)(EARA)作為控制變量。股權(quán)集中度由2017—2018年度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表示;公司成長性由2017—2018年度主營業(yè)務(wù)收入增長率表示,企業(yè)年齡以注冊日開始算,企業(yè)所在地區(qū)根據(jù)企業(yè)注冊地區(qū)和四大經(jīng)濟(jì)區(qū)對企業(yè)所在地區(qū)進(jìn)行編碼,將中國東部地區(qū)編碼1,中國中部地區(qū)編碼2,中國西部地區(qū)編碼3,東北地區(qū)編碼4。
3.3 模型構(gòu)建
3.3.1 環(huán)境披露與企業(yè)績效
研究環(huán)境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情況,要以企業(yè)績效(ROA)為被解釋變量,以環(huán)境披露指標(biāo)(EID)為解釋變量,以股權(quán)集中度(TOP1)、公司成長機(jī)會(GROW)、企業(yè)所在地區(qū)(EARA)、企業(yè)年齡(CAGE)為控制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多元回歸模型如下。

3.3.2 高管特征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為了進(jìn)一步分析高管特征對環(huán)境信息披露與企業(yè)績效的影響,分別選擇高管平均年齡(AGE)和高管政治背景(PC)構(gòu)建如下調(diào)節(jié)模型。

4 實(shí)證分析
4.1 描述性統(tǒng)計(jì)分析
下面對得到的被解釋變量指標(biāo)(企業(yè)績效ROA),自變量指標(biāo)[環(huán)境披露指標(biāo)(EID)、調(diào)節(jié)變量(高管政治背景(PC)、高管年齡(AGE)],控制變量指標(biāo)[股權(quán)集中度(TOP1)、企業(yè)成長機(jī)會(GROW)、企業(yè)年齡(CAGE)、企業(yè)所在區(qū)域(EARA)]進(jìn)行描述性統(tǒng)計(jì)分析,對各個(gè)指標(biāo)的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標(biāo)準(zhǔn)偏差、偏度和峰度進(jìn)行分析。
從表2可以看出,企業(yè)績效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比較大,企業(yè)的平均凈資產(chǎn)收益率為3.84%,環(huán)境信息披露情況平均值為13.87,企業(yè)高管絕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高管的平均年齡大于50歲,股權(quán)集中度平均值在31%左右,樣本企業(yè)的收入增長率偏低,平均值處于0.16%。

表2 描述性統(tǒng)計(jì)分析
4.2 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
模型回歸結(jié)果見表3。其中,模型1為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模型,模型2為以高管董事任職政治背景為調(diào)節(jié)變量情況下,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模型,模型3為以高管年齡為調(diào)節(jié)變量下,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模型。

表3 回歸模型
模型1中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信息披露正向影響企業(yè)績效,而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環(huán)境信息披露(EID)每增加1%,則企業(yè)績效可提升0.515%。說明環(huán)境信息披露得分越高時(shí),會進(jìn)一步促進(jìn)企業(yè)的績效水平的提升,假設(shè)1得到證實(shí)。股權(quán)集中度也會正向促進(jìn)企業(yè)績效水平的提升,而企業(yè)所在區(qū)域、成長機(jī)會和企業(yè)年齡則影響不顯著。
模型2中發(fā)現(xiàn),當(dāng)加入高管政治背景作為調(diào)節(jié)變量時(shí),環(huán)境信息披露依然對企業(yè)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當(dāng)環(huán)境信息披露得分越高時(shí),會進(jìn)一步提升企業(yè)的績效水平。同時(shí),高管政治背景與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交叉項(xiàng)的系數(shù)也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高管任職時(shí)的政治背景可以有效促進(jìn)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主要原因可能是高管也負(fù)有一定的政治任務(wù),前面的假設(shè)3得到驗(yàn)證。
模型3中發(fā)現(xiàn),當(dāng)加入高管年齡為調(diào)節(jié)變量時(shí),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有正向促進(jìn)作用,而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當(dāng)環(huán)境信息披露得分越高時(shí),會進(jìn)一步提升企業(yè)的績效水平。同時(shí),高管年齡(AGE)與環(huán)境信息披露的交叉項(xiàng)的系數(shù)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高管平均年齡越大,越能促進(jìn)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正向影響;隨著高管的年齡越大,企業(yè)的績效水平越高,前面的假設(shè)2得到證實(shí)。
5 結(jié)論與建議
本研究分析了污染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信息披露、高管特征與企業(yè)財(cái)務(wù)績效的關(guān)系,選取2010—2019年的A股市場污染比較嚴(yán)重的573家上市企業(yè),將企業(yè)績效作為被解釋變量,將環(huán)境信息披露作為解釋變量,將高管特征作為調(diào)節(jié)變量,將股權(quán)集中度、公司成長機(jī)會、企業(yè)所在地區(qū)和企業(yè)年齡作為控制變量展開研究。研究發(fā)現(xiàn),企業(yè)績效與環(huán)境披露指標(biāo)具有顯著性的正向相關(guān)性,說明環(huán)境披露指標(biāo)得分越高,企業(yè)績效水平越高;企業(yè)高管政治背景和高管年齡都有效提升了環(huán)境信息披露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效果。
基于上述結(jié)論,提出以下幾點(diǎn)建議:第一,建立一套科學(xué)完善的披露管理機(jī)制,提高對環(huán)境問題的監(jiān)察力度。以法律的手段規(guī)范企業(yè)的發(fā)展,保證環(huán)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正常實(shí)施,重視環(huán)境問題比較嚴(yán)重的企業(yè),嚴(yán)查嚴(yán)打這類型企業(yè)的環(huán)境問題。第二,加強(qiáng)人力資源管理,合理優(yōu)化高管團(tuán)隊(duì)結(jié)構(gòu)。企業(yè)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管的影響,高管團(tuán)隊(duì)的綜合素質(zhì)和能力越高,對環(huán)境問題重視程度也就越高,當(dāng)前我國正朝著資源節(jié)約型的方向發(fā)展,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優(yōu)化高管團(tuán)隊(duì)的建設(shè),使其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fā)展,合理地對高管團(tuán)隊(duì)進(jìn)行調(diào)整,進(jìn)而推動企業(yè)的全面發(fā)展,提高企業(yè)的環(huán)保能力和經(jīng)濟(j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