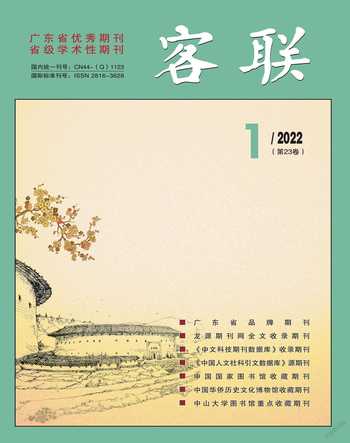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規制
張雨
摘 要:《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以來,家庭暴力構成違法犯罪的觀念逐漸得到人們認可,不再簡單的將其認為是家庭私事,特別是《民法典》的實施明確了禁止家庭暴力,強化了公民的人格權保護。基于家庭暴力關系不對等性、暴力循環性、隱蔽性、持續性的特點,長期以來家庭暴力在罪名適用、自訴模式上存在一些爭議,文章從多個方面對家庭暴力犯罪行為提出刑法規制建議。
關鍵詞:家庭暴力;特征;爭議;刑法規制
一、家庭暴力的特點
家庭暴力相較于其他暴力類型主要區別在于它是發生在家庭親密關系中的暴力,基于此,家庭暴力的特征具有了關系不對等性、暴力循環性、隱蔽性、持續性等特征。
具體來講,家庭暴力的發生表現為家庭關系的一種博弈,通常是家庭中經濟、健康等占優的成員對其他家庭成員施加的暴力,故具有關系不對等性;根據學者曲木玥者(2021)的觀點認為,家庭暴力全階段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憤怒積蓄期,暴力出現期,誠心道歉期和親密互動期,在此之后通常會因為溝通不當等原因,又在矛盾沖突的積累中循環進入下一個憤怒積蓄期,故具有暴力循環性的特征 [1];從功能性上來看,家庭具備私密性特征,實踐中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成員往往基于多種因素往往選擇容忍或者縱容,導致家庭暴力具有隱蔽性和持續性。
二、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律爭議
首先是對家庭成員施暴在罪名確定上的爭議。當前,我國對家庭成員施暴在罪名確定上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兩者在家庭暴力層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主體為家庭成員,主觀上為故意,侵害的客體為人身權利,客觀上都實施了暴力行為等。但是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分屬兩種不同罪名,構成要件存在差異,且處理結果同樣存在差異。雖然說兩者在罪名設置的關注重點上不同,兩罪造成的結果也不同且主觀方面也存在一定差異,但是兩者的區別是相對的,這造成了實踐中區別兩者的難點。由于家庭暴力通常具有隱蔽性,法院在認定其是屬于虐待行為還是故意傷害行為存疑時,應當結合上述區別進行主客觀分析,同時我們也應當積極思考虐待罪的入罪標準是否需要再進一步細化,對兩者的界限進行明確區分,防止家庭暴力施暴者逃避法律的制裁。
其次是自訴模式的適用存在爭議。刑事自訴模式是公權力讓渡私權利的體現,也是刑法謙抑原則的具體體現。這種訴訟模式多適用于一些輕微的、針對公民個人權益的犯罪,單純對虐待罪而言并無不可。但是,家庭暴力犯罪對被害人人身權利的侵害程度不亞于一般性的暴力犯罪,有時甚至更為嚴重,因此,單純依靠自訴模式顯然是不完善的。如果未能在犯罪初期就對行為人加以規制,則在日后一貫性、長期性的虐待行為中,往往會惡性升級,給被害人、家庭都帶來更大的傷痛,故需要尋求多元化的處理途徑。
三、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規制
(一)采取單行刑法立法模式
首先,我國目前家庭暴力犯罪的研究討論與司法處理還在起步階段,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都需要跟據現實狀況的變化進行更新,結合家庭暴力司法實踐來看,在家庭暴力發生以后,如果受暴者保持緘默,則外界知曉便會滯后。由于單行刑法立法模式的靈活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家庭暴力隱蔽性的缺點。
其次,刑法典具有穩定性與權威性,我國現行刑法實施的時間并不長,并且我國家庭暴力犯罪的研究并不完備,貿然將家庭暴力犯罪統一規定在刑法中,由于時機并不成熟,無法取得較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單行刑法與刑法典并不重合,而是起到補充作用,基于此,在家庭暴力犯罪的規制上,制定單行刑法是確實具有可操作性的。
(二)注重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訴訟模式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于暴力的產生往往源于家庭關系的不對等性,很多情況下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者迫于施暴者的恐嚇威脅不敢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基于輿論壓力,顧及自身顏面等原因不愿提起訴訟。同時,提起自訴的門檻過高,受害人常常無法達到法院提出的證據要求,造成的結果便是勸其撤訴或者不予立案。對通常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而言,更理性的選擇是在自訴為主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公訴制度,建立起“以自訴為主,以公訴為輔”的訴訟模式。但是對于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依然具有存在的可能性,比如實施情節惡劣、手段殘忍的虐待行為,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實施侮辱、誹謗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國家利益等。這些行為不僅侵犯了家庭成員的人身和財產權益,更危及到了社會秩序,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此時,應當由公安司法機關介入提起公訴。
(三)適當調整法定刑的種類與幅度
基于法定刑的種類而言,部分罪責設置過重,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最低刑為6個月以上拘役顯然不合理,不但無助于環節家庭關系,可能會引發更加惡劣后果。可考慮管制最低刑,不予關押而限制行為人一定自由的刑罰,能夠在監獄外對行為人予以懲罰,不至于進一步惡化家庭關系、激發矛盾,同時不會明顯影響家庭收入。
就法定刑幅度而言,存在部分危害行為與量刑幅度不匹配的情況。在面對同樣危及家庭成員的行為甚至是更嚴重的危害行為時,卻反而配置更加輕緩的量刑幅度,這無疑削弱了刑法的威懾功能。對此,只能提高遺棄罪的量刑幅度,實現刑罰配置均衡,才能實現其預防功能。同時,應當對家庭暴力常見的三種罪名均配置管制刑,為較為輕微的家庭暴力犯罪留出余地。
(四)明確虐待罪入罪標準
我國現行刑法分則的規定中對虐待罪的定罪尺度較為模糊,筆者認為應對其予以明確。首先,確虐待罪中規定的“情節惡劣”這一入罪要素的具體要求。不管是從行為手段、持續時間或是傷害結果等哪一方面進行界定,應對情節惡劣做出具體解釋。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中這樣說到:長達半年、隔三差五的施虐行徑,應當被認定為“情節惡劣”。對此,筆者認為,在進行司法解釋時,應規定出具體、明確、客觀的標準,運用精準的法律表述來規避日常生活用語在司法實踐中的漏洞,從而降低隨意裁量的可能性。其次,虐待罪要求將行為的經常性、一貫性作為入罪標準進行考慮,但虐待行為的具體時間及次數都沒有明確規定,這導致行為沒有具體明確的參照標準,在實踐中極有可能導致受害者在遭受侵害后無法確定是否能依照刑法追究行為人的責任,如果訴諸法院,被告人因不具有虐待罪所要求的侵害行為持續性,同時又未造成故意傷害罪的傷害結果而不予受理,那么無疑是逼迫受害人放棄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將其置身于更加危險的家庭暴力環境內。
(五)明確從寬處理考量要素
對于家庭暴力犯罪,在適用從寬處理時,應依照案件具體分析。首先,從量刑的預防根據考察,就再犯可能性而言,在以暴制暴案件中,由于反抗者已經使用自力救濟的措施懲罰了具有不當行為的被害人,犯罪目的基本已達到,其再次實施犯罪行為,侵害其他無關人員的可能性并不大,基于此認為其再犯的可能性較小,其人身危險性也相應較小。綜合考察以暴制暴案件中的情況,由于反抗者無論是主觀惡性、再犯可能性以及人身危險性都比較小,量刑時應當從寬處罰以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其次,對于反抗家庭暴力導致對施暴人造成傷害的,應根據實際情況,結合依法從寬的原則進行處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在考量具體要素時,應對事實認定、證據采信、法律適用準確,避免引起冤假錯案。
參考文獻:
[1]曲木玥者. 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規制研究[D].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21.
[2]我國家庭暴力犯罪的原因與對策研究[D]. 王方圓.安徽大學,2020
[3]家庭暴力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究[D]. 張曉嬌.山東政法學院,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