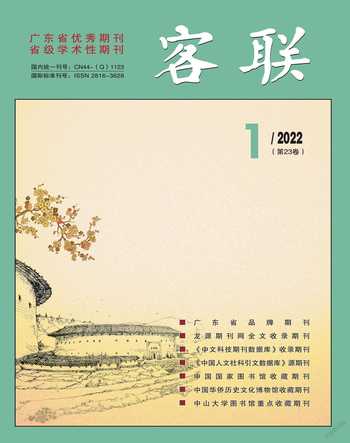從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理解國家整合
烏日偲
摘 要: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共正式放棄了“民族自決”和聯邦制而選擇了以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國家整合的制度基礎。這一決斷的做出不是由于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所具有的優越性,而是由于中共成立以來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和對中國領土觀、民族觀的認識進一步加深。
關鍵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國家整合
一、問題的提出
1947年5月1日,新中國首個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宣布成立。回顧歷史,為什么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對內蒙古地區進行進一步的國家整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憲法》規定的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如何將少數民族地區納入中國這個超級大國?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以一種實用主義的、自下而上視角回顧當時具體的歷史情況,從憲制的理論中,尋求可能的答案。
二、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成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一)近代以來內蒙古地區的民族問題
清末時期,孫中山等前革命黨人的民族政策是“排滿”,所以導致在動員人民推翻清朝統治的同時,培植了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也滋長了部分蒙古族的獨立情緒。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的思想從“排滿”逐漸轉化為強調“中華多民族統一”的思想。在袁世凱執政之后,北洋政府面臨外蒙古等各個蒙古地區“獨立”的情況,為了穩定局勢,袁世凱政府照搬了清朝全套的民族政策。1928年,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宣布熱河、察哈爾、綏遠特別行政區改為行省,推行中央集權統治,原內扎薩克6盟均劃歸不同行省。1929到1932年,民國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辦法推行蒙地放墾,進一步加劇內蒙古地區對民國政府的不滿情緒。抗日戰爭勝利后,民國政府繼續推行“以實施省制為中心的”的方針政策,盟旗與省縣的沖突在行政區劃、管轄治理方面進一步激化。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內蒙古地區的民族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內蒙古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送來了曙光。
早在1920年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要幫助蒙古、西藏、青海自治自決。i中共二大《宣言》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 ii的主張。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在內蒙古地區就建立了黨組織,提出了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政治綱領。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又領導了內蒙古的抗日救亡運動。
抗戰勝利后,內蒙古地區情況異常復雜。1945年原偽蒙疆政權中的一些官員和青年知識分子在蘇尼特右旗的德王府成立了“內蒙古人民委員會”和蒙古青年革命黨,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見此狀況,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派烏蘭夫等赴蘇尼特右旗展開工作。最終,絕大部分蒙古青年革命黨人放棄了之前自己的主張,其中大部分成員投入到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當中。
隨著自治運動的深入發展,內蒙古各族人民都在期待著實現民族自治,成立統一的自治政府。1947年5月1日,內蒙古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舉行選舉,烏蘭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同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
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內蒙古歷史上發生的具有時代意義的大事,意味著首個基于民族平等的民族政府在內蒙古得以建立,實現了內蒙古地區各族人民長久以來渴望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愿望,也證明了中共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所制定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方針是正確的,是在當時的中國可以實施的,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最終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依據。
三、中國共產黨關于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構想:從幼稚到成熟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主張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自決理論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中共二大就提出民族自決綱領。直至抗日戰爭前期,中共仍然是以“民族自決”作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團結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基本綱領。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提出了建立少數民族自治區的主張,并在《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做出了具體的規定,這是中共關于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探索過程的一個重大飛躍,為當時制定具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實踐開創了嶄新的局面。直至六屆六中全會后,“民族區域自治”成為了中共民族政策的主角。
在發動內蒙古自治運動的過程中,中共強調應成立自治政府而不是獨立政府。在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指示:“應確定內蒙古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它在內蒙古民族自治區仍屬于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 iii。
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主張是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舉行,參會代表們討論得出:中國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并沒有經過民族分離,因此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更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區域自治,對實現各民族平等的目標是更有利的。經過各民族代表的共同討論、協商,按照民族自覺的原則,確定了中國采用單一制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并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最后,本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把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正式用文字的表達方式確定下來。
四、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分析
(一)民族區域自治是最適合當時中國的選擇
站在理性主義視角分析中國的憲制問題時,往往忽略國家建立時的歷史情況,僅僅從理論上對制度進行理性設計,或是霍布斯討論的建立利維坦的集權國家,或是盧梭討論的社會契約論的民主國家兩種進路中選擇一種可能更好的更符合現代民主國家的進路。但是,需要注意到不是憲制創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創造了憲制,人民所創造的憲制會進一步影響現實政治生活的運作。國家的建立不是僅僅可以通過制度的理性設計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面對當時的約束條件進行制度的決斷。
內蒙古地區各族人民從第一次民主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實踐。這種實踐是內蒙古地區的的各族人民,渴望擺脫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各民族平等,實現在自己的領土上安全的生存,并誠懇的懷有美好生活的愿景。蒙古人民本著這種目的,投身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當中,投身到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共產黨的懷抱中,選擇建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阿克曼在《我們的民主》三部曲中,試圖指出憲法權力的最終來源:我們人民。正如阿克曼提出的美國建國時的“憲政時刻”一樣,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內蒙古人民的選擇,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一項憲制,也是由人民作出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治理的設想一直到20實際30年代后才逐步放棄民族自決和聯邦制的政策取向,主要原因是出現了一些影響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新因素,這些因素成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形成的關鍵節點。在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馬克斯·韋伯在分析卡里斯瑪領袖出現時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關鍵節點來分析某種合法性基礎的持續和斷裂。具體而言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治理設想的關鍵節點可以從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面臨的國際形勢兩個變量進行具體的分析。
1、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使得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少數民族的利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文化的中華民族意識覺醒,到從治理的領土結構發生了改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長征途中經過數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和雜居區,建立了甘孜巴博政府、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等,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停留過程中,對各個地區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增進了了解,對少數民族所面對的來自各方不平等對待的現狀有所了解,也對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反抗壓迫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這些現實情況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比較模糊的中華民族的意識。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把國家的領土分為“本部”和“疆部”,并且從“本部”和“疆部”的視野出發對各民族關系進行定位和制定民族政策,所以也就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方式解決中國邊疆少民族地區的問題。隨著中國各民進一步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本部”“疆部”的領土觀,發生了改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以“中華民族”為題,闡述了中華民族的領土和地理位置、人口及其發展過程,中國是由多民族的中華民族所共同構建的。在八路軍政治部印發的《抗日戰士政治課本》中更加明確指出“內蒙古、西藏兩個行政區域”,內蒙古、西藏不再是“疆部”而是行政區域。在抗戰時期基本上就已經放棄民族自決的聯邦制而轉向能更好的把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納入中國領土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在少數民族地區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中共對于“中華民族”的認識和中國領土治理結構的理論進一步成熟,逐步認識到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經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模糊的”中華民族演變為“分享同樣歷史的”中華民族,是真正的構建起新中國的人民;也逐步放棄了運用聯邦制將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納入中國領土的主張。
2、面臨的國際形勢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給天皇的奏折中就提出預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預稱霸世界,必先征服中國。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為實現“分而治之”的計劃,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利用古代、近代以來統治階級大漢族主義造成的民族問題和民族矛盾,煽動少數民族貴族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傀儡政權,1936年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的“高度自治運動”,通過扶植德王為首的“蒙疆聯合委員會”,企圖將內蒙古東部地區通過“民族自決”從中國分離出去。與此同時,英國也趁火打劫,在西北地區從事民族分裂的活動。“民族自決”異化為國外勢力企圖分裂中國的“遮羞布”,民族自決使得本來復雜的民族問題更加復雜。
在中共少數民族地區的實踐和國外形勢等因素的影響下,中共逐步改變了在第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初的民族自決和聯邦制的思想,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初步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思想。民族區域自治是在當時出于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保留中華民族的延續的情形下,最適合中國治理少數民族地區的制度。
(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把少數民族地區整合到中國當中,不斷把少數民族整合到中華民族當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其中的共同締造不僅僅體現在歷史文化當中,也體現在自1840年以來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歷史上的共同締造。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后的幾個政權都涉及與少數民族的聯合,特別是建立陜甘寧邊區政府后,為團結蒙古族人民進行抗日,建立的內蒙古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等。1947年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又是推翻國民黨統治,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戰爭的一部分。內蒙古地區各族人民同新中共分享同樣的歷史,這是內蒙古自治區得以成立,并且日后不斷被整合進中國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費孝通先生,把“中華民族”成長歷程分為兩個階段:自在存在與發展的階段與自覺存在與發展的階段。然而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狀態的轉變過程中,不是民族間的交往自我有序的發展,而是“自在”狀態下“中華民族”整體面臨生存與發展危機的結果。正是近代以來,動蕩不安的中國,漢族同個少數民族共同反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不斷重塑中華民族的狀態,也真正意義上將少數民族不斷整合到中華民族當中。
五、結語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研究中以一種“問題化”的方式展開他的研究。這并非一種“歷史主義還原”,而是重新書寫一種歷史。福柯試圖從制度中抽取出權力關系,對它們進行技術分析;從功能中抽取權力關系,對它們進行策略分析;還要抽取出比對象更優先的權力關系,并把對它們加以分析的視角重新置入知識領域和范疇的建構之中。本文正是以問題化的方式,而非進行制度的規范研究,展開了對建國前為何選擇民族區域自治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治理的研究。受到當時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中共反帝反封建革命進程和國外勢力多重影響,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延續和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
當下,全球民族分離主義的復興和民族分離活動高漲提醒我們,需要以一種實用主義的視角,對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行抽象的功能主義分析,再把這種分析重新還原到當下的制度構建當中,不斷實現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國的進一步整合。
注釋:
i 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ii 參見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iii 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內蒙古自治問題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1034頁。
參考文獻:
[1]白拉都格其.略談共產國際與內蒙古革命[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8(05):28-32+52.
[2]朝魯孟. 自治與革命: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歷史研究(1917—1947)[D].內蒙古大學,2017.
[3]崔月琴,王嘉淵.以治理為名:福柯治理理論的社會轉向及當代啟示[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2):58-67.
[4]戴小明:《中國民族區域自治的憲政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1
[5]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載《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第1頁。
[6] 郝維民:《內蒙古革命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86-586頁。
[7]何俊志等編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頁
[8]黃光學.談談我國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J].法學研究,1959(04):42-46.
[9]加里·古廷:《福柯》,王育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10]焦洪昌:《憲法制度與法治政府》,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1
[11]金炳鎬、王鐵志主編:《中國共產黨民族綱領政策通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526頁。
[12]康玉梅.“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民教育與國家認同[J].環球法律評論,2018,40(02):165-177.
[13]李辰.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其在內蒙古的實踐[D].中共中央黨校,2019.
[14]李玉偉. 內蒙古實現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與實踐[D].內蒙古大學,2004.
[15]列寧:《論民族自決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列寧論民族問題》,第311-312頁。
[16]林苗.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內蒙古經驗[D].中共中央黨校,2018.
[17]劉鳳健:《民族區域自治理論與實踐研究:兼論李維漢對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貢獻》,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庫(答辯時間:1999年5月),第32-33頁。
[18]劉晗.民主共和與國家統一:美國早期憲政中的北方分離運動[J].環球法律評論,2011,33(06):110-123.
[19]呂永紅:《民族、國家與制度---歷史制度視域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 2014年5月 ,第173頁。
[20]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第102頁。
[21]史筠:《民族法治研究》,第87-88頁。
[22]田雷.第二代憲法問題——如何講述美國早期憲政史[J].環球法律評論,2014,36(06):96-120.
[23]王克,張英達.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J].法學研究,1958(0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