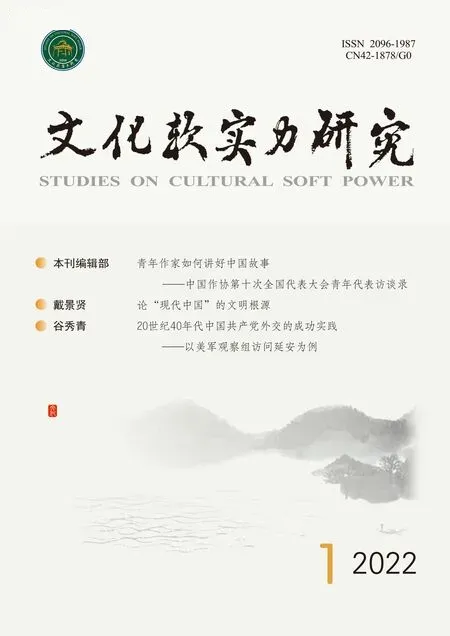傅抱石作品中的長江文化與時代精神
閆彬彬
(中國藝術研究院 藝術與文獻館,北京 100029)
長江連同黃河一起,哺育著中華民族,孕育了中華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品格,厚植著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長江是文藝創作的永恒主題,一大批美術家感嘆于長江自然景觀,感悟于長江文化精神,刻畫一批長江主題美術作品。傅抱石在建國前后創作了一批以長江文化為題材的美術作品,包括屈原和屈原賦題材創作、《九歌》圖冊創作以及毛澤東長江題材詩詞主題創作等。本文試圖考察研究傅抱石的相關創作,在文化強國建設成為國家戰略的當下,為新時代長江主題美術創作乃至文化事業繁榮發展提供有益資鑒。
一、其命維新:傅抱石生平及其長江主題創作背景
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長生、瑞麟,號抱石齋主人。生于江西南昌,是“新山水畫”代表畫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執教于中央大學。建國后曾任南京師范學院教授、江蘇國畫院院長等職。他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新風、描繪祖國山川巨變的水墨畫作品,這些作品及其繪畫思想成為今天研究二十世紀美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傅抱石擅畫山水,筆致放逸,氣勢豪放,尤擅作泉瀑雨霧之景;晚年多作大幅,氣魄雄健,具有強烈的時代感;人物畫多作仕女、高士,形象高古。著有《中國古代繪畫之研究》《中國繪畫變遷史綱》等。他創造了散鋒用筆連皴帶擦的新穎技法,被稱為“抱石皴”,這是山水畫技法的一種。著名畫家張安治評價其畫:“一大片一大片的水墨,簡直是西洋印象畫派以后的作風;畫山石的皴法亦前無古人。隨意縱橫,信筆點染,確已做到物我兩忘,離形去智的超然境地。”[1]
傅抱石發展了石濤的“筆墨當隨時代”論,向同時代畫家提出“思想變了,筆墨不能不變”的口號:“筆墨技法,不僅僅源自生活并服從于一定的主題內容,同時他又是時代的脈搏和作者的思想、情感的反映。……由于時代變了,生活感情也跟著變了,通過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筆墨技法的基礎之上,大膽地賦予以新的生命,大膽的尋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們的筆墨能夠有力地表達對新的時代、新的生活的歌頌與熱愛。換句話,就是不能不要求變。”[2]早在40年代,傅抱石就提出了中國畫的三原則:超然性、民族性、寫意性。他認為這是中國畫的基本精神。在對新的技法、意境、創作內容的探索中,傅抱石一直在探索如何用水墨來表現重大革命實踐、經濟社會發展等全新的領域,他作了許多深刻的思考:“當畫家們深入到生活里面,面對著今天日新又新、氣象萬千的現實生活,能夠無動于衷、沒有絲毫的感受?不能,這是絕對不會的,也是不合常情的。我認為,畫家的這種激動和感受,就是畫家對現實生活所表示的熱情和態度,對現實生活的評價。另一面也是畫家賴以創作,賴以大做‘文章’,大顯身手的無限契機。我們知道,每一個人的素養、興趣、愛好乃至筆墨基礎都是不同的,所以每個人的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和評價也各有差別,正因為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擅長和每個人的創造力量。”[3]傅抱石在探索中不斷尋找新的表現形式,使新中國畫有了鮮明的新時代特色,亦有闊大、深遠的意境。
傅抱石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使他在20世紀40年代創作了大量的以楚辭為題材的作品,建國后創作的《九歌》圖冊則又有了新時代的昂揚歡快之風。他亦投入巨大的熱情和思考來嘗試中國畫的新發展,為衰敗的中國畫尋找新的出路。他探索的毛澤東詩意畫已成為時代的旗幟,一道永恒的風景。而在當今建設文化強國的大環境下,傅抱石對中國畫的新探索,賦予時代新的含義,尤其是其以長江文化為主題的創作,更是在湖北文化的發展中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二、以屈原和屈賦題材的長江文化主題創作
(一)19世紀40年代以屈子和屈賦為主題的繪畫
屈原,楚國丹陽秭歸人(今湖北宜昌),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后,自沉于江,以身殉楚國。屈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被譽為“楚辭之祖”的屈原可以說是長江文化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宋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講到屈原賦中的《九歌》:“故事圖貝闕珠宮、乘黿逐魚,亦可施于繪素,后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4]因其飽含著作者的思想感情與豐富的想象,語言凝練而形象性強,具有鮮明的節奏,和諧的音韻,故是適合入畫的,且格調應為“清致”。歷來備受畫家的青睞,宋代的馬和之、李公麟,明代的蕭云從、陳洪綬,清代的門應兆、丁觀鵬等畫家都以《九歌》為主題創作了格調高雅的作品。
“五四”運動之后是一個思想觀念大變革的時代,藝術家一方面接觸了西方文化,多去海外學習新的藝術形式。另一方面,他們心中的家國情懷,也使他們在藝術創作中有了獨特的表達。而屈原的高尚人格情操以及悲壯的愛國情懷,讓他們在屈賦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鳴。1938年《新民報》刊載的徐悲鴻《西江漂流日記》中提到:“當筑一堂,臨于江湖之上,廣植修篁叢桂,開蘭成徑,令有數十里之香,堂壁繪《九歌》,中繪屈子,以空靈之筆,為隱艷之采。寫其幽思逸響,當成人生另一種境界。國危如縷系,有此玄想,亦可悲也!”[5]這亦是當時愛國藝術家憂國憂民的的真實寫照。
傅抱石原名長生、瑞麟,出于對屈原抱石投江以死赴國難之精神的敬仰,十七歲時改名抱石,取自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之“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生活的戰國正值劇烈動蕩的時代,楚國由于受到秦國的壓迫,疆土不斷東移,導致楚國的都城和楚國貴族的食邑也一再變化,而屈原一生,更是讓處于不斷的顛沛流離中、有著同樣遭遇的傅抱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而屈賦中的浪漫主義情懷又與其追求的藝術境界一脈相承,這也不難理解傅抱石創作了大量楚辭為題材作品屈原像、《九歌》題材繪畫,甚至鈐印也多刻屈賦,如《漁父》《離騷》等全文都被刻在鈐印的邊款上,印證了傅抱石對屈原以及其作品的鐘愛。

圖1 傅抱石《屈子行吟圖》(私人藏)
另一方面,1942年,郭沫若于重慶創作歷史劇《屈原》,表達對當時時局的不滿,傅抱石亦作為回應,開始了以屈原像與屈賦為主題的創作。傅抱石創作屈原像多幅,其中1942年7月完成的《屈子行吟圖》畫屈原行吟于江濱將投江之情景,滄浪之水,煙波浩渺,屈原長發披散,顏色憔悴行走在散亂搖曳的蘆蕩中,氣氛尤為感傷和悲壯。郭沫若題詩曰:“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三戶可亡秦,奈何不奮起?吁嗟懷與襄,父子皆萎靡。有國半華夏,篳路皆經紀……中國決不亡,屈子芳無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 顯然,不管是畫作還是郭沫若題詩,與屈原此時的心境都是相同的:“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6]36
(二)建國后創作的《九歌》圖冊對屈賦的全新詮釋
《九歌》圖冊為傅抱石解放后五十年代所作,于1954年寫給郭沫若信中,詳細講到了郭沫若對屈賦的研究,并講明其在郭沫若研究的基礎上來作畫:“竊以為公之《今譯》是一、二千年來劃時代的再創造。數月來除研究工作之外,創作方面為《九歌》之經營,系以我公譯文(《屈原賦今譯》)為主——從形象表現,唯公譯最好設計構圖——已完成七幅。”[7]在此將《九歌》圖冊畫作和題款與屈原《九歌》原文相較,分析其畫作中所表達的思想情感和藝術特色。
其一,《東皇太乙》,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款識:“拿起鼓槌打起鼓,徐徐歌唱慢慢舞。鼓瑟吹笙聲悠揚,美貌妖嬈,衣裳楚楚。香啊香,香滿堂。滿堂樂器會宮商,你高興,我們喜洋洋。抱石寫東皇太乙。” 鈐印:朱文圓印“傅”、白文方印“抱石之印”、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
東皇太乙,即太一,是戰國時期楚國百姓信仰和祭祀的天神。《九歌·東皇太一》是屈原對“東皇太一”的頌歌,是屈賦中最為隆重、莊肅的一篇,其詩自始至終只是對祭禮儀式和祭神場面的描述。傅抱石所作東皇太一“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6]44,正從云端向香煙繚繞、云氣縹緲的祭祀場所而來。此幅畫作所繪云層次和立體感較強,下面的云層上,有六名樂師在演奏箜篌、拍板等樂器,旁有兩名仙子在翩翩起舞,所用為高古游絲描的筆法。這種歌舞樂器演奏在古代雅集圖中較為常見。《楚辭·九歌》所描繪的祭祀場面氣氛隆重、熱烈、莊嚴、肅穆、歡快:“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揚袍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6]44-45傅抱石畫作較為符合此種情境,更顯活潑和歡快,其題款“你高興,我們喜洋洋”,用較為現代的俗語打破了嚴肅的氣氛。
其二,《云中君》,中國美術館藏。款識:云神放輝光,比賽得太陰和太陽。坐在龍車上,身穿著五彩的衣裳。她要往空中翱翔,游覽四方。抱石寫云中君。鈐印:朱白文方印“抱石父”、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朱文方印“其命維新”。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歌舞辭,以主祭的巫同云神對唱的形式,來頌揚云神,表現對云神的思慕之情。傅抱石所繪云神高古典雅,“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6]46,她在云海中駕著飛馳的龍車,所到之處霞光萬丈,在這動態極強的畫面中,她顯得安靜從容。傅抱石此幅畫作云海散鋒用筆連皴帶擦,是典型的抱石皴。云用濃墨皴擦,有排山倒海之勢,與霞光相互映照,更能凸顯云神“與日月兮齊光”[6]46的場景。而屈賦原文“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6]47等傷感情緒,傅抱石并未表現,其款識“她要往空中翱翔,游覽四方”,是輕盈而歡快的。

圖2 傅抱石《湘君》(中國美術館藏)
其三,《湘君》,中國美術館藏。題識:我望著老遠老遠的岑陽,讓我的魂靈,飛過大江。魂靈飛去路太長,妹妹憂愁,更為我悲傷。抱石寫湘君。鈐印:朱文方印“傅”、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6]48-49屈原詩中的哀愁和愛恨是非常強烈和決絕的,傅抱石畫作中,湘君立于江邊,手執象征愛情的方若,有著淡淡的憂愁,倒更有“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之境。
其四《湘夫人》,中國美術館藏。款識:公主們來到這偏僻的島上,望眼欲穿,繞著愁腸。草木搖落秋風涼,洞庭湖中起著波浪。抱石寫湘夫人。鈐印:朱文圓印“傅”、白文長方印“抱石”、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朱文方印“新諭”。
《湘君》畫作體現了傅抱石“畫岸不畫水”的思想,是嫻靜的美;而《湘夫人》描繪的則是動態的湖水她仿佛立于水上,秋風吹過,水面泛起陣陣漣漪,大片的花瓣飄落,湘夫人憂愁滿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6]51-52傅抱石在題款中用到了“公主們”,打破了這種憂愁的情緒,使畫面活潑起來。《湘夫人》是傅抱石最為鐘愛的題材,亦多作于扇面,所作意境與場景皆似。
其五,《大司命》,中國美術館藏。題識:“天門大打開,乘著烏云出來。叫狂風在前面開道,叫暴雨為我打掃。云中君你已旋回著飛往下界,我要翻過空桑跟著你來。九洲四海不少的男人和女人,是我掌握著他們的壽命。抱石寫大司命。”鈐印:白文方印“抱石之印”、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
“何壽夭兮在予”[6]55,王夫之《楚辭通釋》說:“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曰少;大,則統攝之辭也。”[8]傅抱石此作為其最為擅長的畫雨技法,使人感受到雨的速度和力量。其所作大司命為意氣風發的男子,他以龍為馬,以云為車,命旋風在前開路,讓暴雨澄清曠宇,儼然主宰一切的天帝。而屈賦的基調是內斂沉靜的,并有著幾分愁腸:“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何為。”[6]56
其六,《少司命》,中國美術館藏。題識:“荷花衫子蕙花帶,你忽然去,忽然又來。你晚上睡在天宮,在云端為誰等待。抱石寫少司命。”鈐印:朱文方印“傅”、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朱文長方印“往往醉后”。
“少司命”是主管人間子嗣與愛戀的神,她美麗、善良、溫柔、圣潔。畫中少司命乘著云,“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6]57。她從天宮里來,她的衣裙和長發隨風飛舞,“在云端為誰等待”。
其七,《東君》,中國美術館藏。題識:“青云袍子白霓裳,手挽長箭射天狼。我拿著雕弓往西降,舉起北斗舀酒漿,酒中桂花香。我抓緊轡頭在天上,迷迷茫茫又跑向東方。抱石寫東君。”鈐印:白文回文印“傅抱石印”、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
畫中東君“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6]60遠處河面上太陽升起,照亮的天際,為“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之意。而屈賦中“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6]59,情緒低沉反復惦念的傷感情緒在此畫中并未表現。
其八,《河伯》,中國美術館藏。題識:“和你一道游九河,沖起大風破大波。龍車水上浮,荷花車蓋罩當頭。有角龍,兩條青。無角龍,兩條白。龍車飛上昆侖山,眺望那東西南北。抱石寫河伯。”鈐印:朱文方印“傅”、朱文“一九五四”。
此幅圖是較為生動的一幅,龍車行于水上,旁有一只鴨子水中游。用一把荷葉當傘,河伯與美麗的女子深情相望。此圖與原詩最為契合:“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悟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游兮河之渚,流凘紛兮將來下。與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6]60-61
其九,《山鬼》,中國美術館藏。題識:“有個女子在山崖,薜荔衫子菟絲帶。眼含秋波露微笑,性情溫柔真可愛。抱石寫山鬼。”鈐印:朱文長方印“傅”、朱文長方印“一九五四”、朱文長方印“其命維新”。
畫中及題詞重在表現美麗女子溫柔的性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畫中亦有其“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的場景,而“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6]62-64的情緒并未表現。
其十,《國殤》,南京博物院藏。題識:“真有力量又有勇,剛強絕頂誰能動?身子雖死精神永不磨,永遠是鬼中的英雄!寫《國瘍》。右《九歌》十幀,乃據郭沫若先生《屈原賦今譯》經營成圖。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傅抱石南京并記。”鈐印:朱文扁方印“抱石”、朱文長方印“往往醉后”。
畫中用一個倒地的士兵和傾倒的戰車來作尸橫遍野的戰場,一名勇士為剛強絕頂有視死如歸之態,很好表現了原文中悲愴和視死如歸的情境。“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云,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6]65-66
由此可見,傅抱石雖于40年代已開始《九歌》題材的創作,但于新時代所作的《九歌》圖冊明顯充滿了激情昂揚和較為歡快的情境。屈賦中的低沉、內斂、克制明顯減少,甚至用了許多俗語來打破悲傷的情緒,對《九歌》的新詮釋也使他的創作充滿了活力,成為新中國畫的先驅者。
三、以毛澤東詩詞為題材的長江繪畫創作
東漢時劉褒取《詩經》所作之《云漢圖》《北風圖》,開啟了詩意畫創作的先河。到宋徽宗朝以詩意畫為遴選畫士的甄試科目,詩意畫創作成為官方提倡的一種繪畫形式。在傅抱石看來,“山水畫家應該是詩人,同時要具備科學知識,但重要的是做個詩人”。1942年10月,傅抱石在壬午重慶畫展自序中表達了對詩畫關系的獨特見解:“我認為一幅畫應該像一首詩,一闕歌,或一篇美的散文。因此,寫一幅畫就應該像作一首詩,唱一闕歌,或做一篇散文。”[9]他對詩與畫關系的思考,也為他以毛澤東詩詞入畫提供了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他認為筆墨不能脫離現實,在20世紀50—60年代,他做了大量關于繪畫與政治關系的思考:
“我認為充分體現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和大躍進的形勢鼓舞下,畫家的思想上,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變化。因為有了政治做統帥,才可以揮灑自如,橫掃千軍,畫出這幅氣象雄渾而優美清新的畫來。”[10]
“我想,單純的筆墨觀點,必然導致脫離現實,脫離政治,走向‘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反動道途。……今天對國畫家來說,通過勞動鍛煉,投入生活,改造思想,爭取政治掛帥,爭取更好地為人民多畫些好作品,筆墨才可能從創作實踐中得到提高。……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群眾的幫助,‘筆墨’!‘筆墨’!我問‘您有何用處’?”[11]
毛澤東的詩詞既有浪漫主義的氣質,意境的闊大和深遠,作為領袖對現實的關注,對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宏偉藍圖的歌頌和憧憬,這與傅抱石的蓊郁淋漓、氣勢磅礴有內在的一致性,亦易生發深切的認同感。因此,傅抱石創作毛澤東詩意畫能夠有較高的成就,與兩人在內在的契合度是分不開的。
解放初期,傅抱石即開始創作毛澤東詩意畫,創作了《七律·長征》《沁園春·雪》等作品。然而,他并未停步于此,實際上他對此時毛澤東詩意畫是不甚滿意的。“記得1950年至1951年之間,我開始獨自摸索……由于沒有生活,到1953年還只是勉強完成了《強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兩幅,參加1953年第一屆全國國畫展。”[12]
“在探索中變革,在變革中探索,是傅抱石1950年代創作的主旋律。”[13]在大量的思考和實踐后,1959年傅抱石與關山月合作《江山如此多嬌》巨幅畫作,以毛澤東《沁園春·雪》(作于1936年)為意,卻也有了更多新的表達。如原詞中“須晴日”,此畫中為紅日升起。原詞中描寫北國“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此畫中遠景為北國風光,近景為江南春色。此時,傅抱石毛澤東詩意畫已經成熟,成為新時代主題創作重要的代表畫家。傅抱石結合自己的實踐,多次談到毛澤東詩意畫創作心得:“1.深刻體會作者的意,不拘于跡象,自然合拍這是最好的畫法但最難,不多見。2.其次,把全文的意思,全面畫出來,句句扣緊,而畫面與主題一致。3.其次,全文包涵太多、太雜,不易在一幅之中聯系起來。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畫其中主要的一句、一聯,或一部分的(孤立的畫一句、一聯、一部分也可以)。”[14]

圖5 傅抱石《水調歌頭·游泳》(南京博物院藏,1959年)
1956年,毛澤東在武漢橫渡長江,即興寫下一首《水調歌頭·游泳》,一經發表,聞名于世。傅抱石于1957年創作《水調歌頭·游泳》,繪毛澤東橫渡長江的情景,遠景為“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武漢長江大橋。傅抱石將遼闊的江中波浪翻涌,主席卻“勝似閑庭信步”的境界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在1959年,傅抱石又作《水調歌頭·游泳》,只用“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意,所繪的是亭亭玉立、美麗動人的少女,仰頭望著遠方,這與其擅長的仕女畫是一脈相承的。“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也常常出現在后的以長江為題材的山水畫中作為題款,或用此鈐印。
毛澤東詩詞中對長江的表達,為這片自然山水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性,是新時代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歌頌和豪情的表現。傅抱石的繪畫,則用更直觀的手法,對毛澤東詩詞作出了準確的闡釋。
1957年,江蘇省國畫院籌委會宣告成立,傅抱石任主要負責人。1960年,他組織帶領的江蘇“國畫工作團”,歷時三個月,行程兩萬三千里,進行了一次被譽為美術長征的集體寫生活動,其中,工作團順長江乘船從重慶到武漢,長江三峽的綺麗風光吸引了一行幾乎所有人的筆墨,催生了一批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長江山水畫。

圖6 傅抱石《西陵峽》(中國美術館藏)
在此次寫生途中,經過湖北,西陵峽(西起湖北省秭歸縣西的香溪口,東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關,歷史上以其航道曲折、怪石林立、灘多水急、行舟驚險而聞名)雄奇秀逸的壯闊景色,是傅抱石擅長也鐘愛的題材,他創作多幅《西陵峽》,為晚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傅抱石所作《西陵峽》“力求表現真實景物的地域特征與內在神韻,他一改過去的散鋒筆法,代之以粗獷、勁挺的筆線,順逆飛動,勾斫皴擦,線條長短互用,凌厲斜披,近似傳統荷葉、亂柴皴法而又有所創發新變”。[15]
三峽為長江上的一段雄奇壯麗的山水畫廊,傅抱石所作《三峽圖》用長卷表現,延綿不絕的山峰使江水更加險峻,把“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的長江地形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遠景和近景的山峰處理得極為巧妙,江上有小船,有李白詩歌“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之意境。傅抱石亦有《三峽行舟圖》《三峽紅葉》等氣勢磅礴的畫作。
從傅抱石的創作來看,湖北長江文化精神的浪漫奇崛,風景的雄奇秀麗,毛澤東詩詞的氣魄宏大、意境壯闊,與雄渾闊大、氣勢豪邁、意境深遠的藝術特點是不謀而合的。他的創作也為湖北長江文化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用他一生的創作證明了他的美術思想,“中國畫是可以表現現實,為新時代服務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