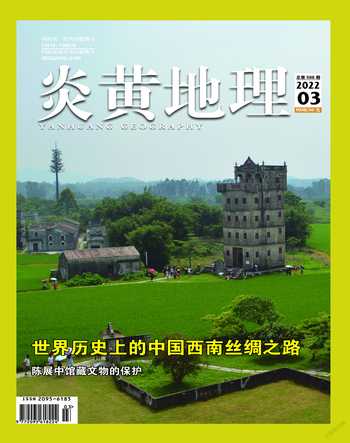絲綢之路上的中亞使者
王君如




自張騫出使西域鑿空絲綢之路東段后,直至中世紀前期即蒙古登上絲路的舞臺為止,絲路重心大部分轉移至海路。在這段歷史時期里,中亞因處于歐亞大陸東西交匯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僅成為商品貨物的匯集中轉之地,而且還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中介。從使者來往交流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古代東西方文明交往的方式和意義;由于使者的文化交往,不僅加強了中亞地區與東西方政治經濟的往來,也傳播了新思想新宗教,將絲綢之路上各個民族和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是晚近的發明,古代和中世紀生活在這些商路的人并不使用這個稱呼。直到1877年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發明“絲綢之路”這個名詞。陸上絲綢之路東起中國長安,西至原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連接著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國家。絲路上最主要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比如香料、金銀、寶石和絲綢,而絲綢作為最早和最主要的奢侈品,使得這條商路以此命名。自西漢時期張騫“鑿空”西域,標志著古代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亞歐大陸的經濟文化交流和政治軍事活動不斷延伸發展。從地理上來說,絲綢之路連接了從東方到西方沿線的所有地區,將這些地區囊括到統一的活動范圍;經濟上來說,絲綢之路作為媒介,連接著不同地區的商貿往來,互通有無;政治上,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贈送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從文化角度來說,這又是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之路。
古代中亞使者交流
中亞地區以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兩河流域作為中心即“河中地區”,該地區處于肥沃的則拉夫善河流,即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全境和哈薩克斯坦南部。中亞使者與東方、西方的對外交流,和地緣關系密不可分。帕米爾高原高聳入云,將中亞分為東部與西部,它也是古代軍事遠征難于逾越的障礙。在古代到中世紀的官方使節歷史記載中,有很多關于中亞與中國以及波斯、拜占庭的政治軍事交往。因此使者的往來會代表一個地區或者民族與另一個地區和民族的和平交往,他們往往攜帶著本國的貨物去往東方與西方,進行朝貢貿易。這種包裹著友好朝貢外衣下的使者交往,實質是一種官方的外交活動,還促進了物質文化的交流。正所謂,貿易在任何時候都是文化交流的先導,通過使者們進行的朝貢外交,會帶來物質上的交換,比如那些本不屬于中原地區本土的物品,像葡萄和辣椒、香料等等。
中亞使者交往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表現在商業和宗教文化歷史上。這種文明的交流傳播,是以相互間直接或間接交通的存在為前提的。來往于這個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是粟特商人,中國史書稱為“胡商”,他們也被稱為東西文化的“使者”。貿易往來不僅使物品得到傳播,同時更促進了宗教文化的傳播。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有著不同的宗教傳播,比如佛教傳播。佛教進入中國中原地區的過程,基本上最先經印度再到中亞地區,經傳教者來到東方世界。歷史上,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徒就是中亞人。
在某種程度上,中亞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是中亞人和他們的文化向外圍地區的連續運動,以及外圍民族和他們的文化向中亞地區的連續運動。在古代絲綢之路上,中亞和東西方來往的使者中,有些是奉命因政治軍事和朝貢貿易而來;還有是來自中亞的商人以及貿易使團、各宗教的傳教者和翻譯家……這條橫跨亞歐大陸的復雜貿易線路,不僅促進商業貿易的繁榮,還因在絲綢之路上有這些不同身份的使者,他們攜帶著新物種、新思想,是文化傳播的“中間商”,將亞歐大陸各地區緊密聯系。
使者交流的開端
將“兩漢”時期稱作絲綢之路使者文化的正式開端,是因為自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后,打通中亞和東方直接的通道,還帶回了關于西域各國的風土人情。自此中國史書開始官方記載中亞各國以及和中國的來往狀況。自從《漢書》以后中國各個朝代所編正史中,都把中亞列在“西域”之中。這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如漢、唐、元、清等王朝統治時期,所管理統治的地區范圍一度擴展至西域中亞地區。中亞地區的原住民和后來的征服者成為溝通東西方的中間使者,不斷展開與中國、波斯、羅馬等在政治軍事上的外交、經濟上的商業貿易、思想宗教的傳播等。
自漢武帝遣使張騫溝通與西域的往來,古代中亞與周邊民族和國家的互動便逐漸活躍起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使者以及隨行的使團來往絡繹不絕。在西漢時期有為軍事聯盟而出使的張騫,東漢班超命甘英遠赴大秦(羅馬)但最后只到達波斯灣;在軍事原因中,例如唐朝時期中亞各國因大食的入侵遣使求援,如此加強了中西方之間的聯系。從促進絲綢之路上國家之間交流的角度來看,古代交通技術并不發達的情況下,代表國家的使者就是外交官。因出使的目的不一樣,所以代表不同的身份,有象征和平的外交使者,有為爭奪絲路貿易中利益的談判使者。
粟特商人與貿易使者
粟特又稱昭武九姓、九姓胡等,在西方古典文獻記載為索格底地區(Sogdiana,音譯作“索格底亞那”,意思是漂亮的神圣清潔之地)。粟特商人在陸上絲綢之路最活躍和興盛的時間大概是公元三到八世紀,最后在十世紀完全消失。直到近代斯坦因等探險家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有關粟特語的古信札,才使粟特人的歷史重見天日。
歷史上的粟特人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長期受周邊強大的外族勢力控制,先后臣屬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大月氏貴霜、嚈噠、西突厥等。粟特商人在絲綢路上參與絲綢商貿活動,經過長時間組建起幾十或百人的商隊,販運絲綢和香料等大宗商品,主要來往于中國、印度、波斯、拜占庭等。除了善于經商,頭腦精明外,粟特商人精通多種語言,不僅和中國唐朝聯系最為密切,還將足跡擴展到了印度、波斯和東羅馬帝國,“凡利之所在,足跡無不至”。通過使聘貿易等方式,中亞各國與東西方建立了友好屬國關系,而絲路貿易所構成的區域經濟環境又把它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撒馬爾罕出土的阿弗拉西阿卜壁畫中展現撒馬爾罕與外部世界的使者關系,這些使者描繪中,中國人在最中間的位置,可見當時雙方的盟友關系。除此之外,壁畫中有各國使節四十二名,反映出當時統治撒馬爾罕某位國王正在進行與鄰邦諸國的貨物貿易。
粟特商人販運胡粉(化妝品)、胡瓶、胡盤(金銀器)珠寶等奢侈品的記載,曾在出土的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大量出現。并且古代世界的寶石貿易中心是拜占庭帝國的敘利亞省,因而可以推測這些奢侈品大多出自波斯和東羅馬。而絲綢作為奢侈品,在西方需求量也很大。所以在亞歐大陸上,東方與西方由于生產商品的互補性造成商品交換的客觀需求。粟特人所在的本土地區——中亞索格底亞那,地理位置正處于絲綢之路陸上的中心樞紐之地。尤其到中國唐代中期,粟特人的商業活動達到極盛,他們的經商路線不僅沿用絲綢之路的主干道,而且經由突厥、吐蕃、回鶻等民族政權控制的地區,促進了亞歐內陸的多邊貿易。
貿易之路上的中亞宗教使者
除了政治、軍事原因導致的使者交往,宗教與商業一直是文化傳播中更長久和重要的交流方式。利益與信仰是驅動不同文化民族之間交往的直接動因,雖然絲綢之路因為沖突、戰亂等政治原因而不時中斷,卻因這些經商者、傳教者的堅持而不斷暢通。縱觀絲綢之路的歷史,思想和技術沿著貿易路線傳播,而商人一直是主要的傳播媒介,這并非巧合。因為商人不僅僅是運送、出售和獲取貨物,他們在進行的路上會進行社交、互動和觀察,從而把學到的內容帶到各處。貿易路線的存在和長期商業活動,意味著宗教思想可以較為容易沿著橫跨亞歐大陸的貿易網絡傳播。在古代絲綢之路文化傳播史上,各個地區之間為了結伴進行長途貿易,相互建立聯系,就會學習不同的語言以及信仰不同的宗教。這樣一來,在經商之路上,所到一個地區宗教會再次傳播。
宗教與貿易的關系是相互加強的關系。例如,佛教的擴張帶來對絲綢的需求增加,大規模的絲綢被用于佛教儀式,從而進一步刺激長距離的貿易活動,而在這個長距離的貿易中,又會加強佛教的傳播。宗教思想沿著絲綢之路傳播,主要是通過使者的傳教活動。但由于路途遙遠艱險,亞洲內陸有大片不適宜居住的土地,通常沒有水,人煙稀少,加上干燥廣闊的沙漠,以及極端的大陸性氣候所阻礙,無論在冬季還是夏季,旅行都非常困難。為了確保能活下來到達目的地,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入同方向行進的商隊。對于商隊來說,他們遵循既定的路線,通常由職業的商隊領隊帶領,偶爾商隊會在經過特別危險或盜匪猖獗的地區時,還會得到軍方的護送。
同時,高僧進入中原傳播宗教,與胡商的商業活動有密切關系,僧侶和這些商人互相幫助。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傳播宗教的僧侶與粟特商人或者其他商人同行。由于穿越亞歐大陸的地理自然條件惡劣,相互結伴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旅途的風險。商人不僅能保障僧侶的正常生活需求,與此同時,這些僧侶還可以在宗教上給予經商之人心理上的幫助。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宗教的傳播。隨著更多的粟特人成為佛教徒,他們在主商道上建起越來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薩(Hunza)谷可以見到的:無數過路的粟特人將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邊的石頭上,以求漫長的旅程平安而有收獲。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在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Merv)發現的大量建筑,以及在伊朗腹地發現的一系列碑文,都證明佛教有能力和當地的宗教競爭。
從兩漢之際,佛教已開始傳到中國內地,傳教的正是貴霜國的佛教徒,當然還有來自中亞地區的佛教徒。來華的佛教僧徒中有很多是來自中亞康居、安息等地的僧侶。在這些佛教徒中,安息人中大多為姓安或姓支的大月氏人。粟特人大多懂得外語,有些人甚至能讀會寫,經常擔任口譯和翻譯員,將佛教、摩尼教的大部分宗教文本翻譯成各種語言,從印度的阿拉姆語、或帕提亞語到大夏語、吐火羅語、土耳其語或漢語。一旦佛教在中國建立起來,絲綢之路就提供了一個天然的通道,中國佛教的影響可以通過中亞再次向西傳播。
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打通陸上絲綢之路東段,整個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才算正式開始。在古代,除了戰爭以外,國家之間和平友好的往來方式就是使者往來。絲綢之路上代表國家出使的外交使者,就是早期原始的國際外交活動。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參與傳承才得以生生不息。文明演進的過程不是由獨立的個體或民族國家完成的,而是要超越種族、國家、宗教視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使者不單是那些承擔政治軍事和貿易宗教等特殊使命的人,而是人類文明不斷前進發展中有過溝通和貢獻的所有參與者。最后,引用季羨林先生說過的話作為結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文化一旦產生,就必須交流,這種交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