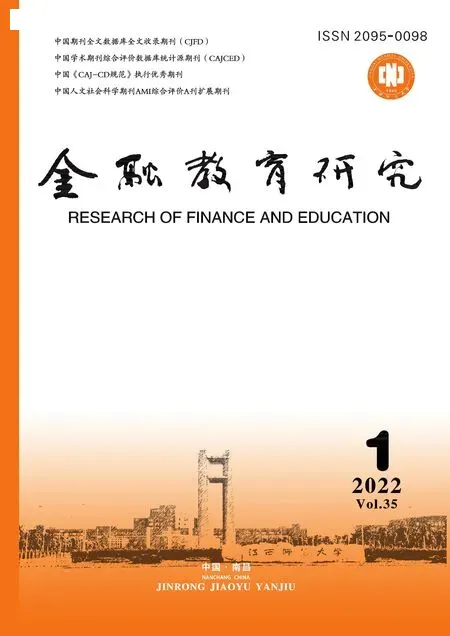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
——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的經驗分析
李 奧, 桑晨穎, 呂勇斌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金融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引 言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意在進一步提升農村地區數字金融服務質效、有效銜接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戰略,最終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讓農民生活更加美好的長遠目標。事實上,中國政府一直重視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的發展。2015年來,中國政府分別發布《推行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1年)》《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等重要文件,明確提出利用數字技術發展普惠金融、助推鄉村振興、建設數字中國。從現實來看,中國的數字普惠金融在過去十年得到了跨越式發展,在全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益平和黃卓,2018)。根據郭峰等(2020)[1]的研究,2011年中國各省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中位數為33.6,到2018年上升到294.3,年均增長達36.4%,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趨勢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自2016年以來,中國政府推出“三去一降一補”五大改革任務,去杠桿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工作內容。《202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完成“三去一降一補”重要任務。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提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重大歷史任務,專業化的“三農”金融服務可以更好地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金融需求,在現代農業經營體系中堅持構建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等新型農業集體經濟。基于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和“三農”發展的政策傾斜,家庭金融行為不再只滿足于資產端的收益,還會逐漸參與信貸市場,獲得一定比例的家庭貸款(尹志超等,2018)[2]。從實際來看,去杠桿政策主要集中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層面,家庭部門的杠桿及債務問題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家庭作為數量最多的微觀經濟主體,其過高的杠桿水平、過快的債務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危害不容忽視(Reinhart & Rogoff,2008[3];馬勇和陳雨露,2017[4])。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就是家庭杠桿率飆升,造成大量普通家庭資不抵債。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報告,2000年底,中國家庭的宏觀杠桿率為12.4%,2009年底上升至23.5%,2019年底高達55.8%,顯著高于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家庭過快、過度加杠桿的行為不僅會造成家庭財務危機和貧困脆弱性,甚至破壞金融穩定,影響經濟增長(Schularick & Taylor,2012[5];Bhamra & Uppal,2019[6])。由此,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降杠桿一樣,家庭部門的高杠桿和債務風險也應高度重視,農戶家庭的過度負債問題同樣如此。
鑒于此,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于數字金融對家庭經濟行為的影響(Agarwal & Chua,2020[7])。本文關注的是數字金融與家庭過度債務的影響。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來提供新形式的支付、借貸和投資等金融服務,有可能改善家庭的資產負債表,通過讓家庭實時控制其財務狀況而受益(Brainard,2016[8])。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能刺激過度的信貸增長和高杠桿以及向風險更高的借款人放貸,從而導致家庭債務危機,并可能進一步惡化更廣泛經濟領域的債務和違約問題(Mian et al.,2017[9])。由此,數字金融和家庭債務之間的關系尚不能完全厘清。此外,數字金融對家庭債務的影響是不均衡的,數字技術促進普惠性增長的數字紅利,在不同家庭中產生異質性的影響。對于那些金融素養較低、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由于無法接觸到互聯網等新技術,無法享受到數字金融發展帶來的數字紅利,新技術可能產生新的不平等即數字鴻溝問題。
因此,隨著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有必要研究家庭是否確實從新的金融創新中受益。本文重點考察數字金融發展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之間的因果關系。盡管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但兩者關系的確定還缺乏足夠的經驗證據。相關研究多是基于宏觀層面、企業或政府層面來評估金融發展與杠桿率及債務風險的關系(馬勇和陳雨露,2017[4];劉貫春等,2018[10];紀洋等,2018[11])。從家庭微觀層面展開的研究,多是評估數字技術對家庭支付、借貸和投資組合的影響(Agarwal & Chua,2020)[7]。從數字技術的角度來評估普惠金融與家庭過度債務及風險問題,相關研究較少(Basnet & Donou-Adonsou,2016[12];吳衛星等,2018[13];Hong et al.,2020[14])。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試圖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貢獻:第一,在數字技術驅動金融創新的背景下,匹配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從微觀視角研究數字金融發展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之間的關系,以豐富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相結合的交叉研究;第二,利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構建家庭層面的數字鴻溝指數,從數字鴻溝、信息不對稱的機制渠道挖掘數字金融影響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作用機理,探尋數字金融發展的獨特機制渠道;第三,選擇農戶所在城市到互聯網骨干直聯點城市的距離和北京大學創新創業指數作為工具變量,解決計量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并通過替換關鍵解釋變量等做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以獲得可靠的結論。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及樣本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家庭微觀層面的數據,采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CHFS主要收集家庭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保險與保障、人口與就業等家庭金融信息。考慮到數據的時效性問題,選取2019年被訪問到的家庭作為樣本。數據范圍涵蓋我國29個省份163個城市,2019年參與調查的人數為107008人,家庭共34643戶,其中農村樣本總人數為40630人,農村樣本家庭11821戶。第二部分是地區層面數字金融發展程度的數據,采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郭峰等,2020)[1]。該指數涵蓋中國31個省份、338個地級市以及近2800個縣域,全面刻畫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趨勢與空間特征。根據研究需要,選取2019年城市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代表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第三部分是地區層面的經濟數據,主要采用Wind數據庫、《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統計數據。
本文將三部分數據按照地級市層級進行合并,并采用通行方法對家庭數據進行處理:剔除家庭收入、家庭資產和家庭負債為負數的家庭;剔除資產與負債類別數據缺失的家庭;對連續型變量進行雙側1%的縮尾處理。最終選定一套包含2019年有效樣本為8304戶的農村家庭數據集以及對應的2018年城市級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集,覆蓋全國30個省份、151個地級市。數據的匹配與處理有助于精準識別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之間的關系。
(二)農戶家庭過度負債指數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結合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內容,從債務償還率、貧困線和家庭自評償債能力的主客觀指標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進行測度。
1.客觀指標測度。從償債成本的角度出發,已有研究通常使用償債收入比DSR(Debt-Service-Ratio)作為界定家庭過度負債的指標。通過整理分析,發現農戶家庭除了農業生產和工商業生產帶來的生產性收入外,還有房產收入和金融資產收入,雖然只有極少部分農戶擁有金融資產。為了更加客觀地評估農戶家庭的負債情況和償債壓力,本文在對過度負債的指標測算中,在償債收入比DSR的基礎上,假設家庭在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時會將金融資產變現用于還債,這樣就會成比例地減少其償債成本,但同時相應的家庭收入也會減少。具體測算公式如下:
(1)
其中,DSR1為調整后的償債收入比,Debt為家庭負債總額,AF為家庭擁有的金融資產價值,AR表示除了房產以外的其他資產,R表示家庭年度償債總支出(包括本金和利息),Y表示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YCF表示家庭金融資產收入,YCA表示家庭房產收入。本文界定,當調整后的償債收入比DSR1大于0.55時,家庭處于過度負債狀態,即OI為1,反之為0。
貧困線是判斷家庭經濟狀況的公認指標。筆者也考慮采用貧困線來判斷農戶家庭是否過度負債。以貧困線判斷過度負債的測算公式為:
(2)
其中,Y表示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R表示家庭年度償債總支出(包括本金和利息),N表示家庭人口規模。采用相對收入貧困線和絕對收入貧困線來判斷。相對收入貧困線判斷是指,當Line小于全樣本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時,判定為過度負債家庭,OI為1,反之為0。絕對收入貧困線判斷是指,當償債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即Line低于3473元,判定為過度負債家庭,OI為1,反之為0。
2.主觀指標測度。從主觀角度來看,相關研究使用家庭自評償債能力定義過度負債(Lusardi & Tufano,2015[15];吳衛星等,2018[13])。選用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問卷中“您認為當前償還住房欠款的經濟能力如何?”問題,根據農戶的主觀感受進行測度,建立家庭過度負債主觀指標Subjective。當回答“沒問題”“基本沒問題”和“不存在住房欠款”,則認為該家庭的負債在可能償還的能力范圍之內,不存在過度負債問題,此時OI為0;當回答“難以償還”和“完全沒能力償還”,則認為該家庭償還債務存在困難,超出了家庭可承擔范圍,存在過度負債問題,此時OI為1。
(三)解釋變量的選取
1.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找到合適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DIF)的度量指標,是本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關于數字金融的度量,郭峰等(2020)[1]采用螞蟻集團的交易賬戶大數據,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支持服務程度三方面,編制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時間跨度為2011—2018年,具有代表性和可靠性。李春濤等(2020)[16]通過提取互聯網金融、機器學習、智能投顧等48個金融科技關鍵詞,將這些關鍵詞與297個地級市或直轄市相匹配,運用爬蟲技術對百度新聞高級檢索中出現的“地級市+關鍵詞”組合數據進行爬取,并將同一城市層面的關鍵詞搜索數量進行加總后取對數,作為該城市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時間跨度為2011—2018年。采用郭峰等(2020)[1]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做基準回歸,采用李春濤等(2020)[16]的數據做穩健性檢驗。
2.其他控制變量的選取。參考已有研究,結合CHFS問卷,除數字普惠金融(DIF)外,在回歸模型中還控制了戶主特征變量、家庭特征變量和地區特征變量。戶主特征包括性別(Gender)、婚姻(Marriage)、年齡(Age)、工作(Work)和教育水平(Eduyear)等。家庭特征既包括家庭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如家庭的人口規模(Familynum)、家庭不健康人數(Unhealth)以及家庭成員的金融素養(Fl),也包括家庭的經濟特征,如家庭醫療保險情況(Medins)和家庭總消費(Consume)情況。地區特征主要包括城市級的人均GDP(perGDP)和金融發展水平(FD)。
變量的具體說明見表1。

表1 變量說明
(四)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2匯報了變量描述統計結果。

表2 變量描述統計
本文關注的是過度負債家庭的特征(見表3)。通過對樣本中存在過度負債和不存在過度負債的家庭特征均值比較分析發現,農戶家庭的過度負債行為在年齡、婚姻和性別方面差距不大,而在戶主工作狀況、教育年限、家庭醫療保險持有狀況、家庭不健康人數、家庭消費支出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表3 過度負債家庭特征均值比較
其中,無過度負債家庭戶主有工作的比例、受教育年限與醫療保險持有比例均大于過度負債家庭,從家庭不健康人數比較來看,平均每個過度負債家庭都有一名健康狀況不好的家庭成員,且過度負債家庭的金融素養水平低于無過度負債家庭。特別是,家庭總消費高于無過度負債家庭,這說明農戶家庭的過度負債可能是因不合理消費引起的。
從各類負債額度的均值比較來看(見表4),農戶戶均負債總額為29273.205元,低于城鎮居民負債水平。其中,購房負債均值(13296.947元)最高,符合當前我國房貸為家庭主要負債的基本事實(占總負債比例45.42%)。通過對家庭負債結構的進一步比較來看,所有樣本的負債結構中,擁有房貸的人數占比最高(59.53%),也說明本文在主觀測度指標中使用對于償還房貸的壓力問題來衡量家庭過度負債是合理的。此外,還發現雖然醫療負債的均值在所有負債類型中均值居于第四位,但擁有醫療負債的家庭比例達到49%,僅次于房產負債。

表4 農戶家庭負債結構均值比較
進一步,通過對過度負債家庭的區域分布特征進行比較發現,三個測度指標表示的過度負債家庭占比,東部地區分別是2.04%、26.08%和3.32%,西部地區分別是3.38%、32.88%和6.98%,均是中西部地區占比明顯高于東部地區。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參考張勛等(2018)[17]、尹志超等(2020)[18]的做法,采用面板Probit模型來研究數字金融發展對家庭過度負債的影響。被解釋變量家庭過度負債為啞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是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控制變量包括戶主層面、家庭層面以及地區層面的特征變量。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影響的基準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Pr (OIij=1)=α0+α1DIFj+α2Indij+α3Hhij+α4Cityij+εij>0
(3)
其中,下角標i表示家庭,j表示城市。OI表示農戶家庭是否過度負債的二值變量,存在過度負債則取值為1,否則為0。核心解釋變量DIF為家庭所在城市j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Ind為第i個家庭的戶主特征變量,Hh是第i個家庭的家庭特征變量,City為家庭i所在城市j的控制變量。ε為隨機擾動項。模型中加入時間和省份雙固定效應,以控制部分遺漏變量。為避免地區內部家庭之間的相關性問題,模型的標準誤聚類到地級市層面。本文關注的是待估參數α1的方向及顯著性,預計α1的方向為負,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農戶家庭發生過度負債的概率越低。
表5匯報了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無論是由兩個客觀測度指標衡量的農戶家庭過度負債,還是主觀測度指標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負相關,證明了數字金融發展能夠顯著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在債務償還指標OI1中,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每上升1%,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則下降5.6%;在相對收入貧困線指標OI2中,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每上升1%,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則下降28.6%;在主觀指標OI3中,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每上升1%,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下降13.02%。

表5 基準回歸結果
在個人特征控制變量中,加入了年齡(Age)和年齡的平方項(Age2),結果顯示年齡與過度負債之間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關系,即隨著年齡增長,家庭過度負債的概率會先上升再下降。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家庭的負債水平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上升,到了中老年時期開始下降直至為0,家庭負債水平最高的時期就是家庭的年輕時期,借款的可能性更大(Kumar & Liang,2019[19]),也是形成家庭過度負債概率最高的時期。戶主是否有工作(Work)與過度負債關系在三個指標中分別呈現10%、1%和1%的顯著負相關,說明未失業的戶主家庭過度負債的概率更低。此外,受教育年限(Eduyear)與過度負債分別在10%、1%和5%的水平下顯著負相關,教育水平每提高1%,家庭過度負債的概率分別下降0.11%、0.97%和0.18%,說明戶主的受教育水平越高,過度負債的可能性越低。
在家庭特征控制變量中,家庭成員醫療保險持有狀況(Medins)與金融素養水平(Fl)都與過度負債呈現顯著負相關,家庭不健康人數(Unhealth)與家庭消費(Consume)與過度負債呈現顯著正相關。說明家庭越多成員持有醫療保險,家庭過度負債的概率越低,家庭不健康人數越多,過度負債的概率就越高,該結論也證實了農戶存在因疾病過度舉債的情況,并且農戶購買醫療保險的意識還不夠普遍,如果家庭成員繳納社會醫療保險或者購買其他醫療保險,醫療負債會降低,家庭的經濟壓力較小,發生過度負債的可能性降低。家庭成員金融素養水平越高,產生過度負債的可能性越低,該結論與Gathergood(2012)[19]、Lusardi & Tufano(2015)[15]等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可能的解釋是,金融素養高的家庭對于負債成本、償債成本和利息計算等方面擁有更正確的認識,能夠較為準確地計算負債本息,更可能通過正規信貸渠道來持有負債,但也正因為其具有較好的風險認知能力,在家庭經濟決策中,該類家庭能基于其家庭實際資產質量來判斷自身的還款能力,進而決定是否舉債、將舉債進行到何種程度,因此金融素養高的家庭會降低過度負債、債務違約的概率,減少債務過度自信和家庭財務風險。
地區層面的宏觀經濟控制變量人均GDP和金融發展水平與家庭過度負債的關系并不顯著,說明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對家庭金融決策的影響較小。
(二)內生性處理
數字普惠金融與家庭過度負債之間的關系可能受到內生性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較小。從變量的選取來看,家庭過度負債屬于家庭層面的指標,而數字普惠金融是城市層面的指標,且這兩份數據來自兩個不同的數據庫,故兩者之間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比較小。從數據的抽取來看,根據家庭金融調查問卷設計,CHFS在抽樣時采取了分層、三階段和規模度量成比例(PPS)方法,而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編制采用了主客觀賦權相結合的方法確定權重,兩份數據都較為準確和可靠,這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測量誤差問題。本文在使用數字金融指數做分析時,已經選取該指數的滯后一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內生性問題。
盡管如此,兩者之間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而導致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工具變量估計方法來處理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具體來說,本文構建基于地理距離的工具變量(IVdistance)和以創新創業指數(IVcreate)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處理。
1.平均地理距離工具變量的構建。基于地理距離構建的兩個工具變量分別計算的是農戶所在城市到國家級互聯網骨干直聯點(National Internet Backbone Straight Point)的距離。互聯網骨干直聯點是國家重點信息樞紐,匯聚了區域通信流量,作為互聯網架構的關鍵基礎設施,與數字金融發展的網絡基礎和技術基礎密不可分,這些互聯網骨干直聯點由國家政府牽頭設立,不受家庭金融行為影響,滿足工具變量選取的兩個條件,即相關性和外生性。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座城市在我國最早設立國家級互聯網骨干直聯點,2013年,我國增設7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包括武漢、成都、重慶、西安、沈陽、南京和鄭州。具體來說,首先,在百度坐標系統拾取樣本城市WGS_1984坐標系的經緯度坐標。其次,基于各城市經緯度坐標計算得到各城市與骨干直聯點城市的距離,再計算平均距離。其中,distance1是從農戶家庭所在城市到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平均距離,distance2是農戶家庭到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重慶、西安、沈陽、南京和鄭州等十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的平均距離。最后,以平均距離的倒數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即IVdistance1和IVdistance2。
表6是基于三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構建的平均距離工具變量(IVdistance1)估計結果。其中,第一階段沃爾德內生性檢驗Chi2分別在5%、1%和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第一階段F統計值為1922.34,工具變量t值為155.96,AR和Wald檢驗結果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基于三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構建的平均距離工具變量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說明該工具變量是合理的。

表6 平均距離工具變量回歸結果1
表7是基于十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構建的平均距離工具變量(IVdistance2)的估計結果,第一階段沃爾德內生性檢驗結果Chi2分別在5%、1%和1%的水平下顯著,第一階段F統計值為1345.63,工具變量t值為129.78,AR和Wald檢驗結果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基于十個互聯網骨干直聯點構建的平均距離工具變量是合理的。

表7 平均距離工具變量回歸結果2
從估計結果來看,在加入工具變量后,表6和表7顯示數字金融與農戶過度家庭負債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與基準回歸方向一致,并且邊際系數有不同程度的擴大,進一步說明數字金融能夠顯著降低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
2.創新創業指數工具變量的構建。“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是由北京大學與龍信數據合作編制發布,該指數包含了省級層面和城市級層面的數據,包括新建企業數目、風險投資、吸引外來投資、吸引風險投資、專利授權數量和商標注冊數量在內的6個維度,全面反映各地區創新創業的水平。數字金融的成長本身就是創新的一種表現形式,當地的創新水平能夠驅動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因此,區域創新創業指數(IVcreate)與數字金融發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此外,創新創業指標是城市層面而非家庭層面指標,與家庭的負債情況沒有直接關系,因此該指數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表8為區域創新創業指數工具變量(IVcreate)的回歸結果。第一階段沃爾德內生性檢驗Chi2在1%的水平下顯著,存在內生性問題,模型第一階段F統計值為1309.52,工具變量t統計量為127.96,AR和Wald檢驗結果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加入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之間仍然在1%的水平下呈現負相關關系。這再一次驗證了數字金融發展能夠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

表8 區域創新創業指數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四、進一步分析
(一)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本文用不同測度方式構建新的被解釋變量來替換原始模型的因變量。基準模型的被解釋變量OI是基于家庭的資產、負債余額、償債支出等數據構建而成。在穩健性檢驗中,參考吳錕等(2020)[20],將債務償還比率OI4、絕對收入貧困線OI5作為被解釋變量。
在債務償還比率OI4中,分別比較閾值為30%、50%和55%的過度負債測度方式,來證實在任一當前可使用的閾值下,數字金融發展與農戶過度負債因果關系的穩健性。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基于三種閾值的債務償還比率測度,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與農戶過度負債的關系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數字普惠金融每提升1%,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概率分別下降8.83%、9.24%和8.58%,與基準回歸結果邊際效應方向一致。

表9 穩健性檢驗1:使用債務償還比率的不同閾值
在前面的討論中,將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去家庭償還債務的總支出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國家貧困線的家庭,界定存在過度負債。需要說明的是,吳錕等(2020)[20]的研究將絕對收入貧困線定于2300元,該取值是基于我國《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規劃,該規劃將2010年我國的貧困線定于2300元。但通過查閱資料發現,我國貧困線每年都依據經濟發展狀況和扶貧開發實況進行調整,貧困線已經由2010年設置的2300元,升至2019年的3473元。本文嘗試將3473元作為絕對收入貧困線來測度過度負債OI5,得到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數字金融發展顯著抑制農戶過度負債發展的概率,與本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

表10 穩健性檢驗2:使用絕對收入貧困線
2.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參考李春濤等(2020)[16],使用2018年金融科技指數(Fintech)作為數字金融發展(DIF)的代理變量進行替換。該指數基于百度新聞高級檢索結果進行度量,在已有研究中作為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的指標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回歸結果如表11所示。可以看出,在替換被解釋變量后,數字金融仍然在1%的水平下顯著降低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與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這進一步證明,基準回歸的結果是穩健可靠的。

表11 穩健性檢驗3: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二)異質性分析
1.基于區域層面的差異分析
(1)東中西部的差異性。我國地域遼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2018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城市梯隊圖來看,東部省份的城市在數字金融發展方面遙遙領先。本文將樣本劃分為東部與中西部兩個區域,對不同地區數字金融對農戶過度負債的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表12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對過度負債的影響系數在10%、1%和5%的水平下均顯著為負。這說明,與東部地區相比,數字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的效應更加突出。這一發現與已有研究一致(張勛等,2019[17])。可能是因為在數字金融快速發展之前,東部地區資金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相對較弱,產業結構相對完善,金融服務范圍較廣泛,傳統金融的信貸渠道也可以滿足該地區家庭的負債需求,因此數字金融的普及并不會明顯抑制該類家庭的過度負債。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業發展需求更迫切,資金使用率相對較低,區域交易成本較高,技術創新和數字普惠金融對中西部農戶家庭投資的溢出效應較為明顯,同時,由于數字金融得益于數字技術在當地的快速傳播和普惠金融對小微農戶家庭的強包容性,信息技術帶來的邊際效應在中西部地區更明顯,金融安全知識也如信鴿一般飛進了千家萬戶,家庭的金融素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打破了其對金融行業的認知壁壘,家庭逐漸領悟到“風險與收益呈正相關關系”“杠桿越大,風險越大”,保持較穩定的儲蓄率,不再盲目擴張負債自信,因此從主觀意識上降低過度負債的概率。此外,數字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性和區域交易成本,為中西部地區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提高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理財的收益占比,降低農戶家庭的貧困脆弱性和財務風險,因此數字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的效應更加突出。

表12 基于區域位置差異的分析結果
(2)貧困縣與非貧困縣的差異。根據農戶家庭所在區縣是不是國家級貧困縣,將縣域劃分為貧困縣與非貧困縣。劃分依據是2019年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公室官網出具的《831個貧困縣歷年摘帽退出名單》,剔除2018年宣布脫貧的縣、保留2019年仍處于國家級貧困縣范疇但是2019年底才宣布脫貧的縣。據表13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對非貧困縣的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抑制效應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對貧困縣的回歸結果基本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根據需求層次理論,大部分農戶仍然停留在第一層次的生活基本需求,不會額外產生消費型負債,過度負債的概率低。而在非貧困地區,農戶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已經得到滿足,追求更高層次的消費愿望更大,更換家電、購置新房等高層次需求明顯,由此產生消費型負債。因此,數字金融對非貧困縣農戶過度負債的邊際效應更加突出。

表13 基于區域位置差異的分析結果
2.基于家庭層面的差異分析
(1)信貸需求的差異分析。農戶的信貸需求分為正規信貸需求和非正規信貸需求兩種。參考傅秋子和黃益平(2018)[21],選用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問卷中“目前,您家是否因農業/工商業生產經營活動有尚未還清的銀行/信用社貸款”“您家為什么不從銀行/信用社申請貸款獲取所需資金”“您家未能獲得貸款的原因是什么?”和“您家計劃從下列哪個渠道借入所需資金?”四個問題的回答,對農戶家庭的信貸需求差異進行識別,將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的、且農戶自身能夠償還的負債意愿識別為正規信貸需求,將其他情況視為非正規信貸需求,具體如表14所示。

表14 信貸需求的識別
在劃分信貸需求不同類型的樣本后,對具有正規信貸需求的農戶與非正規信貸需求的農戶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15所示。可以看出,從正規信貸需求來看,數字金融與過度負債之間的邊際效應為正但不顯著,從非正規信貸需求來看,數字金融發展則能夠顯著抑制農戶家庭的過度負債,且數字金融指數每提升1%,非正規信貸需求組的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分別下降8.67%、48.41%和18.24%,該研究結論與吳雨(2020)[22]等人的研究結論相似。數字金融發展能夠顯著降低家庭的傳統私人借貸需求,即從親戚朋友處借貸的需求,從供需層面產生了替代效應。基于非正規信貸渠道產生的負債門檻低,容易形成多頻次、高額度的負債,造成家庭過度負債的可能性較大。因此,數字金融降低來自非正規信貸需求產生的過度負債效應更加突出。

表15 基于信貸需求差異的回歸結果
(2)風險態度的差異分析。根據2019年調查問卷“如果您有一筆資金用于投資,您最愿意選擇哪種投資項目?”來確定農戶的風險態度,將農戶家庭劃分為風險規避型和風險偏好與中性型兩大類,并對兩大類別分組回歸。表16的分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抑制風險規避型家庭過度負債的邊際效應更加顯著。可能的解釋是,風險偏好源于過度自信(李莉等,2020)[23],風險偏好越強的家庭負債的概率越大(何麗芬等,2012)[24]。風險偏好型農戶家庭可能會過于相信主觀判斷、忽視客觀存在的風險,而風險規避型農戶家庭對于進行大量負債的決策更加謹慎,會更加謹慎考慮有關負債風險的信息,數字金融抑制過度負債的效應更加顯著。

表16 基于風險態度差異的回歸結果
(三)機制檢驗
1.調節效應檢驗。寬帶與移動電話是居民接觸數字金融最常用的終端設備。通過互聯網和移動電話,農戶家庭可以獲得更多的金融產能品信息,緩解農村地區因“硬件設備”落后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對于數字金融的發展有顯著的支持作用。參考已有研究,引入移動電話持有率(Mobile)與寬帶普及率(Netrate)作為調節變量,加入交乘項Digital×Mobile與Digital×Netrate,檢驗地區移動電話持有率和互聯網寬帶普及率對數字金融發展抑制農戶過度負債的調節作用,回歸結果如表17所示。

表17 移動電話持有率與寬帶普及率的調節效應檢驗
從中可知,移動電話持有率與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的交乘項(Digital×Mobile)系數方向均為負,且都通過了不同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互聯網寬帶普及率與數字金融發展水平的交乘項(Digital×Netrate)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移動電話持有率和互聯網寬帶普及率對數字金融影響農戶過度負債具有調節作用,并且移動電話持有率與互聯網寬帶普及率的提升顯著強化了數字金融發展對農戶過度負債的抑制效果。因此,農村地區繼續加強“硬件設施”建設,繼續提高農戶家庭寬帶接入數量,加快推進農戶家庭移動電話持有量,縮小城鄉之間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的差距,以更好地發揮數字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抑制作用。
2.中介效應檢驗。當數字技術逐漸成為一種通用技術,因新技術的使用差異而導致的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問題逐漸凸顯。為進一步考察數字金融能否通過彌合數字鴻溝來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參考尹志超(2020)[18]的做法,根據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問卷調查,選用“您家擁有以下哪些類型的耐用品?”(是否有智能手機)“是否開通支付寶、微信支付、京東網銀錢包、百度錢包等第三方支付?”“多久網購一次”“是否有互聯網借貸?”四個問題,利用因子分析法構建數字鴻溝指數(Digital_divide),以數字鴻溝為中介變量,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1)限于篇幅,本文未匯報農戶家庭數字鴻溝指數的因子分析結果。。
在兩個過度負債的客觀指標測度中,第一步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抑制農戶過度負債的總效應分別為-0.0560和-0.2858,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第二步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對中介變量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且影響效應為-17.9959,說明數字金融發展能夠彌合數字鴻溝,與前文理論分析部分相一致。第三步回歸結果顯示,控制中介變量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后,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抑制農戶過度負債(OI)的總影響分別為-0.0490和-0.2430,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與農戶過度負債在1%水平下呈現顯著正相關,邊際效應分別為0.0003和0.025,說明當數字鴻溝每縮小1%,農戶的過度負債的概率下降0.03%和2.5%。
在過度負債的主觀指標測度中,中介效應模型第一步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抑制農戶過度負債的總效應分別為-0.1302,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第二步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對中介變量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且影響效應為-17.9959。第三步回歸結果顯示,控制中介變量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后,數字金融發展水平(DIF)抑制農戶過度負債(OI3)的總影響為-0.1183,即數字金融發展水平每上升1%,農戶過度負債的概率下降11.83%,數字鴻溝(Digital_divide)與農戶過度負債呈現正相關關系,邊際效應為0.0003。

表18 基于數字鴻溝的中介效應檢驗1

表19 基于數字鴻溝的中介效應檢驗2
上述中介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說明,數字金融發展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有著明顯的抑制作用,并且這種抑制作用可以通過彌合數字鴻溝實現。這一結論對于數字金融本身具有很強的普惠性優勢(陳冶國和白鳳嬌,2021)[25]。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一方面,農戶家庭通過互聯網、移動終端與淘寶、微信這樣的場景緊密聯系,另一方面,又通過社交、網購、理財等大數據挖掘,為農戶家庭做信用評估,數字鴻溝問題在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下不斷縮小。
此外,銀行等正規金融結構借助于數字技術、掌上銀行等方式,降低了農戶家庭從正規信貸機構獲得借貸資金的門檻,對非正規渠道的資金借貸形成擠出效應,從而使農戶家庭的負債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能夠有效地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行為。
五、研究結論
適度的負債有助于居民平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但過度負債對個人、家庭、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都有嚴重的負面影響。而數字金融這樣一種利用信息技術驅動金融創新的模式,使金融服務的可得性、便利性、包容性大幅改善,這為抑制家庭過度負債提供了有利條件。
本文的貢獻在于構建了實證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對農戶家庭過度負債的影響,以豐富數字金融和家庭金融相結合的相關研究。本文將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9年的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8年的數據進行匹配,評估了數字金融發展與農戶家庭過度負債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夠顯著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這種抑制作用主要是通過縮小數字鴻溝、緩解信息不對稱的機制渠道來實現的,尤其是對中西部地區、非貧困縣以及有非正規信貸需求、風險規避型態度的農戶家庭而言更加明顯,數字金融展示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的顯著優勢。上述發現在更換關鍵變量的度量指標和處理內生性問題后,結果都是穩健的。這些研究基本證實了新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對家庭經濟行為具有積極影響的特性。
本文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第一,在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去杠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要密切關注家庭杠桿問題,既要合理控制家庭負債的總量,也要嚴防家庭負債的風險,尤其是其過度負債風險。第二,數字金融服務對抑制農戶家庭過度負債具有積極的作用,因此需要繼續推進數字金融的發展,特別是提升其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以更好地發揮數字金融的積極影響。第三,在推進數字金融發展的同時,要重點關注農村地區特殊家庭的數字鴻溝問題,為此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推進金融知識的普及和推廣,完善互聯網等新技術設施建設,加快數字技術的深層次應用,以使更多農戶家庭彌合數字鴻溝、釋放數字紅利,讓數字金融體現出更強的包容性。第四,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表現出很強的地區收斂性,中西部地區數字金融的發展與東部沿海地區差距大幅縮小,但還有一定的追趕空間,因此要進一步加強中西部地區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引導數字金融在中西部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也適用于貧困縣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