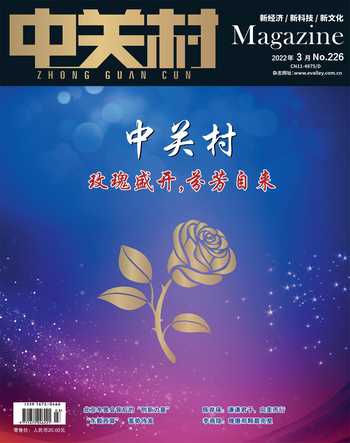思鄉情難遏,家國駐心底
蕭惑之

葉嘉瑩先生是當代研究講學中國古典詩詞的教授學者專家,詩論詞論造詣精深,多有獨家見地;在詩詞創作的園地里,篇什頗豐,妙句迭出,乃真情感自然流淌。一部《迦陵詩詞稿》幾乎成為當代弄舊體詩詞圈內人之案頭書。先生自云,“《楞嚴經》中鳥名迦陵者,其仙音徧十方界,而‘迦陵’與‘嘉瑩’之音,頗為相近,因取為筆名焉,是為第一次詞作之發表。”據考當是1942年受業于顧隨教授,詩詞創作漸豐的學生時代。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葉嘉瑩先生的著作遵循這一古訓,“是中國最美先生,飽受苦難卻笑傲人間”。先生經多難多彩的生活洗禮后自云,“20世紀70年代后期,因多次返國,為故國鄉情所動,始再從事詩詞之創作……”愚以為,這正是“故國鄉音動情思,潑墨感慨胸有詩”。這也正是我再讀《迦陵詩詞稿》的一點新感悟。先生又說,“近歲以來,雖因故國鄉情之感,重拾吟筆,而功力荒疏,縱有感發之真,而殊乏琢煉之巧。”這自然是自謙之語,實則是先生看到國家重振,百業方興,欣然感悟,潑墨碼字,心語鑄魂,留存佳篇。“讀書曾值亂離年,學寫新詞比興先。歷盡艱辛愁句在,老來思詠中興篇。”此絕句,可見先生老當益壯扶犁耕耘的心態是多么強烈。這正如先生所說的“由于時代不同,不須更以隱晦之筆寫凄楚之音”吧。
葉嘉瑩先生豆蔻年華的青春期,知性單純,已經有詩作留存,不乏佳句。諸如,對窗前秋竹有感“忍向西風獨自清”。詠蓮則有“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之問。詠菊留下“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的感嘆。1941年母親謝世,“淚哭無語暗吞聲”,“悔不當初伴母行”。對一個青春多夢喜歡詩詞的少女而言,苦雨、春風、秋意、寒冬……“有心秋添愁,無夢愁亦秋”,都可以撩撥少女敏感的神經,走筆成詩。
“五十而知天命”。1974年秋天紅葉時節,葉嘉瑩先生久居異鄉后第一次回到祖國探親旅游,興奮不已,感慨萬端,伏案寫就七言古體詩《祖國行長歌》近300句美篇。“思鄉情在無時已”,“眼流涕淚心狂喜”。“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親”。“千年帝制興亡史,從此人民做主人”。……長句的結尾,吟唱道出鄉情之幽思,“早經憂患久飄零,糊口天涯百愧生,雕蟲文字真何用,聊賦長歌紀此行”。我們吟讀這些發自肺腑悲喜交加的詩句,可以想見葉先生是何等的動情!兩年前,先生在《春日絕句四首》中還吟唱“斜暉凝恨他鄉老,愁誦當年韋相詞”。韋相者韋莊也,晚唐詩人,詞風清麗,“花間派”的代表,可見年輕時的葉先生對韋莊詩詞情有獨鐘。黃金時代造就才女,“驀地青山夕染紅,神州沃土沐春風”。從此,葉嘉瑩先生的詩詞作品如噴泉流淌,“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獨有豪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詩詞留香,心態也。
1977年仲夏時節,葉嘉瑩先生借回國探親之際,參觀了大慶,“所見所聞,皆為古典詩中所未曾前有之事物”,先生作了“融新入古之嘗試”,創作《大慶油田行》,別開生面,充滿激情,“大慶油田潑墨行,知君心愿神州紅”。從“松花江水嫩江東,草原如海迷蒼穹,空有寶藏蘊萬古”發端,到“吁嗟乎創業艱辛業竟成,飛鵬從此展云程,中華舉國興工業,大慶紅旗是典型”收筆,一氣呵成七言古體詩120多句。字里行間,欣喜欲狂,“敢教日月換新天”,詩人放歌唱大風,祖國,母親,游子歸心,滿目陽光,“胸中有大愛者,舌端斯有驚語”也。
“小窗細嚼梅花芯,吐出新詩字字香。”葉先生每次歸來飽覽祖國大好河山,訪問工廠田園,都詩情大發,隨手拈來皆妙句,“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繼《大慶油田行》后,又有《旅游開封紀事一首》,五言古風60句,紀事多感慨,今天讀來可見那個時代的祖國風貌。“遊子還舊邦,行程過古汴,魏宋渺千年,人間市朝變”。“鐵畫與銀鉤,意氣何遒健”。“更欲索新詩,愧無珠玉獻”。接續下來的《紀遊絕句十一首》更是真情狂泄,不乏妙句。諸如,“今日我來真自喜,還鄉值此中興時”。“已掃群魔凈惡氣,放懷堂上論詩文”。“陜北歌傳金匾名,新詞三疊表深情”。……1978年春寫就的《向晚二首》真情狂瀉,“近日有歸國之想,傍晚于林中散步成此二絕”。詩云,“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余金。漸看飛鳥歸巢去,誰與安排去住心。”讀此,可見葉嘉瑩先生有“歸去來兮”之感懷。詩作發表后,國內的友人“心有靈犀”,鴻雁傳書,葉嘉瑩先生感慨萬端,《再吟二絕》,聊以自慰,謝答友情。詩云“海外空能懷故國,人間何處有知音。他年若遂還鄉愿,驥老猶存萬里心。”余讀罷,“胡不歸”,在書眉碼字,“向晚踽行值鳥歸,君心藏愛盼重逢。國疆無界唱詩慟,萬里有情托夢行。”葉先生的心境是彷徨卻明晰的,“力挽東流變海桑”,“可有遊魂化鶴來”,“不為蒼生謀社稷,壽山福海總虛名”。
葉嘉瑩先生1945年畢業于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曾在中國臺灣任教15年,1969年遷居溫哥華后,被聘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文學院士”。先后被美國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聘為客座教授。葉嘉瑩教授教書育人最輝煌的時期當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應邀回國講學。“自此每年假期自費回國講授詩詞至今”。北大、北師大、南開、川大、武大等數十所大學留下葉先生的身影和聲音。最值得書寫一筆的是,1993年葉嘉瑩教授在南開大學創辦了“中國文學比較研究所”即后來的“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還用自己的一半退休金10萬美元建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為普及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貢獻自己的力量。葉嘉瑩是屬于我們當代的“大先生”,國之瑰寶,不僅精于中華文化尤其是詩詞學,而且具有“世界的心”,能熔中西文化于一爐。
葉嘉瑩先生術業有專攻,著作博精深,“詩言志”,“文傳道而明心”,“腹有詩書氣自華”。先生的詩論詞論“極重感發興起之功”,是百年不多見的大家見地;舊體詩詞創作更具有時代氣息和家國情懷。李清照的《漱玉詞》名傳千古,一句豪邁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巾幗不讓須眉。今人評論葉嘉瑩先生則有“續易安燈火,得唐宋薪傳,繼靜安絕學,貫中西文脈。你是詩詞的女兒,你是風雅的先生”之感慨。這部《迦陵詩詞稿》則是我們探秘“嘉瑩心聲、讀書脈絡、靈魂騰空、創作足跡”的最好文稿。
“白發猶能寫妙詞,曲園家學仰名師。人間小劫滄桑變,喜見風儀似舊時。”這是葉先生“贈俞平伯教授”的心之聲,在淡淡的酸楚中讓人暖懷。讀后驚嘆,“矮紙君能碼小字,深情落墨皆詩詞”。《楊振寧教授七十華誕口占絕句四章為祝》中,佳句雋永,“過人智慧通天宇,妙理推知不守恒。”“我愧當筵無可奉,聊將短句祝長春。”惺惺相惜兩心知,語短情長,奮斗在異國他鄉,心系祖國繁榮富強。《陳省身先生悼詩兩首》寫于“甲申孟冬大雪之節”,“先生長我十三齡,曾許論詩獲眼青。此去精魂通宇宙,一星遙認耀蒼冥。”讀此讓人聯想到世界以陳先生之名命名的小行星,“數學大家伴星舞,華裔神算思遠圖”。讀《迦陵詩詞稿》最讓我不能忘懷的是,中國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過世時,葉先生應邀為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開追悼會代撰挽聯——“革命為人民求解放,盡瘁忘身,不惜憂勞終一世。 運籌為舉世拓新猷,折沖尊俎,長留功業在人間。”一代偉人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官文如是,享譽世界;葉先生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長年伴虎生涯,苦意有誰知,忍聽人傳身后謗。千古臥龍相業,憂勞終身殉,固應祠向世界留。”嗚呼!“千秋功罪誰人評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至上”,字里行間留下歷史的細節,開國元勛,國之棟梁,永垂不朽!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感發意志”,“考察社會”,“相互感化”,“怨刺上政”。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讀《迦陵詩詞稿》可以看到一位年近期頤之年長者壯麗人生的奮斗之路——家國情懷,大愛流淌,文采飛揚,詩言志,詞詠懷。葉嘉瑩先生是中華民族文化長河中“懷京華北斗之心,盡書生報國之力”的當代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