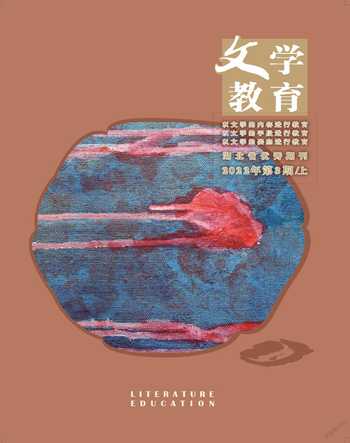楊絳《洗澡之后》的語言得體性分析
劉東青
內容摘要:得體性是修辭的最高的原則,得體性原則體現為話語對語言環境的適應程度。本文以《洗澡之后》為例,從語言世界語境、物理世界語境、文化世界語境和心理世界語境的角度分析了楊絳先生的文學語言藝術。從得體性原則來看,這部新作的語言得體性體現了楊絳先生一貫的藝術追求。
關鍵詞:《洗澡之后》 語言 語境 得體性
楊絳先生在103歲時發表了《洗澡》的續作《洗澡之后》。續寫經典的初衷是“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1]1《洗澡》對故事情節的勾勒就像中國水墨畫一樣寥寥數筆就把人物刻畫得十分傳神,而在人物命運和人物關系上的留白處理,雖然給讀者留下了無盡的想象空間,卻給作家留下了一絲隱憂。于是她決定續寫這個故事,為這部經典作品畫上圓滿的句號。楊絳先生是語文的高手,《洗澡》的語言藝術爐火純青,其語言特色一直為后學者所津津樂道。而《洗澡之后》愈發體現了繁華落盡見真淳的藝術境界,盡管呈現給讀者的不再是才情橫溢的妙語連珠和綿里藏針的反諷隱喻,但是其文學語言的得體性仍是她一以貫之的藝術追求。
以往我們以“修辭三性”——準確、鮮明、生動作為衡量修辭質量的標準。對此凌德祥(1987)指出:“從表達角度來看,只有一性——合適性。一切合意、合時、合地、合乎身份、合乎對象、合乎文體等等的表達,準確也罷,模糊也罷;鮮明也罷,含蓄也罷;生動也罷,質樸也罷都是合適的表達。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下,規范語法中所講的‘病句’,只要在表達中不能被其他所謂更合適的語句所代替,這種語句也可以合適地用于表達。”[2]凌德祥先生的“合適性”與王希杰先生(1996)在《修辭學通論》中的觀點近似,他提出“修辭的原則只有一條,那就是:得體性原則。一切其他的原則都從屬于這個原則,都是這個最高原則的派生物。這個最高原則制約著和控制著一切其他的原則”[3]343。他還指出“得體性就是話語對語言環境的適應程度。脫離了特定的語言環境,就沒有得體不得體的問題。”[3]346得體性是相對于具體語境而言的。王希杰先生把語境分為語言世界語境和物理世界語境、文化世界語境、心理世界語境。“四個世界”理論是得體性原則層次系統的劃分依據,他的零度與偏離理論、潛性與顯性理論也是以“四個世界”理論為基礎進行分析論述的。這三組概念與“得體性”這個修辭的最高原則構成了修辭學界著名的“三一”理論。本文擬從“四個世界”的角度賞析楊絳《洗澡之后》的語言得體性。
從語言世界語境的得體性來看,憑借作者深厚的語文功底和縝密的構思,《洗澡之后》遣詞造句仍舊保持精致淡雅的特點。從語境的層次來看,語言世界語境是小語境,通常通過上下文分析詞句的得體性。這個層次的語境包括語言材料語境以及語言風格語境兩個方面。從靜態的語言材料來看,小說的語言語音和諧、語義明確、語法通順。作為翻譯家和作家,楊絳的文字功底是很強的,偶有不完全符合現代漢語表達習慣之處,可能與她的方言背景有關系,如“姚太太心里踏實了,放放心心地收拾了家里的東西,搬往陸家去”[1]11,“許彥成很出意外,他看了姚宓交給他的地址”[1]25,其中“放放心心地”“很出意外”不符合普通話的語法規范,但不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從語體和風格來看,《洗澡之后》的語言仍不失典雅、細膩、平淡、含蓄的風格,而為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綿里藏針的言說方式在續作中卻不十分顯眼。楊絳先生慣用的反諷的手法在小說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比如“一九五七年早春,全國都在響應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1]61一節中運用了情境(形)反諷,把陸舅舅對于政治運動的態度和他個人的政治結局和人生結局對比形成了鮮明的反諷。而對于人物性情的描述則基本不再使用冷嘲反諷的手法,而是給予他們更多的寬容和體諒。比如,杜麗琳在前一部《洗澡》中的形象俗氣、造作得可憎,而在《洗澡之后》的杜麗琳雖“不幸劃為右派”,吃了趨炎附勢的教訓,卻也因此找到了意中人,與許彥成平靜分手。作者對這個人物似乎多了一些同情和克制,經歷了一次次運動讓杜麗琳有所收斂和成長,人物的性格會隨著情節的推進而發生變化是合情合理的。
物理世界語境的得體性包括語言的主體、對象、以及時間、空間、事件的得體性。楊絳先生在文論中曾說過:小說家構思時要把人物和情節“納入合情合理的軌道,使人物、故事貼合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因為故事必須合情合理,才是可能或必然會發生的事,我們才覺得是真事。人物必須像個真人,才能是活人。作者喜怒哀樂等感情必須放在活人心上,才由抽象轉為真實的感情,而活人離不開我們生存的世界”。[4]148可見,這是作家早已自覺遵從和實踐的寫作理念。小說中各個故事的前因、后果、時間、地點等情況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盡管作者強調故事是虛構的,廣大讀者還是覺得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客觀、真實、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處境和狀態,甚至有很多讀者會有意無意地把小說中的故事與作者親身經歷聯想到一起。雖然楊絳先生創作《洗澡之后》的動機是要保全姚宓和許彥成的清白以及他們之間的純潔的情誼,“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她在將人物的命運和故事情節推向預設的結局時,最大限度地顧及到了物理世界語境的得體性,并把故事中的小事件與時代的大事件巧妙地關聯起來,使故事更加真實可信。例如,小說開篇就是從搬家開始的,“這一帶房子,地契上全是姚家的,公家征用了”[1]1,“她(姚宓)說:‘當時為給媽媽治病,我急得沒辦法,匆匆忙忙地賣了(四合院),現在還能買回來嗎?’羅厚說:‘大概沒問題,舅舅面子大,關系廣,辦法多,什么都好商量。只是怕姚伯母吃虧了’姚太太說:‘吃不吃虧,我不計較,反正便宜的是公家’”[1]2。在這段對話中,巧妙地交代了事件發生的背景,姚家曾經顯赫的家世,家道中落后面臨的窘境,社會變遷給這家人帶來的生活和心理的影響,以及在事件中姚宓賣房子給母親治病、舅舅憑關系為他們買回四合院、姚太太對“吃虧”的淡然和無奈,都是在事件推動下的非常自然地表現出來的情節。楊絳先生講故事給人的印象是作家在老老實實、原原本本地交代一段歷史,介紹一群身邊的人物。她一向主張刻畫人物務求真實自然,高度重視情節設計要入情入理,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令“讀者不覺得那一連串因果相關的情節正在創造一個預定的結局,只看到人物的自然行動”。[4]188
文化世界語境的得體性包括時代、地域、民族、性別、年齡、職業、避諱的得體性。文化語境不僅對語言活動起到制約作用,對語義也有不可替代的解釋和說明功能。在《洗澡之后》一書中,文化語境是格外突出的。比如:姚家家道沉浮、姚家母女的小心謹慎都與時代背景有密切關系;杜麗琳與葉丹愛情表白的方式以及他們后來“偷偷”交往的方式與他們當時的身份和處境也十分契合;姚宓在婚前表現出的羞澀和矜持,與她的年齡、性別、出身和教育背景都非常符合。再比如:姚母得知陸舅舅死訊后不同意陳姨媽去吊喪的理由是,“你是剛來的客人,我們都是要對遺體扣頭行禮的,陸舅舅不能受你的禮,你只能算一個吊喪的客人”[1]66,寥寥數語,就讓事件的發展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禮儀禁忌。書中還描述了姚宓初次和圖書館館長談話的情形,“館長在沙發上坐了,也請姚宓坐。姚宓不敢和館長并排坐長沙發,拉過一張木椅,坐在館長的斜對面。”[1]12這個細節的描述恰如其分地突出了姚宓在館長面前舉止的得體性和她禮貌周全的知識女性的素養。接下來的朱館長的開場白也十分得體,“他慢吞吞地說:‘當初令堂要求另設‘紀念室’,本館從來沒有個人的‘紀念室’,很抱歉。不過府上捐贈的善本、孤本,都有姚騫先生的印章,我們一律不出借的。’請告訴令堂,請她放心。”[1]12這段話既符合了朱館長作為圖書館領導的身份,又不失老知識分子應具備的談吐修養,還體現了他對圖書捐贈人家屬的尊重,以及二人初次見面時的客氣的成分。小說中值得細細品味的精彩段落很多,因作者對文化背景的準確把握,才能入情入理地表現人物和情節。當許彥成在圖書館遇到姚宓并得知她搬家后的地址,便說:“告訴姚伯母,這星期六準來看伯母”[1]24,許彥成說得是“告訴姚伯母”,實則是告訴姚宓,他說“看伯母”,表現的卻是對姚宓的關心,同時這句話又符合二者的身份和禮數。許彥成并沒有隱瞞此事,他回家后對杜麗琳說“我星期六進程去看姚伯母,你也同去嗎?”[1]28他沒有說“咱們去”或“我能不能去”,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場,讓杜麗琳有知情權,同時也讓她有自己決定是否隨他前往姚家的選擇權。杜麗琳當然是知趣的,并沒有去姚家。但許彥成見到姚母后,還是說了一句“麗琳有事不能來,叫我問伯母好”[1]30,看似不經意的寒暄之詞,卻表現得非常得體,完全符合當時的人物的關系和人物身份,也符合作家對兩個主人公發乎情止乎禮的純潔情誼的預設。
從文化語境的角度仔細推敲,我們還發現小說有一些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地方。首先,小說的某些細節值得商榷,比如:許彥成在向伯父伯母稟告自己離婚一事之后,得到伯父的回信,其內容是“伯父恭喜侄兒終于甩掉了那個俗氣美人。”[1]116從民族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長輩以書信的形式祝賀晚輩離婚,這不太符合傳統的家庭觀念,從杜麗琳的性格特點來看,她在許家長輩面前的表現不至于讓他們如此嫌棄,起碼在前文沒有足夠鋪陳的情況下,這樣的情節有些突兀。另外,根據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許彥成和姚宓領結婚證書、籌辦婚禮、布置新房、宴請賓客都在一日完成,且不說這種行事作風不符合姚家母女和許彥成謹慎持重、禮貌周到的風格,當時結婚需要獲得“單位批準”等組織程序,恐怕不是想領結婚證就能立刻辦到的?從嚴格的時代背景來看,小說的語言運用也存在個別瑕疵,比如姚宓給李佳看羅厚的照片時,“小李說‘他好帥呀!可是他完全沒有帥哥那種氣派,他不臭美’”[1]40。“帥哥”是近年來流行的新詞語,該詞在五十年代的人物對話中出現就顯得太合適。
人類的語言行為是心理活動的反映,心理世界語境涉及的因素非常復雜。概括來講,心理世界語境的得體性體現為個人心理因素與社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下的語言行為的可接受性。就具體的文學作品而言,人物的語言行為能夠恰切地傳達出一定的態度和心理意識,且能夠被接受主體所接受,那么,我們就會認同其心理語境的得體性。人類的普遍心理是趨吉避兇,經過“洗澡”運動之后,大家的防范心理普遍增強,但他們仍會因個性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姚宓在外更加謹慎安分,在運動中“只求‘安居中游’”,許彥成更加“淡定低調,裝得自己庸庸碌碌”,姜敏因被劃為右派而自殺,朱千里因老婆把動員他大鳴大放的人趕走而逃過一劫,愛出風頭的杜麗琳在運動中盲目跟風,說錯了話而被勞動改造,在后文中她與新的意中人葉丹在鄉下勞改時發生的愛情雖不失真摯卻也不得不遮遮掩掩。這些行為和心態正是社會心理與個人心理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時代背景下恰恰凸顯出姚家、陸舅舅家、李家的朋友圈的情誼是彌足珍貴的,也透露出作家對人性的信心和對人間美好情誼的堅守。當然,其信任程度也體現出了一定的“得體性”,比如“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運動中,王正、馬任之“和姚太太交換過對整風運動的個人意見”[1]61“陸舅舅一度很興奮,很熱衷,覺得這是國家大事。姚宓不敢把王正、馬任之他們的意思說出來,可是愛護舅舅,還是勸了一句:‘舅舅,說話小心啊’。”[1]62這個情節非常符合人物關系,也為下一步情節的發展埋下伏筆。還有,在李佳談及父親對許彥成的看法時,她察覺到了姚宓“臉都紅了”,“她懷疑姚宓看中了許先生,或者許先生看中了姚宓”,[1]38她不便當面求證而是繼續引用父親的話試探,姚宓卻只裝作不經意地答話并急著改換話題。作家在對話中把年輕女性之間的微妙心理活動處理得十分巧妙,也表現出兩個女孩子的敏感聰慧以及交流的分寸感。小說中類似的心理活動描寫非常豐富,心理活動是這部小說推動情節發展和刻畫人物品性的重要手段。
作家錘煉語言,讀者品味語言,語言決定了作品的風貌。研究語言自身固然重要,而我們研究語言賴以存在的語境以及語言與語境的關系,使我們得以在更廣闊的視域中理解語言的真諦和魅力。《洗澡之后》語言的得體性與楊絳先生一貫堅持的“真實”的寫作,以期“貼合人生真相”,表現人情世態的藝術追求是一致的。在作品中她力求使“每個人的一言一行和內心的任何波動,都籌劃妥帖,細事末節都不是偶然的”,“把整個故事提煉得精警生動,事事都有意義。小小的表情,偶然的言談,都加深對人物的認識,對事情的了解”[4]188。《洗澡之后》于《洗澡》不是畫蛇添足也不是錦上添花,她只想保全那些可愛的人物,保全人和人之間的純潔的情誼。兩部小說的語言風格不盡相同,但從修辭的得體性的原則來看,兩部作品的水準是一貫的。
參考文獻
[1]楊絳:洗澡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8月版。
[2]凌德祥:論語言的表達,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2期。
[3]王希杰:修辭學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
[4]楊絳:楊絳作品集,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作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