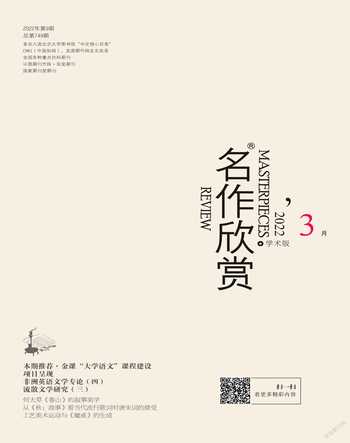異托邦、非場所與擬像的狂歡


摘要:《這不是一只煙斗》是福柯著名的藝術評論文本之一,在這一文本中,福柯通過對馬格利特的兩幅畫作《形象的背叛》和《雙重神秘》及其他畫作的“六經注我”式評論,完成了對傳統圖像與文字關系的顛覆,這同時是對傳統形而上學表象秩序的意識形態批判。福柯認為,馬格利特的畫作摧毀了表象秩序所賴以建立自身的共同場所,敞開了根基撤離的非場所,而這又同福柯哲學中的“異托邦”“擬像”等概念息息相關,典型地呈現了后現代哲學對差異重復、偶然性、不確定性、雜多性的關注。
關鍵詞:《這不是一只煙斗》福柯異托邦擬像
對藝術尤其是繪畫的關注構成當代法國哲學的顯著特征之一,梅洛·龐蒂、福柯、德勒茲、德里達、馬里翁等著名哲學家均表現出對繪畫的極大興趣,更有甚者直接參與到繪畫的創作實踐中。 a 他們有關繪畫的論述明顯溢出了傳統的藝術評論,以“六經注我”的方式完成了對自身哲學架構的有機支撐,如克羅索夫斯基、福柯、德勒茲的差異哲學,馬里翁引領的所謂現象學的神學轉向,均與對繪畫的介入息息相關。本文將深入福柯繪畫批評的經典文本《這不是一只煙斗》,透視其背后的哲理蘊含與哲學動機。
《這不是一只煙斗》寫作于1968年,出版于1973年,是對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的兩幅畫作《形象的背叛》和《雙重神秘》及其他系列畫作的評論。在《形象的叛逆》中,馬格利特精心繪制了一只煙斗,卻匪夷所思地在其下方配文“這不是一只煙斗”,而在《雙重神秘》中,馬格利特將前一幅畫作置于三腳架上的畫框中,在畫框之上又畫了一只更大的煙斗。通過對馬格利特畫作的戲劇化解讀,福柯闡述了其對原本——摹本等級關系的顛覆,以異托邦的方式敞開了不可化約的、為偶然性所支配的無限可能性。
一、圖形詩的解體:傳統圖文關系與表象秩序的崩潰
福柯的問題意識始于《這不是一只煙斗》第三部分《克利、康定斯基、馬格利特》中對15至 20世紀主宰西方繪畫的兩項原則的指認。其一是“確認形體再現(它強調相似性)和語言指涉(它排除相似性)之間的分離”。“人們通過相似性來觀看,通過差異性來言說,結果是兩個體系既不能交叉也不能融合。”b 在這一傳統中,圖像符號和語言符號是兩套各自獨立的符號體系,前者通過相似性從形體上再現其對象,至于后者,“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是任意的”c。而在二者共同出現的場合,二者總是受到一定的等級秩序支配,“總有一種順序,從形態到語言或者從語言到形態,按等級把它們排列起來”d。例如在圖畫的題詞、說明性文字中,文字受到圖像的支配;而在書的插圖中,圖像受到文字的支配。其二是“把相似與再現性關系的確認這二者等同起來”e。圖像同其對象的相似同時便意味著命名與確認的完成,話語悄悄潛入了相似性關系中,完成了“是”這一確認動作,而在帶有標題或指示性文字的圖像中,文字則光明正大地扮演了確認者的角色。
在此,福柯無意標識兩套符號系統的客觀差異和各自的分工,恰恰相反,他正是通過揭示潛藏于“常識”中的觀念構型來說明貌似不證自明的秩序對于藝術實踐之可能性的限定。而保羅·克利和康定斯基無疑突破了這種限定。(關于克利和康定斯基的革命性實踐,福柯分析已備,本文不再贅述)福柯說明的兩項原則中,兩套符號系統彼此涇渭分明,卻又聯結形成各司其職的關系,這早已成為常識,它井然有序地保證了符號再現的統治地位。正如福柯為德勒茲所寫的書評《哲學劇場》中所言:“常識,就其識別力而言,就其對距離的估量,就其進行同化和分隔而言,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劃分力量,而正是這種常識在再現的哲學中占據了統治地位。”f而使得這一秩序得以可能的,是被福柯稱為“共同場所”的可能性條件。福柯舉了帶插圖的頁面上的文字和插圖中間出現的空白作為例子:“在這個幾毫米寬的空白處,在酷似岸邊無聲的細沙上,詞語和圖形結成了指示、命名、描述、分類等各種關系。”g 這一空白隱喻使得表象秩序以自明的效果呈現出基礎性平臺。如同“光”在西方哲學史上的作用一般,它雖自身不可見,卻是萬物得以可見、邊界得以明晰的前提條件,只不過這一可見性在福柯看來不過是一種光之暴力,是偽裝的同一性等級序列,這一序列試圖將純粹的事件歸納為規范化的概念體系。他在《哲學劇場》中論述了三種試圖對事件進行概念化的哲學,即新實證主義、現象學和歷史哲學,三種哲學分別建構了以世界、自我和上帝為中心的牢固秩序,將事件強行還原成為同一性的從屬和派生。h 而傳統的文圖關系同樣并非基于符號的“本質”,不過是一種被建構的觀念形態。
在定位了傳統文圖關系的語境下,也就不難理解福柯為何要將圖形詩作為剖析馬格利特作品的切入點。圖形詩指的是將詩行以圖形的形式排版,以求詩作呈現出來的視覺外觀同其語義指涉相吻合的詩歌創作,典型作品如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的詩集《圖形詩》。圖形詩消除了文字與圖像賴以區分的間隙,表面上同克利和康定斯基的創作實踐類似,突破了傳統的窠臼,“試圖游戲般地消除我們字母文明中最古老的對立:展示與命名、繪制與言說、重現與表述、模仿與意指、觀看與閱讀”i。然而在福柯看來,這反而是上述古老對立的極端化呈現。首先兩類符號系統的對立并沒有真正消弭,它產生了一種“圖文二象性”的效果,如同思想實驗“薛定諤的貓”一樣,既是圖像形式的文字,也是文字繪制的圖像,其具體的錨定取決于觀測者——然而只能二者擇其一,因此“圖形詩徒有其表,它那鳥、花或雨的外表不會說:‘這是一只鴿子,一朵花,一場正在落下的傾盆大雨。’而當它開始講述,詞匯開始說話并表達一個意思的時候,鳥兒已經飛走,大雨已經停止……這可見和可讀的同一物,在視覺中被封口,在閱讀中被隱形”j。其次兩類符號系統非但沒有改變各自在傳統文圖關系中的定位,反而在圖形詩中達成了最精密的合謀。圖形通過外形、詞語通過指涉完成了對事物的雙重捕獲,“用雙重措施保證了話語自身或單純的圖畫都無法實現的這一收獲……這是雙重的陷阱,不可避免的羅網”!1。將事物牢牢固定在既定的意義網絡之中,逃遁無門。
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重新打開了圖形詩所消弭的文圖之間的間隙,以看似最古板的方式,即圖像下方配文的外觀呈現在觀者眼前,貌似是傳統的回光返照,卻以戲仿的方式無情地揭穿了傳統圖文關系虛偽的面具,“它外表看來是回到了之前的布局,重拾其三項功能,但目的是顛覆它們,并由此打亂語言和圖像之間的所有傳統關系”!2。這一顛覆的關鍵在于一個簡單的否定,首先文字與圖像之間的關系被這一否定所挑撥離間,由相互配合、各司其職轉變為極端的不信任甚至互相攻訐,文字取得了脫離曾經需要為其命名之物的自主性,而圖像則執著于自身的惟妙惟肖,拒絕語詞的冗余描述。其次,代詞“這”的含混指涉無疑引發了圖像和語詞的交錯,使得其間的關系變得撲朔迷離,由此引發出如下圖所示的三種解讀方式。
“陷阱縱向遭到破壞,圖像和文字各自從自己的方向,按照本身固有的引力跌落下去。它們不再有共同的空間,不再有一個可以相互影響的場所。”!3圖像和文字既終止了合作,又糾纏于不確定的關系之中,曾經出現于文圖之間并使得其區分與并存得以可能的空白,如今坍塌為“一個不確定的模糊的區域…… 更應該說這是空間的一種缺失,是書寫符號和圖像線條之間‘共同場所’的刪除”!4。而在《雙重神秘》中,福柯將三腳架上的畫作置于一個虛構的課堂中,認為該場景“為重建圖像和語言的共同場所做了必須所做的一切”!5。然而這一重建的努力遭遇的是更為刻薄的諷刺,確定性平臺的自負再次面對無可挽回的結局:“共同的場所——平庸的畫作或者日常的課程——消失了。”!6
簡言之,圖像與文字在馬格利特的畫作中喪失了賴以聯結在一定等級秩序中的共同根基,構成了非場所中的非關系。由此,畫作也就暴露了傳統再現秩序的非自明性和非必然性,構成對傳統的反諷。
二、擾亂人心的異托邦:差異的獨立宣言
福柯在文本中一再提及的“共同場所”的消失,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對馬格利特繪畫的評論中,而是植根于福柯哲學的整體框架,指向其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即異托邦(les hétérotopies)。
福柯最初提出“異托邦”是在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前言中那個著名的大笑場景,因其看到博爾赫斯的書中提及某部中國百科全書里的另類動物分類法。這種分類法沒有統一的標準,而是深陷在對事物的雜多感性體驗中:“動物可以劃分為:①屬皇帝所有;②有芬芳的香味;③馴順的;④乳豬……”!7在這里福柯看到了一個語言的他者構境,一個沒有家園和場所的語詞的星叢,這一他者使得西方人看到了自身思想的邊界,看到了一種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事物失去了賴以井然有序被分類排列的場基:貫穿于博爾赫斯列舉中的怪異性則在于這樣一種事實:使得這種相遇得以可能的那個共同基礎已經被破壞了。……除了在語言的非場所,它們還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并置在一起呢?……被撤銷的是著名的“手術臺”……另一重含義指的是“圖表”(tableau),它使得思想去作用于存在物,使它們秩序井然,對它們分門別類,依據那些規定了它們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名字把它們組集在一起。有史以來,語言就在這張圖表上與空間交織在一起。相對于同一性邏輯統攝的烏托邦,這樣一個異托邦無疑是干擾思維的:“異托邦是擾亂人心的,可能是它秘密地損害了語言,是因為它們阻礙了命名這和那,是因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詞,是因為它們事先摧毀了‘句法’。……異托邦(諸如我們通常在博爾赫斯那里發現的那些異托邦)使語言枯竭,使詞語停滯于自身,并懷疑語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異托邦解開了我們的神話,并使我們的語句的抒
情性枯燥無味。”18在 1967年世界建筑學會的演講稿《另類空間》中,福柯重點闡釋了“異托邦”概念的空間維度,強調的同樣是同質化的既定秩序之外的不可化約的異質存在,以及對使既定秩序得以可能的共同場所的質疑,正如福柯研究專家阿蘭·布洛薩所指出的:“異托邦的功能和效果是質疑,即質疑被看作自然和合法空間的所有不證自明的樣式,質疑這些自然和合法空間之權力和權威的所有不證自明的樣式。異托邦的本質就是向權力關系、知識傳播的場所和空間分布提出爭議。”!9馬格利特的兩幅畫所產生的同樣是異托邦的效果,它損害的正是傳統的“這是”的命名和確認,摧毀的正是圖像和語言得以被比較“同”和“異”的平臺、得以找到確定的一席之地的“圖表”,它打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非場所”,在文圖關系的不可能之域游蕩,在思考的邊界處向秩序和權威提出質疑,乃至嘲弄。
而這一理論取徑又同法國哲學對于差異的理解相關聯,文森特·德貢布在其《當代法國哲學》中描述了這一理解:“此時的問題是為思考一種非矛盾、非辯證的差異開辟道路,這種思考不把差異視為同一性的簡單對立,也不強求在差異自身中看到與同一性的‘辯證’統一……與之相比,先前所有的討論都仿佛是搖晃不定的指南針。”@0在福柯處也不例外,差異正是擺脫了同一性的統攝的差異,差異是差異自身的絕對存在。思想應當擺脫作為“差異的支撐物、差異的基地、差異的限定者、差異的主宰”的統一性,轉而“以差異的方式來領會差異,而不是尋求差異之下隱藏的共同要素”,如此,“將我們帶向概念的一般性的差異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作為純粹事件的差異”@1。這也正是摧毀共同場所的意義所在,擺脫先驗范疇的頤指氣使,擺脫偽裝為自然的知識構型,敞開被屏蔽的“游牧性的雜多”,使其“在重復的游戲中堅持存在和持續存在”@2。
“在哲學中‘解構’的目的就是顯示哲學話語是如何被建構的。”@3對于福柯而言,批判的目的正如他在《何為啟蒙》一文中指出的,在于找出“在對于我們來說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東西中,有哪些是個別的、偶然的、專斷強制的成分”,“而是從使我們成為我們之所是的那種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們之所是、我們之所做或我們之所思的那種可能性”@4。馬格利特的畫作所證明的,也正是在符號領域革命永恒的潛在性,它是擾亂人心的,然而正是這種異托邦式的擾亂不斷動搖著秩序的根基。具體的藝術實踐可能會被收編,成為新的神話,如喬納森·卡勒在論述羅蘭·巴特時所言:“消除神秘性的努力并沒有真的消滅神話,反而賦予了它更大的自由……最堅決的反文學性的運動并沒有消滅文學,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流派。”@5但異托邦的“清單永遠也不會完結。每個人都能在此狀況下對之有所體會:一旦開始被這個主題糾纏,就會在閱讀過程中、在旅行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異托邦經驗”@6。
三、骰子一擲:哲學劇場中的擬像之舞
在《這不是一只煙斗》的后半部分,福柯區分了兩個對立的概念,即仿效(la similitude)和相似,其區別如下表所示:
在此,福柯的矛頭顯然對準了西方哲學的柏拉圖主義傳統,這也是馬格利特的畫作所突破的傳統文圖關系背后的終極背景觀念,正如他在法蘭西學院講座中提出的:“在現代藝術中有一種反柏拉圖主義…… 反柏拉圖主義即:藝術作為讓一個場所生存的基本狀況涌現出來,被剝光。”@7柏拉圖在《理想國》第十卷給定了三張床,分別為神、木匠、畫家所制造,神只制造了一張“本質的床、真正的床、床本身”,木匠是“具體的床的制造者”,而畫家則絕對不能被稱為制造者,只能被稱為模仿者,他進而推及悲劇家,認為畫家和悲劇家“與真理隔著兩層”,只是對實在顯示出來的影像進行模仿。@8這是一個從原本到摹本的森嚴的等級序列,本原物與派生物沿著單向的價值鏈條謹慎地恪守著自身的位置,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則就是僭越,這是真理的政治學。而仿效則標志著一種反柏拉圖主義,秩序瓦解的每一個碎片都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其間的任何關系都變得可逆而不確定,秩序井然的空間瞬間墮入一種極端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以《雙重秘密》為例,畫中的每一個成分圍繞“這不是一只煙斗”的判斷均取得了話語權,從而形成多達七種聲音:畫中煙斗的聲音、畫框上方煙斗的聲音、文字的聲音、被畫框圈起的煙斗及文字共同的聲音、兩只煙斗共同的聲音、文字和上方煙斗共同的聲音以及漂浮不定的畫外音。“要想摧毀仿效被相似性的論斷所囚禁的堡壘,一個也不能少。”@9觀者在這個飄忽不定的空間中體驗影像的自由舞動,每一種關系的聯結都稍縱即逝,無始無終,方生方滅。這即是福柯、德勒茲、德里達、鮑德里亞等人均論述過的擬像的特征:沒有本原,只有無限增殖的差異與重復。
在文本的最后,福柯以重復收束全文:“這一天終將到來,仿效沿著一個長長的系列不確定地轉移,圖像本身帶著自己的名字,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Campbell,Campbell,Campbell,Campbell。”#0 這是對安迪·沃霍爾的作品《坎貝爾的湯罐頭》(Campbell’sSoup Cans)的致敬,該作以批量生產的湯罐頭的極端重復為表現內容。福柯在《哲學劇場》中論述“非范疇的存在”時重點提及了他的藝術實踐。范疇作為知識的先天形式扮演了頤指氣使的發號施令者與對錯判定者的角色,“在知覺中確立了相似的合法性”#1,這無疑是柏拉圖主義的秩序維護者。而在非范疇的存在,例如沃霍爾的“湯罐頭”中,曾經的愚笨被接受,“我們看見它,我們重復它,而且以柔和的方式,我們呼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2,所謂的深度被消弭,純粹事件的無政府主義游牧被開啟,“這是差異帶來的震撼。一旦悖論顛倒了再現的表,緊張癥就在思想的劇場中上演了”#3。而支配這一劇場的不是先在的“劇本”,而是偶然性法則:“思想作為事件就像擲骰子一樣獨特”#4,“擲骰子的結果,另一場游戲的命運……它用心地在戲劇中重復自身;它將自身拋出了骰子盒”#5。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馬拉美那令法國當代哲學家癡迷的詩歌文本《骰子一擲永遠取消不了偶然》,這一文本同樣是圖形詩解體的產物,它讓讀者墜入最極端的不確定性中: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詞的位置、大小及內容,唯有在純粹偶然性的深淵中持續墜落。馬拉美、馬格利特、安迪·沃霍爾,這些文學藝術的實踐者,同當代法國哲學家一道,將哲學從立法者與奠基者的神壇請入了劇場,以扮相的方式呈現在這一持續動蕩、危險而迷人的場域。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將德勒茲的哲學文本以及諸多文學藝術作品指認為哲學劇場,而其自身的行文同樣充滿戲劇性。如在《哲學劇場》中提到的戰爭與課堂教學場景,也分別出現在《這不是一只煙斗》中對《形象的叛逆》和《雙重神秘》的分析中,尤其是后者,學生的嘲弄和教師的窘境被描述得活靈活現,煞有介事。馬格利特的畫作未必暗示了戰爭和課堂教學的意圖,然而并不妨礙福柯作如此的解讀,正如博爾赫斯的中國百科全書未必不能是杜撰的一般。羅蘭·巴特在回應比卡對“新批評”的抨擊時指出:“今天人們責難新批評,并不是因為它的‘新’,而是由于它充分發揮了‘批評’的作用,重新給作者與評價者分配位置,由此侵犯了語言的次序。”而“批評所能做的,是在通過形式——即作品,演繹意義時‘孕育’出某種意義”#6。既然可能性高于既定性,批評未必不能成為一種創作,福柯在《這不是一只煙斗》文本末尾與安迪·沃霍爾的互動,同樣以重復的方式展現,這是在召喚安迪·沃霍爾本身的在場,也是一種哲學文本以其自身的形式成為藝術品的沖動。
a如尼采主義哲學家皮埃爾·克羅索夫斯基同其弟巴爾蒂斯·克羅索夫斯基都是著名畫家。
〔法〕米歇爾·福柯:《這不是一只煙斗》,邢克超譯,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第38頁,第39頁,第28頁,第17頁,第22—23頁,第17—18頁,第18—19頁,第28頁,第28—29頁,第30頁,第33頁,第69頁,第79頁。譯文有所改動。
c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2頁。
〔法〕米歇爾·福柯:《哲學劇場:論德勒茲》,見汪民安主編:《生產第五輯:德勒茲機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頁,第192—193頁,第 198頁,第201頁,第201頁,第204頁,第205頁,第 195—196頁,第206頁。
〔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頁,第3—5頁。
〔法〕阿蘭·布洛薩:《福柯的異托邦哲學及其問題》,湯明潔譯,《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法〕文森特·德貢布:《當代法國哲學》,王寅麗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頁,第109頁。
〔法〕米歇爾·福柯:《何為啟蒙》,見杜小真編選:《福柯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頁。
〔美〕喬納森·卡勒:《羅蘭·巴特》,陸赟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頁。
〔法〕米歇爾·福柯:《說真話的勇氣:治理自我與治理他者Ⅱ:法蘭西學院講座系列,1984》,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頁。
〔古希臘〕柏拉圖:《國家篇》,王曉朝譯,見《柏拉圖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617頁。
〔法〕羅蘭·巴特:《批評與真實》,溫晉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第45頁。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德勒茲美學研究”(13071056)階段性成果
作者:尹昌鵬,南京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當代法國文論。
編輯:曹曉花E-mail: 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