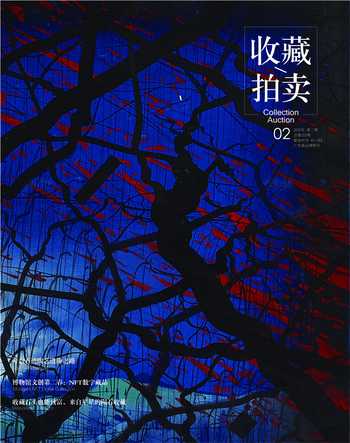藝術圈“吃快餐”,遠離了傲慢還是加深了偏見?
馮善書
中國的大眾藝術品消費市場行情已經啟動。這是近兩年筆者浸淫各地藝博會和一些藝術電商平臺得來的直觀感受。不管是從社會關注度,還是從實際交易量來說,以那小先、陳建周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畫家,都已經具備相當的流量和能級。資深的買家和消費者,可以在這個名單加上更多的名字。特別是借助了“數碼版畫”這一可以批量復制的杠桿工具以后,他們獲得了比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國內首先吃螃蟹、靠模仿美國當代藝術起家和爆紅的那批先鋒藝術家無與倫比的市場活躍度。當然,這些年輕的網紅畫家的作品多以一次性交易為主。
在消費市場上討飯吃的藝術工作者,只要抓住了流量,就可以快速把自己的社會知名度變現為可見的商業利益,因而其最突出的市場特征就是以量取勝。以量取勝并不一定要薄利多銷,他們的數碼打印作品,在京東和Artand等平臺上,可以賣到幾千上萬元一幅。這類作品因為不需要像傳統雕版版畫那樣經歷復雜的制作工序,因而,可以在現代印刷工業流水線上快速生產復制,每一款限量版數從幾十到數百或上千不等。
這些流量畫家的生產方式也非常相似且具有代表性。他們像早期的一些曾經被評論家吐槽為“賣藝術快餐”的波普藝術家一樣,將一些在社會或藝術圈已經有廣泛知名度的人物、作品和商業標簽“信手拈來”,普遍以模仿、復制、拼貼、改編、演繹、調侃等方式和手法進行加工和再創作,從而可以快速、批量地向市場推出帶有自己署名的作品。
“90后”畫家那小先非常巧妙地借用名人名作的既有知名度和那些讓人耳熟能詳、過目不忘的文化標簽、藝術元素和風格特征,找到了一條快速被別人接受和認可的辦法,并創造出驚人的市場效益。陳建周作品中的經典形象則是《西游記》里的唐僧、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他的慣用手法與那小先如出一轍。除了那小先和陳建周兩位,我們可以從知名美院或各地畫院、畫廊的簽約畫家里邊找到許多靠類似的手段在市場上揚名立萬并賺得盆滿缽滿的藝術工作者,有的甚至編造了一個藝名來闖蕩市場,但依然不妨礙他們站在藝術消費的風口上快速和大量收割商業利益。
當然,他們自己不會說自己是在模仿、剽竊和改造,而更習慣說自己是以再創作的方式向經典人物和名作致敬。不管以什么樣的新鮮概念來包裝和美化自己的行為,都逃避不了文化圈對他們是“傍名人”和“搞藝術快餐”的指責。
值得一提的是,與安迪·沃霍爾等早期的波普藝術家不同的是,中國的新生代“快餐藝術家”普遍放棄“運用廢棄物、商品招貼電影廣告、各種報刊圖片作拼貼組合”等綜合加工的辦法——那樣實在太費勁了,復制起來也不方便。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在電腦上制作,或者把自己的手工繪畫作品高清掃描之后再進行數碼打印。
數碼版畫,也被稱為數字版畫、數位版畫、電腦版畫或計算機版畫。說白了,就是用科技含量高一點的高清數碼打印機,在一些特制的版畫紙上直接打印出來作品。與傳統的木版、銅版、鋼版、石版、膠版印刷不同的是,數碼版畫的母版可以電子化,有的直接就是在電腦上繪制的,不像傳統雕版那樣會自然損壞,因而理論上是可以無限復制的。就算作者第一批進行了限制印刷,但因為電腦打印輸出實在太方便了,將來有人如果想超量復制其實非常方便快捷,其制作出來的翻版實際非常難以證偽。
正因如此,這一新興藝術形態在市場上仍然是極具爭議的。除了有限量簽名以外,它跟我們平時看到的畫冊復制品沒什么兩樣。我買過一些藝術家的數碼版畫作品,不管作者標榜的“打印機”和進口畫紙再怎么高級,它在畫面上傳遞出來的那種味道仍然比不上傳統手工印刷的作品那么有溫度和力度。找一塊放大鏡,只要放大到幾十倍,它就變成了千篇一律的點陣圖。
誠然,任何一個成熟的商業市場,都避免不了投機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投機確實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促進藝術消費市場的繁榮,甚至在加快當代藝術對年輕一代的普及教育。不管是那小先,還是陳建周,他們都非常用心且巧妙地把傳統和當代的藝術元素融合運用到不同的作品,形成了一系列可以在年輕社會群體中廣為流傳的藝術形態。必須承認的是,年輕一代有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需求,他們成長和生活在一個信息傳播和交流比以往更快、而且科技發展瞬息萬變的社會,面對物質過盛和信息爆炸的時代,他們不可能重蹈我們過去的那種生活方式。
因而,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看到這些快餐藝術的積極一面。但是,從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角度來說,一旦這種行為現象成為藝術和商業的主流的時候,又非常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畢竟吃軟飯不可能吃成一個藝術強國,僅僅靠消費市場也支撐不了中國藝術從傳統走向當代并不斷融合發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