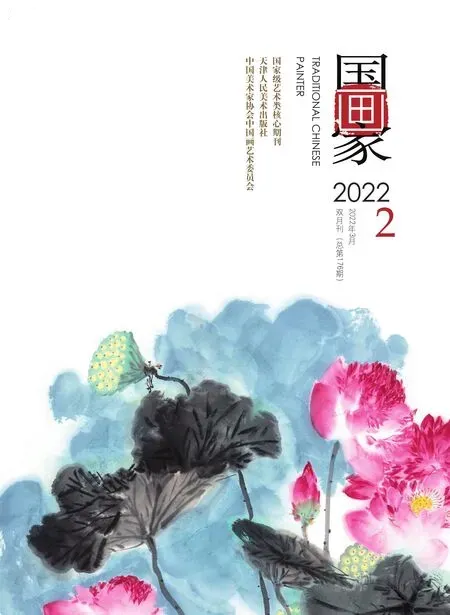莫高窟北周第428窟故事畫的“動勢”理念研究
西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 郭兆龍
一、莫高窟北周故事畫的形成
“刻木為佛,以形象教人”,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多通過繪畫、塑像等藝術形式傳入,因而又稱為象教。印度佛教本是“以塔代佛”進行禮拜,直到犍陀羅藝術受希臘藝術的影響,“英雄式”佛像出現;逐步影響到了龜茲及敦煌一帶,楚王英至桓帝、靈帝時代,禮拜佛像成了禮拜佛陀的主要形式。
佛教造像最早出現以單畫面為主,塑像也多以獨立方式出現。犍陀羅藝術最早禮拜對象以佛塔為主,佛本生故事、本行故事等都是作為塔的浮雕而出現。佛教故事主要包括佛傳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因緣故事,為便于傳教,壁畫中開始呈現。莫高窟壁畫中表現佛教故事畫,一方面,受到西域石窟的影響,另一方面,故事畫的形式在中國漢代就已出現,漢代“事死如生”,墓室壁畫、畫像石與畫像磚就有宣揚帝王賢臣、仁孝禮制的故事畫。莫高窟故事畫自北涼就已出現,至唐才逐漸減少。北周428窟是北周典型的中心柱窟,故事畫分布在四壁,東壁有薩埵太子本生圖、須達拿廣行布施圖,北壁畫有降魔變等,內容宏富。
二、畫面中的“動勢”理念
“動勢”在造型藝術中主要指使對象具有動感而言,畫家通過變形、夸張、模糊、連續等方式,利用視覺神經學、心理學等科學,使得靜止的畫面造成運動的視覺感受。立體的表現有助于畫面“動勢”的呈現,而立體化的呈現主要靠透視法,北宋郭熙“三遠法”透視使得山水空間層次明朗、豁然大氣,西方文藝復興“成角透視”“隱沒透視”等使得畫面更加真實,但真實不等于動勢。早期繪畫的平面式呈現依然能夠表現出畫面的生動,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彩陶就開始嘗試表達人物的運動,馬家窯文化彩陶《舞蹈紋彩陶盆》盆內壁描繪了三組手拉手踏歌而舞的人物形象,其中每組外側兩人外手臂均繪制兩根線條,像是表現頻繁的舞蹈動作,這是在畫面上表現運動最初的嘗試;四川漢代弋射收獲畫像磚中獵人張弓欲射的姿態也以夸張手法表現其動勢。

對于動勢,更在于外在形式的表達。拿木棍與繩子來比,曲線相對于直線更有動勢,莫高窟連環故事畫以山樹組合構成曲線來分割畫面,極具動感;四方建筑對于江南園林,氣勢上也許咄咄逼人,但江南園林的動勢及韻律則是更勝一籌;20世紀未來主義畫派巴拉《拴著皮帶的狗的動力》表現了正在行走的人和狗,可見,重復連續性的表現亦可增強動感。
三、北周428窟故事畫“動勢”表現
(一)莫高窟北周428窟藝術特征
第428窟為莫高窟最大的中心塔柱窟,經甬道進入窟內,南部為人字披,此時洞窟形式已受到中原式建筑的影響,窟內設有中心塔柱,塔柱四面各開一龕,信眾繞塔禮拜。造像方面比起北魏的“秀骨清像”,北周形象表現面型方圓,整體質樸厚重,衣飾方面保留著“褒衣博帶”的特征,壁畫人物暈染更偏向西域式畫法。
(二)東壁《薩埵太子本生圖》
《薩埵太子本生圖》(圖1)位于428窟東壁門南,畫面以長卷式構圖表現,異時同圖,共有三層,講述薩埵太子野游,遇見餓虎饑腸轆轆,為救回餓虎,縱然躍下,舍身飼虎,尸骨被人們起塔供養之事。畫面以山川樹木分割出騎馬出游、舍身飼虎等多個場面,視線自上而下依次是:第一層從右往左、第二層從左往右,第三層再從右往左,整個構圖呈“S”形動勢。
畫面第1、2情節表現三王子告別父母出游,三王子跪拜與騎馬出行,這種“勢”是由“重復序列”而體現的,同種樣式表現人物,能更清晰地體現人物之間的關系。此時背景的山川樹木是靜態的、筆直的,以靜顯動,表現了一種正常的運動狀態,畫幅上方有老虎逐鹿,此場景的老虎雄壯有力。第3、4場景以不同的姿態表現了三兄弟射靶訓練以及兄弟繼續前行。第5、6場景表現三兄弟見餓虎,薩埵囑二兄先回。第7場景薩埵脫衣躺到虎旁,任其食肉,此時薩埵雙臂舒展,可見他面對死亡的坦然,更能體現出“我佛慈悲”及“眾生平等”的理念。此時的“動勢”是由薩埵舒展的雙臂體現的,老虎雖體型較大,但瘦骨嶙峋,此時的老虎形象與第二場景的“老虎逐鹿”中的虎又是表現有別,也可與三太子馬的形象作為對比,馬雄姿勃勃,老虎虛弱無力,形銷骨立。第8場景跳崖舍身,餓虎嗜血食肉,這種餓虎食肉的動勢也像是“降魔變”的向內集中式。第9、10場景是二兄見弟尸骨,難過至極,飛馳宮中。第10場景為了表達兄弟之急切,馬的步伐更加矯健,馬蹄騰空的高度比出游時馬蹄高度要高很多,有風馳電掣之勢,為了表達速度,周圍樹的姿態跟馬動了起來,表現得極為傾斜,對比襯托,很難想象北周藝術家構思如此縝密。第11、12場景表現了稟告父王以及收尸骨起塔供養的情景。
(三)北壁“降魔成道圖”
北壁東起第二幅是《降魔成道圖》,降魔變最早見于印度桑奇大塔的雕刻。北周428窟降魔變以單幅形式描繪了群魔為阻止釋迦牟尼成道而進行施法作惡的場景。構圖呈中軸對稱式,釋迦牟尼結跏趺坐于畫面中間,鎮定自若,群魔面目猙獰,施出武力、魔力襲擊釋迦牟尼,但依然無法傷害;波旬又讓自己女兒向佛陀獻媚,但佛陀致其女兒成老嫗。北周時期佛的背光表現簡約,但總之表現的是“光”,但是“降魔變”里表現的像是遁甲,群魔無法靠近,群魔眼神、武器之勢都朝向佛陀,這種以群體的朝向表現畫面的動勢,更能體現群魔對于釋迦牟尼成道的恐懼。

圖1 薩太子本生圖 莫高窟北周428窟東壁門南
此外,洞窟西壁有著莫高窟最早的涅槃圖,釋迦牟尼安詳入滅,弟子們悲痛欲絕,藝術家為表現悲傷,用夸張的手法,眉毛、眼角、嘴巴下垂,極力體現悲傷之情。南壁說法圖上部四身飛天都為半裸,有別于巴米揚石窟長著翅膀的天使形象的飛天,為了表現飛動之勢,夸張動態,加長飄帶,增加云紋,依靠人物動態和衣帶飄舉,營造自由的飛天氛圍。
四、總結
觀畫本是視覺審美活動,繪畫是把某種物質、情緒、思想等以圖像形式表現在二維媒介上的過程,動勢即在繪畫中表現出視覺上產生瞬間動力的感覺。通常方形的構圖難以體現動勢,多給人以平靜之感,而曲線的趨勢更易表現運動性,北周428窟《薩埵本生》《須達拿本生》構圖以山川樹木構成的曲線趨勢分割畫面,《薩埵本生》第10場景“回城報信”中馬的奔跑與樹的傾斜襯托出當時之急切,又增強了畫面的動勢。總之,重復性形狀的表現可以增強勢,曲線式趨勢有助于增強韻律,圓形集中式構圖更能突出重點,夸張化的形變以及對比襯托、重復性序列都是增強畫面動勢的因素。在繪畫實踐當中,要在靜止的畫面里表現“動勢”的視覺感受,莫高窟這些無名藝術家的作品確實值得今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