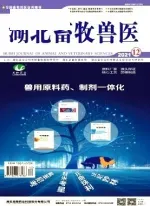西藏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基于七地市層面的實證
于 泳,葉 竹
(西藏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拉薩 850000)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戰略,對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和任務進行了明確的剖析和建設。產業振興則是“五大振興”中的首要任務,不僅是實現現代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前提,而產業振興發展狀況評估工作則是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基礎,構建產業振興發展評估指標體系迫在眉睫,這不僅為新時代農村現代化發展戰略提供范式,更為全面建設中國農業提供強有力的內生動力和發展效益。無論從地市間,還是城鄉間來看,西藏區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鄉村產業整體發展和競爭水平相較于內地仍顯得薄弱,主要表現在農產品生產結構、多功能發展水平和對社會貢獻率方面[1]。準確把握黨的十九大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理論內涵基礎上,科學嚴謹地構建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這對于推動西藏鄉村農業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第一,對西藏鄉村產業振興發展理論內涵進行解析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出切合西藏實際情況的鄉村產業振興指標體系,這不僅為西藏鄉村振興戰略順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基礎,更為民族地區鄉村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和科學范式[2]。第二,本研究通過構建西藏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對西藏七地市鄉村農業產業發展水平進行測評,不僅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西藏七地市間鄉村產業發展水平,而且可以從中找出西藏七地市鄉村產業發展的短板,這可為實現西藏鄉村振興并助推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本研究從黨的十九大關于鄉村產業振興理論內涵視角出發,通過對其進行解構分析,構建出切合西藏實際情況的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在西藏七地市層面進行評估,找出西藏區域間鄉村產業發展的差異。本研究的主要創新點具體如下:一是在對鄉村產業振興理論內涵進行解構的基礎上,從農產品產業體系、多功能產業體系和支撐服務體系對西藏鄉村產業振興指標體系進行建構,從而可以科學合理地對西藏七地市鄉村產業區域發展水平進行評估。二是從西藏七地市層面采用層次分析法+熵權法的TOPSIS 法,構建13 個細分指標評價了西藏七地市的鄉村產業發展水平,使得各指標在各地市之間具有普適性和可比性,為診斷各地農業經濟發展狀況提供了科學量化依據。三是系統評估了西藏七地市農業產業發展的區域梯度差異性,為逐步分類推進和因地制宜特色化指導西藏鄉村振興提供了有力的經驗證據。
1 鄉村產業振興理論內涵解構與指標體系構建
1.1 鄉村產業振興理論內涵解構
對于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應該從系統性視角去統籌考慮,鄉村產業振興理論中產品產業體系、多功能服務體系、支撐服務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其中,農產品產業體系是基礎,決定了多功能體系和支撐產業體系的發展;而多功能產業體系是延伸,為農產品提質保優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而支撐產業體系則是前兩者的重要保障,為農產品產業體系和多功能服務體系提供堅強的后盾(圖1)。三者之間相輔相成且相互獨立,既能體現鄉村產業振興理論內涵,又能體現各自特色內涵,是鄉村產業振興的內涵要求。

圖1 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理論框架
1.1.1 農產品產業體系是農業多功能產業體系構建的載體和基礎 農產品產業體系是重要基礎,是農業多功能產業體系構建的載體。這主要體現在:第一,農產品產業體系能夠有效地配置人力、物力和財力,大力發展包括種植業、畜牧業和漁業等在內的產業體系,是確保鄉村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為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和農產品升級換代提供有效載體,并進一步拓寬鄉村農業多功能體系,促使農產品產業鏈升級,提高農產品生產效率。第二,農業多功能體系是農業產業體系進一步延伸,反作用于農業產業鏈不斷升級換代,專業化程度和集約化強度不斷加強。為了滿足這一要求,農業產業體系要加強創新,推動新技術和新科技的發展和應用。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人們越來越注重農產品質量的提升,這對農業產業體系、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進一步推動完善農業多功能體系的建設。
1.1.2 拓展農業多功能性 在農業產業體系價值內涵的基礎上,農業多功能體系是在其基礎上的延續,同時也是三產融合的必要要求。第一,在三產融合中,農業是基礎,發展農業不僅能夠確保農民增收,同時還能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大力發展農業,積極拓寬農業多功能體系,不僅能夠實現農業產業體系轉型升級,還能拓寬農業發展邊界,為三產融合指明新的發展方向。第二,三產融合并不是簡單相加,而是能夠產生“1+1>2”的效果,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僅能夠強化拓寬農業產業價值鏈,而且能推動農業產業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發展。
1.1.3 農業支撐產業體系是農產品和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的有力保障 農業支撐產業體系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基礎,不僅可以推動農業產業鏈升級發展,還為農業產業融合提供助力。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發展,農業支撐體系的保障作用越來越明顯,在農業科技體系、農業信息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建設更不容忽視。只有加強現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才能確保農產品高質量發展和多功能產業體系的建構,進而增強農業產業內生發展動力,推動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
2 研究設計
2.1 評價指標選取
以國家發展戰略為中心,堅持可比性原則,突出農民的主導地位,并在數據可選擇性的基礎上,構建了西藏鄉村產業振興三級評價指標體系[3-5]。所選指標如表1 所示。

表1 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
2.2 數據來源
數據來自《西藏統計年鑒2020》《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0》《拉薩市統計年鑒2020》《山南市統計年鑒2020》《林芝市統計年鑒2020》《昌都市統計年鑒2020》《阿里地區統計年鑒2020》《那曲市統計年鑒2020》。
2.3 研究方法
為確保指標賦權的嚴謹性和客觀性,采用層次分析法+熵權法對三級指標進行賦權,并使用TOP?SIS 法進行綜合評價。
2.3.1 綜合賦權方法 綜合賦權方法,即是將主觀賦權法得出的權重與客觀賦權法得出的權重進行線性組合,得出綜合權重,不僅避免了過強主觀性,同時也解決了過度依靠數據統計的弊端。采用層次分析法+熵權法進行賦權。
1)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的核心是將多目標決策問題作為一個整體系統,并將決策總目標分解成目標、準測、方案3 個層次,從而構建出有序的階梯式指標體系,通過專家對定性指標進行模糊量化,得到兩兩階梯式對比矩陣,并通過對判斷矩陣進行求解特征向量,從而計算出每個層次各元素的權重,最終得到方案層指標體系的最終權重。層次分析法適用于具有多級評價指標體系而且各指標體系又難以使用定量方法去計算的問題。本研究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構建出西藏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分析模型[6](圖2)。

圖2 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層次結構模型
2)熵權法。按照信息論基本原理,信息是一個有序系統,而熵則是系統中無序的度量單位,二者呈現出反方向變動。熵可以用來表示某個變量的離散程度,離散程度越大,則該變量所包含的信息就越大,權重就越大;反之,該變量權重就越小。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的重點就在于其可以充分考慮各變量數值之間離散程度,進而彌補了主觀性過強的缺點[7]。利用信息熵這個方法,可以計算多元指標體系的權重,并為多指標綜合評價提供科學的依據。
3)綜合賦權法。層次分析法和熵權法從不同角度來確定權重,兩者各有優劣,客觀賦權過于信賴數理統計,從而忽視主觀分析;主觀賦權完全信賴專家意見,而拋棄科學的客觀賦權方法。綜合賦權法是將兩類方法確定的指標權重進行有機地結合,從而使得到的權重值能更科學地反映評價指標的本質[8]。采用簡單乘法將2 種賦權結果綜合起來,得到組合權數。計算式如下:
式中,αi為指標Xi的主觀賦權,βi為客觀賦權,ωi為組合權數。
2.3.2 TOPSIS 法 TOPSIS 法又稱優劣解距離法,屬于多目標決策分析,是一種逼近于理想解的排序法,根據有限個評價對象與理想化目標的接近程度進行排序。傳統的TOPSIS 法有3 大缺點,其中最大的缺點在于權重的事先隨意性,為克服這一缺點,采用改進的TOPSIS 法進行評價,具體步驟如下。
步驟1:評價指標賦權。由規范化決策矩陣B 與指標權重矩陣G 的哈達馬積,得到加權規范化決策矩陣X:
步驟2:確定理想解和負理想解。假設理想解和負理想解分別為X+和X-,令
步驟3:計算各評價地區指標值與理想解和負理想解的距離:令D+i和Di分別為評價地區i的各項指標值到理想解和負理想解的距離,計算式為
步驟4:計算各評價地區指標值與理想解的相對貼近度。
按Si值的大小進行排序,該值越大,表明越接近理想解,評價地區越接近最優水平。
3 實證分析
為了驗證基于以上方法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合理性,收集了西藏地區7 個地級市2019 年度的指標數據,從地市級層面的實證分析中來進行驗證。
3.1 指標權重確定與結果分析
在運用綜合賦權法確定指標權重的過程中,通過層次分析法對西藏鄉村產業振興的各級指標進行主觀賦權[9],再通過使用熵權法對各級指標進行客觀賦權,最后計算各三級指標的綜合權重[10],各指標權重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農產品供給結構無論是主觀賦權還是客觀賦權均占有較大權重,說明專家對該指標的主觀認知和客觀數據統計所反映情況一致。從農產品生產能力維度來看,主觀賦權權重為0.333 3,位居第1,說明專家普遍認為西藏農產品生產能力對于西藏鄉村產業振興同樣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客觀賦權權重僅為0.164 3,占比不高,說明西藏七地市該指標數據存在較大差異。從總體來看,歸一化處理后的指標權重更加貼近于主觀賦權權重,因此需要對主觀賦權權重進行適當地調整,以使整個指標權重更加合理。

表2 指標權重
3.2 指標得分計算與結果分析
在確定指標權重的基礎上,運用TOPSIS 方法計算出西藏七地市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得分,計算結果見表3。由表3 可知,從西藏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得分的計算結果來看可以得到:第一,從總體上看,西藏鄉村振興總體水平普遍較低。在研究的七地市當中,鄉村振興總體水平得分大于0.4 的地市有5 個,占總數的71.43%,而得分大于0.5 的地市僅有拉薩市和日喀則市,說明絕大多數地市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與理想水平差距較大。第二,西藏地區間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的差異十分明顯。根據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得分和研究地區的數量,將西藏七地市的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分為3 個梯隊,總體水平得分排名前2 位的省份為第一梯隊,排名中間的3 個地市為第二梯隊,排名后2 位的為第3 梯隊。從結果來看,第一梯隊的拉薩市和日喀則市占據著地理優勢,在鄉村產業方面發展較好;第三梯隊的2 個地市為昌都市和那曲市,這2 個地市在產業方面發展相較于第二梯隊地市較慢,這說明西藏七地市間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第三,西藏自治區七地市內部鄉村發展不平衡。從13 項三級指標的綜合權重來看,無論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得分排名靠前還是靠后的省份,其三級指標賦權之間均存在較大差異。

表3 西藏七地市鄉村產業振興總體得分水平
4 結論
運用層次分析法與熵權法相結合的綜合賦權法確定指標權重,運用TOPSIS 方法計算指標得分,從而構建起一套評價西藏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的指標體系,并利用該評價指標體系對西藏七地市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如下。
1)綜合賦權法在反映通過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進行主觀賦權,又依據統計數據的差異程度對主觀權重進行了調整,使其更符合實際情況。
2)從總體上看,西藏七地市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普遍較低,與理想水平差距較大。
3)西藏七地市間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的差異十分明顯,主要體現在西藏中東部地市鄉村產業振興總體水平明顯高于西部地市。
4)西藏七地市內部鄉村產業發展不平衡,各項三級指標間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