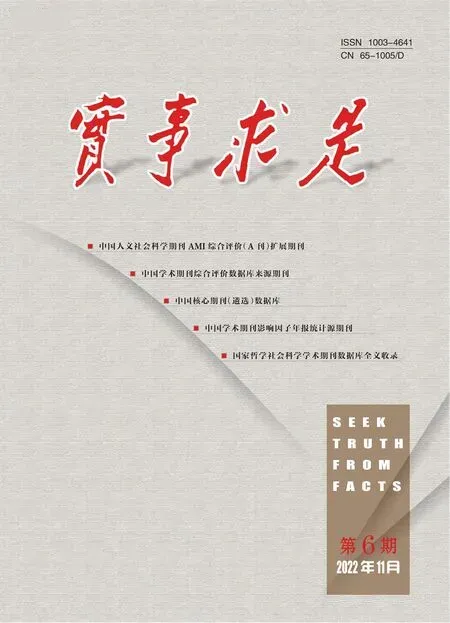是共存還是支配:數字文明正重塑世界*
呂彥瑤 馬新月
(山東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14)
當前,數字文明席卷全球,正重塑世界樣態。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向以“邁向數字文明新時代——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時,提出要共商數字文明造福人類的大計,引發各國的廣泛關注。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他又提到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1](P30)由此,數字文明正式開啟中國之旅。從本質來看,數字文明是以數據為中心形成的以5G、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技術文明,數字公民、數字經濟和數字空間成為數字文明打造世界的“三要素”。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深度挖掘數字文明背景下人、社會與經濟發展變化及未來世界的走向,理應成為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任務和使命。
一、數字文明下人的出場方式——數字公民
當下,數字文明如同“全景監獄”般規訓著人的存在方式、交往模式和勞動方式。一方面,人主動接受數字文明的規定,甘愿為數字文明服務;另一方面,人被迫置身于數字文明之中,接受數字文明的熏陶與洗禮。在“主動”與“被動”的矛盾交織中,人被卷入數字漩渦之中,成為被智能化信息技術重塑的數字人(數字公民)。[2](P115)
(一)數字文明支配人的存在方式
數字文明革新了人的存在方式,賦予人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以雙重身份。尤其在虛擬世界中,人擁有專屬自身賬號和密碼的新身份,人的身高、體重、血型、指紋甚至愛好、性格都以數字形式被記錄。這樣,人的身份以數據形式實現了永存。在現實和虛擬之中,人的存在具有雙重在場性,這是數字時代人的特殊存在形式。人的數字身份既是抽象性的存在又直接對應著物理存在本身,而且其物理存在越來越依賴數字身份甚至受數字身份的支配。
人的存在方式本質上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與確證。在數字世界中,人的本質被框定在數字邏輯規定的范圍之內,人的自身活動與數字世界相輔相成。一方面,正是人類活動創造數字世界;另一方面,數字世界深刻改變著人的活動方式和存在方式,將人從現實世界的單一人格變為現實世界和虛擬數字世界交互的雙重人格。這種改變具有強制性,若有人不接受數字的洗禮,便被隔離在世界之外。而在現實世界中,人會歷經生老病死,其存在具有有限性。但在虛擬數字世界中,數字平臺擁有精確的數字公民的“副本”。此“副本”是依托于現實的人生成的,決定著人的存在的永恒性。因為人去世之后,其“副本”以“凍結”形式保存下來,在某種意義上使人的生命得到了永生。
(二)數字文明變革人的交往模式
數字文明創造了全新的數字交往形式,打造出嶄新的交往模式。數字,包括一切形式的數字軟件,既是文明交往的中介,又是“共有”交往的載體。一切人的情感、思想、語言等,都暴露在數字之中,受數字的監控和規訓。受數字的影響和主導,人與人的交往打破了時空限制,實現了虛擬與現實的統一,形成了數字文明時代特有的交往模式即數字交往。
數字文明將人與人的交往數字化,重塑了主體之間的交往關系。在數字世界中,各主體在一個不見其人的聲音世界里悠然自得,這個世界充滿了與時空本源相左的言談,無須借助舞臺或地點集合觀眾就能進行的表演,以及無須身體加入的對話。[3](P36)主體與主體之間跨越了時空界限,其交往“無須擁有同樣的建筑邊界或自然邊界.關鍵在于通過共用電子通道可同時獲取相同的信息”。[3](P23)由是,數字對人類交往的介入,成就了人類共同在場的條件,以數字形式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距離。事實上,人的共同在場是以身體在感知和溝通方面的基本狀態為基礎的,而完全符合條件的只有發生在那些物質在場的人之間的無中介接觸,但各種現代電子通訊手段已使得中介性接觸帶有共同在場情形下的某些親密性特點。尤其是各類數字軟件,如微信、QQ、釘釘等的層出不窮,使數字在規訓人的同時,也建構著數字文明時代特有的交往模式。
由于數字的虛擬化,依附于數字規訓的交往模式,呈現出“空靈性”的鮮明特色。這一交往模式依賴于各類數字平臺,打破了人傳統意義上的存在方式,模糊了虛擬與現實生活的界限,實現了人的實體的“虛無化”和虛體的“實體化”的統一,從而形成以數字為主導的交往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人之內涵和生存空間得以拓展的同時,人也受到數字的監控和操縱,失去了原有交往的感性和真實性,在一定程度上變得“虛無”。
(三)數字文明改變人的勞動方式
在數字時代,人改變了工業文明時代的勞作方式,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數據創造,成為進行數字勞動的數字人。數字勞動是指參與、加工和傳播信息的所有勞動的統稱。數字勞動可以是直接操縱符號來生產原創知識的勞動,也可以是通過網絡獲取信息的技術勞動,甚至可以是裝配電腦線路和原件的勞工從事的勞動。總之,在數字時代,每個人都有潛力且必須成為數字勞動者。“在互聯網的利潤再分配框架中,一旦你解開了商品之謎,你同樣也可以解開勞動之謎。我們經常說我們是產品,但這肯定是錯誤的概念,因為我們并未處在奴隸經濟之中。但是,認為我們的身份是生產者的觀念并沒有錯,我們工作(免費),我們為生產資料付費,通過網絡生產文檔,就像曼徹斯特紡織工廠里的工人使用織布機生產織物一樣。”[4](P50)因此,刷抖音、逛淘寶等數字活動是數字文明時代特有的勞動形式,人在數字平臺進行瀏覽、游戲、視頻等一切無報酬活動都屬于數字勞動。
當前,人類在數字平臺上進行勞動,數字平臺也記錄著未付報酬的人之勞動,兩者的交互作用不斷擴展著數字的邊界。數據成為人類進行數字勞動的原料,成為一種被提取、被精煉并以各種方式被使用的一般數據。數據越多,用處越大。因此,在數字文明時代,人憑借著社交媒體和數字網絡,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不斷輸出數據,進行一系列數字勞動。而數字平臺通過算法分析人所創造的一般數據,準確掌握一切數字勞動者的興趣愛好、行為習慣等信息,通過推測數字勞動者的可能性需求而提取出重大價值,實現對數字勞動者的腦力、精力及情感的剝削。“互聯網比任何人都懂你”,或許是數字文明時代的最貼切而真實的表達。數字勞動者即數字公民,在享受數字平臺提供的便利的同時,也完全赤裸且深陷于數字平臺之中,逐漸淪為數字的奴隸。
二、數字文明下的“立體”開拓——數字空間
數字文明在打造數字公民的同時,也在進行“立體”開拓,建構起數字空間,極大拓展了數字公民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尤其是數字城市的建設,將人與城市有機統一在一起,實現了現實與虛擬的有機互動,在人與空間的互動中不斷提升人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滿足感。
(一)數字文明創造數字城市
在數字時代,城市也被打上數字的烙印。數字城市通過數字化的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不斷提升城市系統的產出、配置、效率,以全新的數字系統引領城市數字化發展。城市多媒體電子地圖系統正是數字城市發展的典范。
在傳統城市地圖系統的基礎上,城市多媒體電子地圖系統利用先進的信息手段和電子工具,將現實城市的各項多媒體資源數字化,形成一個數字空間系統。這一空間系統是現實城市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延伸,是在建設數字地球、數字城市、數字社區等大環境下提出的全新系統。隨著數字系統的持續發展,數字加快了全球化進程,以虛擬形式即數字將世界統一起來。在這種統一中,一切人被數字化,演變為數字公民;世界也被數字化,成為由諸多數字空間組成的數字世界。同時,一切存在者都無法脫離數字空間和數字世界,因為一旦存在者脫離這種數字統一性,他們將被數字世界拋棄。
數字為城市裝上“大腦”,促進城市的高能運轉。數字把城市中諸多瞬息萬變的信息變為可度量的數字,并將這些數據引入計算機以建立數字模型,從而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城市文化繁榮和城市社會進步。實質上,數字對城市建設的影響,常見于對人生活工作的影響。比如,數字化城市中的重要存在——數字交通系統,正是運用數字技術,利用計算機構建一個全感知、全聯結、全場景、全智能的數字交通系統;數字對城市公共安全、市場監管、社會治理、應急響應作出更準確的研判,合理調度和充分利用資源,使城市成為智慧城市。同時,人生活在數字城市之中,主動或被動接受著數字的影響,成為推進數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設的主體力量。總之,城市以數字形態提供各類豐富且無形的數字服務,如智慧出行、數字養老、線上醫療、云上教育等,在技術賦能城市的全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同時,也促使城市變得更加便捷、更加溫暖、更加美好。
(二)數字文明搭建數字空間
數字空間是以自然空間為原料生產出來的數字化產物。它基于現實又超脫現實,旨在實現數字與經濟、政治、文化等的融合,從而滿足人的全方位需求。數字空間的誕生,意味著一切不變動的自在存在淪為“NPC”,意味著數字化的自為存在成為數字空間的主體。數字空間作為人創造的產品存在,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一方面指向自然界,另一方面指向人類自身。說它是具體的,因為它不僅是物質的,而且還是我們服從或者反抗行為的一部分;說它是抽象的,因為它有清晰的、可測量的輪廓,其實質是一種社會性存在,是新社會關系的載體。數字空間將主體數字化,使人類大腦成為數字大腦,并將數字保存在大腦之中。同時,數字空間借助主體的數字意識,拓展著主體的存在與發展空間,使世界統一于數字世界。
數字空間是靜止與運動的辯證統一,靜止是指其構成的物質內容是相對靜止的,運動是指其為數字信息的傳遞提供支持。鑒于數字在數字空間內部活動,宏觀上看,數字空間是靜止存在的。但數字空間內部的數字不斷運動,并源源不斷產生新數字,以適應人類需求。因而,在微觀層面,數字空間又是運動的。在數字時代,數字化的產物已經將自然的、自發的東西驅趕出去,使自然僅僅成為其活動背景。在數字空間中,數字公民也在積極地創造著數字空間,不斷擴展數字空間的范圍。人類一方面享受著自身所創造的數字成果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又因為數字長期支配和規訓著人類的心靈而依賴數字產物。
三、數字文明下的經濟新形式——數字經濟
數字時代改變著經濟的存在方式、構成形式和運轉方式。數字使經濟向實體與虛實結合的方向發展,成為數字經濟。《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2016)對數字經濟作了界定,指出數字經濟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數字經濟注重將政治經濟學邏輯與數字網絡緊密結合,以數據和云計算為重要依托為經濟注滿新活力。在數字文明時代,經濟發展以數字為支撐、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結合、產品物質性成本的降低等,展現出數字文明時代經濟發展的特有風貌。
(一)數字文明改變經濟存在方式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的發展,經濟存在方式已打破原有形式,進入了數字智能化時代。人類進入發展新階段,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應用在為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時,將人類文明推向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的發展新階段。在數字主導的今天,我們要把握數字海量性、多樣性、高速性的特點,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數字產業升級,以數字優勢發展新興文化業態,不斷推動信息化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創造數字經濟新形態。
伴隨全球從信息化時代走向數字化時代,數字轉型改變了經濟運轉的方式,將生產商品、客戶經營流程管理等用互聯網連接,重塑在線環境,實現了從用戶接觸到后端辦公室工作再到全方位數字化的跨越。傳統經濟正是通過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改造,實現了更加低成本、高效率的配置和生產要素數字化的轉向,進而構建起集線下業務、產業鏈、線上銷售等一體化的數字化系統。目前,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其作為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備受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因此,我們應“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5](PP24~25)數字化建設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不斷“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1](P30)不斷激活數字經濟發展的生機活力。隨著數字化進程的加速發展,數字經濟將主導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走向。
(二)數字文明改變經濟構成形式
數字文明加快了一般數據的普及與應用,改變著目前經濟的構成形式。當前,構成經濟的要素不僅僅是指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更為重要組成要素是融合在經濟中的數字。現今,大數據是數字時代的重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數字流正成為激活物流、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的關鍵載體。數據作為數字化發展的核心,其安全流通與共建共享是決定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核心生產力。數字的加入在促使產品的物質性成本所占比例急速下降、智力成本的比例迅速上升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經濟的構成方式和發展進程。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群落廣泛運用,并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使得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革,為經濟加入了強力催化劑——數字。推動數字與經濟的融合發展,不僅取決于技術的提高、基礎設施的完善,更為重要的是產業組織和經濟結構層面的數字化創新發展。從數字化戰略和發展路徑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要立足技術、產品層面的戰略布局,還要高度重視產業和經濟結構層面數字化模式的創新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講,數字是一個階段性存在,經歷了數字經濟階段之后,數字必然會得到進化。數字不是休止符,而是進行曲。若只是將數字看作產業構成的終極形態,看作經濟發展的終極歸宿,非但無法促進它的發展,甚至還會將它的發展帶入死胡同。因此,我們要真正將數字聚焦在實體經濟的賦能和改造上,建立一種全新的聯通關系,“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1](P30)這將是數字時代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
(三)數字文明改變經濟的運轉方式
數字化轉型是數字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識和鮮明特色。數字介入經濟發展后,深刻改變了經濟的存在和構成方式,進而變更了經濟的運轉方式。傳統經濟正是通過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改造,以一般數據來表達企業、產業運行狀況,實現了自身運行方式的轉變。
經濟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形成更具導向性的運轉方式,對經濟產業和業務過程進行重塑。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服務于產業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愿景,通過數字化的手段,能有效幫助企業提升內部運營效率和業務開展效率,從而有效降低企業成本,實現企業數字化發展。比如,生產商通過云計算和大數據獲得市場信息和產品銷售數據,及時調整生產方向,以更好適應市場需求。從本質上看,經濟發展是為人服務的。更具導向性的經濟運轉方式能準確定位市場需求,不斷滿足人的生產、交往、消費、娛樂的全方位需求,進而加快經濟的運轉速度。在這一經濟運行模式下,人與智能系統協同勞動的經濟運轉方式基本建成,經濟智能化程度加深,勞動力質量實現由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的轉變。智力資本的發展與數字技術的發展相輔相成,一方面,智力資本以核心關鍵性技術,促進了數字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反過來促進了智力資本的應用。基于此,智力資本以及數字資本對現代科技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發展起著重要引領作用,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的技術變革、產業變革和社會變革的根本推動力,越來越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四、數字文明下的世界走向——數字文明共同體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進入數字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利益和科技競爭演變為對各國數字的爭奪戰,數字作為橋梁將世界日益連成一個整體,實現了人類在時間和空間上真正意義上的統一。但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造就了全球數字共享的不平等。因為“這種由上億的匿名用戶生產出來的數據產品(數字資本)成為數字時代資本家占有的對象,也正是對數字資本的占有,使數字資本家處在整個資本運轉鏈條的頂端”。[6](P32)因此,要摒棄資本主義國家對數據私人占有導致的異化弊端,就要抹平數字鴻溝,實現數字共享,建設數字文明共同體。
(一)抹平數字鴻溝,實現數字共享
在數字文明支配下,一切存在者都被打上了數字烙印。互聯網的普及,計算機和智能手機的廣泛應用,將人們卷入數字時代的漩渦之中。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原理,事物是對立統一的,數字的發展也不例外。數字在人類文明的廣泛應用必是一把雙刃劍,對人類文明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數字文明支配著人、城市、經濟的發展走向,促使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城市更加和諧美好、經濟發展更有效率更可持續;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對數字信息占有的不平等性,導致了社會分化嚴重、數字鴻溝不斷擴大,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因此,抹平數字鴻溝、實現數字共享,是實現數字文明時代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數字鴻溝是數字主體之間由占有數字不平等導致的在諸多方面的數字差距。在數字時代,數字作為人從事的數字活動,作為經濟資源而存在。因此,對數字的獲取、利用和占有,成為數字公民生存發展的必備技能。但在獲取與應用數字中,占有主體表現出鮮明差異。處在優勢地位的主體,善于有效地利用數字技術獲取和利用數字資源,能夠為自身謀取更多利益以促進生存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數字富人”;反之,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無法有效及時獲取數字信息,逐漸淪為“數字窮人”,最終被數字時代所拋棄。同樣,企業、國家同樣如此,對數字的占有成為企業、國家增強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不同主體對數字信息的接受程度不同,可接受和可利用的數字資源也就不同。數據猶如石油和稀有金屬一樣珍貴,因而實現數字共享尤為重要。如今,共享經濟發展壯大起來,共享單車、共享汽車、共享雨傘、共享充電等層出不窮,彰顯著數字在經濟社會的充分運用和良好運行。數字共享作為一種新興的共享形式,主導著人類文明發展趨勢和發展走向,因為“這種共享勢必讓我們走向一個新時代,讓私人數據壟斷逐漸成為不可能,一個基于共同數據的未來共同社會正在數字時代的地平上露出它的曙光”。[6](P33)可以說,數字共享能夠使數字的價值發揮到最大,進而提高整個社會效率,加快社會發展的進程。
(二)擺脫數字綁架,構建數字文明共同體
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應用,加快了人類文明數字化進程,使得人類擺脫了地域的限制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結為真正的數字共同體。從“地球村”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共享數字發展成果,打造真正的數字文明共同體,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平等。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加速演進,5G技術、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迭代更新,人類文明展現出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隨著數字對人類支配程度的加深,數字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不可估量。數字語言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數字活動是一切數據思維能力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數字的運用人類甚至無法發展出最基本的數據思維,因而無法在數字時代生存。所以,在數字時代,擺脫數字綁架、尋找新的社會聯合方式,是實現全球數字平等的迫切要求。就國與國之間來講,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都具有平等享有數字的權利,并且都應受到維護和尊重;就民族而言,實現數字平等和共享是實現一個民族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保證,建設數字文明共同體理應成為一個民族發展強大的必由之路。
人是數字世界的主體,數字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所有的個人都相互為對方發展創造條件,“以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他的人的本性”。[7](P626)“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8](P571)在數字文明共同體中,“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5](P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