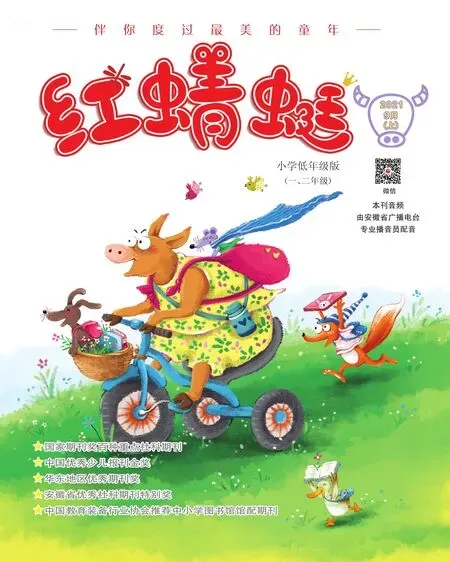美人魚
2021-09-22 02:12:48于曉宇
紅蜻蜓·低年級 2021年9期
于曉宇



準(zhǔn)備材料
舊蛋托、鉛筆、繩子、顏料、剪刀、卡紙等
1? ? ? ? ?準(zhǔn)備一個(gè)舊的蛋托,剪下每一個(gè)小蛋托,并修剪整齊。
2? ? ? ? 將蛋托涂上喜歡的顏色,重復(fù)制作6-7個(gè),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顏色哦。
3? ? ? ? ?在卡紙上剪出小人魚的身體部分,可以先用鉛筆描出形狀。
4接著我們剪出小人魚的頭發(fā),并畫出漂亮的衣服和可愛的五官。
5? ? ? ? ?用卡紙剪出小人魚的尾巴尖,在上面打好孔。
6將剪好的蛋托小心地鉆個(gè)孔,再把繩子打結(jié),穿過蛋托,重復(fù)這個(gè)步驟直到穿完所有的蛋托,再把尾巴尖也穿上。
7最后把身體和尾巴粘起來,小美人魚就誕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