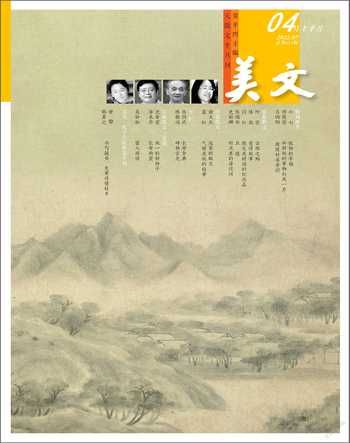我的經驗
向灣硚
十九世紀后期,城市漫游者(flaneur)由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勾畫出來。他們游走于現代城市生活的街道景觀之中,捕捉城市中不斷消逝的即刻之景,被視為現代生活的描繪者。 本雅明以此人物為基底,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大談現代性。
在西方發展史里,現代城市景觀的興起是現代性的一大特點。城市漫游者是那個身處于畫面之中、但不陷入其中的觀察者,他們保有一份藝術家的熱情,孩童一般的好奇——對于任一不同的細致都倍感新鮮,激動不已。他們游走在城市里,閱盡千帆,不為永恒,只為瞬間的捕捉。
兩百多年以后,城市漫游者被稱為無所事事的人,心無掛礙。幾萬公里之外,席卷全球的疫情把很多獨居的人重新塑造為漫游者。我是那其中一個。
生活變得扁平了。不需要去自己房間外的公共空間,不需要與他人共享任何場所,不需要記得禮貌,只需要鏡頭前的端莊。所有的社交生活、與人連接都通過那一方小小的屏幕存在。或許是《黑鏡》(Black Mirror)里劃定的世界,就像還有很多人不需要活在這個格子里。
我先是將自己的房間打造成讓我滿足愜意的王國,培育各種植物,發展各種小樂趣:打毛線、涂鴉、唱K、一人火鍋、一人蹦迪、一人讀詩……很快就膩了,很久才會再對這些提起興趣。還是得出去走走,即使一直戴著口罩。我唯一時常散步的鄰居是一個白人同學,我一周或幾周跟他沿著附近走走,他有輛摩托車,說如果需要,可以載我,但我還未讓他幫忙過。
冬天一來,圣誕節前夕,這個美國南方小城,街道上幾乎空無一人,也有來來往往的車輛,載著不駐足的過客。這是一個人們離開后不會懷念的地方。大多數人都是學生,來這里上大學,酒吧街商店都為他們而開,夏天和冬天假期,就冷清下來。每次有朋友離開后回來探望,我都問:“你懷念這里嗎?想去哪兒看看?”“The place? no. People? yes.” 沒有人懷念這個地方,只是懷念這里的某些人。我希望,我以后可以住在一個離開后也會懷念的地方,不只是因為人。
我最常散步的路徑是去學校,那里或許是這個城市里最美的地方,如果你到谷歌上搜索,前三個旅游景點可能都在我們學校。學校里還有一個奴隸區域(Slave quarter), 標明這里最初的工人是一群奴隸。南方的城市,稍有點歷史的建筑,大多都是這樣,最初是奴隸一磚一瓦筑起來的。奴隸區域在校長房子的旁邊,每次走到校長房子外面都遙望里面懸掛的燈飾,窗戶上的松樹枝環。當然,我最喜歡看的地方就是校長房子后面的玻璃花園溫室——里面層層疊疊好多新奇的植物花朵多肉,房子外面也隨著季節變換有不同種的花朵環繞。有一次,一個員工告訴我,這里面培育的植物都是給校長房子準備的,這更激起我去校長房子里看看的欲望。
我總是在午后或是黃昏到這里,從來沒有碰到任何人進出,只是偶爾門口的大風扇會突然轉起來,調整溫度。
前些天,我走到了附近一個中產的街區,有時候還會看到教授遛狗。這個街區的房子前都有自家精心布置的花園,給小鳥喂食的小房子,迎接圣誕節的裝飾品,彩色球繞在樹上,松樹枝蝴蝶結掛在門上,街邊滿是橙紅的糖槭樹,偶爾還有深紅小巧的日本楓葉。我總想走進去看花園里的裝置,我的美國同學告訴我,這是不太好的,因為那是私家領域——即使它們就在路邊。
今天我漫游的是平日里我窗戶里的景色,我口中的“酒吧街”。我很少在這街道里走動,因為仿佛總覺得會有人喝醉了闖出來。而現在,這寂靜的冬天白日,沒什么人了。周一、周四、周五、周六的夜晚,我總能聽到窗外各種人失控的聲音,我一直覺得有趣,仿佛總有人可以用嚎叫發泄出他們的挫敗不滿和苦痛,仿佛那是一種很方便很簡單的方式,是這些本地年輕人才可以擁有的方式。這個學期還沒結束的時候,我這棟公寓右邊的“甲板”酒吧外還總是擁擠著人,那些穿著與“餅干模子”(cookie-cutter)衣服別無二致大學女生,那些穿著棒球衣,走路隨意的男生,那些“喝酒、喝醉”(drink, get drunk)的年輕人。深夜里也會看到爛醉的女生被一兩個男生攙扶著走。記得是前年的時候,這里發生了一起“優步”(uber)司機殺人案,一個女生凌晨打“優步”回家,誤上了壞人的車。幾天后,警察在附近的加油站看到了這輛車里的血跡,遂破案。后來,學校的電梯里出現了抵制“優步”、讓大家參與調查的傳單。
我走過“屋頂”酒吧,和大多數商店一樣,它現在空無一人。一兩個月前,大學生們還都摩肩接踵排隊等待入場。我的白人同學告訴我,有一次他和一位黑人朋友想進入喝酒,結果在門口被攔下,說“這個場合不能讓穿沙基褲(saggy pants)的人進”,但這種褲子恰是年輕黑人男性喜歡穿的。另一次,我跟他走去折扣店買酒,他指給我看那些鎖在玻璃柜里的酒,“你知道為什么這些要上鎖嗎?”“因為貴?”“不是,是因為它們是黑人最喜歡的酒。”
我來到酒吧區旁翻新的公園,在入口處的駐石上寫著我們高中語文課本里馬丁·路德·金的那篇《我有一個夢想》里的句子——
This is our hope, and this is the faith that I go back to the South with.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我懷著這種信念回到南方。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從絕望之嶙劈出一塊希望之石。)
當一個標語歷經多年依然被不斷提起,依然被銘記,那是因為,問題依然存在,且重要。
我在這里教大學生中文課,課上很少有黑人學生,有的時候一兩個。學校里食堂和其他地方做清潔的人,放眼望去,大多都是黑人。有一個黑人學生特地來選我的課,他對中文特別感興趣。他說,在他小時候,有一個中國朋友,午飯時,他們一起吃飯,朋友給他分享了自己飯盒里的,然后就自然而然也來他飯盒里夾菜,他當時非常不解,問他為什么還要夾我的,朋友說,在他的文化里,就是你給我,我也給你,一起吃飯就叫互相分享。他從沒想到居然會有這樣的不同,因此想要了解中國文化。他參軍后,每次來上課總是穿著制服,課程中途,他有時會有強制的特殊訓練,所以不能保證每次來上課。另一位老師告訴我,一些制度因素會影響他們的成績——例如因為家庭貧窮而參軍,但是參軍就會有各種訓練,必定影響課程參與。
樓里的保潔阿姨很可愛。一開始我不太能聽懂她的口音,不過也只是日常打招呼,所以并不大礙。有一次我找不到鑰匙,想到是不是丟垃圾的時候扔進了垃圾桶,于是便問她有沒有清理垃圾袋,然后我準備翻倒那個垃圾袋找鑰匙。她說這會弄臟你的手,我有經驗我來,然后一點點翻倒,幫我找。那之后,每次看到我,她都提醒我:Mind your keys(留意你的鑰匙)!
她的頭發細卷,時常擦著藍色的眼影。有一次,她頭上戴了一個小塑料王冠,還擦了口紅,我問她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她說是她的生日!我去辦公室拿了蘋果,坐在一樓,想給她,怎么都沒等到,或許是去其他樓了吧。還有一次,我們一同被困在一樓,等雨停。她一個人住,有輛車,她說要做的就是勤奮工作,有了錢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意。她還說她有自己的生意計劃,沒有告訴任何人,只要努力,相信自己的計劃,好事就會發生。她的眼睛并不看我,滴溜在松垮的黑臉蛋上。
夏天的時候,街上都是松鼠,沒有了人的打擾,它們更加喧鬧。秋季學期,人回來,松鼠藏起來。現在是冬天,它們又出來了。
窗外電線桿上的鴿子還是會偶爾飛到我的窗前,轉轉頭,停幾秒,又飛走。
窗臺上的蔥,一周了也沒長兩厘米,或許是冬天太冷,遠不如夏天熱鬧放肆。
我在一戶人家門前又看到了搬家丟棄的一眾雜物。我摸出包里的手套,戴上,搬了其中一把椅子回家。我原本的椅子是之前的室友留的,她也是從路上撿的,黃色坐墊,白色漆,頗有歐洲風格,于是她留作裝飾,而我卻是真的拿來做椅子的。坐墊的木塊幾近散架,我再疊上一塊,勉強用著,想著可以撐著,也許又會有新的飛來舊物,今天,就得到了。
我想著可以讓有摩托車的白人同學載我到一元店(Dollar Tree)買些便宜的圣誕裝飾物,一聯系他,才知道他三天前剛遭遇車禍——一個酒駕司機將摩托車和他撞離馬路,隨即送入醫院。現在,他已經離開了這里,回到家人身邊,得到照顧。我唯一的散步伙伴也走了。那我的散步,就真的是,心無掛礙,只有外物了。
波德萊爾筆下的漫游者還就得是無所事事的,除了觀察和體驗之外,他不該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于是,他可以敏感地聽聞街道的心跳,看出皮膚顏色變化,他的目光才可以四處游離,沒有預設的濾鏡,一切都可以進入他的眼睛,一切都是新的可能。
轉眼就碩士畢業啦!花一點時間來作個小結。
和“大學生”相比,“碩士”這個頭銜仿佛意味著一些理性、沉著和成熟;而我自問,我心一如大學時躁熱、不安、困惑多多。
不同的是,對于同一個問題,多了一些看待的角度;對于同一現象,所產生的疑問和解讀不再局限于結局本身——
在大學的時候最常問的是“為什么”:為什么要求知?為什么有些歷史是不可以討論的?為什么父母即使錯了子女也不能反抗?為什么要承接傳統?為什么要向西方學習?為什么窮孩子必須上大學才能改變命運?為什么一件事大家都知道錯的卻沒有人站出來改變?為什么需要遵守“道德”?為什么需要“民主”?為什么“優秀”是通過聽話完成作業的“績點”來衡量?為什么“愛”都不能被認可?
現在來看,當時的一些困惑,從提問用詞上便可以解答。
例如“為什么父母即使錯了子女也不能反抗”,并不是“不能”反抗,而是反抗無意義——要求父母那一輩來理解這一代本身就不應該,他們的生長背景和教育環境塑造了他們的價值系統,而這一價值系統或許在某些時候和我們的產生沖突,反抗的姿態在中國權威型親子關系前幾乎等于毀滅,唯一有效的只能是和緩的溝通,而最簡單粗暴的是放棄迅速“改變父母”的想法,不激烈反抗,不改變,聰明地做自己。
一些提問本身就是出于無知,是沒有獨立思考前的被動接受。傳統必須要承接嗎?不見得,也不過是衡量的價值體系不一樣。
一些問題引導我去更深地認識了“社會構造”和中國的社會現實。例如窮孩子也不是必須上大學才能改變命運,只是在城鎮鄉村信息分化逐漸增大的今天,上大學仍然是他們唯一的社會階梯。
一些問題引導我認識了中國的近當代發展史。例如為什么有些歷史至今仍是禁區,為什么說要民主,為什么說向西方學習,為什么一些人的存在本身就不被認可……這些現象所來由深,理解它們需要縱向看歷史,也需要橫向比較其他社會中如何處理相似問題,更需要看當下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
而正是這些理解中國當代社會的問題,推著我求學:我希望自己擁有更強的獨立思考能力,遇事不再空有一腔“為什么”的憤怒,而還能有獨立分析判斷的智識,探尋這些問題是怎么產生的,現象何以至此。
碩士兩年的比較文學,三門必修理論課——研讀古希臘至今的西方經典文論,我喜歡柏拉圖對于理想國的思考,用它分析了《1984》;我也熱愛席勒高呼“藝術使人完整”的通篇論證;贊嘆于黑格爾關于“主奴辯證”的洞察;又驚訝于福柯解構權力之可怕……這些理論就像是人類歷史長河里閃亮的星星點點,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里,它們真的改變著世界。
除此之外,專業課方面我需要修六門第一文學,三門第二文學。這些都是討論課, 每周讀資料,寫讀書報告,上課提問討論。每個老師的風格都很不一樣,但我喜歡的就兩種:一種是在課開始的時候給出一些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來給課一個方向,引導同學們有目的地討論;一種是要求每個人都積極參與討論,老師也作為一個平等的討論者但又同時扮演著一個討論推進者的角色。當然,也有個別老師因為太厲害,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吸收,巴不得他說完一整節課。
這兩年的我并沒有很快樂,究其原因有很多。但此刻去敘述似乎顯得多余,想要寫下一些值得感激和銘記的時刻,讓那些光亮存留著。
讀碩士之前,對于這個新的地方有些惶恐,一位加州的老爺爺對我說:There are wonderful people everywhere, you just need to find them.(每個地方都有特別棒的人,我們只需要找到他們) 在這里每一次寂寞時,或是遇見喜歡的人時,都會想起這句話,很是寬慰。
來這里第一天,去系里報道,很多問題,一一向系秘書詢問。她是一位即將退休的老人,戴著波西米亞風的大亮耳環,畫著眼線,一頭卷發。她慢慢聽著我噼里啪啦一連串焦急的話,微笑著跟我解釋,在我每一個點頭后安慰道:“See, how easy it is?”這句話,讓我愿意相信一切都可以“簡單”輕盈。
出現程序性問題的時候,總是去找我們的顧問老師,她很憨厚,給人“外婆”一樣的安穩感,眼睛總是在眼鏡后瞇成一條線,配合著突出的笑肌,很是正向,一頭剪短的白發顯示出干練。一次我跟她說著問題,說著說著就哭了,她像安慰嬰孩一樣安撫我,嘴里甚至發出那種對待小孩哭鬧時候的寵溺聲音。我曾在她的辦公室里問了一個小時的問題,也曾哭一個小時,她一直那樣寬容對待,像是世間最溫和的老人。
碩士要結束時,我對于自己該如何抉擇的問題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詢問我的導師。我的導師是“像山一樣”的大女人,在我還未出生時她已經從美國到了北大學中文,在長城上梭滑梯。她說話直接真誠,褪去了美國文化里那份遇見任何事都只說“Everything is gonna be fine”卻不言他物的表面。我說出了我深層的恐懼:如果我一直默默無聞寫著無人問津的論文該怎么辦?平庸是一件可怕的事。她與我分享,一個人能做什么便努力去做便是,她自己的滿足感來源于自己教授美國學生可以讓他們認識一個更全面的中國,改變一點對于中國的看法,這便是她的職責。
有一次一個系里同學過生日,我們約著去跳舞。那已經是凌晨,到地方后,我們五六個人圍成一個圈搖晃著,一個白人男性加入進來,然后對著另一個中國女生作了“瞇瞇眼”的動作,看到第一次的時候我懵住了,直到他再作第二次——同行的另一名白人男同學立馬沖過去制止他。后來那個人來向我們道歉,我們拒絕了。此后,我只覺得同行的這個男同學是個“英雄”,在那樣的場景里,他不僅看到了,還冒著危險勇于作出行動,令人可敬。
大多數課上都盡是白人同學,少有其他膚色的,我的存在也是一種“少數”象征。在一門英文系課上,我們談到了censorship(審查制度),當然又不免提到了我國。一名同學拋來一個很空闊的問題,似乎是要這方面的專家才能回答,我一時錯愕,應付著。下課之后,課上另外一位黑人女同學找到我,她問我:“Are you OK?”只因為她注意到了我在聽到那個問題后的一癟嘴。她說,因為膚色,她也曾遇到過同樣的情況:因為是某個場景下的少數人群,所以被要求代表這個少數人群來解釋現象與問題,而我們并不能給一個完善的答案。但是,中國人就了解中國的全部嗎?
我也非常佩服這樣一位同學——她年近中年,工作多年后,想到自己要是一生都這樣下去的話,實在沒有任何希望,于是想到了自己一直以來的興趣“寫詩”,沉浮兩年,申請來了我們學校讀創意寫作里的詩歌專業。我問她寫什么,她說“family secrets”,我打趣——那豈不是要背叛你的家人嗎?答:Betraying my families is to set myself free。是啊,不管在哪個國家里的家庭,總是有萬千羈絆甚至于控制。而成為自己,有時候甚至免不了要敘述背后的故事,哪怕會被稱作“背叛”。這堂課,本是非常自由的,暢所欲言,還有一名同學跟我們聊男性要聲稱自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該有多難,因為那意味著他需要時刻反思他自己所有關于性別的理解,而且這反思必將持續一生。沒什么必然聯系,但那真是一堂快樂而親密的課。
可以寫的還很多,給我論文細致的建議評論,尊重我的狀態、引導我去成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教授,不時關懷理解的同學,在這里時常幫助我的朋友……
There are wonderful people everywhere.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