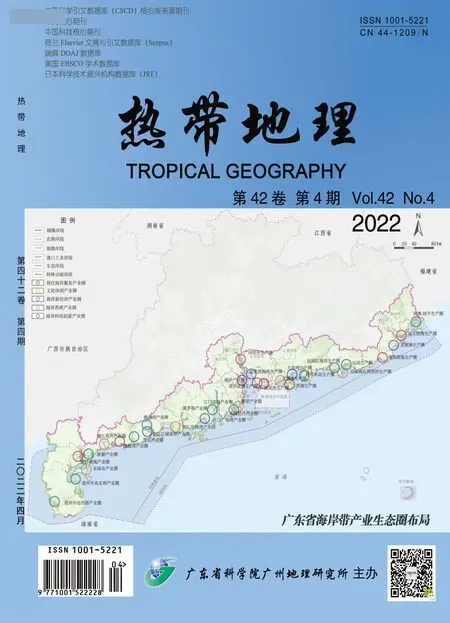情感地理視角下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
——以湖南省十八洞村為例
陳馳蕊,何 峰,湯放華
(1. 湖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長沙 410082;2. 地理空間大數據挖掘與應用湖南省重點實驗室,長沙 410082;3. 湖南城市學院,湖南益陽 413000;4. 數字化城鄉空間規劃關鍵技術湖南省重點實驗室,湖南益陽 413000)
緊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并列提出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0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改進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政績考核的通知》中要求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評判領導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政績的重要標準。黨對民生“三感”的重視,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且在制定民生政策時,其關注點已由物質、精神層面上升到情感、心理層面。因而從農戶的情感層面分析脫貧攻堅政策的實施效果,是響應國家重視民生“三感”的號召。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實現中國農業與農村現代化和農民生活富裕的兩項重大戰略任務,而產業興旺是銜接兩項政策的關鍵環節(汪三貴等,2020),人才興旺是產業興旺的支點。農村發展的人才“缺位”問題,需要“返鄉”人口來解決(林亦平等,2018)。如何留住人才,激發農戶內生動力,實現人才興旺是脫貧村實現振興首要解決的問題。精準扶貧工作在完善基礎設施、優化產業結構和升級鄉村服務水平等方面成績斐然(汪三貴等,2020),在物質層面為脫貧村“返鄉”農戶回鄉架橋鋪路。“返鄉”農戶回鄉,不僅需要脫貧村營造良好的物質環境,還需要情感關懷。情感關懷有利于個體作出正確的行為選擇(楊寶泉等,2008),可幫助“返鄉”農戶消解歸鄉疑慮,更快更好地適應重構后的鄉村環境。同樣,對于一直留守鄉村的農戶,也需要從情感層面給予引導,將其“消極情感”轉為“積極情感”,激發內生動力。
“情感轉向”是人文地理學繼“文化轉向”后的又一次強有力的哲學思潮,人文關懷和情感關懷在地理學中將能得到更充分的體現(朱竑等,2015)。2002 年9 月,第一屆情感地理學國際研討會成功召開。隨后,《情感地理》論文集的出版和情感地理專刊Emotion,Space and Society的創建,引發不同學科領域學者對情感地理學研究的重視。情感地理學者關注人在社會情境中情感的建構機制及其與空間場所的相互作用,從而使地理研究突破唯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實現“情感轉向”。目前,國內有關情感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游客的情感體驗(趙昭等,2018;孫小龍等,2019)和評價(劉逸等,2017)、流動人口或家庭的情感感知(鄒雪瓶等,2020)和情感重構(陶偉等,2019)、城市居民情感與地方環境的關系(王孟永,2018;行騰輝等,2021)、鄉村地域居民情感依戀(呂龍等,2021)及其與鄉村治理的關系(林元城等,2020)等方面,對鄉村地域系統重構中農戶情感變化的研究較為薄弱。外在環境對個體內心的刺激是情感產生的必要因素,因此地理環境和空間場所是情感發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吳麗敏,2020)。情感作為個體生活的中心,能夠敏感地感知到周圍物質空間和社會環境的演變,故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William,2001)。事實上,中國的精準扶貧政策蘊含著情感維度,但已有研究過度強調技術理性而忽視了對于情感性因素的探討(程軍,2019)。農戶是農村中集生產、消費和血緣于一體的基本社會單元,其行為邏輯不僅具有經濟理性,還具有社會理性(趙明,2020)。農戶在決策時,常常會為了家庭團聚、子女教育、贍養父母而犧牲一定的經濟收入。在經濟積累到達一定程度后,農戶的需求會轉向精神性價值需求,如競選村長,獲得名譽和聲望。農戶情感需求層次的演替是農戶行為邏輯變化的內在根源。因此,情感研究在人地關系中恰恰是最應該關注的領域。不了解人地關系重構中農戶的情感訴求,就無法準確理解農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無法保證脫貧村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順利接軌鄉村振興戰略。
目前,針對脫貧村情感維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層面,如從“情感治理”(程軍,2019;向德平等,2020)、“精神扶貧”(程肇基,2016;房彬等,2021;曹艷春等,2018;)等角度探討扶貧工作者如何將情感融入政策實踐,使鄉村治理更加有溫度。也有涉及脫貧農戶情感歷程的研究,如左昭(2018)、陳淇淇(2019)、丁波(2020)等探究了易地扶貧搬遷戶在遷往城鎮安置區后,生活空間、社會屬性突然轉變后的情感不適應性。這些成果集中探討如何自上而下消減脫貧農戶的消極情感,卻沒有將農戶這一微觀主體的情感變化在宏觀政策的語境中完整地展現出來。因此,本文從農戶微觀視角出發,采用質性研究的方法,探討精準扶貧政策引發的鄉村地域系統變化對脫貧村農戶情感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投射到行為上的表現,并由此探究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機制,以期為促進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有益參考。
1 情感地理視角
1.1 情感的特征
情感地理理論認為,情感具有空間性、時間性、社會性和層次性4個特性。“民族心理、情感的形成往往與地區內的自然環境、文化環境相關”(邵培仁等,2011),體現情感的空間性。在不受到任何外界的干預下,人們對某一地方的情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衰弱、模糊甚至消亡。依照時間性的特點,情感可劃分為即刻性、短暫性和永久性。情感的社會性體現在情感同化,指個體情感可以影響他人的情感和思維,也容易受社會潮流感染。層次性指經過長期的社會互動和人際交往,初級情感會轉化為高級情感,高級情感可以調節、支配初級情感,且更加穩定,不易隨時間而改變。
貧困村主要分布在深石山區、高寒區、生態脆弱區、災害頻發區和生態保護區(劉彥隨等,2016)。偏僻的地理位置、惡劣的自然條件、少量的就業機會使當地農戶承受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對貧困有著深深的畏懼感,對未來產生消極、迷茫的情感,這體現情感的空間性。長久的貧困狀態導致農戶對貧窮形成刻板印象,變得無助、麻木從而喪失脫貧動力,降低自我效能,影響心理健康(Micklson et al.,2008),這種情感和態度經過時間沉淀成為永久性情感,體現脫貧村農戶情感的時間性。貧困群體人際關系狹窄,懼怕對外的社會交往,形成內部交往的“小圈子”,從而加重其與社會脫節程度,同時這種固化的“小圈子”內部的消極情感也會通過傳染和強化,形成規模效應,體現脫貧村農戶情感的社會性。一旦農戶對貧困產生恐懼感和無助感,沒有外界的干預,這種情感會隨著時間固化,并經過代際傳遞成為高級情感,長期支配農戶的行為,體現農戶情感的層次性。精準扶貧政策影響下的脫貧村農戶情感充分體現情感地理理論提出的情感具有空間性、時間性、社會性和層次性4種特性。
1.2 情感的維度構成
重構指對當前出現矛盾而無法正常運行的系統進行重新建構進而實現系統良性運轉的過程(Kiss,2000)。Woods(2011)將鄉村重構定義為快速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結構的重新塑造。本文的情感重構特指精準扶貧語境下的脫貧村農戶情感的重新塑造。為了能準確解析脫貧村農戶的情感,首先需要確定農戶情感的研究維度。吳良鏞先生認為,村落也是社區(吳良鏞,2001),而Ma‐clver(1931)認為社區自身意識、位置和身份感、依屬感是社區居民情感的3 個維度;鄧遂(2003)則認為,社區情感只包括積極情感,即有利于人們和諧關系的情感總稱,如社區歸屬感、認同感、親密感、依戀感等,其中社區歸屬感是核心情感。鑒于研究對象為脫貧村農戶這類特殊群體,將從歸屬感、幸福感、風險厭惡感、相對剝奪感和失落感等5 個維度來分析其情感重構。情感雖捉摸不透但也有跡可循,人們的行為與決策是思想、情感作用的結果(Nancy,2004),因此,將農戶行為和決策視為個體情感表征,據此探究農戶對地方的情感重構。
2 案例地及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概況
十八洞村隸屬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雙龍鎮,是一個典型的苗族聚居行政村。2005年7月因區劃地名調整,十八洞村由原來的竹子村、飛蟲村2個村子合并而成。其中,飛蟲村包括飛蟲寨和當戎寨,位于村北端;竹子村包括竹子寨和梨子寨,位于村南端,兩村相隔約4 km(圖1)。連綿的群山造就十八洞村優美的自然環境和豐富旅游資源,也造成人均耕地僅0.06 hm2的惡劣生活條件。2013 年以前,雖然國家政策一直在支持,但仍存在“年年扶貧年年貧”現象。

圖1 竹子村和飛蟲村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Zhuzi and Feichong Village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十八洞村視察,首倡“精準扶貧”理念,十八洞村的發展才出現轉機。通過幾年的扶貧建設,十八洞村不僅脫貧成效顯著,還探索出可復制可推廣的扶貧經驗,成為全國脫貧攻堅樣板村,昔日貧窮落后的偏遠苗寨蛻變成中國脫貧攻堅歷程中的地標。因此,選擇十八洞村作為案例地分析精準扶貧戰略影響下農戶情感與地方、情感與行為之間的關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2.2 研究設計
2020年之前,精準扶貧政策使得多方力量參與貧困村的建設,貧困村人地關系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在外界力量干預期間,農戶生活的物質空間、社會關系、價值觀念和人力資本等都發生了改變,從而引發農戶地方情感的重構。目前,脫貧村中存在3類農戶,第一類是“留守”農戶,即一直生活在村子里,沒有離開過村子的農戶;第二類是“返鄉”農戶,即從務工的城市回到脫貧村的農戶;第三類是外城農戶,即仍然在城市務工,但是與脫貧村保持穩定聯系的農戶。由于“留守”農戶和“返鄉”農戶參與脫貧村的生產、生活和治理決策,其情感重構能有力說明十八洞村從貧困村到脫貧村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發展變化對農戶地方情感的重塑。此外,個人情感與集體情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麻三山,2009),情感的社會性又要求在研究過程中重視集體情感對個人情感的約束和管理,因此,本研究對象界定為“留守”農戶和“返鄉”農戶的個體情感和集體情感。
情感地理需充分汲取女權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法和非表征理論等多元的理論方法(朱竑等,2015),而定量研究方法用“科學”“客觀”“中立”“自上而下”地展現社會的方法,其驗證假說的過程較為“標準化”(陶偉等,2019),難以呈現農戶這一基本社會單元動態的情感感受,因此基于質性研究方法,通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對研究現象進行深入的整體性探究,從而了解農戶在生產生活方式、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現狀與變化,并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
于2021-01-12—15、09-23—26 對案例地及其農戶進行調研和參與式觀察。1)從線上線下查閱、收集資料,初步了解案例地在扶貧前、中、后時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人居環境、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等的大致變化情況,確定調研的樣本結構和訪談重點。2)通過參與式觀察,了解農戶的基本情況、生活軌跡和行為邏輯。3)聯系農戶,說明調研的目的,結合實際情況,在每戶中抽選1~2個訪談對象,對每個訪談對象進行15~50 min 的深入訪談,在征得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4)訪談內容以農戶及其家庭成員基本信息、農戶在城鄉間的流動經歷為切入口,采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讓被訪者敘述真實的生活經歷和體驗,將口頭表述與生活實踐有效結合,形成對社會事實具有說服力的厚重描述。5)初步整理筆記,對存疑的地方,進一步追問被訪者;對農戶多次提及的歷史事件,重點追述。6)向被訪談者致謝。7)將錄音資料逐字逐句謄寫。8)篩選樣本,保留具有代表性的訪談記錄。9)針對遺漏或需完善的調研內容進行補充調研,調研過程與首次調研基本相同。訪談地點在小賣部、廣場、村口和農戶家中,訪談時常常有幾戶人聚集,并且參與了訪談。訪談者及其基本信息詳見表1所示。

表1 訪談者及其基本信息Table 1 Interviewers and their basic information
3 脫貧村農戶的情感重構
3.1 歸屬感上升
地方歸屬感指居民對所在地方社區和所屬群體的認同、喜愛和依戀(杜宗斌等,2013)。地方歸屬感分為地方認同和自我認同2個階段,地方認同是自我認同的基礎。其中,地方認同是功能依賴,自我認同指在地方建立社會關系,參與地方活動,為地方做貢獻的傾向程度(古麗扎克伯等,2011)。個體對所在社區和所屬群體的認同感越強,將這種情感轉變成實踐行為的幾率越大,相應地,會越發關注社區的發展與建設(丁鳳琴,2010)。
脫貧攻堅時期,食品充足、人身安全等是農戶的首要需求;后脫貧攻堅階段,教育、娛樂、發展前景等成為農戶的功能性需求。如果地方順應社會發展,及時提供滿足農戶需求的條件,人與地方的聯系將更加緊密。如果地方囿于困境無法承載這些功能,無法滿足農戶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那么人與地方的情感會由緊密變為疏遠甚至斷裂,表現在現實中就是人的遷徙和村落的衰敗。2013年前,十八洞村以第一產業為主,農戶入不敷出,生存艱難,產生逃離感,村中2/5的勞動力人口選擇外出打工。脫貧攻堅階段,通過各項扶貧措施,十八洞村實現鄉村地域系統的重構,滿足了農戶的基本生存和發展需求,吸引許多在外務工的農戶返鄉。至2020年底,在外務工的十八洞村農戶中有一半選擇返鄉,此時農戶對地方是功能性依賴,處于地方認同階段。十八洞村農戶積極參加合作社,支持村集體經濟發展;組建志愿者隊伍參與村中建設;在修建基礎設施時,響應號召改造庭院、出讓土地、支持村中拓寬道路;為實現脫貧目標,農戶穿起苗服,營造苗族文化氛圍,積極推動鄉村旅游業發展;當有個別農戶阻撓發展進程時,農戶們自發用傳統的方式積極維護村集體的共同利益。農戶與十八洞村的聯系由單方面的功能依賴轉為雙向互動,農戶情感由地方認同上升至自我身份認同,歸屬感上升。
“在外面會想念家鄉……想念家鄉農閑時,休息的時候,去山上找野果吃,那個時候有很多樂趣。我也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不向往城里的生活……我喜歡自己的村子,自己家的感覺。我喜歡寬敞,我不喜歡在城里擠來擠去的。”——訪談對象1
“2014 年,村里要修路,需要的石板要從山上搬下來,于是村里青年們組成青年突擊隊去幫忙搞建設,義務工作,不要一分錢,全是村里的人,每家都出勞動力,干了3 年,一分錢沒要。”“之前(駐村)工作隊修路,要從(一戶)村民的田地里經過,他家不讓……我們一個寨子的人就勸他,然后那戶人家就同意了。”——訪談對象5
“關心村中的建設呢,他們要擴寬那個馬路,把我家這個房子都拆掉了,他們就重新(蓋成這種房子)。村里面的建設也支持,用到我們地盤哪里,(要)讓出來的,哪能不讓,村里面要開發啦。”
——訪談對象11
“一直在外面打工八年了,2017 年的時候才返鄉的。因為家里有就業崗位提供,可以就近就業,然后就可以照顧到家里的老人孩子……在外地打工肯定會想家啊,非常想啊,背井離鄉嘛,照顧不了家里面,有的時候有四個春節是沒有回家過年的,那家鄉的鄉愁對于在外的人來說都是有一種牽掛,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孩子感冒啊,不舒服啊,太遠了,你也(照顧不到)。”——訪談對象22
3.2 幸福感增強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9)。幸福感是指居民對其生活質量做出的認知和情感的總體性評價。生活質量、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是衡量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標(Moeinaddini et al.,2020)。經濟收入方面,2013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1 668元,收入來源以“務農+打工”為主。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由于村內產業結構優化、各種經濟體繁榮發展,農戶收入結構轉變為“務農+零售業+打零工+合作社分紅”,收入來源多樣化。至2020 年,人均收入達到18 369 元,較2013年漲幅明顯。
十八洞村地處偏遠深山,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封閉、落后,農戶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買、農產品的銷售等均需要前往排碧鄉或麻栗場鎮。由于交通不便,農戶出行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精力,因此解決交通問題是十八洞村農戶最大的心愿,對交通通達性的渴望影響著一代代的十八洞村人。
“沒扶貧之前,中國煙草來村子里讓每家每戶種煙葉,煙草公司就給村里修一條路(機耕道),當時所有人都回來種煙草,外面打工的人都回來種(煙葉)了,就是為了那條路(機耕道),讓大家方便。以前我們種稻子都是從那邊搬過來,都是走的小路,那很遠很遠的。”——訪談對象1
“以前交通非常落后,村民出行全靠兩條腿,經常要走2、3 個小時的山路才能與外界取得聯系……那個時候山路很窄,只能用肩膀(扛)、挑、背……現在從村里到花垣縣和吉首市差不多遠了,吉首市雖說(距離村子)有38 km,但現在不一樣了,有了這個高速,路程基本上都是40 min就能到的。”——訪談對象5
扶貧政策實施后,政府拓寬村道4.8 km,打通了進村公路,并開設了村寨間的直通車、城鄉干道車等交通線路,徹底改變了十八洞村農戶的出行方式和范圍,有效提高了十八洞村寨的可達性,方便農戶與外界的溝通交流。基礎設施的完善和經濟收入的增加,提高了農戶的生活質量,削弱農戶的愁苦、無奈等情感。農戶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洞村首倡精準扶貧政策,給十八洞村帶來了新希望和好生活,如今十八洞村勤勞致富的形象,獨特的民俗文化和紅色教育意義讓農戶倍感自豪,讓生活在十八洞村的農戶幸福感與日俱增。
“就是非常自豪,你看以前村里的人就比較自卑啊,人家說嫁人啊,千萬不要嫁到這里來。特別是這里的男青年,出去的話不敢說是從這里出去的。現在我說是吉首(市)啊,花垣(縣)啊,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我說是十八洞村,很多人都知道了。”——訪談對象22
“以前路沒通的時候,肥料要到排碧去挑回來。那個最讓人惱火啦……因為沒有路,走的都是彎彎曲曲的小路哇……現在條件好了,現在我們村子上光小車(汽車),就有幾十部了,我家里就有2 部……”——訪談對象33
3.3 風險厭惡感下降
風險厭惡來源于經濟學,指投資者對方案風險的態度。引用該概念表達農戶對貧困和經濟決策的態度。雖然現行脫貧標準下貧困人口已經實現脫貧,但多數農戶的生活仍處于生存線的邊緣,基于思維慣性和對貧困的畏懼,他們的行為是不冒險的,會考慮盡量減小最大損失概率(羅婷,2020)。風險厭惡是這些農戶的生存需要,是基于“災難避免”的理性考慮(蔣莉莉,2012)。這種觀念阻礙著脫貧村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
十八洞村山高地陡,耕地零落,難以發展規模農業。2014年,駐村工作隊和村支兩委采取“飛地模式”發展集體經濟,在臨村流轉土地種植優質獼猴桃,成立十八洞村苗漢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倡導村民以產業扶貧資金入股,日后參與集體經濟收益分紅。但是農戶們認為資金跟著干部,如果干部走了,投資就“黃”了。后來由于有黨員的帶頭加入,農戶才將信將疑地投資入股。
貧困農戶因為缺乏認知資源和投資的能力,經常會作出低質量的經濟決策(杭承政等,2017),他們更多地關注眼前利益,投資行為主要跟隨集體決策而非自發意識。扶貧工作隊用“以身試險”和“以身作則”的方法,消解了農戶心中的不安;并用工作成果穩定農戶對投資收益的信心。村委考慮全局,給當初沒有加入合作社的農戶也分發利潤,共享集體經濟收益的果實,激勵農戶的投資行為。投資行為是農戶的理財意識初步覺醒,也反映其脫離“掙扎在生存線邊緣”后的心理狀態。如果沒有政府和黨員行動的引領,農戶很難在短時間內接受這種投資行為。
“一開始本應該是從村民家開始,但是村民不同意,就先從黨員開刀。有時村民會想,別人給十八洞村投資了多少多少錢,但是村民們沒有立刻看到,就會說一些難聽的話。像獼猴桃產業,等人家(駐村工作隊)走后,獼猴桃(合作社)分紅了,村民才意識到,人家(駐村工作隊的做法)可能是對的。”——訪談對象5
“其實我們年輕人都好說話,就是老人家會認為,土地給了人家,就是人家的了,拿不回來了……可是你看,土地種了那么多年,不還是那個樣子,也不能賺好多錢,還不如給上面,讓上面的人去搞。”——訪談對象16
“之前進獼猴桃合作社,要每人拿出100元的租減費,飛蟲寨那邊的人沒交,后面也分錢給他們了,就是分的少,現在他們也后悔了。”
——訪談對象33
3.4 相對剝奪感產生
當個人將其處境與參照群體中的人相比較,發現自己獲取的權益處于相對劣勢后產生的情感即為相對剝奪感。它是一種消極情感,反映人們對現實的不滿情緒,一旦這種情感轉化為行為動力,就可能對社會秩序產生強大的破壞(李平等,2013)。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指與參照群體對比的同期經濟收入)的差異會影響農民的相對剝奪感。
十八洞村由飛蟲村和竹子村合并而成,受地理區位和資源稟賦差異的影響,兩村多年來存在人心不齊的現象。飛蟲村因為靠近國道G209,較早修通連接國道的公路,當時的村部也建在飛蟲村,對于飛蟲村的農戶來說,其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一直高于竹子村。2013年,因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的是十八洞村更深處的竹子村,因此,竹子村成為十八洞村的核心景區,精準扶貧廣場、精準扶貧展覽館、游客接待中心、高端民宿和精品旅游線路等都分布在竹子村中,村部也從飛蟲村遷往竹子村。不僅如此,竹子村維持著整潔統一的村容村貌,尤其是梨子寨的民居群、巷道、基礎設施和周邊環境等都進行風貌的整治,人居環境得到大力改善。但飛蟲村風貌相對較為雜亂,傳統民居中混雜突兀的現代建筑,村貌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大不如竹子村。由于許多政策福利和產業紅利向竹子村傾斜,飛蟲村農戶的相對剝奪感較為強烈,產生怨恨情緒,不利于整個村子的和諧穩定發展。
“那肯定梨子(寨)開發得好啊,開發也就開發那邊(梨子寨去,這里(飛蟲村)沒什么的。有時候旅客們問我們說這里(飛蟲村)是哪里,我們就說,到那邊(梨子寨)去,我們這里(飛蟲村)不是十八洞,我們是十九洞。” ——訪談對象8
“他們那邊(竹子村)一個樣,我們這邊(飛蟲村)一個樣,這邊(飛蟲村)都沒怎么搞,都是一個村,我們會有意見的……像這邊(飛蟲村)以前有村部,都搬到那邊(竹子村)去了。竹子那邊的農家樂和民宿也比飛蟲多,游客都到那邊去了,在我們這里(飛蟲村)停一下就走了,留不住人。”
——訪談對象14
3.5 失落感產生
“社區失落論”的倡導者主張,大規模的城市化加劇社區居民的分化,物欲橫流的社會環境使得人與人之間猜忌懷疑、關系疏離、人情冷漠,導致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逐漸淡化(丁鳳琴,2010)。同樣,這種失落感也出現在脫貧村。
“人們之所以變得冷漠,因為缺乏凝聚力,缺乏使人們團結的力量”(Mike,2003)。十八洞村農戶的凝聚力,一是來源于族群身份的認同。十八洞村是一個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苗族沒有文字,其民族文化通過苗歌和苗語世代相傳。苗歌和苗語不僅是苗族文化的載體,而且也是苗族人民集體情感的載體。苗族人民通過唱苗歌、說苗語,強化族群的文化記憶,找到同族人民的身份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二是來源于村中守望相助的民風。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之前,農業耕種是十八洞村農戶最基本的經濟活動。他們在同一環境下生活,保持相同的生產方式,相似的生活邏輯,必然會發生多方面的、頻繁的互動,最終形成一個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的“熟人社會”。
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后,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增加,以及網絡通訊技術的普及,苗歌和苗語的使用機會被大量壓縮。年輕群體迎合現代生活習慣,民族文化觀念變得淡薄,苗歌、苗語和苗繡這類承載集體記憶的民族文化在十八洞村的苗族農戶中逐漸消亡。民族文化的消解和傳統文化觀念的沒落使得十八洞村農戶失去表達文化認同的能力,從而產生失落感。
“我們會一些簡單的兒歌,平時唱給寶寶聽,像我媽媽(輩份的)老人家會的(苗歌)多,平時在家里做活的時候也會唱……反正到我們這代什么都不會,繡花也不會……我們在孩子面前要說普通話,因為(孩子)學校里要考,和家里人在一起時會說一點(苗語),但是也有許多太土的話不會說了,爺爺奶奶那些老人家還是會說的。”
——訪談對象16
脫貧攻堅期間,十八洞村通過招商引資不斷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市場經濟,農戶的生計以經商或打零工為主,務農為輔。農戶逐漸從傳統的家族或集體中脫離出來,越來越多地依靠市場滿足其勞務需求,以支付勞酬的方式逐步取代傳統的社會協作方式。農戶之間由“血緣”“地緣”互助關系變成“業緣”的競爭關系,在社會交往中更加注重經濟利益,社會關系變得復雜脆弱,從而產生失落感。以往小農社會中互幫互助的民風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不再被需要或被認同,這種民風反而讓一些農戶產生道德綁架的壓力和逃離的想法。
“畢竟你在農村啊,鄰居家里有點什么事,請假也請不了,所以村里有事的話就會很為難……(外)出遠了,你不管人家也不會不計較了,(如果)你住的近,就不可能不去(幫忙)。”
——訪談對象6
“現在讓人家幫忙很難了,還是以前好一些,現在讓人家幫忙都是要開工資的,以前哪里有人要工資。”——訪談對象21
“以前,村中有人蓋房子,全村人都會去他家里,一次就要把房子蓋成……現在的年輕人,眼中只有錢,人情談不上了……現在(有事)都要請人了,(村里人)就算幫你,也只能幫你做個一兩天,他們也要過自己的生活啦。”——訪談對象33
4 脫貧村農戶的情感重構機制
4.1 農戶認知是情感重構的核心力量
復雜系統理論認為系統主體是系統內部的具有自身目的與主動性的、積極的“活的”主體。這種主動性以及它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是系統發展和進化的基本動因(陳述等,2005)。十八洞村農戶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和互動正是其情感重構的主要原因。心理學主張認知是情感的基礎,情感是行為的源泉,當三者協調一致時,有機體才會處于積極的心理狀態(王雁,2002)。在精準扶貧前,未經開發的十八洞村,惡劣的自然條件無法滿足農戶的生存需求,迫使農戶背井離鄉,靠打工維持生計。此時,農戶的認知、情感和行為處于割裂狀態,情感上仍然依戀家鄉,但對現實環境的認知,使他們必須外出謀生,農戶處于消極的心理狀態。如果沒有外界干預,任憑這種消極的心理狀態一直持續,將會導致農戶形成悲觀、頹廢的生活態度;或者有些農戶在外謀得好生活,就會將家人接到身邊滿足團聚的愿望。這兩種結果,都不利于鄉村的繁榮興旺,也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背道而馳。
精準扶貧后,政府部門對村子的各項改革和建設,讓農戶認識到村中現有的資源條件、發展潛力、可獲得收入足夠支撐未來的生活,于是選擇回鄉就業,既滿足團聚的情感需要,也可以維持良好生活。此時,農戶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協調一致,農戶擁有積極的心理狀態。當農戶對所在村落的歸屬感和幸福感等積極情感強化,其擁有的情感能量會發揮正向功能,促使農戶作出正向的反應行為。農戶會努力地去維護現在所處的環境,并盡力維持或者強化目前良好的心理狀態。如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十八洞村農戶逃離村落,政策實施后,農戶組織志愿隊主動投入脫貧村建設;精準扶貧政策實施前,十八洞村農戶排斥扶貧工作,政策實施后,農戶積極捕捉商機拓展收入渠道,如“返鄉”農戶回鄉開農家樂、年輕群體創業發展網紅經濟、留守婦女成立苗繡合作社,盤活村落特有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實現從“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我要致富”的轉變。農戶是村內生產生活的主體,相關政策只有尊重主體的心理需求和行為邏輯,滿足主體的切身利益,才能行之有效。但也應該注意到,農戶的認知水平低,目光不夠長遠,容易受到誤導或者被利益蒙蔽而作出低質量的決策。如在精準扶貧政策下,外部資源短時期內涌入村內,村落物質環境大為改善,農戶通過改變行為方式,促進自身與環境的不斷交互,在資源轉換機制作用下將資源轉換為自身所需,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改善,但卻忽視了傳統民族文化和淳樸民風的傳承,導致承載集體記憶的民族文化逐漸消亡,疏于溝通的鄉鄰關系也日益脆弱,集體認同感降低,產生了失落感。長此以往,苗族文化的活態性、原真性和獨特性的消減將反噬村中旅游業的發展,集體認同感的衰退會導致村中凝聚力下降(麻三山,2009)。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負面影響將使農戶的積極情感消退,消極情感滋生。
4.2 政府行動是情感重構的主導力量
政府通過重構村落人居環境系統,優化產業結構,引入先進的生產、經營和治理理念等方式重塑農戶的地方情感,是農戶情感重構的主導力量。首先,政府通過制定政策和組織編制規劃保障其他主體參與扶貧治理的秩序,如編制《十八洞村2014—2016 年扶貧工作總體規劃》《十八洞村傳統村落保護規劃》等系列文件,以“修舊如舊”“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為理念,保護村落傳統的空間格局和古樸的建筑風貌,全面實施“三通”“五改”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大力改善和優化其人居環境。其次,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積極探索產業扶貧新思路,大力發展特色種養殖業、鄉村旅游業、教育培訓產業、礦泉水產業等,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業態不斷創新,農戶經濟收入不斷增加。再次,政府通過管理培訓和技能培訓,提升村委和黨員管理治理能力,培養農戶特色種養殖專業技能,啟蒙農戶的理財意識,提供多樣化致富及參與村內建設的渠道。最后,政府通過舉辦苗舞、歌詠、苗鼓、小品等文娛活動,豐富農戶的業余生活,滿足農戶對家園的依戀和現代文明生活的向往的雙重情感需求。政府作為精準扶貧工作的主管部門和服務部門,其主導地位不可動搖。但也應該注意到,在施策過程中,如果政府部門難以平衡村組之間的各項權益,便會讓農戶間產生相對剝奪感,不利于脫貧村和諧穩定地步入鄉村振興階段。
4.3 企業行動是農戶情感重構的輔助力量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指出:“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通過多種方式參與扶貧開發”(中國政府網,2011)。打贏脫貧攻堅戰需要動員全黨全社會的力量,社會力量包括各種社會組織、民營企業和個人力量等。其中,民營企業在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下,通過開發資源、投資興業、捐贈救助、智力幫扶等多種方式參與扶貧工作,并且利用自身優勢,發揮市場經濟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提高脫貧村抵御風險的韌性和扶貧工作效率,因此企業行動是推進脫貧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如“步步高”集團與十八洞村合作,投資建設十八洞水廠,采用“資金入股+保底分紅”模式發展自來水產業。作為十八洞村第一個集體經濟,水廠給農戶帶來極大的精神鼓舞。時任十八洞村第一支書石登高感慨道:“不僅改變了村里的經濟狀況,更改善了村里人的精神面貌”。衡陽市投資援建的白芨中草藥種植項目簽約十八洞村,企業提供技術指導,并承諾三年后保底收購,消除農戶的后顧之憂。除此之外,十八洞村還與湖南國強文化有限公司建立合作關系,發展文化產業,村集體以門面租賃方式獲取收益。民營企業通過多種方式入駐十八洞村,為農戶提供就業機會,并通過技能培訓增強農戶的人力資本,給農戶提供參與村中經濟建設的多樣化渠道,調動農戶的積極性。
在上述三類行動中,農戶行動屬于村落系統內部力量,政府和企業行動屬于系統外部力量。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共同構成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的動力機制(圖2)。

圖2 農戶情感重構機制示意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armers'emotion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5 結論與討論
1)精準扶貧政策語境下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主要包括歸屬感、幸福感、風險厭惡感、相對剝奪感和失落感5個維度。其中,歸屬感和幸福感屬于積極情感,風險厭惡感、相對剝奪感、失落感屬于消極情感。它們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2)各項扶貧措施的實施使得脫貧村的物質空間、產業結構、經濟收入、治理服務等得到優化或提升,引發農戶的地方歸屬感上升,幸福感增強和風險厭惡感下降。然而,由于扶貧力度的不均衡,導致部分農戶產生相對剝奪感;傳統文化的消解和社會關系的重構等使部分農戶產生失落感。
3)在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過程中,農戶認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動起主導作用,企業行動發揮輔助作用。政府和企業行動通過重構鄉村地域系統的物質空間、經濟空間和社會空間刺激鄉村地域主體即農戶認知轉變,繼而引發情感的重構。
情感可以激發主體的后續行動,消極情感能夠破壞目標定向行為,而積極情感可以維持目標定向行為(Pranken,2005)。脫貧村為保證脫貧效果,促進和諧發展,并順利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應該注重采取相關措施弱化農戶的消極情感、強化農戶的積極情感,促進農戶情感的正向再生產(劉玉珍,2019)。情感的空間性決定積極情感的產生前提是良好的生活環境,包括美麗宜居的人居環境、和諧的鄰里關系。情感的社會性則為鄉村治理提供新思路,即利用榜樣的積極情感同化感染農戶,使個人積極情感轉變為集體情感;同時通過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留住集體記憶,是消除失落感,增加歸屬感的重要途徑。情感的層次性和時間性意味著農戶的積極情感經過時間磨煉后,可以固化為高級情感,從而阻止消極情感的代際傳遞。這呼吁社會各界力量通過發展農村教育,提升農戶的認知,增強農戶抵御風險的自信心,消除風險厭惡感。政府行動是引導農戶和其他社會力量積極反饋的主導力量,因此政府部門一旦發現農戶的消極情感,應該及時疏導,并調整自身行動。同時,也需要注意到,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銜接階段,農戶的情感需求也出現新層次的變化,如對娛樂生活的需求上升。脫貧村應該組織多種體育類、益智類和文娛類活動,豐富農戶的業余生活,營建活力四射的民風。只有通過提高農戶主人翁的身份認同感,調動其參與村內建設和治理決策的積極性,充分發揮村落系統內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才有可能促進脫貧村向鄉村振興有序躍升。本文通過“地方-情感-行為”分析模式,有助于理解宏觀政策語境下鄉村地域系統重構中農戶情感、行為與社會物質環境的互動過程以及農戶的主體意義,為促進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提供有益的參考。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對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的研究,僅基于十八洞村的個案研究發現,其結論是否普遍適用于不同人地關系系統中的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的解釋,還需要通過后續相關案例研究予以佐證。此外,本研究在構建脫貧村農戶情感重構維度的過程中,取“留守”和“返鄉”兩類農戶的共同點進行分析,尚未對兩類農戶情感重構各自的特點及其差異進行深入的討論;同時,對第三類農戶即外城農戶的情感重構也尚未涉及,這需要在后續研究中進行補充與深化。
致謝: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和建議!